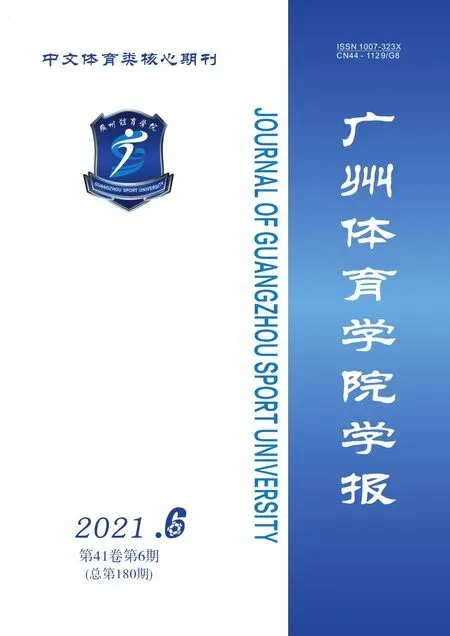古代武舞的起源与演进研究*
陈新平,谭广鑫,李兆伟
(1.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研室,广东 广州 510650;2.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3.广州中医药大学 体育健康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武舞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以武术和舞蹈动作为素材,通过徒手或持械形式,表现一定思想内涵的身体运动。本研究以历史发生发展的顺序,通过对二十四史及其相关研究资料、武术研究历史文献的梳理,对武舞演化历程进行较为详细梳理,期冀为武术史研究添砖加瓦。
1 巫、舞、武——武舞萌芽的杂糅互渗
武舞的产生与原始宗教和战争紧密相连。最初用于军事活动,通过手持武器的舞蹈来祈祝克敌制胜。“这一功能滥觞于龙山文化晚期,形成于夏商时代,随后渐变为敬天祀祖、娱神降神、象征兴亡的重要宗庙舞蹈形式。[1]《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争神,被杀而不屈的神话:“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186这则充满神话气息的记载,更像是描绘一场远古时期执干戚而舞的祭祀仪式。广西左江岩画保存了古骆越人武舞祭祀的场面。岩画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裸体,形似巫师的长者面戴假面具,统领腰佩大刀、短剑等兵器的人群。胡新生在关于中国古代巫术的研究中指出:“巫术与武舞曾经长期保持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时代越久远这种依存关系就表现得越明显。”[3]35
武舞与战争的关联亦有文献为证。《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里的“干戚舞”既是军事操练,又带有武力炫耀,具有“用武力威逼有苗臣服的意思”。[4]135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说:“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惟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事情,它也是对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5]184对此,王岗[6]认为:“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的人群要进行战斗的操练和演习,以便于熟悉用于战斗的那些击刺的动作,于是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
从早期字形和字义来看,“巫”“舞”“武”除字形相似之外,三者之间的释义也存在联系。巫,在甲骨文中作,小篆中作,现代汉语中指巫师、巫术。甲骨文中,“巫”的字形有祭祀时巫师手持道具,祝福祈祷降神之意;舞,甲骨文作,小篆中作,现代汉语中舞指舞蹈、跳舞,作为象形文字,“舞”字有研究者说是舞者双手持流苏一类鞭状物,也有研究者认为是持牛尾而舞,据郭沫若[7]112《殷契粹编》的考证,甲骨文中便有头戴羽毛,手持干戚而舞的祭司;武,在甲骨文作,小篆中作,现代汉语中“武”指武事,与“文”对应。“武”字,字形由“止”和“戈”组成,“戈”是一种武器,“止”代表人的足部,戈下置一足,也说明人持戈移动的状态。武术的基础与跑、跳、投,甚至舞蹈密切相关,舞练作为武事在史籍中常有记载,如《山堂肆考》:“舞者,乐之容,用之于武事,则为武舞”。《说文》中“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的记载则表明,舞蹈在先民看来本身就是连通神灵的巫术活动。由此可见,萌芽时期的武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而是处于巫、舞、武杂糅互渗的混沌状态。
2 制礼作乐——武舞的仪式化嬗变
西周初期,为强化王室权威,周公旦制定出一整套法定的礼乐制度,史称“制礼作乐”。礼乐制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它结束了中原诸侯国混乱复杂的文化,并以周礼、周乐作为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这对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伟大的开端。”[8]西周礼乐制度在沿袭前代内容与风格的基础上,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9]813的宗教意识不同,西周礼乐制度强调的是以乐飨神过程中的等级次序,即所谓的“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周代礼乐制度中,文舞主要颂扬帝王德行,武舞主要歌颂帝王功业。文舞左手执龠、右手执羽,武舞左手执干,右手执戚。乐舞表演时,八人为一列,称为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这种“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佾舞”的礼乐形式被后世称为“雅乐”。与前代相比,西周武舞合乐、舞、歌为一体,不仅具有“事神祈福”的巫祭性质,更是彰显等级社会秩序的王权统治工具,而其军事训练的功能也逐渐褪去,成为一种固化的仪式符号。
西周的礼乐体系主要由“六大乐”和“六小乐”构成。六大乐分别是《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旧唐书》载:“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10]891《大濩》亡佚已久,无从考证。《大武》为周代祭祀先祖之乐,共分六段:“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9]560《大武》的六个段落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第一段舞队北向进,象征武王开始出兵伐纣;第二段象征灭商;第三段象征灭商后向南用兵;第四段象征将南方各国都收入版图;第五段象征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第六段舞者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表示舞蹈已经结束。《大武》的六成之法也被后世沿袭,历代宗庙武舞大多效仿此法。《大武》声势浩大,壮怀激烈,彰显了武王的威力,神化了周的统治。
六小乐主要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包括《祓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其中,《干舞》执盾牌而舞,属于武舞。周代武舞除了两大乐舞体系的《大武》《干舞》外,学界普遍认为还有一种被称为《象舞》的乐舞,其依据是郑玄《诗经·维清》中的一段注解:“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然而,从后世其他学者的注疏来看,《象舞》也可能是指《大武》。孔颖达疏曰:“《维清》诗者,奏象舞之歌乐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为象舞。”马瑞辰通释:“舞、武古通用。象舞,蔡邕《独断》作‘象武’,盖以象文王之成功也。作‘舞’者,通借字耳。”周代制礼作乐确立了武舞在礼乐体系中的地位,文武二舞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乐范式被后世沿袭,成为中国礼乐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3 礼崩乐坏——武舞的雅俗分化
3.1 礼乐的雅俗分化
《礼崩乐坏》最早见于《论语·阳货》:“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1]380此后,“礼崩乐坏”用来形容西周“礼乐”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落寞的局面。从春秋时期的社会形式来看,礼乐崩坏的主要原因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体系逐渐瓦解。春秋时期,奴隶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天子号令诸侯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各地诸侯独霸一方。周桓王以后,诸侯几乎不再朝贡天子,原有的礼乐制度也失去了昔日的约束力,各地诸侯纷纷“僭于礼乐”。如鲁国卿大夫季平子无视礼乐制度,僭用天子八佾乐舞,孔子斥其“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1]41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使得雅乐在乐舞体系中地位大不如前。又因雅乐形式沉闷僵化,逐渐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和艺术感染力。与此同时,俗乐(又称“新乐”)以其灵活新颖的形式逐渐兴盛,并受到社会各阶层青睐。战国时期,魏文候曾谓子夏言:“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9]583-584齐宣王亦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12]59尽管雅乐有着中正肃穆的审美效果,但其严肃刻板的仪式风格终究难以阻挡俗乐的汹涌来袭。周代礼乐体系独兴雅乐的历史就此终结,分化出来俗乐的不断兴盛,呈现出雅俗共存的历史格局。
“雅乐”最先出自《论语·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从孔子的言论来看,“雅乐”是与郑乐(俗乐)相对立的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雅乐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儒家思想的浸染尤为深刻,带有非常浓厚的阴阳五行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雅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领域,基本上垄断了历代宗庙和先祖的祭祀用乐。“俗乐”一词出现较晚。《明集礼》载:“俗乐之名,古未尝有,至齐宣王始有今乐、古乐之辨。”[13]61与雅乐担负祭祀的性质不同,俗乐主要用于日常娱乐欣赏,不属于礼乐范畴。从历史文献的梳理情况来看,“武舞”概念严格来讲属于雅乐范畴。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武舞”的概念外延不断扩大。因此,本文的“雅乐武舞”主要涉及用于祭祀的礼乐舞蹈,“俗乐武舞”是指表演性质的观赏舞蹈。
3.2 雅乐武舞的延续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建立新的政治文化体制。受焚书坑儒之影响,先秦流传的乐舞几乎殆尽,典礼所用前代之乐仅存《大韶》《大武》两部,用于古乐演奏的乐器也大多失传。为了昭示礼乐不相沿袭,秦始皇改《大武》为《五行》。秦始皇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后世效仿,但凡朝代更替,新的统治者大多会改易前代雅乐,歌颂本朝功德。汉代的雅乐武舞基本沿袭秦代礼制,最大的变化在于祭祀先祖时,不同庙号的先祖使用不同的庙乐。“《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14]456“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探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15]2302-2303从后世的评介来看,秦汉时期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雅乐的形制,但无论是内容、乐器种类和对对雅乐的理解,都难与前代同日而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雅乐武舞虽有施行,但受战争影响,雅乐乐器、乐章等古制迭失严重。“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10]896曹魏统一三国后,在吸收汉代礼乐的基础上创制了《昭武舞》《武颂舞》《大武舞》等武舞。“(魏)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舞》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16]446晋代沿袭魏制,并无突破。“……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昭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17]530
与此同时,随着清商乐在魏晋时期的逐渐兴盛,雅乐在宫廷礼乐中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冲击。魏晋两代虽然都做过修复古乐的尝试,但终不及清商乐之影响。“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魏武既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15]2303南北朝时期,雅乐境遇更不如前,北魏雅乐不设舞名,仅以文、武舞相称,其境遇可见一斑。“今聖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15]2319南朝宋、梁两代也有关于武舞的记载,“宋,文舞曰前舞,武舞曰后舞。梁,武舞曰大壮舞,文舞曰大观舞。”[18]935但其形制已较为简陋。
3.3 俗乐武舞的兴起
春秋以降雅乐体系的逐渐崩坏,为俗乐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了对“俗乐乱雅”的不满,“郑音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惊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19]418“古乐衰而新乐盛,正声微而淫声兴者,在当时是一种趋势。”[20]149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的剑舞、戟舞、刀舞等武舞表演风靡一时。一些舞蹈素材经过改造后进入宫廷,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武舞内容,如巴渝舞、剑舞、大面舞等。
巴渝舞本为巴渝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歌舞,后被汉高祖引入宫廷,并令乐工进行习练改造,命名为《巴渝》。《旧唐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描述,“《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汉伐楚,以版楯蠻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10]901巴渝舞以其雄壮武勇的气势,在宫廷音乐中延续千年。虽在隋文帝时期遭遇罢废,但在唐代十部伎中得以重现,可见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历史可谓家喻户晓,说明秦汉之际已有剑舞存在。在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剑舞、戟舞、剑戟对舞、刀舞等内容比比皆是。而项庄舞剑时项伯以袖对舞的场景被创编成舞蹈,称为“公莫舞”“巾舞”,在魏晋南北朝广为流传,唐代燕乐亦有存续。“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涛云:“项庄因舞,剑欲高祖,项伯纡长袖捍其锋,魏、晋传为舞也焉。”[10]900
《大面舞》也是宫廷俗乐武舞的代表。兰陵王高长恭为北齐将领,长相柔美,作战时常佩戴狰狞面具威慑敌人。邙山大捷后,将士为其作《兰陵王入阵曲》。《兰陵王入阵曲》雄浑悲壮、古朴悠扬,隋朝时被列为宫廷乐舞,唐代流行的假面舞,又称“代面”“大面”亦是源自该舞。《旧唐书·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10]910-911在中日交流过程中,大面舞东传日本,在奈良王朝风靡一时,并流传至今。
除此之外,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曾经流行一种模仿战场搏杀、舞姿雄壮的力士舞。《魏书·奚康生传》载:“ 正光二年(公元 512 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踏足,瞋目颔首,为杀搏之势。[15]1368除此之外,汉代盛行的角抵戏《东海黄公》中,也有角力相搏的武舞内容。由此可见,礼乐崩坏虽然造成了雅乐武舞的式微,但却为俗乐武舞的勃兴创造了机会。秦代之后,俗乐武舞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焕发出勃勃生机。
4 雅俗互融——唐代武舞的繁荣
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南北对峙的战争局面。在颜之推等大臣的谏言下,隋朝开展了一场关于雅俗音乐的辩论,史称“开皇乐议”。这场持续13年的争议,虽然没有恢复雅乐盛况,但由此引发的考证修复,扭转了雅乐凋敝的境况。另一方面,隋朝在继承清商乐的同时,兼容并蓄地吸收其他民族和异邦音乐的精髓,为唐代武舞的兴盛夯实了基础。
4.1 雅乐武舞的复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安定的政治环境和富强的经济基础为礼乐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唐代立国之初,礼乐沿袭隋制。李世民登基后功成作乐,贞观二年,祖孝孙等人在继承古代雅乐传统,吸收此前诸朝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大唐雅乐”,扭转了雅乐凋败的颓势。“唐代雅乐乐悬的编制是十分庞大的,非前朝诸代可比。其所用乐器,虽也以古代的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但也加进了一些新兴乐器,其乐悬,已大大超过以往各代。”[21]99
唐代最初制定武舞是在贞观二年(626年),祖孝孙、窦进、张文收等人议定雅乐,创制“十二和之乐”,其中包含了武舞内容。“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孙定乐,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凯安》。”[22]469通过这段记载可知,《凯安》严格按照周代《大武》的“六成之法”之法进行创制,更加符合古制。“《凯安舞》是贞观中所造武舞,準《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興參野,二变象克靖關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獫狁讋伏,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10]890-891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雅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又名《七德舞》。《神功破阵乐》原名《秦王破阵乐》,为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打败叛军刘武周,其将士所作。李世民登基后,制《破阵舞图》,令乐工加以习练,并更名为《七德舞》。《旧唐书》对此进行了记载:“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已,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踴躍,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10]245
《秦王破阵乐》本为俗乐,用于宴飨。“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22]467更名《七德舞》之后,最初用于朝会庆贺,《旧唐书》载:“令儿童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偕奏于庭。”(旧唐书 卷二十八 中华书局 1975 1046)麟德二年,唐高宗正式下诏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即《七德舞》。虽然《七德舞》被修入雅乐,但其用于郊庙文武舞的时间并不长。
仪凤二年(667年),太常少卿韦万石以《庆善乐》不可降神,《破阵乐》不入雅乐为由,奏请更置。鉴于《破阵乐》为先皇所作,唐高宗将其改用于殿庭,武舞复用《凯安》。《破阵乐》之所以被排除在雅乐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表演乐器、舞具皆不合古制。“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龜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和之钟磬,以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自武后称制,毁唐太庙,此礼遂有名而亡实。”[10]891
《破阵乐》表演时“皆雷大鼓”,虽然很有气势,但与雅乐“钟磬”不合。为了将《破阵乐》编入武舞,曾对服饰和乐器等进行削足适履地改造。“麟德二年十月,制曰:‘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阵》之乐,皆被甲执戟,其执纛之人,亦着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并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10]1047-1048虽然做了较大改动,但仍有许多未能融通之处,“其舞犹依旧,迄今不改。”最难磨合之处在于雅乐有着非常严格的礼制,乐舞表演必须遵循“六成之法”,而《破阵乐》很难完美地契合其中。“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10]1049两遍的演奏节次显然不符合雅乐“六成之法”的定法,这也是《破阵乐》被清理出雅乐体系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秦王破阵乐》“由俗到雅”的转变还是打破了雅乐与俗乐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改写了雅乐武舞只用“干戚”的历史,丰富了雅乐武舞的内容,在武舞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4.2 俗乐武舞的兴盛
除雅乐复兴外,俗乐在唐代也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如三大乐、十部伎、坐立部伎、法曲、杂戏等多体裁、多风格的俗乐体系盛况空前,其中也包含丰富的武舞内容;二是武舞形态的多元化,如唐代燕乐分为“健舞”和“软舞”“健舞”动作硬朗、快捷,而“软舞”则安详、舒展。
《秦王破阵乐》与《庆善乐》《上元乐》一起,构成唐初的三大乐。虽然经历了并入雅乐后的弃用,但仍旧盛行于朝会、宴飨等场合。龙朔元年(661年),唐高宗欲伐辽东,鼓舞士气,赞扬其武功,就在屯兵的军营教练兵舞,名为《一戎大定乐》,亦称《大定乐》。《大定乐》气势恢宏,共有舞者一百四十人,皆身披五彩盔甲,手执槊,象征平定辽东而边疆安定。[23]110
唐代燕乐根据舞蹈性质和形态,分为“健舞”和“软舞”。“健舞”动作爽朗、快捷、刚健,“软舞”舒徐、安详、温婉。健舞包含不少武舞内容,如“剑器舞”“黄獐”等,其中《剑器舞》最负盛名。唐代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24]35中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生动形容《剑器舞》的精妙之处,并赞叹:“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史念海[25]258根据“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的序文,推测这种《剑器舞》可能发源于山西、陕西的黄河两侧之地。“根据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记载:‘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看来,《剑器舞》还有多种舞曲,杜甫所见的《剑器浑脱》就是其中的一种。”[23]122-123
5 重文轻武——武舞的式微
唐代以后,武舞逐渐式微。雅乐武舞在礼乐体系中虽然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形式单一、刻板,其影响力逐渐削弱。受重文轻武思想影响,俗乐武舞在宫廷中的发展大不如前,更多地转向民间。北宋虽然统一了长江南北,却仍不断面临辽、金、西夏等国的侵扰,终宋一代并无宁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的危机唤醒了宋儒们“尊王攘夷”的忧患意识,在批判唐代夷狄之风的同时,强调“华夏为尊”。正如葛兆光所言:“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就得想方设法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文化自身的合理性。”[26]260
这一时期的雅乐呈现出强烈的复古情结,然而在追求“雅正之音”的过程中,忽略艺术性、审美性的雅乐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工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改《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其后又创制了《天下大定之舞》《降真观德之舞》《威加海内之舞》等武舞。其中,淳化二年(991年)创制的《威加海内之舞》,汇集了建国以来的武功大业,“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27]2395武舞颂扬功业的政治意味在宋代得以强化,但艺术性却衰减弱化,谏官就曾表达过“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27]2430-2431的质疑。此外,宋代明确了“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27]2394的演奏次序,并为后世所遵从。
元代虽沿袭旧制,但重视程度远不及宋,郊祀武舞为《定功之舞》,宗庙武舞为《内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灭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诏,六成臣高丽、服交趾。”[28]1319元代武舞虽沿袭古制,但所用器具的制式有所不同,“戚六十有四,制若剑然。”[28]1327明代创制了《平定天下之舞》和《武功之舞》等武舞,在宗庙、郊祀、宴饗之时使用。《平定天下之舞》彰显了开疆辟土的武功谋略,“拔剑起淮土,策马定寰区。王气开天统,宝曆应乾符。武略文谟,龙虎风云创业初。将军星绕弁,勇士月弯弧。选骑平南楚,结阵下东吴。跨蜀驱胡,万里山河壮帝居。”[29]1200明代雅乐武舞虽有复兴,但颓废之势已积重难返。清代祭天、祭祖先沿用入关前的萨满教“堂子祭”,武舞规制从简,在雅乐体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弱化。清代后期,“惟先师庙祇文舞六佾”,只在祭祀孔子时使用雅乐文舞,雅乐武舞的历史就此终结。
俗乐武舞在重文轻武思想影响下发展同样受到限制。“宋人尚文,武舞因此减少,娱乐的美术舞极盛。”[20]149元代立里甲为制,禁汉人田猎、习武,民间武舞逐渐走向与戏剧相融合的发展道路。元代戏曲专有“朴刀赶棒”之类,其中不乏武舞表演的形式。明代武舞也沿袭了戏曲表演的发展道路,武生成为戏曲表演的重要角色。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曾创制扬烈舞、庆隆舞等用于宴乐的表演性武舞。对此,《清史稿》乐志八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扬烈舞,用戴面具三十二人,衣黄画布者半,衣黑羊皮者半。跳跃倒掷,象异兽。骑禺马者八人,介胄弓矢,分两翼上,北面一叩,兴,周旋驰逐,象八旗。一兽受矢,群兽慑伏,象武成。”关于“庆隆舞”,清人姚元在其所著《竹叶亭杂记》中描述:“庆隆舞,每岁除夕用之,以竹作马头,马尾彩缯饰之,如戏中假马者。一人踩高跷骑假马,一人涂面、身着黑皮作野兽状,奋力跳跃,高跷者弯弓射。旁有持红油簸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跷者逐此兽而射之,兽应弦毙,人谓之‘射妈狐之’。此象功之舞也。”[30]482
6 结语
武舞发端于史前干戚之舞,其起源与原始宗教和战争紧密相连。萌芽时期的武舞并非独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巫、武、武杂糅互渗的混沌状态。经过周代初期的制礼作乐,武舞从混沌状态中脱颖而出,演绎为彰显统治阶级地位的固化仪式符号。朱干玉戚、六成之法、八佾而舞的规制贯穿于武舞发展之始终,与文舞相结合的雅乐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鲜明表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随着雅俗分化格局的逐步呈现,雅乐武舞的地位渐为弱化。秦汉两代雅乐武舞虽存形制却不传真义,无论是乐章节次、乐工数量、乐器种类,都难与前代同日而语,而俗乐武舞的艺术形态不断丰富,剑舞、戟舞等俗乐武舞方兴未艾。魏晋南北朝时期,雅乐武舞所用乐器、技法等古制迭失严重,以巴渝舞、大面舞为代表的俗乐武舞开始广为流传。礼乐崩坏虽然造成了雅乐武舞的式微,但却释放了俗乐武舞勃兴的空间。
唐代武舞呈现雅俗互融之格局,以《秦王破阵乐》为代表的俗乐武舞融入雅乐体系,改写了雅乐武舞只用“干戚”的历史,打破了雅俗武舞此前泾渭分明的历史界限,扭转了雅乐武舞凋敝的境况。与此同时,隋唐时期的俗乐武舞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音乐精髓,以《剑器舞》《黄獐》为代表的俗乐武舞盛极一时,武舞发展达到雅俗共兴的历史新高度。唐代以后,武舞发展逐渐式微。雅乐武舞在礼乐体系中虽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形式刻板单一等原因,凋敝之势积重难返。宋代雅乐武舞呈现强烈的复古情节,艺术性、审美性逐渐弱化,颂扬功业的政治意味不断强化。元明时期,雅乐武舞的表演形式愈加僵化,成为彰显统治阶层武功韬略的文化工具。清代祭天祭祖沿用入关前习俗,雅乐武舞规制从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俗乐武舞在“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下,走向了与戏剧融合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武舞最初的巫术色彩和练兵功效早已消减蜕化,雅乐武舞的历史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也画上了休止符,俗乐武舞则以戏曲、舞台剧等更具活力的形式不断传承,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