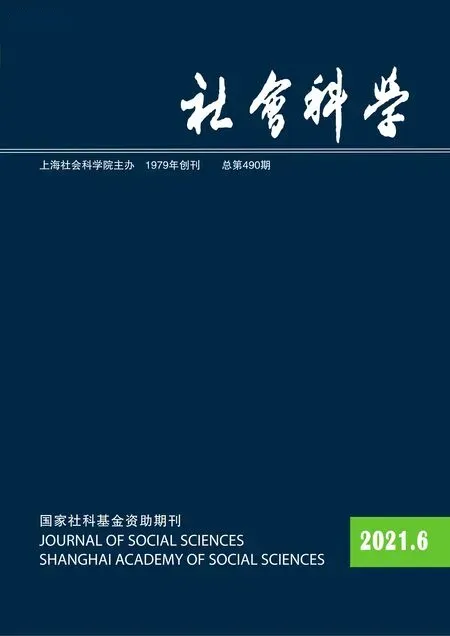线上情感劳动: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男性气质
——基于快手的数字民族志研究
吕 鹏
一、导 语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用情境(situation)融合的观点,(1)[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麽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发展了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台、后台的场合(occasion)理论,(2)[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他所论述的是基于电视等电子媒介对于社会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正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了拟态环境(3)[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会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民众一样,互联网、移动传播、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使虚拟世界已经成为人类真实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科技与媒介不但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作为人的定义都可能被更改。(4)[荷]朗伯·鲁亚科斯、瑞尼·凡·伊斯特:《人机共生:当爱情、生活和战争都自动化了,人类该如何自处》,粟志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澳]理查德·沃特森:《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赵静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这个角度而言,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理论现在看来也稀松平常。情境是制度/机构的一种,当一种情境是转瞬即逝,是偶尔出现,还是如影随形不离不弃,显然起到的作用对包括本文所要研究的线上情感劳动在内的诸事是不一样的。
早在本世纪初,席勒(Dan Schiller)就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两个增长极,一个是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一个是快速崛起的中国。(6)Dan Schiller,“Poles of Market Growth?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Information,and the World Economy”,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iton,Vol.1,No.1,2005,pp.79-103.当下中国,正处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集合性、国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逐渐衰退,而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个体性、商业性的社交媒体平台逐渐崛起的时代——这也是对全球化的平台资本主义(7)Dijck,José van,Thomas Poell,and Martijn de Waal,The Platform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Nick Srnicek,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7.趋势的呼应。这些以智能设备为依托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媒介的转型,是情境的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转型之中,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便是劳动及其形式的变化。无怪乎学者们吁请传播学回归劳动研究。(8)[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聚焦于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直播平台中的(数字)劳动——情感劳动,我们把它命名为线上/在线情感劳动,以区别于非在线/线下的,如护士、空姐以及柜姐等的情感劳动。在与经典的情感劳动研究对话的基础上,本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究数字智能时代情感劳动是否有新变化和新特征;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情境和实践,探讨情感劳动是否有不同,二目的又缠绕在一起,不可分离。文章在综述劳动及其变化的基础之上,主要以极有数字智能时代中国特色的短视频/直播App快手为例,分析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主播是如何进行情感劳动的?有何性别和阶级的转变?其收益来自何处以及其劳动的本质是什么?
鉴于研究对象和其服务的对象及其背后的平台都处于虚拟网络世界这一文化情境(context)(9)Christine Hine,Virtual Ethnography,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9,pp.15-27.和生活现实之中,本文主要通过数字民族志(10)数字民族志有众多不同的称呼,包括虚拟民族志、网络民族志、针对网络的民族志等,它们之间有差别,但更多的是同一性的东西,本文以数字民族志统称这一针对数字虚拟在线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参见[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曹晋、孔宇、徐璐:《互联网民族志: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2期;Christine Hine,Virtual Ethnography,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Christine Hine,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Embedded,Embodied and Everyday,London:Bloomsbury,2015;Tom Boellstorff,Bonnie Nardi,Celia Pearce,T.L.Taylor,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A handbook of Metho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进行研究。田野的对象为快手中的主播。快手作为当下展现中国底层社会生活在场域上的重要性,以及(数字)民族志重要田野点的特别性,如何肯定似乎都不为过,甚至有学者先锋地提出“快手民族志”(11)赵旭东:《视频直播的民族志书写——一种信息传输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转型人类学》,《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的概念。快手的前身为“GIF快手”,是一款诞生于2011年3月用来制作和分享GIF图片的手机应用,2012年11月该应用从纯粹的工具应用转型为一个短视频社区,2年后更名为快手,并在2015年6月突破1亿用户。(12)快手:《关于快手》,https://www.kuaishou.com/about/,2020-08-06。这是一款主要面向中国三四线或更小城市、农村乡镇以及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的一款短视频/直播应用。笔者是从2015年7月开始使用快手,至2020年8月,一共对快手进行了5年时间的使用和观察。从最先开始选取到当年年底陆续关注了粉丝数前一百位的主播,到后面不断地进行主播的观察和关注,至2020年8月,笔者共关注主播889人,含括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主播,基本上每天都保证了2个小时以上的App使用,并在五年间访谈了70余位各类主播。
在笔者五年多的使用和观察中,快手发生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转变。第一次重大的转变是由一款以短视频为主、直播为辅的应用,转变为短视频和直播分量相当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快手的商业化一直表现得不甚明显——直到笔者进行观察的第二次重大转变之前,快手有限可见的收入,如其他众多直播平台一样,(13)Xiaoxing Zhang,Yu Xiang and Lei Hao,“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Ha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3,2019,pp.340-355.主要是来自主播礼物打赏的提成。第二次重大的转变是以快手较大的商业化变化为特征的,表现在除了礼物打赏提成外,快手开始接受广告的投放、引入主播间的PK以及允许主播进行商品的售卖等。快手营利模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快手主播获取收益的方式的变化。文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打赏获取收益为主的线上情感劳动。
二、劳动的变迁:从劳动到线上情感劳动
为更好地研究线上情感劳动及其与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关系,有必要简要分析回顾下劳动与媒介发展的关系。历时地看,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与工业时代相配,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与后工业社会相伴而生,而信息社会则是以互联网等的发展为标志,如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得出媒介不同发展阶段也代表着相应时代和社会劳动的不同形式和转变。即,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占据主流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性劳动(14)[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选》,载[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8-975页。占据社会主导的时代,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社会主导媒介的时代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奈格里(Antonio Negri)非物质劳动(15)[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主的时代,而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作为非物质/非生产性劳动的一种数字劳动则成为主流。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是媒介不断发展的社会,也是媒介及其技术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现实的一部分的社会,同时社会民众的从业劳动由生产性/物质性劳动越来越向非生产性/非物质性劳动转变的社会。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媒介及其技术越发达,则非生产/非物质性劳动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二者呈正向关系——虽然生产性的劳动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见,劳动的变迁和媒介的变迁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工业时代是劳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的发展的话,那么当科技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种生产力(16)[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载[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7页;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6页。的信息/智能时代,反倒是媒介科技的发展使劳动的重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因而才有学者指出“劳动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不一样的”。(17)[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生产性劳动,是因为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性劳动是最为重要的劳动形式;正如奈格里关注非物质性劳动,是因为在后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或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1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东旭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非物质性劳动是社会主流的劳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具有历史特定性,而不是超历史的”。(19)[加]莫依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认为,服务业的增长,意味着“沟通”和“日常接触”将成为如今的核心工作关系。(20)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Basic Books,1973.而在以服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中,情感劳动的重要性被不断地凸显。(21)Cameron Lynne Macdonald,Carmen Sirianni (eds.),Working in the Service Socie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6.
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这一概念,是美国情感社会学领域重要的学者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于1983年在其出版的著作《心灵的整饬:人类情感的商业化》(TheManagedHeart:CommercializationofHumanFeeling)中提出的。她认为情感劳动需要一个人“表现或压抑自己的感受以支撑其外表,从而与他人的心态相适宜”;在此过程中,“这种劳动可能让劳动者与自我的某一方面——既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灵的某一层面——相疏离或异化”。(22)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7.该书已有中文翻译版,参见[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1页。引用部分为本文作者翻译。2004年艾哈迈德(Sara Ahmed)提出感受/情动经济(Affective Economies)概念后,情感(emotion)之于工作的重要性更加为学者们所关注。艾哈迈德发展了霍克希尔德几乎都是偏向“正面”的情感劳动,她认为包括“恨”在内的负面的情感,也是感受/情动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情感劳动的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步入21世纪以来,数字劳动的重要性不断突显,主要在服务业等这样的非物质劳动中被论述的情感劳动,也逐渐被引入数字劳动之中被研究。由此,我们把情感劳动进行了区分,分为线下的情感劳动,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感劳动,本文把后者定义为线上情感劳动。这一概念源自情感劳动,但因数字媒介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所带来的新气象,与线下情感劳动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征。
数字劳动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化生存(23)[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的信息/智能时代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突显的。虽然作为理论的数字劳动是2000年代末期才逐渐被提出和流行的,但其实践是伴随着互联网(24)Trebor Scholz (ed.),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2013.出现和发展而早已存在,并随着数字信息科技在社会中越来越重要而越来越凸显其地位。可以认为数字劳动是非生产劳动/非物质劳动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形式,数字劳动研究在国际上可谓最负盛名的福克斯(Chiristian Fuchs)认为数字劳动是与数字媒介的生产与消费相关的文化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借鉴了威廉斯(Raymods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25)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的观点后,他认为数字劳动可能既包括生产和使用数字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包括创造信息的劳动。(26)Christian Fuchs,Marisol Sandoval,“Digital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A Framework for Critically Theorising and Analysing Digital Labour”,TripleC:Capitalism,Communication & Critique,Vol.12,No.2,2014,pp.486-563.因而数字劳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分类,它包含生产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中的所有活动,前提是它是对数字工作(digital work)的异化。(27)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4,p.351.这也是为什么邱林川会把富士康工人的劳动也定义为数字劳动的缘故。(28)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4期;Jack Linchuan Qiu,Goodbye i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6.不过中(29)姚建华、徐偲骕:《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化的劳动:数位劳动研究的内涵、现状与未来》,《新闻学研究》2019年第4期。外(30)Trebor Scholz (ed.),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2013.都不乏学者对福克斯的观点不以为然。
虽然数字劳动的概念似乎宽泛而不容易把握,但如果将其放置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进行理解,就会发现脉络的一致性和清晰性。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一是数字劳动一定是与媒介信息技术有关,二是数字劳动与阶级、异化,也即资本的剥削有关。所谓线上情感劳动,是指在线通过媒介技术进行情感劳动,它是情感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数字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当今主流的对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普遍认为其是免费的,即无酬劳的;(31)Tiziana Terranova,“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2000,Vol.18,No.2,pp.33-58;Armin Beverungen,Steffen Böhm,Chris Land,“Free Labour,Social Media,Management:Challenging Marxist Organization Studies”,Organization Studies,Vol.36,No.4,2015,pp.473-489.而以服务业为主的(线下)情感劳动则显然是有酬的。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则达6.17亿。(3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02-03,第50、52页。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2021-03-10。而在2019年快手就宣布其日活用户(DAU)已经超过2亿;2018年,在中国有超过1600万人从快手平台获得了收入。(33)花子健:《快手宣布日活破2亿 1600万人在平台获得收入》,凤凰科技网,2019-05-29。http://tech.ifeng.com/c/7n4FTNFashE,2019-08-15。直观的数据说明的是,无论对于中国的短视频/直播平台,还是对于短视频/直播平台的领头羊之一的快手而言,都有极其巨大的人群在从事着线上情感劳动的工作。观察快手上的线上情感劳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线上情感劳动目的的明确性,即获得收益。与不自觉地被资本平台当成获利的工具,比如微博、百度百科以及知乎等平台绝大部分的用户进行“信息”的生产是出于乐趣或权威感的获得的需要不同,也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学者把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解读成一种受众劳动(34)Dallas W.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No.3,1977,pp.1-27.这种更加隐藏并伴有是否是劳动的争议性的劳动不同,绝大部分进驻快手的主播都有明确地想要通过快手获得劳动的收益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明确性,表现在众多的主播汲汲于想要当“网红”。在我们的访谈中,当“网红”或者对于成为“网红”之后经济收入的寻求,是快手主播们进行数字劳动最为直接的动力,主播们几乎都丝毫不掩饰对这种目的的表露。这至少说明了在快手的主播的朴素认知中,劳动是要与实际的收益相挂钩的。无酬的劳动,或者自愿的无酬劳动是否应该被定义为一种“劳动”,则是有待商榷的。
其次是线上情感劳动的收益的不确定性。雇佣劳动是线下情感劳动获得收益的保障,这种收益以工资形式得以确认。而非雇佣的线下情感劳动,其进行的情感劳动的收益是不能被保障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主播也自称为“要饭的”的缘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自己非雇佣劳动过程中线上情感劳动收益的不确定、不被保障,甚至有一些污名化以及社会与自我的不认同看作与“乞讨”相当。同时,网络主播在访谈中,也策略性地表达了对线上情感劳动收入不稳定的清醒认知,认为短视频/直播就是“玩玩”“养活不了自己”。
第三是线上情感劳动主体——主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有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形式。所谓自愿是指主播们因为各种原因发觉在平台的情感劳动并不足以支撑其个人的存活,因而放弃平台。这也说明了主播是一个远未达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职业”,更多的人把在线情感劳动视为一种过渡,并不抱着持续地从事的态度,用主播的话来说就是“打兔子当捎带”。而非自愿的流动性,多数表现为主播账号被禁或被销(号),从而在制度/机构层面上被动地被阻止从事线上情感劳动。因为主播的进入门槛低——无论是知识储备、专业技能抑或是资格审查等几乎都不存在,也造成了主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人群整体状况。快手作为短视频/直播平台有大量的“监管人员”来处理违反平台规定的主播;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作为最高层面的治理者,也可能象征与示范性地对主播进行意识形态和法制治理意义上的社会治理,主播“MC天佑”就是例证。除了这种永久性的被禁止在平台上从事线上情感劳动外,也有禁播不同天数等的惩罚措施,以部分时长中断主播的线上情感劳动,从而实现对主播的规制。
三、线上情感劳动的实践:表演与“话术”
按已有的研究来看,线下情感劳动有两种基本的特征,其一是有一定基本或标准的社会形式。“如欲管理私人的爱和恨,就得参与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私人情感体系之中。当这一体系的要素被拿到市场上作为人类劳动出售时,它们就被塑造成标准化的社会形式。”(35)[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8页。
其二是,线下的情感劳动并不是真情实感的介入,具有疏离感,并排斥情感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服务与被服务对象对此都有基本的认知。“在此类形式中,个人对情感的贡献变得稀薄,后果也无关紧要;但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似乎不像是源于自我,也不像是指向他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种情感更易于让人产生疏离之感。”(36)[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8页。
与线下各种服务或实体业的情感劳动不同,短视频/直播中的情感劳动并无标准化的社会形式。将短视频/直播视为一项工作的主播会考虑其情感劳动的投入成本与其收益之间的多大程度上是等价并有盈余,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播的心理期待值所决定的,而并不是如线下情感劳动一样,有成体系的规范和要求。与此同时,快手的主播们并不排斥情感的介入,也很少会考虑基于职业道德而产生的服务与被服务对象的疏离关系,而是不断地形塑、打造、强化以及延续这种情感的纽带和联系,以达成“劳动”的目的——报酬。于是,与线下情感劳动的标准形式不同,线上短视频/直播的情感劳动更多地被称为“套路”,是利用社会中各种现实的朋友、家人、爱人等情感关系而在虚拟世界中打造虚拟的情感关系,并将这种情感关系极力地往更加亲密的程度上引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关系”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播的可以榨取收益的多少。
而在这些关系的塑造中,朋友、家人和爱人间的情感是主播们最常借用的资源。于是,老铁、家人和臭妹妹/弟弟就成了短视频/直播中最常使用的关系语言符号。在快手中,“老铁”是最先开始流行并成功“出圈”的词汇。连带着,在快手中常常听见的“老铁没毛病”“老铁扎心了”“老铁666”等也有了一定的社会流行度。“老铁”,是为我国东北方言中对铁哥们的称呼,在方言中更惯常的说法是“铁子”,更多用于世俗且底层的民众生活中。早期快手主播人群中聚集了大量的东北人,“老铁”被引进快手的短视频/直播之中,成为界定主播和粉丝之间关系的用语。“老铁”既是对一般的观看短视频/直播的网友“礼貌性”和常规性称呼,也是将虚拟生活现实生活化的称呼,还是直播平台主播和粉丝之间的底层特色凸显化的称呼,更是拉进粉丝和主播之间关系的策略性话术运用的称呼。访谈中,很多东北地区以外的主播并不了解“老铁”的具体内涵,但并不妨碍他们利用快手已有的直播环境中对该词的理解和学习来建构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而家人则是进一步的发展,是用来指代专门“粉”某一个主播的一群人。如果说“老铁”是策略性的对粉丝个体化的称呼,那么“家人”则是对粉丝集体的话术运用。主播借用家庭关系将主播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符号化,粉丝们成为大家庭中的成员,而主播则是粉丝的兄弟姐妹中的一员。于是,与世俗间家人之间的互助关系一般,主播的短视频/直播家人们就有“义务”进行分享和点击,而当主播进行直播PK,又没有“大哥”在线的话,家人们就有“众筹”守护主播的义务。这里的“大哥”,特指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喜欢主播的人,某些平台将这些人称为“金主”。在快手中,这些金主也被家庭关系化,成为守护主播的大哥——一如现实中国家庭关系中“长兄如父”,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在笔者的访谈中,“大哥”是网络主播们最看重和喜欢的粉丝,主播们甚至会利用下播后的时间来维系和“大哥”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在线的聊天的方式,从而保证打赏的持续性和“大哥”对自己的维护。
前面两种关系化的称谓是男女主播所共用的,而臭弟弟/妹妹这一类关系,则有男女主播的分别。所谓臭弟弟/妹妹并不是家人的关系,这一带有调侃的“臭”是两性情爱关系的表现,所以臭弟弟/妹妹是把主播与粉丝的关系情爱化。有时候这种称谓也省去“臭”字,男主播大多时候也称其粉丝为“妹妹”,或“小姐姐”;女主播称“弟弟”或“小哥哥”。这种称呼,也与老铁和家人的称呼不同,带有调侃、暧昧以及调情的意味,因此绝对的大主播不太会使用这样的关系言语,而中小以及以性感和外貌为主要“卖点”的主播则会常规性的使用这一关系称呼。
由这些带有极强符号化的称呼中,至少可以想象主播在进行线上情感劳动时的表演技巧和话术使用。虽然随着短视频/直播的发展,主播们对自己也有相对明确的归类,比如自我认知为情感主播、颜值主播或才艺主播等,但无论哪一种主播,其在短视频/直播中进行情感劳动时,都是用着一套话语系统进行表演,从而获取粉丝的打赏。对于线上情感劳动而言,表演中最重要的手段是语言,这是主播与粉丝之间沟通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于是对于主播而言,其语言的表达是否流畅和“话术”采用是否高级,是其线上情感劳动能否获得收益的关键。而基于朋友、家人和恋人的符号关系的话术采用,也决定了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者情感的深入介入。在这种情况之下,主播的私人情感和生活也成为线上情感劳动的表演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察已经正确地发现了表演在情感劳动中的重要性。线上情感劳动的“表演”,可能与戈夫曼所谓的“表演”以及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称的“表演”在具体所指以及意义上有差异,但这些表演所共通的东西都是指社会及文化对于情感上能够产生影响的语言、姿态、表情等的共识性规定。
“舞台演员将情感的发现和表达,作为自己主要的专业任务。”(37)[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8页。舞台或剧场中的演员,处于戈夫曼所谓的前台之中,其知晓其表演为其工作,并且其工作是和其生活与本人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才会有前台和后台的区别。而对于线下的情感劳动而言,则需要努力地使被服务者相信自己的表演的真实;但被服务对象很大程度上也明了,这是情感劳动所表现出来的表演,其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是可疑的,但在付费“协议”的框架之内,被服务对象则在规则之内需要享受这种表演,而不管这种表演是否发自内心和是否真诚,对于被服务对象而言,享受应该享有的情感劳动的表演,则是更加重要的。
然而线上情感劳动则不同。对于短视频和直播中的主播而言,他们显然也知晓其“工作”的绝大部分是进行表演,然而这种表演是消弭了前台和后台之间的关系,生活与表演是融合在一起,因此身份是合一的。在此情境之下,所有的主播都是极力地使观众/粉丝们相信,表演的主播和生活中的人是同一个人。因此对于主播来说,重要的不是表演或者扮演一个人,而是管理或者塑造一个“人设”,在“人设”的支撑之下,来进行表演。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主播的“表演”既是其收益的需要也是粉丝/观众心理的期待。主播与受众/粉丝,也即服务者和被服务作者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舞台上的表演者和观众,也不同于线下情感劳动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他们之间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不但前后台的关系消弭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心知肚明的“协议”关系也消弭了。于是,对于进行线上情感劳动的主播而言,让受众相信其“表演”与其真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契合度和真实性的大小以及真诚的程度,基本上决定了主播获得收益/打赏的多少。
对于舞台的表演者而言,其私人生活和其所从事的工作几乎是不相关而分离的;而对于线下的情感劳动而言,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理论上以及理想状态是分离的,也绝大部分是分离的,但因为是服务与被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接触的关系,因而虽然在职业关系之中,却也难免会有私人生活些微地渗透入公共生活之中。而对于线上情感劳动而言,则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则完全是融合的,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在其形式上,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在主播的表演和情感劳动的付出和受众对于主播的心理和情感期待认知上。舞台的表演、线下的情感劳动的表演以及线上主播的表演,实际上都是有着共同的目的,即进行报酬的获取,然而这种报酬获取过程中,私人生活、个人真实情感作为资源被调用的程度则是截然不同的。
伴随着线上情感劳动的是个人人格以及私人生活的商品化,线下情感劳动大抵会存在私人人格的商品化,(38)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Lond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82-188.但几乎不伴有私人生活的商品化,而线上情感劳动需要不断地用主播自己的私人生活以进行“表演”、展示(39)Bernie Hog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eity,Vol.6,No.30,2010,pp.377-386;Rob Cover,“Performing and Undoing Identity Online:Soical Networking,Identity Theories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Online Profiles and Friendship Regimes”.Co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ida Technologies,Vol.2,No.18,2012,pp.177-193.和话语策略的实施。大多数主播是真实的对个人从学历到家庭到情感状态到收入等等的自我叙述过程中完成“人设”,这种一定要看起来和听起来真实、真诚的“人设”就成为主播与粉丝——老铁、家人、臭弟弟/妹妹——进行情感沟通的桥梁,从而达到收割受众并将其情感劳动转化为获益的商品进行售卖的最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主播的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实际上已经遵从商业的逻辑,这种商业逻辑从微观处着眼是快手所营造的短视频/直播的共享文化对于主播的情感和个人生活中可供售卖的部分的提取,从宏观处着眼是科技发展之后,媒介成为人们真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之后,对于整个社会心态、生活的商业形塑。
主播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人格和生活作为线上情感劳动的一部分进行贩卖并甘之如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播认识到社交媒体平台和社会都在不断地鼓励和诱导他们进行这种操作,并从这个操作中获得以经济收益为主的褒奖。
在这一劳动过程之中,主播的个人人格实际上是被主播自己所征用的。只是与线下的情感劳动的征用有可能是无奈的或被动的不同,主播对自己人格的征用是主动并积极的,虽然中间可能也如线下情感劳动一样,有着挣扎和痛苦。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播而言,对于自己人格的征用的过程中,自我的表演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而线上情感劳动越接近真实自我,就越有可能获得“人设”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话术之于表演如此重要,而表演之于线上情感劳动如此重要的原因。言说是线上情感劳动最重要的武器。
四、线上情感劳动的转变:底层参与和男性主导
霍克希尔德指出,“在人类情感的日常和商业用途中,既存在着性别模式,也存在着阶层模式。”(40)[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7页。情感劳动的性别模式,尤其与女性的关系,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和研究。(41)Rebecca J.Erickson,C.Ritter,“Emotional Labor,Burnout,and Inauthenticity:Does Gender Matter?”,Social Psychology Quartely,Vol.64,No.2,2001,pp.146-163;Elaine J.Hall,“Smiling,deferring,and Flirting:Doing Gedner by Giving ‘Good Service’”,Work and Occupations,Vol.20,No.4,1993,pp.452-471;Robin Leidner,“Selling Hamburgers and Selling Insurance:Gender,Work,and Identity in Interactive Service Jobs”,Gender & Society,Vol.5,No.2,1991,pp.154-177.这是因为情感劳动研究“对女性具有特殊的相关性,也可能更多地描述了她们的体验。作为传统上私人生活里更为能干的情感管理者,女性比男性投放更多的情感劳动在市场上,因此她们也更加清楚需要付出的个人代价”(42)[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6页。。相关研究大体上都揭示了在情感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状态,即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这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使得女性更多从事需要情感劳动的职业;第二是即便是相同的工作职业,女性也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
而在短视频/直播这种线上情感劳动中,主播的相貌、人格、社交技巧乃至生理缺陷等都会成为用来赚钱的资本,因此在这种情境之中,男女之间在线下情感劳动中的差别就最大程度上被弥合了。漂亮、性感、美丽这些之前主要被赋予女性性别优势的外部特征,在短视频/直播中现在也同等或者更加明显地被男性所强调。于是,打光、开设美颜几乎都是所有主播的常规操作,而进阶的男主播开始化妆,以至于整容——笔者的观察对象中整容以文眉和割双眼皮最为常见,偶有隆鼻和打瘦脸针之类的。
男主播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外貌,这是因为在短视频/直播的声画世界中,形象的重要性无以复加,它决定了是否能够开始吸引受众的眼光,从而进行下一步的把主播的情感作为资源进行劳动从而获得收益。美丽的、漂亮的、性感的外貌是如此,与之相反的,丑陋的也是相似的道理,通过反面的审丑效应,达到吸引人的效果,从而达到通过情感劳动获得收益的目的。虽然对于短视频/直播而言,两者都存在,但前者是更加普遍的。在访谈中,当谈到外貌问题的时候,很多主播直接说出“谁还不喜欢好看的”“长得好就是有优势”等话语。并且当被询问是否化妆以及是否可以接受整容等,绝大部分的主播都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并且男主播尤其是年轻的男主播,对于画眉毛这样的化妆,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和心理上的负担。
如果说朱迪斯·巴特勒所谓的表演作为一种对性别的社会要求,更多地作用和压迫女性的话,(43)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那么在短视频/直播中男性对于性别的展演和对于情感劳动的付出,则具有极深的矛盾性的中和。一方面他们需要不断对外貌凸显和性感等的强调强化女性对于男性的“凝视”,(44)朱晓兰:《文化研究关键词:凝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这一过程中,帅气的脸、八块腹肌、公狗腰、麒麟臂、大长腿,以及翘臀等都是男性进行自我展示的重要资本;而另外一方面男性却用通过不断的话语策略,进行情感劳动,强化男性对于女性的征服、勾引和诱惑,(45)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通过性感为标签的男主播,很有可能吸引到的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主要粉丝群体是男性而非女性,有些男主播对于男性的以同性恋为主的粉丝持厌恶和反对的态度,有的则比较暧昧,既不表达厌恶也不表达喜欢,也不乏很多男性是利用这种现实进行专门针对男性市场的进行收益的获取。本文不关注这一群体和这种现象,因此主要在异性恋话语中展开讨论。这又完美契合了父权制中男女两性性别气质的要求,即男性处于主动征服的地位,而女性则处于被征服的境地。而后者既是技巧、是策略,更是社会的规训。(4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此过程中,男性以十分矛盾的状态从事着线上情感劳动,一方面他们要不断地打破原有的男性形象和男性气质的认知,以商业和社交媒体对男性的身体形象和美进行自我包装和塑造(47)Grace Holland and Marika Tiggemann,“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Body Images and Disordered Eating Outcomes”,Body Image,Vol.17,No.16,pp.100-110;Joanna Elfving-Hwang,“Cosmetic Surgery and Embodying the Moral Self in South Korean Popular Makeover Culture”,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1,No.24,2013,pp.1-18.以作为线上情感劳动的基础,这种通过带有强烈的性意涵的外表和身体来获取资本的方式,有可能对男性造成极大的压力,(48)[美]哈里森·波普、凯萨琳·菲利普:《男性的美丽与哀愁:“猛男情结”剖析》,但唐谟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并对男性而言是一种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则需要不断地进行公众认知中对于霸权男性气质的要求进行操演,(49)Raine Dozier,“Beards,Breasts,and Bodies:Doing Sex in a Gendered World”,Gender &Society,Vol.3,No.19,2005,pp.297-316;Candace West and 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Gender & Society,Vol.1,No.2,1989,pp.125-151.从而符合受众对于男性从身体到外貌再到行为的期待。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性的情感劳动也逐渐地表现出人格/个性/男性气质商品化,男性及男性气质经由短视频/直播这样的社交媒体进行售卖就会呈现标准化、琐碎化以及虚拟私人化的特点。
另外一对矛盾的地方是,传统社会中的男性并不需要持续和外显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劳动,无论是在何种亲密关系之中。而在短视频/直播中,男性需要至少不少于女性地进行情感劳动,以维系作为主播的自己与作为受众的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无法获得心理或情感上男性更多的情感劳动,因而求诸短视频/直播中的在线、直观但虚拟的情感慰藉,也是短视频/直播的情感劳动何以有如此大的市场潜力的社会背景之一。有社会学的研究显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地进行情感表达,这是与父权制对于男性气质的要求相左的;(50)Sam de Boise,Jeff Hearn,Are Men Getting more Emotional?Crit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Men,Masculinities and Emotions.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5,No.4,2017,pp.779-796.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生活中不论,至少在线上情感劳动中,男性是乐于并善于进行情感表达的,毕竟情感“话术”是男主播们进行线上情感劳动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快手主播们的线上情感劳动在性别上对线下的情感劳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之外,在阶层上则有了更加突出的变化。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和观察中,“如果说在两性之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专门从事着情感劳动,那么在阶层系统中则是中层及上层部分最需要这种劳动。”(51)[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6页。“绝大多数的情感劳动从业者,属于中产阶层。”(52)[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91页。然而快手主播的线上情感劳动则是完全推翻了这种观察和结论。快手作为一个短视频/直播平台对于阶层和情感劳动对于阶层的一般论述的一大突破之处是,它使得个体化的媒介内容生产者不再受限于他们的文化资本,(5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而学历、资历以及专业的知识技能等是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用户内容生产者必不可少的进入门槛。(54)吕鹏:《作为假象的自由:用户生成内容时代的个人与媒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1期。对于快手的“内容生产”而言,只是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在此基础上,快手的线上情感劳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阶级的限制,使得小城镇和农村的用户得以参与到线上情感劳动之中,(55)Miao Li,Chris K.K.Tan &Yuting Yang,“Shehui Ren: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Youths’ Use of the Kuaishou Video-Sharing App in Eastern Chin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DOI:10.1080/1369118X.2019.1585469,2019;Jian Lin,Jeroen de Kloet,“Platform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Social Media+Society. hDttOpsI://1d0o.i.1o1rg7/71/02.10157673/2051613095818139483830430,2019.也分享部分平台经济带来的红利。至于为什么是快手,而非其他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实现了线上情感劳动阶层上的松动,则是由快手的服务对象和使用对象偶然中必然促成的结果。这样讲,是因为快手作为一款短视频/直播App从未将自己定位于服务小城镇和农村用户,并努力撇清小城镇、农村以及低学历者是这一App的主用户的事实(56)宿华:《快手CEO宿华:5000万日活用户中87%是90后》,腾讯科技,2017-03-20,https://tech.qq.com/a/20170320/031884.htm,2017-05-20.——虽然之后又直接(57)侯慧雪:《快手合伙人:用户来自二线以下城市 最高学历低于高中》,北青网,2017-12-26,https://www.sohu.com/a/212818164_255783,2018-05-20。或婉转(58)张研、申俊涵:《快手CEO宿华:快手的用户定位是“社会平均人”》,《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4月16日。21世纪财经: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0416/herald/306242f55989a7d9bdb37d5884b8334f.html,2017-05-20。地自证了,因而阶级的转向和松动从这一角度而言是偶然的;而必然则是因为,随着短视频/直播平台对于市场的开发,占据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口的农民阶层势必会成为平台最大的富矿,注定会被开发,只是时间早晚以及哪一家社交媒体平台而已。数字科技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使快手阴差阳错中开启了先河。笔者自己经年的田野观察以及访谈的主播的出身,也都直接证明了快手的网络主播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是以农村或小镇出身为主,学历程度不高。这些主播们无论在快手的直播还是在采访中,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甚至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农民”出身。当然这种自我强调或“农民”的标榜,并不代表主播们对“农民”这一身份的情感认同以及自豪,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快手作为一个平台,粉丝所认知的平台的整体文化中对农村农民的关注和认可。更加直接地说,这种认可和关注转化的主播对自己出身的标签化可以带来其想要的打赏这一结果。
与主播层与受众层最主要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短视频/直播平台——比如以游戏、城市以及时尚等——相比,快手的主播层和受众层基本上是以乡镇农村、小城市底层以及进中大城市务工人员等用户为主体,这几乎是所有用户的基本认知。主播们甚至以符号标签的形式尽力地凸显“乡村”“农民”的特征。既不同于网络游戏为主的“玩工”(playbours)(59)胡冯彬:《边缘的游弋:中国网络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新闻记者》2020年第7期;Julian Kücklich,“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Fibreculture Journal,Vol.1,No.5,2005,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 .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Adam Arvidsson and Kjetil Sandvik,“Gameplay as Design:Uses of Computer Players' Immaterial Labour”,Northern Lights,Vol,No.5,2007,pp.89-104.等创意劳工的身份特征,也不同于服务于城市及中产的女性主播的特点,快手中以男主播为主的主播群体特征,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相对底层的社会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资源,从而能够在短视频/直播中利用这种资源或资本从事被城市中产看来比较低端的工作,但对于资源更少的底层女性而言,这种赚钱的方式却是令人羡慕的;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底层的短视频/直播使用者的审美需求中,男性拥有更多的市场。底层民众的情感需求是以消费男性及其男性气质的方式得以体现,这种男性气质和对男性情感劳动的消费,既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隐约而不自觉的抗争,正是因为现实生活和世界中稀缺,才能够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商品”。
五、线上情感劳动的实质:被剥削者的剥削
即便不具备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也大概会明白,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情感劳动,是媒介中介、虚拟的、非面对面的情感劳动。这种线上情感劳动与线下情感劳动又有劳动雇佣的非正式与正式的区别,即线下情感劳动是有收益作为补偿的,而线上情感劳动的收益是非确定性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一方面短视频/直播平台只是给予主播——情感劳动的付出者——一个劳动的“机会”,但并不以任何的形式保障这种情感劳动会在相应的付出之后拥有相应的收益,但倘若有收益的话,这些收益是要以一定比例分成给平台的。
另一方面是主播与粉丝观众之间也并没有制度化的“协议”关系,也就是说主播的情感劳动付出之后,同样是否在享受到主播的情感劳动的粉丝那里获得收益也是不确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制造了新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简单地将平台、主播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抽离为五种:一种是平台对主播的剥削,(60)Tan,Chris K.K.,Jie Wang,Shengyuan Wangzhu,Jinjing Xu,and Chunxuan Zhu,“The Real Digital Housewives of China’s Kuaishou Video-Sharing App”,Media,Culture & Society,DOI:10.1177/0163443719899802.2020;Tan,Chris K.K.,Jie Wang,Shengyuan Wangzhu,Jinjing Xu,and Chunxuan Zhu,“The Abject as Mass Entertainment:Micro-Celebrities in China’s Kuaishou Video-Sharing App”,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DOI:10.1177/2050157920904980.2020.第二种是平台对于粉丝的剥削,第三种是主播对于粉丝的剥削,第四种是主播对于平台的抗争,第五种是粉丝对于平台和主播的“象征性”反抗。五种关系中,平台作为资本的运作者和商业规则的制定者,虽然也面临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但相对于主播与粉丝而言,其在关系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平台对于主播和粉丝的剥削是绝对的剥削。
然而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快手平台中,快手与主播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主播对于快手平台的普遍的称呼中窥见一斑——主播们把快手平台称为“官方”。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称呼,比如我们一般情况下使用微信或微博,不会把微信或微博发布的规则或管理的规定称为“官方”,而主播们对于快手“官方”的称呼,带有非常明显地将平台视为“官”将自己视为“民”这种非常中国民间化的理解,而在此关系之中,主播会把平台的管理和规定自然化和合理化。比如快手起先的直播是允许露纹身的,而后期禁止露纹身的时候,平台上所有的大小主播一夜之间全部都用各种方式遮蔽纹身,并没有任何人进行抗争,这种对于平台的依从和顺从,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是很少见的。当主播被快手平台限流时,绝大部分主播是在短视频或短视频下方用文字表达出希望官方不要限流的恳请;至于“#感谢官方#”这样的标签,几乎是主播普及性的标签。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并在实际中发现平台对于主播的剥削,表现在主播获得礼物打赏转化的收益的50%是需要被平台提成的。然而在笔者的访谈中,除了个别主播抱怨平台的提成比较多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主播觉得提成是不合理的,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剥削,反而很多人觉得没有这种提成——也即剥削——就没有自己可能的获得收益的机会。从主播对平台“官方”的称呼,以及主播们对于平台的“理解”,一方面可见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其机会的稀缺和对赚钱机会的珍惜;而另外一方面可见底层民众实际又实用的思维方式。这种实用主义和底层生存的智慧,也表现在主播们对于平台的“抗争”之中。实际上主播对于平台的抗争据笔者五年来的观察,主要表现在对“禁播”的“反抗”,这种反抗基本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平台进行申诉,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对于平台规则的遵守;另外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是当直播被禁止后,通过发短视频的方式与“官方”进行“理论”甚至破口大骂——而这种理论或破口大骂实际上针对平台的意味很弱,很像一种“弱者的武器”,(61)[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更大的是对粉丝的表演、告知和安抚。
而对于粉丝而言,他们既是平台的二级被剥削者,也是平台的隐藏被剥削者,更是平台最实质的被剥削者,因为平台和主播的实际收益都来自粉丝的贡献。然而粉丝可以通过选择不打赏来进行理性的、消极的或象征性的抵抗,从而实现金钱剥削的失败。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斯迈兹的观点,(62)Dallas W.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1,No.3,1977,pp.1-27.受众是种商品,正是由于把受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才实现了媒介营利的可能。在资本所钳制的文化之下,由资本所区分的消闲和劳作,又由于媒介的发达和介入从而使得消闲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又被消弭,消闲也变成劳作的一种。斯迈兹的观点虽然惊世骇俗争论不断,但也不乏后继者为之鼓吹,(63)Sut Jhally.“Probing the Blindspot:The Audience Commodity”,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6,1982,pp.204-210.并以电视为例,用“观看即是劳作”(64)Sut Jhally and Bill Livant,“The Television Audience/Watching as Working: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6,No.3,1986,pp.124-143.进行证明。顺着这一研究脉络以及媒介的持续进化发展,受众作为商品的卷入度越来越高,之前只是“看”而已,而现在则需要看的同时也生产内容,于是“产消合一者”(65)George Ritzer,Nathan Jurgenson,“Production,Consumption,Prosumption: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10,No.1,2010,pp.13-36;David Beer,Roger Burrows,“Consumption,Prosumption and Patricipatory Web Cultures:An Introduction”,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10,No.1,2010,pp.3-12;George Ritzer,“Prosumpiton:Evolution,Revolution,or 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14,No.1,2014,pp.3-24;George Ritzer,Steven Miles,“The Changing Natur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cDonald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Vol.19,No.1,2019,pp.3-20.这种属于社交媒体时代以用户生成内容(UGC)为特征的消闲方式也被纳入观察和研究的范畴,从而批判资本及数字平台等对数字媒体时代的新型受众的异化和剥削,(66)Edward Comor,“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Ephemar: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Vol.10,No.3/4,2010,pp.439-454;P J Rey,“Alienation,Exploitation,and Social Medi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cist,Vol.56,No.4,2012,pp.399-420.斯迈兹的理论也在数字时代(67)Lee McGuigan and Vincent Manzerolle(eds.),The Audience Commodity in a Digital Age:Revisting a Critical Theory of Commercial Media,New York:Peter Lang,2014.和数字劳动(68)Christian Fuchs,“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Prelegomena to a Digit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TripleC:Cognition,Communication,and Cooperation,Vol.10,No.2,2012,pp.692-740.的研究下重新被审视。
如果说斯迈兹等把付出观看以及背后的时间、但不付出其他的受众消闲,认为是劳动的判定还有很强的争议,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到了数字媒体时代“产消合一者”和“玩工”的出现则不但付出“看”和背后的时间,还亲自上阵生产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可能为平台所利用获利,那么受众为平台“做工”则就比较好理解。到了短视频/直播时代,受众不但付出“看”及背后的时间,还直接通过打赏的方式进行了金钱的付出,而关键是这些付出不是直接给予平台的,而是与平台并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主播。受众及劳动的异化和剥削呈更加隐秘的方式。用一个可能不太形象的比喻的话,是主播们分包了平台剥削的任务,主播们通过对粉丝们价值的榨取完成了平台的资本的剥削。一方面主播是被平台剥削,是被剥削者;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剥削者,不停地被平台所裹挟不断地剥削受众。即便没有直接的打赏,但大量的流量涌入和时间投入,又转化为平台获利的源泉,因此对于粉丝而言,终究是逃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人都成为资本机器的零件,从而完成资本获利和剥削的运行。但在整个这一资本运行的过程中,主播的线上情感劳动既是中介,也是核心。
与粉丝观看短视频/直播的目的或需要不同,也即粉丝使用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目的不同,主播使用此平台,并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媒介的“使用与满足”,而是为了获得那种不确定性的报酬收益。“在任何系统里,剥削取决于多种利益——金钱、权威、地位、荣誉、幸福——的实际分配。因此,提出何为情感劳动的代价的问题的,并不是情感劳动本身,而是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报酬系统。”(69)[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6页。作为被剥削者的主播就必须拼尽全力从粉丝那里榨取价值,在自己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在实现帮助平台剥削粉丝。对于粉丝而言,他们是双重被剥削者,而对于主播而言,他们是被剥削的剥削者。
短视频/直播中的主播之间的线上情感劳动的竞争是如火如荼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条件和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使得成为主播们进行线上情感劳动的物质等条件变得基本上不再是一种障碍;另外从从业者的资历和能力的要求而言,主播的进入门槛较之所有行业都低,无论是技能还是学历。因此主播与主播之间形成一种野蛮而蓬勃的江湖暗战。这种竞争有可能是明面上的,但更多是同类之间暗流涌动的较量。“当情感劳动被投放到公众市场时,它就表现得跟商品一样:对其需求的涨落,端赖于行业内的竞争程度。”(70)[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9页。
于是,对于主播来说,其情感劳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并不是市场自发的需求,而是一种创造。在这种情形之下,主播的情感劳动并没有“涨落”的变化,而只有制造的需求的多少,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需求的制造还是基于社会大众自知或不自知的社会需求。
六、结语及讨论
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而通过短视频/直播这种社交媒体来赚取钱财作为一种“劳动”的方式的逐渐流行和普及,则更进一步更改了劳动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模式。以底层用户为主的快手的出现,所具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革命意义——虽然是无心插柳的,实际上还远未为学界所关注和理解。快手使底层可以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参与到数字劳动之中,实际上是历史上第一次让中国城乡二元划分之下的“乡”这一向度的人可以与“城”这一向度的人在理论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实际而平等地进行劳动并获得收益。这是阶级层面快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快手的主播实践说明,线上情感劳动不再是与女性有着特别相关的模式,两性性别在短视频/直播中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快手主播们的线上情感劳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男性气质的认知,男性气质以影像的方式进行再生产和传播,已经有了可以松动霸权男性气质(71)R.W.Connell,Masculinities,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的某些可能。
可以肯定地说,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72)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这种赋权使底层民众都可以通过像快手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浮出历史地表,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73)Kevin Ziyu Liu,“From Invisible to Visible:Kwai and the Hierarchical Cultural Order of China’s Cyberspace”,Global Meida and China,Vol.5,No.1,2020,pp.69-85.然而,看到数字媒介技术光明面的同时,也不必过于乐观,因为这种可见确切地说仍然是在底层之中的可见,只是通过快手使得底层民众有了更广范围的文化和娱乐的分享,也即更大的底层社群在网络虚拟世界的联结。这种联结自然有其极为有意义的地方,之前更多的是中产和拥有更多社会文化资本的人才能享有的数字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便利,现今可为底层所享有,并可能利用这些技术的发展而通过线上情感劳动获得收益;然而它也让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得到更大的凸显,加大了阶层和文化之间的隔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底层文化在快手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形成全国性的共识和认同,这是底层文化之间天然的联盟和自发的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之下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另外一方面,主流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快手这样的社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底层文化不断地用“土”和“低俗”等负面词汇进行报道和渲染,更加加重了主流社会阶层对于底层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想象。这种隔阂,无论对于阶层的打破还是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都不见得是件乐见的事。
然而底层与所谓的中产分享了数字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和“权利”,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不存在雇佣劳动、生产工具/资料看似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对于普通的在社交媒体中从事线上情感劳动的主播们而言,他们依然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服从资本的社会关系。“资本使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过程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秘密并不在于流通的交换关系,而在于生产过程”,(7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8页。也即劳动的过程。因而只要资本,也即“人的被颠倒的社会关系”(7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4页。不变,无论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劳动的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如线上情感劳动的出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实践的本质都不变。而认识这些新的现象和劳动形式,则需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非物质劳动/非生产性劳动,以及数字劳动和线上情感劳动等的物质性或生产性。(76)Armin Beverungen,Steffen Böhm,Chris Land,“Free Labour,Social Media,Management:Challenging Marxist Organization Studies”,Organization Studies,Vol.36,No.4,2015,pp.473-489.
媒介技术越发达,劳动的形式就丰富。数字媒介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也是不断地发展,这些都导致了劳动的方式、劳动的形态以及劳动的形式也会不断地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劳动的外延越来越丰富的原因。线上情感劳动的形式和特征,也会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已经有诸多的案例表明,线上情感劳动有某些雇佣化的趋势,比如快手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其竞争对手就挖角快手的主播与其签约并禁止他们在其他平台进行直播等活动。(77)娱乐独角兽:《今日头条挖角MC天佑、10亿押宝“火山小视频”,短视频战场迎来“巨头”入局者?》,2017-05-17,https://www.sohu.com/a/141351708_549401,2017-10-02;大条:《2000万挖走天佑?今日头条杠上快手!10亿之后再砸》,镜像娱乐,2017-05-17,https://www.sohu.com/a/141358610_305277,2017-10-02。虽然快手平台并没有签约的主播,但快手中的大主播成立公司签约小主播,以及某些公司雇佣并包装主播进行市场化的运作,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其他短视频/直播平台签约主播,则是一件较为常规化的运作了。可见,劳动的形式,端赖资本以何种剥削的形式更能够获得收益来确定和实践的。未来主播们线上情感劳动的具体的、主流的形式会如何,其实是难预测和把握的。现象是纷繁的,但本质是不变的。而对本质的观察和了解来自于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再回归和再解读,是以众多学者们呼吁透过当下社会现象了解社会包括劳动、媒介传播等问题在内的内在本质,都需要回归马克思。(78)[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线上情感劳动作为劳动的一种,其抽象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种本质也只有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之中才能拨开迷雾和表面的各种伪装,从而准确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