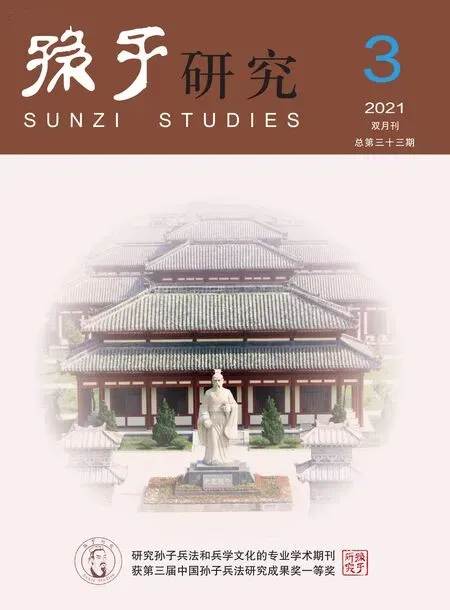齐鲁兵家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仝晰纲 罗 琳
齐鲁文化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宏的孔孟儒学,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的兵学文化,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神宗元丰年间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必读的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四部兵学著作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其中,姜太公被称为兵家始祖,孙武被称为兵圣,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
一、齐鲁兵家出现的文化氛围
兵家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这实际上是论述了兵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线索。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皆出于齐、鲁,因此,齐鲁兵家堪称中国兵学文化的典范。齐鲁兵家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
1.历史地理文化的自然塑造
文化区域是实际地域与意识观念形成的结合体,地理状况造就的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人文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区域的形成。因此,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能脱离人类在时空上所处的特定自然条件。齐鲁兵家文化正是在它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的自然塑造中逐渐形成的。
齐、鲁初封时都不过是方百里的方国。《孟子·告子下》曰:“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可见,齐国最初不过是占有营丘〔1〕周围方圆百里左右地盘的一个小国。《史记·齐太公世家》曰:“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这大致可以看作是西周时期齐国最强大时的疆界。齐桓公时,齐国疆域“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灵公、景公时,疆界又有所扩大。至战国时期,齐国地广而兵强,方二千里,《战国策》云:“齐南有太(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战国策·齐策一》)实际上,齐国的疆域远不止如此,东已基本囊括整个半岛地区,西已至黄河故道,北至渤海,南至今鲁南地区。
鲁国初封时,封土也不过百里,到后来“鲁方百里者五”(《孟子·告子下》),即鲁国的疆域超出了初封时的数倍。诸如根牟、项等小国都被鲁国吞并,邾、莒、曹、宋等国的部分土地也曾被鲁国占有。鲁国以曲阜为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拓展。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许多小国纷纷朝鲁,并且至鲁观礼,鲁成为当时的大国。其控制范围基本囊括了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区。
齐、鲁的疆域,基本上覆盖了今山东省的全部及周边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的山脉和河流。其地形大势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这一特点又决定了水系比较发达。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齐鲁儿女健壮的体貌。据古人类研究专家考证,“纵观全国汉族两性身高均值的地理变化,北部地区居民身高与南部地区居民身高有显著差异,前者身材较高,后者身材较矮”〔2〕。据张振标先生统计,中国新石器时代男性身高以山东、河南一带最高。这种南北身高的差异,显系地理因素所成。
地理环境不仅对人的体貌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的性格形成也起着无形的作用。汉代学者班固认为,人的性格受水土风气的影响,他说:“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汉书·地理志》)如果说班固讲得比较笼统,那么管子所言则比较具体。他说:“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管子·水地》)近人刘师培在论证自然环境与性格关系时指出:“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韧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3〕由此我们说,齐鲁之人好勇、尚武、坚韧不拔、粗犷刚烈的性格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塑造有着必然的关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
2.东夷民族的尚武传统
齐鲁大地上的居民是东夷人。东夷人身高体壮,好战善射。《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说文通训定声》云:“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生动地将东夷人高大、尚武的形象描述出来,这都说明东夷民族是一个具有尚武善战传统的民族。
蚩尤是传说中东夷民族的一位首领,勇猛善战,《龙鱼河图》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威震天下。”〔4〕蚩尤曾与黄帝的部落联盟战于涿鹿,这可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最终虽兵败被杀,但他那勇武的品格受到世人的敬重。齐国有八神主的祀典,八神主之第三神主就是“兵主,祀蚩尤”(《史记·封禅书》)。在齐鲁故地,有许多蚩尤的遗迹。据说,郓城境内有蚩尤冢,“高七丈,民尝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命为蚩尤旗”〔5〕。巨野县境内有蚩尤肩髀冢,大小与蚩尤冢相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6〕据王献唐先生考证,今山东邹城西周春秋时期有邾国,即蚩尤的后裔。〔7〕
战神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尚武习俗。曾与黄帝争斗过的蚩尤被民间奉为早期战神,“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秦始皇东巡时,祭祀名山大川及各路神灵,其中就有兵主蚩尤(《史记·秦始皇本纪》)。刘邦在沛地起兵前,也“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史记·高祖本纪》)。
夏启夺得天下后,淫佚无度,东夷人的首领后羿发动了反抗夏统治的斗争,并夺取了夏政权。后羿,号有穷氏(今山东德州市附近)。传说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命羿“上射十日”,所谓“十日”,和“猰貐”“凿齿”等可能是尧的敌对部落。由于羿善射,所以尧令其用武力征服。羿在征讨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勇敢,传说他手操弓矢,百发百中,“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淮南子·本经训》)。
商取代夏后,特别是盘庚迁殷后,山东地区出现了许多统治的空白点,姜姓集团得以迅速发展并对商的统治构成威胁。帝乙时,曾“征夷方”,商纣王时曾对东夷大举用兵,史称“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尚武善战的秦人、赵人也都以鸟为图腾,与东夷相同,他们应是东夷移民。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东夷民族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
3.发达的兵器文化
关于兵器的发明制造,《孙膑兵法·势备》曰:“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我们认为这段话是出自传说,并非历史真实。事实上,许多兵器的发明都与齐、鲁大地上的先民有关。
东夷人是弓箭的发明人。“夷”字即人背弓之形。《山海经·海内经》云:“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礼记·射义》疏引《世本》云:“挥作弓,牟夷作矢。”《说文·矢部》:“古者牟夷初作矢。”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甲骨文的“齐”字,似是箭头的象形,以致有人认为“齐”之得名源于箭、矢。〔8〕我们置其正确与否不论,只从这一象形字来说明东夷人与弓箭发明的关系。在山东邹城野店、曲阜西夏侯等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有以石镞、玉镞装饰躯体的习俗。有的戴在头右侧,有的戴在左肩上,更多的是佩戴在腰部。〔9〕从此可窥见东夷人对弓矢的爱好。
《管子》中有蚩尤发明“五兵”的记载,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管子·地数》)《龙鱼河图》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10〕这段神话传说可以给我们提供两个信息:一是“铜头铁额”,可能是蚩尤发明了金属盔甲;二是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冷兵器的发明可能与东夷人有关。
殷商、西周时期,传统兵器主要是青铜兵器。所谓“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齐语》),就是说青铜主要用于制造兵器,铁主要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齐鲁是青铜兵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战国以前作战以战车为主,戈是车战长期使用的主要兵器,因此齐国的兵器制造以戈为主,如“高阳左”戈〔11〕、“安平右”戈〔12〕、“平阿戈”〔13〕等。高阳、安平、平阿都是齐邑。
鲁国的兵器制造业也很发达。春秋时期,鲁班善于制造攻城器械,楚欲攻宋,鲁班曾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城器械。墨子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守城器械。如木鸢、桔槔、罂听、连弩之车、转射机、藉车、校机、行城、悬陴等。
从齐鲁地区兵器铸造地点的分布看,可大体分为潍淄区和汶泗区。潍淄流域是齐文化的中心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兵器铸造也十分先进。现已知的兵器铸造点主要有齐城〔14〕、淳于城〔15〕、平寿〔16〕、高密〔17〕、计斤〔18〕、昌城〔19〕、莒〔20〕、平陵〔21〕等。汶泗流域在西周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鲁国的中心地区,进入战国后,渐归齐国。在这一地区已知的兵器铸造点主要有:平陆〔22〕、平阳〔23〕、亡盐〔24〕、郈〔25〕等。高度发达的兵器文化,对齐鲁兵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互融
齐鲁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互融过程。齐、鲁立国后,都把周文化移植到了各自的封国,并都把周文化视作官方文化,只是由于两国的国情不同,在推行过程中把握的深度和广度存有差异。从整体上讲,鲁国要比齐国彻底一些。
齐、鲁地区曾是商的中心区域之一,因此都有大量的殷商遗民。齐国据薄姑旧地,薄姑系殷族。《史记》称齐太公对“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的五侯不是五等诸侯,而是指殷东之五侯,即薄姑、徐、奄、熊、盈。因此,殷商文化势必存在于齐。鲁国则有“殷民六族”,“周社”“亳社”也同时存在。“周社”是周人社祭之所,“亳社”是殷人祭祀之所,鲁国阳虎政变时,“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二者同时并存,说明殷人在鲁国为数不少。大量的殷商遗民,虽然处在周族的统治之下,但其生活方式仍保存着商文化的特色。孔子临终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礼记·檀弓上》)这说明商文化在鲁国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齐、鲁初封时,方不过百里,随着其势力的扩张,周边东夷人居住的地区渐渐被其蚕食鲸吞,东夷人也就成了齐、鲁的国民,东夷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齐、鲁。一直到春秋时期,孔子仍然对东夷文化怀有向往之情。郯国是东夷之国,鲁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来鲁访问,孔子曾向郯君请教东夷文化的问题。《左传》记述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还曾有过“欲居九夷”的念头,当有人说东夷鄙陋不可居时,孔子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由此我们说,东夷文化在鲁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齐国,东夷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实质是承认了东夷文化在齐国存在的合理性。周灭殷后,封齐于东方,就将东夷势力进一步压缩在半岛一隅,于是就发生了“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纪·齐太公世家》)。莱人,就是东夷人。东夷人有自己的礼制,太公至齐后,允许东夷人保留其传统习惯,对于缓和矛盾和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东夷人有太阳崇拜之俗,齐太公的继承人丁公吕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均以日干为名号,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东夷人的习俗。齐国有八神将的宗教信仰,其中第三神兵主蚩尤,是东夷族的首领。由此可知,东夷文化在齐地并未受到抑制,而是在和周文化的互融中得以保存和再生。这种周文化、商文化、东夷文化的互融,为齐鲁兵家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素养。
二、齐鲁兵家的发展轨迹
地域文化虽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的形成和发展毕竟脱离不了历史的机缘。人类初始,为了生存和繁衍,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和措施来防范野兽或周邻同类的抢掠,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兽处群居,以力相争”(《管子·君臣》),“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吕氏春秋》的作者说“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荡兵》),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说,战争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齐、鲁立国前,齐鲁大地是远古时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地区,尧以前的君主,几乎无一不与这片土地有关,古史传说中的战争,多少都与齐、鲁大地有所联系。这种厚重的战争文化积淀,对齐鲁兵家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浸润作用。
齐、鲁立国后,两国都根据各自的国情对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改造,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鲁国则“变其俗,革其礼”。简礼从俗,产生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学术思想。革礼变俗,产生了敦厚、理性、仁治、王道的学术思想。前者以力行霸业、一匡天下为最高追求,后者以仁义至上、礼治天下为最高境界。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而且是互补的。因此,齐学、鲁学的不同风格并不妨碍齐鲁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体性的区域文化。兵家虽首倡于齐,但它的文化基础不仅仅是齐学,而是丰厚的齐鲁文化。
齐鲁兵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齐鲁兵家的萌始时期,其标志是姜太公和周公军事思想的形成。在西周灭商的过程中,姜太公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牧野之战时,姜太公“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26〕,他是周军的指挥者之一。太公封齐后,齐与以莱夷为代表的东夷方国也曾进行过领土争夺斗争,直到齐灵公时,才最终灭莱。周公是西周政权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无论在武王灭商还是在佐助成王治理天下时,周公都有着卓著的战功。他的分封地是奄商旧地,也是战略重地。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周公东征,才使周朝得以镇抚东方。因此说,周公也是一位韬略满腹的军事家。
姜太公和周公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姜太公的兵学理论主要保存在古《司马法》和《六韬》中,虽然对古《司马法》和《六韬》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有异议,但其中包含有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当是不容怀疑的。周公的军事思想主要保存于《周礼》和《周易》中。《周礼》的最初成型应是周公所规划。《周礼》中的《春官宗伯》讲军礼,《夏官司马》讲军制与“大司马”之职。相传《周易》卦辞的作者是周文王,爻辞的作者是周公,郭沫若认为:“《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事项之上。”〔27〕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说《周易》是一部兵书并不过分。姜太公和周公的军事思想是西周初年兵学理论的代表。齐、鲁立国后,姜太公和周公的军事思想自然而然地带到了齐国和鲁国,从而为齐鲁兵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养。
第二阶段主要在春秋时期,是齐鲁兵家的正式形成时期,其标志是管仲兵学理论的形成及《孙子兵法》的问世。春秋时期,由于“王纲解纽”和“礼崩乐坏”,人们的思想开始突破传统的束缚而获得解放,进入了一个大创造、大繁衍的时代。同时,由于王宫文化从周王室一降而至各诸侯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齐鲁兵家文化正是在这种社会整合中于齐鲁地域内逐渐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王纲解纽”只是普遍的大环境,那么,齐鲁地区的社会状况则是齐鲁兵家出现的直接因素。春秋时期,周天子威风扫地,给各国诸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谁走在时代的前列,谁就掌握着历史的主动权。齐国的管仲首先改革,使齐桓公首霸中原;孔子首先冲破官学的束缚,开创私人讲学之风,使鲁成为文化中心。这一时期的齐鲁地区,不停地革故鼎新,不间断地改造社会,许多英雄人物脱颖而出。最先推上历史舞台的就是管仲。他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的制度,“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为齐国训练出一支三万人的强大队伍,奠定了齐称霸的基础。在齐称霸过程中,管仲南征北伐40 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兵学经验,今本《管子》中有许多篇章实际上就是兵学著作。其后,孙武名显诸侯。孙武兵学理论的应用是在吴越争霸时期,但其兵学理论的形成是在齐地。孙武本是陈公子完的后裔,田氏代齐后,言兵之风日盛,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兵家学派,孙武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因齐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他才避祸于吴,做了吴王阖闾的大将。在吴国的征战经历,又丰富了他的兵学思想。
老师以桃李芬芳为荣,总希望自己培育出的学生个个有出息。因此,我觉得,作为学生只有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感激老师的精心培育和呵护,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春秋之际,随着社会变革日趋激烈,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殷商、西周时期作战受礼制束缚较多,进入春秋以后,诡诈权谋的应用越来越多,战争方式和战争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时,战争规模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春秋以前,军队数量较少,军队编制中“师”为最高建制单位,进入春秋后,军队数量大增,“军”级的军队编制开始出现,从而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除投入兵力不多的阵地战外,用兵较多的运动战开始出现。这一变化是决定战略战术变化的前提所在。
第三阶段主要在战国时期,是齐鲁兵家的大发展时期,其标志是吴起、孙膑、田单在军事实践中的活跃和《孙膑兵法》《吴子》《司马穰苴兵法》的出现。
战国时期,自西周以来一直在中国兵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齐鲁兵学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战国初期,魏国首霸中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吴起为魏国训练了一支素质良好、所向披靡的“魏武卒”。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应属齐鲁文化圈,将其列入齐鲁兵家是名正言顺的。吴起初为鲁将,因不受重用而奔魏,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军事改革,使魏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吴起离魏奔楚后,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吴起列传》)。吴起的《吴子》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齐鲁兵学。齐国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他们争论的不少内容涉及军事。齐威王曾对孙膑说:“齐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孙膑兵法·强兵》)可见有许多学派的兵家思想,这无疑对齐国兵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齐威王任用孙膑治兵,终于使齐国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纵横家苏秦形容齐国国力时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战国策·齐策》)孙膑在齐,使齐国威服诸侯,取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孙膑兵法》是孙膑在齐国军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兼容其他兵学理论形成的一部军事著作。在齐威王时,齐国士大夫们还对古《司马法》进行了追论,并将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附入其中,形成了《司马穰苴兵法》。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齐国兵家们既互相论辩驳难,又相互交流提高,使兵学理论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
至齐缗王时期,由于各国力量的制衡,齐国势力一度削弱,以至五国伐齐,乐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齐几乎亡国。在这危急关头,田单用火牛阵将燕军击退,收复了失地。但齐国经过此役的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迅速崛起的强秦相对峙。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此后,齐鲁兵家文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融入了整个华夏文明之中。
三、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
1.齐鲁兵家的多元文化性
齐鲁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过程,在齐鲁兵家文化的再组合过程中,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封齐后,把西部华夏文化带向齐地的东夷,东夷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本能的反抗力。姜太公刚刚来到齐封地,就受到莱夷的攻击,并与姜太公争夺营丘。从太公立国始,经传中经常出现“伐莱”“侵莱”“攻莱”“制莱”的记载。姜太公就国后,还出现了“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狂矞、华士以及“以仁礼乱国”〔28〕的营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姜太公。这实际上是东夷文化对西来的中原文化的对抗。面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姜太公采取了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的政策,即“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谓“因其俗”就是因袭东夷人的生活习俗,所谓“简其礼”就是对东夷人现存的制度进行适度改造。这种改造过程当然包含着周文化对东夷文化的渐进性改造。实践证明,姜太公采取的政策比较适合当时齐国的国情,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
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同样也存在着当地文化与周文化的冲突问题。鲁国位处奄商旧地,紧邻徐戎、淮夷。伯禽就鲁不久,就发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鲁地文化的抵抗,实际上是奄商与周的对抗,因此周在鲁没有“因其俗,简其礼”,而是“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即用周礼的模式来改造鲁地固有的传统习俗。
齐鲁地区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撞击的同时,也逐渐吸收和融进了外来文化,在兵家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姜太公将周代的司马法带到齐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李卫公问对》卷上)。孙武至吴后,一方面将中原兵学带到吴地,同时也吸收了吴越地区的兵学理论。吴、越没有“以仁为束,以礼为固”的思想影响,用兵时大量采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等诡诈战术,颇有点道家和阴阳术数的特点,这必然给孙武以十分深刻的影响。孙武与吴国军事家伍子胥相善,两人又同时受命为将,两人之间切磋兵学理论、相互取长补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孙武在广泛参与吴国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南方军事文化的影响。《孙子兵法》中极力宣扬“兵者诡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武吸纳南方军事文化的结果。
稷下学宫兼容并包了当时儒、墨、道、法、兵、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号称“百家”,而在学宫游学或讲学的稷下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孟子、鲁仲连、田巴、荀子等诸子,并称“诸子百家”。他们自由辩论,相互攻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互补和兼容现象。在稷下学者的辩论内容中,也不乏精辟的兵学理论,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详考。但《司马兵法》《子晚子》以及《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等言兵著作,当为稷下兵家所作。〔29〕在稷下“最为老师”的荀子,也有《议兵》之作。稷下兵家虽很少是驰骋疆场的军事将领,但他们对兵学的探讨,无疑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
2.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
务实,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齐鲁兵家无不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而他们事业成功的历程,也就是务实、拼搏的人生经历。齐鲁兵家务实,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姜太公刚到齐地时,面对齐国地薄、人少、国贫、临海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强制推行周朝的农耕文化,而是制定了“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发展方针。齐国东临大海,盛产鱼盐,当地的传统生产是植桑养蚕,生产丝麻。因此说姜太公的政策是合乎实际的。春秋时期,管仲相齐,使齐国首霸诸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从齐国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务实改革。管仲相齐期间,不尚空谈,真抓实干,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主张“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管子·立政》)。这种在特殊地理环境下,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措施,正是务实的具体表现。
齐鲁兵家对自然条件的利用不仅仅表现在发展生产上,还表现在军事实践中。《孙子兵法》有《地形篇》,通过“地有六形”和“兵有六败”的论述,来揭示自然地理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孙子将自然地形看作是“兵之助也”(《孙子·地形篇》)。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孙子兵法》中还有《九地篇》,从军事地理学角度,来论述战略进攻中实施突袭的若干问题。在战争中,重视地点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注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孙膑兵法》则有《地葆篇》,葆,通宝,将行军作战中的有利地形视为宝。〔30〕
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还表现在因民俗上。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姜太公就国后,面对以东莱为代表的抵抗势力,他没有强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而是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赢得了东夷人的拥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所谓“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姜太公因民俗的必然结果。管仲相齐时,继承了姜太公因民俗的传统,他说:“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俗之“所欲”或“所否”,实际上就是百姓民众的“欲”和“恶”。基于这一认识,管仲在齐国实行“四民分业定居”制度,使人民各安其居,各守其业。根据齐人好技巧,以致富相竞的风俗,“通货集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种“与俗同好恶”的政策,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说齐桓公的霸业与管仲“与俗同好恶”的务实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姜太公、管仲的影响,“因俗”成为齐国的治国传统。齐景公时,晏婴提出了“一民同俗”的主张。他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遗,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晏子春秋》)但一民同俗,并非完全认同民俗,也不否定视民俗现状进行引导和改良。如齐国有奢侈之俗,晏子则主张节俭,以引导民俗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贵势”是齐鲁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所谓“势”,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所谓“贵势”,即机动灵活,随势而动。《管子》中有《形势》《形势解》《势》三篇来论述管仲对“势”的见解。管子认为,凡事顺势则成,逆势则败。《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到“势”,如:“计利已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始计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势篇》)再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是指孙膑能根据敌情、地形、气候、阵法等各方面的条件,机动灵活,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形势。
由上述可知,遵天时,就地利,因民俗,顺形势,构造了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
3.齐鲁兵家的人本特征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师克在和不在众”(《左传·桓公十一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用间篇》)《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司马穰苴所谓的“怀德”和“正则”,实际上也是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所谓“怀德”,就是要求将帅对士卒关心和爱护,施以恩德,“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司马法·严位》)。关心和爱护士卒的出发点就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所谓“正则”,即以己正人,要求将帅具有较高的思想品德,勇于承担责任,功劳归于大家,自身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以自身修养来实现“人”的价值。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吴起用兵,视文武兼备的良将为战争胜利的关键。他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吴子·论将》)也就是说,一个将领,但凭独夫之勇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素养,才能成为良将,才能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稍后的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
4.齐鲁兵家的辩证思维特色
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西周。西周末年,周大夫伯阳父在论述地震原因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将阴阳看作是对立的一对矛盾。同一时代的史伯则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把“和”与“同”看作是一对矛盾。这都足以说明在西周末已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到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十分精辟。人们这种对事物的辩证认识,自然而然地会渗透到兵学理论当中。孙武在以辩证法观点去分析、总结战争规律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敌我、主客、彼己、阴阳、动静、进退、攻守、强弱、速久、胜负、奇正、虚实、勇怯、避就、专分、治乱、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劳逸、迂直、内外、卑骄、生死,等等。这些对立范畴,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31〕。孙武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战争,大大丰富了兵学的内容。据姜国柱教授研究,其军事辩证思想主要有:以我为主,因敌制胜;杂于利害,趋利避害;奇正相生,以奇制胜;任势造势,以实击虚等。〔32〕
司马穰苴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也是以辩证的观点来认识战争。杀残暴的人是为了保护、安定善良的人,出兵他国,又要爱护他国的百姓,发动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司马穰苴还认为进军要有“节制”,他说:“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司马法·天子之义》)这都含有辩证的色彩。
孙膑军事思想中,辩证思维特色更加浓厚。《孙膑兵法·积疏》曰:“[积]胜疏,盈胜虚,径胜行,疾胜徐,众胜寡,佚胜劳。积故积之,疏故疏之,盈故盈之,虚[故虚之,径故径]之,行故行之,疾故疾之,[徐故徐之,众故众]之,寡故寡之,佚故佚之,劳故劳之。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 为变,佚劳相] 为变。毋以积当积,毋以疏当疏,毋以盈当盈,毋以虚当虚,毋以疾当疾,毋以徐当徐,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毋以佚当佚,毋以劳当劳。积疏相当,盈虚相[当,径行相当,疾徐相当,众寡]相当,佚劳相当。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径故可行,疾[故可徐,众故可寡,佚故可劳]。”
【注释】
〔1〕营丘位于何处,史载不详,历来颇有争议。《史记·周本纪》:“封尚父于营丘,曰齐。”《正义》曰:“临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故有营丘之名。”后人多从此说,认为营丘即后来的齐都临淄。
〔2〕张振标《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变异》,《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2 期。
〔3〕《刘申叔先生遗书·南北学派不同论》。
〔4〕《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5〕《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
〔6〕《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
〔7〕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1~68 页。
〔8〕王树明:《齐国地名推阐》,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9〕参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 期。
〔10〕《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
〔11〕《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0、24。
〔12〕《三代吉金文存》20、35、4。
〔13〕《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0、52。
〔14〕齐城,即今山东临淄。《三代吉金文存》20、14、1 有“齐城右造车戟,冶期”。《缀遗斋彝器款识》30、26 有“齐城子造,□戈右”。
〔15〕淳于城,位于今山东安丘附近。《齐乘》:“淳于城,安丘东北潍汶水交处,古有此城。”《三代吉金文存》20、14、1 有淳于公戈。
〔16〕平寿,《齐乘》:“平寿城,潍州西南三十里古城。”《三代吉金文存》19、39、1 有平寿戈。
〔17〕高密,位于今山东高密。《史记·高祖本纪》:“汉三年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三代吉金文存》19、35、1 有高密造戈。
〔18〕计斤,《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崔杼伐莒,侵介根。”杜注曰:“介根,莒邑,今城阳黔陬县东北,计斤城是也。”《三代吉金文存》20、7、1 有“切斤陡戈”。黄盛璋先生在《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 期)认为切、计通假,切斤即计斤。
〔19〕昌城,《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0、26、1有昌城右戈。昌城位于临淄西南,《史记·乐毅列传》:“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正义》云:“古昌城在淄州淄川县东北四十里也,燕昭王以昌城而封乐毅为昌国君。”
〔20〕莒,《沂蒙金文辑存》60、1 有莒戈。莒,战国时属齐。
〔21〕平陵,位于今山东济南章丘区境内,《三代吉金文存》20、8、1 有平陵右造戈。
〔22〕平陆,《三代吉金文存》20、9、2 有平陆左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鲁败齐平陆。”《集解》引徐广曰:“东平平陆。”《正义》云:“兖州县也。”
〔23〕平阳,《三代吉金文存》19、44、1 有平阳高马里戈。《左传·宣公八年》“城平阳”,杜注:“今泰山有平阳县”。
〔24〕亡盐,《三代吉金文存》19、31、4 有亡盐戈。亡盐在今山东东平。
〔25〕郈,《沂蒙金文辑存》72、1 有后生戈,后、郈通假。郈在今山东东平东南。
〔26〕《绎史》卷二〇引《帝王世纪》。
〔2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 页。
〔28〕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 页。
〔29〕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98 页。
〔30〕姜国柱:《〈周易〉与兵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 页。
〔31〕姜国柱:《〈周易〉与兵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59 页。
〔32〕《孙膑兵法·积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