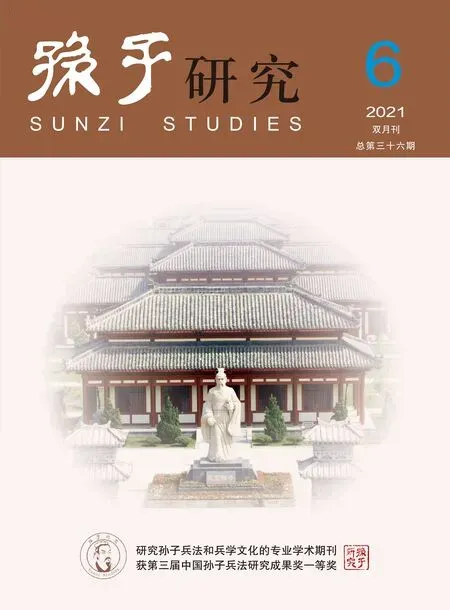西汉定襄郡的设置与汉匈战争
丁赵旭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定襄郡,高帝置。”后世学者一部分赞同此观点,另一部分则通过考证认为定襄郡应该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支持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周振鹤,在其著作《西汉政区地理》中引用《汉书·高帝纪》的记载:“十一年,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他对该诏书进行解读并得出两个推论。其一是高帝调整了旧云中郡的边界,以云中县为界,西部为新云中郡为汉中央管理,东部设立新的定襄郡划归代国。其二只是调整雁门、云中两郡边界,将云中县以东划归雁门郡。因并无史料证明划入雁门郡之事,所以他选择了第一种看法。后者主要是王国维和谭其骧,他们认为定襄郡的设置当在汉武帝时。马孟龙在《西汉侯国地理》中也指出:查阅史籍,武帝元朔以前从未出现“定襄郡”的记载。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定襄郡设置的时间,但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关于汉匈战争的记载往往会涉及这一带,只要梳理清楚汉匈双方在这一区域所进行的战争过程,就能为推断其设立时间提供可能。再依据定襄郡本身的地理特点,探讨其在西汉北部边疆建立整体攻防体系的意义。
一、汉武帝以前汉匈战争背景下代地的局势
这一时期汉匈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汉高帝时期,特点是匈奴利用汉朝统治者高层之间的矛盾深入内地,代表性事件就是韩王信和陈豨的叛乱。二是文、景时期,特点是汉匈双方以边郡作为拉锯地带,总体上是匈攻汉守。
高帝时期,因汉朝统治者高层的内部矛盾激化,不断有人叛逃匈奴,引发匈奴对汉朝内部干预的兴趣。其实,匈奴入侵内地早已有之,《史记·韩王信列传》载韩王信上书请求移都马邑的原因就有:“国被边,匈奴数入。”高帝七年秋,韩王信因被猜忌而反叛,攻占晋阳以及周边各城。关于这次军事行动散见于《史记》的高祖本纪及周勃、樊哙、郦商、韩王信等世家、传记中,《史记·匈奴列传》中也有简单的记载,但这些记载之间矛盾颇多。平叛过程大致如下:刘邦亲自统军北上攻击韩王信。另分出一支偏师,由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人指挥,绕过晋阳城,过葰人,联合郦商在上谷的军队,向北攻击韩王信后方的代郡、雁门郡和云中郡。周勃军大破匈奴军于武泉北,然后掉头南下会合刘邦的部队,破韩王信军于铜鞮,汉军乘胜收复太原郡所属的六个城。韩王信战败后一边拥立赵国后裔赵利为王,借其名声重整兵马,一边向匈奴求援。匈奴派左右贤王南下,与韩王信大将王黄会合,在晋阳城下与汉军大战,结果又被打败。汉军攻下晋阳向北进军,在硰石取得胜利,收复了楼烦三城。匈奴在几场战斗连续失利以后采用诱敌之计,《史记·匈奴列传》载:“于是冒顿佯败走”。匈奴的计策因刘邦轻敌而实现,轻兵急进导致汉军被围困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最后陈平献出秘计,汉军才得以顺利突围。高帝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叛乱,并联合韩王信部将王黄劫掠赵、代。刘邦分军平叛,一支由他亲自率领,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平定赵地,另一支由周勃率领,“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在楼烦攻破韩王信与陈豨联军,后向西平定雁门、云中各县,再向东攻代郡,于灵丘斩杀陈豨。
结合山西北部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马邑城(今属山西省朔州市)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向西北沟通了雁门、云中,向东北沿桑干河谷沟通代郡,南面把守通往晋阳的大道。不论匈奴从哪一个方向进攻,都必须先打马邑,这也是韩王信要求移都于此的初衷。匈奴反应速度超出韩王信的判断,冒顿亲率大军包围马邑,迫使韩王信投降。汉王朝的策略是先恢复西北边郡,切断韩王信与匈奴的联系,再回师消灭叛军。此时汉军难以有效控制雁门和云中二郡,韩王信与匈奴联系没有被完全切断,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为后来的大胜提供了便利。平定陈豨叛乱的周勃军队在攻克马邑后也是向西北的雁门、云中进军,稳定了这一带后再向东打击陈豨军。匈奴的核心区位于阴山以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地理志》在五原郡稒阳县下有“头曼城”的记载,头曼是冒顿父亲之名。《史记·匈奴列传》中还有一条记载:“头曼不胜秦,北徙……于是匈奴得宽。” 表明秦王朝大军只是将匈奴驱赶到阴山以北,此地距河南地不远。又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说明趁中原内乱,匈奴又越过阴山南下进入河南地。雁门、云中二郡是联系匈奴核心带与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似可以解释汉军在两次平叛时为何选择先平定这两个郡。关于高帝末年的形势,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言中进行了概括,论述燕、代两国疆域用的是“雁门、太原以东”,论述中央直属地区时称“北自云中至陇西”,没有谈及雁门和云中间的定襄郡。司马迁本人精通地理,在记载中不太可能遗漏一郡,若当时无定襄郡,则可说通。
第二阶段战争特点是匈奴主动侵扰,汉王朝进行反击。此时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边郡,这是汉王朝政权在边界逐步稳固的一个表现。依照《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以前,上郡和北地郡是匈奴入侵的主要目标,代地的记载较少,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有云中太守魏尚击杀匈奴一事。据文帝三年(前177)六月下的诏书中可知匈奴单于已派右贤王经略河南。后元六年冬,匈奴开始分两路兵入侵云中和上郡,每路各三万人。〔5〕汉廷派令勉和苏意去加强代地飞狐和句注的防守。这两地分别位于雁门郡南缘和代郡东南。
景帝时匈奴入侵规模扩大。据《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前144)载:“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结合《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八月,匈奴入上郡。”这是两条当时并无定襄郡的重要证据。匈奴的行军路线,据当地地理情况和刘统考证推断,当是沿荒干河谷(今大黑河谷),越过大青山南下。《汉书》中记载的是匈奴先入雁门郡,后过云中郡的武泉县,可说明定襄郡在当时不存在,且该郡后来自雁门郡析置。景帝后元二年(前142)正月,《史记·景帝本纪》中载“郅将军击匈奴”,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郅将军”即郅都。《汉书·景帝纪》记载原太守冯敬在与匈奴作战中阵亡后,郅都继任雁门太守,匈奴慑于其威名,不敢与他交战。此外还记载“(匈奴)竟郅都死不敢近雁门”。《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同年)三月匈奴入雁门。”此时郅都已经因逼迫临江王自杀一事被窦太后处死了〔6〕。这一时期汉军无力与机动性极强的匈奴军队作战,边郡建设虽有一定成果,但不能防御匈奴大军,边郡仍是双方的拉锯带,不得已只能守住边郡通往内地的险要关隘,阻止匈奴深入。
二、定襄郡的设置与汉匈战争局势的变化
文、景统治时期注重恢复国力,武帝继位时,汉王朝反击匈奴的物质条件已具备,战略战术也多有调整。战略上,完善和加强边境重要据点和其他防御工事的修筑,建立后勤基地,满足大军征战所需。战术方面,改变以往被动反击的战术,在边境集结大规模骑兵军团主动出击。当然,这种战术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汉武帝即位初期,延续对匈奴防守的政策。《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前134)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结合《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选择水草较好的地方屯兵,没有军中的繁文缛节,只是派遣斥候调查匈奴的情况,最后全军安全返回,程不识军队的行为与李广相反。从这两个记载推断,李广、程不识这次行动还是防御作战,他们防守的地域应是居云中和雁门二郡之间的荒干河谷,这似可说明当时并无定襄郡。上述记载还能使我们了解此地水草条件较好,但人烟稀少,需要防备匈奴的偷袭。元光二年(前133)始,汉王朝开始实施反击计划,标志性事件是马邑诱敌。《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元光元年王恢向汉武帝上书告知聂翁壹的计策,元光二年聂翁壹逃到匈奴,利诱单于入塞。这一诱敌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从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这场战役证明马邑城在汉匈战争中的重要性。聂翁壹诱惑单于时指出“财物可尽得”。且汉军在马邑城附近伏兵高达三十多万,后勤补给需要马邑及周边地区提供,侧面说明在高祖时代被严重破坏的马邑城再度成长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单于带领十万人南下,目的不单是抢掠马邑城的财物,更希望通过占领该城,削弱北侧汉朝云中、雁门和代郡一线的防御体系。二是单于入塞走的路线是武州塞(今大同市左云县)一带。这一次行动是偷袭计划,所以单于会挑选一条不易被发现的道路进军。单于的计划可能是沿今原子河河谷直达马邑城,该河谷在西汉时尚未设立郡县。匈奴这次行动使汉王朝认识到雁门郡防御地域边界过长,防御压力过大的问题。〔7〕这可能是在荒干河谷设置新郡分担雁门郡防御压力的原因。
此役之后匈奴不再轻易南下,汉军开始主动进攻。元光六年(前129),武帝派卫青、公孙敖、李广和公孙贺四将各领万骑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出击。除卫青略有小胜外,其余三路得不偿失,李广更是兵败被俘,冒险逃走。此次出击失败的主因是兵力分散,缺乏统一的指挥,被匈奴各个击破。元朔元年(前128),匈奴开始反击,先进攻辽西,杀太守。又侵入雁门,杀略数千人。再攻入渔阳,击败太守率领的千余人,包围将军韩安国。〔8〕汉廷为了反击,派卫青领三万人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斩杀数千人,这一次汉王朝将边境军队置于统一领导下。卫青此次从雁门出击应该走的是荒干河谷,其驻扎地应该也在雁门郡与云中郡交界处,这便于他明年出云中郡向西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再一次入侵上谷、渔阳。汉廷派卫青帅六将军出云中向西攻打到高阙塞,占领河南地,直至陇西,在今河套地区西部设立了朔方郡。《汉书·武帝纪》记载则是设置了朔方、五原两郡。这是汉王朝将国防力量向西延伸的一个重大举措。朔方、五原二郡设立保证了上郡和北地郡的安全,如果匈奴侵入这两个郡,汉军可以西出,断其后路。元朔三年(前126)夏,匈奴数万骑侵入代郡,杀太守恭友,劫掠千余人。秋季又攻雁门,斩杀千余人。汉廷为了加强北部防守,命令苏建修筑朔方城。这几场战争反映出汉军改变了原有的作战理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四路进攻失败使汉廷开始调整行军制度,以后汉军行动尽可能集中兵力,将各军置于统一领导下。汉朝集中兵力与匈奴作战,不但给予匈奴有效打击,还收复了河南地,取得了较大战果,这更坚定了汉廷采用集中大兵团作战的战术。同时,在边境集结大军需要稳固的战略后方,调整原有边郡建置就被汉廷提上了日程。
定襄郡大概设置于元朔三年到四年春。元朔四年(前125),史籍中第一次出现“定襄郡”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记载这年夏天,匈奴侵入代、定襄、上郡等地。《史记·卫将军列传》记载匈奴此次向每个郡都派三万人,右贤王因失去河南地而出兵攻击朔方。虽然战果不大,但匈奴此次多方向联合出击的目的应是为了截断汉军新取得的土地与雁门郡的联系,孤立并消灭河南地的汉军。定襄郡的设置使雁门郡摆脱了长期遭受匈奴入侵的困扰,此后关于匈奴侵入雁门的记载都在东侧代郡方向。同时,汉武帝还对北部边郡建置进行了大幅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河郡设置于元朔四年。这些调整使匈奴在战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元朔五年(前124)春,汉军十余万在卫青带领下自朔方、高阙出击,重创右贤王。同年秋,匈奴攻代郡,杀都尉朱英。汉军已经在定襄郡周边做好了反击准备。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卫青带领十余万人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回师定襄、云中、雁门休整。夏季再次出击,结果“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斩首虏万余人。”汉军损失也较大,将领赵信被迫投降。苏建军遭围攻,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十余万汉军在定襄一带休整,可见汉北部边郡的后勤能力得到了极大加强。这些军事行动彻底扭转了匈奴“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的局面,汉骑可不日至单于庭。赵信投降匈奴后,劝说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就说明战争主动权易手。赵信深知双方实力差距,与其留在南面处于被动,不如将主力北撤以拉长汉军的补给线,创造更多战机,这个建议影响了此后的汉匈战争。元狩四年(前119),汉王朝派给卫青、霍去病各五万骑,步兵数十万,从定襄和代郡出击。汉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捕捉并打击单于的主力。史籍中提到一开始安排霍去病出定襄以挡单于,只是误以为单于转移到了东面才改变命令,让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最后是自定襄出击的卫青部抓住并击败单于主力,可见定襄郡战略意义之所在。此战以后,汉匈双方国力都因长期战争损耗严重,无力再组织大的军事行动。以后双方争夺焦点向西北转移,汉朝北部威胁顿减,定襄郡的战略地位随之下降。
三、定襄郡设置的政治地理基础
从《汉书·地理志》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相关图幅中可看出,与同期其他边郡相比,定襄郡的特点是面积小,所辖县分布较密集。在人口方面,《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定襄郡户数38559户,口数为163144 人,与汉末雁门郡的73138 户、293454 人相比,定襄郡人口密度要高很多。〔9〕上述信息从侧面说明这一带农业生产条件不错,具备成为战略基地的潜力。《汉书》中记载定襄郡有十二县,现有九个县位置可以大致确定,其中七个县发掘出了城址。郡内县治分布很不平衡,北部近边地区县治集中,南部近黄河一带次之,中部几乎没有县治。这个分布态势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该郡南北两侧都是河谷平原,中部为山地。中部山地将郡内主干道分成两条,这两条干道起点都在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道沿着浑河河谷直达今清水河县城一带,联通南部三县(骆、桐过、武成)。北线先沿浑河河谷北上,出大青山南到达定襄郡(今和林格尔西北),然后向西直通朔方郡一带。北线在秦朝时就是沟通雁门与云中两郡的驰道,当是汉王朝自内地向这一带输送补给的主要通道,定襄郡的治所和西部都尉分别设置在这条道路上的成乐县和武进县。成乐县大致处于郡中央,便于沟通郡内各县,且靠近白渠水,农业条件较好,作为郡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定襄郡的东部都尉(驻扎在武要县)、中部都尉(驻扎在武皋县)与云中郡东部都尉(驻扎在陶林县)都驻扎在荒干水河谷,相距不远,目的是为了控制河谷,阻敌南下。
定襄郡的析置是西汉战略调整在行政区划上的体现。汉朝在主要交战地带设置新郡,是根据新的战争形势需要对被动防御型边郡体系的一大调整。原有的边郡体系的特点正如周振鹤概括的,都是“南北向长,东西向窄”,拥有较大纵深,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翻看以往汉匈战争史就会发现,中原政权虽多以防御为主,但也有采用大兵团出击的记载,赵将李牧和秦将蒙恬都是先在边境集结大军,再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尽管史料记载简略,但可以明确这两员名将在战前都做了长期的后勤准备工作。汉武帝君臣在前期战争受挫以后汲取经验,变分散出击为大兵团作战模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这种作战模式对边郡的后勤补给能力是一个考验,加强对交通要道附近的补给能力迫在眉睫。在这种地方设置新的郡县可以很好地在当地集中军事和行政资源,进而影响整个战局,以上是定襄郡设置原因的推测。
定襄郡设置后,卫青等人率领大军以此为基地不断向北打击匈奴的大本营,迫使单于不得不北撤,彻底扫清了这一带的威胁。以后再派霍去病在河西,李广等人在右北平不断打击匈奴两翼,在汉匈战争中逐步掌握主导权。
定襄郡设置之初匈奴仍频繁活动于上郡一带,秦代修建的直道难以发挥联接关中与河套的作用,河套诸郡与东部各郡的联系变得十分重要。确保定襄郡的安全就可以保障内地与定襄郡及其西部诸郡的联系。定襄郡的得失关乎整个北境防御体系的安危,关乎打击匈奴的战略能否顺利推行。为此,汉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定襄郡的防御性能,传统史料和考古资料都可以说明。史料记载汉廷在郡北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包括修缮长城,设置各种亭障等。定襄和云中二郡在荒干河谷密集分布许多县城,两个郡有四名都尉驻扎在这些县城中也可以反映这条河谷的战略价值和汉朝的控制力度。定襄郡治成乐县临近云中郡,能加强与云中郡的联系。从考古成果看,呼和浩特东北塔布秃村遗址可能是武泉县,该城有“回”字形的两道城墙。美岱古城同样有内外两城,可能为安陶县。卓资县三道营遗址当为武要县,有东西两城,城周设有马面,东、南两面有城门,该县位于最北侧,城门位置表明西、北两面是主要防御方向。陶卜齐古城当为武皋县,城墙外也有马面。以上大致可以看出定襄郡属县军事防御功能是非常突出的。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定襄郡完美发挥出了区域的战略优势,但为确保该郡军事职能的发挥消耗了汉王朝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定襄郡属于司马迁划分的龙门、碣石以北的畜牧区,这里靠近黄河及其支流,土壤肥沃,但气候严寒,作物生长期长。汉武帝向这一带移民,大面积开垦土地,只在短期有效,长期的大规模农业开发会严重危害这一带生态环境。该郡常有军队驻扎,庞大的非生产型人口对地方而言是巨大的负担。单是粮食需求恐怕已经是附近几个贫瘠的边郡所无法提供的,更不用提作战所需要的武器、服装等必需物资了。这一巨大的物资缺口只能靠内地填补,经济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是主要的物资输出地。调运路线还要经过山西高原,这里交通条件不算很好,这就又增大了物资的消耗。此外汉王朝还需要供给其他几个方向的军队作战。以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给内地的人民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王朝在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同时也耗尽了自己的国力。
此后汉匈战争的战场西移,定襄郡不再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在国防体系中的作用下降。东汉初年匈奴南进,汉廷一度废弃包括定襄郡在内的沿边八郡。虽在南匈奴内附以后各郡又重新恢复建置,但因前期过度开发及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一地区的人口已无法恢复到西汉时期的规模。〔10〕南匈奴依附后,边疆战略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汉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郡县调整。定襄郡北部各县尽数划给了云中郡,取雁门郡治善无与中陵县和旧定襄郡南部的骆、桐过、武成三县组成新定襄郡,以善无为新郡治所。新定襄郡基本囊括今山西浑河流域,从边郡变成了内地郡。云中郡完全拥有了荒干水和白渠水,但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失,定襄郡属县的密度也远不如西汉。东汉政府也未对这里进行经营,失去物质基础导致本区军事职能无法发挥,这也是两汉与北方游牧民族攻守形势的转化在行政区划方面的体现。
四、结论
秦汉时期郡县制的沿革变化情况是研究中国行政区划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关于西汉的政区变迁,周振鹤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因史料本身匮乏,部分郡的沿革变化情况难以复原,需要研究者“适当运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缺环”。定襄郡地处交通要冲,多次成为汉匈双方交战的战场。其建置情况尽管没有太多史料可以直接证明,但通过梳理相关史料,也能找到一些线索。“定襄郡”这个名称首次出现于元朔四年,正处汉武帝对匈奴大举用兵之际,二者当存在一定的联系。定襄郡出现以后,史料中雁门和云中二郡并列叙述的情况消失,出现定襄与云中二郡并列的情况,可以推断出定襄郡当从雁门郡分出。关于开头提到的高帝十一年诏书的解读,周振鹤的第二个解读更显合理。刘邦为了分担代国的军事压力,在这一年将云中郡收归中央,又不想由中央独自承担这一地区的防御任务,就采取将其与雁门郡的边界西移,使二郡共同控制荒干河谷,达到与代国共同面对匈奴威胁的目的。关于定襄郡的职能,周振鹤已经注意到其与其他北部边郡一样的防御功能,而通过分析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的特点,也可以挖掘定襄郡在汉军作战模式由防御调整为进攻以后发挥的职能。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目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消灭敌军,占领敌人的国土和征服敌人的意志.。定襄郡距匈奴的核心统治地阴山以北不远,汉朝在这一带集结大军,很容易实现上述目的。汉匈战争西移后,定襄郡战略意义下降,史料中提及该郡的次数也大幅降低。到东汉时因国力衰弱,两次废弃包括定襄在内的边郡,迁走当地的居民。这使后人更难了解这些边郡的具体情况,唐人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甚至将河套诸郡的位置定在了今天的陕北一带就是一例。
【注释】
〔1〕《史记·周勃列传》作“霍人”。
〔2〕武泉县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
〔3〕《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作“离石”,周勃、灌婴列传都作“硰石”。按西汉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在晋阳西且距离较远。硰石,据张守节《正义》云“在楼烦县西北”,结合战争形势可知此处应当是硰石。
〔4〕陈豨为何人所斩存疑。《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杀陈豨者为樊哙军卒,韩王信为柴武所斩。《史记·樊哙列传》则记载樊哙军卒斩的是韩王信。《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陈豨为周勃军斩。按《樊哙传》错误较多,似乎将樊哙平定韩王信之乱时的行军路线与平定陈豨时的行军路线混为一谈。《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樊哙军斩陈豨,地点却又在当城。
〔5〕这次匈奴两支部队人数都有较具体可信的数字,可能从侧面反映中行说对匈奴的贡献。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6〕也可能是匈奴在这一时期只是不靠近雁门郡治所善无,也不能排除史家夸大之语。《汉书·郅都传》明确记载他死于汉景帝时,此时距离景帝去世只剩一年半,所以郅都担任雁门郡太守时间不长。
〔7〕《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夏记载:“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可能就是受这次单于入侵的影响。
〔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将此事记载于元朔二年,《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窦田灌韩传》中都标明在元朔元年。班固可能也发现了《史记》中的这个问题,所以在《卫青霍去病传》中未提及此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关于元朔元年和二年匈奴入侵的记载有很多混乱之处,故以别的列传为准。
〔9〕据葛剑雄推算,定襄郡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55 人,雁门郡每平方公里为12.05 人。
〔10〕人口大幅减少,也是因为游牧民族大规模移居此地,挤占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内迁的匈奴有自己的组织,东汉政府难以获得准确的人口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