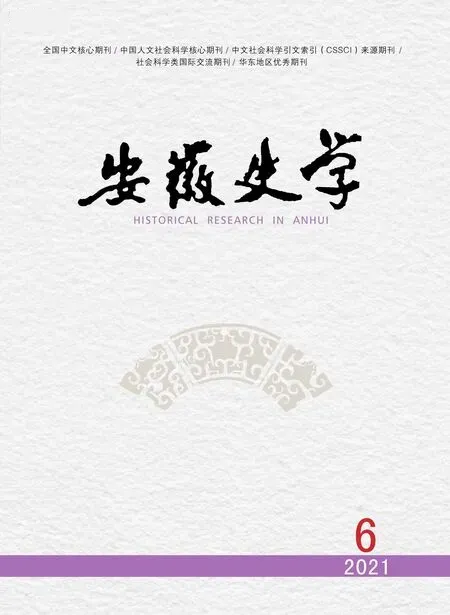中法越南交涉时期中国的“瓯脱”筹议
易 锐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9世纪后期,随着藩属走向解体,中国边疆出现了屏藩丧失、强敌逼处的空前变局。受此变局刺激,一些国人积极谋求因应之策。此中相关史实,早为学界熟知。至今少有学者关注的是,面对边疆之新情势,晚清君臣曾纷纷筹议“瓯脱”古法(1)“瓯脱”一词,较早见于《史记·匈奴传》:“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后人讨论“瓯脱”,多会溯源至此。关于“瓯脱”古义,学界多有争议。本文所论“瓯脱”为晚清语境中的概念,系指国界之间的缓冲地带。前人在相关研究中也运用过一些近似概念来表述有关隔阂或缓冲功能的区域,如“缓冲地带”“隔离地带”“中立地带”“分界保护”等。相比之下,“瓯脱”有如下特点:1.处于国界之间;2.任何国家不对其享有管辖权;3.一般为不居住人的“弃地”。,试图以国界之间设立缓冲地带的方式,来实现隔阂强邻、保疆固圉之目标。这些反复而曲折的“瓯脱”之议,深刻反映出时人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挽救边疆危局的努力,构成晚清疆土观念走向近代过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一环。据笔者观察,晚清“瓯脱”之议主要出现在光绪前中期的界务交涉中,其中以中法越南交涉时期筹议“瓯脱”之法的人数最众、时间最长、影响最巨。本文将深入考察中法越南交涉中清朝“瓯脱”之议的缘起及其发展演变,进而揭示这一阶段中国疆土观念变化的特征与趋向。(2)对此问题有所探讨的论著主要有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明:《中法勘界斗争与北部湾海域划界》,《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吴智刚:《中法战争前后清廷的中越近边“区画”及其流变》,《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一、曾纪泽与中法“瓯脱”之议兴起
1882年,法国进攻越南北圻(3)当时,越南分为南圻、中圻、北圻三部。北圻为宁平省以北地区,又称“东京”,其首府为河内。北圻地图,可参见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70—271页。,引起中国重视。清朝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积极关注着越南局势,自该年起,多次对法国阐发“隔阂”理论。中法越南交涉时期的“瓯脱”之议,即滥觞于此。
5月10日,曾纪泽就越南问题与法国外长佛来希尼(Charles de Freycinet)会谈,谓:“中国愿与越南为邻,不愿与大国连界,与大国连界,恐生事端,两不相宜。查泰西各国,公立比利时、瑞士等国之意,原为隔阂大国,以杜争端。越南介于中国地方与法国属地之间,其势相同,不可废之。”(4)《曾纪泽向总署抄送与法外长会谈节略及照会》(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1页。此为曾氏对于“隔阂”理论的较早阐述。12月13日,曾对法再申此论。(5)《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与杜格来问答节略》(光绪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247页。曾氏之意,是希望援引西方以小国隔阂大国的惯例,来达到存越固圉之目的。
是年底,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使宝海(Albert Bourée)议定草案,拟由中法对北圻“分界保护”。(6)关于“分界保护”的详细讨论,参见吴智刚:《中法战争前后清廷的中越近边“区画”及其流变》,《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 111—114 页。1883年2月,态度激进的茹费理(Jules Ferry)上台组阁,否定了李宝协定。6月21日,曾纪泽与茹会谈。他在继续阐发“隔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深不愿与西洋大国为邻,故法欲保护越南,则须与中国分护,使越南作为间隔之国”。茹则表示,法“非欲并土地”,与华无须间隔。(7)《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与茹费理晤谈节略》(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411页。
9月15日,法国外长沙梅拉库(Paul-Armand Challemel-Lacour)在节略中提出:“自沿海某处起至红江上游之保胜止,就纬线之二十一度及二十二度之间,定一界限,凡在此界与北面中国边界中间之地”,中法“概不占据,亦不施其权力”。此地“吏治之事,仍归越南官员办理,不许在此建筑炮台”。(8)《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送法外部划界通商节略》(光绪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655页。这一“中立区”(或称为“中立地带”)方案,与曾氏“隔阂”理论形同实异。曾氏之目的是为保存越南而维护中国权利;法国之意图则在于排除中国而独自控制越南。对此,曾纪泽有着清晰洞察,他于18日会见茹费理,指出清政府“愿意‘一个良好的国境加上一个保护地带’而不愿意一个中立地带”。(9)《外交部记录 茹费理与曾侯的会谈》(1883年9月18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9、191页。
27日,曾与茹费理会谈,进一步阐明清政府态度。其间,茹云:“如贵爵所指方向,则是中国欲得东京全地矣。”曾曰:“中国吩咐大致如此。据本爵私意,或者稍有变通,即将厂平关左右作为瓯脱之地,中国允许不占,亦是通融之法。”(10)《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送致法外部照会及辩论节略》(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675、677页。在笔者所见文献中,这是曾氏首次向法方提出“瓯脱”之法。可见,曾意识到“中立区”归越管理有名无实,故倾向于划定国界而获地利。不过,他依然强调中法“隔阂”的必要,因而提出设立“瓯脱之地”。其时,曾氏方案为北圻全归中国,而“瓯脱”处于南、北圻之间,以北纬20度为限;法国方案则是中国退出北圻,中立区仅限于中国南境近边,亦即北圻的东北一带。曾氏之要求,与越南局势变化和总署指示直接相关。自8月25日《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深受刺激,情绪普遍激昂,多主北圻归华。(11)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13—114页。由于双方要求相距甚远,故无法谈拢。
在国内,李鸿章与法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的谈判也同时展开。9月25日,脱向李提出:“若由北圻海岸斜趋至保胜,定为瓯脱之地,界画可略宽些;若分定边界由中国自行主持,应在滇、粤本来边境之外,不能过宽,断无允至河内之理。”(12)《附 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需注意的是,其中“瓯脱”之表述,并非法方对中国古代概念的借用,而是当时中方节略对法方言论的转译。此处“瓯脱”,与9月15日法方向曾纪泽提议的“中立区”并无二致,而与中国传统意义上作为“弃地”的“瓯脱”相差较远。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此时尚未普及“中立区”之类的近代概念,而中国古代固有的“瓯脱”概念与之有一定相似之处,故清人以后者来指称前者。此类在表述缓冲地带方案时而出现的名异实同与名同实异的情况,在中法越南交涉中较为常见。
法方方案,同样遭到李氏反对:“中立区是不可能中立的。”(13)《“伏尔达”号舰长福禄诺致海军及殖民地部长》(1883年12月6日于长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5册,第445页。他坚持以河内为限“分界保护”,并强调“中国众人意见拟将北圻全归中国”。(14)《附 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273页。显然,李认为“分界保护”更具实质意义。然而,一个月前法国已借《顺化条约》取得对越保护权,此时断难接受前已否定的“分界保护”方案。因谈判无果,一个月后脱氏离开中国。
二、奕譞等人对“瓯脱”方案的态度变化
曾、李两头的谈判皆陷入僵局之后,法国政府仍冀望中国接受其“瓯脱”方案。11月21日,茹费理语曾纪泽曰:“从前本国所开办法,甚为允当,所谓议定瓯脱是也。惜乎中国未肯允许。另开办法咨送前来,而本国亦难就中国之议。据我看来,若能照本国原拟办法,作为商议之根,本国情愿就商。”(15)《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呈致法外部照会》(光绪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第791页。
11月29日,即位不久的越南皇帝阮福升为权臣杀害,法国态度转趋缓和。12月中旬,总署电李鸿章:“劼刚电:越弑新王。茹松口不提北宁,不至保胜,言以山西作瓯脱。日本吴启泰云系得十三日来电:越杀新王拒法。望确访电复。”(16)《附 与译署来电》(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亥正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05页。李复称:“越弑新王,他处未报,俟有确信奉闻。议以山西作瓯脱,似宜复准。”(17)《复译署》(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亥正),《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05页。尽管他尚不确定此事的准确性,但认为应接受以山西为“瓯脱”的提议。
这一时期,醇亲王奕譞的相关言论颇值得注意。自1883年7月慈禧太后令其会同军机处与总署办理法越事宜后,奕譞常在书信中就越南问题与军机大臣翁同龢商讨。12月,奕譞得知越弑新王后,函翁同龢曰:“适得抄件,局势一变,至此未悉诸公商及通盘否?愚见若系全越拒法,则瓯脱之议我不必轻诺,致受其欺,转以我借口,坐收南圻之利也。”(18)《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十六》(无年月),《朴园越议》第1册,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此时,奕譞考虑越南局势变化或许对中国有利,但担心中国答应法方“瓯脱”之议陷入被动,遂主张暂观时局而不轻诺。
不过,奕譞的看法很快改变。12月19日,他致翁函曰:“法屡添兵,越无的耗,岑之难抵彼都亦犹张耳。再不能力支,北圻全局涣矣。……瓯脱出自茹口,非我因败自减之价。苟设法留为后图,彼则驷不及舌,我亦不伤体面,且有戢兵保泰之大度以示各夷。……凡此下策,原皆违心之论,倘越自翻局,岑、刘全捷,自当别筹变计也。”(19)《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三十一》(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朴园越议》第1册,第78—79页。经权衡北圻战事形势,奕譞意识到有必要将“瓯脱”之议留作下策。
23日,奕譞对“瓯脱”方案的态度更趋积极,其复翁函曰:“瓯脱先不理,后议及,原系为势所迫。纵彼以此缓我,我则不妨故作诚信,告以此节关系紧要,迟迟答复者,因廷议数日,佥谓如法撤兵,可以商办,看其如何。倘彼彷徨不决,直可遍告各国:现有此议,我中国悯华洋生灵物力,已勉准其请云云。……兰太笃实,骤说必不入,屏人婉商,或冀省悟,此则非宏才不办也。”(20)《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三十二》(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朴园越议》第1册,第81—82页。“兰太笃实”一语中,“兰”应为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字“兰生”之略。奕譞觉得以李之性格,断难接受“瓯脱”之议,故须请人与之婉商。
24日,奕譞致函翁同龢:“适接公函,立即修复,明早当供众览矣。复内以瓯脱、清野、民团再三陈说。张既赴津,可否以鄙见向彼商,或望有济。合肥以息事为主,未必大作门面也。”(21)《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三十三》(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朴园越议》第1册,第84页。“张既赴津”中的“张”,系指该月甫任总署大臣的张佩纶。奕譞之意,是希望张能去天津向李鸿章转达包括“瓯脱”在内的越事主张。这一点,也得到慈禧授意。(22)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4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831页。至此,奕譞已然成为朝中力主“瓯脱”方案者。不过,因北圻战事持续展开,中法一时暂无重回谈判之条件。其后奕譞等人对越事的关注,也主要转移到战局方面。
三、中法订约与朝野“瓯脱”呼声的起伏
自1883年12月至次年4月,中国在北圻战场节节败退,清廷渐有对法妥协之意。1884年4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Francois Ernest Fournier)开始议和,决定“画界分守”。5月3日,《申报》载文发表意见:“事已至此,所画之界相去不远,中间必无瓯脱之地,暂时相安,能保日后无越畔之争乎?”(23)《法人心服刘军说》,《申报》1884年5月3日,第1版。即认为中法之间无“瓯脱”,日后终存隐患。5月11日,《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具体如何议定界务是其后需重点讨论的问题。6月26日,军机处上奏:“仍以红江为界,最为上策。否则,亦宜以四月十五日以前驻兵之地为界,或于关外空出若干之地作为瓯脱,彼此均不侵占亦可。”(24)《军机处奏简明条约界字不明拟令李鸿章与法使力为辩论片》(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第390页。在此,军机处以红河为界作上策,同时提出以关外之地为“瓯脱”的替换方案。这种方案,与奕譞之主张不无关系。盖该年4月8日“甲申易枢”之后,奕譞取代恭亲王奕訢成为军机处实际掌权者,而在上年12月,他曾积极主张“瓯脱”之法。从后文来看,清廷对“瓯脱”之议予以重视和支持,亦与之相关。
6月23日中法发生北黎冲突后,战事再起。7月19日,诏令曾国荃与法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议约,指示“应于关外留出空地,作为瓯脱”。(25)《旨授曾国荃议和机宜电》(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七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5页。不过,随着战场捷报频传,清廷态度很快转趋强硬,不再强调“瓯脱”问题,而几乎要回到《顺化条约》以前的状况去。(26)《军机处预拟与法议约八条》(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6册,第102页。
北黎冲突之后的大半年里,中法在中国东南海疆和越南北圻近边展开战事。1885年3月,清军取得镇南关——凉山大捷,由此引发法国政潮,茹费理内阁随之倒台。不过,法方并未转变其对华战争政策。清廷则决定乘胜即收,与法议和。4月4日草约订立后,中国官员请设“瓯脱”之声渐强。
4月16日,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奏:“东则谅山、高平、广安,西则保胜,凡与我界近之地,宜作为瓯脱。虽法保护,仍不得屯兵筑炮台,以免离近生衅。”(27)《张之洞致总署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张之洞档》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6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2页。此奏折中,张氏主要从避免中法冲突的角度阐述设立“瓯脱”的必要。20日,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亦奏请筹设“瓯脱”,立论与张类同。(28)《广西护抚李秉衡请在北越设瓯脱致总署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丑刻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第633页。同日,张在电奏中,又据条约论证设立“瓯脱”的合法性:津约第一条“既有均应字样,自是中、法均可同任保护。……洞前奏请作为瓯脱,禁彼勿屯兵筑炮台,正符前约”。(29)《津约第一条宜改 致总署》(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亥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随后,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对游勇问题的建议,使张愈感设立“瓯脱”之必要。张在5月2日电奏中,将唐议上陈,谓“此诚善策,不惟栖流,兼可捍边兴利,越官尚易谕遵。”(30)《张之洞致龙州李护院(李秉衡)岑宫保(岑毓英)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张之洞档》26,第436—437页。此时,安置边外游勇,已成张氏请设“瓯脱”的主要理由之一。
5月5日,上谕正式同意筹议“瓯脱”,惟强调不能以“瓯脱”安插边外游勇。(31)《致南宁岑宫保》(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15页。有此上谕,张之洞等人对设立“瓯脱”之期望更加强烈。5月10日,唐景崧电张,再申设立“瓯脱”之迫切:“谅山、牧马不作为瓯脱,此后沿边竟须长驻兵,主客军酌留几何?”(32)古辛整理:《唐景崧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3页。14日,张电总署:“道远运艰,机失势钝,再进不易,不借兵威,难争瓯脱,我务诚信,彼专凶狡;违约进兵,伺隙屠杀,要挟难量。”(33)《两广总督张之洞请禁法进踞害民致总署电》(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辰刻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第669页。
不过,随着对谈判进程的了解,张之洞渐感“瓯脱”纳入条约之望渺茫。19日,张收到李鸿章电报:“详约有眉目,未定。瓯脱争数次,不允。”(34)《李中堂来电》(光绪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14页。6月9日,《中法新约》签订,该约规定仅可对中越旧界稍作改正,“瓯脱”之议终无体现。(35)《附 中法约款十条》,《李鸿章全集》第11册,第92页。
四、勘界前夕国内“瓯脱”筹议的高涨与顿挫
在过去数年,廷臣疆吏、驻外使节、报刊舆论,皆不乏积极主张保藩固圉与“瓯脱”隔阂者。即使和议已成,上谕已下,其内心断难立即甘心接受藩属丧失和强邻逼处的事实。随着补救之法的酝酿和法越局势的变化,“瓯脱”之议在中法勘界前夕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
(一)“瓯脱”之议的高涨
1885年下半年,出使英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呈其与法人巴吕(Pallu)密谈节略,建议设立“瓯脱”:“边界最要之处,在于谅山、保胜两路。按谅山地势在分水岭之东,本宜划归粤界,第津约既有东京归法之说,若欲以谅山归华,须待辩论。分界之时,若能于两界之间留隙地若干里以为瓯脱,可免争端,统在两国分界官员斟酌办理。”(36)《出使英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呈与巴吕密谈节略》(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第768页。随后,使法大臣许景澄亦有类似建议。(37)《使法许景澄致总署越南勘界请与法议宽留瓯脱以杜争衅函 附译报》(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到),《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54页。
上述建议,对清廷产生明显影响。11月8日,清廷电谕勘界大臣周德润、邓承修等人:“若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以免争端,最属相宜。”(38)《谕周德润邓承修着会同各督抚妥慎分勘越界电》(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53页。17日又谕张之洞等人:“前经总理衙门呈递许景澄信函,所陈宽留瓯脱以杜后来争衅等语,与前次谕饬办法正相吻合。目前与法使会议分界事宜,必应博采众说,以资辩论。岑毓英拟请开导法使,令其退还北圻数省,于河内、海阳地方通商等语。周德润、邓承修等与法使晤谈时,不妨姑持此论,以为抵制。总之,分界一事有关大局,周德润等务当详度地势,设法辩论,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39)《谕张之洞周德润邓承修中法界务宜妥慎筹办电》(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59页。此时清廷不仅主张力争“瓯脱”,甚至连岑毓英令还数省之请也予以一定认同。
自1885年11月至年底,是中法战争前后清廷支持“瓯脱”之议最为坚定的时期。其间,疆臣边吏、勘界代表、驻外使节纷纷响应,但是彼此之间态度、方案、目标却多有不同,反映出各方疆土观念的差异。
(二)纷繁的“瓯脱”歧见
张之洞对于力争“瓯脱”的上谕,态度颇为积极,提出慑以兵威与议界从缓的对策。他于11月30电奏:“归谅、瓯脱两节诚要”,“恐非口舌所能为力,惟有盛我兵威,隐相慑制”。(40)《附 粤督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614页。12月7日,又因越民抗法电奏:“议界宜缓,待彼迄不能定,然后以瓯脱为排解之策,劝留数省以处越团游勇。”(41)《两广总督张之洞报越抗法团民四起请缓议界电》(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第772页。从随后信函可知,其方案大抵是拓界百余里至谅山,以南数百里设“瓯脱”,且中国可在边界“屯兵筑垒”。(42)《致龙州邓钦差、李护抚台》(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发),《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37页。他强调,其目的非图越土地,而是为固我疆圉与安插游勇:“南关如门,谅北如栅,聊设斥堠足矣。即屯数营,出关四十里,路非甚远,运非甚艰,饷非甚多,可固疆圉,费亦何辞。即不屯营,亦可其权在我。果使法许瓯脱,关外纵横甚广,游勇开矿垦山,足可自给,团结扼守,为我外卫,患不多耳,岂忧安插无地乎?”(43)《致龙州邓钦差、李护抚台》(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38页。张之所以对“瓯脱”之议较有信心,除认为有条约依据外,与他所掌握的情报也不无关系。(44)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云贵总督岑毓英要求则颇激进,提出“瓯脱”宜宽至千余里。12月15日,岑上奏曰:“《史记·匈奴传》云:‘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盖瓯脱留地必宽,始便屯守,若仅数十里或百余里,一旦有警,朝发夕至,防不及防。……臣毓英前奏请旨敕总理衙门开导法使,退出北圻宣光、兴化、太原、高平、谅山各省,只在河内、海阳地面设埠通商,中间千有余里,中法彼此不居,还诸越南,亦正窃取瓯脱之说。”(45)《商办滇边界务情形折》(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黄振南、白耀天标点:《岑毓英集》,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尽管岑奏称其主张与清廷“瓯脱”谋划暗合,但内心明显更希望法国能退还数省以安游民并存越祀:“中越疆土毗连,其间险隘之区,多在越地。越本属国,作我屏藩,寄之要区,原属守在四夷之义。今越已入于法,循故辙则失险,分越地则悖名。英议以五省还越,庶几屏藩不撤,而义民游勇皆有归束,中外均安,不第可存越祀已也。”(46)《议勘滇越边境奏稿》,孙学雷、刘家平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2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8613—8614、8610—8611页。
负责滇越勘界的周德润,亦有以“瓯脱”来安插流民的想法:“自古以空虚之地为瓯脱,今以聚处之地为瓯脱。欲弃地,将弃民乎?惟有营田之法,募瓯脱之丁壮,耕我边陲,分里筑室以居……如瓯脱可成,即创置营田以招流民,而尽地利。所以整军旅者在此,省转输者在此,洵保边实塞足国安民之上策也。”(47)《议勘滇越边境奏稿》,孙学雷、刘家平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2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8613—8614、8610—8611页。在周看来,设立“瓯脱”正合条约之义,他致函总署称:“如舍旧界而议瓯脱,虽变通新约,亦即新约所谓稍有改正者也。以瓯脱为改正,两国公商原非悖约,但彼必请示本国,倘因势转圜,实朝廷百世之利。”(48)《勘界大臣周德润向总署陈报北圻局势并论界务商务函》(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第780页。
负责桂越勘界事宜的邓承修和李秉衡也较积极。邓自11月底与李连日商晤,“佥谓非两界之间广留隙地,则不足以限彼族而固边防”。12月3日奉到筹办“瓯脱”上谕后,复称“揆时度势,事不宜迟”,并电请总署频催法使。(49)《办理勘界事宜邓承修奏折》(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7册,第22页。但相比之下,二人态度不及岑毓英强硬。12月7日,邓、李明言:“岑拥重兵,攻宣光一隅,旬月不能下。今约定欲以口舌,令还数省,议必无成,徒贻口实,食言取侮,转伤国体。”(50)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有别于岑氏“瓯脱”方案,邓、李主张的“瓯脱”仅宽数十里。(5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5页。同时,二人反对张之洞所说的于“瓯脱”边界屯兵筑垒,称“瓯脱则民无所属,属越与法无异,尚费经营,惟例不屯兵筑垒,暂弭边衅”。(52)《致广州制台张宪台电》(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09页。
这一时期,李鸿章对于“瓯脱”之议态度始终冷淡。11月30日,李电邓承修:“或谓谅山宜归粤界,宽留瓯脱,此前所议而未成者,公能设法争否?”(53)《寄龙州邓钦差》(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已刻),《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614页。邓复以不惜以决裂力争,李则表示:“乞酌议,即不合必不致决裂。”(54)《寄龙州邓钦差》(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637页。与之类似,随邓办理勘界事宜的直隶候补道李兴锐,也不甚看好“瓯脱”之议。12月13日,其日记载:“午后,连接张香帅电信,意在力争北圻,广筹瓯脱,然恐不能。”17日,又载:“香帅两电论争界,颇存意见,然不中肯。此公功名得意,早通经,未能制用,亦吾儒之病也。”(55)《李兴锐日记》,第157、158页。
(三)“瓯脱”谋划的终止
清廷虽主画宽“瓯脱”,但唯恐与法开衅,立场并不坚定。1886年1月8日,清廷因越南兵势稍振,“事机自较顺手”,而据约“展宽瓯脱一层亦属有词可措”,乃谕勘界大臣竭力办理。(56)《勘界大臣邓承修奏行抵桂边日期附陈关隘大略情形折》,《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87—1288页。不过,其态度很快因法方质询而转变。17日,上谕曰:“我若逾约而争,彼或借口罢议退去,则衅端终归未了。该大臣等守定‘改正’二字辩论,甚是。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借端生衅为主。”(57)《寄龙州邓钦差李护抚》(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646页。
不过,地方督抚和勘界大臣随后仍在积极谋划。如张之洞旋以其情报电请总署代奏:法国众多议员和提督杜布来皆主张放弃北圻,“果如所云,是法弃北圻与否,全在商界之迟速。前商务妄求,已经钧署驳拒,而界务又不予速竣。三个月后,彼饷匮力绌,必当变计,瓯脱诸说,庶乎可行”。(58)《粤督张之洞致总署巴黎函法议员愿弃北圻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到),《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93页。周德润等人则于1月20日奏称:“界务关系匪轻。法使到时,臣等惟有加意联络,设法论辩,恪遵圣训,以会典、通志为体,瓯脱为用,务期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59)《会办中越勘界事宜周德润等奏折》(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7册,第34页。
随后,法方指责中国违约,并以停止勘界相威胁,清廷态度进一步变化。1月底,总署电邓承修:“此事应遵迭次电旨,按约速了。若在谅山以北择地划界,与约尚不相背,勿过争执,致令借口违约,竟至罢议,别生枝节。”(60)《附 译署致邓钦使》(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653页。2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即日约会浦使,先按原界详悉勘明,以后稍有改正,再行妥商续办,如今春赶办不及,缓至秋末再勘。所有现议多划之界,均作罢论。云南、广东一律遵旨按约办理,不得违误。”(61)《寄粤督抚张倪并邓钦差李护抚周钦差岑督》(光绪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第22册,第5页。这一上谕,意味着清廷态度的重大转变。此后,清廷基本放弃了“瓯脱”方案,转而一再饬令勘界大臣勘定原界。在此情形下,相关官员也不得不遵旨而行。次年6月,中法签订《续议界务专条》,中越勘界告一段落。
结 语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清朝的“瓯脱”筹议经历了颇为曲折反复的演变过程。1883年,受曾纪泽一再阐发的“隔阂”理论影响,法国顺水推舟提出有名无实的“瓯脱”方案。法国方案虽遭中方反对,但因越南局势变化,旋为醇亲王等人所重视。1884年李福协定签订前后,朝野请设“瓯脱”之声渐起。至1885年《中法新约》议订时期,清廷亦开始积极谋划“瓯脱”。中法勘界前夕,国内“瓯脱”呼声再次高涨,一时盛况空前。然而由于法方强烈反对,清朝“瓯脱”之议最终被迫于1886年停息。这一历史过程,充分反映出晚清藩属丧失与强邻逼处的新情势下,时人以传统古法来隔阂强邻、保疆固圉的迫切心理和艰辛努力。从中可见,时至19世纪后期,国人对边界、边防以及主权的看法,仍与近代领土理念存在不小差异。
当然,清朝内部对于“瓯脱”之法的认知与态度之分歧也不容忽视。与张之洞等人积极倡呼“瓯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鸿章始终对此态度消极,而寻求更具实际意义的分界保护或边外拓界。不仅如此,“瓯脱”倡议者心中的方案,也颇有不同。如张之洞提出在“瓯脱”边界屯兵筑垒,邓承修则以其不合“瓯脱”本义而极力反对;与他人方案中“瓯脱”范围较为狭窄不同,岑毓英则主张“瓯脱”宜宽至千余里。这说明,持“瓯脱”之论者,很大程度上是以“瓯脱”之名来标榜各自的边境筹划方案。
经过中法越南交涉时期的重挫,清朝“瓯脱”筹议基本走向消退。(62)在1890年代初的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瓯脱”之法虽被提及,但这种微弱的呼声,非但未为英方接受,而且在国内也缺乏响应,旋即走向沉寂。甲午战后,中国遭遇了朝鲜这一最为重要的藩属解体的打击,但“瓯脱”之法未见国人再次提起。“瓯脱”之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疆土观念突破了过去一种重要的思想藩篱,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