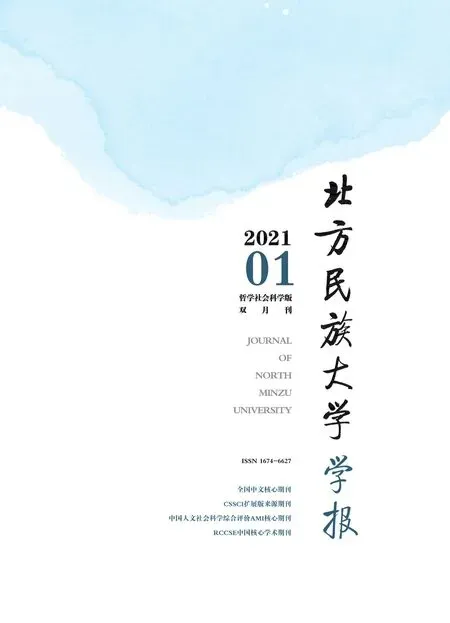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陈正府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我们无法静态地、本质地、结构地理解社会与文化,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社会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而在村庄里做研究。”[1](29)我们研究人,发现人与环境、自然紧密相连;我们研究一个地方或群体,但实际逃不开“关系”与“场域”;我们研究一种文化,发现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我们研究一种“物”,发现“物”与“非物”充满着各种联系;我们研究社区,发现社区里充满着协商、谈判与冲突;我们研究民族,发现民族是关系的产物[2];我们研究组织,发现组织是靠行动者的合作与关联维系的[3](29)。总的来说,人们逐渐发现世界是一个相对的、关系的、共谋的世界。对此,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说:“认真地重视相对主义的问题,或准确地说,我所说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那么,实在论的所有进展必须归因于关系主义及其方法的进展,也就是说,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的能力,以及在不可通约的观点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记得德勒兹(Deleuze)说过这样的话:‘相对主义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关系的真理’”[4]。英国人类学家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认为,“人类学是一种知识实践,是将关系置于其他关系之中所做的研究”[5]。如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典主题——亲属关系理论,实际上是为了揭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理论。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哲学思潮与社会理论倾向于从关系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文化现象。这一转向的背景是相对论与量子物理为代表的科学范式革命,社会科学中文化相对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殖民语境下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与原住民自治权益的诉求。此前以发现普世规律(如进化论、本质论、实在论以及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为己任的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越来越难以应对和解释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与多元多样的文化差异,这些为关系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发展空间[6]。可以说,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也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7]。关系民族志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超越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要提倡关系民族志,民族志如何实现新的知识生产?本研究拟从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分别从“世界是关系的”“社会是关系的”“文化是关系的”三个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就是整体观,这是民族志的首要原则。我们研究人,其实是研究人的整体性,也就是一切与人相关的关联性。关系民族志实际上是人类学整体观的一种精致体现。
二、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
当前的民族志研究为何要提倡关系主义?主要是基于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视野的盲点。本质论(essentialism)实际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或规律。陶东风在《文化研究导论》中如此定义本质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把任何文化的分类编组加以模式化的基本原则,都是在用本质主义的方式进行运作。”[8]近年来,人类学界受后现代建构主义一些学者的影响,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知识社会学、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符号学、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以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认为本质论的静态式、模式化和规律化的分析已不能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福柯认为,所谓的“本质”是由带有偶然性规范和人的知识权力塑造而成的;赛义德认为,“东方”不是一个本质的实体,而是西方文化通过“定型化”“模式化”建构出来的。从知识论上来看,本质论还是一种以二元论的简化视角去解释这个世界,认为认识事物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于是相信宏大叙事,相信客观真理,从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一些珍贵的细节与流动的意义,也轻视了知识背后的语境性、地方性与实践性。
1903年,涂尔干与其外甥莫斯(Marcel Mauss)在《原始分类》一书中试图从原始人的氏族图腾制所体现的集体意识和分类原则来找寻人类思维的起源与规律。他们基于社会的普遍进化论,假定人类心智的思维结构一致。后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此基础上,将语言视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基于图腾制模式构建了语言符号模型。语言学就是对其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进行结构分析,这是结构主义的起源。后来,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又从亲属制度、神话分析对结构主义进行了发展。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干脆用“社会结构”代替了人们一直以来对图腾制、亲属制与神话的结构分析,认为任何社会与文化都有结构,文化不过是表象,人类学的任务是通过人们的经验和文化符号来揭示社会运作的普遍性规律。总体而言,结构主义采取的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化和归纳式的分析路径,认为大多数的文化功能复杂、意义多样,需借助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从而以简驭繁,以静制动;结构功能主义通过亲属研究、神话思维和图腾制度,将人类的思维结构视为相同的,并探寻不同文化背后的深层“语法”。
二元论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即认为世界是由两种不同元素(方面)构成的,认识世界可以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进行,如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唯物与唯心、黑与白、阴与阳、善与恶。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相信人类的心智是二元对立的,认为这是人类思维的普遍法则,其特点是通过类比(analogy)而不是逻辑(logic)来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的分类,如天地、左右、生熟、男女等[9](67~68)。二元论思想最先由柏拉图和笛卡尔提出。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极”和“现象极”组成;笛卡尔认为,身与心是独立存在的。一段时间以来,二元论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其背后有着西方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维基础,从古希腊哲学中广泛存在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到启蒙时代受自然科学影响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再到工业革命以来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区分。二元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独立与个体的客观实体,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有它的本质与规律[10](35~36)。但二元论越来越为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批判,他们认为二元论不过是人为简单划分的抽象概括,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认识模型,完全与实际经验和现象不符。特别是20世纪初,受物理学领域中量子论与相对论的影响,人们才意识到“时间与空间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与观察者相对的”[11](526)。
三、世界是关系的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世界应是关系的。首先,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关系的有机生态系统。此系统是以生物多样性为前提,人类与动物、植物、昆虫,以及森林、土壤、河流等相互关联和依存,才构成世界这个“生命共同体”。动物、植物和其他非人类不能被当作世界的异类或物化的客体,应与人类一起被视为生态链条中的一环或节点,共同地、平等地参与世界生态环境的构建[10](94~95)。人是自然世界的产物,人类的文化不过是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的产物。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关系的,这种关系建立在整体主义(holism)的基础上,大自然所有的物种、土壤、河流、森林与人类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赖,相互牵制,都是生物圈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缺少任何一个或缺少万物之间的联系,地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失衡。其次,作为人类意义的人文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主要由人们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构成,交往的产物就是文化。尽管自笛卡尔以来西方的世界观一直主张主客二分,高扬人的主体性,但没有意识到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以“他人”“他者”的关系性存在为前提。人文世界里,人们存在的意义世界与文化的多样性都是在探讨“我者”“我族”与周边世界的各种“他者”“异邦”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早期古典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研究的经典命题“万物有灵论”,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侧重于研究“世界是关系的”一个主题[12],反映了人类从古至今体验和认识世界的一种视角与方法。万物有灵论实际上在强调一种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和关系认识论(relational epistemology),主张通过“万物有灵”来探索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与宗教、认知、生态、习俗等领域相关的一种关系学。如今,万物有灵论与生态宇宙观、多元本体论、跨物种民族志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如当代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10](7)、纽里特·伯德·大卫(Nurit Bird-David)[12]、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13](87)等近年来热衷于从“万物有灵”角度,探讨认知与生态环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relational stance),他们声称“万物有灵”作为一种关系的认知论与本体论,认为世界是通过探索万物之间的关系而得以了解,各物体之间应以相互转化的视角与立场把握整体。作为人类学之父的“万物有灵”提出者,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e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最先把人类的生命和心智与动物、植物甚至矿物资源等联系起来,认为“万物有灵”是原始部族将身体与万物相关联的一种思维操作,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日常实践。
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一直反对自然与文化的分野,他认为万物有灵主义(animism)、图腾主义(totemism)、类比主义(analogism)这些经典的人类学关键词恰好证明了“世界是联系”的观点[13](68~69),新的自然主义应侧重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混合,而不是截然对立。布鲁诺·拉图尔认为“我们从未现代过”,当下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把人与树、房子、车分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是处于自然、社会、科学、技术相互混合(hybrids)的网络关系(networks)中[14](21~32)。此外,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人与“人的猎物”之间可以交换视角。因为“万物有灵”,视角交换后,实际上人与万物可以共享一种文化系统,由此实现从单一的自然多元文化(single nature-multiculturalism)到单一的文化多元自然(single culture-multinaturalism)的转换。总而言之,“万物有灵”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伴随着人类纪(anthropocene)的到来,整个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万物有灵”有助于将“以人类为中心”的意识扩大到更多的非人类,为当代世界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即“人类中的自然”与“自然中的人类”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万物共享一个“生命圈”,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纪。
四、社会是关系的
社会是关系的集合(assemblages),这里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之所以成为人,只有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才能理解人的存在,并考察人作为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与经验意义,但这种关系不是原子关系的集合,更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人类学视野中的社会关系考察的是在一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关系。人类学早期的民族志大多以考察“异文化”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是当地部族或部落的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纳入殖民管理。无论是泰勒的《原始文化》、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还是莫斯的《礼物》、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些经典民族志除了对当地的文化习俗进行记录和分析外,大量的笔墨也在描写社会关系。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人类学家考察的对象不是狭义的家庭、社区、游群、部落与近代定义的民族,实际上是广义的“社会共同体”[15](33)。泰勒对原始社会的分期与发展路线进行了划分;摩尔根就易洛魁社会的家庭关系、财产关系、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进行了分析;莫斯对前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物的互惠交换关系进行了精辟的揭示;马凌诺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的社会生活(包括巫术、宗教、贸易、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描述。
此外,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作品中,以中国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社会关系与人情互惠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观察,展现了当地的关系伦理与社会逻辑,对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礼物交换”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16](9~10)。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反映着个体、家庭、社会的关联,以及私人生活与社会空间的变迁。礼物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礼物馈赠与人情的互惠交换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独特内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世界与道德规范,特别是在关系紧密、相互依存的乡村社会里,以人情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往往比物质和金钱更宝贵,由此产生了送礼习俗,并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网络的亲疏[16](35~36)。
杨美惠以福柯式的手法对中国城市中的关系学进行了知识考古与权力解构。她认为,中国的关系学是靠礼物馈赠、人情宴来维系的,背后牵涉的是权力运作与主体性建构。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学除了权力交换外,还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亲缘感与伦理特征。中国民间社会还通过“根茎式”的人情关系网对抗正式的官方规定与权威,成为特定情景中僵化体制与社会规范下的润滑剂,使得个人、团体、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流动、合作与交换更为灵活。杨美惠还提到,当下的“跨国的华人资本主义(transnational Chinese capitalism)”就是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学与人情关系,超越了国家与政治的边界,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商人和企业家联结起来,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资本主义富有竞争性的一个特征。这种被称为“中国关系网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这些企业是由小家庭作坊或家庭企业发展而来,背后承载的是中国传统的男权权威与人际信任,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基于社会契约与法律系统发展而来。基于中国社会关系网构成的商业关系比西方个人化、合同化性质的商业交易更富有人情味,效率更高[17](62~67)。
五、文化是关系的
文化是什么?从“人类学之父”泰勒最初提出的“复杂的整体”到克罗伯(A.L Kroeber)和克拉克(Clyde Kluckhonn)梳理的一百多条定义,人们发现文化就像人赖以生存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涵盖范围极广,内容多样,难以明确定义。当代人类学家马克·霍巴特(Mark Hobart)认为,与其定义文化是什么,不如定义文化的特征有哪些,该如何研究文化[18](10~11)。“关系”是文化的重要特征,关系主义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众多的人类学经典理论证明了这一点,如德奥文化圈理论、马凌诺斯基的库拉圈理论、莫斯的礼物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理论、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施坚雅的市场体系、利奇的过程论等。其中,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定义最让人印象深刻:“我以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5)。究竟该如何研究文化?格尔茨认为,我们在做民族志调查收集材料时,首先面对的是大量复杂的概念结构,“其中许多结构是相互层叠在一起,或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结构既是陌生的、无规则的,也是含混不清的,而民族志学者首先必须努力把握它们,然后加以翻译”[1](12)。换句话说,民族志调查的任务是梳理这些复杂材料之间的关系,并对之进行深度阐释和翻译,从而洞悉当地人的心智结构与情景意义;同时,要学会以小见大,将局部的、微观的发现与更大的世界关联起来[1](28)。
在一些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品是侧重于关系描写的典型案例。比如文化传播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具有的相似性及其关联因素,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就以非洲和新几内亚猎弓的相似性为例,证明两地之间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文化是可以通过接触而产生相似性的。传播论的理论范式主要有文化圈和文化区理论。文化圈是注重文化特质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探寻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之间的传播途径与时间上的叠压关系。文化区主要考察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之间的关联性,描述文化特质、文化丛结、文化类型、文化带与文化区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范式为后来的跨文化分析以及文化的适应、发明与创造提供了实证材料。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以库拉圈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通过交换得以维系,文化意义才是交换的重要价值。但是库拉圈又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交换,实际上是加瓦岛人的一个有关身份、名望、地位的“关系网”或“联系机制”[19](13)。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在《努尔人》一书中,除了考察努尔人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外,重点描述了努尔人的三种关系,即亲属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努尔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牛相关,而牛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认知方式相关。比如,他们对牛的态度决定着他们对邻居的态度,而各个氏族和宗族之间发生的争端又常与牛相关。他们之间亲属关系网络与婚姻关系的建立往往是通过牛的交换和宰杀来实现的。同时,努尔人还将牛与鬼魂和神灵联系起来。可以说,与牛的关系几乎决定了努尔人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20](24)。
六、关系民族志:一种整体观的体现
关系民族志的理念挑战着人们对于人类学整体观的思考。一直以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人类学的学科观就是整体观,人类学必须按整体原则来了解人类。生物存在和文化存在不能分离,同时还要考虑自然环境。“人类既是许多不同的、相互联系的因素的整体,又是它们的产物。”[21]文化不是各部分简单之和,而是大于整体。但到底什么是整体观,如何把握整体性?众多文献似乎没有给出直接的、明确的定义。早期人类学者提倡一种静态式与结构下的整体观,主要指一种功能式的、组织式的整体观,代表人物有马凌诺斯基。马氏选取相对封闭和具有明确地理及文化边界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通过事无巨细的科学主义田野调查,分析各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地的文化体系进行整体性的解释。当下一些人类学家侧重于以社区为单位,除了挖掘社区日常生活体验与组织关系,更多是从社区的地理和文化边界中超脱出来,关注特定个体、群体与组织如何能动地与外面更广泛的社会相关联。如美国罗兹-李文斯顿学会(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中的人类学家主张通过网络化的田野实践,侧重当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情景化分析,理清个案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多重关联。网络化整体观还主张对不同时空的事件进行情景分析,通过找寻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来勾勒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生活缩影。
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正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所述,单一的、静态化分析的民族志不足以解释日益变迁的社会与文化。基于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更需要提倡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方法,考察更多相互联结(connections)、联合与复数的关系(putative relationships),以发掘更丰富、更生动的日常生活细节与社会文化逻辑[3](81~82)。“多点民族志会导向共谋的田野关系,其主旨思想是你是如何看待不同场景当中一系列复杂关系的。”[22]由此可见,乔治·马库斯倡导的多点民族志实际上也是关系民族志,它不局限于一个群体或地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社会空间场域里不同群体或行动者之间关联或冲突的过程与关系,同时考察民族志设计时人类学者与报道人之间的合作策略,以及多点田野中地方表征体系的复杂性与差异性[3](81~82)。为此,哈佛大学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教授总结出关系民族志的四个特点:一是研究场域而不是地方;二是研究边界而不是固定的群体;三是研究过程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们;四是研究文化冲突而不是群体文化[23]。
七、结语: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
当下是一个多元和复数的时代,诚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一书中所描述的,这是一个众多主体、众多韵律、众多学科不断生成(becoming)和共变的“根茎式(Rhizomes)”时代[24](7~9)。如何描述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这为民族志的研究与撰写提出了新的要求。自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出版以来,学术界对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一直在不断反思和讨论之中。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以及《文化人类学》杂志对此还分别举办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2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19年,乔治·马库斯在云南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合作人类学”的概念,主张民族志要在方法论、研究场所与田野设计上进行创新,尝试跨学科、多声部、多点田野的“合作性民族志”,让民族志的实验与撰写更加契合全球化时代的需要[23]。由此看来,关于民族志的理论反思与方法研讨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的话题,它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理解和表述这个世界,更是一个不断革新知识生产方式的问题。
无论是多点民族志、多声部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合作民族志,还是世界体系、全球化理论以及“本体论转向”,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一种关系,倡导当下民族志书写应赋予一种更大的理论关怀,即世间一切都是关联的,跨界、多元与混合应是当下世界原本的现实。我们要超越时间、空间与地域上的限制,树立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与合作观。除了考虑生物与文化的整体性,还应考虑人类与非人类、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整体性。换而言之,我们关注整体,除了关注群体、结构与边界,更要关注个体的位置、意图与想法,同时也要关注整体之外与部分之间的关联,让个体与部分嵌入更宏大的体系,实现与外界扩展性的互动。由此看来,关系民族志不只是深描一张意义之网,更是一种行动倡导与合作实践,在这张网之中,人、物、技术、自然、社会、话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都相互关联与共谋;各种研究平台、通道、项目和活动一起参与合作,相互共享,互为主体,从而实现新的知识生产[25]。我们也应看到,人类纪(anthropocene)与资本纪(capitalocene)的时代,达尔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应对当下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我们只有以“同生共存”的整体观与合作观,超越自我与他者、自然与文化、身体与心灵的两分,以关联的视角探寻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人类才能同这个世界的其他一切物种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