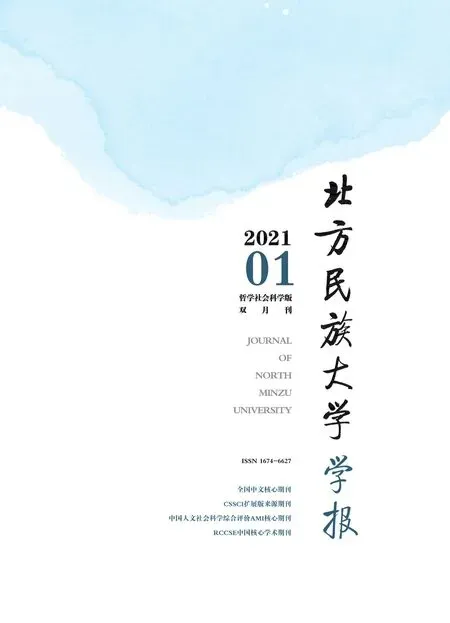告示语的言语行为分析
刘晨红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告示语作为一种社会用语,涵盖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关于告示语的概念,人们较多采用陈新仁的界定,“告示语是一种公示性话语,是指在公共场合张贴或印刷的旨在为一般公众或特殊群体提供指南、提醒、警告等帮助的宣传性、服务性语言标牌标语”[1]。凡是公开发布的标牌标语都属于告示语的范畴。
关于告示语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某一类告示语的语言特点进行研究,比如王彩丽对警示类告示语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2];袁周敏、陈新仁对187条环保类告示语语料从语用角度进行研究,总结了其语用语言特点以及相关语用策略的使用状况[3];陈丽、龚维国结合告示语例证,从隐喻角度分析了隐喻产生的机制,总结了告示语告知性、劝说性和警示性的隐喻效果[4];江旭睿从言语行为视角对公益广告语类告示语进行了研究[5]。另一类是对某一区域或某一城市的告示语进行调查研究,比如陈新仁调查了江苏省某重点大学一校区物业管理公司发布的告示语,从语言顺应理论角度分析其语用语言特点及策略取向[1];何正英对南京城市告示语英译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6];刘晨红调查分析了宁夏银川告示语的使用及接受情况[7]。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人们普遍关注告示语的语用语言特点及英译状况,并对其进行归纳分析,从言语行为角度分析告示语的成果不多。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使用的告示语,不仅要考察语言表征的特点和表达方式,还要考察语言的社会功效。本文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宁夏银川市告示语进行分析,归纳告示语的言语行为类型,考察近年来比较多见的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表达策略及指令效果,以期管窥城市告示语的现状及社会效力。
本文涉及的告示语是通过两次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次是2012年5月、6月、10月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的主要街道、商业区、居民区等场所出现的各种告示语拍照、记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对调查来的告示语进行整理,除去重复信息,共收集语料360条[7]。第二次是2019年10月进行的补充调查,主要选取了银川市北京路、贺兰山路两大主要街道及沿线单位,新华街、西夏万达广场和金凤万达广场3个商业区,西夏区两所高校校园,3个居民小区作为调查点,对调查所得与第一次的信息对比,去除重复信息,新增135条语料。
一、告示语的言语行为类型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不仅传递信息,而且是直接用来做事的,即说话就是做事,交际活动是由一系列言语行为组成的[8],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使用语言以实现一定意图就是完成一个行为。人类的行为有各种类型,通过使用语言而完成的行为是一种外显的符号互动行为,被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叙事行为、施事行为、成事行为三类[9](152)。言语行为的主体是发话者和受话者。语言使用者是言语行为的主体,任何话语都是怀有一定意图的发话者在一定语境中针对能产生一定效果的受话者发出的。离开发话者的意图和受话者对意图的理解以及与意图表达和理解相联系的语境,话语的语用意义是无法确定的。
告示语的功能是为了以言行事,影响受众的行为举止,属于以言行事的指令行为。指令涉及说话人(指令的发出者)、听话人(指令的接受者)和说话人想要听话人实施的行为这三个基本要素。告示语的实质就是发布者(管理者)对大众直接或间接地发布某个指令,禁止、祈求、建议、提醒、提示、告知公众实施某一行为。告示语又是特殊的指令类言语行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非口语的言语交际,而且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作为交际的参与者,话语双方不是以个体身份出现,发话者是组织团体而非个人,受话者是群体。例如,“严禁践踏草坪”严厉地表达了一种指令,“银川是我家,卫生靠大家”,“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都是号召人们为同一目标努力,也表达了一种指令。根据告示语话语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告示语分为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和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两类。
(一)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
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就是通过告示语的字面意义能够确切直接地发布一个指令,告示语发布者的指令意图直接由告示语字面意义表达出来,对受话者通过话语形式直接发出了某种指令,要求或请求实施某种行为。直接指令告示语要受话者实施一个行为的意图是明确的,受话者接受告示语的话语后非常清楚应该实施怎样的行为。根据语句特征,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禁止性指令类告示语。这类告示语的“交际意图在于以强制性方式来阻止或预防特定行为、事件的发生”[1]。语言表达多采用祈使句,并且带有标记词语“禁止”“不得”“谢绝”等,指令明确外显,语气强硬。如:“施工现场谢绝参观,外来人员禁止入内”(建筑工地);“此处禁止停放自行车”(某学校大门口);“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学生宿舍楼前);“禁止吸烟”(加油站);“无票人员谢绝入内”(候车室)。
二是祈求性指令类告示语。祈求性指令类告示语以言行实施行为,与禁止性指令类告示语相比,礼貌性强一些,指令语气稍弱,祈求性的告示语多带有“请”“请勿”“要”等标记词语。如:“为了您和您的家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道路旁);“好花大家享,请勿摘取”(小区内);“请爱护公共设施”(学校体育场);“请自觉排队买票”(车站售票处);“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某校园内)。
(二)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
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就是告示语字面意义是非指令行为,但实际意图是发布了指令行为,即间接地实施了指令行为。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话语形式与功能是不一致的,一条告示语的功能不只是字面意义,其真正意图经由字面意思,需要借助一定的认知推导来理解。
在我们搜集的告示语中,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主要是建议告知性的,这类告示语表达形式灵活多样,没有明显的用词特征,多使用省略句或修辞格表达,其指令的交际意图需要结合语境才能解读。比如,“文明、洁净、和谐、幸福银川”,其字面意思是告知公众一个关于银川的信息,真实意图是号召人们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把银川建设成文明、洁净、和谐的城市,使生活在银川的人们有幸福感。再如“弘扬社会正气,赞颂民族团结”(西夏区某高校校园);“爱护公物,珍惜资源,勤俭节约,共同发展”(街头);“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贺兰山路旁)等,这些告示语的字面义是告知公众某种政策、观念、方法等,实则建议人们为某一目的或宗旨而努力,告知信息是表层目的,终极目的是指导人们如何行事,带有一定的指令性,指令语气弱化,是一种间接指令类以言行事行为。
总体来看,在我们搜集的告示语中,禁止类言语行为告示语不多,出现场合也极其有限,其他的言语行为告示语比较多见,尤其是建议告知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告示语最为多见。由此可见,社会语用中告示语的一大变化特征就是,改变过去动辄“禁止”“不许”等强硬的命令方式,采用弱化的指令方式实施指令性言语行为,直接指令告示语的表达形式有明显的词句特征,规律外显,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表达形式灵活。
二、间接指令行为告示语的表达策略
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9](176)[10]。据此,间接指令告示语也可以从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方面考察其表达策略。
(一)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规约性表达策略
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语力”做一般性推导而得到的间接言语行为[9](176)[10]。对“字面语力”做一般性推导,就是根据句子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以立即推导出间接的“实施语力”[9](176)[11]。塞尔总结了六类可以惯例化表达间接指令的句子,分别是:(1)涉及听者实施A(Act)的能力的句子;(2)涉及说者希望或要听者实施A的句子;(3)涉及听者实施A的句子;(4)涉及听者实施A意愿的句子;(5)涉及实施A的理由的句子;(6)把上述形式中的一种嵌入另一种的句子,以及在上述的一种形式中嵌入一个显性指令性施事动词的句子[9](176~178)[12]。
告示语在表达间接指令时较多使用第(5)和第(6)类句子。例如:“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财富,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幸福”;“绿色,是自然之美,是心灵之声,是人类的依靠”等,属于惯例化表达间接指令句子的第(5)种情况,涉及实施A的理由的句子,前者表达了注意安全的理由,间接地向司机发出指令——安全行驶;后者表达了环保层面的理由,间接地向公众提出保护环境的要求。再如:“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带走的花儿生命短暂,留下的花儿才是永远。敬请脚下留‘青’”等,属于惯例化表达间接指令句子的第(6)种情况,把涉及实施A“每天锻炼一小时”和“敬请脚下留‘青’”的理由的句子“健康工作五十年”和“带走的花儿生命短暂,留下的花儿才是永远”嵌入当前告示语的句子里,间接向受话者发出指令、提出希望,希望人们锻炼身体,指令人们爱惜花草。这些告示语实施的言语行为,结合句法形式,做一般的推导即可实现。
(二)间接指令告示语的非规约性表达策略
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也要通过推导实现,但推导不能通过句子的句法形式实现,而要结合说话双方的语境和共有语言信息。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语言表达形式复杂。梳理相关文献,没有发现总结研究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表达形式或者表达策略,但现有的告示语中非规约间接指令的告示语很多。例如:(1)“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学校餐厅内);(2)“喧闹在这里停止,思想在这里升华”(图书馆内);(3)“眼观古今中外,耳需一时清静”(图书馆内);(4)“带走满腹知识,留下一架好书”(图书馆内);(5)“绿草茵茵,踏之可惜”(公园草地上);等等。例(1)本来是人们熟悉的诗句,当它出现在餐厅、食堂中时,就不能仅仅作为一句诗来理解,而是一个告示语,它间接地向受话者发出一个指令,要求人们节约粮食。例(2)、例(3)结合出现的语境——图书馆,间接地向受话者发出一个指令,要求人们在图书馆保持安静。例(4)也是图书馆的告示语,“好书”语意双关,既指内容好的书,也指无破损、外观好的书,发布者所表达的意图主要是后者,这个意图理解需要结合语境进行推理。对例(5)指令意图的理解也要借助语境。
告示语的发布者表达一个间接指令,应该使受话者能够明白理解其间接指令,并按照其指令行事,这样,告示语才能有效发挥社会交际功能。间接指令性告示语的实质是发话人利用各种话语策略促使受话人采取发话人所希望的行动。对于规约性表达间接指令的话语形式,上文我们看到塞尔总结出了六类句子。非规约性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话语策略是什么呢?
结合语料,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笔者认为,非规约性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表达策略之一是互文。《变异告示语的互文研究》一文解释了互文概念,通过翔实的例证阐释了引用式、仿拟式、照搬式、烘托式、谐音式五种互文类型,分析了变异告示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从言语行为角度看,该文涉及的变异告示语大多是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由此,我们认为互文也是非规约性间接指令告示语的表达策略之一,间接指令告示语的“互文表达有词句性的引用、吸纳、模拟,也有整体语篇借用搬用的情形”[13]。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校园告示语);“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爱鸟告示语);“但愿人长久,热血注心田”(义务献血告示语);“鲜血诚可贵,助人价更高”(义务献血告示语)等,这些告示语有的直接照搬诗句、歌词,有的仿拟诗句、俗语,这些告示语与原文本(话语)都有互文关系,不管用何种互文方式生成的告示语,都不是直接表达某个指令,其指令意图不是一般推知的“字面语力”,它的“实施语力”必须借助语境间接推知。这种互文策略是用其他文本的话语作为告示语向公众发布某种指令,由于被引用的话语在人们的认知中已经存在,借助一定的语境,管理者(发话者)的指令意图能够表达,同时弱化了管理者的身份,模糊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势关系,被管理者(受话者)容易接受指令。
三、告示语指令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指令效果
告示语作为广泛使用的社会用语,从言语行为角度进行研究,还要联系言语行为的主体,关注为什么这样说和说后的效果,也就是关注告示语指令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功效。
(一)告示语指令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指令类言语行为中,言语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即说话人(指令的发出者)与听话人(指令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影响指令如何发出,也就是影响话语形式的选择。影响言语行为主体关系的因素很多,在指令性告示语里,主要表现为社会角色关系。社会角色决定了说话人(发出指令者)拥有话语权,有权利发布告示语,发布指令。社会角色随着语境的变化也会有所变化,带有某种主观性,在一定交际中,发话人的社会角色带有的主观性直接影响话语形式的选择,影响告示语的表达,即直接表达指令或者间接表达指令。
樊小玲认为,指令言语行为形式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话语权力’”,“指令行为发出者对‘话语权’强调程度的差异,在话语层面会显示为不同的指令形式”[12]。根据这个特点,将指令类言语行为分为命令、请求、建议三种类型,告示语的指令性言语行为的形式选择也表现出相应的特点。
强调自身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告示语,即命令[12]。比如带有“严禁”“禁止”“不许”等字眼的告示语,告示语的发布者发布命令是通过强调自己拥有话语权来促使他人采取某种行为,是强制的命令形式,强调对方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告示语,即请求。比如带有“请”等字眼的告示语,是告示语发布者凸显对方话语权力和权势,也就是告示语发布者故意弱化自身的权势,表现亲和力,以“请求”的形式向公众发出指令,强调自身话语权力、权势的指令告示语和凸显对方话语权力、权势的指令告示语都属于直接指令告示语。
模糊双方话语权力和权势的指令告示语,即建议[12]。比如,“消防连万家,安全你我他”,使用“你我他”暗含告示语的发布者与公众别无二致;“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对公众表达了良好的祝愿,没有管理者的盛气凌人;“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爱鸟告示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都是采取刻意将双方的权力和权势模糊的指令方式。管理者采取模糊话语权力和权势的语言形式向被管理者发布告示语,以缩短话语双方的心理距离,构建平等友善的话语交际语境。
言语交际过程中,发话者的话语被受话者接收、理解后才能取得交际效果,同样,作为特殊交际方式的告示语,发话者发布的告示语只有受话者看到并理解其真实意图,才能产生效果。直接指令告示语,由于指令本身出现或者指令本身和指令理由共现,受话者容易理解说话者的指令意图。对于间接指令类告示语,如何模糊双方的话语权势,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又能够使大众理解告示语发布者的真实意图,这关系到告示语最终交际效果的实现。间接指令类告示语的理解一方面需要受话者进行认知推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发话者提供“明示”信息。“明示”不仅体现为告示语出现的场合和时间,也是语言形式的明示。对于间接言语行为告示语,受话者理解接受,提供明示信息很重要。比如,“眼观古今中外,耳须一时清静”,这是图书馆中的告示语,场合和关键字眼“清静”起到了明示性作用,受话者可以清晰解读其指令意图,从而保持安静。
(二)告示语的指令效果
李宇明曾举例说明汉语中依次增强的指令语力,比如当让某人实施关窗户的行为时,用疑问句“今天很冷,是吧”的形式表达指令,是间接指令类言语行为,语力最弱;采用祈使句“给我关上窗子”或者“你这个混蛋!给我关上窗子!”这样的形式表达指令,是直接指令言语行为,语力最强[14]。由此可见,间接指令类言语行为的指令力度小于直接指令类言语行为。
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告示语的指令力度越大,指令效果就越好呢?从我们的观察和调查来看,有些直接指令告示语的指令效果不佳,比如“此处严禁倒垃圾”,实际情况是有些人很反感这样的命令,故意往此处倒垃圾。相反,一些间接指令告示语的指令效果较好。这个与礼貌度有关,指令力度高的告示语礼貌度低,指令度低的告示语礼貌度高。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想让别人实施某一行为,采用指令度低、礼貌度高的言语行为,交际效果最佳;反之,不讲礼貌或礼貌度很低、指令力度高的言语行为,交际效果不佳。
笔者曾对银川市市区15~25岁,25~35岁,35~45岁,45~55岁,55岁以上六个不同年龄段的196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观测公众对直接指令告示语和间接指令告示语的接受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有164人接受间接表达指令的告示语,占83.67%;有124人认为间接表达指令的告示语更加人性化,占63.27%。由此可见,间接指令告示语公众接受度较高,指令效果较好。因此,建议管理者根据情景发布间接指令告示语,较好地实施言语行为,圆满实现交际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