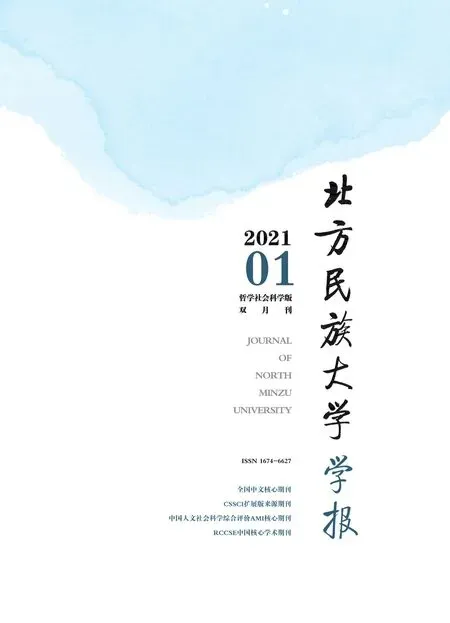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王精金,崔贵默
(高丽大学 东亚文学研究所,韩国 首尔 02841)
元代诗坛盛行“宗唐得古”的风气,揭傒斯所谓“学诗以唐人为宗”[1](14),王恽称“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2](312),这些向唐人学习的言论显示了当时诗坛的主流取向。在宗唐诗风炽盛的态势下,宋诗的地位虽然无法与其抗衡,但文学自身的作用力常常让人难以预设,宋诗之于元代并非毫无影响,元人对宋诗的研究并未完全消歇,宋诗接受的暗流也在潜滋暗长。元人在选评、刊刻、论说以及宋诗学理论建设等方面均有创建。
一、勾勒宋诗版图
从宋诗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可以揆度出各诗学流派以及各历史阶段的诗学风貌。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其《送罗寿可诗序》便是一篇阐述宋诗演进的史论,序云: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文禧、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帷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栓取或不尽然,胡致堂低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掌。乾淳以来,尤、杨、范、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3](12470)
方回从宋诗发展的视角着眼,将宋诗大体分为四个时期,这是最早为宋诗发展做出界划。
宋诗的雏形期。宋诗发展初期是“晚唐风采”和宋诗风格初具的交替时期,此时,“白体”“昆体”“晚唐体”占据诗坛,“三体”诗人承袭唐五代遗风,宋诗自身的特色尚未形成,故当时诗人追踪前朝遗迹不可避免地带有“唐朝锦色”,如方回指出王禹偁“元之诗学乐天”[4](185)。
宋诗的兴盛期。出现了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其杰出才华变革唐诗,出之以变化,从而铸就了宋诗的特色。方回评价梅尧臣云:“梅公之诗为宋第一,欧公之文为宋第一,诗不减梅。”[4](925)指出梅尧臣雄踞宋代诗坛之冠,充分肯定了他开创新风气的作用。对于元祐诗人,方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元祐诗人诗,既不为杨、刘昆体,亦不为九僧晚唐体,又不为白乐天体,各以才力雄于诗”[4](886)。指出这一阶段的诗歌已超越了晚唐和宋初诗风的束缚,建构了宋诗的特质。方回论苏轼云:“坡,天人也。作诗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4](797)认为苏轼以其出众的才能,诗风不拘规矩,自成天然之态。
宋诗的中兴期。南宋初期诗坛以“中兴四大诗人”为代表,他们的出现给宋代诗坛带来了中兴的局面。方回《跋遂初先生尚书诗》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早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3](415)《晓山乌衣圻南集序》云:“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3](29)尤、杨、范、陆四家以盛唐诗歌为学习典范,并取法江西诗派的“活法”说,又加以变化,别出机杼。方回评陆游云:“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4](215)认为陆游诗歌学习江西诗派但不为其所拘囿,兼取唐诗。
宋诗的衰颓期。南宋后期诗坛主要以“四灵”和江湖诗人为代表,但方回对“四灵”和江湖诗人评价不高: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诗曰《西岩集》;徐玑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诗曰《泉山集》;徐照字道晕,号灵晖,诗曰《山民集》;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诗曰《天乐堂集》。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诗家,自是始降而为江湖之诗。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4](771)
永嘉“四灵”因学晚唐姚、贾,诗歌“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4](339),方回认为其作品境界逼仄、气象狭小。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号剡源先生,浙江奉化人。戴氏从宋诗演进的历程,对宋诗发展过程做了分期,体现了元人系统的宋诗观。《洪潜甫诗序》云: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迩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5](195)
戴表元从宋诗之变的视角,将宋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北宋初期,以“西昆体”(学李商隐的“博赡”)和“白体”(学白居易的“豁达”)为代表,此时的诗风还带有晚唐诗歌的印迹,也即戴表元所称的“绝无唐风”,宋诗的特色尚未具备;第二个发展时期为梅圣俞等所开创的宋代诗风,尤其当梅尧臣之“冲淡”诗风出现,宋诗才真正摆脱了五代诗歌的影响而变为唐音;第三个发展时期为黄山谷等所形成的特色独具的宋诗,黄山谷之“雄厚”堪称宋诗之代表;第四个发展时期为“四灵”诗派所代表的宋诗,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清圆”。四个发展时期展示了宋诗演变的历程,同时也是宋诗特色逐步形成的过程。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浙江鄞县人。袁桷从宋诗的发展历史谈起,注重宋诗各个发展阶段的变化联系。袁桷指出:
风雅异义,今言诗者一之。然则曷为风?黄初、建安得之。雅之体,汉乐府诸诗近之。萧统之集,雅未之见也,诗近于风,性情之自然。齐梁而降,风其熄矣。由宋以来,有三变焉。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高者凌山岳,幽者穿岩窦,而其反复蹈厉,有不能已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奇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苏公以其词超于情,嗒然以为正,颓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6](690)
风与雅在黄初、建安、汉乐府中颇有遗存,而齐梁以降,风雅已不复存在。宋人反复蹈厉,一变再变,欧、梅以“古远平淡”一变初宋之风,苏轼以“波澜富而句律疏”和“法度去前规”成就自己的特色,江西诗派嗜奇好险,其“变有不可胜言”[6](714)。不过,袁桷在此所论述的宋诗“三变”仅仅是论述了北宋诗坛,忽略了南宋诗坛的变化。《跋吴子高诗》云:
故夫绮心者流丽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夭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满者犹不悟,何也?杨、刘弊绝,欧、梅兴焉,于六义经纬得之而有遗者也。江西大行,诗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烂而不可救,入于浮屠、老氏证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6](705)
袁桷补充了宋诗之第“四变”,就是宋室南渡(陵夷渡南)之后的诗坛变化,不过袁桷对南渡诗坛持否定态度,所谓“糜烂而不可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7](1441)宋王室南渡之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诗派“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就是指“糜烂而不可救”。
二、界划宋诗流派
方回对宋诗流派做了划分,他在《恢大山西山小稿序》和《瀛奎律髓》中有类似的论断:
王维、岑参、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至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而乾淳诸人,朱文公诗第一,尤、萧、杨、陆、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韩南涧父子、赵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炎祚将迄,天丧斯文,嘉定中,忽有祖许浑、姚合而为派者,五七言不能为,不读书亦作诗,曰学四灵,江湖晚生皆是也。[3](12491)
殊不知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如苏子美、梅圣俞并出欧公之门,苏近老杜,梅过王维,而欧公直拟昌黎,东坡暗合太白。惟山谷法老杜,后山弃其旧而学焉,遂名黄、陈,号江西派,非自为一家也,老杜实初祖也。[4](18)
方回所言宋诗流派与严羽大体相似,但对于“老杜派”(江西派)的提出则是其独创,而且所涵盖的人数和时期贯穿了整个唐宋时期,宋代有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尤、萧、杨、陆、范等众多诗人;其他宋诗流派有“晚唐体”“香山体”“西昆体”“四灵”“江湖”等五种。
袁桷用宗派的观点来评价宋诗,这种宗派意识观说明他对宋诗在总体上有“清醒认识”。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6](678)
袁桷在这里用“宗”给宋诗流派命名,“临川宗”“眉山宗”“江西宗”为其所发明,这种给文学群体命名的方式带有典型的宗派意识。袁桷从宋诗的源头论起,学李商隐而自成一体的“西昆体”,其“襞积组错”“命意深切”还带有唐人的影子。欧、梅初显,发“自然之声”,以“穷极幽隐”之态挺立于初宋诗坛。嗣后,作为临川之宗的王安石,以不拘格律、语丰意赅自张一军;以苏轼为代表的眉山之宗,以笔力雄厚、气势磅礴自立一帜;以山谷为领袖的江西之宗,以神清骨爽、声振金石自为一体。临川灭,眉山、江西兴。南宋诗坛,理学盛,“三宗”与唐音俱衰。
三、论评江西诗派
杜甫乃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大宗主。方回通过追溯江西诗派的历史渊源,明确江西诗派出自正统,为提高宋诗地位找到了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江西诗派高举杜诗这面大纛确实为自己找到了取法的对象,成为唐诗“正宗”的直接继承与光大者。方回云:“知江西诗派非江西,实皆学老杜耳。”[4](1114)黄庭坚学诗以杜甫为最高典范,以“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以故为新”为创作法则和目标。
“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4](42)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为宋诗之冠。陈师道虽为黄庭坚的学生,但亦学杜,所谓“谓后山学山谷,其实学老杜,与之俱化也”[4](16)。陈与义为另一宗主,其地位与黄庭坚不相上下,方回评曰:“简斋诗独是格高,可及子美”,“简斋诗即老杜诗也”[4](492)。以“格高”称扬陈与义,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他的崇高地位。
袁桷评论江西诗派主要着眼于其变化,他认为其变化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有违诗道之雅正。袁桷指出:“昆体之变,至公而大成。变于江西,律吕失而浑厚乖。驯致后宋,弊有不胜言者。”[6](649)“律吕失”为声律之变,“浑厚乖”与唐诗之淳雅相悖,江西诗派走上了猎奇缒险之路。
其二,破弃声律。袁桷云:“诗盛于周,稍变于建安、黄初,下于唐,其声犹同也。豫章黄太史出,感比物联事之冗,于是谓声由心生,因声以求,几逐于外。”[6](689)从《诗经》开始至盛唐,诗之声律相通,自黄庭坚出,废比兴,倡“声由心生”,而后偏离诗歌抒发真情的轨道,以法驭情,离唐愈远。唐诗最能在声律上保持其纯正:“诗盛于唐,终唐盛衰,其律体尤为最精。各得所长,而音节流畅,情致深浅,不越乎律吕。后之言诗者,不能也。”[6](691)唐诗“不越乎律吕”和恰当把握“情致深浅”,成为后世不可移易的典范。而江西诗派则有违此典则,所谓“后之言诗者,不能也”。
其三,理学兴盛有损于江西诗。袁桷云:“(戴先生)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6](424)“理学兴而文艺绝”,说明理学的兴盛导致理与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论唐宋诗因革
宋诗演变的过程就是宋诗质性形成、成熟、蜕变乃至衰亡的过程。因革涉及唐宋诗创作和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的递嬗关系,而变化的动因离不开其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交感共振。
第一,宋源于唐。方回追根溯源,从唐诗中寻觅宋诗的纯正基因,宋诗是结胎于唐诗。方回云:“殊不知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如苏子美、梅圣俞并出欧公之门,苏近老杜,梅过王维,而欧公直拟昌黎,东坡暗合太白。”[4](18)从唐诗中找到了与宋诗一一对应的关系,说明宋诗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为自己的立说找到证据。
第二,尊唐而不废宋。戴表元自是宗主唐音,但未画地为牢,主张转益多师,博采诸家,他用“酿蜜之法”做了形象的说明。其《蜜喻赠李元忠秀才》云:
酿诗如酿蜜,酿诗法如酿蜜法。山蜂穷日之力,营营村廛获泽间,杂采众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咸甘苦之味无可定名,而后成蜜。……诗体三四百年来,大抵并缘唐人数家;裕达者主乐天,精赡者主义山,刻苦者主阆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建者主许浑。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子美之于唐为大家,豫章之于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时名人大老,举倾下之,无问诸子。自是以后,学豫章之徒一以为豫章支流余裔,复自分别标里,专其名为江西派。[5](491)
用“酿蜜之法”来学诸家诗学,不失为一种好方法。采百花之芳腴,溶液浑成而无迹;陶钧百家而自成一家,渣滓净去而无痕。这是戴氏针对宋末元初诗坛江湖诗派一味学晚唐、江西诗派及其后学独拟杜诗而言的。唐诗有其“裕达”“精赡”“刻苦”“古淡”和“整建”者,宋诗也有其“老健”者,不可拘泥于一家一派,限制了自己的取法视域。
第三,唐宋诗之“复变”。“复变”重在变能启盛和会通适变(“变而返”)。吴澄(1249~1333),字幼清,江西抚州人。吴氏从发展演变的视角看待唐宋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皮昭德诗序》云:
《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汉五言至是几亡。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变之中有古体、有近体,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宋氏王、苏、黄三家,各得杜之一体。[8](卷15第22页A面)
此序是一篇元前诗体发展演变史,阐明了自《诗经》至唐宋的因革关系,指出了其内在演变之道,这就是明人所谓“体以代变”。就唐诗的演变来说,有“三变”:陈子昂变颜、谢,此其一变;李、杜因子昂而变,此其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此其三变。不过,这“三变”也是变中有复,因中有革。而宋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家“各得杜之一体”,此三家学杜以己之性情适彼之性情且自得之,由此也说明这三家诗自身也蕴含着对唐诗因子的传承,因而唐宋诗并非凿枘难合,可众美兼具。
何以会出现这种因革变化?“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诗之体裁各种各样,诗人之才情也各有不同,故各以其才适配其体,各成一家之言,这好比自然界的“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各得其宜,均为万千大巧之一巧。吴澄还在《诗府骊珠序》中谈及唐诗内在因子的变革:
呜呼!言诗,颂、雅、风、骚尚矣。汉魏晋五言讫于陶,其适也。颜、谢而下勿论,浸微浸灭,至唐陈子昂而中兴。李、韦、柳因而因,杜、韩因而革。律虽始而(于)唐,然深远萧散不离于古为得,非但句工、语工、字工而可。[8](卷15第19页A面)
吴澄把唐代诗人的因革分为两种:一为“因而因”,即只有传承而无革新,如李、韦、柳等;一为“因而革”,即虽有传承但在革新,如杜、韩等。杜、韩诗歌已有开启宋诗门户的端倪,李、韦、柳诗则更多具有唐诗的本色;对杜、韩诗歌的肯定实际上是对宋诗新变的赞许,推而广之,也证明了唐宋诗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诗歌因革的角度来辨析唐宋诗的界域,这样更能厘清唐宋诗内在的传承和变化脉络。
第四,折中唐宋。傅若金关于唐诗和宋诗的看法,没有同时代诗人的偏见,亦不厚此薄彼。《诗法正论》云:
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昌黎后出,厌晚唐流连光景之弊,其诗又自为一体。老泉所谓“苍然之色,渊然之光”是也。唐人以诗取士,故诗莫盛于唐然诗者。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诗,子美自有子美之诗,昌黎自有昌黎之诗。其它如陈子昂、李长吉、白乐天、杜牧之、刘禹锡、王摩诘、司空曙、高、岑、贾、许、姚、郑、张、孟之徒,亦各自为一体,不可强而同也。[9](2451)
傅若金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诗莫盛于唐”为南宋以来宗唐观念的延续。关于盛唐诗盛兴的原因,他认为有两个:一是“海宇一而文运兴”和“文与时盛衰,道斯系矣”[10](248),文学的盛衰与时代息息相关;二是“唐人以诗取士”,这是唐诗高于宋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点并非傅若金的新创,却是他对唐诗繁荣原因的总结。第二,宗奉李、杜。李白天纵英才,迥出同侪;杜诗兼备众体,集诗学之大成。傅氏对李、杜并不区分优劣,由此可见,元人并未扬此抑彼。第三,唐诗风格多样又自成一体。无论是李、杜抑或韩愈,甚或陈子昂、李贺、白居易、杜牧、许浑等皆独具风貌。
五、编辑宋诗选本
元人普遍存在“宗唐抑宋”的诗学风气,人们编辑宋诗选本的热情极低,选本不多,但是元代的宋诗选本极具特色,出现了以某一类人为主的专门性诗歌选本,如《濂洛风雅》;诗社选本,如《月泉吟社诗》;遗民诗人选本,如《谷音》;分类宋诗选本,如《瀛奎律髓》;诗选和评点相结合,如《瀛奎律髓》。
《瀛奎律髓》,方回辑,凡49卷,共选录宋代五七言律诗1 671首,以时代世次选编。入选的宋代诗人中,陆游188首,位居第一;梅尧臣127首,为第二名;张耒79首,居第四;陈与义68首,居第五。《瀛奎律髓》每卷均列有小序,并附有诗人小传,诗作中大多有评注及圈点,在其评语中体现了方回的宋诗观。《瀛奎律髓》为一部声名极响的唐宋律诗选本,有明成化三年(1467年)紫阳书院刻本。
《宋诗拾遗》,陈世隆辑,凡13卷,清抄本。陈世隆,字彦高,元代钱塘人。此选共录宋代诗人781家,诗1 470首。该选无序跋,以诗人世次为编选体例;选编的意图是“拾遗补阙”。《宋诗拾遗》所选诗歌数量超过此前及其后的任何一种宋诗选本,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著名诗人一首未录,却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立传,以引起关注。
《濂洛风雅》,金履祥辑,凡6卷,第一部理学家诗歌选集,是“有关名教之书”。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浙江兰溪人。此选所录诗作从周敦颐始,迄于王偘,选录两宋48位理学诗人的诗作453首。此选集仿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例作《濂洛诗派图》,以师友渊源为统纪,以周敦颐、二程、杨时、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为正传。选录之时,按风雅之变化,风雅之正为第一卷;风雅之变为第二卷;第三至六卷为风雅之三变,所录作品为五七言古风、绝句、律诗。此选有同治八年(1869年)金华胡氏退补斋刻本。
《谷音》,杜本辑,凡2卷,是一部宋遗民诗选集。杜本(1276~1350),字伯原,江苏清江人。《谷音》收录宋遗民诗人30家,诗101首,其中可考者24人,无名氏6人,所录宋遗民诗人分为节士和幽人两类。张榘《〈谷音〉跋》谓之:“宋亡元初,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毛晋《题〈谷音〉后》云,“宋室既倾,诗品都靡,独数子者,心悬万里之外,九霄之上。或上书,或浮海,或伏剑沉渊,悲歌慷慨”[11](卷末第359页),说明了编录的目的。此选有毛晋汲古阁《诗词杂俎》本。
《宋僧诗选补》,陈世隆辑。清抄本,凡3卷,共1册,现藏南京图书馆。该选无序跋、评点和批语。共录宋代诗僧33家,诗87首,上卷录诗僧16家,诗32首;卷中录诗僧16家,诗33首;卷下录诗僧永颐1家,诗22首。在所有入选诗人中,永颐22首,道璨15首,斯植13首,位居前三位。此选对保存宋代诗僧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人对宋诗的系统研究,从勾勒宋诗发展版图、界划宋诗流派、论评江西诗派、诠释唐宋诗之因革、编辑宋诗选本等方面深入展开,各自从不同的视域展开,丰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批评上所达到的认识水准。如元人勾勒宋诗发展版图时所具有的诗学谱系意识,界划宋诗流派时所具备的宗派思想,诠释唐宋诗之因革时所独具的融通观,无不说明元人在宋诗研究方面已具备了独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