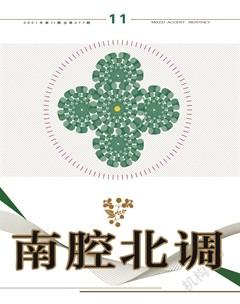想象织就的自卫式梦幻
朱星颖
摘要:“驱魔”是亨利·米修诗歌的主要诗学主题之一,它体现了米修对诗歌价值的重新定义,对于挖掘米修诗学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米修强调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他以狂热的想象、沉浸式的幻觉将现实抽象化,用文字的敲击力消解伤痛。米修的驱魔诗作为一种反击工具,其写作对象和形式多变,是诗人一生体验探索的文字表现。
关键词:亨利·米修驱魔诗 想象书写 反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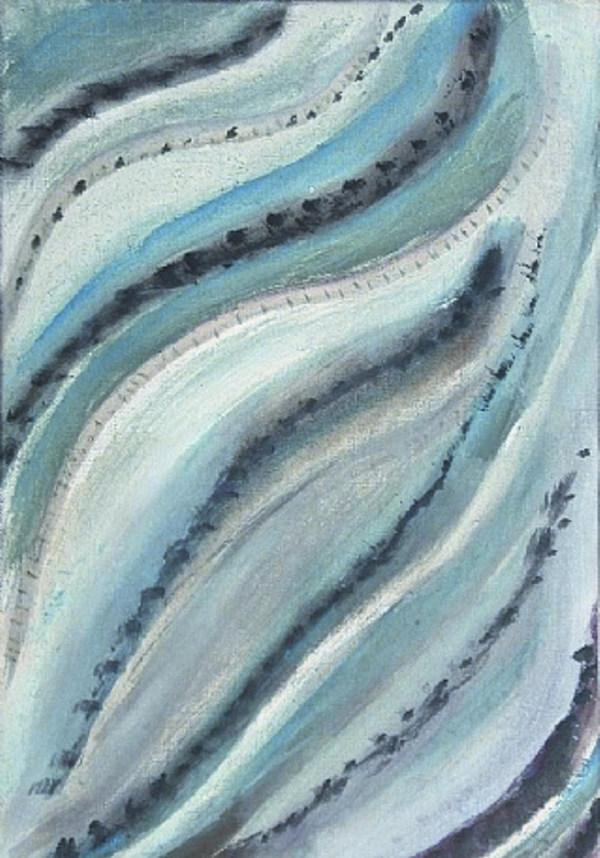
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 1899-1984)是法国当代著名的诗人兼画家,其诗以怪著称,他被公认为法国20世纪不可或缺的诗坛怪杰。米修的诗歌作品,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流派体系,却兼有超现实主义的迷幻、洛特雷阿蒙式的反叛和神秘主义的诗性世界观。在米修诗歌所呈现的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中,不難发现诗人对外部生活和内部世界的反叛性探索,米修以此“驱魔”。对诗歌“驱魔性”的追求是米修对诗歌价值的重塑,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宗旨。
米修在其完成于1945年的诗集《考验,驱魔》的序言中指出他诗歌的驱魔性质:“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某种取巧式的驱魔,我写作,为的是挫败周围敌对世界的强大攻势。”[1]在米修看来,驱魔是为了治愈生活中消失不了的心理创伤,摆脱现实中无奈的依从,“在伤痛和黑念头之处,插入无限的狂热,绝美的暴力,结合文字的敲击力,使恶渐渐消融,代之以轻盈魔媚的圆体——美妙的景状!”[2]因此,米修诗歌的“驱魔”是被现实囚禁的人在意识深处对苦难的形而上的反击。
一、抽象化的现实
米修“驱魔”的对象大到社会现实的黑暗与创伤,小到个人心里最隐蔽的苦难。米修针对他所体验到的残酷展开消解,表现社会和内心世界的狰狞,他描写现实却非复现现实,通过颠覆性的想象和狂热的暴力将现实抽象化,在文字构建的意识世界中获得解脱与胜利。
(一)战争与群魔
米修最早在诗集《考验,驱魔》的序言中提出了驱魔的作用和定义,《考验,驱魔》是他唯一一部直接以“驱魔”命名的散文诗集,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背景下,“驱魔”直接成为诗人对战争侵袭下满目疮痍的世界的呐喊与反抗,在意识层面驱除战争带给社会的绝望与创伤。
诗歌《信》与《隧道中的历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应,以写实的笔墨描述了战火焚烧下的人间炼狱——“金属从未如此坚硬,火药何曾这等暴烈,两人狼狈为奸,合伙落入无辜的人群。在这个世纪,被死亡拦住的人们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3]米修利用这一类抗战诗“驱魔”的第一步就是将他眼中的破碎与死亡忠实地以文字展现出来。《信》是诗集中用书信体写就的抗战诗,在这首诗中,米修以战争亲历者的口吻,将现实的混乱和残酷道来,在法西斯的控制下,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痛苦与绝望:“鹦鹉洲上再无孤居,坠落中,邪恶现了原形。”[4]诗句的语词之间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这种黑暗将个体湮没在时代中,代之以群起的激愤和作为时代受害者的审视。《隧道中的历程》由多首书写战争的诗歌组成,这组诗用真实而又狰狞的词汇构建了一个信仰崩塌、群魔乱舞的世界,“骨骸、尸骨、死去战士的眼睛、弹片、血肉、坟墓、阴魂”,这些恐怖的字眼是米修对现实黑暗的认知,他所描述的战争下的人性是触目惊心的,“翱翔苍天的信天翁,让绳索系住了脚,只有待在水桶边。有人将我们的兄弟缝进驴皮,将我们的兄弟缝进猪皮,缝在猪皮里,然后,把他们赶到我们中间,和我们永远在一起。啊,残杀。”[5]在这首诗里,“驱魔”并非远离现实而构建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而是针对异化的现实进行记录思考并寻求解脱。通过对战争景象的糅合与想象,诗人把战争社会的群魔立体化,展现生存的艰难,最后问道:“既然老虎伸出了利爪,人为何无动于衷?既然苍蝇已抖起了翅膀,人何处不能腾飞?”[6]这是诗人面对无止境的冬夜发起的复仇,是对现实苦难和生存艰难的共情与反叛。
(二)欲望与解脱
结合米修的创作背景看,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只是一部分,米修认为“诗即驱魔”,他把驱除苦难、摆脱虚无、获得意识世界的解脱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驱魔”是一个更广泛的手法,其所选择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在米修的诗歌创作中,对“驱魔”的实践很多,他常常以一种怪诞的幽默将现实和想象融为一体,以看似荒谬的方式在内心中驱除伤痛,使欲望获得满足,使精神得以解脱。
如诗歌《获得满足的欲望》描写为了满足伤人(那些被我视作敌人的人)的欲念,在内心中对其施以酷刑——“若有人向我板起可憎的面孔,我便把他的头塞进肩胛,尔后,处以极刑……”[7]类似这种暴力、残酷的刑罚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在诗人所谓的内心的屏幕中上演,是通过意识展开的想象。诗中没有复杂的辞藻,诗人只是直白地讲述内心的斗争过程,在现实中受到道德、制度限制的行为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在意识中完成,我们从这些诗句中,能够感受到怪诞的解放。
再如诗歌《布袋法庭》中叙述的将厌恶的人装进虚构的布袋中随意痛打的发泄方式,诗人在这首诗中仍然是将现实的艰难交给想象的反击以求获得解脱,这是没有能力的小人物无奈的“驱魔”方式,这种无奈是我们在诗歌中能够真切感受到的:“没有这门小艺术,我又如何能在众人的肘拐丛中度过沮丧贫困的一生呢?又如何在众多头领的管辖下,在失意的汪洋,打发几十年的光阴?”[8]诗人展现了在社会中生存艰难的人的无力感,因为在现实中个人的力量太过薄弱,所以只能以自我解脱的方式拯救被从属关系、社会变故、精神迷失压抑的自我,以一种荒谬的想象驱魔,向绝望发起反抗。
由此可见,以想象的“驱魔法”获得解脱,是应对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抗争欲望的无奈却合理的方法,米修的诗歌中不乏此类以内心阴暗情感为对象的驱魔。米修重视诗歌的驱魔作用,他利用文字的敲击力寻求内心的解脱,正是对现实的无力发起的反抗。
二、“驱魔”与米修的探索
米修是一个不断行走的人,他游历四方,又游走在想象和现实的边界。他一生都在寻找精神的归宿,寻找填补内心空虚的方法。法国评论家布露尔评价米修说:“他描写群魔,为的是恢复健康,摆脱夜间的晕眩,摆脱‘虚无的纠缠,那比黑暗中向我们狂吠的奇幻更怪诞更恐怖的虚无。”[9]因此,米修对内心宇宙和外部世界展开有限地或无限地探索,涉足人的心灵中隐蔽的无人涉足的领域,用他所接受的四方智慧,用狂热的想象在文字世界中展开驱魔,摆脱虚无。
米修的寻找,与他与生俱来的空虚感不无关联,这种虚空可在他行至南美洲写下的一首名为《我生来身上有洞》的诗中窥见一二,他在诗中写道:“我建立在一根缺失的脊椎上。”[10]后来他游历亚洲,感受各种文化,试图以此驱除虚无、获得盈满。米修的文化精神之乡无异是在亚洲,印度和中国对他的影响颇深,中国文化对米修有着启示作用,这在他的游记《蛮子游中国》以及之后的创作精神中都有所体现。米修的空虚感不仅是因为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深沉的内心,更与当时欧洲社会的危机感有关,在这种背景之下,米修暂时卸下欧洲本位文化,以文化中立人的身份渴求文化滋养,这种给予他新生的文化,他在东方找到了。“少女、中国、美、文化……穿过这我领悟了一切,一切以及我自己。从此我以另一眼光来看世界。”[11]在东方,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关照,这对他之后的思想、写作有直接的影响。米修在四处行走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文化,也审视着自我与诗歌的价值,他对周围的一切始终是怀疑的。因此,米修行走、寻找也是为了驱魔,为了摆脱生命中由来已久的虚无,为了探问存在。黄蓓在谈及米修对“别处”的探索时说:“旅行的全部意义,于亨利·米修,便在于离开‘原点,在移动中,实现生命的自由。”[12]
在东方的旅行中,与中国文化的碰撞,让米修发现了中国艺术。米修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同样,作为一个画家,米修享有盛名。米修喜爱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他在水墨画呈现的运动变化中,看到了线性的艺术。诗人在诗歌《线》中写道:
在墨迹中变高贵,一条细线,一画,没有丝毫臭味。
并非为了解释,并非为了展示,不重叠,不宏伟。
更像是遍地的起伏、曲折,仿佛有一群闲游的狗。
一线,一线,或多或少一条线……
碎断,起始,防不胜防,一线,一线……[13]
《线》是米修后期评中国绘画与书法而作的诗歌,在这首诗中,米修对水墨画中线所带有的艺术力量进行了分析。米修在对中国绘画展开评价时说:“中国绘画主要是山水画,事物的生动性,不是靠其厚度及其重量来表现,而是靠其线条来表现,可以这么说。中国人能够将事物浓缩为最具含义的事物。”[14]诗人意识到中国绘画之所以重线性,是为了减去现实的厚重感。米修认为现实已然是琐碎无奈的,却总有很多绘画用画笔复刻现实的狰狞,因而他痛恨绘画。而在中国的水墨画中,米修看到了绘画的另一种可能。米修将中国艺术对线条的运用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他运用想象将现实抽象化,剥离沉重和狰狞,给现实猛烈一击,以达到驱魔效果。
从1956年开始,米修开始用一种实验性的精神书写服用麻醉品后的感受,陆续发表《悲惨的奇迹》《骚动无限》《得自深渊的知识》等书写服毒经验的作品,在虚幻与真实的交织中挑战自我,游离于精神世界中找寻无限以驱魔。米修尝试在麦司卡林构建的视域中观察人以及人的精神活动,从幻觉的角度探索意识、思考现实。在服用了麦司卡林后,诗人的感官与情绪被药物放大了,声音带有了某种形态和紧张感,视觉边界模糊化,“突然间,喜马拉雅山冲了出来,比任何山都高……最后淡于天际,巨大,呆滞。”然后所有事物都消失,他看到了白:“絕对的白,超出一切的白,从天而降的白,决不妥协的白,排除一切的白……白色将在我脑海里留下某种极端的意味。”[15]白色本就是包含了光谱中所有颜色的光的颜色,所有的颜色归于一处便是白色,因此,白既是所有,亦是无。米修在麦司卡林的指引下看到了混乱的真实,在这种真实中,现实的一切都被消解、被扭曲,声音、色彩、线条等所有感官都处在一种被模糊的迷幻状态,这种混乱的真实让米修重新审视外部世界,在一种归于原始的状态中体验生命、思考存在的意义。这种沉浸于潜意识的、探索新的真实的写作形式便是米修“驱魔”之路上的一大实验。当然,这种“实验”不值得效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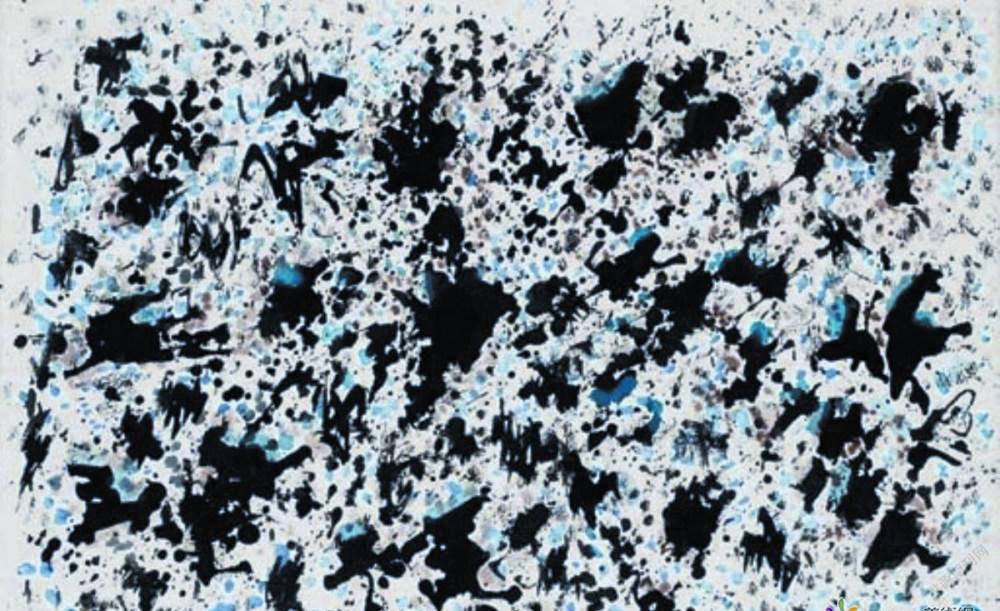
米修在创作的中后期,将探索与驱魔置于他想象的国度。他虚构了一个个奇异的国度,在这些想象的异国中有各种奇怪的人,各种荒诞的事,皆与现实相悖。大加拉巴是米修创造的一个新社会,这个世界中的各个国家有着各自的秩序,或残酷、或冷漠。哈克国崇尚搏斗,每一次犯罪活动都被视作一场寻常的节目,因此社会秩序混乱,人的生命毫无价值;在阿拉拉斯国,警察、罪犯、妓女、寻常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功用相互颠倒,土匪到警察局受训,警察到歹徒中实习,妓女充当家庭和政府的顾问。在米修创造的世界中,可以没有秩序、没有道德、没有人性,看似残酷又狰狞,但是现实的人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之所以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想象的世界,便是借无厘头的荒诞与幽默,嘲讽现实的异化与无力,在虚构世界里的随心所欲,恰恰能够抚慰现实的恶带来的疲累与绝望,以此获得精神的解脱,达到“驱魔”效果。
米修的驱魔与反叛在他不断地体验探索中完善,他怀疑、寻找、审视、再寻找,所以他渴求文化的滋养,深入潜意识探求存在与真实,甚至颠倒现实以求解脱,他正是以各种形式的“驱魔”寻找语言的活力,建立自己的文字宇宙。
米修虽然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但是他的创作是极具现代色彩的,让人在抽象中品悟现实,在想象中感受解脱,这是米修诗歌创作独特的力量所在,也是诗人一直追求的诗歌价值。当然,米修诗歌的“驱魔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实力量的薄弱与无奈,但是米修创作中真实、想象、梦幻的交织所呈现的现代反叛精神正是诗人不断探索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6][7][8][9][15][法]亨利·米修.我曾是谁[M].杜青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32,132,136,134,143,146,149,151-152,177,174.
[10][法]亨利·米肖.厄瓜多尔[M].董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2.
[11][法]雨果,等.法国七人诗选[M].程抱一,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24.
[12]贝阿特丽丝·迪迪耶,孟华,主编.交互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292.
[13]杜青钢.米修与中国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5.
[14]亨利·米修.一个野蛮人在中国[J].刘阳,译.当代外国文学,2001(02):70.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