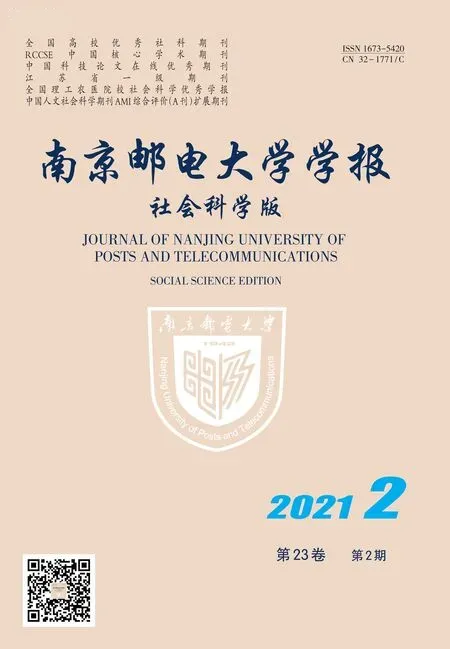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未来
——斯蒂格勒对列斐伏尔城市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发展
鲁 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城市哲学则是对人类迈入都市社会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的思想操演。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迅猛扩张与全球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巨大时空变迁与日常生活结构转型,城市空间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时代意义,它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事关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的未来,已成为哲学理论反思的重要课题。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开辟了城市空间哲学研究一股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潮流[1],其思想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诸如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保罗·维尔诺、伯纳德·斯蒂格勒等人那里产生了诸多化合反应。2020年去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试图发扬列斐伏尔城市空间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认为列斐伏尔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完全都市化的预见,如今已经从潜在的、虚拟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无可争议的社会现实。斯蒂格勒基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提出智能城市的概念,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城市化应用与发展是智能城市成为现实的重大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批判与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哲学视野在当代智能城市问题上偶然相遇了。简言之,列斐伏尔提出的都市社会问题更新升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工业城市问题,使都市社会成为一种研究范式,斯蒂格勒则在数码资本主义或者智能城市时代再次发现了列斐伏尔有关完全都市化、城市信息化、城市权利等重要理论的当代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全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总问题。作为技术批判哲学家的斯蒂格勒,侧重于从人类身体器官的生物进化史和外化史来理解城市智能的问题;与之不同,列斐伏尔则倾向于从社会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角度来理解人类空间生产、栖居的意义以及差异性的都市社会。要理解智能城市,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本文试图通过审视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斯蒂格勒对智能技术时代都市空间生产状况的独创性哲学阐释,为诊断当下都市空间的生产特征、权力机制及其矛盾后果提供镜鉴,为展望人类未来理想的城市社会图景提供一种可能的新视角。
一、自动化社会:智能城市的虚拟与实现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都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一生著述颇丰,在1968—1974年间,他集中创作出版了《进入城市的权利》(1968)、《都市革命》(1970)、《从乡村到都市》(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即《进入城市的权利》第二卷,1973)以及最终的集大成者《空间的生产》(1974)。由此,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大约在同一时期共同开创了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流派。通过将批判哲学的根本问题域从宏大的社会历史规律变迁转移到对微观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世界,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翼批判哲学焕发出新的时代色彩。日常生活、城市权利、都市革命、都市社会以及空间生产等重要哲学概念的创造,为我们打开了把握新时代、诊断新问题的别样天地。如果把马克思的著作看作是对颠倒的世界的揭露以及对矫正它所做出的尝试,那么列斐伏尔则意图为颠覆世界的使命增加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通过都市革命、都市社会、差异性社会空间的生产规划补充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革命的理想[2]。社会的完全都市化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指示了社会向一种都市社会彻底转变的前提和可能性[2]167。
首先,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空间中心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都市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以及《空间的生产》的深度阅读,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列斐伏尔在他的时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社会空间中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以及智能技术的都市化、空间化。不过由于彼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列斐伏尔没有看到也没有对智能城市问题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系统性论述。斯蒂格勒随后在《自动化社会》一书中指出,列斐伏尔有关完全都市化和信息技术的都市化思想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城市智能与智能城市社会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方法论洞见和乌托邦想象。(1)除了对完全都市化社会的想象之外,列斐伏尔还预见到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对整个城市空间的网络化结构化重塑。许多深刻而富有预见性的观点如散金碎银分布在他的著作中,例如,“我们的房屋会变成可以从各个角度透视的,能量流以各种各样的途径使用与消耗尽:水、气、电、电话线、收音机和电视信号,如此等等。它的不可移动的画面将被一组完全动态的画面所取代,被一束进进出出的导管所取代……类似的观察还可以用到有关一整条街道、一条输送导管所组成的网络上面……或者与整个城市有关。”参看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Blackwell Ltd,1991, p.93.与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一道,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重点阐述的科学技术成为固定资本与一般智力,在如今“完全自动化社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检验[3]。斯蒂格勒试图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列斐伏尔曾经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于是,自动化社会或者智能化城市社会就成了斯蒂格勒非常急迫研究的重要社会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列斐伏尔的城市图绘中,完全的都市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市化扩展甚至会达到覆盖整个星球的程度。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将这种扩张现象概括为一个“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的过程,这个过程将郊区、乡村、荒野等大片的土地空间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个支撑都市生活方式的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物质关系的总体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的总体系统,形成了世界规模的都市网络(urban fabric)。”[2]141972年,列斐伏尔对在欧洲刚刚出版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展开了研究,尤为关注马克思提出的工人对机器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是指出社会知识与一般智力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整个社会生活已经“沦落到由知识来控制”,自动化机器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直接的器官”[4]55-56,以至于,人类自身掌握的技术知识或者一般智力脱离人类的掌控而发展为资本的内在属性了[5]92-93。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逐渐转向了对空间本身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信息技术、电子机器以及诸种自动化设备逐渐从工厂空间扩展到了城市街道、日常生活空间中,与城市空间融合为一体[4]。这种融合日益使得都市空间替代工厂空间,汇聚了“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智能化的方面”[6]390。此刻,资本主义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器”[6]345。列斐伏尔启发我们要时刻关注智能技术城市化的现代性后果。
其次,20世纪末21世纪初,斯蒂格勒认为自动化社会的建立为智能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斯蒂格勒在其刚出版的著作《自动化社会:未来的工作》中强调,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工业革命初期由资本家管理的工厂空间的劳动生产过程内部,但是由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技术与电子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机器的自动化体系已经跳出工厂狭隘的劳动生产空间而扩张到整个社会空间之中了。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工业劳动技术以及生产运输的功能规划设计城市空间的,由此产生了工业化的城市革命。斯蒂格勒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无限扩张,使城市被塑造成了超级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再将这种扩张过程定义为工业化的城市革命已经不能解释我们遭遇的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向我们显现出新的景观,即由完全自动化的超工业强力带来的智能城市革命。那么这种城市空间的性质到底如何呢?实际上,列斐伏尔与斯蒂格勒都反对将如今的城市空间看作是某种纯粹量化或者技术化的企业主义单元,这就与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了,在后者那里,城市只不过是技术性的后福特主义劳动组织统治方式的完全自动化想象,它代表着整个未来社会的基本空间形态。不过斯蒂格勒批判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后者的洞见仍旧局限在福特-凯恩斯式的组织化资本主义之中。
若想要理解何谓自动化社会,我们必须回顾下福柯与德勒兹对于当今社会性质的判断。众所周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由人口的空间分配技术建构的规训社会,随后吉尔·德勒兹在《关于控制社会》一文中提出,当代大都市因为计算机的普遍发展而正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转变。他认为权力不再是通过某种规训装置来运行,而是通过可被控制的计算机网络来运行[7]。控制社会不再是固定的空间类型,而是一种液态的、流动性的空间,或者更像是“智能空间”[8]68-69。
肯定了德勒兹的重要判断之后,斯蒂格勒就抛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从1993年以来,全球技术网络体系与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具有流动性、数字化特征的所谓“第三持存”构成了斯蒂格勒提出的自动化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动力。
何谓自动化社会呢?简言之,自动化社会的实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大数据以及算法治理实现的电子网络基础设施向整个社会空间的扩张,“通过完全集成化的物联网、超控环境以及各种智能化的传感器的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地球周围环境、城市空间与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完全自动化的社会已经成为现实”[3]108。仔细审视不难发现,斯蒂格勒提出“自动化的社会”并非纯粹理论推演或者乌托邦空想,其现实条件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随着互联网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协议的全球普及,网线将被更深地嵌入到物联网中,它将构成‘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迅速成为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数字集成将使所有经济部门的自动化普遍化。”[3]93-94在智能化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表现出了更加“智能化体系化无限完美化”的观念。
最后,从虚拟到现实的转换:智能城市时代来临了。无独有偶,法国速度政治哲学家、城市理论家维希留也提出了智能化的城市群岛概念,他认为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世界化的远程在场社会,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智能住宅与数据的远程遥控,从而远程通信的线上城市化替代了地方性的线下空间城市化[9]。与维希留略有不同的是,斯蒂格勒紧紧抓住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科学知识为资本服务的普遍智能化的趋势,总结了智能城市的基本内涵,即智能城市是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所谓的高效率的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线上线下联动的即时算法治理,从而达到塑造甚至提前干预城市的空间组织和发展的城市新形态:智能城市的隐匿技术“把自己编织成日常生活的结构,直到二者难以区分开来。计算机化的城市化是由大型设备制造公司推动的,这些公司共同设计新的基础设施,并在城市区域内进行建设、维护与管理。因此,算法治理将在区域范围内以系统的方式在各个空间和时间层次上加以开发和管理”[3]104。
斯蒂格勒借用洛特卡的人类器官体外化思想反对当下城市化的技术化数码化控制趋势,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的谱系学溯源,指出智能城市是自动化社会的缩影,是在外在化器官的进化动力机制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类智力与器官的工具化外在化(exosomatic)的有机体。但是,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数码算法的全球空间尺度的技术覆盖与垄断,并没有服务于人类的居住,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新的控制与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斯蒂格勒认为这种情境是不可持续的,技术主义的城市建设思路必将导致更大的失败。于是斯蒂格勒抛出了其根本的批判性立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被所谓智能城市的营销策略掩盖了,智能城市空间生产与操纵的机制是“电子利维坦”式的算法治理。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奈格里那里可以得到互证:奈格里认为“智能城市”和“智能社会”是纯粹的迷信,一方面,它是休闲阶级的意识形态构造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被它重塑为巨大的资本主义平台[8]。
二、算法治理:智能城市时代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
斯蒂格勒对列斐伏尔的城规主义批判尤为欣赏,他试图重新利用列斐伏尔《城市权利》《都市革命》与《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的重要思想,整合维纳的控制论,香农的信息论以及海德格尔、西蒙栋、福柯、德勒兹等人的技术批判论述,揭示并批判作为固定资本的技术知识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对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政治统治问题。在列斐伏尔城规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斯蒂格勒提出算法治理是智能城市时代的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2)令人惊讶的是,列斐伏尔早在1970年的《都市革命》一书中就对算法语言与大数据的可能性及合法性进行了反思与质疑:“我们能够为计算机提供某特定问题的全部数据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机器只能使用以‘是’与‘否’为答案的问题构成的数据。而计算机本身只会对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应。此外,谁能够确保所有数据已经凑齐了呢?谁将保证这个数据大全使用的合法性呢?这种机器难道没有冒着变成掌握在压迫集团与政治家手中的工具的风险吗?”参看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M].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66页。算法治理最初是由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erns)与安托瓦内特·罗夫洛伊(Antoinette Rouvroy)阐释的一种技术乌托邦理想。毫无疑问,他们二人论述的主要核心概念取自于福柯(治理与真理制度)、西蒙栋(个体化、跨个体化以及分离)、德勒兹(块茎)以及瓜塔里(机器无意识)。不过斯蒂格勒认为,务必要将这一重要概念置入数码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中进行重构和创造性阐释[3]。
那么智能城市的算法治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机制进行操作的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斯蒂格勒首先对福柯所说的“治理”概念与算法治理进行了区分。福柯从生物政治学和治理学的概念出发阐释了权力问题:规训技术旨在“控制社会主体的最优元素,通过它我们到达社会的原子,也就是个人”,生命政治的目标是人口而不是个人,其宗旨是“利用这些人口作为生产机器”[3]109。而算法治理实际上避开了主体,在此福柯式的控制个人的技术不再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专门用于捕获数据的社交网络自动化操作和统计。算法治理抹掉了主体,因为它关注的是关系,它是一种关系型的治理,它预先消除了个体化与集体化的差异性。
第一,数码资本主义与城市数字经济试图将一切都还原为数字,算法治理在大数据、高性能计算以及各种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普遍信息化、网络化与自动化发展,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时间与空间都被数字化了,康德所谓的人类知性已经变成了自动化算法分析的权力,此种权力通过传感器以及网络驱动器根据形式化的指令进行操作,而现实的城市空间真正成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数学概念。城市数字经济就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私人数据、标记以及其他跟踪技术的基础之上。由此,智能城市时代,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能够产生痕迹,所有的痕迹都成了计算的对象。在发展“开放数据”的背景下,拥有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人们居住的所有空间都变成了数字区域。城市数字经济的算法运行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各大资本主义平台大规模收集未被分类的由用户产生的网络数据,建构可计算的数据库;二是通过接近光速的高效率的自动化计算与数据挖掘,提取这些数据个体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形成一种所谓的绝对客观的知识,从而摆脱偶然性与主观性;三是运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的数据流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例如,可以使用城市区域的智能设备预测城市居民、生产者、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流动、活动等,从而改变当地城市的区域动态,这就是所谓智能城市[10]。在这一点上,奈格里似乎与斯蒂格勒达成了共识,他认为智能城市假设一切都可以通过实证主义的方式去认识和占有,所有的城市关系都可以由理性或者数据信息控制手段来建设和塑造。
第二,在数码资本主义与智能城市空间中,空间隔离与驱逐的逻辑变得更加灵活,具有虚拟性、实时性与匿名性。列斐伏尔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强调,由于土地的私有制垄断和都市中心化,穷人、无产者、边缘人都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租金被直接或者间接地赶到了城市的边缘贫民窟。所谓智能不过是控制系统,“控制城市中发展的劳动力,控制社会剥削所必需的劳动力,控制暴力以确保社会的有序进程”[8]149。斯蒂格勒认为,大数据与算法治理核心机制就在于将一切人群、城市空间、物质活动与社会关系都同质化为可计算的数字,然后通过嵌入在城市物理空间的诸种智能设备来完成精准的预测与自动化干预。与此同时,它也不断规避、消除无法数字化系统化自动化的“歧义”(disparation),于是形成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数码真理与规范:“算法治理呈现出一种总和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中消除了创造未来的任何形式的力量、‘他性’(otherness)的任何维度,以及任何虚拟性。使失误失效,消除了世界内部可能出现中断、陷入危机的力量的可能性。”[3]120总而言之,无法被算法治理与数字化的人或者空间都被排除在自动化社会之外,对城市空间的治理使得广阔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都被殖民化了,这种殖民化正是通过算法治理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空间的数字化发展,从所谓的智能城市渗透到“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和社会环境的计算达到的,因此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短路与跨个体化的毁灭[3]。随着网络通讯技术与远程登录技术的发展,空间隔离问题与不平衡发展的危机加速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瞬间流动,全球区域发展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因世界性的智能数码经济而不断重构,形成了世界性的超级网络社会,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垄断与理论化的智力智能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这既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与灾难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第三,世界的普遍无产阶级化与身份危机。谁才是城市社会的真正建设者和使用者呢?列斐伏尔认为是用户,然而智能人则成为了城市知识的支配者。1971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超前、深奥而又带有卡夫卡式讽刺意味的著作《诌论智能人》(Verslecybernanthrope),他认为智能人是反人道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备受诟病的人机结合物(man cum machine),是装载有调节装置并沉迷于信息系统的官僚,他拥有科学理性,拥有分辨与控制能力。智能在思想和行动上取消了人文主义,抹除了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幻想[11]。在斯蒂格勒看来科学知识的外化与固定资本化过程意味着无产阶级知识的丧失的过程。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完全自动化的技术已经不再需要工人去工作,同时普遍化的自动化导致了人类大脑的去价值化,即大脑的报废,进而导致专业化分工知识的终结,于是产生了系统化愚蠢(systematic stupidity)。这种由数据经济决定的生产过程逐渐覆盖世界的主要地域空间,从而形成了世界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化。甚至,数码资本主义与大数据算法形成了一个“电子利维坦”(Electronic Leviathan)[3]233,它负责自动化社会的运营和监管,无产阶级不再是劳动生产实践的主体和社会权利行使的主体了,一切的工作知识、生活知识与理论知识都被转变成没有主体参与决策的机器的自动化运转,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身份危机[3]。
三、去自动化的智能城市与负熵化的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格勒通过智能城市技术哲学批判这个总问题,激活了列斐伏尔20世纪阐述的完全都市化的社会、空间生产、城市权利等理论的潜能,发扬了其当代价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差异,列斐伏尔自始至终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通过持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升级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试图建立或展望一种消除同质化抽象空间统治的差异性社会主义理想空间。而斯蒂格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借助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人类生物学的工具进化史或者说是人类器官不断外化的历史,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理解为技术不断熵化的历史。斯蒂格勒的未来社会理想是建构一种去自动化、反对计算主义的逆熵化的社会形态。
借助勒鲁瓦-古兰的技术人类学外在化思想,斯蒂格勒认为数码资本主义与算法治理霸权性地服务于一种超级中心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加速了消费主义对世界破坏的节奏,认为这是人类存在的语法化、程序化,是基于计算机化程序将日常生活节奏殖民化为一种被管理的自动化社会节奏[3]。同时这也是全球性的高速、大规模的毁灭过程,自动化与数据化的控制建立了一种结构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熵(entropic)的剧增[12]。所谓“熵增”即是指数字资本主义的自动化社会不断加速,它必然会破坏社会生活与生命的有机组织,并且导致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与知识丧失,以至于无产阶级成为机器编码程序中的重复性系统性操作的数字符码,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与认知都不再是真实的而成为了大数据算法程序生产出来的标准模式和数码拟像,这便是不断熵化的人类纪。而斯蒂格勒力图寻求一种去自动化负熵化的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去自动化的城市创造,才可能发明新的城市知识,这种知识将城市理解为人类智能的集体化的体外化器官,实现“智能基建”[13],重塑城市并使其适宜人类居住。斯蒂格勒最后给出了他的规划:通过城市智能中涌现的贡献型城市经济,充分利用数据化的共享进行反熵化的斗争,以智能化的公有制的共享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动化技术,重新夺回居民对城市的权利,将城市变成集体创造的作品与自治区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