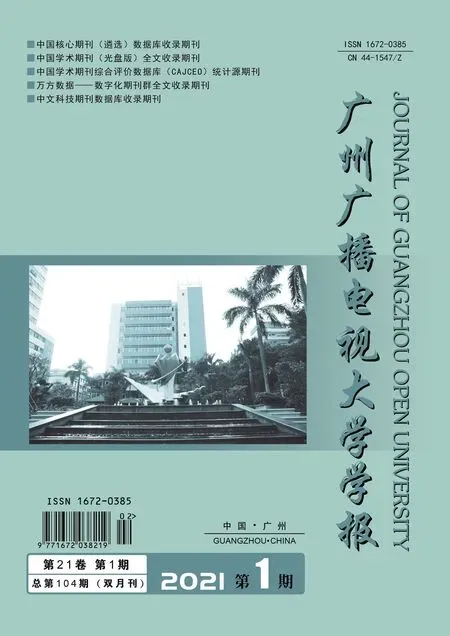走向现代的焦虑
——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冯 达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1岁时,沈从文离开乡村来到北京,学历低的他,想进大学读书,结果不成,便留在北京一边自学一边练习写作。他的前期小说文笔粗糙,几乎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熟练掌握,小说结构相对松散,显得不够成熟,可是具有写作才华的他成长很快。三十年代开始,沈从文写出了以湘西地区为主题的佳作,这些小说使他名声大噪,渐渐闻名于文坛。那些注重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似乎才符合他“乡下人”的气息,这些乡土小说也使得他获得了“文体家”的美誉。
沈从文怀着理想到了北京之后,除了期间短暂回到湘西,便一直寓居城市。不论他是否抱着成为一名“绅士”的理想而走进都市,可最后还是成为了教授,负责几家有分量报刊的编辑工作,成为了一位大城市中“绅士”,在都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湘西的乡土生活始终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
一、对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抒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裹挟之下,瓦解着乡村的方方面面。沈从文不满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下湘西淳朴的风土人情遭受种种破坏的趋势,在他的作品里努力打造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乌托邦式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似的乡土世界,着力描绘山水画般山灵水秀、悠远静谧的湘西边地,那里人性淳朴,未经现代文明的腐蚀与侵染。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境界中隐含他对现代文明带来糟粕与丑陋的批判。
沈从文时不时提起自己“乡下人”的身份,给萧乾写《篱下集》题记时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1]还曾提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2]即使沈从文迫切地融入城市,使自己混成了城里人,可是思想态度、性格气质、审美理想依然与现代都市人格格不入。他笔下的城市生活终究无法与如诗如画的边城世界相比拟,对现代文明下都市的人性进行了嘲讽与戏谑。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对沾染着商业世俗气息的海派文化嗤之以鼻,对洋场文化的排斥,未经污染的、淳朴民风的家乡自然成为了抒写的对象。作家明显的情感取向在小说中有所投射,魂牵梦绕的乡土与喧嚣丑陋的二者相互对峙、水火不容。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很少对城市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洋场风景、城市空间等进行细致地描绘,而是着重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对都市人性的探索。比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或人的太太》《有学问的人》等小说。《八骏图》写的是八位大学教授来到青岛海边度假,揭橥了道貌岸然的绅士知识分子们压抑的扭曲的恋爱态度与病态心理。雍容尔雅的外表之下个个虚伪庸俗、无聊猥琐,压抑着内心的情感与欲望,最终愈加严重乃至变态。《绅士的太太》里的绅士与太太逢场作戏,夫妻之间心照不宣地玩弄着对方,只有瞒和骗。绅士迂腐放纵,荒淫无耻,与其他女人搞暧昧;太太浅薄无聊,乱伦放荡,与西城的大少爷发生乱伦行为,充溢着强烈的物质欲望。《都市一妇人》中历经多次爱情的女子,韶华渐渐逝去,担心与自己相恋的年轻英俊的军官嫌弃她,将她抛弃,便用毒药将这位军官眼睛毒瞎,以便与他长相厮守。虽说妇人对这位英俊的军官感情真挚、一往情深,却使用自私甚至病态的手段来达到自我的目的,小说批判了都市社会中自私自利、变态扭曲的爱恋关系。《或人的太太》《有学问的人》同样写的是都市人不正常的、扭曲病态的两性关系。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描绘了山水画般山灵水秀、悠远静谧的湘西边地,这里人性淳朴,未经现代文明的腐蚀与侵染。他独辟蹊径,想象着与都市空间不同的湘西景色,渲染了环境的牧歌性。《边城》中对茶峒的景色毫不厌烦地再三描写,吊脚楼、河水、山头、河滩等自然景物融为一体,独具风味。《雪》描绘了远离都市,静谧闲适的雪的世界。《菜园》中种了不少花木的玉家菜园,晚风中飘来沁人心脾的花香,秋天时开满了一地的菊花。《萧萧》中乡村夏天的光景、温柔的晚风、绵密的落雨、作物的收成等组成了浑然天成的风景画,萧萧的命运置于诗一般的意境之中。这些优美的自然风景的描绘不是多余之笔,可以说写景就是写人,来烘托人性。沈从文所推崇的人性,决不是他所刻画的城市里那种病态的、虚伪的、怯懦的人性,而是在湘西世界中自在的、健康的、充满生命强力的人性。
二、理想主义色彩与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沈从文对湘西的神往或许过于执着,把湘西人情风俗以及人性想象的过于美好,并且醉心于塑造与城市相对立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久居都市的他为何对乡村风景恋恋不忘?难道仅是风景秀丽让人痴迷?与其说他是对乡土风景的依恋,倒不如说他“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3]这里人性便是处于未被外力扭曲的自然的状态,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三三》中的同名主人三三情窦初开、纯净温柔、善良机敏,被城中来乡下养病的年轻男子扰乱了朦胧的未觉醒的情思,随着城里青年的病逝,内心又复归平静,最终三三和母亲并没有去城里,继续守着碾坊,平静地生活。《丈夫》描述的是黄庄过于贫穷,为了生活,男子让妻子老七到县城沿河的码头上做船妓,来补贴家用。乡下的丈夫带着地里的土产来看望妻子,看着自己的妻子接待其他男人,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最后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乡下。《萧萧》写的是一个童养媳的命运,作者并没有像其他乡土小说家那样,叙述宗法制农村下童养媳被压迫、被虐待的悲惨经历,而是给了萧萧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被帮工花狗大骗取身体之后怀了孕,她并没有按照习俗被沉潭或者发卖,顺利地生下了男婴,像以前那样继续生活。《边城》更是一首对淳朴干净的人性的颂歌,翠翠天真善良、清纯温柔、机敏可人;老船夫忠于职守、老实厚道、慷慨豪爽;官兵们与民同乐,连商人们也重义轻利……这些乡土小说里都寄托着沈从文对理想的人生形式的一种思考,他试图建立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桃花源”。都市文明对这里的影响微乎其微,像一阵微风吹过平静的水面一样,引起阵阵涟漪后水面又复归平静,这是对商业化、物质化、世俗化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反拨与挑战。
沈从文天生的保守性,努力地坚守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边城》中那个象征着湘西古朴文化的白塔在一夜之间倒塌,后来又被重新建起。《牛》讲的是孤独的农民大牛伯与牛相依为命的故事,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牛是耕种庄稼的重要生产力。小牛在大牛伯的眼中不仅是畜生与工具,而是具有灵性的“人”,大牛伯与小牛之间在劳作中建立起了深深的温情,小牛强行被征收,侧面展现了对和谐温情的乡土文明的破坏。大牛伯的焦虑与懊悔,也正是作者对乡土农村受到冲击的焦虑与隐忧。《新与旧》写一个名叫杨金标的战兵充当刽子手,在清朝光绪年间负责执行犯人的死刑,杀了犯人之后便跑到城隍庙请罪。民国十八年的时候,杨金标被召去处决两位有共产党这一政治身份的中学教员,事后再次到城隍庙请罪的时候,被当做疯子,最终惨死。沈从文对“新”与“旧”有着自己的理解,对“新”势必战胜“旧”,新比旧好,未来必定比现在好的进化论观念表示怀疑,对势在必行的现代性变革提出了质疑:“新”未必比“旧”好,这也体现了沈从文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内在原因。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讲述的是在北溪村设“官”的风波,打破了这里原本宁静的生存状态。北溪村的七个男子试图阻挠政府在此设官,均已失败告终,无奈一起搬到山洞里做起了野人,暂时摆脱地方官征税与其它束缚,设官后的第二年,过完了迎春节,七个野人便全被杀头了。官和政府给北溪村带来了征税与杀戮,暴力地破坏了北溪村本来原始的、自由的、安详的生活方式,七个野人尝试着捍卫家园,守护着乌托邦式和谐美好的湘西,野人的悲惨命运,也是湘西被损坏的命运。沈从文的情感倾向十分明显,作者乌托邦式的想象正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持厌恶与批判的态度,对乡村正在走向墮落表示担忧与焦虑,这篇小说诉说的正是乡土文明走向崩溃的悲凉挽歌。
三、民族性格与文化重构的想象
苏雪林认为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4]沈从文对都市人病态的、畸形的、委琐的都市病的批判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甚至认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5]他的这种“偏见”出于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走向未知的命运时,内心涌出的忧患与焦灼。沈从文有着自己的“野心”,他对湘西的塑造可以说是对中国走向现代的一种想象,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提供自己的设想与方案。
沈从文的一些小说洋溢着狮子式的雄强的生命力,他推崇的是乡村那种朴野的,像动物一样的原始的刚强的民族性格。他声称自己“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6]小说《柏子》写水手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性爱故事。柏子精力充沛、潇洒自在,爬上船桅上嬉笑唱歌,不惜把出航冒险一两个月才赚来的金钱物资,全都花在相好的妓女身上。满足自己的性欲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回到船上做工,始终保持着这样自在的状态。《边城》里男人们粗犷、豪迈、精力充沛。男性佩刀、决斗,发生流血也是常见的事。《虎雏》写“我”极力想驯化一个跟着六弟外表乖巧的青年勤务兵,不顾六弟的反对,把他留在“我”身边读书,想把他改造成一个知识分子和绅士。可是青年勤务兵流淌着湘西人难以驯服、强悍的血液,改造因勤务兵在城市里杀人畏罪潜逃而告终。《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七个男子真诚勇敢、天性自由,不甘接受“官”的管理,继续痛饮,欢度着迎春节。《龙朱》中苗族族长的儿子龙朱“美丽强壮像狮子”,他美丽、温顺,是权威,是光,他被赋予了人类几乎所有的高贵的品格。这些完美的、强悍的、雄强的人物性格寄托作者的完美人格的理想,来替代那些庸俗的、怯懦的、空虚的性格。
沈从文还有一些大胆描写性爱的小说。笔触清新自然,不虚伪做作,不流于猥琐低俗,展现的是一种健康自在的生命状态。《采蕨》同样写的是在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环境中青年男女的性爱故事。《夫妇》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南山,不避白天在南山坳做爱被村民抓住的故事。这些年轻的男女似乎不懂什么叫做下流,只是在原始性欲的指引下,在自然的见证之下,无所顾忌地展现着自我的性欲,恣意享受着情爱,赞美着优美的自然与炽热的情欲。《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小说写的都是爱情的悲剧,但是所描写的爱是如此热烈。他笔下的情爱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质朴健康,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对身体充满肉欲的刻画而流于情色,爱情被描写的那么惊心动魄乃至达到了人性的极致。
拥有健康的、刚强的性格之后,老迈龙钟的民族便有了新鲜的血液,这样的性格在世俗化的都市中可能会被磨平了棱角。长久生活在城市中,不免沾染了世俗的气息,生命俨然渐渐空虚,只剩一个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如何在商业化的都市洋场中避免生命力的萎缩?长篇小说《长河》写现代文明来到了湘西,表面上现代的生活用品普及了这里,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实际上国民党当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对湘西乡民的压迫与剥削,对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的破坏。面对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人际关系与处事态度面临着瓦解的境况,湘西乡土社会中直率、慷慨的人性或许才是缓解民族衰老的灵丹妙药。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塑造了田园牧歌的湘西世界,他对湘西的乡村进行了理想化和留恋式的抒写,对民族的未来充满焦虑与担忧,对现代文明的入侵乡村持警惕、批评和拒绝的态度,借此来重塑民族性格,使民族焕发活力,以争取未来民族的生存权利,这才是沈从文创作的深层原因。他对都市文明的反感,对乡土人生式样的亲近与皈依,往往被贴上“反现代”甚至是“反动”的标签。西方的现代性表现出对进步的时间观念信仰,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而沈从文的思想却与之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沈从文给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