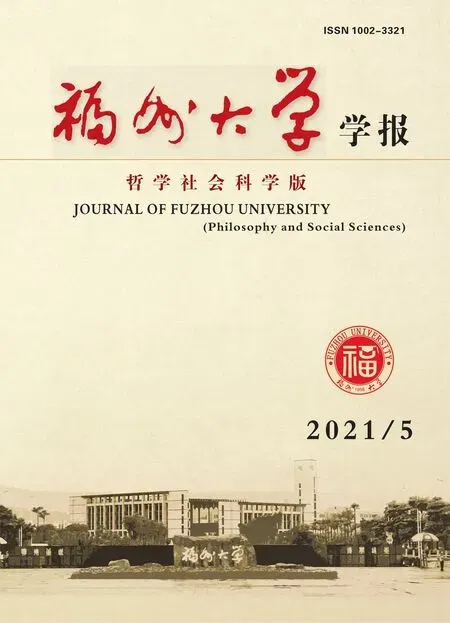严复“新民德”教育思想简论
黄德焱
(宁德师范学院, 福建宁德 352100)
近代中国由盛转衰,国力贫弱,曾让李鸿章感慨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是变局,前者对中国而言是外部力量介入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后者则是内部发展需要寻求机遇和变革。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博弈再次凸显,这种博弈,本质上仍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博弈。
一、道德之殇:社会转型与道德失范
“教育救国”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方时,探索出的一条不流血的改良之路,他们认为救亡图存要从国人的改变开始,通过教育教授技术、改变观念、变革制度,从而实现国民素质的提升。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面对教育的缓进与革命的激进,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的理想不时为频发的战乱中断。在当代中国,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社会在知识普及和技能方面的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智育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当受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时,可以看到的是普遍的焦虑感也在社会中蔓延。学校教育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知识教育、应试教育上,与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能力相关的道德教育、实践教育往往被忽视。
教育之于国家、民族、个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育背负着一个国家、民族以及个体全部的希望。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科技飞速发展令人应接不暇,制度建设常常滞后于应对层出不穷的科技变幻。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每个人都是道德的法官,键盘侠们在网络上喊打喊杀,戾气十足。各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维凸显了我们偏狭的视域,也反映出许多公共领域道德的缺失。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关于现实人性的反思。正如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凯伦·奈亚里(Kamran Nayeri)在其文章《作为文明危机的新冠肺炎的流行》中所说,新冠病毒不是文明的终结者,但它是一场测试,包括对人性的测试。[1]灾难之下,更能显现一个人是否具备“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他人隐私和权利的尊重”[2]。“走向世界”固然是发展的目标,但“重返人类”亦是需要守住的底线。社会急剧转型期,道德容易陷入失范状态,就如同近代救亡图存的中国,又比如在全球化时代寻求转型的中国当下。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严复,是“中国近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第一人,真正立身严正并用理智思考问题的第一人,真正能将西方近代典型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3]。1861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教育论——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书出版,严复深受其影响,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当时的中国,“民力已堕、民智已卑、民德已薄”[4], 严复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性问题,他认为要想自强保种, 首要的是“新民”,即提升国民素质,培养现代公民。在这种认识指导之下, 严复将“鼓民力 、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5],他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尤其重视学校教育,其相关论述初步构建了现代教育体系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国民,这是严复“三民”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的尝试。严复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超越,也是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超越。
二、新民德要义
1. 新民德之标的:培育“公治之德”
深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提出德、智、体三者并重,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但后来严复却认为,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理念,作为教育者应该审时度势,突出轻重。他说:“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6]严复认为,国家的竞争表现为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溃败,固然有封建统治腐朽、国力贫弱、制度落后等原因,但国民素质低下,缺乏对国家的责任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军火商人用铁渣沙泥等渣滓冒充火药掺入炸弹以牟取暴利,此种罔顾国家安危、百姓安乐的利己行径凸显了“民德已薄”,“新民德”教育刻不容缓。严复在其所译《群己权界论》中得到启示,认为需要划分出“群”“己”界线,才能更好地实现“群”“己”利益的平衡。与斯宾塞强调社会应为个人造福有所不同,严复很重视群,并从“保群”“合群”的角度来理解个体存在的意义,他更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所以“新民德”意在除旧布新,中国传统社会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家国同构的伦理前提下,忠君即为爱国,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逻辑上转化为君民关系,即一种私人之间的道德伦理。严复批判传统伦理强调的私德,他认为社会需要的是“公治所需之道德”,这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处理群己关系平衡、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所在。梁启超也曾经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7]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传统中国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中,修身养性、克己复礼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道德要求维系的是私人关系[8],所以道德规范只在熟人社会里有效,并且因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因而公共领域旁若无人的喧哗、混乱无序的插队、随意丢弃的垃圾比比皆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生活圈子从熟人社会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陌生人社会,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并存的社会结构格局,要求我们的道德规范从熟人网络延伸至更广泛的公共空间,从“自扫门前雪”延伸到“关心他人瓦上霜”。道德教育亟需建设其公共性、社会性的一面,即培养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他人隐私和权利的尊重、对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宽容”[9]。
求变图存的近代中国需要“公治之德”,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格局变迁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公治之德”仍需建设。斯宾塞说过,在他人变得幸福以前,没有人能完全幸福。自扫门前雪未必就能获得幸福,他人瓦上霜未除,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西方现代道德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先生认为,道德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而并非是固定、绝对的道德真理。道德教育有效会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地上划一条线是为了拦住人,拉一条警戒线再配上一个监督员也是为了拦住人,显然前者的成本要低得多。发展道德的公共性向度,道德教育应指向群己关系的构建,而学校正是这样一种能够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连接起来的具有真正社会意义的中介组织。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0],借助学校这个载体发展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向度是应有的路径选择。
2. 新民德之路径:学校教育实践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新式教育的兼容并蓄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从英国留学归国之后,先后履职于近代中国的各大新式学堂,并于1912年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受教育与从教的经历,让严复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严复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德育,重德育却并不得法。他重视学堂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的学校教育设置来践行“三民教育论”,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虽然个体的道德教育始于家庭,但家庭中个人化的权威决定了道德教育具有情感性、情绪化的特点,并不利于道德实践。相较于家庭,学校的公共性面向更适合塑造个体道德的公共性向度。现代复杂的社会中,家庭的教育功能日渐弱化,正式教育的大规模发展日益取代了家庭的一部分教育功能,家庭结构的裂变提前了个体接受正式教育的年龄,文凭主义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延长了个体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学校越来越成为个体完成道德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场所。法国社会学家埃弥尔·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一书中谈及教育目的时,认为课堂是一个不能被推演、也不能被还原的社会,是儿童未来社会生活的试验场,因此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应是单纯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11]。学校教育在儿童道德发展中负有重任,这体现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文化面向。
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均有开设专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来进行道德教育,但应试教育模式下,道德教育主要是为考试而设,缺乏必要的实践性。课堂上传授的道德知识,需要经过学校和社会的生活实践才能真正内化为个体内心的道德准则。德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要遵循个体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小学阶段是个体道德基础的建构时期,如果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脱离生活实践造成道德基础薄弱,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个体到了大学阶段,道德感已基本确立,之后的道德发展则主要受更具不确定性的社会生活经历的影响,而非学校教育。道德教育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是在学校中得以培育。当儿童离开家庭进入学校,首先要学会的是服从学校中非个人化的权威,这种服从有别于家庭中对个人化权威的服从,它不允许有个人偏好,遵守规范是一种义务,这便是纪律精神的养成。因此,对于当前中国小学教育而言,建立一个具体的、人性化的、普适性的学生规范是必要的。例如,《小学生守则》第4条“明礼守法讲美德”,要求遵守国法校纪,但却没有明确国法校纪的具体所指,规范过于抽象,难以达到便成一纸空文。对于道德发展还处于“常规前水平”阶段[12]的小学生而言,其道德判断来自于关系亲密的重要他人——父母、老师、朋友,因此学生纪律精神的养成需要家长与学校的配合,学校建构规则环境,家长树立行为参照。例如,各小学门口拥堵的接送场面一直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时常可以看到家长带着孩子不按学校规划的接送路线行走,无视各种“禁止”警示,只图自己方便的各种违停、逆行造成交通拥堵,学校除了增派人手疏导交通也别无他法,如果适当增加规范的制度效力,约束家长的违规行为,相较于背诵规则,学校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会更有助于孩子培育纪律精神,发展出最基础的道德感。“言传”还需伴以“身教”,家长作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知行合一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为孩子纪律精神的养成构建良好的环境。
道德教育,尤其是公德教育在小学阶段打好基础,才能为未来的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做好准备,为未来生活构建一种公共精神。
3. 新民德与开民智之关系:道器一体
学贯中西的严复看到西方知识教育带来的社会进步,力主通过“开民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但在看到“民德已薄”后提出“德育重于智育”,认为学习和使用科技的目的在于利国利民、造福人类,所以学习科学不能只“言才”而不“言德”,否则不但不能造福天下,反而危害天下苍生。[13]严复提倡学习西学之长——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认为中学的“国律人伦”不可废。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曾用“马体”“牛体”形象地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14]古人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西学之所长十有八九是“器”,器本无所谓好坏,“器”若用于善事,则利人;若用于恶事,则害人。正如钱财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但如何获取钱财却有道德水平的差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歹人爱财不择手段。因此严复认为社会的维系要依赖形而上之道——即德育。[15]德育维护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是以为道;智育则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故为器。严复对于“道”与“器”的内涵诠释阐明了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开民智”需要“新民德”,德育与智育都是“利群”,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因此,道德教育无论是斯宾塞所言“为完满生活做准备”,还是涂尔干所提“培养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其终极目标都是构建起个体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群己有界,但却不可分割,这也正是严复选择通过“新民德”来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原因所在。
正如赫尔巴特指出:“教育的唯一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中——道德。”[16]道德教育的内容应渗透于教学的全部过程,目的是让学生懂得平常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自律以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比如英国人认为“道德是被感染的,而不是被教导的”。所以,不管以何种形式践行教育,教育的目标主体是人,教育既要“增长知识”,也要“开瀹心灵”。不讲德育的智育,不讲智育的德育,都是对教育目标的偏离。
三、结语
教育目标的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倾向,我们的教育目标从德、智、体全面发展到今天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德”始终摆在首位。严复早期强调智育,后来认为“德育尤重于智育”,把德育摆在首位。“民智未开”的近代需要“公治之德”以实现“保群”,而在智育过度的当代,需要“公治之德”以实现“合群”,保证“器”之为善。严复的“新民德”教育思想指向新型群己关系的构建,发展道德的公共性向度是“利群”的必然要求。“人人独善其身是私德,人人相善其群是公德。”[17]在当下教育改革发展陷入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深水区时,回顾严复的教育思想,“乃是要重新激活我们在教育中对古典经验的记忆,内在地扩展教育的时间内涵,提升当下教育的精神高度”[18]。扩展道德的边界,构建良性的群己关系,为个体发展提供更有弹性的空间和更多选择的可能性,才能为多元化的社会实现社会整合提供更多的资源。
注释:
[1] 转引自徐 贲:《疫情,放大了互联网的暴力分贝》,《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3期。
[2][9] 王伯庆:《教育的目的》,中国教育网,2013-09-09。
[3]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转引自陆小兵、王 飞:《传统与现代博弈场域中孕育的中国近代教育哲学——以严复教育哲学思想为考察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5期。
[4] 严 复:《原强》,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26a5a78e6e1aff00bed5b9f3f90f76c660374c5d.html。
[5] 杨志霞:《严复三民思想述评》,《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6] 郑银凤:《对严复教育思想的当代思考》,《世纪桥》2014年第9期。
[7][17]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2页。
[8]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
[11] [法]埃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 杰、朱楷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12] 劳伦斯·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型将道德发展水平分为常规前水平、常规水平与常规后水平三个阶段。
[13] 谢伟健:《严复科学教育思想初探》,《文教资料》 2008年第15期。
[14] 严 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59 页。
[15] 魏义霞:《严复德育思想探究》,《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6] 赫尔巴特:《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59页。
[18] 刘铁芳:《从苏格拉底到杜威:教育的生活转向与现代教育的完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