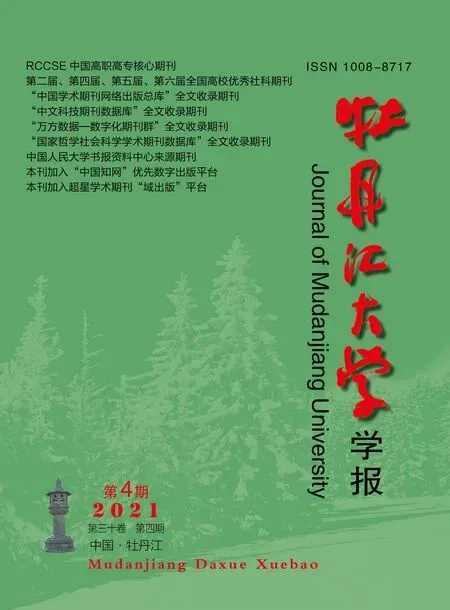布迪厄文化资本视角下严复《天演论》译述研究
江治刚 许紫薇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1972 年,荷兰裔美国学者霍姆斯 (James Holms) 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作了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主题发言。该论文对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性质、研究领域、问题设置以及学科范围提出了创建性的意见,被公认为翻译研究学派 (The Translation Studies)的奠基之作,是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尤为可贵的是,在谈及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研究(function orient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时,霍姆斯强调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对翻译作品本身进行描述,而在于描述他们在接受者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因此是语境而不是文本的研究。对于该类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就可以带来“翻译社会学领域的发展”。[1]或者,更确切地说,叫做“社会—翻译研究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因为它不仅属于社会学,而且也是翻译学的一个合理存在的领域。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对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议程。到了90 年代,翻译研究者开始系统借鉴社会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以期使翻译研究的体系更趋于全面完整,由此产生翻译社会学。翻译社会学也被称为翻译的“社会转向”,是继翻译的“文化转向”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虽然社会与文化总是交叉甚多,难以区分,但许多学者都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过阐释 (Pym,2006;Chesterman,2006;Wo lf,2007;Tyulenev,2014)。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指的是价值观、传统惯例、意识形态等因素,而社会则指的是译者可观察的行为和译者执行工作的体系(Chesterman,2006:11)。[2]也就是说,文化转向范式关注权力、伦理、价值观等因素对译者思维的影响,及其对翻译文本的操控:而社会学转向范式则关注译者行为及翻译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间相互协商、斡旋的整个过程,是对翻译这一社会实践背后宏大的社会体系进行描写与重构,并寻求解释。与以往的范式相比,翻译社会学是一个更加宏观、全面的视角。
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启蒙家,有着“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1854-1921)以“严译名著”闻名于世。“严译八大名著”中,尤以《天演论》阐述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考虑到中国近代经历的重大社会变革以及变革的复杂性,严复译述《天演论》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引起了包括翻译研究者在内的广泛学术关注,意在从不同视角切入翻译实践本身,在检视不同研究路径的同时,由此呈现翻译实践更宽阔的社会图景。崔娟、刘军显(2017:81-85)从意识形态角度入手,以“论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决定作用——以严译《天演论》为例”为题,强调译者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王家根、陶李春(2019:12-15)以“传播学视角下的严复编译研究——以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为题,讨论了严复编译《天演论》涉及的传播学问题;同样是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周楠、谢柯(2018:80-84)以“传播学视角看《天演论》的译介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启示”为题,充分论证了严复遵循传播原则及规律是其《天演论》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重要原因这个判断;赵蕊君(2020:142-143)以“译者主体性视域下《天演论》的翻译研究”为题,充分肯定了严复作为《天演论》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重要影响。综合考察以上种种研究努力,据笔者目力所及,鲜有从文化资本视角对严复译述《天演论》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尝试。
为了更全面地呈现这桩中国近代史上的翻译大业,本文将从文化资本视角切入,通过罗列与比对《天演论》译述前后严复拥有文化资本的差异,深化对翻译活动社会属性的认识,以进一步增强对翻译活动社会影响的关注。
一、翻译与文化资本
与主要作为经济学术语的“资本”稍有差别,“文化资本”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布迪厄(1997:192-193)认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即具体化资本、制度化资本和物化资本。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包括一个人有意识获得的和被动地继承的属性,例如一个人受家庭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内化于个人身上的学识和修养,我们亦可称其为文化能力。[3]制度化资本包括对个人所拥有文化资本的制度性认可,通常以学历或资格证书的形式出现。而物化资本主要指作品、绘画等实物,其物质性是可以传播的。
自翻译研究发生“社会转向”以来,翻译实践的社会属性被重新揭发出来,以揭示社会关系样态为主要研究目的的各色社会学理论逐渐进入翻译研究的理论光谱,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与翻译研究最终相遇。作为一项根植于特定社会语境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实践既是文化资本流通的重要途径,更是利用已有文化资本以积累更多文化资本的重要手段。而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改造现有社会结构。如曾文雄(2011:20-26)在“文化资本与文化会通——对明末至五四时期文化翻译观的考察”一文,通过考察中国明清科技翻译、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发现,文化会通体现翻译的宏观文化观和微观的语言观,受翻译语境影响,并对社会文化语境起反作用,最终促成中国社会变革。[4]
二、严复译述《天演论》之前占有的文化资本
严复译述《天演论》的创举离不开他当时已经占有的各种文化资本,主要存在形式包括具体化资本与制度化资本。虽然严氏1879 年英伦留学归来后,常有“局外人”之感,甚至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这样的诗句,就其获得的制度化资本而言,不可谓不丰厚。严复是官派第一批留学生,于1877 年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Greenwich College)攻读航海学专业。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1879 年学成归国后,先在母校担任教员,次年(1880)调入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前期任职洋文正教习,1893 年底以后任总办。
就其占有的具体化资本而言,严复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他的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国学造诣也非常之高。所以,严复7 岁入私塾,又请当地大儒黄宗彝开设家塾,专门为他一个人授课。黄宗彝高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品格,都深深影响着严复。留学英伦期间,严复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甚至没有上海军舰艇实习,却对西方社会背后的“通理公例”大感兴趣。他去法院旁听审判,觉得列强之所以富强,完备的司法体制就是原因之一;他陪同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去巴黎等城市考察市政,觉得到处井井有条,这是因为西方“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人民自然像爱家一样来爱城市。通过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严复丰富了自己的见闻。与郭嵩焘一起纵论中西学术,严复做好了思想改良的准备。
对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三种形式的划分,就译述《天演论》之前的严复而言,他就读洋务派西式学堂以及留学英伦辛苦获得的制度化资本并不为那些笃信科举取士的当权者所认可。当时的严复没有功名,人微言轻,他自身积累的文化资本不足以让他在清末的文学场域发挥领导作用,文人士大夫们依旧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也正是这些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资本,在具体化资本的帮助下,为严复走上“启民智”的翻译之路奠定了基础。严复希望利用已有的制度化资本和具体化资本来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大肆宣扬的“社会进化论”,希望能在“学问饥荒”的年代,振作民心,救亡图存。译述《天演论》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三、严译《天演论》及其重大影响
受甲午战败的巨大触动,信奉达尔文(Charles Darwin)自然进化论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庸俗进化论的严复翻译了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的前半部分,定名为《天演论》。初稿落笔于1895 年春,1895年3 月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初印,1898 年6 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私自木刻印行问世,为第一个通行本;1898 年12 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发行,是刻印质量最好的版本之一。因为这部译作的发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呼声震动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5]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后,称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回忆认为,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实际上,胡适的“适”字以及胡适的字“适之”都是严译《天演论》宣扬“适者生存”影响深远的证据。因此,《天演论》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还做了中学生的读物。
四、严复译述《天演论》之后积累的文化资本
据不完全统计,在1898 年以后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无法比肩的。自《天演论》之后,中国陆续出现许多关于进化论的著作,许多和进化论相关的词语,也频频登上当时的报纸杂志,为公众所熟知。正是因为译述《天演论》这项活动,在原有文化资本基础上,严复积累到了更多的文化资本,提高了他在文学场域乃至权力场域的地位,进而对当时社会意识的塑造与社会结构的改造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一)具体化资本的积累
严复积累的具体化资本主要源于与当时文坛领袖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甚密过从,严复在古文词上深得吴的指点。翻译《天演论》期间,严复经常与吴汝纶通信,吴还为该译作写了序言。此外,按照吴的建议,将最初在《天演论》译文中掺杂的自己发挥的文字一律归入按语附在译文后,成为现在定本的样式。[6]
按桐城派要求,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必须简洁、雅驯、严整、流畅而有生气。在翻译《天演论》时,吴汝纶要求严复在译文中尽量“化俗为雅”,[7]严复深以为然,随之采用精妙的中文以阐发原作者用文字表达又隐藏于文字背后的那些更为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严复能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总结提出“信达雅”这样的翻译标准“三字经”,与这些审美要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通过不断借鉴吸收桐城派的精华,严复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渐次提高,从而转化为自身的具体化资本,内化了的学识和修养使他能够更好地投士大夫阶层的语言表达之好以扩大“社会进化论”在上层统治阶级的影响力。在严复看来,《天演论》及其社会发展的观念必须以占据权力场域中心位置的统治阶级为受众。[8]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他们才是能够影响其他人的有影响力的人。希望他们可以顺应社会发展大势,主动完成自上而下的变革。
当然,严复对古文的追求并非故意玩弄辞藻,他也决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翻译家,而是一个真正“开眼看世界”的启蒙思想家。文化能力的提升和积累使严复能以其“雄笔”更好地向国人宣扬“生存竞争”“救亡保种”的爱国主义呐喊,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李泽厚在《论严复》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9]他所选择的译作表述形式,体现了他对“生存斗争学说的诠释和对社会进化论的反复思考”。[10]
(二) 制度化资本的积累
严复积累的制度化资本突出表现在各形各色的“官职”上。伴随着译述《天演论》,严复文名大噪,声名远播,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也多了不少煞有名头的“官职”,如上海复旦公学校董、中央教育会会员、北京大学校长、资政院议员等。同时,严复也被誉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和翻译家,毛泽东同志称他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此外,以译述《天演论》弥补科举考试屡次不第之憾,为其积累制度化资本。因自觉“习旁行书”而备受排挤的严复自1879 年回国,自知读洋书、学洋务非官场正途,曾先后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结果都不理想。当其时,严复明白维新运动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但作为多次科举落榜的边缘人物,他无能为力。只有在文化场域占有更多资本,他才有话语权。因为这桩译事,科举考试没能带给他的制度性文化资本,《天演论》做到了,从而为他赢得了在社会文化场域的重要地位。
(三) 物化资本的积累
严复积累的物化资本主要是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译名著”以及以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而蜚声翻译界的《天演论·译例言》。
就《天演论》传播的社会进化思想而言,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不啻于一场思想界的大革命。严复以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为武器,向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强权政治发起大胆的正面冲击。《天演论》的发表让严复声名鹊起。他和朋友王修植一同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也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直接促成了后来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之风。[11]因此,严复久负中国近代社会“西学第一人”以及思想“盗火者”的盛名是公正的,也是客观的。这样的物化资本因其难得一见故而尤为可贵。
实际上,“信达雅”在译学场域的地位丝毫不逊于“适者生存”在中国近代社会场域的影响力。一方面,“信达雅”的提出是我国传统译论向翻译理论体系化迈进的一次重要尝试和巨大进步,与之前甚至之后那些重直觉、碎片化的静态化译论截然不同。[12]这也是自提出之后,被奉为翻译标准之圭臬,一直备受关注,并且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信达雅”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章学,深得中国古典美学之精髓,不仅奠定了严复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的尊高地位,在中国文坛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我们还注意到,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资本流动与传播与源语文本声望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文化资本会从享有盛誉的文化流向相对贫弱的文化。[13]具体到《天演论》的译述,在当时英美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空背景下,中国文化处于待填补状态,外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很容易占据本地文化话语的中心地位。所以,在译述《天演论》过程中,赫胥黎“社会进化论”携带的文化资本自然而言地转移到了译者严复身上。
作为一位主要通过译介西方社会学思想以启蒙国人的近代知识分子,严复积累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译述《天演论》这项社会实践来完成的,译述《天演论》前后的文化资本对比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看,译作《天演论》作为物化资本,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为严复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化资本,从而极大提高了他在文学场域的地位。
进一步而言,因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可以说,积累了大量文化资本的严复就有了自己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资本关涉的种种社会关系网,社会地位提高了的严复可以更好地积累文化资本,比如之后严复又陆续翻译了《国富论》《社会通诠》《论法的精神》等西方重要人文社会学著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知识阶层的显耀地位。
五、结语
紧随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发生的翻译研究“社会转向”,让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域。作为西方社会学的重要人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虽然源自社会学,却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景象。本文以布迪厄文化资本及其分类为理论视角,重点考察并比对了严复译述《天演论》前后占有以及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情况,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的文化资本变化情况,突出了翻译实践在文化资本流通与积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