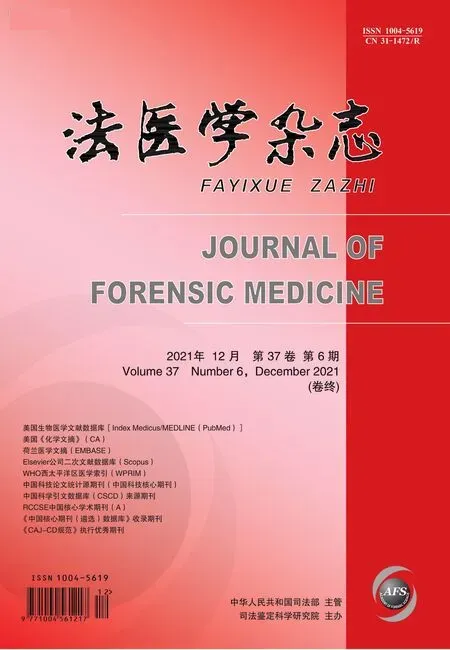医疗用药品的滥用问题与防治
孟适秋,时杰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北京100191
药物滥用是指出于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地使用具有依赖特性或潜力的药物[1]。近年来,医疗用药品的滥用日趋严重,在损害个体身心健康的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和经济压力[2]。易被滥用的医疗用药品主要有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曲马多、美沙酮、芬太尼等)、镇静催眠药(如苯二氮䓬类、非苯二氮䓬类等)以及中枢兴奋剂[如利他林(哌甲酯)、阿德拉(苯丙胺盐混合物)等用于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和莫达非尼等治疗过度嗜睡的药物,俗称“聪明药”]等[2-3]。《2017 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4]显示,2017 年我国医疗用药品滥用和使用率(2.8%)总体明显降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滥用和使用率为2.5%,比2013 年(4.9%)下降了2.4%;滥用和使用率最高的前5 种医疗用药品分别为吗啡(含控释片和缓释片)、曲马多、地西泮(安定)、美沙酮(口服液和片剂)、复方地芬诺酯。本文综述了阿片类药物、镇静催眠药、中枢兴奋剂等医疗用药品的国内外滥用趋势与危害,总结了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管控措施与防治策略,以期为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管控和防治以及未来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 阿片类医疗用药品的滥用与危害
阿片类物质是指任何天然的或合成的、对机体产生类似吗啡效应的一类药物,具有缓解疼痛等作用[5]。阿片类医疗用药品滥用具有地域差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9年度报告[6]显示:北美、西欧、中欧、大洋洲是全球阿片类药物使用量最高的地区,2016—2018 年阿片类药物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比利时。以美国为例,2018 年美国共有67 367 人死于药物过量使用,其中70%涉及阿片类药物[7]。滥用阿片类药物的种类也有所变化,1999 年美国由于阿片类医疗用药品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开始显著增加,2010 年由于海洛因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开始显著增加,2013 年以芬太尼类物质为代表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开始显著增加[8]。芬太尼是一种强效阿片类药物,其镇痛作用约为吗啡的100 倍,作为一种强效麻醉性镇痛药,在外科手术中普遍使用。在过去20 年,以芬太尼为代表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使用呈指数增长,直到2018 年才略有下降[6]。2017 年,美国以芬太尼类物质为代表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死亡人数高达2.9 万人,相比2016 年增加了47%,远超海洛因及其他毒品。为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2017 年10 月,美国宣布正式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2018 年死于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数下降至4.48 万,较2017 年下降了2%,但以芬太尼类物质为代表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有关的死亡人数占2/3,相比2017 年增加了10%[7-8]。
我国滥用和使用率最高的前5 种医疗用药品中阿片类药物有3 种——吗啡、曲马多、美沙酮(口服液和片剂)[4]。吗啡是一种强效镇痛药,我国2017 年共报告滥用和使用吗啡(含控释片和缓释片)2 531 例,滥用和使用率为0.9%,与2016 年持平,但与2013—2015 年相比显著升高,排名由2016 年的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4]。曲马多的镇痛作用为吗啡的1/10~1/8,镇咳作用为可待因的50%,我国曲马多滥用和使用率从2013 年的1.9%持续下降至2017 年的0.5%[4]。美沙酮主要作为海洛因成瘾的替代治疗药物,2017 年我国美沙酮(口服液和片剂)的滥用和使用率为0.2%,较2016 年的1.2%显著降低[4]。可待因具有良好的镇咳、镇痛作用,可待因制剂(止咳药水)滥用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我国2017年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滥用和使用率为0.3%[4]。
阿片类医疗用药品滥用带来众多危害。首先,阿片类药物滥用可引起脑结构和功能变化,长期使用处方阿片类药物会导致情感、冲动控制、奖赏、动机相关的脑区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患者双侧杏仁核的体积明显减少,前脑岛、伏隔核、杏仁核等脑区功能连接显著降低[9]。其次,阿片类药物滥用会增加患躯体疾病的风险。前瞻性队列研究[10]发现,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且两者之间存在剂量依赖性。研究[11]发现,随着阿片类医疗用药品在慢性非癌性疼痛患者中的广泛应用,大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尤其是可待因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过早死亡率增加相关。可待因在体内可由细胞色素P450 2D6(cytochrome P450 2D6,CYP2D6)酶转化为吗啡,导致血液中吗啡水平升高,由于遗传变异的原因,部分患者对可待因代谢较快,特别是超快速代谢的儿童,容易在服用治疗剂量可待因后导致呼吸抑制甚至死亡[12-13]。再次,阿片类药物滥用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关于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数据(2000—2012年)的回顾性队列分析[14]发现,每日吗啡最大使用剂量增加较快的人群,新发抑郁症的概率也随之增加。使用阿片类药物还会增加子女自杀的风险,研究[15]发现,有1 年以上阿片类药物使用史的父母,其子女自杀风险显著升高。美国的一项针对非自然死亡孕妇的研究[16]发现,其中54%与处方药(尤其是阿片类药物)相关。纽约1 970 名自杀者中,16.4%与处方类精神药物有关[17]。2016 年美国缅因州因药物滥用被逮捕的2 368 名罪犯共涉及2 957 种物质,其中59.8%涉及列管的处方药物,6.8%涉及未列管的处方药物;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丁丙诺啡和羟考酮)滥用占逮捕人数的一半以上(51.3%),其次是兴奋剂(29.0%,如可卡因)和镇静催眠药(7.6%);2016 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涉及羟考酮的被捕人数显著减少(51.9%),涉及阿普唑仑的被捕人数增加(89.3%)[18]。关于芬太尼及其透皮贴剂误用和滥用致死以及其法医学鉴定方法已有大量报道[19-23]。国内也有关于曲马多等医疗用药品滥用死亡法医学鉴定分析的报道[24-25]。
2 镇静催眠药的滥用与危害
镇静催眠药是指能诱导睡意、促进睡眠的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广泛的抑制作用[5]。常见的镇静催眠药包括苯二氮䓬类药物(如地西泮、阿普唑仑、奥沙西泮等)、非苯二氮䓬类药物(如唑吡坦、佐匹克隆、扎来普隆等)、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如雷美替胺、阿戈美拉汀、美拉托宁等)、食欲素受体拮抗剂(如苏沃雷生)、巴比妥类药物(如苯巴比妥)、抗组胺药(如苯海拉明)以及曲唑酮等抗抑郁药。长期或高剂量使用苯二氮䓬类和非苯二氮䓬类镇静催眠药易产生依赖性。英国一项针对苯二氮䓬类药物和非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者的研究[26]发现,在1 500名受试者(16~59岁)中,7.7%的人出现一种或多种药物滥用,其中15%的滥用者滥用频率高于每周1 次。
近年来,苯二氮䓬类药物的全球使用量显著增加,其中欧洲的使用量始终位居首位,其次为美洲[6]。2017 年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27]显示,超过25 万的人群正在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且使用时间远超过建议的2~4 周。法国的一项研究[28]发现,在6 万多名接受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的人群中,用于睡眠治疗的人中有30%存在不合理使用,用于抗焦虑治疗的人中有20%存在不合理使用。2019 年,美国12 岁以上人群中有2.1%在过去1 年中滥用镇静催眠药[29]。使用或过量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均呈上升趋势[30]。一项针对2015—2016年纳入美国药物使用及健康调查的10.2万名成年人的研究结果[31]显示,12.5%的人使用了苯二氮䓬类药物,2.1%至少有过1 次误用情况,0.2%符合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障碍。在巴西,苯二氮䓬类药物的终生使用率和12 个月使用率分别为9.8%和6.1%[32]。在韩国,苯二氮䓬类药物的处方量超过其他镇静催眠药,且一直处于升高趋势,与短效、长效的苯二氮䓬类药物相比,中效的处方量更多[33]。
唑吡坦、佐匹克隆、扎来普隆等非苯二氮䓬类药物的依赖性低于苯二氮䓬类药物,但近年来使用量也有所增加,且各地区唑吡坦的使用情况存在巨大差异,每年欧洲的使用量最大,其次是美洲和亚洲[6,26,34]。美国一项基于35 427 名唑吡坦使用人群特征及使用模式的调查结果[35]显示,唑吡坦用量随着年龄(18~85 岁)的增长而增加,其中女性用药人数为男性的两倍;当年龄≥65 岁、每日用药剂量≥10 mg、持续用药≥61 d 时,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女性在非苯二氮䓬类药物滥用、成瘾及戒断中表现出更多不良反应,可能是因为体内性激素水平会影响细胞色素P450 3A4(cytochrome P450 3A4,CYP3A4)酶代谢活性,从而影响药物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动力学[36]。
镇静催眠药的滥用和误用所造成的危害是多维度的。首先,镇静催眠药可能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研究结果[37]显示,使用镇静催眠药的失眠患者精神疾病的发生风险高于不使用镇静催眠药的患者。15.7%的唑吡坦使用者出现躁狂伴妄想;26.3%的唑吡坦使用者合并其他药物依赖或滥用;47%的唑吡坦使用者并发抑郁或焦虑障碍,其中75%的抑郁障碍患者用药时长大于1 年,且日使用剂量明显高于非抑郁障碍患者[38]。氟西泮、替马西泮、三唑仑、唑吡坦等镇静催眠药单独使用或与其他镇静类药物及乙醇共同使用,均可导致自杀风险增加[39-40]。美国一项病例对照研究[39]发现,在2004—2013 年有自杀记录的成年人中,其自杀风险与唑吡坦使用显著相关。其次,镇静催眠药可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大规模回顾性队列研究[41]发现,与未使用镇静催眠药的人群相比,使用镇静催眠药的女性患甲状腺癌、乳腺癌、卵巢癌和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而使用镇静催眠药的男性患前列腺癌、脑癌和肺癌的风险增加。再次,术前使用镇静催眠药可增加术后风险。回顾性队列研究[42]发现,在术前90 d 内使用一种或多种苯二氮䓬类或非苯二氮䓬类药物会增加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尤其是在术前联合使用阿片类药物。此外,镇静催眠药对后代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临床观察发现,孕期服用唑吡坦的孕妇,分娩出早产儿、小于胎龄儿及先天畸形儿的风险较高[43]。苯二氮䓬类药物还可能增加自发性流产风险。加拿大的一项队列研究[44]发现,1998—2015 年,在怀孕初期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的1 163 名孕妇中,有375 人发生自发性流产,怀孕早期接触苯二氮䓬类药物显著增加自发性流产风险,且不同药物的风险系数不一,与日使用剂量呈正相关。孕妇同时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和阿片类药物会增加新生儿发生戒断综合征的风险[45-46]。镇静催眠药与其他类成瘾性药物联合使用的现象较常见。一项回顾性研究[47]结果表明,患者同时使用阿片类药物和苯二氮䓬类药物会增加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以及死亡的风险。多项研究[48-49]结果显示,老年人群中同时服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和阿片类药物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联合用药增加了死亡风险,也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负担。
除对身心健康的损害外,镇静催眠药的滥用还极易引发事故,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和非苯二氮䓬类药物后,可出现明显的次日宿醉现象和严重的日间功能受损等后果。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9 年度报告[6]显示,2018 年有32 例药后驾驶事件涉及苯二氮䓬类药物及其衍生物,最主要的是依替唑仑和溴替唑仑。韩国一项研究[50]结果显示,致死性机动车辆碰撞事故的发生风险与唑吡坦使用显著相关。在几种常用的非苯二氮䓬类镇静催眠药物中,与艾司佐匹克隆相比,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唑吡坦,出现创伤性脑损伤及髋关节骨折的风险较大[51]。研究[52]表明,与不使用镇静催眠药的个体相比,长期使用唑吡坦可增加严重损伤(包括头部创伤或骨折)发生的风险。瑞典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将全国处方登记系统与法医毒理学数据库相关联,发现医疗使用和娱乐性使用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受体激动剂类镇静催眠药可能都会增加犯罪和杀人的风险[53]。
3 中枢兴奋剂的滥用与危害
易被滥用的中枢兴奋剂包括利他林、阿德拉、莫达非尼等,主要被滥用于增强认知、提高学习成绩,又被称为“聪明药”或“认知增强剂”[54-55]。利他林,又称“专注达”,化学成分为哌甲酯。阿德拉,化学成分为苯丙胺盐混合物。此两者被用于治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服药后可提高注意力。莫达非尼属于促觉醒药,主要用于治疗以过度嗜睡为主要症状的睡眠障碍[54-56]。上述三者均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具有成瘾性,是被管制的精神药品。
近年来,中枢兴奋剂滥用的现象愈演愈烈,全球使用中枢兴奋剂来提高记忆力或注意力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08 年,由1 400 多位Nature读者参与的调查研究[57]结果显示,约20%的人承认服用过利他林、莫达非尼等中枢兴奋剂。一项在德国外科医生中进行的研究[58]结果显示,超过20%的人至少使用过1 次中枢兴奋剂来增强认知。超过3%的英国和爱尔兰学生曾使用过中枢兴奋剂来增强注意力[55]。2018 年一项针对15 个国家的调查结果[59]显示:有13.7%的受访者(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在过去12 个月内至少服用过1 次中枢兴奋剂来提高工作或学习表现,远超2015 年的4.9%;美国中枢兴奋剂的使用率最高,2017 年有29.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曾在过去12 个月内至少服用过1 次中枢兴奋剂,高于2015 年的20.1%;欧洲国家中枢兴奋剂使用率的增幅最大,法国的使用率从2015 年的2.7%增至2017 年的16.2%,而英国的使用率则从5.3%增至22.6%。
中枢兴奋剂会增加精神疾病、先天性心脏病、先天畸形等的发生风险。通过对13~25 岁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进行随访发现,服用利他林的患者中重性精神病的发生率为0.1%[60]。大规模队列研究[61]表明,怀孕早期服用利他林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会导致婴儿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稍增加。在怀孕早期服用莫达非尼出现婴儿先天畸形的风险(12%)要显著高于孕期服用利他林(4.5%)或者未服用这两种药物(3.9%)[62]。利他林还会影响脑功能连接。研究[63]发现,服用利他林可以增加左侧前扣带回与右侧海马旁回、伏隔核与右侧颞上回的功能连接,降低左侧扣带回与顶下回、右侧伏隔核与右侧苍白球的功能连接。
4 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管控与防治
4.1 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管控和预防
在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管控方面,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于1985 年加入了《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国务院分别于1987 年和1988 年颁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96 年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1996 年版)。2005 年8 月,国务院颁布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并经过2013 年和2016 年两次修订,旨在加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保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安全、合理使用。该条例规定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麻醉药品目录》和《精神药品目录》。例如,吗啡及其盐和各种制剂、美沙酮等均属于我国严格管控的麻醉药品,利他林、阿德拉、莫达非尼等中枢兴奋剂属于我国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上市销售但尚未列入目录的药品和其他物质或者第二类精神药品发生滥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该药品和该物质列入目录或者将该第二类精神药品调整为第一类精神药品。2007 年,我国将阿桔片、吗啡阿托品注射液列入麻醉药品管理,γ-羟丁酸(包括其盐和单方制剂)、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由第二类精神药品调整为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曲马多(包括其盐和单方制剂)、氨酚氢可酮片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2013 年,将佐匹克隆(包括其盐、异构体和单方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2015 年,将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2019 年,将口服固体制剂每剂量单位含羟考酮碱大于5 mg 且不含其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复方制剂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将口服固体制剂每剂量单位含羟考酮碱不超过5 mg 且不含其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复方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将丁丙诺啡与纳洛酮的复方口服固体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2005 年,卫生部制定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以加强和规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用管理,保证临床合理需求,严防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2007 年,卫生部印发了《麻醉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以加强对麻醉药品临床应用的管理,保证麻醉药品安全、合理使用,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用药行为。2020 年9 月1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的通知》,以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管理,保障临床合理需求,严防流入非法渠道。此外,我国依据《处方管理办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严格的处方管理制度,防止医疗用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针对阿片类药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阿片类药物尤其是芬太尼类药物滥用引发的阿片危机,包括监测流行趋势、收集和分析过量用药数据、提高公众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认识、加强阿片类药物的处方管理、与执法部门合作打击非法市场等[8]。为应对严峻的芬太尼类药物滥用的国际形势,我国政府不断强化管控措施,先后多次增加列管品种,并于2019 年5 月1 日起,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针对含可待因类的药物,多国已对18 岁以下儿童青少年限用、禁用含可待因类药物,2011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可待因从基本药物名单里删除,2015 年欧洲药品管理局规定可待因不应用于12 岁以下儿童咳嗽和感冒治疗,并建议12~18 岁有呼吸问题的青少年不应使用可待因。2017 年1 月,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修改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的公告,在“禁忌证”中明确增加“12岁以下儿童禁用、哺乳期妇女禁用、已知为CYP2D6超快代谢者禁用”等内容,并于2018 年6 月再次将“禁忌证”中相关内容修订为“18 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
针对镇静催眠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8 年更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中,将戊巴比妥、布他比妥、氟硝西泮、格鲁米特列为Ⅲ类管制药品,而其他镇静催眠药大多列为Ⅳ类管制药品。我国将地西泮、阿普唑仑、唑吡坦、苯巴比妥等镇静催眠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
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药物和不断变化的滥用趋势,这些管控措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医疗用药品的监管,实时监测流行趋势,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发现新发滥用药物并快速纳入监管。
此外,加强处方管理、宣传教育和替代药物的开发也是预防医疗用药品滥用的重要手段。各级医院应建立严格、完善、周密的医疗用药品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加强处方管理,注意用药规范,从源头上减少有滥用风险的医疗用药品的获得,降低医疗用药品滥用风险。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机构、学校、社区等应加强科普宣传,普及疼痛、睡眠障碍治疗和医疗用药品相关知识,增强民众对医疗用药品滥用危害的认识,使其提高防治意识。科研院所应致力于开发无滥用风险的替代药物,发展物理疗法等非药物治疗方法,或开展多种疗法联合治疗,减少有滥用风险医疗用药品的使用。
4.2 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治疗
关于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治疗,目前的治疗方法疗效有限,且缺乏系统研究。在戒除躯体依赖阶段,可根据患者戒断综合征的严重程度选择不同药物进行治疗。阿片类医疗用药品滥用的常见治疗药物有美沙酮、丁丙诺啡及其与纳洛酮的联用等[5,64-65]。研究[66]发现,对阿片类医疗用药品滥用患者给予短暂的丁丙诺啡-纳洛酮治疗(2 周稳定期和2 周减量期),有效率小于7%,延长治疗后,有效率显著改善,如治疗12 周有效率可达49%,但在第二次减量后下降到9%以下。对于镇静催眠药滥用的治疗,可采用药物剂量递减法、替代疗法等。目前尚无批准用于治疗苯二氮䓬类药物成瘾或戒断的药物,但一些临床试验表明,氟马西尼可以用来减轻或者缓解苯二氮䓬类药物成瘾的戒断症状[67]。在苯二氮䓬类药物停药的过程中,卡马西平和丙戊酸钠等抗惊厥药可起到辅助作用[65]。针对药物滥用所引发的继发性精神障碍,可考虑使用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等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心理支持在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治疗中非常重要,应贯穿于整个治疗,同时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也是医疗用药品滥用的常用治疗或辅助治疗手段[5,65]。深部脑刺激、经颅直流电刺激等神经调控技术作为新兴的干预手段,在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治疗中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未来需大力推动相关科学研究,开发针对不同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特异性药物和非药物干预方法。
总之,医疗用药品滥用形势日益严峻,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因此,医疗用药品滥用的防治至关重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政府管理,完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医疗用药品的管理流程,建立长效监查机制,及时发现相关滥用问题并快速响应,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普及医疗用药品滥用的相关知识,开发医疗用药品滥用的新型治疗药物和干预手段,促进医疗用药品滥用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