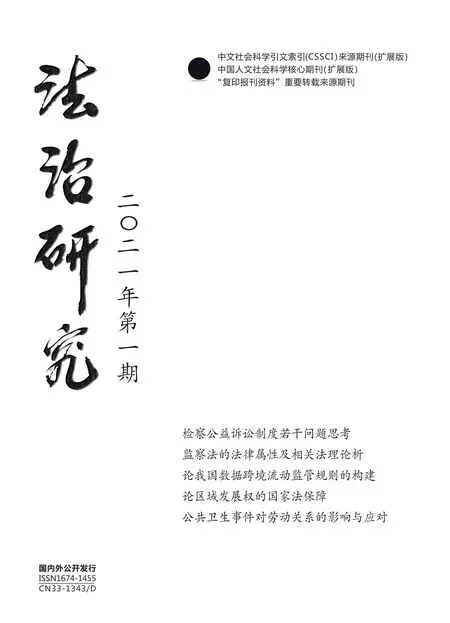我国食品安全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刍议*
李 响
一、引言
源于英国而兴于美国,惩罚性赔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经过近三十年的碰撞与融合,惩罚性赔偿已经在我国遍地开花,在食品安全诉讼、消费保护纠纷、商标侵权责任、医疗产品事故、房产销售案件、旅游合同争议等诸多与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成为了社会主义法治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近年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持续扩大、力度不断深入、比率逐渐增加,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尤以适法上的叠床架屋与释法上的莫衷一是最为突出,这不仅导致了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且有些时候取得过易也实在有违这一制度的本意,亟需一次全面的审视与纠正。
本文秉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写作方针,以重申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逻辑为起点,梳理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规定,并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最后提出几点改进建议。从王利明教授2000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扛鼎之作算起,国内学者研究惩罚性赔偿的学术成果可谓琳琅满目,有些侧重理论探索,有些偏好实证分析,而本文主要把重心放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上,通过目光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寻梭,争取能发现一些真问题,以及提供一些新思路。①参见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二、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逻辑
(一)惩罚性赔偿的起源
判处给受害人远超出其实际损失的赔偿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么匪夷所思的主意,据考证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古希腊乃至古巴比伦时代的法律里就有所谓“倍数赔偿”(Multiple-Damage Remedies)的规定存在,诸如“偷了寺庙一头牛,就要赔给寺庙三十头牛”(出自《汉谟拉比法典》)之类的,但说实话这看起来更像是某个王公贵族为了恫吓老百姓,灵机一动的脑洞产物,而不似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②James B. Sales & Kenneth B. Cole, Jr.,Punitive Damages: A Relic that Has Outlived Its Origins,37 Vanderbilt Law Review.1117 (1984).
学界公认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源于英国:在1763年的Wilkes v. Wood(98 Eng. Rep. 489)一案当中,原告是一名国会议员,因为在自办的杂志上批评国王无能卖国而遭搜查逮捕,获释后遂将主办此事的国务秘书告上法院,指控其开具空白搜捕令(不填姓名与事由)的行为违法,结果陪审团判处被告应为此赔付1000英镑。为了驳斥被告律师提出的给予原告超额赔偿在王国内无此先例的抗辩,时任最高法院首席的Pratt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力陈:“陪审团有权给予原告超出其所受真实损害的赔偿。要知道赔偿的意义不仅在于弥补受害人遭受的创伤,而且也是为了惩罚加害人的违法行为,以及用来震慑后来者不要做类似的事情,这同时也表明了陪审团是有多么厌恶被告的所作所为”。③Paul A. Hoversten, Punishment but Not a Penalty? Punitive Damages Are Impermissible Under Foreign Substantive Law,116Michigan Law Review.759 (2018).这一段话确凿无疑地表达了“惩罚性赔偿 = 惩罚 + 震慑”的理念,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对惩罚性赔偿性质与作用的认识。
然而,惩罚性赔偿随后在英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最初的挑战主要来自于1792年的Duberley v.Gunning(100 Eng. Rep. 1226)一案,陪审团裁决被告应为自己的恶行(与原告妻子通奸)向原告支付高达5000英镑的赔偿。面对原告的损失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的质疑,王座法院支持了这一天价裁决并在判决意见当中坚称:“鉴于本案的现状(损失很难用金钱准确计数),受害人的心灵遭受了无与伦比的重创,从今往后的幸福生活霎时间荡然无存,以至于法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准来判断赔偿给他这些钱是不是太多了”。④Anthony J. Sebok, What Did Punitive Damages Do? Why Mis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Punitive Damages Matters Today, 78 Law Review.163 (2003).我们不难想象当年的5000英镑价值几许,所以本案的判决结果虽无惩罚性赔偿之名,却有惩罚性赔偿之实。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该案主审法官提出了另一种有竞争力(迷惑性)的解释路径,即精神损害无法用金钱衡量,以填补损失为原则的传统补偿性赔偿对此无能为力,所以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补偿性赔偿在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之不足而设立的。于是,公式在这里变成了“惩罚性赔偿 = 精神损害 + 补偿不足”。
显然,这与Wilkes案的逻辑存在分歧:如果说前案的惩罚性赔偿是法官故意为之,因被告行为特别恶劣触发,充满杀鸡儆猴意味,效果波及到不特定对象,与补偿性赔偿并行不悖,那么本案的惩罚性赔偿更多是法官放任的后果,由原告遭受精神创伤引起,不过就事论事而已,效果局限在本案范围内,是补偿性赔偿的补充替代。
易言之,这场路线之争的实质是:在Wilkes案当中,惩罚性赔偿被视为了一种准刑事制裁措施(Quasi-Criminal),与其说赔一大笔钱是在奖励原告,倒不如说是在惩罚被告,乃至借此警告有和被告同样想法的人,其立意已经超越了原告个人的得失,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在Duberley案当中,惩罚性赔偿仍未脱离纯民事补偿措施的范畴,其目的并不在于让被告承担任何超出其行为后果的额外责罚,而是主张用相对宽裕的赔偿来抚慰可怜的原告,尤其是当原告遭受了一些非比寻常且难以估量的损害时(通常是精神或情感方面的),在传统补偿性赔偿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法官应该足够宽容以确保原告能够得到充分救济,因此这里的惩罚二字其实徒有其表,归根结底是在说法官的裁判尺度。
从最终结果来看,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上述路线之争是以前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Wilkes案确立的“惩罚 + 震慑”说成为了当下学界的主流见解,该案也被奉为了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开山鼻祖,应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侵权法律的迅速发展极大拓展了金钱救济的适用边界,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原先被视为难事的精神损害赔偿,越来越多的权利在法庭上被明码标价,一些在过去看来不可思议或惊世骇俗的侵权后果,如今也都能在司法流水线上被见怪不怪的法官和律师以合适的价码轻松搞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Duberley案的立场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缺陷,那就是明里暗里将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混为一谈,即从根本上不认可惩罚性赔偿的独立地位,将其视为补偿性赔偿的一种补充或附庸,这显然不利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长远发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重温这桩两百多年前的公案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因为还有人没有忘却以Duberley案为代表的不同声音,一个个犹如天文数字般的赔偿金额不断刷新纪录,从而促使我们去深刻反思惩罚性赔偿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它的本意。
虽然诞生于英国,可是囿于英国人天生保守的性格,英国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使用始终抱以一种克制谨慎的态度,所以其在英国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不仅在适用范围上受到较大限制,一般被局限在公职人员违法、被告精心算计或成文法律授权这三类案件以内,而且在赔偿金额上也有严格约束,超出实际损失3倍以上或单笔50000英镑的惩罚性赔偿就会被法官认为不太正常了。⑤参见崔明峰、欧山:《英美法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
(二)惩罚性赔偿的发展
真正把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扬光大,甚至上升为一门国粹的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据史料记载,惩罚性赔偿制度登上这块新大陆的第一起案件是1784年的Genay v. Norris(1 S.C. 3)一案,被告在原告的酒里偷偷下药致使其在随后与自己的决斗当中身负重伤,因而被法官判处惩罚性赔偿,并明言这是为了防止以后再有其他人行此卑劣之事。随后在1791年的Coryell v. Colbaugh(1 N.J.L. 77)一案中,一名男子因背誓悔婚而被处以惩罚性赔偿,法官指示陪审团:“你们不用过多考虑原告到底蒙受了怎样的实际损失,而是应该主要着眼于本案的示范效应,即多大数额的赔偿才能制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到了1851年的Day v. Wood Worth(54 U.S. 363)一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中宣称:“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惩罚性赔偿在诸多司法判例中得到了反复适用,其已经牢固矗立于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在非法侵入或其他类似诉由的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被告的行为罪大恶极,陪审团可以对被告施以惩罚性(或曰示范性 / 报复性)赔偿,而不用管他造成的实际损失有多大。”接下来在1864年的Hawk v. Ridgway(33 I.I.I.473)一案中,法官在判决意见中阐明:“如果恶行是被告故意施为或放任不管的结果,陪审团有权在要求其弥补实际损失之外另行对其科以一笔赔偿作为惩罚,用以保障社会生活的宁静祥和。”⑥Michael L. Rustad, How The Common Good Is Served By The Remedy Of Punitive Damages, 64 Tennessee Law Review. 793 (1997).回顾这些早期判例,我们可以发现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一开始就被定位成了一种社会干预工具,游走在民法与刑法的中间地带,与其说是为了补偿原告个体利益,倒不如说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至少在1868年,即第14修正案生效的那一年,惩罚性赔偿就已经毫无疑问是美国侵权法律的一部分了。”1991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在Pacifi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499 U.S. 1)一案判决意见中如实写道。但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的美国,包含惩罚性赔偿的判例并不十分常见,即便有,金额也都不很大,有史可查的最大一笔只不过4500美元而已。⑦David Owen,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74 Michigan Law Review.1257(1976).惩罚性赔偿真正炙手可热还是在美国一步步走向超级大国的20世纪中后期,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与物质的过剩,美国开始逐渐步入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在遏制产品责任事故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两方面需求的刺激之下,惩罚性赔偿越来越频繁地出没于陪审团的裁决之中,企业取代个人成为了惩罚性赔偿收取的主要对象,赔偿金额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20世纪初期最多也就在10000美元上下;30年代差不多是50000美元封顶;50年代也不过涨到了75000美元左右;但是到了70年代就开始有点刹不住车了,千万美元级别的惩罚性赔偿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最高峰是1979年的一起证券欺诈诉讼(Harmsen v. Smith, 693 F.2d 932),创下的1475万美元惩罚性赔偿的纪录。然而在80至90年代这个纪录一再被打破,随着烟草、制药、汽车、农业、金融、食品、化工行业的巨头们纷纷被推上被告席,惩罚性赔偿正式进入了比拼天文数字的新时期,超过千万美元的判例不胜枚举,一长串的0即便隔着屏幕也着实让人神往。近年来这个上升趋势仍在延续,最新摘得桂冠的是孟山都公司,在2019年发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起诉讼当中,因为长期隐瞒草甘膦致癌的真相,而被陪审团裁处需要向两名由此患上淋巴癌的夫妇支付55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和2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⑧参见陈雪梅:《域外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12月13日,第8版。
如今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运用极其广泛,从侵权到违约、从环保到雇佣、从垄断到知产,几乎所有民事诉讼领域都允许惩罚性赔偿存在。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100万美元以上的惩罚性赔偿判决数量几乎翻上了一番。仅在2001年,法院最终判决的惩罚性赔偿总额超过1620亿美元。⑨参见阳庚德:《普通法国家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以英美澳加四国为对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那么,为什么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开展得这样如火如荼呢?
首先,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全世界只有美国市场上才能容下这么多掏得起这笔钱的公司,尽管成千上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在普通人看起来触目惊心,但对这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来说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起码从来没有一家大公司是被惩罚性赔偿罚破产的。很多人把惩罚性赔偿制度理解为一种严刑峻法,这并不完全正确,其目的更多在于给那些胡作非为的企业一个深刻教训,让它们学会尊重消费者,而不是直接判它们死刑,因此美国很多州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平衡,金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一定比例(通常是10%-30%之间)。⑩参见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另外,对企业来说,惩罚性赔偿能促使自己下决心把不合格产品退市,所以很多时候这只是长痛与短痛的关系而已,是经常赔一点小钱好,还是一次赔一笔大钱好,相信企业一定算得清这笔账。
其次,相当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少有的仍然坚持在民事诉讼中广泛采用陪审制的国家,宪法第七修正案保障了在此类案件中使用陪审团的权利,而陪审员们不过就是一些和受害者一样的普通人,会对原告因为商家不负责任的行为而遭受的伤害感同身受,故而在斟定赔偿金额的时候往往感性大于理性,头脑一热就多出了几个0。可想而知,凡是高出天际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一定都是由陪审团裁决的,尽管每次都有法官在最后关头把握分寸,但如果基数已经很高的话,再怎么削减也少不到哪去。不过这笔钱花得值不值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因此给全社会节省下来的事故损失、医疗费用、诉讼开支远远超过了此数。
再次,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诉讼文化非常盛行的国家,打官司在这个国家犹如家常便饭,每年经由联邦和州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不计其数,这就意味着虽然相关判例在绝对数量上确实不少,但实际上只占全部民事案件的3.3%,平均每个案子获得的赔偿也就只有38000美元。⑪Tort Trials and Verdicts in Large Counties,1996,U.S.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CJ179769 (August 2000), p. 7.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惩罚性赔偿在美国遍地开花乃至唾手可得,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对个别明星案件连篇累牍的报道,那长长的一串数字实在太吸引眼球。而这也恰恰是立法者们希望看到的,通过对少数屡教不改的企业施以重手,再配合高曝光率形成警示效应,从而达到整肃市场秩序的目的。另外,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珠联璧合的还有美国根深蒂固的私人执法传统,即由老百姓自发充当“检察官”来维护社会正义,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无形之中为大家主动与不法行为作斗争提供了额外的物质奖励。
最后,美国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帝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让法律如此深刻地介入自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遵从法律、信仰法律、崇拜法律,如此靠法律来明是非、匡正误、定行止,没有任何其它东西比法律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对于法院来说,惩罚性赔偿无疑是一种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的高效社会治理工具,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太太被麦当劳咖啡烫伤案”(Liebe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 P.T.S., Inc., No. D-202 CV-93-0419)为例,大家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因为自己不小心被烫了几个泡皮而“幸运地”获得了将近50万美元赔偿的故事,但其实背后存在的是以麦当劳为首的快餐企业为了追求所谓最佳口感,十多年来一直向顾客出售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和警示文字的滚烫咖啡。每年造成数以百计的烫伤事故却从来都不放在心上,正是靠这一次出乎意料的惩罚性赔偿才迫使这些快餐企业把咖啡降到了安全的温度,并且还标注了醒目的警示文字。请问除了惩罚性赔偿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这样干脆利落地了结此事?事实上,区区50万美元还不到麦当劳一天卖咖啡的收入,但真正可怕的是如果不及时整改,还会有很多5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在等着麦当劳。因此,波斯纳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青眼有加,认为惩罚性赔偿通过给商家增加经济上的负担,有效促使了商家自觉采取安全措施来防止事故的发生,而在这个过程中毋须动用政府管制或刑事处罚,真是尽显法经济学之妙。⑫参见方明:《论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现代侵权法功能的嬗变——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评议》,载《学海》2012年第2期。
惩罚性赔偿与集团诉讼是美国民事司法的两大看家法宝,分别在各自领域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前者彰显了历史永不遗忘,一个人会为自己曾经作过的恶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后者则昭示了每一份权利哪怕再卑微也都值得被珍惜,只要想办法团结在一起就可以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作为一个法治后进国家,中国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已经早一步被吸纳,集团诉讼也刚刚在证券欺诈诉讼领域有所借鉴,但法律移植从来都不是照抄几行法条那么简单,如何避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尚需三思而后行。
(三)惩罚性赔偿的未来
常言道盛极而衰,惩罚性赔偿制度正在经历自己的鼎盛时期,那么会不会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呢?这一点笔者无法预测,但唱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人一直都不少,常见的理由包括:(1)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异乎寻常严厉的制裁措施,有可能会剥夺了被告的大量财产,却只由几个陪审员轻而易举地投票决定,有违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2)惩罚性赔偿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界限,实际上是在借赔偿之名而行罚款之实,因而应该使用刑事诉讼而非民事诉讼程序,这样才能给被告更好的保障;(3)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之外另加的处罚,相当于对被告的一次错误行为施加了两次制裁,这对被告来说不公平;(4)惩罚被告也许是合理的,但原告凭什么能白白一夜暴富,凭什么天上掉馅饼砸到他的头上,凭什么要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他个人,这属于不当得利,也容易激发老百姓的投机心理,引诱他们去滥诉;(5)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太轻率随意,没有一个相对固定可靠的标准或比率,几乎变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行为,看人下菜碟的现象普遍存在,有钱就多罚一点,没钱就少罚一点,而和原告的实际损失没多大关系;(6)羊毛出在羊身上,惩罚性赔偿看似从商家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大笔钱,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商家都可以通过涨价或其他更加隐蔽的方式,最终把这笔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就等于全民在给惩罚性赔偿埋单;(7)惩罚性赔偿难以做到刚刚好,如果过重会导致“寒蝉效应”,企业不敢研发新产品,如果过轻则达不到震慑目的,无法产生让人望而生畏的效果,但轻重与否极难在当时知晓;(8)受限于技术或成本等客观因素,有些事情商家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罚它再多也没有用,这个时候惩罚性赔偿就是在故意找茬(碰瓷);(9)现在绝大多数州都不禁止商家专门为惩罚性赔偿购买单独的保险,这其实就抵销掉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大部分意义,反倒把这变成了保险公司的一门生意。⑬参见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平心而论,上述这么多指责中有些一语中的,比如程序保障不够充分和赔偿金额难以预计确实击中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软肋;有些则不值一晒,比如惩罚性赔偿制度和双重制裁或不当得利压根也扯不上任何关系;而有些纯粹就是在吹毛求疵了,比如天底下有什么道理规定商家不能通过提高售价或购买保险来化解市场经营当中的诉讼风险。⑭参见向朝霞:《论民事制裁的变迁——以惩罚性赔偿为视角》,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对于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联邦与各州的立法者们也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例,近三十年来就曾多次出手试图厘清惩罚性赔偿制度当中的正当程序问题:
在1991年的Pacifi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499 U.S. 1)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按照普通法长久以来的习惯做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属于陪审团裁决的事项,法官应指示陪审团根据被告恶行的严重程度与威慑类似行为的需要来斟定数额多寡,而后法官有权对陪审团确定的数额加以审核以确定其合理与否,并且容许被告以赔偿数额畸重为由提起上诉。
在1993年的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509 U.S. 443)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坦承对当事人请求自己发明一个检测惩罚性赔偿数额是否合宪的数学公式无能为力,要知道在合宪的数额与违宪的数额之间不存在一条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显著界限,仅仅因为实际损失与赔偿数额之间比例悬殊(超过500倍)这样一个事实,不足以推断惩罚性赔偿就一定是不合理的。
在1994年的Honda Motor Co. v. Oberg(512 U.S. 415)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对于陪审团裁决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被告有权要求法官进行司法审查,如果法官拒绝则构成违宪,因为这剥夺了被告获得法院救济的机会。从普通法的历史来看,在出现了惩罚性赔偿的场合,法官审查陪审团的裁决是非常有必要的,后者经常不按照指示行事。
在1996年的BMW of North America v. Gore(517 U.S. 559)一案当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提出了法官在审查惩罚性赔偿数额是否过高时,可依据三项标准加以判断:(1)被告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被非难的;(2)原告遭受的损失与他可能获得的惩罚性赔偿之间是否相差巨大;(3)同类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怎样的处罚或制裁。
在2001年的Cooper Indus-tries v. Leatherman Tool Group, Inc.(532 U.S. 424)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针对有关惩罚性赔偿合宪性的上诉,上级法院应该采用“重新审理”标准(de novo standard)来给予审查,而非“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abuse of discretion standard)。
在2003年的State Farm Mut. Automobile Ins. Co. v. Campbell(538 U.S. 408)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称:(1)陪审团在斟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该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不应该把未经法庭讨论的事项纳入考虑范畴,更不应该把其他人的所作所为算到被告头上;(2)惩罚性赔偿应与补偿性赔偿具有起码的可比性,如果完全不顾及补偿性赔偿的实际情况,那就有可能构成对被告财产无理且武断的剥夺;(3)法院不可能为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例设定一个固定的数值,但如果这个数值大幅超过了个位数的比例(达到9倍以上),那么就极有可能违反了正当程序。
在2007年的Phil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549 U.S. 346)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不能把被告对本案当事人以外的人作的恶,计算在本案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当中,但是相关证据可以显示被告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与恶劣影响。换句话说,本案的陪审团不能拿被告对别人作的恶来增加对原告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却可以用来评价被告这个人是多么恶贯满盈(按照Gore案的标准,这也会影响惩罚性赔偿数额)。不出意料,有法官(Justice Stevens)在反对意见里抱怨,这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会搞得陪审团不知所措。
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这些年针对惩罚性赔偿的正当程序与数额计算问题作出过的判决还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已经足以显示联邦最高法院是多么重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宪性,并且也在不断调整立场以期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关注联邦最高法院说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提醒了我们千万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惩罚性赔偿制度,它仍然是在不断成长变化过程中,在未来具有无穷的活力与潜力。
(四)小结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逻辑可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价值逻辑来看,惩罚性赔偿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巨额罚款(经济负担),即被告的不法行为十分恶劣,不仅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而且已经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却又没有触犯刑法,无法给予其刑事处罚,这时就可以用惩罚性赔偿的方式对其进行制裁,并震慑其他潜在威胁社会安宁祥和的不安定分子。言下之意也就是,要不要施加惩罚性赔偿与被告给原告造成了多少实际损失无关(但是不能一点实际损失都没有,并且这与惩罚性赔偿数额有关),而归根结底取决于被告行为的反社会性。因此,笔者反对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功能的说法,其与补偿性赔偿应该分别计算,不能因为该补偿给原告多少才能填补损失算不清楚,就改以惩罚性赔偿的名义,反正总数上只多不少。惩罚性赔偿应该被定位于民事补偿与刑事惩处之间,在前者意犹未尽,后者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其功能只有制裁和威慑两种。因此除非被告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并且通过制裁能起到威慑作用的,否则就不应该动用惩罚性赔偿,以免其沦为一种泄愤的手段。
从发展逻辑来看,惩罚性赔偿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救济措施,必须遵循慎用、少用、限用的原则,即便非用不可也应该经由法院遵循正当程序审理后,由法官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确认适用。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惩罚其他人,况且惩罚性赔偿只不过给予了受害人一个权利而非权力,而且也因为惩罚性赔偿从性质上讲仍然属于一种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责任,所以法院而非行政机关拥有惩罚性赔偿的决定权。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也不应该随便滥用,而是应该考虑何时用与怎样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于是判一堆小企业各自罚一点点钱,不如判一个龙头企业罚一大笔钱,显然后者更容易上报纸头条。
从运行逻辑来看,惩罚性赔偿应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本来就是惩罚性赔偿的一个不可或缺组成部分,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公众对惩罚性赔偿的最大敬畏心。俗话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是说如果法律的底牌被人摸透了,那么威慑力就少了大半,因此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高悬时才能发挥作用,一旦落下人们也就觉得不稀奇了。惩罚性赔偿的一半作用在于制裁被告,一半作用在于警告世人,如果把该赔多少钱明明白白写在法律里,就会立刻陷入两难境地,写多了会引发重罚必反的“撑骨裙效应”,写少了又压根起不到阻吓的效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都拒绝给一个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公式,而且对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例也从来都含糊其辞,为的就是帮助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持天威难测的神秘感。
三、我国食安法律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及其问题
(一)立法梳理
虽然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恪守公私法调整范围的界分,拒绝将惩罚性因素包含在民法概念范畴内,因而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表现出了较为抵触的态度,但我国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异数,没有受教条主义的干扰墨守成规,在上个世纪90年代重拳出击整治市场乱象的方针指导下,未经太多犹豫就引进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且经一段时间实践检验后,社会各界都对其反映良好,所以目前正逐步将其推广到了更多领域。⑮参见李明发:《论我国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载《学术界》2010年第9期。
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聚焦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看看在这样一个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领域,都有哪些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其第49条规定了消费者对于欺诈经营者有权索取双倍赔偿,首开假一赔二的先河,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具有破冰之功。
受当年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影响,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在其第96条也放出了惩罚性赔偿这样的大招,并且将标准一下子提升到了价款的十倍,但随后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规定华而不实,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⑯参见王成:《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条款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009年,《侵权责任法》在其第47条规定了基于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一词,但是该法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回避了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等具体技术性问题。
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迎来了修改,载有惩罚性赔偿的条文被改到了第55条,其中第1款是针对欺诈经营行为的,变化除了将惩罚性赔偿数额提高到三倍以外,还设置了500元的赔偿下限,以及规定了援引其他法律的情况,而第2款是针对造成消费者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此时惩罚性赔偿数额为不超过损失的两倍。
2015年,《食品安全法》也经历了一次修改,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法条被挪到了第148条,并且数额由原先的十倍,改为了现在的“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
2020年,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正式出炉,其第179条列举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明确指出:“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另外,其第1207条吸收了《侵权责任法》确立的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
(二)特点与问题
有了前文对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介绍作为参照,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中惩罚性赔偿相关规定的别具一格之处便显而易见了,而且特点与问题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干脆就合在一起展现给大家:
第一,在我国,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资格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即只有在获得了成文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原告才有权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向自己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易言之,惩罚性赔偿仅在有条款明文列举的情况下适用,只相当于英国允许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的第三种类型。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我们自认为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就算惩罚性赔偿是一个源自英美法系的制度,既然来到了中国就要入乡随俗,以文字的形式落在纸面上。但问题在于我们居然在食品安全法律领域一口气订立了3个存在交集的法律条文(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产品责任),而且它们之间是互不统属的相互平行关系,无法通过上位优于下位或者特别优于一般的冲突规则来解决适用问题,这就让人感到困扰了。⑰参见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载《法学》2015年第4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假设有天笔者买了一个自热小火锅,完全按照说明书指示成功加热,谁知刚刚吃了几筷子,底部的发热包突然爆炸,锅里的热水四溅致使笔者裸露的皮肤被严重烫伤,这时笔者该如何获得救济?至少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起来,上述3个法律条文规定的条件均有机会满足,因为同时具有商品消费者、食品消费者、产品使用者三重身份,所以既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要求获得所受损失的两倍以下赔偿,也可以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要求获得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207条要求获得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至于怎么破解这个僵局,有学者主张应该参照《合同法》第122条的“请求权自由竞合说”自择其一,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不妥,最好借鉴《刑法》当中的“想象竞合犯”理论按其中赔偿较多的一个论处,那么请问究竟哪一个能赔得最多呢?⑱参见周江洪:《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竞合及其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之适用关系》,载《法学》2010年第4期。这个例子也许永远只存在于想象中,但相关法律条文政出多门、叠床架屋的现象却不是虚构出来的,不仅各条文所涵盖的范围交叉重复,层级不清,其责任构成要件也是相互借鉴,不甚明晰,也许这就是把一项普通法上的制度硬塞进成文法里(却又缺乏必要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吧。⑲参见张红:《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体系》,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9卷第1辑。
第二,就篇幅而言,上述三部法律中涉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文都不算长,具体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两个条款加在一起是207个字,《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降到了135个字,而《民法典》第1207条更少,就只有68个字。如前文所示,惩罚性赔偿这么复杂深奥的一个制度,光是英美两国就用了两百多年时间,积累了成千上万的案例,还没有完全把它搞懂吃透,现在仍然不断会有疑难问题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我国只用总共不到500个字,就能把食品安全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在法律里规定清楚。再字字珠玑、微言大义也不可能,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宣示性条款,只想装个样子没有打算真正投入使用;二是原则性条款,规定个大概也不管你好不好用的。不出意料之外,事实也大抵如此。⑳参见张媛:《聚焦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案件原告胜诉率仅30%》,载《法制日报》2015年4月9日,第4版。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况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关规定的印象,那笔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粗糙”二字。实在是太惜字如金了,这些法条制定者的头脑似乎还停留在过去那个主张“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年代,竟然舍不得往法条里添加哪怕一点点细节,仿佛生怕我们借此窥探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的确,多写多错、不写不错,但这样一来,谁还看得明白法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举个例子,《食品安全法》里有一个千古难题,那便是第148条第1款和第2款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第2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到底是基于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法学界居然至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法院也莫衷一是,难怪消费者们只有不到三成的胜率,因为可能就连法官都搞不清楚这条法律是什么意思。21参见刘大洪、段宏磊:《消费者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嬗变与未来改进》,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说得直接一点,这种立法上面的懒政,本质上就是在给老百姓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明明美英两国在惩罚性赔偿方面积累了那么多经过了长时间实践检验的原则规定,例如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Gore案当中确立的审查惩罚性赔偿数额是否过高的三条标准,或者把英国上院在Kuddus案(Kuddus v. Chief Constable of Leicestershire Constabulary,2 A.C. 122)中列举的限制惩罚性赔偿六大措施,写到我们的法律里面不好吗?既然惩罚性赔偿整个制度都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再多拿一些细节过来有什么违和吗?
第三,英美两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惩罚性赔偿数额多寡恐怕是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环节最重要同时也最棘手的问题了,如何在触及被告灵魂的同时,向社会传递出强烈的告诫信号,还不违反当事人依宪法享有的正当程序权利,是对陪审团和法官极大的考验。然而,在我国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法律基本上都已经提前设定好了固定的倍数,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两款分别规定的是三倍和两倍(以下),《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的是十倍或三倍,就只有《民法典》第1207条没有规定,为此还曾在审议过程中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抱怨。22参见舒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时建议明确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倍数》,载《全国人大》2019年第17期。当然,《民法典》第1207条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惩罚性赔偿计算方法没有一丁点提示,这无疑会让法官在裁判时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固定倍数意味着法官在裁判此类案件时,在确定赔偿数额方面是没有什么自由裁量权的,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乘法就可以了。但问题在于,既然如此省事,除了极个别情况(反垄断惩罚性赔偿固定为三倍),为什么美国人不用这个办法呢?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导致惩罚性赔偿数额畸轻畸重的情况,试想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采购食品,一般不会买太贵的,一次买的数量也不多,所以食品安全诉讼绝大多数标的额都不很高,即便乘以十倍也没有多少钱。可想要拿到这笔为数不多的钱却十分麻烦,要固定证据、要准备诉状、要出席庭审,最后胜诉率还不到30%。23参见杨涛:《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作用未必大》,载《检察日报》2009年6月2日,第5版。但凡是一个理性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干脆自认倒霉算了。这么多年来的司法实务也证明,十倍赔偿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对老百姓的激励作用相当有限,结果反倒成了职业打假人的主战场。24参见吕来明、王慧诚:《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条件》,载《人民司法(应用)》2019年第1期。有人会提出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出现,相关法条里还设计了最低赔偿保障的机制,但这只不过徒增笑耳,500元和1000元,试问在哪个国家见过这样廉价的惩罚性赔偿?要知道现在就连小额诉讼的标的额都上涨到5万元了,绝大多数食品安全诉讼能够获得惩罚性赔偿的上限,居然连小额诉讼标的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四,上述列举的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内的惩罚性赔偿法条都属于实体法的范畴,而没有丝毫诉讼程序方面的精细安排或强化保障,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案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该缺席判决就缺席判决、该一审终审就一审终审、该简易程序就简易程序,完全不给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任何专门照顾。然而,在美国,正当程序是惩罚性赔偿案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障碍,几乎所有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上诉都会把违反第14修正案作为最主要的理由,而我们在前文中也看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惩罚性赔偿案件也全都围绕着正当程序展开。这说明如何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给予被告适当的程序保障是惩罚性赔偿案件中一个至关重要也最富争议的问题。尽管中国没有第14修正案,也未明文规定正当程序,但程序正义的道理是全世界相通的,尤其是在要罚被告这么一大笔钱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像美国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审判程序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吗?
也许有人会申辩因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内的惩罚性赔偿涉及的金额一般比较少,所以不需要太在意程序问题。这个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就把问题引向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到底是因为赔偿少所以不需要正当程序,还是因为没有正当程序所以赔偿不可能多呢?而且从法条本身的文字解读,我国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也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的规定,万一哪天又出了一起像“三鹿”奶粉这样的案子,我们现如今的民事诉讼程序能从容应对吗?范愉教授在描述我国的法治环境时用了“低端司法”这个词,意在形容整体社会资源投入不足情况下法律的简陋与法院的窘迫,虽然听上去刺耳,但大体上属实。25参见范愉:《诉讼社会与无讼社会的辨析和启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社会》,载《法学界》2013年第1期。于是,减配的惩罚性赔偿配合减配的正当程序,倒也相得益彰。然而,有时候警察会把索赔是否超过十倍作为判断敲诈勒索成立与否的尺度(参见郭利案),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第五,惩罚性赔偿需要建立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之上,一般是侵权,有时也可以是违约。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两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分别是建立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基础之上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既可以建立在侵权责任基础之上(针对生产者),也可以建立在违约责任基础之上(针对经营者),而《民法典》第120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则显然是建立在侵权责任基础之上的。26参见刘俊海、徐海燕:《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解释与创新》,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10期。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哪怕放到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也是如此,基于违约责任与基于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基本上平分秋色,这使得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即由侵权引发的惩罚性赔偿和由违约引发的惩罚性赔偿各占一摊,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表明我国的立法者不是很重视惩罚性赔偿的道德批判成分,即并不主张挖掘并证明被告行为的可非难性,一般只要求明知就可以了(如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些时候甚至压根就不在乎被告是怎么想的(如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然而在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传统上主要适用于侵权责任中,在违约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属于例外情况,用《合同法重述》第355条的话来说也就是:“合同救济制度的核心目的是补偿而不是惩罚……除非违约行为同时构成侵权行为,否则仅仅违约不得主张惩罚性赔偿”。27梅龙生:《我国惩罚性违约金制度的理论反思和重构》,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之所以这么规定,主要是因为侵权属于过错责任,而违约只看客观结果,所以谈不上什么恶意不恶意的,不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甚至为了效率赞成主动违约,这里面自然没有惩罚性赔偿的容身之地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惩罚性赔偿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合同法律领域,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惩罚性赔偿有意识地忽略了侵权与违约的区别,只要出现了根据社会普遍道德观念难以容忍的恶行,比如恃强凌弱、背信弃义、为富不仁,惩罚性赔偿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不用顾忌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
(三)小结
看了英美法系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对比,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莫不是引进了一个假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如果我们用英美法系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的相关法条都和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差甚远,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国现在所有的其实并不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而只不过是一种加重型赔偿制度或者奖励性赔偿制度?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我国的“惩罚性”赔偿门槛太低。以《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为例,该法条提示的构成要件包括:生产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 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 = 赔偿损失 + 十倍或三倍的赔偿金。换句话说,原告需要在法庭上证明的是:食品是被告生产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自己属于消费者、自己遭受了损失、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证明这些,原告就可以获得针对自己损失的补偿性赔偿,以及十倍或三倍的赔偿金。在这整个举证过程中,原告根本就不需要专门就十倍或三倍的赔偿金做任何事情(顶多提供一下购物小票),就好像是买一赠一一样,只要法院判决应该获得补偿性赔偿,那么十倍或三倍的赔偿金就等于是自己送上门的。原告不需要证明被告的主观恶意、不需要证明被告行为的反社会性、不需要证明自己所受伤害有多严重、不需要证明非罚被告一大笔钱不足以平民愤、不需要证明确有必要给予胆敢效仿者一个响亮警告,天底下有能躺赢的惩罚性赔偿吗?
第二,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力度不足。有学者统计我国法院适用十倍赔偿规则判处的金额,平均为3580元(最低仅有30元),就凭这千儿八百的赔偿数额,谁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严厉制裁?28参见李友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中国模式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谁又会被震慑得不敢再犯?如果说这是给原告的奖励,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说这是给被告的惩罚,那就是在开玩笑了,被告可能更多觉得是一种羞辱而非心痛。十倍赔偿规则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市场是不会说假话的,难道这几年还少了苏丹红、瘦肉精、孔雀石绿?可见,惩罚性赔偿根本没起到让不良商家胆战心惊的预想效果。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惩罚性赔偿想要有用,关键是要让不良商家相信自己很容易被抓住,并且一旦被抓住就要赔一大笔钱,风险远大于收益,于是干坏事变得很不划算了。扪心自问,我国的现行立法能做到这一点吗?
第三,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刺激不足。充分发动群众,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传统手段,我国之所以要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未免没有想要靠经济利益的手段来刺激老百姓投入到与不良商家斗争中去的想法。据一位亲身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条款制定的人大法工委官员坦承,当时国家的想法是:“将法律武器交给广大消费者, 动员亿万群众与伪假商品做斗争, 并使之得以实惠, 就能对伪假商品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使其无处藏身”。29河山:《论缺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思想》,载《法律适用》1993年第8期。虽然事实证明了与打官司的麻烦相比,惩罚性赔偿这一点蝇头小利实在吸引不了太多老百姓参与,但却意外地催生出了一个专门以此为生的职业打假群体,在全国各地知假买假并靠着惩罚性赔偿养家糊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以后,国家最终还是认可了这种做法,不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不支持购买者明知的抗辩,而且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23号(孙银山案,裁判要点:不论消费者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 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那请问,这些人打官司是为了自己赚钱,还是为了惩罚不良商家?
四、余论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该谈谈解决方案了,不过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制度性问题,笔者亦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惟有几点肺腑之言供参考:
第一步,我们需要想一想中国是不是真的需要惩罚性赔偿制度。从1993年开始,我国在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有不短时间了,要说一点用都没有肯定言过其实,但也不至于到了缺他不可的地步。盖因我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靠打官司来治理的国家,起码在现阶段不能指望老百姓自发地充当私人执法者。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目前主要依赖的是行政治理,也就是靠行政机关的监管和罚款,例如《食品安全法》第130条规定,县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对违法商家处以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这个比十倍赔偿规则管用得多,不信去问问门口的小饭店老板,他到底是怕工商城管食药监,还是怕法官检察官。美国倚重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因为它的行政机关没有那么大权力,罚不了那么多的款,而我们明明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体制,显然也更适应中国仍以小商小贩为主的市场环境,为什么非要削足适履去学美国人那一套呢?再者,德国、法国、日本也都不靠惩罚性赔偿制度治理食品安全,人家也都搞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为什么偏要相信只有华山一条路呢?30参见邓辉:《惩罚性赔偿、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美国经验》,载《法治研究》2018年第4期。这个问题想通了,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第二步,如果思前想后觉得我国治理食品安全还真离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那么首当其冲要下决心解决的,也是当前我国惩罚性赔偿立法最大的问题,便是高度的不系统与碎片化。正所谓成也实用主义,败也实用主义,总是信奉“摸着石头过河”摸上了瘾,觉得哪里可能需要惩罚性赔偿,就随心所欲在哪里添上一条,而没有任何整体的规划与通盘的考虑,以至于现在各个规定散见于各种不同法律之中,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造成实务中适用的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我国惩罚性赔偿立法进行适度整合实乃当务之急,即便做不到在民法典总则部分,也应该在其侵权责任编中,增加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此外,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定一部专门司法解释,美国的《惩罚性赔偿示范法》(Model Punitive Damages Act)是个相当不错的范本,稍微本土化改造一下就能派上用场。
第三步,我们要理解惩罚性赔偿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法条,而是由很多具体规定组合而成的制度,既要有内里的核心原则支撑,也要有外围的配套措施拱卫,所以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惩罚性赔偿的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健全,例如律师的风险代理与费用转付规则、政府分成与税金征收安排、惩罚性赔偿的保险涵盖与赔付制度、国际商事仲裁中惩罚性赔偿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机制等等。总之,惩罚性赔偿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制度生态,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构建起一个原生态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