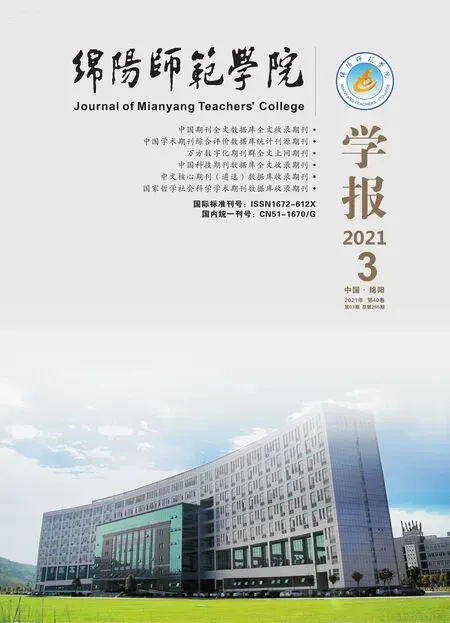礼坏乐崩与《诗》应用的变迁:从歌《诗》、赋《诗》到引《诗》
——以《左传》文本为考察核心
施春华,王贞贞
(1.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 621000;2.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5)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为《诗》或者《诗三百》,其在形成之初,包含了诗歌(文本)、音乐与舞蹈等多种形式,与西周早期的礼乐制度相伴而生。在西周初期通行的“国子”教育体系中,《诗》教作为“乐教”的一部分,以诗乐舞一体的方式,在贵族子弟培育良好德行、塑造言行仪容、熟悉各类礼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国家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权威不断下降,以天子为主导的大型国家典礼,如祭祀、征伐、嘉赏、宴飨、布政、宣令等不再施行,导致原本用于国家大型典礼的《诗》也逐渐失去了应用的场合。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聘问往来取代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各类政治典礼,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流。《诗》的应用和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原本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繁复模式开始逐步简化和瓦解,乐、舞的元素逐步消退,而《诗》的文本意义开始逐步凸显,以适应政治社交场合的实际需要。上层贵族以《诗》为主要社交手段,在邦交活动中完成政治生活领域中诸如规谏、请求、斡旋、威慑等诸多功能,在歌舞揖让、朝会燕飨中以歌《诗》、赋《诗》、引《诗》的方式完成政治使命,实现个人理想。在精简化的各类仪式中,《诗》的功用逐步脱离乐舞凸显出来,拥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成为政治外交中表情达意、委婉陈词的必要工具。
追溯春秋时期政治外交场合中《诗》的应用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礼乐制度消退的痕迹:从“歌《诗》”到“赋《诗》”,舞的元素消退;从“赋《诗》”到“诵《诗》”,乐的元素消退;而从“诵《诗》”到“引《诗》”,礼的元素已经全部消退。《诗》的应用已经从礼仪场合扩展到言谈对话等生活层面,《诗》的文本意义开始凸显,这也为后世儒家《诗》教脱离乐教的束缚,以文本阐释的路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礼坏乐崩:《诗》之用转变的历史背景
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政治生活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井田制度的逐渐消亡,私有经济逐步产生,大量的新兴贵族阶层涌现出来,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剧烈冲击,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开始向以私有经济的个体家族为基础的地域性君主集权方式转变。转变的结果,是经济上的“富”与“贵”开始分离,政治上诸侯王国势力膨胀,而中央王权开始萎缩。如《国语·郑语》中所言:“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1]152王室尊崇时期,各类政治活动以中央朝廷为中心、以天子为主导全面展开。然而王权衰落后,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祭祀、征伐、嘉赏、宴飨、布政、宣令等政治活动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诸侯国之间频繁的聘问往来。据清代马骕在《春秋事纬》中做出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来聘有七,锡命有三,归脤有四,来求有三……鲁诸公之朝齐、晋、楚三十有三,而朝周仅三,诸大夫之聘列国五十有六,而聘周仅五。”[2]这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取代周王室轮流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而原来西周教育体系中为宗法血缘体制下的政体所培养的“乐舞”“乐仪”等用于大型祭祀、燕射之礼的各种技能,随着仪礼种类的减少(与天子有关的礼仪逐渐不再盛行)和礼仪方式的简化(舞的元素逐渐消失,乐的元素逐渐简化),也逐步失去了展示的平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说《诗》、解《诗》为基本方式,以言说义理和德行为主的“乐语”保留了下来,并进一步演化为在燕享朝聘中的“赋诗”和“引诗”等突出《诗》文意的阐释方式。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3]1755
《左传》中记载了大量赋《诗》言志、托《诗》言事的事实。《左传》中记载,在春秋240年间,各种人物在各个场合引用《诗》表情达意达134处。《诗》引用的次数远在《书》《易》之上。《诗》中蕴含的对德性的歌颂和内在对“德”性的要求,使其成为约束和平衡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关系的“金科玉律”。在当时国家层面的社交场合中,贵族们借用《诗》中词句蕴含的关于“德”性的意义,婉转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借以礼敬,或请求帮助,或加以劝谏,或表达感激或者讽刺,以维护邦国利益,完成政治使命。
这一时期,随着王权的衰落,一方面以周王室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开始逐步瓦解,《诗》与乐的教育不再如前期那样系统化和规范化,许多诸侯国的贵族子弟不再熟悉礼仪的严格程序和应用方式;另一方面,礼制不再被严格地遵守,用《诗》的场合和方式也逐步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诗》教的实践,主要反映在朝会聘享中的歌诗、赋诗、引诗、诵诗等对《诗》的实际应用中。
二、歌《诗》:有乐有舞,礼制遗存
在西周初期,《诗》原本就是为了配合礼制而产生,又在形成后实际运用于各类礼制中。周代的贵族《诗》教体系中,也以配合完成各类礼仪作为《诗》的主要教授目的。但观之于《左传》,包含诗、乐、舞等完整礼制要素的礼仪场合中的“歌《诗》”记载并不多,仅有2例。这充分说明随着宗法政治体系的逐步瓦解,礼乐制度也在逐步瓦解,《诗》的实际功用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关于“歌《诗》”的记载,比较典型的一例,是《左传·襄公四年》中记载的鲁国穆叔出使晋国,晋侯以盛大的飨礼招待他,期间按照传统的礼制模式,钟鼓齐鸣,乐人歌《诗》: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2]976(《左传·襄公四年》)
《肆夏》为《九夏》中的一篇,在《周礼》关于钟师职责的记载中提及:“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裓夏》《驁夏》。”而《九夏》,即为夏朝古乐《大夏》,为夏朝流传下来的古乐,是歌颂大禹丰功伟业的诵诗,最初是用于祭祀典礼的《诗》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见舞大夏者……”《周礼·地官司徒》中也云:“以乐舞教国子,舞……《大夏》……”故此晋侯燕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应是乐舞一体的。这是对西周初期传统礼制的全面展现,以显示郑重其事。但对于这样盛大规格的招待,穆叔却并没有还礼——“不拜”。这是因为晋侯以《肆夏》之乐舞来招待鲁国的使臣,其实已经僭越了传统的礼法。包含《肆夏》在内的《三夏》之乐舞,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礼乐。《鲁语》中说:“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接下来,乐工又歌《文王》之三篇诗乐,穆叔仍然不答礼。因为按照《周礼》,《文王》等三篇诗乐,只能用在国君相见之时,穆叔不过是鲁国的使臣,也当不起《文王》的诗乐。直到乐工再歌《鹿鸣》等三篇诗乐,按照礼法,《鹿鸣》是晋国国君嘉许鲁国国君的,穆叔在此代表鲁国国君作出答谢;《四牡》和《皇皇者华》都是国君对使臣的慰劳和嘉许,符合礼制等级,因此穆叔也作出答谢。
此事发生在鲁襄公四年,仍属春秋初期,平王已经东迁,诸侯国开始发展壮大,晋国就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此时西周盛行的礼乐还在诸侯国间有遗存的影子,像鲁国这样重视周礼的国家就保存得较为完整,从晋国能够“金奏《肆夏》,工歌《文王》,工歌《鹿鸣》”的礼仪形式来看,礼制在晋国也有保留。至于为何以天子享元侯之礼、两君相见之礼来超越规格地接待鲁国的使臣,有可能是实力雄厚的晋国刻意为之,试探鲁国对自己“霸主”地位的态度,晋侯试探性地僭越礼法,彰显自己强国的地位。但也有可能是诸侯国之间忙于争霸,虽然保存了礼制的部分形式,但对于具体的使用规则,却早已漠然不晓了。
《左传》中另有一次“歌《诗》”的记载,发生在穆叔入晋之后的二十五年后,即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特地请求观赏周乐,鲁国的乐工为之系统完整地演奏歌唱了《诗》中的各篇,包括十四国风、二雅及诸颂。此间的记载也用了“歌《诗》”之语,可见是配乐而唱,而至于奏《颂》,如《大武》等诸多篇章本有相应的乐舞与之配合,鲁国是否完整展现了诗、乐、武三位一体的盛况,则不可确知。
“歌《诗》”的记载,表明了在春秋初期,诗、乐、舞一体的传统礼制虽在鲁国这样的周公直系之国、晋国这样的同姓大国之间仍有存留,但在其他诸侯国实则已经消失殆尽了,否则吴国的公子不会特地前往鲁国观赏周乐。而即便是存留着传统礼制的国家,在使用时僭越礼法的情形已经出现,《诗》与礼已经开始出现分离的趋势。
三、赋《诗》:有乐无舞,断章取义
与上述零星的“歌《诗》”记载相比,《左传》中关于“赋《诗》”的记载则较为丰富。“赋《诗》”所用的场合,多在燕享朝聘之时,尤以燕飨之礼时赋《诗》最多。《左传》中记载的赋《诗》共计32场次,涉及86篇①,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重耳过秦赋《河水》,终于鲁定公四年秦哀公赋《无衣》,尤以昭襄时期为赋《诗》高潮。
赋《诗》,是与乐相配合的吟诵诗篇,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词典》中就认为春秋时期的赋《诗》就是按某诗的曲调唱其歌词。笔者认为,“赋《诗》”与“歌《诗》”所不同的是,“歌《诗》”仪式感更强,或有舞相伴,而且多由乐工吟唱,是完整礼仪的正式部分。但“赋《诗》”多由贵族阶层本人配乐吟诵,吟诵内容根据实际需要自己确定某一篇章或某篇的某一段,并不固定。可以看出,从“歌《诗》”到“赋《诗》”,礼仪的程度次第消减,用《诗》的方式更加灵活。
根据《左传》中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的赋《诗》,或委婉陈情,或直言讽喻,达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交目的,其断章取义而能心照不宣的应用原则,则依赖于《诗》中关于“德”的描述和歌颂的文本意义。春秋时期,尽管王室衰微,诸侯相互征伐,有礼坏乐崩的苗头和弑君弑父的恶行,但在国家邦交层面,仍然主要以“德”为准则来处理邦交关系。《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有不怀。”文公七年,晋郤缺在劝说执政赵宣子归还卫国土地时,也说“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可见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将德作为处理邦交关系的最高原则。在这样的前提下,邦交之间运用《诗》进行劝谏、调和、周旋、请求和反对才有了保证,只要言之成理,符合“德”中包含的礼、信、仁、义、忠,大都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春秋时期的外交宴会中,宾主相互表达恭维礼敬,常常用《诗》中的篇章来委婉地表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4]3942
外逃的落难公子重耳到达秦国,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款待。重耳借百川归海赞颂秦国的国势强盛,比喻小国家依附于秦国,就好像河水归附于大海一样。当时重耳尚在流亡途中,借用《河水》的诗句,巧妙而得体地表达了对秦穆公的称颂和礼敬之意。秦穆公也听懂了他的恭敬,以《六月》回敬他,取的是以尹吉甫辅佐宣王征伐之意,表达对重耳能回到晋国当上国君,并能辅佐周王匡正王国之意。
又《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宣子自齐聘于卫,卫候享之。北宫文子赋《淇奥》。宣子赋《木瓜》。”[4]3942
韩宣子从齐国到卫国访问,卫侯设宴款待。在宴会上,卫国大臣北宫文子赋了《卫风》中的《淇奥》表示欢迎,《淇奥》主旨是歌颂卫武公的品德和学问,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句,此处是以此诗来赞扬宣子有武公之德,也是一位有品行、有学问的谦谦君子,以表示对宣子的礼敬。韩宣子同样以《卫风》中的诗篇《木瓜》来回礼,《木瓜》篇主旨为表达感恩,珍重友情,宣子借此来表达感激和友好。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较为弱小的国家需要请求别国出兵干预或者帮助时,使臣也常常借用《诗》中的篇章表达请求和催促。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外交斡旋和请托,大都在燕飨的场合,以赋诗为媒介,在酬唱应答中巧妙完成。《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4]4022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鲁文公到晋国朝见,重温衡庸之盟建立的友好关系。鲁文公在回国的路上,郑伯在棐地会见鲁文公,请求鲁国帮助郑国来跟晋国讲和。其中曲折,在诗歌对答中表现得很明显。在棐地的宴会上,郑国的大臣子家赋了《鸿雁》,其首章说:“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主要借用诗句中的“哀此鳏寡”一句,将郑国比喻为无依无靠、处境可怜的鳏寡,希望能唤起文公的同情之心,请他返回晋国,去做晋国的工作。鲁国也很为难,因为鲁文公十二年秦晋在河曲大战,秦国在伐晋之前,曾派大臣来鲁国做过工作,鲁国态度暧昧。河曲之战,晋国失利,因此对鲁国多有不满。此次鲁文公到晋国朝见晋侯,重申昔日的盟约来缓和调整关系。所以对子家《鸿雁》所表达的意思,鲁国的权臣季文子推辞了,季文子赋了《四月》作答,《四月》首章:“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主要是讲大夫行役在外已经很久,想要回到家乡去祭祖。这是委婉拒绝的意思。而子家接着又继续表示请求,赋了《载驰》,这首诗里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是表达小国有危难,想要请求鲁国这样的“大邦”伸出援助之手。意思一次比一次恳切,言辞一次比一次恭敬。鲁国抹不过情面,终于答应为郑国奔走斡旋。此时季文子赋了《采薇》,其四章云:“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取其“岂敢定居”的字面意思,表达愿意折回晋国,为卫国奔走的意思。
除了赋《诗》表达请求、礼敬、友好等意图,也有赋《诗》委婉表达讽刺之意的例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4]4331
齐国的庆封不知礼仪、不通诗歌,是个不学无术的鲁莽贵族。他在接受鲁国宴请的时候,表现粗鲁,对叔孙不敬,因此叔孙用《相鼠》来嘲讽他。《相鼠》是《诗经》中骂人骂得最直接的一首诗,诗意也浅显易懂,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直接讽刺庆封不知礼、不懂礼,然而庆封竟然听不懂。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还记载了一起“诵《诗》”的例子。与赋《诗》相比,诵《诗》没有音乐的配合,更加突出了言语的意义,表达的情感指向更清晰。《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记载,一名乐师为了陷害卫献公,故意违反命令用“诵”的方式将《巧言》读出来,激怒了孙文子。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4]4248
卫献公让乐师将《巧言》的最后一章唱出来“歌之”,用以给孙文子难堪。乐师没有答应这么做,师曹因为与卫献公有仇,想要激怒孙文子杀死卫献公,故此时跳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做这件事。他担心用歌唱的方式,孙文子会听不懂其中的讽刺之意,特地用了更为清楚的朗诵的方式,成功地激怒了孙文子。
诵《诗》,是从赋《诗》到引《诗》之间过渡的特例。它仍然与礼仪相关联,但却再一次突破了礼仪的传统,脱离了“乐”的配合,更加直接地表情达意。但《左传》中关于“诵《诗》”的例子不多,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普遍。
赋《诗》,是春秋时期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歌《诗》相比,它的使用场合多在燕飨这样的正式社交场合,宾主双方相互酬答,配乐而吟唱《诗》中的篇章。它的礼仪完备程度有所削减,削减了“舞”的因素,而且也不必全篇吟诵,可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只选取其中的一章或数章来“赋”。可以说,相对于歌《诗》,赋《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更为实用精简。赋《诗》的过程中,借助于“断章取义”的方式,《诗》的文本意义得到应用和阐释。在春秋时期的外交事件中,《诗》的功能性得到了极大发挥。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各种人物引用《诗经》,或赋或诵,表达了各种丰富的情感,或委婉陈情,或直言讽喻,达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交目的。
四、《引诗》:脱离乐舞,语义独立
在春秋时期《诗》的应用中,引《诗》的例子最多,是赋《诗》场合的2倍以上,共有181条。引《诗》的形式,包括“《诗》曰”“《诗》云”,以及引具体篇章名等。从《左传》来看,最早的引《诗》记载是在鲁桓公六年,郑公子忽引《大雅·文王》中“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一句来拒绝齐国的联姻,比最早的赋《诗》记载(鲁僖公二十三年)要早69年。其间引《诗》的记载不曾间断,而鲁定公四年之后,赋《诗》的记载销声匿迹,引《诗》仍大行其道,哀公二十六年,仍有子赣引《大雅·抑》中“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的记载。
上述现象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引《诗》的方式很早就在贵族阶层的言谈交流中出现,正如孔子所描述“不学诗,无以言”;二是在赋《诗》退出历史舞台后,引《诗》以强化观点、增强说服力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并且在战国时期逐渐从言谈交流发展到文本书写。
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礼仪逐渐被武力征伐所取代,赋《诗》也失去了应用的礼仪场合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脱离了乐舞与礼仪元素,更为直接地在对话或行文中引《诗》的方式就逐渐成为《诗》的主流应用方式。《诗》中的文本字面意义或其引申出的哲理成为表情达意、说服论理的有力论据。引《诗》不再需要乐、舞的配合,也不必在正式的社交仪式上应用,而是深入到日常交谈、说文论道之中。可以说,从赋《诗》到引《诗》,礼仪的因素进一步消退,而《诗》中的语义和意指突破了乐舞的限制,进一步得到发挥。
引《诗》发生的场合,也多在诸侯国往来的君臣政治外交场合中,引《诗》作为有力的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说服对方。这是利用《诗》自形成以来就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所具有的权威性,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颇具“引经据典”的功效。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了北宫文子的一段话,他为说明“威严”的礼仪内涵,多次引用《诗经》来解读礼仪,把《诗经》作为礼仪的范本来解读,充分体现了诗经在春秋时代作为礼仪规范标尺的应用。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4]4437
北宫文子先用了《大雅·荡》中的句子“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推断楚国令尹子围的下场,再用《大雅·抑》中“敬慎威仪,惟民之则”提出为人君者应该具备的德行和礼仪,解释“威仪”的含义和形成,北宫文子先后五次用《诗经》来阐释威仪的意思,体现了《诗经》在礼仪方面的权威性和准则性。
同样与礼仪相关,《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4]4407
叔弓到晋国聘问,晋平公派人在郊外慰劳,叔弓的表现有礼有节,受到了晋国大臣叔向的欣赏。叔向引用《诗经》“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来褒扬叔弓的行为符合礼仪,是有德行的表现,阐明了忠义与卑让,是礼的两个重要方面,进一步说叔弓辞不忘国和先国后己的举动正是忠义与卑让的具体体现。这明显是用《诗》中“以近有德”的句子来突出论证子叔子“近德”。
春秋时期频繁的引《诗》、赋《诗》活动,其实是当时所公认的政治和社会准则,如明德讨罪、尊王攘夷、兴灭继绝的外在实践。这背后所蕴含的,是以德为先、善恶明晰、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价值。所有的赋《诗》、引《诗》行为都是在这样的语义环境下进行的。正是在公认的价值标准体系下,尽管不同的人对《诗》中篇章词句的阐释不同,却能够最终达成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沟通和交流,实现赋《诗》、引《诗》的政治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的引《诗》不仅是将《诗》作为经典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引《诗》的过程中,出现引《诗》之人为强化自己的观点,对《诗》进行的诗旨的解释。这种解释方式极大地影响到后世儒家的系统解诗的观点,成为后世系统解《诗》的渊薮。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楚国政界的人事安排。作者认为这样的安排人尽其才,恰如其分,因此借用《诗》中《卷耳》的句子,来说明楚国“能官人”: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5]888
《卷耳》为《周南》第二篇,其诗旨为何,各家观点不一。但就其文词字面意思而言,应为“怀人”之作。诗中有“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一句,字面意思其实是说,女子思念行役在外的丈夫,将刚刚采集的卷耳放置在道路之旁。但自《左传》将《卷耳》中此句解释为“能官人”——朝廷能够正确恰当地使用人才,将人才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之后,《毛传》《郑笺》《正义》等解此诗,均以为此诗与“求贤审官”相关联,诗旨为“进贤”。如《毛诗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6]543《正义》中进一步发挥,称:“作《卷耳》诗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忧在进贤,躬率妇道,又当辅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贤德之人,审置於官位,复知臣下出使之勤劳,欲令君子赏劳之。”[6]544从《左传》到《毛诗》,此间的关联,清代经学家陈奂讲得十分清楚:“思君子,以周为周之列为,皆本左氏说。”[7]14此类例子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奠定后世儒家《诗》教基本纲领的《毛诗》解诗体系中,许多诗旨的理解和解诗的路径都来源于《左传》中的引《诗》阐释。
可见,在礼乐消退的大势之下,《诗》借助于文本的存在,逐渐从礼乐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文辞独立的应用。春秋时期盛行的引《诗》,为后世《诗》教脱离乐教独立发展,同时也为后世以语义理解《诗》开辟了道路。
五、结语
从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诗》的应用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诗》之用与礼乐的消亡和政治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当周王室失去了对国家政治的掌控力,以王室为中心的祭祀典礼便逐渐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淡出,如《勺》《象》《武》《大夏》这样等配合祭神、祭祖仪式的大型乐舞就此失去了演示的舞台,而在不同的仪式中区分和标志着天子、诸侯、卿士地位尊卑不同等级的《肆夏》《采荠》《驺虞》等乐仪也渐渐退出了政治生活,原本附着于《诗》的乐和舞,也随着实践应用的减少,而在流传过程中渐渐消亡。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到《诗》复合形态的单一化过程。随着礼仪的简化,表现礼仪形式的“舞”与“乐”的功能逐渐消退,而带有明确意义指向的《诗》的功能得到强化。从《左传》中的记载来看,配合乐与舞的“歌《诗》”记载仅有2例,与燕享等礼仪配合的“赋《诗》”共计68例,言谈之间直接“引《诗》”共计181例。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之用越来越简易实际,礼仪功能退化而交流功能强化。从乐、舞、歌、诗一体的崇神仪式,到乐、歌、诗一体的燕享仪式,到以乐配《诗》的歌《诗》,再到无乐而诵的诵《诗》,最后到完全消除了礼仪印记,在言谈之间直接引《诗》的变迁过程,完整映射了西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消亡史。
注释:
① 此处依据毛振华所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左传赋诗研究》第69页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