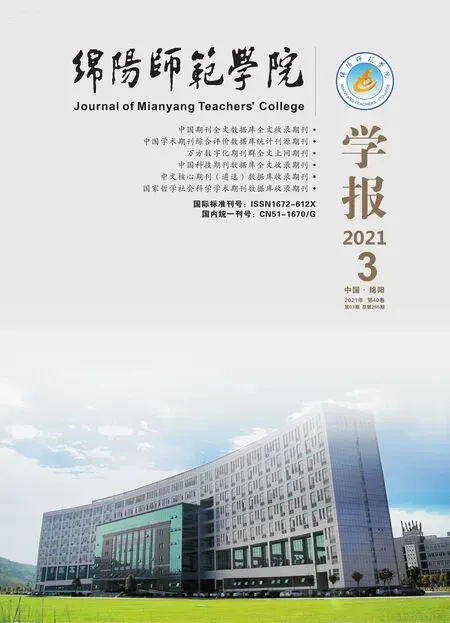浅论周梅森战争小说的艺术特点
徐雪涛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周梅森的战争小说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起很大轰动,其作品以对“战争与人”的反思将战争小说这一类型的创作推到历史纵深,显露出新的文学面相。从创作伊始,周梅森便以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向历史深处掘进。他着重探索历史变迁之间的偶然性、无常性以及人在历史车轮下的脆弱与渺小。当这种历史意识与战争题材相遇,更能从中显示出悲剧情怀与人性挣扎。在《军歌》《国殇》《日祭》《大捷》《冷血》等构成的“战争系列”小说中,周梅森将关注点瞄向作为“人”的独立个体上,关注那场悲壮战争场景下“个体的心灵冲突与命运浮沉,以此来探究人本身”。周梅森通过对以往被遗忘的国民党军人群体的执着书写塑造了新的军人形象,摹画了复杂多元的人性意识,流露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清醒的反思精神。
一、新军人形象的塑造
(一)新军人形象得以塑造的原因:政治与文学的互动
战争小说是以战争行动为主的文学作品,从这一释义出发,战争双方就成为了战争小说作家的重点描述对象与创作内容。对于经历过漫长烽烟岁月的中华大地来说,战争可以算是极具现实感的文学描写题材。在十七年时期,由于文艺方针政策的规约以及主流文艺批评价值取向的导引等原因,当时的战争小说多着笔于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抗击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故事。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在这些以共产党军人为主角的文本中,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处于一种失语或缺席的状况。直到新时期这一情况才得以改观,大量客观书写国民党军人抗战的作品才逐渐出现。
这种现象首先要归结于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肯定与评价。1985年9月3日,首都各界一万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共两党合作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毫无疑问,这场讲话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意义作出了新的评价,同时也为小说创作题材的拓宽奠定了基础。因此一批秉持客观历史态度的作家纷纷开始以超越阶级的眼光来书写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史实。也正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中,大量描写国民党军人的作品问世,被遮蔽的国民党军人群体逐渐被还原成更具真实性的军人群体。不过由于时代的悲剧和自身的缺陷,加之国民党军人所处阵营的特殊性,这些因素合力使得文本中出现的国民党军人的人性内涵更加复杂多元,这也在无形中为塑造新的军人形象提供了发展契机。
张廷竹的“中国远征军” 系列小说、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 、王火的《战争和人》、江建文的《国难》等作品试图探寻历史真相,描写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史实,为战争小说的题材拓宽迈出了第一步。这些作品的出现也说明更加真实、更加贴合历史的全民族抗战图景正在被打开,而周梅森毫无疑问是其中的创作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的“战争与人”系列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视角与描写对象,为读者建构了新的军人形象,还原了更具真实感的历史画卷。从选取题材来看,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国民党军人。《军歌》《大捷》《日祭》《事变》《荒天》《国殇》《冷血》等。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按身份来说,都是自愿或被迫投入战场的国民党上下级军人,甚至是委身附逆的伪军群体。在这些作品中,周梅森没有采取以往脸谱化塑造人物的方式,站在道德和民族的制高点上一味谴责其恶行,而更多的是在剥离了其身份和阶级的基础上,用一种人性的思辨角度还原了在特殊境遇下人物的言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周梅森得以创造出区别于大多数战争小说作家的新军人形象。
(二)新军人形象的英雄色彩和民族气节
首先,周梅森作品的军人形象在打破隔阂与阶级意识的属性外,赋予了人物比以往更多的英雄色彩。周梅森小说的主角俱是国民党军人,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主要人物多处在一种堪称“绝地”的场景中。《军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徐州会战国军溃败被俘的集中营(地下煤矿)中;《日祭》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大部即将沦陷,林启明所部深陷强敌环伺、注定失败的守城战中;《国殇》开局就是陵城保卫战,在面对增援部队或溃散或附敌的情况下,杨梦征的新22军也陷入了绝境。毫无疑问,这些“绝境”的设立使得作品的可读性大大提高,带给读者的直观感受和冲击力也不断加强。
所谓向死而生,在这样的险境中,作者充分塑造了一批体现英雄气概和民族大义的军人形象。《日祭》主要描写的是以林启明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军人于淞沪会战时被迫进入租界,成为战俘而被租界当局关入“第九军人营”的故事。在战俘营中他们始终不忘家国民族,以精神升旗、每日操练等活动提醒自己的身份,彰显爱国的情怀。林启明是作家笔下具有鲜明人物色彩的一个角色,作为国军1776团3营营长的林启明在德信公司领导的战斗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充分显示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面对租界军官布莱迪克上校关于其放下武器进入租界的建议时,林启明的回答充满了民族气节:“可兄弟据守的这座楼房上还飘扬着我们的国旗,中国守军还在战斗。”[1]192在后期被迫进入租界的记者会上,下层军官涂国强的发言也体现了作者浇灌在国军群体上的民族情感。在面对记者关于抗战前途之提问时,涂国强回答道:“兄弟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必定光明!最后打胜的一定是咱中国!战斗虽一时失利,弟兄们的抗战决心偏就更坚定了,有我们国军弟兄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坚强决心,哪有他妈打不败的敌人呢!”[1]210除此之外,像《国殇》中不愿投降率部突围的师长白云森、杨皖育;《军歌》中虽然被俘但是一直渴望重回战场、重拾象征军人尊严的那首军歌的炮营营长孟新泽;《事变》中一心反正带领部队投奔国军的黄少雄;《大捷》中虽被迫担任阻击却打得顽强勇敢的段仁义、霍杰克、方向公与卸甲甸百姓, 这些人物可以说都是充满民族气节和英雄基因的抗日志士。
(三)新军人形象的失败感和落魄感
其次,周梅森笔下的军人形象充满了落魄感和失败感,是一群极具个人色彩的军人画像。作者描写的国军形象突破了以往的“脸谱化”“小丑化”的标签,赋予了他们更多应有的家国情怀,同时因为时代的原因也给他们刻上了落魄与失败的烙印。《大捷》中的“国民革命军23路军新三团”被放置在马鞍山一带阻击日军,可是这支部队却是由县长、保安团长、决死队长、小学校长、甲长、保长、铁匠甚至疯子临时拼凑成的,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乌合之众”。《军歌》中在台儿庄大胜之后,因为上级的不当安排而使得孟新泽“他这个扛了十八年大枪的中国军人竟然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举起了双手”,以至于和无数个军人一起被关押在战俘营而“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悔恨中”[1]4。《国殇》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杨梦征率领的陵城子弟兵在援军或被击溃败逃或被敌伪诱降而倒戈一击的情况下,不得不签下了象征耻辱的投降命令而在三颗信号弹升空之前饮弹自尽,将投降的命运留给了在世者。
《军歌》中的主人公炮营营长孟新泽作为传统的中国军人,面对国破家亡的灾难,他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刻骨仇恨,对刚刚过去的失败悔愧不已。所以这也使得他对过去辉煌胜利的代表——“军歌”——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一想起就激动不已。为了重新拾起军人的尊严,也为了自己的自由,洗刷投降的耻辱,他率众串联起了煤矿地下的暴动,甚至“不择手段”地欺骗战友们外边有游击队策应。在孟新泽的回忆中,激战初期,“他和他的弟兄们情绪是高昂的,他们都下定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以死报国的决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大搏斗”[1]40。所以在开始的战斗中,孟新泽们表现得英勇且坚韧,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和品格。但是作者却把这些情节隐藏在人物的回忆中,更多地将情节聚焦在战俘营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文本中,军人形象被赋予了一种落魄感,始终萦绕在一种失败和耻辱的氛围中。可以说,这种描写使得他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传统军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又赋予了他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写出了他在战俘营的煎熬与挣扎,在崇高性的基础上给人物褪去了高大的光环,还原其为惶惑、愧疚又脆弱的普通人。
毫无疑问,这些军人与以往那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军人形象相差甚远,可以说这样的军人因为战争的失利而显得有些过于颓败,充满了一种伴随始终的落魄感。正是这种落魄感使得周梅森笔下的人物始终处在一种极强的张力中,也使得整个故事由于充满了一种潜在的抗争性而处在浓烈的悲剧氛围中。这种张力一方面使得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另一方面也为人物由落魄向高尚、由平凡至伟大奠定了合理的逻辑起点和故事背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与外在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无关,它取决于个人的意识、尊严、品格,取决于人性中善与恶的博弈。在这样充满张力与流动性的故事下塑造出的人物以其落魄和扭曲显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异化,同时由于其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心理与言行,也让军人这一角色在战争中的成长与升华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赞扬。周梅森敢于把这样身上有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来塑造,即便是写正面人物,也注意到他的复杂性,不去一味美化。这一切都具有开拓新领域、冲破长期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人物的意义,对于战争小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
所以从上述两个军人属性的塑造上,周梅森没有给笔下的国民党军人群体简单地作出“英雄”或者“失败者”的历史二分法型的粗暴评判,“而是力求立体的呈现出人性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与消长, 刻写出一个个正义与罪恶并存, 肮脏与美丽互现的军人的灵魂”[2]。因此出现在周梅森作品里的国民党军人于民族独立与反抗侵略的战场上萌生出的民族正义感与反抗感,使得他们获得了与以往国民党军人不同的人物属性:在落魄中力求生存的可能,在战乱中心怀家国的情怀。这两种属性在周梅森笔下的军人形象中叠织缠绕营造了一种悲壮感。与以往书写战争的悲壮感不同,《高山下的花环》《黎明的河边》《林海雪原》等作品的悲壮感主要来源于主人公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周梅森塑造的新军人形象一方面充满了民族气节和正义感,面对民族矛盾、国家危亡他们挺身而出,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最高当局及军事决策者的昏绩自私乃至险恶用心,常常使第一线的官兵陷入困境乃至绝境”,他们“皆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道义而陷入双重的困境,这就是周梅森军旅小说悲壮气氛的重要成因”[3]。正是在这样极具悲剧感的故事叙述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新军人的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人物画廊。
二、复杂多元的人性意识
周梅森的小说多从历史、现实与土地取材,由此出发他的小说注重着笔于抗战历史的再建构,同时又因为特定的时代使得他笔下的战争故事在重建与解构中蕴含了深沉的人性意识和历史叹息。纵观战争小说的发展历程,十七年时期的战争小说注重以大场面、大构架、大情势来渲染战争场面的宏阔与壮烈。《红日》《保卫延安》等作品就以“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被称为史实性作品。但是十七年时期的战争小说,可以称之为“大众文学”,却在艺术上缺乏一种更为严格的文学审美追求,尤其是人物刻画缺乏深度,影响了其文学价值。直到八十年代,更多的作家开始普遍认同“人性是最为根本的思想、认为文学的最深(也是最后)的层面便是人性之后”[4]286。因此,以周梅森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不仅对题材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弥补了描写对象上不平衡的状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以一种超越阶级的眼光,在克服历史的政治惯性和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上对战争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对于战争中透视出的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挣扎作了文学艺术上的深刻描画。可以说,他“在重新审视战争本身的诸多奥秘的同时,以更为多样的目光致力于战争中的人的存在景况及各种社会人性内容的具体形态的重新发现———他们不再为写战争而写战争:战争的描写不再是目的,描写的目的仅仅在于:经由战争的洞观而重新认识人、重新认识人类的处境”[5]。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的”。可以说,战争是人性冲突爆发的最终方式,也是人性博弈最残酷的场地。周梅森“战争与人”系列小说的立意即在此,他无意于描摹战争场面的激烈与壮阔,而是试图采取一种淡化战争场面的叙述技巧,将更多的笔墨投入在“战前”与“战后”心理精神的矛盾与冲突中,从而在压抑低沉的氛围之中展现人性的裂变。战争在周梅森笔下逐渐退化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作者在一种更宏观也更有距离感的高度,从“人”这一族类意义上的视角去审视战争。经由战争这一显色板,人性在伟大与高尚、黑暗与卑鄙之间的“交战”显得更加清晰,人性之间对于命运和无常的抗争也就显得更加触动人心、扣人心弦。
(一)对于人性恶的直接展示
周梅森对于人性书写的第一个特点即是将人物置于绝境之中,在灵魂的冲突与内心的挣扎中,写出了生死威胁时人性的丑恶,从而指向战争时期人的历史存在的灾难性状态。《冷血》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远征军战事失利败退回国的途中。作者没有着笔描写战争场面的残酷,而是将视角转向战后求生的故事上。在小说中作者极其巧妙地将人物引导到野人山这一生死未卜的场域之中,给了故事很强的巧妙感和可读性,为人性在非常时期的展示提供了绝佳的场地,同时用严酷冷峻的叙述口吻让读者从故事的发展和人性的流变间体会到当时的悲壮与惨烈。《冷血》中的主人公尚武强是第五军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从他在后面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中——“在重庆军官训练团接受蒋委员长的召见”,“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责任,一定会历史的落到他们这代人的肩上”[1]131,可以想象,尚武强也曾经是一个充满愿景和热血的青年军人,他的身上闪烁着属于军人的光辉。在第五军残部一万七千余人奉命穿越野人山,转进印度集结待命时,尚武强“凭借人格的力量和铁一般的意志”奇迹般地稳定了部下骚乱绝望的情绪[1]107,顺利地完成了编组进入野人山的任务。初入野人山,尚武强还能鼓励士气,与恋人曲萍共同扶持。但是在面临缺少粮食给养的情况下,尚武强逐渐变成了曲萍口中的“野兽”。为了活命,他利用强权霸占了曲萍,威逼伙夫老赵睡在帐篷外。到最后,他为了摆脱曲萍自我逃生,甚至装出中毒的症状,在曲萍找人解救他时悄悄溜走。最能暴露人性的就是在尚武强独自求生遇到曲萍的路上。当时尚武强打了两只狼崽正烤得发油,曲萍无意间与之相遇。在食物和恋人面前,尚武强的选择让赤裸裸的丑恶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手枪指着曲萍的胸膛,声音像“一阵刮自地狱深处的阴风”,冲着曲萍喊道:“我不认识了!谁也不认识了!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只有我!给我走开!快!快!快!”“他急迫的一连说了三个快字。”[1]168尚武强的选择是环境恶劣使然,但也是人性深处的裂变,是战争这一残酷行为对人的扭曲和异化。同样表现人性在极端场景下的丑恶还体现在作者的其他小说中,如《军歌》中为求自保而向日本人告密孟新泽等人暴动的刘子平;《荒天》之中无视家国民族,一心只为保存实力和自我权力的形形色色人物;《孤旅》中在民族危难、国破家亡之际,却将其所携带军饷拿去做生意的少将军需官马炳如。这些人物的出现将周梅森笔下对于人性思考的第一个特点展现了出来,说明“人性既受文明社会的道德约束,又受人的种种本能驱使,战争中的人性又比非战争状态下的人性更加复杂和不可捉摸,因为战争迫使人直接面对的是生与死的考验。因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性的最大显微镜,人性的种种美丑善恶尽在它的透视下显现出其本来面目”[6]65。
(二)对于人性善和美的肯定
周梅森对于人性描写的第二个特点即在生存荣辱之际写出了人对于生存和生命的渴望与追求,对于人格中善与美的肯定,对于在特殊形势下军人品格中英雄主义的赞美。《大捷》写的是因为阴差阳错的误会,卸甲甸的百姓被编入“国军”队伍,奉命在马鞍山一带以战死一千六百余人的代价阻击日军三十六个小时而取得“大捷”的故事。故事中的国军并不是因为感受到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才去参军,相反在三个月前他们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只是因为章方正、兰尽忠等人的一时意气,将驻扎在县城但是军纪败坏的国军炮营“连锅端”了,才被23路军总司令韩培戈强行编入队伍并被放置在最前线。前有强敌进攻,后有1761团阻隔后路,这些原本连战壕都挖得松松散散的“乌合之众”们硬是将日军阻击在战线以外,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可以说,这场所谓“大捷”的战绩出自于玩弄心计的“阴谋战争家”韩培戈之手,也同样出自于每一个不屈、勇敢的灵魂。面对困境,他们开始时有着各式各样的目的:有的想要发财,有的想要落草,有的想要投敌,有的想要脱逃。但是正如章方正在战前会议之后所想的那样,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战争是怎么回事。只要打起来,他们的目标就是一致的,命运就是相同的,他不能指望在一场恶战之后,别人都死他独生。事情很简单,兰尽忠的二营打完了,他的一营、侯营长的三营都要上,下岗子村前沿失守了,他们所在的上岗子就会变成前沿”[7]133-134。带着这样共同求生的意念,这些形形色色的想法在战斗开始后慢慢地转化为对于生存的希望、对于生命的渴求。他们与敌人殊死搏斗,“在无法抗拒的双重压榨中,他们的生命走向了辉煌,爆发出令人炫目的异彩”[7]189。最终在战争与生命的毁灭中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升华,展现出了人性中的优秀品格。
(三)对于流动的人性的刻画
需要注意的是,周梅森笔下人物的人性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恶向善的回归,由兽性至人性的复苏始终处在一种变化的过程中。在《军歌》中,孟新泽、项福广、王绍恒、刘子平、耗子老祁、张麻子等人,他们因为徐州的溃败而被俘,最终都被关押在苏鲁交界的一个煤矿当苦力。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的生命处处受到来自煤矿底和日本人的双重威胁,可以说战俘营/煤矿是这些军人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的葬身之地。那些建立在正常社会的秩序、规则、道义和理智在这里荡然无存,生存的法则变为个人力量的博弈。像来自汤军团的普通大兵田德胜,他“凭着一身令人羡慕、又令人胆怯的肌肉,赢得了又一次生存竞争的胜利”[1]13。可以说在这里,一切正常社会加之于人类的规则、秩序和等级统统被打破,弱肉强食和明哲保身成为了人人遵循的不二法则。这种极端的环境设置为作者深层次的剖析人性善恶提供了场景,也让之后发生的故事有了合理的逻辑起点。孟新泽们在前夕还是血战台儿庄、保卫徐州的抗日英雄,但是一瞬间的溃败和投降让他们丧失了军人所有的荣誉和尊严。当直面死亡,人性的丑恶便尽数展现了出来:为了逃命,项福广向日寇告密,使得逃跑的战友惨遭杀害;为了求得生存的砝码,刘子平精心谋划告密的时机;当代替老祁穿梭在坑洞之中时,田德胜对自己找到出路抛弃地下的战友没有丝毫犹豫和愧疚;当越狱暴动因为告密而惨遭失败时,多数人甚至想要抓住暴动的组织者孟新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自私、卑劣、狡诈、猥琐这些丑恶现象的爆发像炸弹一样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但是作者却不是一味地去描写人性的丑恶,而是在变化中写人性,写变化的人性。被孟新泽所感动,田德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将他藏在之前的坑洞中;为了洗涤自己内心的愧疚与惶恐,项福广坚定地站在了暴动的行列中,提着枪走在队伍的前列;耗子老祁在不断的侮辱中,最终点燃了弹药室的引线,一群即将被杀的战俘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随着环境的变化、周围事态的发展,每个人的人性也在起着变化。正因如此,人物形象才显得更丰满,戏剧冲突性才更强,作品才更凝重,流动感也更强,情节进展得紧张起来,紧扣读者的心弦。
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清醒的反思
(一)深沉的历史意识
周梅森小说的着重点除了写活了深层心理中的人性意识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深层开掘人性意识的基础上嵌入了对沉重岁月的历史思考与自我对于战争的独特感悟。厚重的历史感和始终清醒的对于战争的反省,可以说是周梅森作品极鲜明的特点,也是贯穿他作品始终的一个主题。“历史和人的思考,确实是他的小说的潜在本文,是他创造意识上一个中心系之的情结。”[8]十七年时期的战争小说主要目的多是“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思想、生活的意识形态规范”[9]95。这类作品对于历史采取的是巩固的手法,是起着“战争形式的历史教科书”作用的,试图以文学的形式重现那段岁月的革命史。直到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盛行,“被现代主义思潮包围的中国,开始接受另样的历史观,并且由于长期以来文学歪曲存在的真实性而根据英雄主义的需要任意拔高人物、美化人物的做法已使人反感甚至是厌恶,文学对历史换了观察的眼光。而这种眼光受了新的情绪与新的观念的影响,将历史读成了另外一番样子:历史与英雄无关,只与细民有关;历史上本无英雄”[4]295。
在此背景下,文学不再简单地对历史进行重复,而是开始以一种个人性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释义和构造中去。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的:“作为文学创作者的‘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文学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断地‘流通’进行着‘塑造’的作用。”[10]而克罗齐也曾对历史有过经典的表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具有较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文学在与历史的双向互动中不断解构和重构了现实的“材料”,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观越来越受到质疑,个人化的文学想象将历史变为一种不断言说和意义生成的组合形式。周梅森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作者“想象天才的艺术结晶”,跳出了历史法则的局限性,在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的历史结局里找到被粉饰的多样化的进程,发出了以往被遮蔽的声音。
《大捷》背后因为高层的报复而丧命于日军炮火下的卸甲甸百姓;《冷血》中辗转回国路上像曲萍、何桂生这样小人物的痛苦与生命的最后经历;《事变》种砦司令治下的广清八县俨然半封建的旧中国;《荒天》中围绕反正与附敌,众人之间展开的博弈与算计,更让人看到了历史背后隐藏的杀机和圈套。历史对人性的不断深入解剖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国殇》和《军歌》。《国殇》描述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新22军围绕陵城保卫战的失败过程及深埋其中的内部矛盾。作者显然不在于着意描写战争,除了开篇通过军事会议来渲染气氛的紧张外,更多地通过新22军的军官们在战役前后的不同选择展开了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小说根据战役的不断推进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辅之以不同的主要人物。从杨梦征到白云森再到杨皖育,从陵城起家的杨氏子弟兵最终回到了杨梦征的侄子手中,历史在这里巧妙地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形结构,暗示出了历史的波诡云谲以及人在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小说因围绕军权的归属而不断转换的众人走马灯般出现在读者面前,军官们在光荣与耻辱、生存与毁灭前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也透视出人物的性格面目和发展过程。作者以白云森的死暗示了理想主义下传统道德历史模式的破灭,道出了历史无情的铁血法则,而以杨皖育发给中央的电报作为结尾,为逝去的众人安上了“殉国”的帽子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给读者留下了关于历史的深沉思考。当然,对于历史更直接的解构体现在《大捷》这部小说中。小说的下篇以中央社、共同社、美联社、前线社、亚通社、《明报》等报社对于“大捷”的报道以及授勋仪式上段仁义等人对韩培戈的复仇相对比作为结尾,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个光鲜如‘大捷’‘军歌’‘国殇’的名词,而是一段充满了光明与阴暗、鲜花与鲜血的冷漠残酷的蜿蜒曲线。真正的历史不存在结果中,而是存在于过程里。”[11]92
(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清醒体悟
除此之外,不同于以往作家对于战争的礼赞和对英雄的颂扬,周梅森在作品中始终有着清醒的思考。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生动地描写了战争对于美好的摧残,同时也在思考战争状态下人的个体性和自主性。在《大捷》中,团副霍杰克在最后的战役与白洁芬相遇,在为白小姐包扎伤口时,他看到了“那只糊满鲜血的乳房”,“他再也不会忘记战争对美好的摧残,在那一瞬间使他动魄心惊。他曾在用驳壳枪对着前团副章金奎时,无意中瞥见过那乳房,并由此而生出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如今,幻想在严酷的真实面前破灭了,被枪弹毁灭了的美好,使他看透了战争的全部罪恶”[7]197。而在《日祭》中,作者又借林启明这一人物的生死际遇反思了集体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冲突,并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战争涌来,个人被裹挟入国家抗战的巨大变动之间,个人性是否成为了民族的阻碍?看似是作者借助林启明和牛康年的深层次矛盾,思考了“自己个体的生存和民族的生存是否能完全割裂开?民族的生存,是否就是个人生存的天敌和负担?”[1]259-260这样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作者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那就是整个人类对于自由、个体性对于集体异化的一种反思。
但是作者认为,无论是战斗中还是战斗后,林启明都活得太不“自我”,“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活着的时候毅然担起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道义,任何人也编排不出他的不是。他没被责任和道义压垮,这是值得骄傲的。现在他倒下了,身上的责任和道义也就随之消失了。他无需再代表国家和民族,无需再对任何人、任何事业负责,他将作为一个人,一个叫林启明的中国人而迈入生死之间的门槛。这无疑是一种解脱,就象负荷重轭的牛,卸去了背上的重压”[1]270。作者显然对现实主义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才没有使其对于个人性的思考滑入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深渊。最后的结尾,作者借林启明临死时的独白告慰了自我,告慰了整个在战争中牺牲自我的民族:“却不悔,到九泉之下也不悔。如果来世再做军人,再和东洋鬼子打一仗,再到这第九中国军人营走一遭,他依然选择这样的活法。肩着民族苦难的人虽说注定不会有好下场,但一个民族却不能没有这样的铁肩膀,没有铁肩膀的民族是注定要消亡的。只有那些在民族危难时,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由这些真正的人构成的民族, 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1]271
四、结语
总的来说,周梅森的小说习惯在沉重历史的宏大背景下,缓缓叙述一群战败的中国军人的惨痛往事,以一种低沉压抑的笔触描绘了极端环境下的复杂人性。在小说中,作者以粗犷的语言、精心的安排、合理的结构与穿插其中的回忆,写出了新的军人群像。他的作品在绝境的场域中透视了人性的丑恶,又在流动的叙述中描绘了人对于战争这一“大碾盘”的抗争,写出了流动岁月中的真实人性,也歌颂了人性中的高尚品格与伟大精神,让读者在人性的翻滚与变化中领悟到战争这一“碾盘”对于生命和美好的毁灭与摧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周梅森的作品中“深沉的历史意识以及深沉的人性意识,是和谐地共存于一个艺术整体中的。它使得周梅森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凝重厚实的史诗般品格,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能摆脱那种简单化的束缚”[12]。所以,他的军旅小说能够在客观的基础上重现那一时期各阶层人士的表现和复杂的心态,给读者展示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有助于加深对民族力量的进一步认识。而寄寓在他对历史进程和结局的演绎推想,则大大提高了他作品的思想含量和意蕴覆盖,使得文本具有了无限的生成意义和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