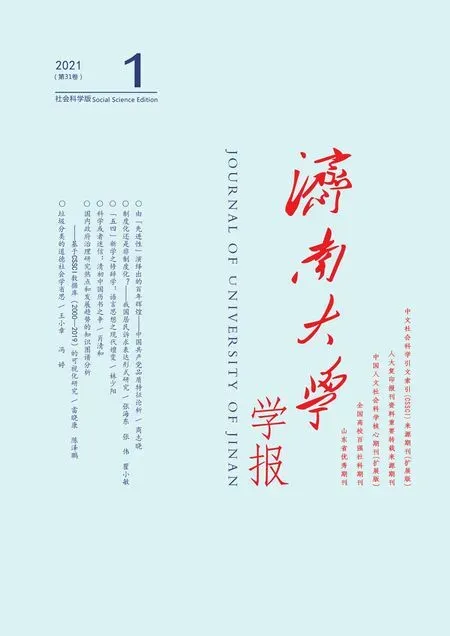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
——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王凤梅,王志霞
(齐鲁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送火神”渊源考
(一)“火神”来自何方
“对人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物,如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下至猫、虎。一类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物,如霤、门、行、户、灶。一类是曾为民创立新法,抵御大灾大难,勤民事劳苦身死,用武力驱杀暴君的古人。”(1)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从史书记载来看,大众意义的“火神”属于第三类。
“火神”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之一,历史悠久,由于受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火神”传说有着多种多样的版本。《左传》记载:“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2)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8-1189页。,火正即火神,帝颛顼时开始设火正,掌管民事,名叫黎,所以流传下来火神祝融说。又有阏氏伯火神说,据《汉书》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25页。这表明在古时候阏伯为“火正”,而火正又被古人普遍认为是火神,阏伯就被认为是火神了。实际上火正是一种官职,并不是火神。综上两种说法,不论是祝融还是阏伯都不是真正的火神,而是古时候的一种官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加之古代的鬼神信仰,“火正”之官就被认为是“火神”了。实际上民众在信仰的时候也说不清源流,也分不清谁是火神,当然也无需分清,作为一种情感和信仰的寄托,有固定的仪式就足够了。
“送火神”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信仰,遍布大半个中国,由于受地域、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各个地方的信仰仪式有各自的特点、各自的方式、各自的举办时间。最为普遍的送火神仪式是在正月初七黄昏时分由年富力壮的年轻人举着燃烧的木棒朝着西南方向送到火神庙中,送完之后绝不可以回头,以防火神附身再带回家中。这个木棒象征着火神,这一仪式就意味着火神被送走了,新的一年里火神不会作乱,一年到头风调雨顺。
(二)大峪村“送火神”仪式的由来
大峪村的正月初五“送火神”民俗信仰由来已久,仪式的过程与时间和其他地方大有不同。这一信仰及其仪式是何时开始、何故开始的呢?村民也不甚清楚,现在这个仪式在他们看来就是为了仪式而仪式,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所以就一直这样做下去。据村里老人说,村里供奉的火神称作“火德真君”。远古有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于是被后世奉为“火祖”,位列三皇之首。也有人尊称燧人氏为火神,又称火德真君,人们为了感念他的恩德定时祭祀,于是有了固定的拜祭火神的事项,当时多是单人祭祀,是民众自己的“私事”,很少集体祭祀,而且时间上不具有固定性,久旱不雨影响收成的时候才会集体举行送火神祈雨活动。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民间信仰的神祇越来越多,对火神的祭拜逐渐淡薄,很少有人去隆重而正经地祭祀了。直到乾隆年间,村里发生了几次严重的火灾,有一次差点把整个村都烧没了,于是就请了一位道士来做法,道士说是因为村里对火神的供奉不及时,以至于火神发怒了,自此以后便开始了该村盛大的“送火神”仪式。当地的张姓家族,是最开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峪村的“送火神”仪式在一代代的操演中得到了传承、保存和发展。由于信仰仪式关乎村落群体的共同利益,是群众为了寻求神祇庇佑、获得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进行的仪式,故而能得到集体的充分重视。伴随着仪式的发展与传承,村落中关系淡薄的各家各户因此而集结起来,共同体意识就在仪式的组织和举办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凝聚起来,民间信仰越来越受到重视,村落共同体意识就不断加强。
二、大峪村“送火神”仪式
临沂大峪村的“送火神”仪式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群体性活动,该仪式盛大而隆重,充分表现出群众对信仰的虔诚。道具准备、举行时间及流程等都有很严格的规范,其过程繁杂,大致包括筹备、上妆、游行、拜祭、恭送这五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凝聚着当地人的智慧、情感,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点,反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去的形象和过去的记忆性知识,或多或少是在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
(一)筹备
在正式的仪式开始之前,筹备发挥了统领全局的作用。只有筹备得当,仪式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该村有“送火神仪式公会”,仪式举行之前,会长会召集会员开会,商定事宜,如拟定参演人员,和参与人员沟通,采购必需品等等,各家各户都有自己要承担的任务。从这时开始,日常生活中少有交集的村民开始产生联系,平时的世俗群众开始向神圣化转变。
(二)上妆
一般天没亮需要化妆的“演员”就在村委会的会议室穿衣服、排队化妆。化妆师是村里有经验的老人,他们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按照“演员”们的服装特色设计脸谱,几笔就勾勒出完整的人物脸谱,用色大胆、豪放,红色、绿色、黑色、黄色等颜色混搭,很有冲击性。人物脸谱来源于当地盛行的京剧中各种常见的历史人物,如曹操、关羽、四大天王、西游记中的师徒等等,但其不拘小节的特色与正宗的京剧脸谱相比,更有生活气息。临沂地区的京剧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据村里有年纪的老人讲述,大峪村以前京剧很流行,村南有戏台子,也有自己的戏剧班子,经常去别的地方表演,也在自己村的戏台子上表演,村里老老少少和十里八村的人闲暇时就会去观看,是村里的一大娱乐项目,村里固有的京剧传统给送火神仪式增添了不少色彩。
(三)游行
装扮好的人物按照次序排好长长的队伍,队伍中有高跷队、锣鼓队、舞狮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的是锣鼓队,敲锣打鼓在前面开道,像是在告诫各方神灵、小鬼,让他们避让,不要“冲撞”了火神。锣鼓队是由一群老人组成的,他们一大早起来就凑在一起练习演奏,演奏的曲目是什么不甚清楚,但是铿锵有力、震撼人心。其次是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其中一位是男扮女装),扮演的是一家三口。男推木车,车上有金元宝,还有一个布偶娃娃,“女人”时不时抱起布娃娃,摇来晃去,像是在哄觉。紧跟在后面的是“老四”,反穿皮袄,带高粱杆做的眼镜,骑在由一前一后两位随从抬着的扁担上,左手鸟笼右手持蒲扇,形象动作相当滑稽。其后跟着的是“地方”,是“老四”的随从,手拿绳索,在游行过程中随机扔向观众,被套中的就来代替抬扁担的人。据说抬扁担的二人是当时的地方官,为“反派”角色,是村里人痛恨和取笑的对象,没有人能说出他们的出处,但看其扮相和动作,能够看出老百姓的智慧和创造力,表现出民众对于装腔作势的“地方官”的讥讽和厌恶。再后面的就是踩着高跷的四大天官、关公老爷、唐僧、悟空等历史人物,他们大多都是京剧中的角色,还有骑毛驴、挑花篮的仙女童子一类的角色,人物众多,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大街小巷。所到之处,各家燃放鞭炮、贡献食物。村里正中央的大街上这一天也格外热闹,很多小商贩来做生意,游行队伍中的人可以随便拿售卖的东西来吃。在仪式的现场来看,仪式的参与者、表演者对于自己的参与很是骄傲。
(四)拜祭
在村里神圣的信仰公共空间——村东南街口上摆好一排供桌,祭品有来自各家各户自酿的黄酒、白酒,猪牛羊三牲,瓜果蔬菜等,食物是祭祀的主要贡品,以食物供神,是为了纪念人类由茹毛饮血向熟食时代的转变。相对于乡村的生活水平,这些祭品相当丰厚,这也离不开家家户户的支持。供桌旁边是家家户户贡献的金元宝、纸钱、花篮等。供桌上摆有两尊神位,右边是玉皇大帝,左边是火德真君,也就是火神;祭拜人员按照游行次序祭拜,最后普通民众再烧香拜祭。通过拜祭,他们表达了该地村民的共同心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五)恭送
送神的时候先向“火神”表达歉意,然后由一些神婆念数次祭文,希望火神不要生气,能够保佑村民,“保本境风调雨顺,佑四方五谷丰登”(5)《送众神文》,《赛书》,咸丰十一年(1861),写本。。拜祭结束后,游行队伍中的四大天官带领众人在村里的空地向西南方向祭拜,将各家各户带来的香火纸钱、金银财宝尽数焚烧,这样就把火神送走了。
三、活动中村民的合作、互动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一)合作
如上所述,“送火神”这一民俗活动过程繁难复杂,不是只要人人参与、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的,这尤其需要参与人员的互相配合与合作。参与人员的装发需要村内“化妆师”和“服装造型师”之间合作搭配,以使人物形象最大程度上贴近原型;仪式过程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锣鼓队有五位老人,锣鼓声音之所以铿锵有力而振奋人心,离不开锣鼓队成员的相互配合。村里日常生活中用不到锣鼓,所以在仪式开始之前的几天里,锣鼓队才会集结练习,直到仪式真正开始,他们通过练习互相配合、调整节奏,以期达到良好的演出效果;游行队伍里扮演角色的每个人,都需要相互合作和配合,这样才会使整个仪式过程和谐,使仪式圆满完成。最重要的合作就是供桌的准备活动。供桌是整个仪式活动的中心,供桌所需要的物品,不仅需要村里神婆的参与,家家户户也都得贡献自己的一份,分工合作去准备不同的贡品、纸扎等等祭祀用品。在准备贡品的过程中,各个家族出代表来说明去年负责了哪一部分,再商量自己这次要负责哪一部分,然后各自分工。一般所需贡品及原材料需要购买,这时就会出现合作性质的购买队,去赶集购买原材料,供奉所需要的黄酒、炸肉丸等以及金银财宝纸扎都由经验丰富的人家合作来做成。
(二)互动
在仪式的举行过程中,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送火神这一仪式过程中的互动环节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上面所提到的“老四”的随从“地方”,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会时不时地甩动自己手里的绳圈去套群众,他的动作很滑稽,旁边的看客会躲闪,人群中笑声不断,其实基本上套不中,所以有时候会强行“耍赖”。用扁担抬着的“老四”,他拿扇子的右手会时不时指向看客,要求看客到他跟前来“侍奉”。抱着娃娃的老人,在“哄觉”的过程中会走向看客,让他们抱一抱、看一看自己的“孩子”。游行队伍后面各种踩高跷的历史人物,会和路边的小商贩互动,“索要”食物,如此之类的互动有很多。在这些互动中,整个仪式显得无比热闹,村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热闹的互动氛围中变得亲密起来,共同体意识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凝聚。
(三)共同体意识悄然而生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组织、强化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和道德力量并使之定期性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手段的集合。”(6)[法国]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1页。“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村落共同体的仪式活动,来源于古老的“火神信仰”,是发自于内心虔诚的信仰。民众对火神信仰的虔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流程、丰厚的祭祀品表现出来,形成了宏大的场面。这一场面的完美形成,需要村里大多数人的参与:仪式的举办所需要的道具不是一己之力就能准备好的,仪式的各种细节需要集体讨论商定、仪式的举行过程也需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都必须有领导力量和集体力量的存在。仪式兴办之初,是由地方官员、乡绅、僧道、普通民众等多方的合作而完成的,久而久之,村落的集体力量和共同体意识就在一次次的仪式操演中得到加强。而在仪式的举办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看客之间的互动,都使仪式笼罩在热烈而又融洽的氛围之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开心的表情,在这种积极的氛围中,村民之间的纽带进一步加强,共同体意识在其中悄然产生并放大。
送火神这一民俗仪式来源于民众的生活和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村落文化的凝结,在仪式的实践过程中,村民在神圣的信仰仪式中获得自豪感,“每年正月初五很多人来俺们这边,十里八村的,还有外地人,这就让我们很有动力,更有热情的去办这个仪式”(7)讲述人:张先生,45岁,男,大峪村书记,农业户口,讲述时间:2019年1月5日。。村民在仪式中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并且增加了自己在村落中的存在感和自我认同感。送火神公会的会长说:“仪式的操办者主要是老一辈的人,人老了,在村里没什么事干,平常很无聊啊,儿女都在外地,过年的时候组织一下活动,村里一起热热闹闹的,自己也忙起来了,就增加了活力,增强了自己的存在感,有些老人啊,每年就盼着这个仪式的举办。”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仪式让该村民众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存在感,这些感觉会让他们期盼这一仪式的举办,最终的结果就是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加强。
在这一仪式的操演中,村民之间需要合作、沟通与互动,这样就加深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使平时没有交往的人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增强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地方”的扮演者说:“平时不见面的人在这一天都能见到,大家都很开心,很多人之前都不熟悉,比如说我和‘老四’,我俩之前一个在村南、一个在村东北,都没见过几次面,前几年村里找我们扮演这个,我俩等化妆的时候一起抽了根烟,说了说话,很有共同语言啊,从那以后经常一起下棋,去村中央的广场上,就是你们来路过的那个四方形空地,‘老四’和‘地方’这两个角色这么多年了都是我们扮演的。”(8)讲述人:李先生,58岁,男,大峪村村民,农业户口,讲述时间:2019年1月5日。听村支书说年前结婚的一对新婚夫妇是在去年的仪式上产生感情的。可见,仪式的举行过程中,村民能够互动、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产生友情、爱情、邻里情等。所有这些在仪式的举行过程中产生的情感,都在仪式的热闹氛围和宏大场面中得到放大和加强,而这些放大的情感又进一步把个体和共同体联结在一起,共同体意识得到很好的加强。
仪式的举办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也是共同体意识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仪式的操演中,乡规民约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并且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使村民对村落行为规范更加熟悉,在以后的生活中更能得到践行,这就使得共同体意识在行为规范中得到更好的加强和巩固。
台湾学者黄应贵认为:“民俗是农村社会的核心,并不意味着民俗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传统。作为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生存策略,民俗可以根据民众而产生自我变迁,使得民俗具有自变和自适应性,能够避开其他文化的锋芒或借助其他渠道和形式,顺势得以传承,跨越时间,跨越环境变迁,保留内核而依然顽强存在。”(9)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解?——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时代的巨大变迁和人口的频繁流动,会让人产生迷离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区域面临被吞并和瓦解的危险,而传统的乡村民俗文化可以给人强烈的归属感和同一性认识,那些远离乡土的人,每年过年回家,在仪式的演绎中体会到自己村落里独有的信仰及其仪式是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是自己的血液,他们在仪式的举行中,喜悦、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共同体意识也在悄然加强。这些习俗、仪式让他们心里更有底气,更能立住脚跟。其实,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只要乡土还在,民间信仰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对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用就不会消失。村里的王先生说:“常年在外,每次快到年底的喜悦就抑制不住,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不觉得疲惫,一旦踏上这片土地心就安静了,每年我都等过了初五的送火神再离开,不看这个仪式我就感觉空落落的,大家在一起太热闹了,对这个仪式的参与让我有一种自信和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希望仪式继续办下去,以后等我回乡了,我一定为传承它贡献一份力。”(10)讲述人:王先生,29岁,男,大峪村村民,农业户口,讲述时间:2019年1月5日。
这一民俗仪式是该村信仰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人民的智慧和生活经验的结晶,在仪式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归属感和自信心,形成强大的共同体意识,以应对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变迁。
四、结论:民俗活动是区域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途径
民俗活动,来自于村落共同体的祈愿,反过来又参与了村落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大峪村送火神仪式的繁琐复杂需要众多村民的参与、合作,也使平常在村子里缺乏存在感的“边缘人”在仪式中受到重视。村民们怀有各自的目的,进行共同的信仰仪式,共享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利益。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里面的人物需要家家户户出人装扮,各家各户都在仪式的举办过程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并且增强了村落各家各户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使平常忙于各家事务或者外出打工的人们,在此仪式中互帮互助、增进情感,从而凝聚村民共识、增强该村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村民和谐相处和村落的和平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或多或少发生相应的变化,村落共同体意识有所削弱。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村民的个体性加强,民众的参与度逐渐降低,随之而来的就是民间信仰的淡薄,民俗仪式难以传承,共同体意识逐步被削弱,共同体面临解构的危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外流严重,从而使得仪式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年轻人常年在外,互相之前情感更加淡薄,这些都导致共同体意识的削弱。但是,随着国家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逐渐深入,送火神民俗仪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影响力得到提升,其产生的经济价值更是不断提高,这就促使村民更多地重视这一信仰及其仪式,使这一信仰继续发挥自身的价值。
信仰本身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正常情况下的信仰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其作用和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它的这种性质来源于信仰群众的自觉性能够对信仰的人做出规范,使信仰群体在面对社会变迁的时候更加灵活、更加镇定,从而稳定群众,稳定社会。
村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极具稳定性的民间信仰及其仪式造就了乡村人民的总习惯,这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模式。不论时代怎么发展,不论村民离家有多远,每个人都摆脱不了这种文化的影响。民间信仰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用,相对于仪式来说是一种隐形的、比较稳定的因素。仪式是信仰的外化,又需要信仰的支撑,仪式所表现出来的民间信仰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村民的自觉作用下而不断产生变化,但其内核仍然是古老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对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用的发挥,是一个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仅需要村落定期举行仪式来传承,而且还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的重视,从而使信仰仪式不断演练,民间信仰得到传承,以期加强共同体意识,稳定基层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