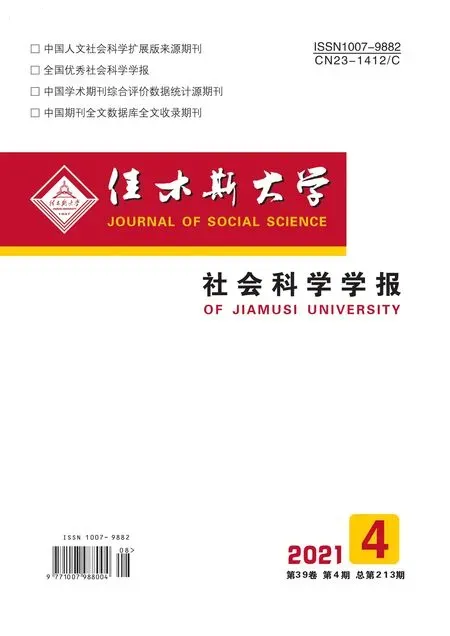论曹禺笔下多元化的母亲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董 洁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一部作品堪称经典,往往离不开对典型的成功塑造。无疑,曹禺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笔下出现的每一位母亲形象,都是个性鲜明的独立个体。其中,不仅有善与美的化身,也有丑与恶的展示。曹禺正是通过这些个性鲜明的母亲形象,寄予着自身对母爱的不同的认知情感,还力求通过对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照,给读者带来多样性的震撼与冲击,体现着极其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人生经历的再现——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感知
曹禺早期作品中对各类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其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客观上来说,剧中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人生经历的再现。幼时的曹禺生活在男权主义至上的封建官宦家庭里,自幼丧母,因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不仅充满了对母爱的渴望,也充满了对封建社会中饱受压迫的女性处境以及遭遇的同情和怜悯[1]。尤其是当他亲眼目睹了旧社会女性作为男权制度体系下的附庸,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并且要时刻面临着来自社会、宗族、家庭的压迫和困境时,他对这些女性们的悲剧命运便达到了更深层次的体悟和认知。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其中,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更是频频出现。正如曹禺所说:“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父权的压迫”,“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2]。
正是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周遭女性悲剧命运的细微感知,曹禺生动刻画出天使般的苦难母亲和平凡质朴的市井母亲两种典型。
(一)天使般的苦难母亲
曹禺是怀着无比尊敬和赞美的态度去描写他笔下的这一类天使般的苦难母亲典型的。在他的笔下,这一类形象的代表是《雷雨》中的鲁侍萍和《日出》中的翠喜。这两个人物均是处于社会底层备受压迫的女性,然而当她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却展现出身为人母最为伟大而光辉的一面,将“神圣的母亲”一词作出了极好的诠释。
鲁侍萍,作为生活在男权社会主导下的底层妇女,她的一生一半属于缥缈的爱情,一半属于令她时刻牵肠挂肚的儿女们[3]。在爱情以悲剧的结尾告终后,她便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的爱与希望都寄予在了儿女们的身上,为了他们,她不惜几次改嫁,尽自己所能去爱、保护着他们。
年轻时的侍萍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对待唯一的女儿,她绝对不允许女儿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侍萍告诉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所以当她亲眼看到四凤正在慢慢靠近自己当年的遭际时,她忍痛逼着四凤在雷声中发下毒誓——再也不见周家的人,逼着鲁四凤跟随她离开周家,远离这一切是非。虽然作品的最后四凤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和她一样惨痛的命运,但是作为母亲的侍萍,至始至终对女儿的爱与保护,却深刻地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这种母爱同样体现在鲁大海和周萍身上。作品中多次采用了细节、动作、语言等描写手法进行了刻画。长大后鲁大海鲁莽易怒的性格,让侍萍深深忧虑着。她极力不想让儿子与周家有过多的纠缠,她对鲁大海说,“你是我最爱的孩子”,并以死相逼阻拦了鲁大海持枪进周家的行为。对待周萍,侍萍更多的是亏欠与牵挂。再次来到周家,为母的本性让她含泪说出了自己积压多年的要求:“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而当周萍与鲁大海起冲突时,“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我是……是你打的这个人的妈”,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之间争斗相残,她心痛却无奈,仅此两句话,就将一个母亲的悲哀做出了最绝妙地诠释。
鲁侍萍这一类“圣母”形象,寄予着曹禺对理想中母爱的渴望与期盼。她一生为子女倾尽所有,不计任何回报。虽然一生苦难,却又用她最温暖的怀抱以及全部的爱,拥绕着她的孩子们,为他们遮风挡雨,这种爱,无关身份地位,伟大而无私。
《日出》中身处风尘却拥有着金子般善良心地的翠喜,无论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小翠,都有着母爱般的关怀。在第三幕中,黑三把小翠拉进屋就是一阵毒打。翠喜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还在屋内,便慌急地乱打着门,“开门,开门!你要吓着我的孩子,我的儿!”“你开门!你开门!黑三!你再不开。我就要喊巡警了。”[4]197即使生活在泥淖中,翠喜对孩子的爱却是永恒的,孩子是她在黑暗中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同样,翠喜也用自己最微不足道的方式,爱与呵护着小翠,给予着她母亲般的关爱,让其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体会到了最后一丝温情。面对小翠被黑三的一次次毒打,她不断地去求情,一次比一次直接而迫切。在她那颗长久麻木的心里,不由地迸发出对小翠母亲般的柔情。她劝说小翠要学会暂且忍耐,免受毒打,“他说的好听的,听着;说的不好听的……我算是满没有听提,这才能过日子。”[4]199这样的翠喜是美的,美得动人;是伟大的,伟大得令人尊重。
侍萍和翠喜,是曹禺所塑造的理想型的母亲形象。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种不计任何回报、超越一切的爱,还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幼时继母和姐姐所给予曹禺的关爱和呵护,让他身上一直保存着的那份对旧社会女性的同情和悲悯之心;更可以看到曹禺对人世间最伟大的女性——母亲的赞美与期许:对待孩子,爱到忍受所有,爱到倾其所有。
(二)平凡质朴的市井母亲
曹禺是带着真实而细微的态度去塑造这类平凡质朴的母亲形象的,在他的笔下,这一类形象的代表是《日出》中的李太太和《北京人》中的陈奶妈。这两个人物均是传统社会中以家庭生计为主的普通女性。她们虽迫于生计,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过多的物质满足,但她们仍旧用自己最纯粹的情感去对待她们的孩子。这类典型是曹禺将母爱回归现实后的真实抒写,在这类人物身上,寄予着曹禺对最真挚、朴实的现实母爱的渴望与赞颂,这也与他自幼丧母,在继母和姐姐的关怀下备受母爱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日出》中李太太生活朴素,与李石清生育了五个儿女,家庭地位不高,对丈夫惟命是从。然而正是这一极其普通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的每次出场,都能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她身上浓厚的爱子之情。第二幕中,当李太太听从丈夫安排和一群阔太太打牌输光了钱时,她委屈的哭了,此刻她想到的是她的孩子们,“可是这是做什么呀!我们家里有一大堆孩子!”第四幕中,儿子小五儿生病了,医院都不肯接收。面对孩子的即将死亡,自身懦弱的性格和手里仅有的十五块钱让她此时只能抽泣着去向丈夫恳求与哭诉,“石清,你得想法子救救我们的孩子”。然而最终儿子还是死去,这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然而虽然李太太深爱着她的孩子们,但是过于依赖丈夫、毫无家庭地位可言的她,即使眼看着儿子死去,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她除了内疚自责,能做的也只有痛苦的抱着儿子的尸身给丈夫打电话“报告”这一噩耗。夫权至上的封建制度长期压抑荼毒着她的思想,低下的家庭地位将她面对儿子死亡时心痛却又无奈的心情刻画到了极致。作为母亲,她的爱是卑微的,是隐忍而又无奈的。让人同情,更让人悲哀,然而这一切罪恶的源泉,则是千百年来统治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体系,曹禺正是透过这一人物的无奈,发出了对封建制度长期压抑人性的强烈痛斥。
曹禺将自己对幼时悉心照顾他的保姆的感情,融入到了陈奶妈这一人物形象中。陈奶妈,一位在曾家做帮佣多年的普通的农村老妇。《北京人》中对她的描写并不多,但我们仍可以透过作品简短的描写,看到一位慈爱且质朴的乳母形象。陈奶妈对待曾文清,始终像对待自己的骨肉一般。被儿子接回家小住一段时日的她刚回来便问曾文清的去处,“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爷不在家?”知道曾文清在屋内,她兴奋至极,文清羞于在换衣服,不让陈奶妈进来,奶妈却笑着说:“清少爷十六岁还是我给他换小褂裤呢。”后来文清出来向她问好,她听后立马面浮光彩,大声地应答着。
从这些小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位老妇心里,一直都是把眼前的这位主子家的大少爷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并且时刻将他记挂在心里,时常惦念牵挂。而正因为她给予了曾文清母亲般的爱与温暖,所以曾文清发自内心的尊敬她,对她始终心存着感激和恭敬之情。这种爱,不就是我们人类最常见的母爱吗?虽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这种爱,平凡却让人感动,细微却见情真。
无论是卑微真挚的李太太,还是和蔼慈爱的陈奶妈,曹禺都意在透过这类形象,向我们传达着这类普通的市井女性对待孩子卑微却真挚、渺小却无私的爱。这种爱是出于人世间最真挚温暖的情感,给予人以感情的寄托与情感的慰藉。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微不足道、却又饱含真情的浓浓母爱。如果说侍萍是曹禺心中理想型的母亲形象的话,那么这类平凡的市井母亲形象,则是他用最平缓真挚的笔触,对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母亲群体的细致模画,他对这些女性投入的关注和感情,深刻而真挚,饱含着同情和怜悯,客观上也是对其自身人生经历的复刻与再现。
二、响应时代的呼唤——对被“巫化”的母亲群体的细致刻画
在礼教森严的旧社会传统家族文化体系中,个人的荣辱往往与家庭的荣辱是密不可分的。而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封建制度的高压下,往往被作为统治奴役的对象,因而一些自小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性格往往变得极其扭曲变态。她们不仅自身是被封建制度毒害的受害者,同时还是封建礼教的执行人与承继者。出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感知,曹禺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群体的戕害,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文化背后的畸形社会制度才是造成旧社会女性的悲剧之源。而封建思想正如一颗毒瘤,不仅深深毒害了这样一批女性,造成了她们的人生悲剧,并且这种从夫、从父、从子的“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还将由她们继续延续,持续戕害着更多的和她们一样处于旧社会中弱势地位的女性。曹禺正是通过在作品中塑造恶魔般的封建母亲这一类人物形象,通过对她们可恶、可恨、可憎又可怜的处境和心态的描写,传达着对封建家庭制度及其文化对人性的戕害的反思与批判,进而无情揭露了封建制度压抑人性、荼害民众心灵的真实面目,从而警醒着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广大女性们,在面对封建文化和制度的戕害时,应保持时刻清醒和理智,并予以积极强烈地反抗。
曹禺是带着厌恶和鄙夷的态度去描写他笔下的这一类恶魔般的封建母亲形象的,这一类形象的代表是《原野》中的焦母和《北京人》中的曾思懿。这两个人物均是掌握封建大家庭最高统治权力的“大家长”类型的女性代表,时刻妄想压制着自己的孩子,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变态畸形的母爱,这种“爱”最终也让她们成为了亲手杀害自己孩子的“刽子手”。曹禺对这类典型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母性神话,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曹禺对现实生活中饱受封建思想荼毒而导致自我性格扭曲并且几近变态疯狂的女性形象的极度批判与讽刺。
焦母是以封建恶母的形象在《原野》中出现的。她敏感多疑,恶毒专制。对待儿子焦大星,她有着极强的控制欲,爱儿子爱得极深,但是这种爱,却是一种畸形变态的爱;对待儿媳花金子,她却又怀有偏见,同时内心还十分嫉恨金子,对待儿媳狠毒又残忍[5]。
她常年禁锢着焦大星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始终认为他是自己的私有“物品”,“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儿子无疑成了她施展淫威的对象。而她对儿子过分的爱与独自占有的欲望也渐渐演变成了对儿媳极度的恨,当她日日面对儿子对儿媳的痴迷时,她便不能容忍儿媳对儿子心灵的占有,因而不仅她将儿媳视为自己与儿子“感情”之间最大的仇敌,处处挑拨儿子与儿媳的关系,甚至用巫术毒害儿媳,欲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自私变态的爱,最终成为了悲剧结局的主要推动因素,加速了悲剧的到来。
从焦母这一母亲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过度和专制的爱有时带来的不是脉脉温情,相反在不经意间能变成一把隐形的“利刃”,加剧悲剧发生。反过来亲手毁掉曾经所珍惜爱护的一切,最终自食恶果。
曾思懿,一个从小在传统礼仪道德和封建文化的教化下长大的女人,嫁到曾家后,她步步为营,虽然成为了大家庭的掌权人,但是她过得并不幸福:作为妻子,她始终没有得到文清的爱;作为母亲,对待儿子,她爱的不得其法;作为婆婆,对待儿媳,她十分的刻薄尖酸。
曾思懿始终用一种专制的爱来压迫着曾霆。她的专制和压迫让曾霆与她日渐疏远。对待儿子与袁园的亲近,她始终反感;即使是让儿子曾霆喝参汤时,也始终不忘记摆封建家长的架子,厉声呵斥儿子喝掉……这些种种,一步一步的让儿子丧失掉了对她的亲情和依赖,产生了更多的惧怕,甚至有一种怨恨在里面。瑞贞和曾霆的婚姻,是曾思懿为了保证长房的地位和权力,一手包办的。婚后,她处处要求压制着瑞贞,并坚信婆婆约教儿媳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时刻说教,将其当做自己泄恨的工具,并要求她恪守妇道,“别糊涂,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辈子的靠山。”当瑞贞不听她的话喝安胎药时,她严厉呵斥并且逼迫儿媳喝药……最终瑞贞忍受不了她的专制和压迫,选择离开了曾家。
封建礼教制度扭曲了焦母和曾思懿的性格,但是她们却把这种痛苦持续传递给了同她们一样深受畸形社会文化毒害的弱势者[6]。她们对孩子的爱,是一种畸形变态且虚伪至极的爱,不仅背离了人世间最原始伟大的母爱,更让子女变成了自己自私残暴控制欲下的“牺牲品”。曹禺通过塑造这类封建恶母形象,打破了以往认知上的母性神话,将人世间的母爱由神圣回归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进而无情揭露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与戕害,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
三、敏感的现实体察——对女性现实困境的关注与反抗
曹禺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自小的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现存的社会秩序对女性群体的挤压和迫害,并让他对这些女性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无限的关爱、同情和怜悯。而成年后的曹禺又被强调个性独立、妇女解放的“五四”时代精神强烈地影响着,尤其在接受了奥尼尔等西方剧作家的影响后[7],他在创作中更多地融入了女权主义思想,更多地去关注和表现女性痛苦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并且在对那些受尽身心折磨却依旧难逃悲剧命运的女性抱以同情和悲悯的同时,意在透过她们在现实冲击下破碎的美梦和最终悲惨的命运,强有力地揭露出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畸形变态的现实文化千百年来对人身心的荼毒和戕害[8]。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系中,“女性-母亲”这一系列的形象往往与神圣、柔弱等词挂钩,然而曹禺却将女性作为一个平等独立的社会主体去看待,深刻地去挖掘探索女性的心理、情感世界,塑造了一批不同于传统认知领域中的亦正亦邪的徘徊者形象,打破了自古以来的男权视角下的母性神话认知,更多地去关照女性主体的身心状态、自我意识以及情感体验。不仅对女性在封建旧社会中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地关注,对女性人格、心理和情感进行了细致地体察,并意在通过深层次地挖掘、剖析这一女性群体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再次颠覆传统认知中的母性神话,强烈呼应着新时代、新思想的号召,宣扬了女性生而平等、个性独立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而实现对封建礼教制度无情抹杀和蚕食人性的强烈批判,对封建文化戕害身心、毒害心灵的省察和破解,以及建立新型社会和新型文化的迫切诉求。
曹禺是带着复杂而纠结的态度去塑造他笔下的这一类亦正亦邪的徘徊者的。她们或是曾追求光明但却日渐被社会腐蚀,步步走向沉沦的陈白露,或是爱自己胜过爱一切,为了追求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繁漪,亦或是敢于对抗专制压迫,炽热张扬的花金子,“反叛”无疑是她们身上最大的共通之处。
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中渐渐迷失了自我的陈白露,因为方达生和小翠的出现,她开始有了“生”的希望,开始渴望“日出”,开始激起内心封存已久的母爱。年轻时的陈白露曾和一个诗人结过婚,结合之初的甜蜜让她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然而当他们的孩子死后,诗人抛下了陈白露,一个人追求他的希望去了。遭受孩子的死和爱情的背叛双重打击下的她,选择了沉沦。作品中更多地体现陈白露身上母性的一面还是在她对待小翠的细节里。小翠的出现使陈白露曾经的良知开始复苏,她看到了小翠,就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想保护好小翠,就像是保护曾经鲜活的自己。因而当她看到弱小的小翠被欺负时,便激起了她曾作为母亲的情感,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她对待小翠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并不惜为她奔波,为她对抗黑三和金八。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母爱,让她拼尽全力地爱着、呵护着小翠——不仅认小翠为干女儿,尽全力保护她,而且在她丢失后也不忘寻找她。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当它被激起时,能让污浊变得纯洁,让麻木的心再次滚烫。
作为母亲的繁漪,是曹禺笔下“反母性传奇”人物谱系中的典型,也是他笔下最不像母亲的存在。具有内在反叛精神的繁漪,在作品中一反“鲁侍萍式”慈爱的圣母形象,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执念和私欲,牺牲并且毁掉一切。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母爱冷酷自私的一面,就连曹禺本人也说:“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
繁漪作为《雷雨》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她虽然深爱着儿子周冲,但是儿子却不是她的中心,她至始至终都沉浸在她的自私与幻想里,甚至为了一己私欲,还妄图利用儿子的单纯去成全自己乱伦的情爱,最终却让儿子成为了自己私欲下的“牺牲品”。当儿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阻拦周萍和四凤私奔时,繁漪愤怒地大叫:“你简直是一条死猪!”此时被私欲冲昏了头脑的繁漪在面对周萍出走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一切暴露后,她自身在儿子心中圣母的面具也被无情的撕扯掉,暴露出了她自私丑陋的真面目[9]。丧失理性的她像一个“刽子手”,最终亲手“杀害”了多年来尊重与爱着自己的儿子。儿子的死最终也让她在狂笑声中发了疯,“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但一切却在倏忽间消逝在隆隆的雷雨声中了。而繁漪对继子周萍的“母爱”,却是一种乱伦之爱。周萍的出现,对繁漪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让她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因而繁漪将自己对爱情和生活全部的期许都寄予在了这个“继子”身上。为了得到周萍,她不折手段,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往她想象中的局面发展。她爱周萍,爱的是如此的卑微,因为在多年来的黑暗生活中,周萍是闯入她内心的唯一的一丝光亮,她必须抓住他!所以当她苦求无果,看到周萍和四凤要一起离开周家时,她陷入了绝望之中,疯狂至极的她提前关上了周家的大门,在众人面前无情地揭露了一切,最终,周萍开枪自杀。封建制度压抑着人性,但是母子乱伦却像导火索一样,加速了满载着“恶果”的列车,最终将所有的一切带向了无尽的深渊。
无疑,整日处于周公馆的压抑环境中,自由不得而又爱不得的生活让繁漪日渐疯狂,让她的性格变得自私且阴鹜[10]。因此无论是对待亲生儿子周冲,还是对待继子周萍,繁漪的这种变态自私的爱,都是人性丑陋而扭曲的体现。
《原野》中的花金子,像一朵野玫瑰,娇艳美丽而暗中带刺,泼辣风流而敢爱敢恨。这种炽热张扬又极具反叛力的野性性格,让她成为了曹禺笔下个性最为饱满的典型[11]。她的反叛精神和张扬个性,体现在她与焦母的对抗以及与仇虎的私情之中。面对焦母的侮辱和咒骂,她没有丝毫的怯懦和逆来顺受,而是用尽各种方式进行了反叛。即使当焦母发现了她与仇虎的私情之后,她也勇敢地承认:“我做了!我偷了人!我养了汉!我不愿在你们焦家吃这碗厌气饭,我要找死,你们把我怎么样吧?”[12]她的野性是炽热而张扬的,就像那无边的原野一样,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而她的美丽和野性,却又是带刺的,过度反叛而伤及他人的行为,也加速了最终悲剧的到来。然而作为母亲的花金子,却又透过细节向我们展示着她的的丝丝柔情。这种闪烁着母爱光辉的真情体现在她与小黑子的关系上。虽然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对小黑子却是十分疼爱的,不仅亲手为小黑子做鞋子穿,包括之后面对焦母对小黑子的误杀时,她更多的是不忍和痛惜。
花金子这一性格饱满的女性形象,以她极具张力的性格特点,不仅向我们传达着与封建专制对抗到底的野性精神,还寄托着曹禺对封建专制下女性个性解放思想的宣扬和赞颂。而其作为母亲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柔情,却和其他典型一起,弥补了曹禺对自幼就缺失的母爱的渴望和向往。
无论是折翼的天使陈白露,还是自私疯狂的繁漪,亦或是炽热张扬的花金子,都向我们展示出了这类亦正亦邪的徘徊者,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时,表现出的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感受到自私虚伪的母爱。透过这类形象,曹禺向我们展现出了人性本身的善恶与美丑,即使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母亲,也不例外。而将母亲这类形象解构并回归到现实中后我们可以发现,母亲首先是一个拥有正常人性的欲望和需求并希望被社会、家庭、情感认可和满足的女人,其次才是作为母亲的女人,她们同样需要拥有着七情六欲,需要拥有着完整的人格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曹禺对这类性格真实、个性饱满的典型的成功塑造,对她们身上那种极其强烈地反抗现实压迫精神的抒写,不仅延展了现代文学长廊中对母亲群体形象抒写的维度,使“女性-母亲”这一独立群体更具多样性、立体性和现实独立性,并且强有力地打破了男权认知体系中的“圣母神话”,将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拉下神坛,对她们进行回归现实后重新解构和塑造,将她们更多地作为独立于男权制度体系外的个体去表述,并透过她们无声却又极其强烈地呐喊、大胆地反叛精神以及难以为道德礼教接受的畸形变态的处世方式,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和反思千百年来被异化的丑恶的黑暗社会对女性群体身心的压制、人格的迫害以及权利的践踏,更多地去认识、探寻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需求、人生信仰和社会地位,唤醒人们给予女性群体的内心世界、情感体验以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更多地关注,从而无情地抨击造成她们“恶化”背后的的深层次原因——罪恶的封建社会秩序和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礼教道德,进而呼吁人们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存的畸形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不分性别、人人生而平等、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环境。
四、结语
童年的曹禺缺少对母亲的记忆,是在继母、姐姐等人的照顾下长大的,因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母爱的渴望和探知的心态始终强烈,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在剧作中塑造各类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的原始情感动力。长大后的曹禺,有着极其细致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和浓厚的人道主义热情,他将他内心深藏已久的对母亲的爱渐渐泛化成了对整个社会女性群体的关爱,进而通过强有力地笔触,不仅刻画了一群饱受社会礼教压迫的苦难母亲形象,还刻画了一群被社会异化的封建恶母形象,更在两者的基础上,刻画了一群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母亲形象,共同构成了一幅形象生动且内蕴丰富的女性人物谱系图。曹禺也意在透过作品中这些拥有着悲剧命运的母亲形象,传递着他本人对旧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切同情,对女性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的殷切关爱,对女性拥有自由平等的人格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呼吁,以及对造成这种现象存在的社会秩序和礼教文化的强烈控诉,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