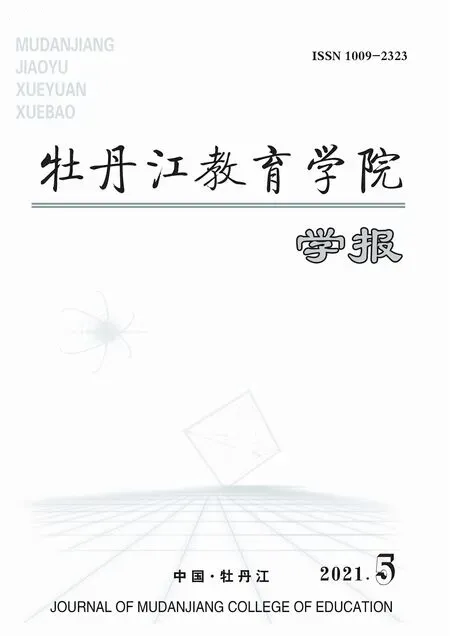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的“亲伦关系裂痕”叙事解读
黄 伟 龙
(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一、引言
亲伦关系是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诸多作品中的重要叙事线索。在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中,亲伦关系裂痕这一显性特征便依稀可见。麦克尤恩早期作品被冠于“震撼文学”,并曾一度引发评论界争议,这与其作品家庭创伤书写中的亲伦裂痕不无关系。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水泥花园》中,作品往往采用非常态人物的叙述视角,以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疏离和男女之间的两性异化为叙事线索,建构了以弑父情结、疾病化叙事方式、人物病态性心理或性行为等为叙述特征的 “亲伦关系裂痕”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勾勒现代工业社会传统家庭道德和价值的坍塌的图景,诉说了亲情创伤下人性迷失和认知错乱,具有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和现代文学特征,不失为创伤叙事现代性的脚注。
家庭人际关系是亲伦关系的本质特征,以亲情为轴心的亲伦关系包含了父母、子女成员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亲伦关系中出现裂痕,意味着父母之间、子女之间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走向负面,处于错乱、敌视或对立状态。亲伦关系是解读麦克尤恩小说亲情创伤的重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尤恩在前期作品中对亲伦关系的描写基本上是负面的、病态的、异化的。首先,无论是小说,还是短篇故事,都充斥着非常态人的叙述视角。非常态人往往是未成年,心智发展和人格塑造处于关键时期,却有失于常态并走向畸形。其次,麦克尤恩笔下刻画了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形象,这些未成年人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游离于伦理道德禁区,在成长过程中难逃厄运。麦克尤恩常常以家庭为着力点,着力考察社会中的诸多变迁和人际冲突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就是有那么点儿观察的癖好,我观察的不外乎两个领域,一是父母怎么跟孩子相处,一是男女怎么相处[1]4。
在麦氏早期作品中,考察麦克尤恩前期作品中的亲伦关系裂痕可从三个维度进行拓展:父母与子女的疏离关系,兄弟姊妹之间的乱伦关系、两性之间的异化关系。可以看出,这些家庭关系都充满着裂痕特征,是人性迷失和认知错乱等个体创伤的起源,对创伤制造和创伤扩散具有促成作用,折射出传统道德价值坍塌下的亲情创伤的负面效应。接下来,笔者从弑父情结、疾病化叙事方式和病态性心理或性行为三个层面来探讨麦克尤恩如何建构亲伦裂痕叙事模式,并阐述这种叙事模式之下的叙事意图和效果。
二、弑父情结
麦克尤恩钟情于描写残缺的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残缺性是以父亲的负面形象或父亲缺场为基础的。它促成了未成年子女成长中的误区和混乱。学者李涯在《从弑父到寻父——论麦克尤恩小说与当代西方文化结构转型》中从父性权威的排斥和解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了“作品的主题从早期到中后期呈现出从‘弑父’到‘寻父’的戏剧性转折”[2]99-104。笔者认为,麦克尤恩前期作品中的父亲具有负面性格或严重缺位,与小说中未成年人的性格异化和个体悲剧不无关联,集中体现了麦克尤恩作品创作中的弑父情结。
在短篇故事《与橱中人的对话》中,父亲在叙述者的人生中严重缺位,母亲与儿子相依为命。母亲宠爱儿子,什么都为他包办,以致儿子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令人意外的是,母亲遇到了自己的情人之后,也就是儿子的后爸,居然绝情地抛弃了儿子,以至于儿子无法正常融入社会。生父的严重缺席,使得儿子的成长危机四伏。更具有讽刺性意义的是,儿子成为亲伦关系中的替代品,凸显了父亲形象残缺的特点——继父的到来给自己带来了厄运。在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主人公罗伯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专制、控制欲很强的人,展现了极权主义的人格特征。罗伯特深受父亲的影响,崇拜男性力量,在今后成人世界的两性关系中扮演了同性恋和施虐者的双重角色。在这部小说中,父亲的残缺性体现在其对子女非理性成长的误导上,这也体现作家作品创作中的弑父情结。
在《水泥花园》中,有着对父亲形象和父亲与子女关系更为细腻、完整的描写,当然这种弑父情结也更为显著。在小说中,叙述者认为父亲形象毫无半点生气。《水泥花园》通过叙述者杰克之眼,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专横、冷漠与严苛的父亲形象:父亲在家庭事务独断专横、与母亲不和、对子女严苛且处处嘲讽。即便是由父亲在场,家庭场景中的亲伦关系也绝非温情和谐,而是具有恶化的趋势。小说中父亲的残缺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父亲脾气乖戾;另一方面,父亲身体具有某种残缺。在小说中,父亲患有的心脏病是父亲最终离场的原因。父亲的离去似乎冥冥注定:父亲与杰克共同修建水泥花园的过程中,杰克借口故意离开,父亲突发疾病而突然晕倒。杰克因为自渎而导致父亲意外身亡,学者称之为弑父行为。弑父这一行为很好地说明了小说对父亲形象的消解,也印证了父亲形象的残缺。与负面父亲形象相反衬是,母亲形象呈现出亲伦关系和缓的修复性特征。明显可见的是,子女更多通过母亲来获取情感依靠,来消解亲情疏离带来的不适。在《水泥花园》中,叙述者杰克回忆道,“我八岁那年,有天早上假装得很厉害,从学校回了家,我母亲就对我宠个没完”,“她知道我其实是趁我父亲和姐姐妹妹不在家的时候跑回来独占她的”[3]25。当然,子女在以父权为秩序的残缺家庭结构中,无法排解认知错乱和人性迷失的苦闷,也从反面证明了家庭亲情荒芜的严重性。亲情荒芜,从杰克对父亲死亡的态度上便知分晓。“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有时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3]3显而易见的是,父子关系已步入决裂。母亲似乎更能了解儿子的一举一动,不仅察觉儿子的自渎行为,而且在临终前叮嘱儿子戒掉手淫行为。对于母亲的劝诫,杰克选择逃避和排斥。“母亲死的时候,在我最强烈的几种情感之下隐藏着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自己都几乎不敢承认...”[3]83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将杰克的人性迷失置于整个残缺的家庭结构之下。正是在父爱的缺失和母亲监管乏力的背景下,杰克个性发展走向畸变,甚至将个性自由凌驾于母亲去世之上。
三、疾病化叙事方式
麦克尤恩擅于利用疾病来预示家庭秩序的瓦解。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对“疾病”的隐喻进行了研究。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 都充斥着意义[4]53。《水泥花园》中,父亲的心脏病预示着强盛一时的父权秩序充满不稳定因素。同时,母亲困囿病床,却连病因都无法为叙述者所知。母亲患病与去世也是一种疾病化书写的方式,显示出父权退却之后母亲在家庭秩序建构上的无力。《赎罪》同样塑造了一个身体孱弱的母亲,因为父权秩序的缺失,只能躺在病床上维持家庭秩序,反而制造了许多人际隔阂。“病床”也可以体现出疾病叙事的特点。床是亲伦裂痕的物理隔阂,床象征着母亲与子女教管责任与教育责任的脱节甚至偏离。在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中,病床现象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时间中的孩子》中,另一次是在《赎罪》中。当父权消失或者父权缺失时,母亲与病床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意味着家庭重大变故的潜在性。纵观《时间中的还子》与《水泥花园》中的母亲形象,都可以看到疾病对母亲的影响延伸到整个亲伦关系当中:母亲因为病情恶化撒手人寰导致家庭秩序崩塌,或者母亲囿于病床导致子女疏于管教、家庭秩序无人操持,都表明了麦克尤恩通过疾病意象书写亲伦裂痕,为后续人物的创伤心理历程埋下伏笔。
疾病化的书写是家庭结构残缺的一面,也隐喻了人物性格的缺陷。在短篇故事集中,疾病化书写融于人物的性格缺陷刻画之中。《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收录的短篇故事《蝴蝶》便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叙述者“我”和母亲一样具有畸变的面貌特征,“下巴和我的脖子互为一体”[5]107。这种残缺的身体所施加地影响极大,蔓延到叙述者“我”的个性发展与社会融入之中。个性孤僻和社会融入障碍是叙述者所面临的问题。正如母亲一样,“我”从未有过任何朋友,且独来独往,“哪怕是独自坐在甲板的椅子上,面朝大海。”[5]107叙述者对死亡的态度是极为冷淡的,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死狗被车碾压,眼珠迸裂,“我”却无动于衷。叙述者“我”甚至逃避母亲离世时的场景,对那些亲戚们也极其厌恶。事实上,叙述者对死亡的认知是病态化的:叙述者罔顾母亲弥留之际,心中无任何悲戚和怜悯可言。叙述者的残缺性从身体延展到社会融入之中。一方面,叙述者因身体缺陷产生自卑心理,因此平时与人交往甚少,但又极度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凝视着自己的身体。我是个长相可疑的人,我知道,因为我没有下巴。”[5]106从这句表述中,可以看出叙述者对社会认可不可得的自卑心理。那也很好解释了叙述者“我”出门前花很长时间穿戴整体却突然厌恶自己的复杂思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戴好。我先把黑色西服烫了一遍,黑色在我看来恰如其分的,然后我挑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因为我不想黑的过头。可是就在差不多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回到楼上把西服、衬衫和领带全都脱了下来,我突然对自己的一番精心准备感到厌恶。”[5]109至此,叙述者对自我的社会融入充满焦虑,具有一种厌世的情绪。
四、人物病态的性心理或性行为
在麦克尤恩前期作品中,作家笔下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对待性的方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未成年在青春期对待困惑和懵懂是通过“乱伦”的成人仪式来消解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而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出现隔阂甚至走向变态的地步。这些性心理或性行为都具有明显的病态特征,是亲伦关系异化扭曲在性主题上的一种拓展。
乱伦主题体现了人物病态的性心理或性行为。乱伦事件在麦克尤恩的前期作品中出现过两次。在《水泥花园》中,兄妹乱伦是对家庭秩序瓦解下未成年子女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收录的短篇故事《家庭制造》中,麦克尤恩书写了叙述者如何在人格异化的雷德蒙的性诱导下,与妹妹发生乱伦的故事。
两性关系的疏离和扭曲体现了人物病态的性心理或性行为。《立体几何》描绘了两性之间的疏离、对抗与变异。丈夫因为不满妻子的性要求,而走上让妻子消失的残忍之路。故事伊始,叙述者“丈夫”的性癖是装着船长“阳具”的玻璃樽与祖父未竟的“性爱理论”。丈夫忽略妻子感情,妻子在一次争吵中失手将玻璃樽摔坏。同样,夫妻间还大打出手,抢夺卫生间。妻子月经周期急用厕所,而丈夫不肯让步,为了保护日记的思路执意躲在卫生间里。在小说中,丈夫对性爱理论的偏执是以牺牲两性和谐关系和牺牲妻子的物理存在为代价的,具有非理性、畸变、病态的特征。同时,在《床笫之间》的《一只豢养猴的沉思》与《临死前的高潮》,叙述者分别讲述了性爱在夫妻两性之间的异化,一个是动物充当叙述者,以动物视角展示了豢养猴对主人的欲望,另一个是叙述者对物的性幻想和性行为,也是病态的性心理或性行为的表现,反映出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错位与异化。
五、结语
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的家庭创伤叙事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麦克尤恩遵循波德莱尔“发掘恶中之美”的美学观,通过病态叙述者之眼理解和描绘家庭创伤现实,蕴藏着作家对人性危机下的生存状况的严肃态度。麦克尤恩通过亲伦裂痕叙事暴露家庭秩序的分崩离析,企图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迫求。因此,麦克尤恩前期作品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和现代文学特征。
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的许多短篇故事以及小说《水泥花园》《只爱陌生人》中,作品以非常态人物叙述为视角,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裂痕和男女之间的两性异化为叙事线索,构建了具有弑父情结、疾病化叙事方式、病态性心理或性行为等为叙事特征的亲伦裂痕叙事方式,书写了亲情创伤下的人性阴暗和危机,勾勒了现代工业社会传统家庭道德和价值的坍塌的图景,不失为创伤叙事现代性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