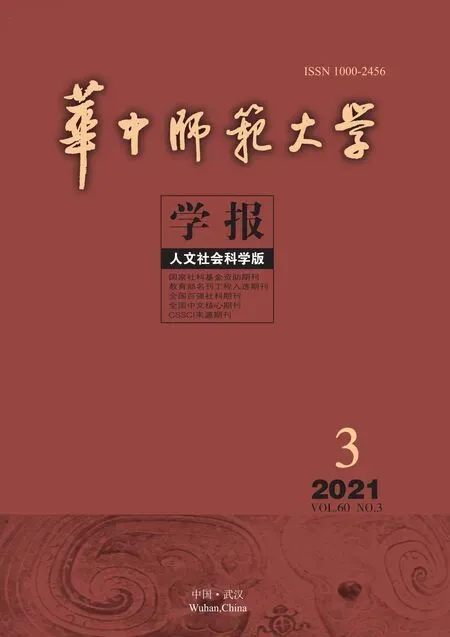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
刘 杰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引言:公共传播的知识危机
近些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传播生态的变迁以及国家与社会多元治理的实际需要,糅合了政治传播、大众传播乃至政府公共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公共传播”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大众传播学旁逸斜出的分支,公共传播尽管日渐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学术谱系,但在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方面依旧众声喧哗,一直没有定论。
实际上,公共传播概念一经诞生,就被赋予了诸多想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知识范式和问题意识上的分化。在最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围绕公众的传播活动都可称为公共传播,探究“公众如何接近和使用媒体以及公共信息的传播和扩散问题”①。之所以会出现分化,则是由于对“公众”的理解出现了差异。此外,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活动“主体”(传者)、“客体”(受者)和“方向”也日渐难以区分,使得公共传播的面目日渐暧昧、模糊。因此,尽管公共传播指向面向公众的、以公共利益为宗旨的传播行为,却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始终处在“任人装扮”的境况中。对于政府来说,公共传播是一种相对于“政治宣传”的政府信息传播活动。政治权力可以用这一概念洗脱“宣传”一词所内涵的操控与说教色彩,用来指称现代政府有组织的、有意识的“新闻管理”策略②。在这个逻辑下,公共传播被视为日益多元分散的实践范畴,公共事件传播、公共政策传播、公共形象、政府公关、舆论管理等都可以被涵盖其中③,或将公共传播视为“公共关系”的新式“化身”,即政治营销、政治广告的同义词。
对学术研究来说,公共传播研究似乎可以网罗若干与大众传播相关的公共议题,将所有非商业性的大众传播议题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公益传播、危机传播等收入彀中,对其做整体主义的考察,亦或是强调一种有别于私人/商业沟通服务的、人人可得的公共服务或信息传播模式,如公共事业广播④、公开演讲等。而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被认为是个体、组织等多元主体在由不同属性媒介构成的开放式传播网络⑤。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通常意义的传播形态相比,公共传播的主体、结构与空间更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⑥。也有学者将公共传播做跨学科的理解,将基层民主协商作为公共传播的载体,从而超越以往传播学以媒体为本位的研究倾向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聚讼纷纭的背后,公共传播的公共性及其对于现实社会的价值性意义往往被遮蔽,公共传播正在遭遇一场知识上的共识危机。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重申公共传播的规范性意义。例如吴飞从迈克尔·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四个分类出发,认为公共传播是区别于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学和政策传播学的一种类型,是回归“芝加哥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尝试,它基于公共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各种社群实践活动,为权利平等、社会公众和民主发展提供介入性和参与性的力量⑧;有学者认为,公共传播虽然在概念上依然漂移疏散,但在脉络主线上却清晰可见,即由公共性理念转向公共实践的一种多元开放的传播场域⑨;在面对社会的“共识困境”时,公共传播可以参与共识生产系统的建构⑩;胡百精则从历史维度梳理了自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以来媒体在化解认同危机、推动多元共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机制作用,认为公共传播是建构协商的重要环节,进一步认为公共传播的诞生基于现代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对话实践,承载了公共治理情境下的意见交换、行动空间与意义网络,可以增进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实验”。
然而,公共传播的知识危机存在双重逻辑,一方面是公共传播的知识基础来源庞杂,在其开展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过程中踞守传播学科,不断与其他学科产生脉络和议题上的冲突与竞合,但在相关社会问题分析的想象力和穿透力上却总是稍逊于其他学科;另一方面则是公共传播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还是公众交往的公共性——因为民间社会的式微而日渐减损,最终遭遇市场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宰制。既有研究或许能够较好地解答第一个维度,而对于第二个维度则着墨不多,引发我们重思公共传播的规范含义、价值立场与学术意义。
于此背景下,理解并重申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就显得颇为紧要。一方面,公共传播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基于公众至上、公共利益、政府与公众间的价值平等、民主社会治理和回归公民参与等准则的大众传播过程。公共传播旨在追求良好的公共生活,实现“共同体的善”这一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公共传播强调通过公开的言说和政治参与以促进协商政治、社会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形成。质言之,公共传播既涵括了政治哲学中关于“公共利益”与“共同体的善”的价值底色,亦具有浓郁的行动者与实践传统。由此,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公共传播在政治哲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与功能,重申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以期丰富对于公共传播的理解。
二、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公众至上、公共利益与表达
在现实生活中,共同体构成了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元,“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在共同体中,一个人自出生就与共同体紧紧相连,与同伴共同分享幸福与悲伤”。在共同体生活中,除了情感纽结之外,共同体生活的维系在根本上围绕利益展开,又由于利益存在个体与集体之分,所以构成共同体生活前提的利益形态即是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勾连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公共利益既可以被理解为现实主义政治中的“社会福祉”、“公共福利”,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共同体内部成员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不确定的个体均可享有的一套价值体系,即“共同体的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而作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城邦,它的追求当然也就是最高、最广的善业”。在亚氏看来,一切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在应然的意义上,都理当秉持“为善”之鹄的,它构成了共同体的规定性特征,是普惠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某种福祉。
“善”既然是共同体的目标,也是成员遵守的价值规范,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德性,那么如何通过“沟通”实现共同体生活中的情感联结、善与正义?或言之,公共传播如何与“共同体的善”接榫呢?在传播理论家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看来,公共性包含了五个方面,分别为作为社会类目的“公众”(public)、作为活动或空间属性的“公共性”(public/ness)、作为人类基本权利的“公开知情”(publicity)、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以及作为意见表达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其中,公众是公共传播的应然主体,公共领域是公众群体性的表达,然而这一“常识”的树立却非坦途,中间历经了复杂的政治社会变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聚集、劳工运动的兴起,大众社会随之降临,但在精英主义看来,大众不过是“乌合之众”,群众政治被污名化为“群氓政治”。在这种群体心理学假设下,公众被想象成暴躁、偏执、夸张、非理性、不负责任的,“他们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大众也容易被种种新闻夹杂着的暗示所驱使,公众之间的观念是涣散不一的,以至于将顽固偏见的大众整合为有机的共同体是一种不可及的幻想。在这一逻辑支配下,脱胎于战争宣传的心理战留下了旨在劝服、说服和控制的知识遗产,并在其后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兴起的背景下,催生出以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为取向的行政学派,传播研究由考察社会关系、共享与社群观念转向了对权力控制和操纵的考察,由关注个体和社会的创造性转向了对受众的分析,以满足客户、赞助人和研究经费提供者的利益需求。因此,“公众”(public)在传播实践中被理解为“受众”(audience),成为大众传播线性模式中的“接收者”,政府和市场都渴望了解“受众”以掌握投票和购买商品的倾向性。由此,公众被降格为被管理、统计和支配的对象而非自我决定的主体。
显然,在这一传播知识史的叙述线索中,大众传播的兴起逐渐悬置了可能的公共立场。实际上,尽管在欧陆群众心理学的阴翳中,大众传播携带着“胁迫术”的标签,但基因里依然含有公共性的要素。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政治的民情与社会基础时指出,报刊可以公开神秘的政治力量,为公民提供参照,维护社群融合,促成统一行动,“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趋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只有利用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这一点也体现在与大众传播兴起于同一时期的杜威哲学中。杜威阐明了传播与共同体的关系,“(传播使得)共同经验的结果被思考、被传递,虽然事件不可能从一个传到另一个,但是意义却可以通过符号的形式而达到共享,欲望和冲动附着在公共意义上,既然它们暗示着公共的、能够相互理解的意义,代表的是新的纽带,并且把共同的活动转化成利益和努力的共同体”。在这一知识线索中,公众在启蒙运动高蹈的人本主义理想被遮蔽之后重新“登基为王”,经由公众的联结扩展个体交往的边界、形塑社群网络,继而开辟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创造公共利益,继而为锻造共同体的幸福提供可能。
前文述及,聚焦于欧陆的传播学知识语境,在现代传播的诞生之处,就包含着公共传播的因子,而公共传播的背后蕴含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追求,公共传播由此被赋予增进公共利益、创造社会福祉的使命。既然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是公共利益,那么如何在公共传播实践中实现并维系公共性?杜威哲学或许提供了答案。他指出,“‘共同的’、‘共同体’和‘交流’这些词不只是在字面上有关联。人们基于共同的事务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而交流则是他们拥有这些共同事务的方式。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在目标、信念、渴望、知识等方面是共同的”。也正是杜威对“交流”重要性的强调,实现了传播文化观/仪式观的发端,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为传播研究注入了“公共性”的基因。雷蒙德·威廉斯甚至将是否具有公共性作为判断传播技术是否具有学术正当性的重要条件,“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它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或者以不完整的共同体为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互不相干”。
如何经由表达实现公共利益?即在公共传播的价值观照下重塑新闻生产与传播主体。新闻是生产和传播与普遍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时事信息的活动或实践,“公共性”因此是新闻正当性的重要尺度。然而,诚如舒德森指出的,新闻包括那些“餐馆评论家的评论、幽默专栏作家的取笑、体育专栏的预测和名人隐私的每个细节,远难达到公共性的程度”。更加吊诡的是,公共领域的重建作为新闻业的根本问题,却逐渐被新闻业本身所削弱,公众逐渐在新闻生产实践中被抛弃。然而,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还是今时今日社交媒体时代的“用户新闻”,无不凸显公众与新闻业的关系在日益发生变革。在当前,社交网络兴起,网民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成积极主动的信息书写者和传播者,“而不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公共传播的主体和场域都被无限放大,也唤起人们将互联网作为公共传播替代性空间的期望,以至于会形成网络公共事件,对政府权威构成削弱,引发政府借由监管权力实施互联网舆论引导等治理手段。
由此,大众传媒和公众致力于形成开放的平台、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言说以实现理性的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尽管出于专业主义与朴素正义感,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若隐若现,但在当前的政府-市场-媒体关系模式下,权力叙事与商业利益占据着媒体,大众传媒有演化成政治化、商业化、娱乐化工具之虞。这一背景下,作为“公器”的大众传媒理应坚守其公共性,视公众为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传播,将自身塑造为自由表达与交换意见的空间,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实践。另一方面,公众需要拥有平等权利去谈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公共事务,通过借助言论的自由流通,反复地言说、沟通和商谈,形成一个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以谋划共同体的福祉。在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中,言说至关重要,她赋予言说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无言的行动不再是行动,而行动者唯有在他同时是一位话语的言说者时,才成为可能,由此区别于制造或创造这些工匠所进行的无需他者在场的活动。她进一步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由人们通过言行(speech and action)表达自我,做自我的彰显(self-disclosuring)”。在这种环境中,参与公共话语的各方都是平等和自主的,言说的前提是借助公共理性与理性平等的交谈,构建一个理想的言谈与协商情境,继而达致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无论是话语还是其使用及运作,都必须公开,公众由此能够充分表达意愿与利益,通过开放、平等理性的交往形成利益群体,继而达致“共同体的善”这一目标。
另需指出的是,对技术的乐观主义并非万能灵药。一方面,“共同体的善”的价值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以个体主义为圭臬的现代性进程,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后,遭遇“个体化”的反噬,法团组织、公共协商以及由此塑造的社会共识难以为继,无怪乎鲍曼哀叹“共同体已经沦落为没有道德责任的、脆弱而短暂的‘美学共同体’”而非道德共同体,制造出一种“差异政治”。另一方面,由传播技术革新所标记的时代变迁也带来诸多隐忧。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垄断、数字分化以及“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所导致的政治极化,更是使得由公共传播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理想趋于黯淡。人们的生活世界被技术所殖民,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行政理性牢牢控制日常生活,把一些道德问题变成了成本-效益问题,导致巨大的社会撕裂。尤其是当下女性主义浪潮、性少数群体权利以及种族关系问题的涌起,更是凸显了旧有“共同体的善”的脆弱性。因此,重拾共同体的理想,是要建立在承认的基础上,从“拒绝承认的差异政治”迈向“平等承认的政治”。换言之,“不仅个体要承认共同体,共同体也要承认个体”,在爱、尊严、责任等价值层面,在法权、契约等制度层面,构建对话、参与式的多元共生、彼此依存的公共秩序。这可能是诊断、理解、走出“共同体的善”当前困境的学术进路。
三、公共传播的实践品格:公共领域、民主商议与行动
尽管“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就现代性社会来说,现代人已不再是僵化、固定、抽象化的存在,而是置身于充满流动性的生存场景之中。正如前文“个体化危机”所表明的,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成员逐渐丧失相应的公共感知和能力,“在承受个体化压力的晚期,个体公民身份的保护性盔甲正逐渐地也是一贯地被剥除掉,而且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一空”。然而,现代政治生活仍需要调和利益冲突与张力,理性的沟通、商谈/协商并展开公共行动依然重要,也就是说,行动、公共领域与民主商议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公共传播在其中不可或缺,也因此具有了浓郁的实践品格。
前文述及阿伦特建构了公共领域的价值性根基,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化并强调了交往媒介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公共领域是以报纸的阅读为中介和以咖啡馆的对话为核心的公共交往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性公共空间。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各种对话构成,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自由地集合和组合,表达和公开它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由此可以判断,公共空间是作为公共领域的物质载体而存在的,哈贝马斯在强调其开放性与平等性之外,亦突出了交往媒介所扮演的关键作用:能够聚合公众、促成议程设置、构建对话平台。正如卡茨所指出的,“公众远非一种身体组合,实际上是一个分散的人群,吸收了传媒的日常议程,然后身体在咖啡馆、沙龙中相聚和组合,并讨论当下事务和形成公众意见”。因此,公共空间中的平等言说、辩论与协商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表达,它同时关涉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学层面的公共参与及行动,同时又由于不同形态的媒介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而也在公共传播领域根植了相应的知识议题。
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了民主协商的重要性,作为使公共舆论充分反映公共意愿的一种手段,协商被认为有确定无疑的功能性效用。要使协商机制充分发挥效用,就应该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协商、讨论和辩论活动,“协商过程的形式是论辩,提出建议的一方和批判地检验建议的一方之间对信息和理由的有序交换。协商是包容的、公共的,原则上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外”。在协商运作过程中,公共对话是核心的要义,通过理性的观点和说服,而不是操纵、强迫和欺骗,使得公众获得更多实质参与机会,缓解精英独断、权威宰制的风险,拓展民主精神与政治平等价值。然而,问题在于,尽管技术进步塑造了一个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日益缺乏公众问题,政治生活图景越来越无法为共同体的内聚性提供足够的养分,人们继而纷纷从公共领域撤退,仅仅关注自己私人化、个体性的事务,例如家庭、职业和个人事业等,导致“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现代个体化社会已无法避免私人事务的增长,公共交往与民主商议何以实现?
公共传播提供了价值性与功能性的生存空间,公共传播的作用在于构建整全的公共协商、商谈的机制和平台,并在其中扮演着议程设置的角色,确保议题进入公共议程,而非被权力或者市场所主导,“健康的公民社会确保社会的交谈基础防止被权力与金钱所殖民,公民社会可以通过公共传播将自身转化为传播力”。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基于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平等参与,而平等参与的前提是对公共议题的知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当保证公众在知情权上的满足,并确保社会沟通渠道的自由通畅,保证议题的普遍关注度,商议实践场域的公开性,商议过程的公平、公正、开放程度,主体间的平等性。只有通过大众媒体对公众知情权的制度性保护,才能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并实现跨地区、跨阶层、跨群体的沟通与对话,继而在不同公众之间展开协商、合作与竞争,从而形成平等、参与的公共精神,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和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恰恰是公共传播在公共言说层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积极公民的行动在塑造公共领域和民主协商的过程中亦至关重要。阿伦特将行动与劳动、工作加以区分,并将其视为除语言之外使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种类的第二个特征,也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具政治性的活动。她指出,“使人成为政治存在者的正是他的行动能力,它使人们能够和同伴聚集在一起,一致行动,追求某些目标和事业”,人们用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行动彰显自己的身份,从而进入群体世界,由此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如果人类没有行动,就很难说是他是“活在人们中间”,也正是行动使一个人离开私人领域走进了公共领域。
加之,业已来临的媒介化社会为个体和公众创造了共同经验的参照体系,而大众自传播模式的出现也增加了行动者的传播自主性和自由度,在传递信息时,不仅会传达温和的希望,也会传达情绪和愤怒,从而促发公民集体行动的形成,也激励更多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阿伦特指出,公共领域“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对政治体的热爱,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因此,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不仅仅通过行动彰显个性,也承担公共责任。进而,一个共同体的公共性,不仅仅涵括了言说的层面,也指向了共同体成员或者说公民在关心某项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诉诸集体行动以捍卫共同体。换言之,积极公民在公共领域中应有的角色认知与扮演,包含了政治性的行动与实践。
那么,公共传播在积极公民的行动层面扮演何种角色?如果依照阿伦特的公共空间与行动理论,积极公民的政治实践则落脚于公民的行动与参与,“公民的政治实践一方面是个人自我彰显的语言,另一方面则是公民相互沟通、结合的联系纽带……政治实践在于公民彼此之间的相互争夺与结合以形成具有政治行动力量的公民结社”。因此,公共传播的角色与功能就在于通过社会动员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公共行动及政治参与。在传统的政治传播框架中,传播技术与体系的功能往往在于提供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从而实现政治说服,而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有赖于公民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协商与行动,因此传播技术与系统应当回归到其天然的规范立场,在捍卫媒体公共性的同时,也为公民自觉、公民参与及行动提供更多的可能方案。换言之,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共传播框架下,(大众)传播并非一个“中立”的“信息服务系统”,而是现代社会共同体通往民主参与的必由之路。在共同体中,公民作为成员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激情、勇气、友谊与能力,也需要意识到共同体的命运取决于每个成员的心智与行为,而公共传播的作用即是赋予公民以传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从而推动社会行动或公民积极主义(civil activism)的形成。
四、结论与讨论
当然,尽管试图厘清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但如果将其放置在中国的现实场域中,却难免存在南橘北枳之嫌。具体来说,传播学自诞生之初就附丽诸多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长期以来的传播学主导知识叙事也将“传播”想象成一种功能主义的角色,用以适配或满足各式各样的组织需求与社会期待,而这一套知识体系与学科预设在舶来中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传播学从概念体系到思维模式都被局限于效率目标与信息概念下,失去了对社会的价值关怀。为了塑造学科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学界积极与政治和商业权力合作,损害了研究的自主性。传播学研究逐渐服膺于“制造共识”或者说劝服(persuasion)这一门古老的技艺,如今也发展成为政府常规职能,公共传播亦复如是。
立足中国的现实语境,对公共传播的理解则更为模糊。一方面,公共传播在中国的概念旅行经历了一定的话语再造,中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语境赋予了公共传播更复杂的内涵,公共传播被窄化为社会治理制度构型中用以凝聚多元社会主体的工具或塑造形象的工具。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治理的领域中,由于冠以“公共”之名,公共传播被理解为“改善组织形象、掌握公众信息”,在近年来兴起的国家与社会治理议题中逐渐演化成为桥接政府、企业等组织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技术——一整套社会治理技术及构型的配件,诸如公共形象及其塑造、公共舆论及其引导、公共关系及其维护等,从而退化成一支潜在的社会规训力量,弱化了公民参与。这种理解进路和处理方式尽管扩展了公共传播的现实范畴和功能,但稀释乃至曲解了公共传播天然具有的反思性气质,也就削弱了传播学在面对公共议题尤其是社会冲突型议题时的敏锐度和想象力。
另一方面,公共传播的价值指引——公共性——也极易在中国的语境下引起论争。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社会关系,过分强调公共领域、公共性或公民行动,容易激发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争论。投射在大众传媒领域,由于特定的媒介管理体制,中国的大众传媒是否具有公共性同样有待商榷。这一点反映在传播学研究上,就形成了一种刻意回避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传媒运作的权力因素等议题取向。现实生活中,过度的商业运作导致大众媒体伦理失范,政治权力控制逐渐强化,网络公共舆论也极易形成极化现象,例如在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种各样的情绪情感互相纠葛缠绕,不同的群体、阶层、区域之间互相撕裂,考验着社会公众与政府在公共性塑造中的价值判断、协商策略和胜任能力,从而不断冲击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和实践品格。
因此,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与传播技术变革的双重语境中,如何重新构建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质?无论是托克维尔笔下的北美十三州,自由结社以及报纸成为美国小镇地方自治与公共生活的源头,抑或罗伯特·帕克笔下的芝加哥,报纸在维系移民群体认同和促进文化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理论资源在理解中国当下的情景时都存在诸多隔膜。按照秦晖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缺乏“小共同体”传统,在个性亦尚未发育之时就进入了“大共同体”本位的一统体制之下。韦伯认为中国人头脑中存在“无法打消的怀疑”、“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和“缺乏同情心”从而导致公共性的难产。费孝通对乡土社会进行分析时亦指出,以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中国公共生活的基本逻辑。在这一语境下,中国当下的公共性议程似乎前景黯淡。然而,我们需看到,传播技术在中国的在地化实践不断对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进行再造,共同体生活逐渐显露出一定的可能性。一方面,在传播技术日渐变革的背景下,借由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的普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由微信群、社区新闻等方式构造线上公共领域,触发了基于社区生活的共同体的回归。另一方面,中国政党政治运作中的“群众路线”理念也重新被嵌入公共生活与社会治理之中,例如借助电视问政、协商民主等公共传播手段重新联结公众、媒体与国家,逐渐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传播图景与公共生活空间。
据此,无论是就理论还是实践而言,重申公共传播被遮蔽的知识叙事与学术谱系非常关键。对公共传播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的澄清与阐释,即是这种努力的尝试。实际上,这种努力也是致力于重申“传播”与“公共”的本义。这里的“公共”不是与私人/个体相对的概念,其在内在规定性上与权力、资本相对照。这里的“传播”也决非仅是一种服膺于大众说服与效果的研究范式,而是强调其公共立场和反身性。诚如丹·席勒提醒我们的,传播研究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只是局限在自己所关切的传媒范畴内,也不能局限于对消费者购物或现代国家如何使用传播进行劝服的研究,而应转向更具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命题,思考传播技术与社会行动、社会运行乃至政治发展的深刻互动。
总之,重申公共传播的价值底色与实践品格,在学术研究层面,旨在找回大众传播中公众至上、公共利益与自由表达的价值,为当前的大众传播研究赋予更多想象空间;在社会实践层面,则在于通过强调公共领域、民主协商和公民行动的意义,为公共领域的言说与政治参与提供诸多可能,给予社会行动中的积极公民以更多的机遇、心智与勇气,从而增进公共利益以实现共同体之善的政治理想。这或许是纾解公共传播知识危机的必由之途。
注释
①James Stappers,“Mass Communication as Public Communicat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33, no.3, 1983, pp.141-145.
②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151页。
③张淑华:《从学术到学科:2015年中国公共传播研究综述》,《新闻大学》2016年第6期。
④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⑤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
⑥⑨冯建华:《公共传播的意涵及语用指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⑧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⑩石永军、龚晶莹:《论公共传播消解“共识困境”的结构性作用》,《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