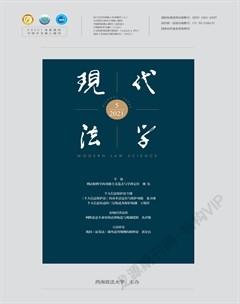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研究

摘 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了特殊法定从宽情节,符合实务界与理论界对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共识,延续了在刑法分则中设立特殊从宽条款的立法模式。其与贪污罪、受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量刑条款形成了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以积极退赃退赔行为获得激励性从宽待遇。它体现了我国重视的被害人损害直接恢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在协调,符合我国刑法体系的内在要求。退赃退赔激励性情节的结构以积极退赃退赔为核心,以提起公诉前为时间要件,在适用时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挽损效果以选择从宽幅度;符合犯罪较轻前提条件的可以适用免刑。贪污罪、受贿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规定更为严格。
关键词:退赃退赔;法定量刑情节;被害恢复;认罪认罚从宽
中图分类号:DF625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 j. issn.1001-2397.2021.05.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分则中增设了两处从宽量刑新条款:一是在《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增设了第3款,即“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在《刑法》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增设了第3款,即“有第一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两处量刑新规属于刑法分则中个别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亮点是特殊退赃退赔情节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在刑法分则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贪污罪、受贿罪也有相似规定,在以往的学理解释和司法适用中已经存在争议。上述条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立法现象,其与刑法总则和其他罪名量刑规定的冲突不容忽视。如何理解和适用该类条文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笔者提倡将上述条文类型化为一种法定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具体而言,依据刑法规定特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免除处罚。这种量刑情节因能更高效地恢复被害与实现刑罚的功能而被赋予更有力的从宽效果。①本文将从对退赃退赔酌定情节法定化的争议出发,评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内容,提炼和论证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概念和根据,对该情节的内部构造和量刑适用进行研究,结合刑法条文从解释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使其与刑法总则、分则的其他法条相协调。
一、对《刑法修正案(十一)》从宽量刑新规的评析
退赃退赔是一个常见的犯罪后酌定量刑情节。退赃是指犯罪嫌疑人将其违法所得的赃款赃物直接退还被害人或者司法机关;退赔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损害范围内对被害人进行赔偿。②在我国的多个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其酌定量刑的地位和幅度。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设置的特殊退赃退赔情节符合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大趋势,适度扩大了量刑从宽的幅度,是一种合理的立法模式。
(一)符合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共识
首先,退赃退赔情节的法定化具有现实基础。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首次将退赃退赔情节作为一个重要的酌定情节加以规定,许多司法解释也强调考察退赃退赔情节。④但退赃退赔的量刑影响仅限于从轻,在实践中效果不佳。特别在经济犯罪中,当犯罪嫌疑人的数额达到“特别巨大的标准”之后,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一般达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犯罪嫌疑人积极地全部退赃退赔,也无法实现刑罚“降等”效果。⑤同时,退赃退赔情节所发挥的作用暧昧不清。囿于酌定量刑情节的性质,退赃退赔情节能否得到采纳、全部退赃退赔与部分退赃退赔是否有所区别、应发挥多大程度量刑作用等均依赖于办案人员的裁量。由此使得犯罪嫌疑人缺乏积极退赃退赔的动力。⑥这导致被害人难以尽早获得退赃退赔,也可能面临终局困境——即使得到有利的刑事判决也得不到补偿。总之,实践已经总结退赃退赔情节作为酌定情节的不利之处为:是否适用无拘束力、减刑效果不强;不能准确反映行为人的预防必要性减轻程度;不利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实务人员提出刑法应当将退赃退赔设定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⑦
其次,理论研究支持对于退赃退赔情节的法定化。一般认为退赃退赔属于事后减少被害人损失的行为,可以减轻行为人的预防刑。①该情节与其他酌定量刑情节的不同是能够对被害人实现最直接有效的挽损。同时,犯罪嫌疑人积极主动退赃退赔是体现预防刑下降的重要情节。一般认为退赃退赔主要影响特殊预防,亦即主要体现了犯罪人的认罪、悔罪的态度。犯罪人的退赃退赔行为是对于自己违背刑法规范态度的反省。并且将犯罪所获利益退回也可以直接减少财产、预防再犯。特别应当注意退赃退赔情节也能发挥重要的一般预防作用。退赃退赔情节实质性地补偿被害人损失,抚平一部分被害人的处罚需求。即便是通过亲属进行退赔,也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②在我国退赃退赔情节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体现。在我国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中它对基准刑的调整幅度甚至高于普通立功、坦白等法定情节③。
再次,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可以实现诸多效果。第一是能约束法官的适用。“应当型”法定情节必须适用;“可以型”法定情节不适用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时,法官应当加以说明。例如,自首属于“可以型”法定情节,一般应依法适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8条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別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法院应在判决书中对认定自首但不从轻处罚说明理由。例如在“杨光毅案”再审判决书中,法院对于原审判决认定自首但是量刑不准确的情况予以改判,对为何自首不从宽进行了详细说明。④因此,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之后成为“可以型”情节,法官对是否具备、能否采纳该情节需要明确说理。量刑直接影响案件判决的效力,这可以促使法官谨慎对待。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中也应当发挥此作用。第二是可以确保其适用效力提升。我国法定量刑情节的一般的从宽幅度是从轻到免除刑罚。如果在实践中根据退赃退赔情节情况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程度的预防必要性,对于情节轻微的案件中积极退赃退赔的可能免除刑罚,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激励作用更显著。
总之,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已成为共识。《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挪用资金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将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符合司法实践和理论的认识。
(二)延续刑法分则量刑情节法定化的模式
《刑法》对于退赃退赔情节的规定已有分则立法先例。《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对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第3款的修改进一步扩大了特殊量刑的规范,“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该条同时影响受贿罪的处罚。由此退赃退赔在个别犯罪中成为了法定量刑情节,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罚。
在认可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方向的基础上,对法定化方式有学者主张总则立法模式。建议《刑法》在第64条犯罪物品的处理增设第2款:“犯罪分子积极退赃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主动全部退赃且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①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中规定的特殊规定延续了分则中立法的模式。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下采取分则量刑情节的立法模式具有合理性。
首先,退赃退赔情节对于不同犯罪的作用差异大,总则立法模式还需研究。一般认为退赃退赔情节对于得利型财产性犯罪能发挥及时挽损的作用,对这些被害人的抚慰较为有效。但是对于人身犯罪、非得利的犯罪则少有退赃退赔的空间,积极赔偿的作用更大。其次,受刑法在量刑从宽体系中保守性的制约。譬如,我国《刑法》第63条减轻处罚中规定了法定减轻和特殊减轻,后者是“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特殊减轻处罚的程序复杂,对于法官欠缺适用的约束力,该条款的适用案例较为稀少。受特殊减刑的内涵辐射,《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规定被理解为只包括法定免刑,不包含酌定免刑。②可见,我国刑法对于减轻、免除刑罚的规定比较保守,重刑的趋势依然明显。再次,受到立法前例的影响。《刑法》对于贪污罪、受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立法已在分则中树立了特殊量刑规范。显然,这对立法者产生约束力,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选择了继续沿用分则立法模式。
在承认《刑法修正案(十一)》采取分则立法模式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還需要进一步深究其内在理论依据。
(三)退赃退赔特殊量刑规范的理论争议
这种退赃退赔特殊量刑规范理论上的实质依据,目前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针对贿赂犯罪的特殊宽宥说。《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继承了我国对贪污犯罪中的特殊量刑规则。③学者认为主要是在打击犯罪时需要对一些贪污罪受赂罪及行贿罪进行宽大化的处理,以更好地瓦解该类隐蔽的犯罪。④这也侧面解释了《刑法修正案(九)》立法同时在行贿罪中规定特殊自首的合理性。①但是,该学说无法解释其他犯罪的类似量刑规则。上述理论亦承认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立法带来了不同犯罪间的“不平衡”问题。②对立法的评价比较负面,认为“违背了刑法公平的原则”③,出现了该规定与其他条款之间的矛盾④。
其二,法益可恢复性学说。该学说认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范评价已经既遂的犯罪,行为人可以通过自主有效的行为消除或者恢复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是法益可恢复性犯罪。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就是典型的法益可恢复性犯罪。⑥这种观点问题在于基本概念模糊——可恢复性所指的法益的“可逆性”。它主张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法益是不可逆的,只有侵害个人财产法益是可逆的。但对于贪污罪的侵害法益则认为是国家公权力不可收买性和职务廉洁性以及国家的财产权,退赃退赔行为对于前一个法益不能恢复,对于国家的财产权可以恢复,总体上可以视为部分法益恢复犯罪。本文认为,该理论依据是被害损失能否恢复,这只是退赃退赔情节可以从轻处罚的原因之一,不足以进一步说明退赃退赔情节为何在某些犯罪中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其三是个人解除刑罚事由说。该学说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是因行为人在事后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已经造成的危害得以消除,刑法规定可以不处罚或者减轻刑罚。该理论的论证理由则比较多元化,其中有奖励说、刑事政策说、刑罚目的说和违法性减轻说等。上述四种理由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学者主张“综合”作为个人解除刑罚事由的基础理论。⑦本文认为,个人解除刑罚事由说主要针对个人所具有特殊情节而不构成犯罪,不是针对退赃退赔量刑情节而言;其所采取的多元理由反映出各国和地区在刑法分则中设置不同类别的解除刑罚条款时差异较大,需要进行更细致地比较研究。
总体来说,对刑法分则退赃退赔特殊规范的理论根据现有学说说理并不充分。
二、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提倡及理论依据
(一)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提出
由上述学术争议可见,对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退赃退赔特殊量刑规范需要新理论进行解读。不再分而治之,而是将《刑法》分则中性质相同的退赃退赔条款进行类型化研究可能获得新进展。同时,我国刑事法律正受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影响,刑法量刑体系也需要对刑事政策、刑诉法的概念及时回应。研究表明在我国的量刑体系中,认罪认罚的“认罚”情节难以找到对应概念。⑧换言之,“认罚”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刑法中的量刑理论可以对其进行衔接。受该观点启发笔者通过类型化研究的方式,将“认罚”的内涵赋予特殊退赃退赔情节,从解释论上尝试理论的创新。
笔者主张将现有分则中的退赃退赔特殊量刑提炼为一种法定情节: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该情节是指:特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免除处罚。“激励性”是指以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悔罪为基础,提供更大幅度的从宽量刑。《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即属于该种规定。该情节也存在于贪污罪、受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之中。
(二)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具有三个理论根据:符合我国重视的被害人权益保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法的量刑体系。
1.该情节是我国为直接恢复被害人损害而设立的特殊量刑情节
从我国刑法来看,为了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赃退赔的行为直接恢复被害人损害,将其规定为激励性从宽情节既符合我国实际需求和法律体系,又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
在大陆法系中传统上犯罪人对于被害人的损害在刑法中作为退赃退赔、民事赔偿的问题在量刑中加以考虑。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被害人权利运动带来了刑法的反思和改革,其启示是:刑法发挥作用依赖于国民的信赖,需要用恢复其损害的方式及时消除被害人对于刑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感。①这种思潮在不同的国家落地开花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方式是将恢复损害作为一种类似刑罚的方法。美国在1982年颁布《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Victim and Witness Protection Act),根据该法联邦地方法院可以在科处刑罚的同时对被告人科处损害恢复命令。损害恢复中首要的是返还财产损失或者支付对价。学者认为这种改革能够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从报应的角度来说,将被告人的不法利益剥夺、直接恢复被害人的利益,原本就是惩罚的应有之义。这能有助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实现,重建国民对于刑法的信赖。消极的一般预防则是使得国民意识到不能通过犯罪获得利益,促使其基于理性的思考遵循刑法规范。对于行为人而言特别预防的效果也是可以期待的。犯罪人通过对被害人的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承担责任,犯罪人从过去的犯罪行为中得以解脱、遵循规范地生活。②
第二种模式是将恢复被害人损害的行为作为激励性从宽的量刑情节。德国将损害恢复纳入刑法,在1994年新增了《刑法》第46条a规定行为人与被害人和解、赔偿损失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学者甚至主张损害恢复应当作为与报应、一般预防、特别预防并列的新的刑罚目的。③但是一般仍然以损害恢复行为对传统刑罚目的的實现来理解刑法的规定。学者罗克辛提出了预防目的的损害恢复论。积极的一般预防是建立在三个作用之上的:对社会而言的学习效果;认识到法得到贯彻的信赖效果;从违法行为被惩罚等中得到的满足效果。④罗克辛认为不能为满足正义感情超过责任刑科处更高刑罚,在实现了满足效果之后低于责任刑的程度量刑则是合理的。损害恢复可以减少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对于大多数来说损害恢复比惩罚更重要。从特别预防来看,行为人自发的损害恢复能够使其体会到正确的意义感,促进其再社会化。损害恢复也可以回避自由刑的弊病。① 这种理论与德国刑法中大量存在以损害恢复行为出罪的规定是协调的。
日本受到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影响,从1970年代开始推动并于1980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付法》。②学者认为,导入美国式的损害赔偿命令有违日本刑法对刑罚的规定,也违背对于刑法与民法的区分。③因此,日本仅仅改变没收与追征的标准以积极实现被害人的权益。2005年《有组织犯罪处罚法》《犯罪被害恢复给付金支付法》均进行了修改,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对有组织犯罪的“犯罪被害财产”实施没收或者追征,由检察官将没收的财产折价以及追征的价款,按照被害人实际的被害额度支付其被害恢复给付金。④这就是第三种模式:由国家主导的特殊恢复被害制度。
对于我国来说同样面临着维护被害人权益的难题,刑法通过追赃挽损制度促进对被害人直接损害的挽回。《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从我国追赃挽损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不佳,原因是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刑民问题交织、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资产处置措施相对缺乏等⑤。并且,追赃挽损的执法中曾出现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甚至是司法不公的问题。⑥学者指出我国刑事的责令退赔与民事诉讼的关系混乱,导致在实践中被害人的利益受损。⑦日本的被害恢复给付金制度与我国现有的追赃挽损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国家主导的恢复被害制度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也消耗巨大的司法资源,只是无奈之举。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国与日本一样对于刑事的退赃退赔与民事赔偿进行严格区分,美国的受害支付命令介于“刑罚与赔偿”之间,其性质难以融入我国法律体系。
总体比较看来,第二种模式中德国将恢复被害人损害的行为作为激励性从宽的情节,这与我国刑法规定在方向和内涵上较为契合。如前所述,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并且较难采纳德国同样的量刑规定,但是分则中设置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本质与其相同。该情节以重视被害人损害恢复为根基,与我国的司法政策中强调“化解社会矛盾”一脉相承。被害人获得刑事判决但利益得不到恢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化解社会矛盾”的实现,损害了刑法的权威性。将积极退赃退赔作为恢复被害人损害的第一选择,高效恢复被害人的物质损害从而实现社会矛盾的缓和与化解。同时,“激励”比“惩罚”更能够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和自新,实现刑罚的目的,减少不必要的刑罚。这也是以激励为导向的模式在三种模式中具有的明显优势。
2.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协调性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印发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认罚”是建立在认罪基础上的一个新概念,其中退赃退赔是最为彻底的认可处罚,也是进一步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前提。因此在实践中退赃退赔被作为典型的“认罚”,在量刑中的地位逐渐强化。①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概念,刑法应当考虑如何用刑法概念转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②显然“认罪”概念与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有所重叠,其是否具有独立量刑情节地位一直存在争议。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十四)……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这表明依据目前司法机关认为“认罪认罚”不具有独立的内涵。
从刑法的角度理解“认罪认罚”,为了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学者提出立法建议。具体可分为总则修改与分则修改的两种进路。修改总则的构思之一是将《刑法》第61条量刑根据和第67条自首、坦白进行修改。③另一种修改总则的构思是把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个全新概念,与原有的量刑情节区分开来,尤其是认罚的内容需要在刑法中加以体现。该观点也承认,除了修改总则之外,我国已经在刑法分则中体现了认罪认罚的内容,例如贪污犯罪。修改分则条文体现认罚从宽也是一种立法进路。④
笔者则认为,从目前刑法分则规定可以看到退赃退赔激励性情节的内涵是“认罚从宽”。换言之,在刑法个别犯罪中“认罚从宽”已经具有了法定依据。首先是退赃退赔激励性情节可以对“认罚”概念进行衔接。“认罚”在刑事诉讼法中指愿意接受处罚。一般认为接受处罚指对具体的刑罚认可,如刑罚种类、刑罚的轻重以及刑罚的执行方式等。⑤《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将退赃退赔作为了认罚的基础。这说明积极的退赃退赔是反映预防刑的降低的重要指标。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积极的退赃退赔是一种实质、切实的认罚。积极的退赃退赔反映出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损失是错误的,并且主动退回犯罪收益、补偿被害人损失,其中体现了“悔罪”,借此重新构建规范意识,这有利于特殊预防。正如上文介绍美国损害恢复命令本身带有刑罚的色彩。从刑罚是对于行为人的恶害而言,我国的追赃挽损是剥夺行为人的不法获益的一种恶害。因此,虽然我国没有将损害恢复作为刑罚,但是追赃挽损对行为人所具有的负面效果与刑罚相似。那么,作为追赃挽损的反面——行为人积极退赃退赔则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认罚,悔罪的程度较高。
需要强调的是,积极退赃退赔是能够落到实处的认罚,对负面评价的认可与执行在较短的时间内主动完成,可以成为预防刑判断的可靠基础。预防刑的判断是面向于未来的预测,是十分困难的。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一审中获得从宽处罚,但又“出尔反尔”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的案件。这表明对于刑罚种类、轻重的认可具有一定反复的可能性。①而积极退赃退赔则是在公诉前完成的自主行为,不停留在“口头”赔礼道歉,更以承受“恶害”来表现悔罪,以此判断特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更为可靠。行为人通过积极退赃退赔行为迈出了主动悔罪赎罪的第一步,借此获得从“泥潭”中走出的正面精神价值也是重新遵循规范的力量。此外,由于得到及时退赃退赔的被害人可能更容易接纳犯罪人,使得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可能性提高。②
积极退赃退赔亦是认罚的核心标志。《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在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表示‘认罚,却暗中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隐匿、转移财产,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见,如果行为人认可量刑、赔礼道歉但是拒不退赃退赔,因没有体现悔罪而难以被认定为“认罚”。
其次,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所强调的积极退赃退赔带来的法律效果是: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种扩大的量刑功能是“从宽”的体现。“从宽”是刑诉法上的概念,所谓的实体从宽在刑法中只能按照现有量刑规则依法从宽。可是,如此理解有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主动认罪认罚获得程序和实体优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现“从宽”没有更大受益时动力不足。没有实体“从宽”,认罪认罚从宽便从一个刑事法整体制度降级为一种速裁程序。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对原酌定量刑情节的突破是,能够将具有悔罪态度的积极退赃退赔的量刑加大“从宽”,体现与一般酌定情节的区分,可以更科学精细地裁量预防刑。这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量刑规定中有所体现。③
再次,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致。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在各种司法规范文件表述中,从最初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发展到“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与“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多元化并存。有的学者认为“公正为本、效率优先”是其价值核心。④有的学者强调“司法效率”的价值。⑤有的学者提出对犯罪人的“实体权利供给”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追求,而司法效率只是其产生的作用之一。⑥笔者认为,“有效惩罚犯罪”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通过对犯罪人从宽的方式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惩治和预防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不同,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特别强调了认罪认罚制度的特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更有利于其教育改造,实现预防再犯罪的刑罚目的”。而刑事速裁程序则是“建立速裁程序有利于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助于简案快审、难案精审,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提高重大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果,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处罚”。①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针对犯罪人的认罚悔罪情节判断其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启动犯罪人的规范意识,以必要的最小刑罚实现惩罚、教育、改造的目的,这就是“有效惩罚犯罪”。此外,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也可以提升司法效率。
3.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符合我国刑法的量刑体系和规范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作为一种独特的量刑规范,与我国刑法关于量刑、减刑和免刑的规定并不冲突。根据《刑法》第61条规定量刑根据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情节”可以解释为既包含构成犯罪的情节主要是影响责任刑的认定,也包含量刑情节主要影响预防刑的认定。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属于影响预防刑的量刑情节。
刑法分则通过特殊规定,将积极的退赃退赔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因此,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也符合《刑法》第63条减轻处罚的规定,属于分则中的“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中涉及法定免除处罚的规定。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退赃退赔特殊量刑情节中“犯罪较轻的”根据情况可以免除处罚,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总则要求。例如,挪用资金罪中规定“犯罪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轻的”与“犯罪情节轻微”都指犯罪的事实不严重。又如,贪污罪中规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中“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指“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再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指符合第37条的“犯罪情节轻微”。换言之,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中并未突破《刑法》第37条的整体规定,不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不能适用免刑条款。
(三)对于可能质疑的再说明
从上文提到的学理争议来看,对于本文提倡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可能存在一些质疑,在此预先进行三点深入说明。
第一,刑法仅在个别犯罪中设置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否带来不平衡。上文提到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最大的质疑正在于此。退赃退赔情节原属于一个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在我国量刑规范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对被害人损害的角度看,在個罪中退赃退赔能够起到“填平”作用的主要是得利犯罪、经济犯罪以及贪污受贿犯罪,而人身犯罪则难有退赃退赔的余地。在得利犯罪、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中选择以经济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的个别罪名加以规定主要是刑事政策的考虑。这种考虑也存在于自首、立功与坦白的立法理由之中。其一是恢复被害人损害的现实需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依托网络的涉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这类案件的被害人数众多、损失数额巨大,追赃挽损十分艰难。在实务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退赔比率不到投资总额的10%,案件的执行结案率极差。①这类案件更需要以激励犯罪人的方式来保障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其二是采取司法主导恢复被害人损害的方式的难易程度。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这类犯罪显示出较明显的组织性特色:犯罪活动复杂,涉案财产被不断隐匿、转移、拆分以及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案财物的认定也存在证据和认识上的争议。②更棘手的是目前侦察、起诉和审判机关围绕追赃挽损没有形成合理的工作机制,甚至导致裁判文书对涉案资产的处置缺乏可执行性。有检察官非常直接地指出:“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各地侦查机关争相立案,分别扣押冻结款物移送至当地法院。但一地法院难以统筹决定全局涉案财物的处理,对涉案财物在裁判文书中只是简单写明‘继续追缴‘返还集资参与人‘责令退赔等,对已经追缴资产的分配方案、继续追缴的措施等提及较少,给后续的案件处理、资产处置埋下隐患。”③这个情况也出现在贪污受贿犯罪之中,在我国打击外逃贪腐分子的行动中追赃出现了特殊问题: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交织以及涉外司法协助困难。与此相比,主动退赃则成为了绕开我国与他国的政治、法律及利益纷争,节约司法资源的最佳选择。④其三是犯罪嫌疑人通过积极退赃退赔反映的可靠悔罪态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嫌疑人通过隐匿、转移、拆分、混同等方式“牢牢”地掌握了赃款赃物。但是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吐出“肥肉”、实施退赃退赔的行为,是一种难度更高的悔罪,足以体现其认罚的态度。外逃贪腐分子主动退赃的行为也同理。从这三个功利性因素来看,贪污罪、受贿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设置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必要性突出,而普通的个人利得犯罪则无。贪污受贿犯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曾被批评为“官官相护”,但下文通过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情节分析发现其规定更为严苛。或许可以转换为在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视野下看待所谓的问题。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条款设立是逐步实现法定化的一步,彻底改变“不平衡”可以逐步推进,通过未来在刑法总则中科学设定退赃退赔情节条文,或者在更多分则中设立类似条款的方式。
第二,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否带来“花钱买刑”的问题。退赃退赔范围是受限的,退赃是退违法所得的赃款赃物,退赔是指在损害范围内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因此,不同案件中具体所指的退赃退赔范围是由犯罪事实来决定的。犯罪嫌疑人的退赃退赔情节是否能适用免刑,可以考察其退赃退赔的程度,但是参考的标尺是相应的赔偿能力。退赃退赔的数额不做“横向比较”,而是“向内参照”。比较而言,刑事和解中所指的赔偿损失是指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数额的高低成为了关键。犯罪人需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才能达成和解。因此容易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而犯罪人为了获得和解以超过能力的方式赔偿的情况。如此看来,退赃退赔的标准避免了“花钱减刑”的问题。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成立不完全依赖于被害人的“情绪”,而是司法人员基于其退赃退赔事实进行的评价,考察其能否积极尽力退赃退赔,因而其结论比较公正。
第三,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与司法解释中的退赃退赔条文是否矛盾。我国的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以退赃退赔为情节轻微、不起诉的规定。例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这些司法解释的特点是以全部退赃退赔及其他条件认定为“情节轻微”从而“不起诉”,属于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规定。有学者认为这种出罪违反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区分,应当将其从出罪事由改为刑罚裁量的事由。①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并重申退赃退赔作为行为人的事后情节只能作为量刑情节影响预防刑。《刑法》规定具有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按照具体情况可以免刑的,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酌定不起诉。这才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处理退赃退赔情节的路径。
三、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构造与适用
目前,贪污罪、受贿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在理解适用中已经出现争议。例如,贪污罪的该从宽情节适用时,法条规定的多个要件是择一即可还是全部符合,如何选择减刑与免刑等。《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从宽情节在今后的适用中也可能出现相似疑惑。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了具体规定:“3.对于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这是对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量刑适用最新规定。为了更好地理解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将其内部构造进行学理剖析,并回应实践的困惑,本文接下来结合具体刑法条文就该情节的构造和适用进行探讨。
(一)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基本构造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具体构造为:A行为要件、B时间要件、C特殊前提与D效果要件,可以细分为ABCD1的减轻免除类型和ABD2的从轻减轻类型。具体分类参见表1。
1.A行为要件是:积极退赃退赔,指由犯罪嫌疑人主导的,据其赔偿能力竭尽所能地将违法所得的赃款赃物退还给被害人、司法机关或者在损害范围内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积极”是对于退赃退赔行为的评价——犯罪嫌疑人具有认罚悔罪的态度。犯罪嫌疑人“主导”是指不配合、服从于由司法机关主导的追赃挽损,而是体现犯罪嫌疑人对成功退赃退赔发挥的重要作用。
退赃的表现有主动将其占有的赃款赃物还给被害人,或者交给司法机关;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因受到强制措施无法进行赃款赃物的退还,只能将赃款赃物的下落主动告诉亲友或司法机关,请其帮助代为退还。退赃在法条中具体规定为: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的公共财物、受贿罪中的贿赂、挪用资金罪中本单位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资金及实物、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的应支付报酬。退赃的本质是将所获赃款赃物向被害人、司法机关返还。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性在于主动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交代赃物赃款的去向,独立或在帮助下改变自己对赃物赃款的支配。在司法实践中全部退赃与部分退赃都被认定为构成积极退赃,这是合理的。因为退赃的比例高低应当与赃物的现实情况相关,在某些案件中部分退赃可能因为赃物赃款已经灭失或不可追回,不应当以此影响退赃的成立。
特殊的情况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罪是行为人具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且有足额履行能力但故意不履行,所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属于赃款。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已经通过转移个人或单位的财产逃避支付义务,在此情况下司法机关很难对“老赖”追赃成功,此时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告知已转移、隐匿的财产去向,主动向劳动者支付全额劳动报酬,是积极退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支付部分劳动报酬不构成积极退赃,因本罪成立是具有足额支付能力恶意不履行,不应当存在无支付能力而构成犯罪进而无法全额退赃的情况。①例如,上海A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检察机关对刘某严肃批评教育,使其认识到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的法定义务,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后果,并向其阐明了对主动缴付欠薪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刘某于11月23日将30万元欠薪交到检察院账户,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于11月26日发还给被欠薪员工。”因此A公司、刘某的行为被认定为符合该罪的特殊量刑规范,被评价为“对于真诚认罪悔罪、知错改正,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危害后果减轻或者消除,被损坏的法律关系修复的,依法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做出了依法不起诉的决定。②
退赔是犯罪嫌疑人退赃不足时赔偿原价值以及其他损害,用自己的合法财产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自愿退赔是一种民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愿为基础。退赔的程度与赔偿范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多寡有关,因此只要在赔偿能力之内尽力赔偿便可以认定为积极退赔。需要注意的是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中没有退赔的规定,法条表述为“积极退赃”“将挪用资金退还”。
对于“积极”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由侦察人员、检察人员在认罪认罚过程中教育引导而推动退赃退赔的,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能够接受退赃退赔、付出努力就属于积极。反之,行为人消极对待、甚至隐匿转移财产则反映了没有认罚悔罪。例如在受贿案中,被告人虽然被检察院认定为具有认罪认罚情节,但在有退赔能力的情况下没有退赃退赔,法院认为被告人不构成“认罚”。③实务中区分全部退赃退赔与部分退赃退赔,一般认为全部退赃退赔对被害人能够更好地挽回损失、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但是不同案件中全部退赃退赔的从轻、减刑、甚至免刑的幅度并非绝对大于部分退赃退赔。退赃退赔的程度是“向内参照”,当部分退赃退赔已经使用了个人的全部财产时,可以认为反映出较高的认罚悔罪态度,评价为“积极退赃退赔”。
在实践中也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在家属、亲友帮助下退赔的,这种情况可以视为犯罪嫌疑人以个人财产进行的赔偿。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的看,犯罪嫌疑人相当于以个人负债的方式退赃退赔,显示其悔罪认罚的态度,在其个人生活中形成防止再犯的私人网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使得公众明白犯罪嫌疑人不能通过犯罪获得任何利益,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积极退赃退赔不是一个情节,只是认定悔罪的一个评价材料。但是退赃退赔本身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即使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退赃退赔不反映悔罪态度,也应当就退赃退赔本身从宽处罚。①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即便行为人是出于功利目的积极退赃退赔的,但是接受财产的负面评价客观上能够预防其再次犯罪。毕竟内心世界是难以完全把握的,悔罪评价应当更重视客观事实造成的影响。退赃退赔情节虽然经常与真诚悔罪联系在一块,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同一层级的关系。
2.B时间要件:提起公诉之前。普通的退赃退赔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在审判中进行也能够成为酌定从轻的情节。但是从理论和实务上看来,提起公诉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
首先,它是刑事程序的重要节点。免刑情节可能成为案件被酌定不起诉的依据,因此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之前进行退赃退赔能够决定案件的走向,一旦被作出不起诉决定则行为性质是“无罪”。公诉前也是不同审判程序的“十字路口”,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就案件情况建议法院采取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其次,退赃退赔不及时会导致被害人损害结果的扩大、难以挽回。提起公诉前退赃退赔情节能节约司法资源,侦察机关不需要就涉案财物、违法所得进行调查、采取措施,检察院、法院也不需要对已经采取措施的违法所得、涉案财物进行审查。再次,与检察院起诉时的量刑建议权紧密相关。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退赃退赔,则该情节可以成为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量刑建议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表现特别突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除法定明显不当情况以外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而在审判中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调整量刑建议。②这说明在公诉前退赃退赔对于量刑获得采纳有决定性作用。最后,在公诉前退赃退赔能够显示犯罪嫌疑人较高的悔罪态度。在侦察和审查起诉阶段,司法工作人员会启发、引导犯罪嫌疑人进行退赃退赔,犯罪嫌疑人应认识到退赃退赔对于被害人损害的恢复作用,在有退赔能力的情况下依然不采取行动,直到案件审判阶段才退赃退赔的显示其悔悟的程度较低。总之,基于上述理由,该时间要件能反映退赃退赔的悔罪程度,也对节约司法资源有重要意义。
3.C特殊前提要件:犯罪轻微。在ABCD1的减轻、免除类型中需要满足“犯罪轻微”条件。该要件限制“免刑”的适用范围,只有在犯罪轻微的案件中才可以通过积极退赃退赔实现免除刑罚。如上文所述,“犯罪轻微”条件与我国《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及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相一致。犯罪轻微指犯罪的严重程度轻微,可以用罪行来衡量。“所谓罪行,是指刑法规定的具有特定构成要件并且配置有相应具体法定刑幅度的行为。”①通说认为在我国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属于轻罪,符合“犯罪轻微”。
以此为标准,采用ABCD1的减轻、免除类型的法条表明“犯罪轻微”是指具体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例如,在第267条之一第3款规定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指的是第一档刑期所对应的“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而非第二档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十一)》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指挪用资金罪的第一档罪行。
4.D效果要件:D1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与D2从轻、减轻处罚。效果是表明符合前述要件后可以采取的量刑幅度。符合“积极退赃退赔”“在提起公诉之前”“犯罪轻微”可以获得D1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效果;符合“积极退赃退赔”“在提起公诉之前”的可以获得D2从轻、减轻处罚的效果。
《刑法》第272条第3款规定挪用资金罪:“有第一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前段为D2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段为D1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76条第3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条仅适用D2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上文所述,该效果要件符合我国刑法对于法定的“可以型”情节的量刑幅度。②
(二)贪污罪、受贿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特殊规定
从内容上看,《刑法》第383条第3款的与其他法条存在明显差异,这需要进一步阐释。本文将其视为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特殊条款,与上述基本构造而言其关键在行为要件更严苛、效果要件更紧缩。
目前,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退赃退赔情节适用,除了“积极退赃”之外是否还需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择一说是多数学说③,少数说是三要件构成说。④
笔者认为择一说不可取,应当理解行为条件有且僅有积极退赃。首先,择一说与我国的其他量刑情节矛盾。择一说中若“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即可适用该特别条款,与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的自首法定情节不相容。对于贪污、受贿罪第一款情节的,其适用效果为从轻、减轻处罚,比犯罪较轻的自首的效果是可以免除更为严苛;对于贪污、受贿罪第二、三款情节的只可以从轻处罚,则比自首的可以减轻处罚更为严苛。这种理解完全不符合该条款为特殊宽宥制度的本意,甚至是特殊“严惩”了。择一说中若“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即可适用该特别条款,与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的坦白法定情节不相容。仅如实供述即可以实现减轻、免除刑罚,远远宽于一般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避免重要后果才可以减轻处罚。原本第67条中的自首比坦白的减免幅度更宽,但择一说的理解却导致属于自首的适用更严苛、属于坦白的适用更宽松,出现明显的结论偏差。如果认为本条与第67条自首与坦白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适用特别法,则可能出现无法解释的罪刑失衡。并且,犯罪嫌疑人既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又符合本条款之时,实务采用择一说将其重复使用,这犯了重复评价量刑情节的错误。①
其次,择一说将非独立量刑情节“真诚悔罪”“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法定化并提升为可以减轻、免除的情节是存在问题的。“真诚悔罪”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而是对行为人情况的综合评价。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更常用的是“悔罪表现”一词。悔罪表现是附着在自首、坦白、认罪、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刑事和解等独立量刑情节上的一个整体评价。悔罪的主观色彩浓厚。②它没有实质的独立内涵,无法单独作为量刑情节适用。③依赖于其他情节之上的真诚悔罪不能独立作为情节考量,否则出现重复评价的问题。反之,如果该理论坚持将一个不依赖于其他量刑情节的真诚悔罪作为一个法定减轻、免除情节,将破坏量刑情节的体系,埋下了随意适用该情节、过宽量刑的隐患。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没有使用“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概念,只在退赃退赔情节中表述为“对于退赃、退赔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这是因为对损害结果的弥补只是退赃退赔行为的结果,可以一定程度反映退赃退赔的情况。在《刑法》第67条第3款中规定“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避免特别严重后果是供述罪行的结果,亦非一个独立的情节。有观点认为“损害结果”非常宽泛,是指赃款赃物之外的直接、间接损失,例如救灾款被贪污造成不能救灾。④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太宽且难以实现完全“避免”,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也有观点认为“损害结果”包括行为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而减轻侦查机关负担、节约司法资源,也包括真诚悔罪而产生的价值及积极退赃后挽回的国家损失。但从实际判决来看,在适用中绝大多数判决未明确要求具备“避免、减少损害结果”要件,该要件被其他要件所包摄的可能性高、难以单独认定。⑤因此,不能认为择一地满足“真诚悔罪”“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就可以适用第383条第3款规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383条第3款表面是四个要件,实际上只有“积极退赃”发挥实际的作用,“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真诚悔罪”是对积极退赃的程度反映、价值评价。因此,三要件构成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由此看来,第383条第3款是本文主张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适例。该条在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基本构造之上,对“积极退赃”所蕴含的悔罪程度要求更高,“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真诚悔罪”为其体现。
用本文观点可以合理解释实务现状。实务虽然认可择一说,但是从判决情况来看三分之一的案件中仅以“积极退赃”而适用之。这说明“退赃”发挥实质作用。在实践中“积极退赃”是适用该条款必不可少的要件,实际判决有的是“退赃”的基础上表现为“真诚悔罪”,或者“退赃”实现了“避免、减少损害结果”。①
从效果上看,第383条第3款后段“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对从宽幅度限制更严,仅仅实现了普通退赃退赔酌定情节的从宽幅度。其从宽较为受限的一个原因是,该类犯罪的法益中包含难以挽回损失的公共法益——职务廉洁性;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对待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犯持更严厉的刑事政策,这从《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终身监禁制度也可得到印证。
总之,笔者认为将《刑法》第383条第3款作为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一种特殊条款,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原意、解释司法实务的做法,并且维持各罪量刑的平衡。
(三)量刑适用的基本问题
1.量刑情节适用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在判断预防刑时会出现两个问题:如何处理可以型情节的选择?多个情节如何适用?
首先,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可以型”量刑情节,代表了立法者的倾向,除特殊情况以外应当得到适用。“可以型”量刑情节介于“应当型”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之间,对于法官的约束力居中。立法通过设立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表明了态度:当符合该情节应当加以适用。这体现在法官采纳“可以型”减轻处罚时,不需要说明理由;当不减轻处罚时需要说明理由。②
犯罪嫌疑人满足条件后应当采纳从轻、减轻还是免刑,本文主张优先考虑免刑,其次才是减轻、从轻。正如上文探讨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具有及时恢复被害人损害、有效惩罚犯罪的优点,量刑的幅度宽大才能更好地激励犯罪嫌疑人。所以,反而是在“可以型”情节适用时选择从轻而不是减刑、免刑需要说明理由。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明确量刑的理由,促进量刑的精细化。同时,在刑法修正的过程中刑罚正不断提高,如果缩小适用减轻、免刑可能进一步加剧重刑化。比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挪用资金罪的法定刑大幅提高,同时规定了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这是立法防止重刑化的平衡之策。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实践中,能够完全退赃退赔的情况极少,犯罪嫌疑人无法全额退赃退赔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只要犯罪嫌疑人在其赔偿能力内尽力退赃退赔,能够挽回重要损失,也应当减轻处罚而不是从轻处罚。
其次,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与其他量刑情节并存时如何处理。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认罪认罚并非独立量刑情节,其内容应当具体化为刑法规定的自首、坦白、立功情节、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等,而后面这些情节彼此独立、可以并用。最新的依据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司法机关认为“认罪认罚”没有独立内涵,而其他独立量刑情节可以叠加适用。举例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供述罪行避免严重后果发生、积极退赃,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量刑建议中就需要注意,构成坦白情节与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均属于法定情节,此时出现了两个减轻情节的并用。但是不可以出现认罪认罚、自首和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三者并用。学理上认为两个可以减轻的量刑情节在实务中最高可以实现下降两个量刑幅度的效果。①
2.在共同犯罪中的适用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疑难问题是对于共同犯罪人的退赃退赔情节的认定。目前对于普通退赃退赔出现了三种标准:独立说,退出自己分得部分为全部退赃退赔;连带说,退出共同犯罪全部违法所得为全部退赃退赔;综合说,不论个别犯罪人的退赃退赔数额,但需全案退赃退赔才认定为全部退赃退赔。②有学者主张“分赃数额说+犯罪总额说”,认为对于共同犯罪人应以本人分赃的数额为准承担退赃责任。但如果每人分得的数额之和少于因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则还要考察共同犯罪的犯罪总数从而给刑事被告人确定一个合理的退赃数额。③
笔者认为,共犯人适用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时,“积极退赃退赔”应采纳独立说。“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责任是指责任刑的连带性,而预防刑是在责任刑确定的程度之内考察个人具有的情节以最终确定个人的刑罚。“连带说”“综合说”以及“分赃数额说+犯罪总额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正确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
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是针对个人的从宽情节,其中共同犯罪人应当以个人获得的赃款赃物及直接造成的损失为总额进行退赃退赔。这种做法更符合退贓退赔情节的性质——在个人的赔偿能力范围内恢复被害人损失,因此不能要求共同犯罪之中的个别犯罪嫌疑人为没有分得的赃物赃款进行退还,也不能要求其超出自己造成损害范围进行赔偿。反过来说,如果要求共同犯罪中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为全部共同犯罪进行退赃退赔才能构成从宽量刑,则实现的可能性极小,犯罪嫌疑人权衡之下甚至可能不愿意在个人所得赃款赃物的范围内进行退赃退赔。表面上看主张“连带性”能最大程度的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但实际则造成被害人损失更难得到及时恢复。
例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犯罪中,个别“金融产品”的销售员被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时就其所获得的“佣金”“抽成”进行退赃、对自己所吸收的金额进行退赔,如果能够全额退赃退赔,当然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应当依法认定为减轻情节。即便其就自己的部分无法全额退赃退赔,但是在其赔偿能力之内尽力退赃退赔的,也符合“积极退赃退赔“的条件,可以适用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依法认定为从轻情节。
四、余论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并实施了《关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从本文研究的视野看该文件的两个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文件认为“认罪认罚”不具有独立的量刑情节地位。这显示出从刑法理论上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还需要加强,尤其是重视与司法实践的对话。该文件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的量刑作用。这有利于进一步精细化地适用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将现行《刑法》中的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规范地适用,才能实现该类条款的最佳效果。在《刑法》未来的修正过程中,对于能够更好实现刑罚效果、对被害人有效恢复的特殊量刑情节可以考虑继续增设为法定情节,并加大其从宽力度,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量刑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A Study of Incentiv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for th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
YANG Ning
(Tianji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The Amendment (XI) to the Criminal Law provides special statutory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for the crimes of misappropriation of funds and illegal absorption of public deposit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onsensus of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on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 of returning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s, and continues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establishing special mitigating provisions in the criminal law sub-clauses. The crime of embezzlement, bribery and refusing to pay labour remuneration an incentiv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for th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 and the incentive mitigating treatment is obtained by the activ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 This is in line with China's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lea system and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The structure of the incentive circumstance of th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s is centered on the positiv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s, with the time element before the filing of the indictment, and the leniency range is selected by examining the repentant attitude of the suspect and the effect of restoration of damages when applying; only those with the prerequisite of a lesser crime can apply the effect of exemption from punishment. In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crimes, the incentiv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for the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 are more strictly regulated.
Key Words: return of illegal gains and compensations; statutory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restoration of victims; leniency in recognition of punishment
本文责任编辑:李晓锋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
收稿日期:2021-07-05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刑法修正的理论模型与制度实践研究”(2016ZDA061)
作者简介:杨宁(1987),女,湖南娄底人,天津大学法学讲师,法学博士。
① 参见韩轶:《刑法更新应坚守谦抑性本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54-55页。
② 本文区分退赔行为与刑事和解中的赔偿以及民事赔偿。退赃退赔主要是对于犯罪行为造成损失的直接恢复和填补。而民事赔偿则是对于其他民事损失的赔偿。
③ 最新的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其中退赃、退赔情节一般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这一点延续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已失效)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的规定。此外,该情节在死刑量刑时还可以发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指出:“对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④ 例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⑤ 参见金懿:《积极退赔退赃应成为诈骗类犯罪减轻处罚情节》,载《检察日报》,2020年10月19日,第003版。
⑥ 参见马涛、吴静:《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退赃退赔行为》,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3页。
⑦ 姜伟:《非法集资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载《检察日报》2020年4月27日,第03版。
① 参见张明楷:《论犯罪后态度对量刑的影响》,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2期,第6页。
②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6页。
③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与2017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对于退赃退赔的规定基本相同。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況,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对于坦白情节,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2)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对于立功情节,综合考虑立功的大小、次数、内容、来源、效果以及罪行轻重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2)重大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④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刑再6号刑事判决书。
① 童德华、陈梅:《刑法中退赃制度的重构——基于海外追赃实践的思考》,载《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10页。
②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7页。
③ 在1979年《刑法》实施之中,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的《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2条规定:“(三)……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1997年《刑法》第383条中规定:“(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④ 参见卢建平、朱贺:《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路径选择及评析——以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款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第4-5页。
①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行贿罪特别规定是指第390条之二:“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被认为是一种特别自首制度。
② 参见卢建平、朱贺:《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路径选择及评析——以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款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第5页。
③ 参见钱叶六:《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载《苏州大学(社科版)》2015年第6期,第99页。
④ 参见赖早兴:《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修正评述——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思考》,载《学习论坛》2015年第4期,第77页。
⑤ 参见庄绪龙:《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第983页。
⑥ 参见庄绪龙:《职务犯罪退赃退赔事后表现对量刑的影响》,载《人民司法》2017年第34期,第33-34页。
⑦ 参见魏汉涛:《“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制度探究》,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第84-85页。
⑧ 参见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38-39页。
① 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152页。
② 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③ Vgl. Dieter R?ssner, Wiedergutmachung statt ?belvergelten, in: Erich Marks/Dieter R?ssner (Hrsg.), T?ter-Opfer-Ausgleich, 1990, S. 7ff.转引[日]本庄武:《刑罰論から見た量刑基準(3·完)》,载《一橋法学》2002年第1卷3号,第737页。
④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
① 参见[日]本庄武:《刑罰論から見た量刑基準(3·完)》,载《一橋法学》2002年第1卷3号,第742-744页。
② 参见[日]濑川晃:《刑事政策における被害者の視点:史的素描と今後の課題》,载《同志社法學》 2000年第52(02)号,第218-227页。
③ 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206页。
④ 参见金光旭:《日本刑法中的不法收益之剥夺以没收、追缴制度为中心》,钱叶六译,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第782-783页。
⑤ 参见吴晓敏:《众型经济犯罪追赃挽损措施实践探讨》,载《做优刑事检察之网络犯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第十六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文集》,2020年11月12日,会议地点:中国江苏镇江,第102-105页。
⑥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此党内法规答记者问时指出,该文件出台背景是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严重的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的问题。参见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03/04/content_2825992.htm,2021年5月1日访问。
⑦ 参见姜瀛:《涉刑财产责令退赔与民事诉讼关系之反思与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149页。
① 姜伟:《非法集资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载《检察日报》2020年4月27日,第03版。
② 参见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175页。
③ 参见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36-37页。
④ 参见孙道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124页。
⑤ 参见石经海、田恬:《何为实体“从宽”: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顶层设计的解读》,载《北方法学》2019年第6期,第39页。
① 朱孝清:《如何對待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反悔》,载《检察日报》 2019年8月28日,第003版。
② 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③ 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中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而普通的酌定量刑情节中的退赃退赔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显然前者的从宽力度更大。
④ 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 2016年第2期,第51页
⑤ 参见张泽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化及其定位回归》,载《法学杂志》 2019年第10期,第1-2页。
⑥ 参见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载《法学研究》 2017年第3期,第163-165页。
① 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① 参见石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司法实践问题之反思——以北京市2013~2019年审结的813件一审案件为样本》,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16期,第5页。
② 参见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涉众型经济犯罪疑难问题研究及预防对策》,载《天津法学》2020年第1期,第107-108页。
③ 吴晓敏:《众型经济犯罪追赃挽损措施实践探讨》,载《做优刑事检察之网络犯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第十六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文集》,2020年11月12日,会议地点:中国江苏镇江,第102页。
④ 参见童德华、陈梅:《刑法中退赃制度的重构——基于海外追赃实践的思考》,载《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2页。
① 参见石聚航:《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及其改进逻辑》,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13-114页。
①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9页。
② 2019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上海A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③ 周庆典、李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确无能力退赃退赔”的理解与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1月12日,第003版。
①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7页。
②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356条规定,被告人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未认罪认罚,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调整量刑建议。
① 郑丽萍:《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第133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的规定中:3.对于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刑法》第176条第3款的规定是:“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仅仅依据该特殊情节并不能适用免除处罚效果。根据本文前述理解,此处的“依法”可能指依据刑法总则中的其他量刑条款,如第37条的具体规定。
③ 参见李冠煜:《贪污罪量刑规范化的中国实践——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的案例分析》,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59页。
④ 参见张旭:《也谈〈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7页。
① 参见李冠煜:《贪污罪量刑规范化的中国实践——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的案例分析》,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63頁。
② 参见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第139-140页。
③ 参见耿磊:《酌定量刑情节规范化路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④ 参见孙本雄:《贪污罪从宽情节的理解与适用》,载《刑法论丛》2017年第2期,第383页。
⑤ 参见欧阳本祺、舒畅:《我国贪污受贿罪中特别宽宥制度的实证研究》,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6期,第78-79页。
① 参见欧阳本祺、舒畅:《我国贪污受贿罪中特别宽宥制度的实证研究》,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78页。
②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页。
①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0页。
② 参见梅传强、欧明艳:《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理研究——以共同犯罪人之间是否负连带责任为焦点》,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9页。
③ 参见姜涛:《我国退赃制度之审视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