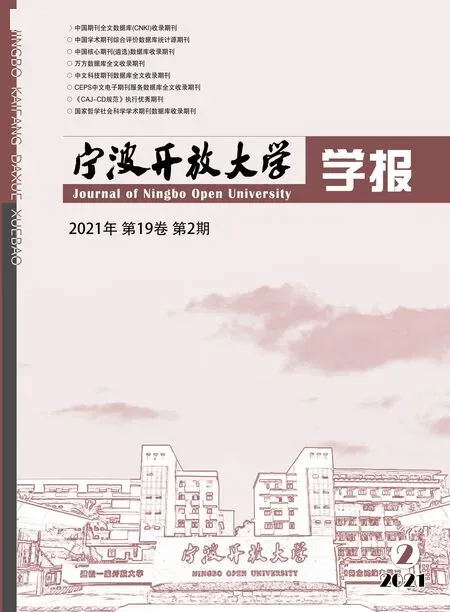从荒谬到深刻
——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鲜血梅花》
谭惠敏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0)
《鲜血梅花》是余华在1989年写的短篇小说,讲述一代宗师阮进武被两名黑道武林高手所杀,妻子立志为丈夫报仇,忍辱负重十五年将儿子阮海阔养育成人后,将“为父报仇”重任交托儿子后自焚。自此,“手无缚鸡之力”“不会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跌跌撞撞的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这篇小说表面上披着武侠小说的外衣,实则内蕴深刻,蕴含着存在主义思想内涵。
先前一直醉心于先锋小说创作的余华,会写这样一篇武侠小说,让人倍感意外。然而这篇《鲜血梅花》与传统的武侠小说大异其趣,传统的武侠小说构建的是中华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表相各异,内涵统一。过往武侠小说传递的多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纵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各不相同,然而体现的都是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如郭靖教导杨过之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1]——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然而《鲜血梅花》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江湖”,实际上写的是“人生”——虚无的人生。《鲜血梅花》以武侠小说做皮囊,骨子里渗透的却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情怀,传统的意象,现代的思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情节结构隐喻“世界是荒谬的”
《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名义上为父报仇,但实际上,无论从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他都不具备为父报仇的条件。主观上,阮海阔根本不知道杀父仇人是谁,母亲让他去找青云道长或白雨潇,获知杀父仇人线索。但问题是,他根本不认识青云道长与白雨潇,也不知道他们去向,更遑论寻找二人;客观上,他“虚弱不堪”“没有半点武艺”,要与杀父仇人——杀掉“一代宗师”阮进武的两名黑道高手比武,并取其生命,绝对是“荒天下之大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即便如此,阮海阔却依然义无反顾,茫茫然踏上他的“复仇之路”:
“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尽管有着百般姿态,然而它们以同样的颜色的树木,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就如同走入了一种回忆。”[2]4
本来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戏剧性的是,正是这样“虚弱不堪”且“不会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这样漫无目的地随意漫游,三年后,不仅意外地找到了青云道长与白雨潇,还阴差阳错地借黑针大侠和胭脂女之手杀了李东和刘天两个杀父仇人,报了杀父之仇。然而阮海阔自己对此却懵然不知,充分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荒诞性”。“世界是荒诞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客观世界是一种自在的、纯粹的、偶然的、无秩序的、不合理的存在,荒诞是世界的本质。萨特在他的代表作《恶心》中,便充分展现了人类世界的荒诞,“荒诞”也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的核心在于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人无法脱离人而遗世独立存在于世界中。人类总是在人生旅程无数的选项当中,自由地作出选择,然而,这一根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与事物,他人与我们自己的关系,这个“选择”导向一个“为我的存在”的世界。因为尘世间,诸如动机与欲望,都只能运作于一个“被选择”的世界之中。正是这样,这个选择本身就是荒诞的,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根本不自由,因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人类的行动与选择,无论怎样都在荒诞之中。换言之,“荒诞”是常态,无论如何选择,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如阮海阔,在没有任何仇人的线索,也不知对方是谁的情况下,竟可以在糊里糊涂,误打误撞地漫游之际,借黑针大侠和胭脂女之手为父报仇,结局本身已荒诞之极。因为按照常理,原本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敌人面前,阮海阔根本不存在任何获胜的可能。然而阮海阔茫无目的的漫游,却可在糊里糊涂之际报得大仇。故事表面上写的是“江湖”,实际上写的是“人生”,漫游之路正如人生之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荒诞”——映射的是人生的“本相”。
二、阮海阔漫游意象隐喻“虚无而孤独的存在”
传统武侠小说有其传统的母题,其内容大都离不开国仇家恨,兄弟反目,江湖传奇,群龙夺宝,武林秘笈等。然而《鲜血梅花》这个复仇故事,不像传统的武侠小说,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江湖传奇,连刀光剑影也是寥寥。有的只是作者余华那散文般,诗化的语言,娓娓道来阮海阔那茫无目的的漫游生涯:
“事实上,在月光照耀下的阮海阔,离开集镇以后并没有踏上昨日的大道,而是被一条河流旁的小路招引了过去,他沿着那条波光闪闪的河流走入了黎明,这才发现自己身在何处,而在此之前,他似乎以为自己一直走在昨日继续下去的大道上。”[2]8-9
由此至终,与其说阮海阔是复仇的主体,不如说,他更像一个“虚无而孤独”的意象。为父报仇,他却不知仇人是谁;想向青云道长与白雨潇打听线索,两人却下落不明。原为主体的孤胆少年英雄阮海阔的复仇故事——经历千山万水,尝尽人情冷暖,当中应有无尽的辛酸经历。然而,余华却没有在这个主题上用力,反而将主体故事不断虚化,一切的一切就像背景,唯独阮海阔那孤独而虚无的背影却异常突出。阮海阔的漫游意象隐喻“虚无而孤独的存在”。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因此无论如何,应该有一种存在(它不可能是‘自在’),它具有一种性质,能使虚无虚无化,能以其存在承担虚无,并以它的生存不断地支撑着虚无,通过这种存在,虚无来到事物中”[3]。阮海阔就像一个“孤独而虚无”的存在,在世间游离浪荡,在虚无中,寻求他生命的意义。萨特认为,人类个体都有行动的自由,人的选择行为并不受目的与动机的制约,个体行动不受任何约束。然而人本身却是孤零零的,因为个体的自由而成为一个孤独者。人们不断选择,不断行动,却像没有任何理由的行动者。小说中,阮海阔就是萨特所说的那孤独“虚无”的象征,在茫茫人海间漫无目的地漫游,在虚无中寻找并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三、漫游故事暗示“悬置”之真谛
这个复仇故事,阮海阔原为报父仇的目的出发,然而,在路上却茫无头绪,不知仇人是谁,不知身在何方;能提供线索的关键人物青云道长与白雨潇却遍寻不获。在漫游近两年后,阮海阔好不容易在渡船上与白雨潇偶遇,却偏偏忘了白雨潇就是他所寻的知晓线索之人,还兀自对白雨潇说找青云道长。阮海阔与白雨潇两人同乘一船,二人一同上岸,甚至走在同一条大道上,最终阮海阔却偏偏眼眼睁睁目送对方离去,与关键人物擦肩而过。真的应了那句俗语“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人生藏着无限的可能,然而相遇无缘之人,即使碰面也未能相认。
事实上,他一路漫游,名为“为父报仇”,然而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首先,阮海阔好不容易遇上白雨潇,本可从白雨潇口中得知仇家去向,那他的复仇旅程就可大大缩短,但他却偏偏对之视而不见,白白错过了这一好机会。
其次,明明为父报仇,然而阮海阔却古道热肠,因为热心帮黑针大侠与胭脂女打探仇家去向,而错过了向青云道长打探杀父仇人的机会(因为青云道长只回答两个问题),耽误了至关重要的“为父报仇”的正事,也因为这样,被迫将漫游继续延长。
然而,正是这样的“随缘任运”的复仇态度,阮海阔却最终终于寻到白雨潇,了解到杀父仇人刘天与李东已被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所杀。仇人被杀,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阮海阔虽非直接手刃仇人,然而正是因为他将李东的行踪透露给黑针大侠,将刘天的行踪透露给胭脂女,无意之中间接导致了两人被杀。亦即是他借黑针大侠和胭脂女之手,替父亲报了大仇。
阮海阔在复仇漫游中的态度与经历,暗示“悬置”的真谛。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悬置”概念:所谓“悬置”,是为了探究真理,暂时停止判断,避免妄下结论。“悬置”概念的提出,源出于笛卡尔的对世界的怀疑精神。胡塞尔认为,“悬置”首先是针对“自然的态度”而言的,放弃一切存在的判断,对存在“存而不论”,对客体的独自性不论,这样通过从“自然的态度”向“哲学的态度”的转变,使人把现实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搁置起来,不予考虑,从而直观“现象”本身即“存在的悬搁”。这样就可以面对事实本身,回到纯粹意识领域,寻获真理,得到“本质的还原”。
阮海阔在这段为父复仇的经历中,正是体现了“悬置”的真谛,名义上是“为父报仇”,但实际上由此至终,他都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一路上茫无头绪,不知杀父仇人是谁,更不知杀父仇人在何方,一路上只是茫无头绪的兜兜转转,像在寻找什么,走过了一个个村庄,一个个集镇。但事实上,他根本无所谓“为了寻找什么”,这趟“复仇之旅”更像是纯意识的驱动,走啊走,走啊走,走啊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营营役役。谁知,正是阮海阔这种既然无法把握世界,不如随缘任运,停止判断,采取“悬置”的态度,跟着感觉走,却让他意外寻到了青云道长与白雨潇,更遇到了两位武林高手黑针大侠与胭脂女,最后更误打误撞,无意之间,借二人之手为父报仇,最终大仇得雪。这个故事,暗示“悬置”之真谛。
四、对死亡态度寓意“向死而生”
阮海阔出身于武林世家,父亲是一代宗师阮进武,凭着一把天下无敌的梅花剑独步武林。这把梅花剑世代相传,是阮家的传家之宝,传至阮正武,已有七十九朵鲜血梅花,父亲阮进武横行江湖二十年,在剑上增添二十朵梅花;阮母书中虽然没有交代其出身,但是作者余华在字里行间透露阮母坚强美丽,想必年轻时也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女侠。
然而,出身在这样武林世家的阮海阔,却“无半点武艺”,身体“虚弱不堪”。然而阮海阔凭着这样的身体条件,却胆敢找杀害父亲的黑道武林高手复仇,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这样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与“送死”没有区别。
在茫茫的复仇漫游中,当阮海阔经过一年又一年徒劳无功的寻找后,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白雨潇,将有机会获悉杀父仇人下落线索之际,作者余华却写到:“接下去他要寻找的将是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也就是说他将去寻找自己如何去死。”[2]18在力量悬殊的敌人面前,阮海阔选择的是“向死而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向终结存在的“向死而生”,即朝着生存之根本不可能的可能性存在前行,只有向死而生才能领会生命之本质,实现向死之自由。阮海阔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与存在主义提出的“向死而生”是吻合的。海德格尔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先行决断”,即预先了解到人生的前方即是死亡,并予以接受。而阮海阔在漫游中的态度正如海德格尔对待死亡的态度,人便是一个迈向死亡的存在,踏上无可取代的固有人生。明知死亡不可改变,何不从容面对?
假如没有命运的安排,假如没有黑针大侠和胭脂女的先出手,阮海阔这次复仇,绝对是失败告终,必死无疑,但是他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执意走上这条“求死之路”,正是隐含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寓意。
五、结语
余华这篇短篇小说只有寥寥八千字,然而寓意深刻,短小精悍,言近旨远。正如余华在自序中所说:“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2]2《鲜血梅花》明里写的是“江湖”,暗里隐喻的是“人生”。余华借这本短篇小说,抒发他对人生的感悟。阮海阔的漫游复仇之路,寓意的是人生的荒诞旅程,从荒诞到深刻,人类就如阮海阔一样,在兜兜转转间,营营役役中,存在着,迷惘着,前行着,摸索着——探求人生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