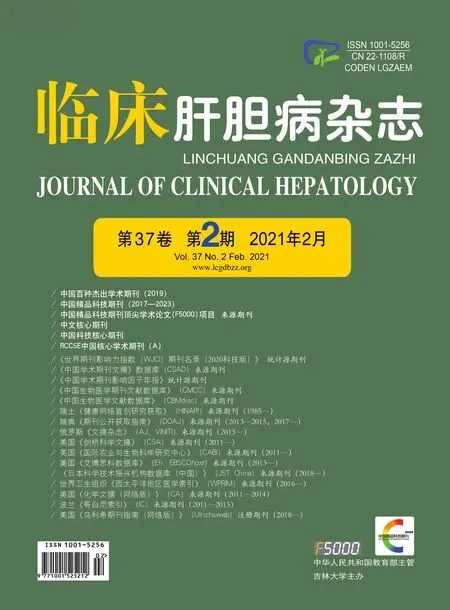移植肿瘤学开创肝移植治疗肝癌新时代
韩承祚, 卫 强, 徐 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杭州 310006
1 溯源
随着外科技术日益精进和围手术期管理日臻成熟,器官移植发展势如破竹,已成为治疗终末期器官疾病及脏器衰竭的有效手段。在全球众多规模较大的移植中心,器官移植已成为外科常规治疗方法。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的不断强化,使移植学与肿瘤学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在此背景下,一个全新的亚学科——移植肿瘤学应运而生。21世纪初,美国DermatologicSurgery杂志推出“移植肿瘤学的挑战与机遇”专刊,集中论述移植术后新发皮肤肿瘤的防治。2014年,“肝移植肿瘤学”这一概念首先由日本熊本大学肝移植专家日比泰造教授提出。当前,移植肿瘤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外科手术学范畴,它是外科学、肿瘤学、免疫学、器官保存、免疫抑制药物学、影像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与促进而形成的综合学科,它以免疫抑制状态下全部移植受者为关注对象,以移植医疗中的所有肿瘤学问题为学科疆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移植肿瘤学开创了肝移植治疗恶性肿瘤的新时代,将助力临床医师更好地实现肝癌精准治疗。
2 多学科交叉融合催生肝脏移植肿瘤学
肝脏移植肿瘤学的发展汇聚多学科力量,包括肝胆胰外科、肿瘤内科、消化内科和麻醉科等临床学科,以及放射肿瘤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临床辅助学科。多年前,对肝移植的探索性实践,催生肝脏移植肿瘤学兴起;而近年肝移植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则是移植肿瘤学发展的生动写照。通过深入了解移植肿瘤学时代肝癌的治疗,可窥知整个移植肿瘤学领域的发展态势。肝细胞癌在我国占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位[1]。近年来,肝移植逐渐成为肝癌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我国每年肝癌肝移植例数占肝移植总例数的30%~40%,而供肝短缺和术后肿瘤复发是当前制约肝癌肝移植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移植学界亟待解决的的主要难题。
3 肝脏移植肿瘤学-肝癌精准诊治全新探索
3.1 实现肝癌肝移植受者合理精准选择 如何合理选择受者是肝癌肝移植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2-3]表明,肿瘤形态学只是影响肝癌肝移植预后的众多因素之一,因此,各移植中心不断探索并拓展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并逐渐突破肿瘤形态学束缚[4-9],以米兰标准为代表的经典标准和以杭州标准等为典范的新型标准,极大地改善了肝癌肝移植受者的预后[10]。肝癌肝移植标准的变迁,从最初的基于肿瘤大小和个数的形态学标准,到引入肿瘤病理学特征和分子标志物对选择标准进行拓展,正是外科学、影像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多学科不断交叉融合的生动体现。而作为精准医疗时代极具发展前景的无创检测手段之一,液体活检在器官移植领域的作用正逐渐被发掘。液体活检是人类体液中几乎所有分子都能被其“捕获”并进行多组学检测与生物信息学分析,进而用于指导临床诊疗。联合运用液体活检与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血清中肿瘤标志物、炎症因子和代谢分子等检测结果用于建立肝癌分子分型,并与现有的肝癌肝移植标准相结合,能显著提高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效能,优化受者选择[11]。
3.2 扩大肝癌患者受益人群 因供肝短缺等原因,选择低复发风险的肝癌患者接受肝移植治疗已是国际共识。近年来,以介入、放射治疗(放疗)、化学药物治疗(化疗)等为代表的肿瘤治疗方法的飞速发展,使得部分超出适应证标准的肝癌患者能通过降期治疗降低肝癌分期而被重新纳入肝移植等待名单。降期治疗方法主要有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等[12]。符合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期间也存在肿瘤进展风险,而桥接或过渡治疗则是等待肝移植期间通过TACE或RFA等治疗控制肿瘤进展。介入等桥接治疗引起的肿瘤完全病理缓解(complete pathological response,CPR)被认为是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及患者预后的有效预测因素[13]。但反复多次的局部治疗也有诸多弊端,如肝功能损害、肿瘤生物学行为改变、肝动脉损伤等。因此,优化治疗方案并尽可能取得CPR是肝移植前肝癌桥接治疗的目标之一。免疫检查点阻断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是近年来治疗晚期肝癌的突破性进展。但ICI应用于器官移植受者有诱发致死性急性排斥反应的风险[14]。美国范德堡大学报道首例肝癌肝移植前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单抗导致移植后致死性免疫性损伤的病例[15]。因此,拟行肝移植治疗的肝癌患者在接受PD-1单抗治疗时需慎重。目前,国内学者正开展肝癌肝移植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相关临床试验。
3.3 促进肝癌外科治疗理念及方式变迁 肝脏外科手术技巧、手术器械、超声和影像等技术不断前进,同时也带来了肝癌外科术前评估、治疗理念和技术细节的不断变革与更新。依托于日益完善的术前评估体系,肝脏外科医生能清楚定位肿瘤、明确肿瘤毗邻关系,使得以荷瘤肝段及回流区域切除的实施成为可能。手术区域则深入到肝门部和尾状叶等以往的“手术禁区”,以肝段、亚肝段切除术为特征的精准肝切除逐渐深入人心,既达到了解剖性肝切除的目的,又保留更多的肝实质,有效提高了治疗效果和肝癌可切除率[16]。而“挽救性肝癌肝移植”、“序贯性肝癌肝移植”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既缓解了临床供肝短缺的压力,也体现了肝癌的外科治疗理念更趋灵活,肝切除术后复发肿瘤根治由“被动肝移植”向“主动肝移植”迈进。将复杂的肝切除技术、器官低温灌注保存技术、静脉转流技术及肝移植管道吻合等技术融合应用于肝移植而出现的“自体肝移植”,不仅降低了部分复杂肝切除的风险,还使在体无法手术的肝癌患者重获手术机会。
3.4 移植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监测日趋精准 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仍是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尽管根据肝移植标准精准选择受者,但术后肝癌5年复发率仍高达30%[17]。如何建立有效的肿瘤复发转移监测体系,以期“早发现”并“早干预”是移植学界的研究热点。术后规律的随访,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结合影像学检查,将有助于早期发现肿瘤复发及转移。鉴于肝癌生物学特性复杂,除了AFP这一预测术后肿瘤复发的经典指标外,需要更敏感的分子生物学指标和更有效的手段来对受者术后复发进行检测。精准医学及高通量生物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则推动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前进,近年来涌现了维生素K缺乏诱导蛋白原或拮抗剂Ⅱ(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炎症相关生物学标志物、AFP异质体和循环肿瘤细胞等。此外,考虑到移植受者术后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环境,通过术后监测机体免疫功能,及时调整免疫抑制强度来达到降低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目的,目前常用于监测患者免疫功能的指标包括淋巴细胞亚群(B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水平、CD4/CD8比值)、CD4+T淋巴细胞活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活性、IL-2等细胞因子水平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等[18-19]。
3.5 拓展供肝来源,缓解供肝短缺 为解决供肝短缺问题,除开展活体肝移植及劈离式肝移植外,提高扩大标准供肝的利用率,是扩大供肝来源的重要途径。扩大标准的供体主要包括:年龄>60岁;供肝大泡性脂肪变>30%;供体在重症监护病房所待时间>7 d。血流动力学的危险因素包括:长期的低血压,应用多巴胺超过6 h以维持血压;或需要2种缩血管药物维持血压达6 h以上;冷缺血时间>12 h;主动脉阻断前高钠血症。此外,ABO血型不相容以及血清病毒学阳性、患有肝外恶性疾病、活动性的细菌感染和高风险生活方式等供体也属于此类范畴。笔者研究团队[20]通过建立ABO血型不合肝移植精准治疗肝癌新方案,使更多符合杭州标准肝癌患者能通过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显著获益,获益人群较全国平均水平提高近3倍,安全有效拓展供肝来源,有效缓解了供肝短缺。扩大标准供肝在扩大供肝来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等各类并发症的发生率。机械灌注作为新一代器官保存技术,克服了传统静态冷保存技术的许多缺点。其中,常温机械灌注技术在修复扩大标准供肝、评估供肝质量、体外干预治疗等方面展现出了不凡的优势,为移植工作从“被动”转为“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器官来源不足的根源在于供者数量不足,这是由当下供者-受者分离的器官移植模式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是同种异体移植免疫排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当下器官移植模式的局限之一。而常温机械灌注技术的到来将引发器官移植模式的新变革,即结合人工肝支持系统和新型治疗方式等,使得受者器官体外修复并自体移植成为可能。供器官保存方法的不断改进与创新,是外科学、基础医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乃至材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结果。正是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相互交叉结合以及供器官保存技术的逐渐成熟,催生了肝移植领域供器官保存理论及技术方面的突破。
3.6 肝移植治疗不同类型肝脏肿瘤 移植肿瘤学涉及的疾病多样,各类型移植技术与各类别器官移植,均在探索治疗各脏器难治性肿瘤疾病。从疾病种类来看,包括肝脏良恶性肿瘤、结直肠癌肝转移、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等。从患者年龄来看,随着成人肝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儿童肝移植正在国内各大肝移植中心逐渐兴起。经过不断探索研究,目前肝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近90%,3年生存率近80%。儿童肝移植术后存活率较成人更为理想。
肝脏是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器官。一直以来,局部切除是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唯一治疗方法,但只有30%~40%的患者在出现疾病时符合切除标准[21]。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无法行肝部分切除的主要原因是残肝容量不足。故对于残肝不足且无肝外受累的患者,肝移植正在成为一种选择[22]。一项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研究[23]显示,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肝移植的5年预期生存率达60%。目前,多项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建立客观、准确的遴选标准与评价体系和标准化的化疗方案将有助于提高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肝移植的疗效。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类起源于肽能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能够产生生物活性胺和/或多肽激素的异质性肿瘤。肝转移在源于小肠和胰腺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中很常见[24]。手术切除是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的最佳治疗,但肝转移灶常累及多个肝叶,且多发,因此,肝移植成为潜在的候选治疗方法[25]。Mazzaferro等[26]制定了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患者行肝移植的适应证标准:(1)世界卫生组织肿瘤分类标准的G1/G2分级;(2)原发性肿瘤由门静脉系统引流;(3)肝脏受累<50%;(4)完全切除原发性肿瘤;(5)疾病稳定或肝外疾病治疗至少6个月有效;(6)年龄<60岁(相对标准)。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术后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97%和89%。肝母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肝脏肿瘤,其发病率在过去20年中持续上升。肝母细胞瘤综合治疗效果良好,手术切除联合化疗是主要治疗方法[27-29],5年累积存活率高达80%。化疗后评估为POST-TEXT Ⅳ期或POST-TEXT Ⅲ期伴有肝静脉或下腔静脉等重要血管受累,无法进行手术的病例可考虑行肝移植[30]。总之,手术切除是低危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高危肿瘤患者或需要复杂肝脏手术或移植的患者应及早转诊到专科中心。
4 移植肿瘤学的未来
虽然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了移植肿瘤学不断发展,但肝移植治疗肝癌尚有很多难点亟待解决,肿瘤复发的防治及进一步机制的探索等仍是未来长期努力的方向。恶性肿瘤作为复杂的系统性疾病,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层面上均可发生异常并密切关联,单组学研究不足以阐明肿瘤复杂的发病机制。大数据时代,肿瘤多组学研究方兴未艾,新型多组学技术必将在移植肿瘤学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多组学与器官移植深度融合、多组学整合分析结合人工智能研究,有望更准确地揭示肿瘤分子特征,克服肿瘤异质性,为肿瘤的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依据,并逐渐成为供受者筛查诊断、预后评估和疗效评判的重要科学方法。此外,免疫治疗突飞猛进,也将使处于肿瘤免疫与移植免疫交叉点的器官移植从中受益,最终整体提高肝癌肝移植的疗效,造福更多的患者。
作者贡献声明:韩承祚负责文献检索和撰写论文;卫强负责撰写及修改论文;徐骁负责拟定写作思路、指导撰写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