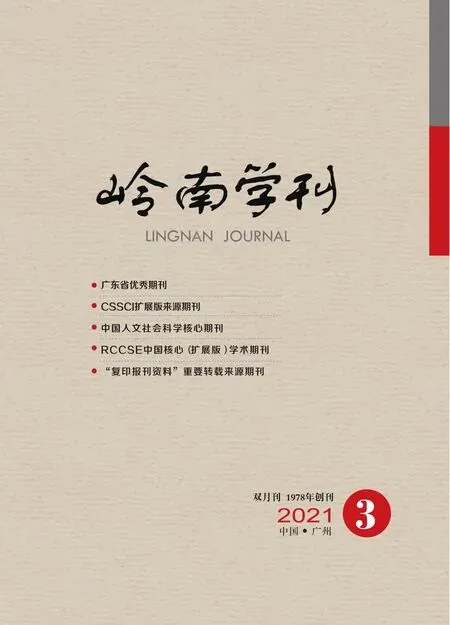“另一只无形之手”:价值观规律及其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
贾彦峰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016年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民心政治”(或人心政治)遂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学者们从思想来源、文化渊源、实践基础[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诸多方面探究了民心政治的相关问题。然而,民心政治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在当下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呈现出什么新的特点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系列核心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厘清。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重要的关联概念——价值规律和价值观规律。
一、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渊源及其误读
毋庸置疑,“看不见的手”(或无形之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隐喻,它既自有其修辞学上的合理性,也体现出亚当·斯密深邃的洞察力,因此,它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生动形象表述为人所熟知。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并未将其当作核心概念加以详细阐释。追根溯源、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斯密曾三次提到“看不见的手”,此外再也没有多加论析。第一次出现是在《天文学史》手稿中:“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所有多神教社会,或者野蛮人当中,就像蛮族人的早期一样,对于大自然无规律事件的解释只能归于某个他们的上主的权力或者是上主的代理人角色所致。烈火燃烧,地水涌出;重物下落,轻物上扬,都是他们自身属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些现象中特意施法的结果。”[2]49这里“看不见的手”被用来喻指“众神之王朱庇特”的力量;第二次出现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无论何时,土地提供的食物大体能养活所有的居民,阔人只是从大量的产品中挑中了最难得、最心爱的一部分,虽说他们都是些只顾自己、自私自利的家伙,雇佣千百人为自己劳作的动机无非是满足自己那点无厌而又无聊的私欲,但他们还是跟穷汉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改良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对生活用品进行分配,而且几乎与所有居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样。这样,就无形地推进了社会的总体利益,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生活保障。”[3]130此处“看不见的手”则被用来形容富人虽然自私、贪婪,但他们雇佣穷人从事生产,客观上增加了生活资料供给;第三次出现在《国富论》中:“他通常既不打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正在什么程度上增进公共利益。……他只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就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达成一个完全不是他本意的目的。也不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就总是对社会有害。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比在实际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4]30而这里“看不见的手”则完整表达了经济活动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思想。
从原著的系统解读中可以发现,斯密从来没有把政治学和经济学机械性地分割开来,也反对将经济活动从政治、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中分割出来,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在斯密看来,没有纯粹的政治政府,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市场。这在斯密置身的时代以及其后数十年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但是,19—20世纪经济学变得狭隘化,选择性地借鉴了斯密的理论,使得看不见的手“所指”变得极其单一。经济学家们专业的自信及其局限性之间形成了较大反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世界观的核心特征——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5]185总之,在斯密那里,“看不见的手”的涵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同时涉及到神学领域、道德领域和经济领域。然而,后人在论及“看不见的手”这个命题时,不约而同地将其指代“价值规律”,并把它当成了描述市场经济规律的专有名词。这种误读显然并不符合斯密的本意,而有意无意地曲解也极大框定和限制了“无形之手”的适用范畴。
二、价值观规律与价值规律的联系和区别
(一)价值规律和价值观规律的联系
单从字面意义来看,价值观规律似乎只是对价值规律的简单比附和概念移植。可能有人质疑,所谓的价值观规律会不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妄推想呢?情况并非如此,二律虽然只一字之差,却绝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价值规律是经济领域“看不见的手”,而价值观规律是思想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也即是说,二者的“所指”虽然不同,但“能指”相同。价值观规律是价值规律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投影,二者形似表里,实则为一。
(二)价值规律和价值观规律的区别
1.价值观规律的概念不同。如上所述,所谓价值规律,指的是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市场供需和资源配置。而所谓价值观规律,是指人们的价值观也总是围绕着核心价值观分化统合、自然排序,其结果决定着人心向背,调节着意识形态变化。它主要内含着价值观分合规律和价值观排序规律。
2.适用领域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后人探讨“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时,主要偏重于“经济基础”领域,而在思想政治等“上层建筑”内未能有所拓展。“无形之手”是一个长期被理所当然地视作经济学领域的隐喻性概念,但随着国情世情的发展变化,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可能继续向新的应用领域拓展。如果说“价值规律”是经济领域的一只“无形之手”,“价值观规律”则是思想政治领域的另一只“无形之手”。
3.遵循逻辑不同。思想政治建设资源,特别是意识形态维稳资源,并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而是另有一套独立的运行逻辑,即哪里价值观分化程度较烈、人心涣散,治理资源就会投向哪里,也即是说受价值观规律的调控和支配。价值规律和价值观规律两者所遵循的逻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一个是资本逻辑,而另一个则是人本逻辑。
4.出场时机不同。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幕,全国上下更看重经济运行规律的探索,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被顺理成章地从斯密的书本里拿到现实中调节市场经济运行。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多样多变,核心价值观统摄性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也已置于议事日程的前列,对于价值观规律的了解、掌握和运用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起来。
5.实践指向不同。“价值规律”指向人民的“实际问题”,“价值观规律”指向人民的“思想问题”。虽然在价值规律中,增进社会利益往往并不是人们出于公利的主观结果,而是自利形成的“副产品”,但如果跳出单一的经济范畴局限而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审视问题就会发现,从“经济治国”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从“思想立国”的角度思考问题则可以进一步把握住国家治理的精神维度。“二律”协同则为解决民心政治孜孜以求的目标——既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又解决人民的“思想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完整闭环。
三、价值观规律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
(一)价值观统合分化规律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
1.价值观的统合规律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机制
(1)共识升华机制。乔治·洛奇说,把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正是民心政治,没有民心政治就没有社会。其实,在价值观与民心政治之间还有一个联系环节——凝聚共识并加以升华。因为,当人们说到价值观时,大多指向的是个体层面,因此说价值观的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而说到民心政治时主要指向的是国家层面,因此民心政治的主体是国家。要把不同理念凝聚为正向的、核心的价值观继而达成共识并升华为整个国家的民心政治,共识升华机制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只有经过这个中间环节,分散的、易变的个人价值观向团结的、稳定的国家民心政治的转变才能完成,从“原子化个体”凝聚成“命运共同体”的转变才能最终实现。
(2)耦合驱动机制。“耦合”源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和紧密联系的现象。如果存在两个具有相近相通,又相差相异的系统,它们不仅有静态的相似性,也有动态的互动性,我们就说二者具有耦合关系。价值观体系与民心政治体系完全符合上述特征。经过价值观统合规律起作用后,二者产生了耦合效应,释放出更大的驱动力;价值观体系又属于民心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这种驱动力是从民心政治的核心部位产生的自驱力,相比外部的推力或者拉力都更加强大。
2.价值观的分化规律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机制
(1)异质监督机制。价值观分化的异质性主要指不同于信访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体制内安排,而是不同价值观持有者所表现出来的或不轻信于权威、或不盲从于官方、或不随波于主流的性质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极似蚌体内的沙砾,虽然让蚌体不太舒适,却最终因为应激作用而在体(制)内孕育出光彩夺目的珍珠。从这个意义上说,异质性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质。实践证明,西方的所谓“吹哨人”制度并不完美,现有设计还不能保证哨声响起一定就被听见并立即做出反应。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群则由于分散在不同的方位而形成“回音壁”效应,因此,在“吹哨人”机制基础上就可以改进形成“吹哨—回音”式反馈机制,能够较好地规避“息音式”治理弊端,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以保证已有政治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2)压力倒逼机制。价值观分化会形成多源性压力,这些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的意见和建议客观上会形成多方诉求参与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倒逼政策制定者顾及各方感受及其带来的压力,形成“压力—回应”式倒逼机制,以促使政策制定更加有效地回应人民合理的利益诉求,有时为了化解这种压力还会变被动为主动,如利用“网络问政”平台等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推进办公网络化、治理扁平化、服务信息化,从而积极吸纳压力,并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治理动力。如此一来,利用价值观分化的压力多源性完善倒逼机制,形成各种“广角式”“全景式”“超时空”的治理视野和治理方式,有利于拓展增量,化压力为动力,促进政治能力不断提升。
(3)鲶鱼效应机制。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28而适度的价值观分化往往会产生新的意见、建议和主张,有利于打破常规,激发活力。而不同观点的碰撞、发散思维的形成和治理手段的创新竞相迸发,就形成了鲶鱼效应。一个社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存在着多元选择,因为多元选择意味着无限可能,意味着“在单向时间里凝聚多样性与可能性”[7]。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多元多样可能性产生的鲶鱼效应,建立和完善“刺激—反应”式激励机制,以挖掘潜量,激发和释放可能的政治能力。
(二)价值观排序规律对民心政治的规范和调适机制
1.矛盾凸显机制。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8]33事实上,主要的矛盾集中点必然也是民众需求的承载支点。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总会以某种形式集中在某一个方面凸显出来。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带有很强的自发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凸显的矛盾并不会自动发出警报,这对国家民心政治安全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要消除这种威胁,还要主动发现、准确研判,否则还是不能清楚地揭示出其中的规律。因此,“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8]33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从现实来看,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敏锐判断和准确把握正是高度关注并善于利用矛盾凸显机制的重要体现。从党的十三大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皆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主要社会矛盾和主流价值观的精准研判而确定战略目标的成功范例。注意发现和化解凸显的主要社会矛盾以顺应主流价值观,成为民心政治合理性的主要来源。
2.优先化解机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对于大多数的民众而言,排在前面的价值需求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毛泽东在1948年晋绥干部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很好地顺应了价值观排序规律,结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日民族矛盾是压倒一切的、排在第一位的矛盾,“驱逐日寇,救亡图存”是那时民众最大的价值需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乃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客观而言,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不仅是某一个别事件如“西安事变”所决定的,而是彼时亿万民众的共同价值选择所驱动的。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经过了14年的抗战,人心思定、和平建国成为当时民众最迫切的价值需求。但国民党政府再次逆势而动,最终土崩瓦解,被人民所遗弃。历史一再证明,只有遵循人民的选择、遵循价值观排序规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3.干扰排除机制。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如果没有坚定的宗旨和原则,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变局时要做出准确的研判并确定最优化决策则绝非易事。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在今天看来非常正确的“武汉封城”决策,当时并不容易定夺——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封城,一系列不堪设想的后果——如物流人流中断、经济社会效益下滑、国际社会舆论压力等问题——将接踵而至。是人民生命重要还是经济效益、政治影响重要?这单凭经济考量和政治智慧可能已经远远不够,最终支持党和政府做出正确抉择的还是“生命至上”的价值选择。可以说,在民心政治理念下,“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已经内化为一种本能。一旦用人民第一、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作为判断标准,其他似是而非的干扰选项就可以自动排除,这为一贯严肃有余而感性不足的民心政治进一步注入了“合情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