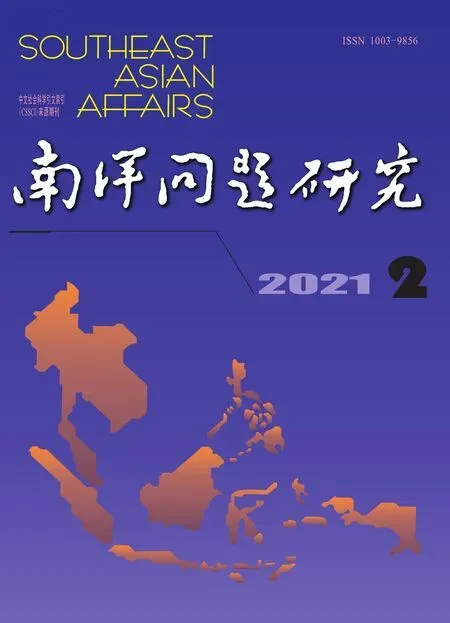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
——八莫之交涉
刘 佳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八莫(Bhamo)(1)时人亦称八幕、八募、巴谟或巴磨等,本文除引文外均称八莫。地处缅甸北部,位于伊洛瓦底江(2)时人亦称厄勒瓦谛江、伊勒瓦底江,本文除引文外均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太平江交汇口,距离今天中缅边境的云南陇川县82公里,[1]是近代中缅贸易重镇。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后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为应对英国的殖民扩张以及防止英国势力进一步侵入滇藏,1885年12月2日,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率先提出:“请英以八幕为我之商埠。彼灭缅,我占八幕。彼保护缅,我保八幕。”[2]可见,曾纪泽从一开始就对英国意图灭缅和对英谈判有心理准备和谈判思路。在英国侵缅伊始通过谈判来争取缅镇八莫,一则可使云南商道经八莫直通伊洛瓦底江和印度洋,二则可使英国势力停留在缅甸境内,避免直接侵入中国。八莫问题由此成为中英滇缅边界交涉之重点。近年来学术界对八莫也有所注意,如朱昭华认为曾纪泽所奏“请英以八募(莫)为我之商埠”,但清政府坚持将缅甸对华朝贡视为谈判第一要义,而八莫问题被逐步忽略;[3]吕一燃也注意到云南巡抚唐炯、驻英公使曾纪泽提出防范英人吞并八莫;[4]王巨新在《清代中缅关系》中提到,八莫问题因光绪帝强调缅祀和朝贡的重要性、英国外交部拒绝让出八莫以及曾纪泽奉调回国等原因而作罢。[5]学界已有观点多限于此,而对八莫问题在中英交涉中的具体过程及存失意义并未展开专题研究。伊洛瓦底江东畔的八莫是中缅两国水陆交通的枢纽,如果清政府当时能够通过对英谈判争取到八莫,那么则意味着伊洛瓦底江将成为两国界河。根据国际法中国家间划分边界的原则,若两国以可以航行的河流为界,则两国边界应定在主航道的中心线上,这就意味着中国西南边界将有可能延伸至伊洛瓦底江并进而与印度洋连通。(3)近现代国家之间划分边界线通常采取3种方法,即几何学划界法、天文学划界法和自然划界法。其中自然划界法包括以山脉为界、以河流为界和以湖泊为界。参见周忠海主编:《国际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3页。正因为八莫如此重要,在曾纪泽的推动下,清政府驻英使馆、总理衙门、清政府海关与英国外交部等相继展开交涉,而该交涉也成为近代中缅边界问题缘起之重大事件。考察这一事件不仅对于理解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后续走向至关重要,而且在中国传统宗藩关系及理念遭到巨大挑战背景下,对深入认识晚清政府外交运转的困境以及中华民族百年复兴这一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都有助益。本文根据清政府外交档案、海关档案、时人信函和报刊等中英文史料,对19世纪晚期八莫之交涉进行考察。
一、八莫问题的提出
两次鸦片战争后,尽管英国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但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对华输出,英国遭到法、俄、美等国的激烈竞争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控制中国腹地市场,就成为英国能否在中国攫取更大利权的关键。云南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和南亚相连的边疆门户,早已引起英人注意。如能打通滇缅贸易通道,英国商品就可不经广州和上海,直接由缅入滇并占据中国内陆市场,甚至还可借机入藏,此举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显著。为此,英国计划勘察从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之八莫朝东北往中国云南腾越,再向东经大理到达昆明路线的可行性,从而打通印度阿萨姆到中国西藏的贸易线。[6]英属印度政府于1868年派遣斯赖登(E.B. Sladen)上校率领的一支远征部队取道八莫,勘探从仰光到云南思茅的路线,后又于1874年派遣由柏郎(Browne,亦作布罗)上校率领的第二支远征队前往。在此行程中,英军翻译官马嘉里(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南蛮允一带遭边民击毙,是为“马嘉里事件”,即“滇案”。其实早在该案发生之初,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就曾上奏要提防英人野心。[7]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法方占领越南。1884年法缅又缔结密约,法替缅王禁锢其王兄,而缅王则将缅甸境内湄公河以东之领土割让给法国,此举对云南边情影响甚巨。1885年法缅密约被公开,英国遂采取报复措施攻取上缅甸(Upper Burma)。[8]
1885年1月28日,已经注意到滇缅边患苗头的驻英公使曾纪泽向总理衙门报告,称有华人占据缅甸八莫城,建议如果八莫华人是由滇边地方官员派遣,则应将此事与英方商谈,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如果八莫华人是乱民,则似乎可以通过招降而得到八莫,将云南边界拓展到伊洛瓦底江,借此打通云南出海通道,并化解边疆危机。[9]然而,曾纪泽的提议并未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朝廷不勤远略,岂有派兵拓界之事?”[10]但是,朝廷对八莫的消极态度并没有让曾纪泽放弃。10月25日,曾纪泽又向总理衙门力陈争取八莫作为清政府商埠之意义:“泽意宜自腾越西出数十里取八幕,据怒江(4)此处“怒江”应为伊洛瓦底江,其相互关系将在后文讨论。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11]在曾纪泽看来,趁英人尚未完全占领缅甸,清政府如能争取到八莫作为商埠自用,不仅可助滇省通商,也可将英人势力阻挡在缅甸境内。然而,清政府高层对于与英交涉缅甸之事极为慎重,加之对云南边界地理情况不甚了解,因此态度趋于保守。光绪对于八莫一事回复曾纪泽说:“交张凯嵩(云南巡抚)查复。旋据奏报,新街(5)新街的位置约等于八莫,其与八莫的关系将在后文讨论。据匪歼除,并无另有华人占据八幕之事。自腾越城南三百五里至蛮允为滇界,至缅之新街计二百八十五里,其间一百六十五里为野人界,向无管辖。所奏拓界一节,窒碍难行等语。”(6)通过分析光绪帝此封旨令,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清政府高层和云南地方官员的认知里,滇界南至蛮允为止,蛮允与新街距离二百八十五里,而且其间有一百六十五里的野人界无人管辖,因此很难将滇界拓展到新街。但后据地理学家姚文栋实地考察可知,“野人山实系中国现属各土司之分地,皆在云南境内,非瓯脱比也……夫云南之得失,关乎天下;而野人山之得失,关乎云南。能保野人山则云南安;能保云南安则天下皆安。”(《禀总署堂宪》,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卷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3页。)若清政府当时能够将野人山地作为自有领土进行考量,将滇界拓展到新街理论上是可行的。[12]那么,总理衙门和光绪帝均不甚了解更无心支持之八莫,何以会成为曾纪泽力争之要地?
伊洛瓦底江全长2090千米,发源于中国西藏境内,其上游恩梅开江在缅甸密支那与迈立开江汇合后称伊洛瓦底江,于缅甸南部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流域面积达409,000平方公里。[13]八莫位于伊洛瓦底江和太平江交汇处,而太平江往东连接着中国现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缅甸往来云南的贸易重镇。如此要地,云南地方官员和部分清政府高层对其多少均有所耳闻。早在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前10年,即1875年5月“滇案”发生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就曾致信总理衙门:“马嘉理被害时,有同行之参将伯郎(即柏郎)过缅甸之巴谟地方。”[14]当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照会总理衙门,告其柏郎等人将从滇回缅,请派人护送,并称“缅甸巴谟地方,距滇省边界为路不远。”[15]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在奏请暂缓柏郎等人入滇时提到:“彼国再由缅甸巴谟地方,派队前来接护到缅。”[16]8月,威妥玛又致信李鸿章,其中提到:“查巴谟离满云不过数英里。”[17]李鸿章据此致信总理衙门:“巴谟在缅、滇交界,系属缅境,滇省奏报所称新街是也。”[18]可见在1875年“滇案”发生之时,李鸿章和岑毓英等人对八莫均有所知晓。但时至1885年,可能是由于时间久远抑或地名翻译所用汉字多变,以及人事变动,总理衙门竟已淡忘,光绪帝更问,“究竟八幕坐落何地,与新街是一是二,其中有无野人间隔?”[19]
清政府对滇缅重镇八莫竟遗忘至此,实际反映出其对边疆危机反应的迟钝和地理知识储备的匮乏。对于总理衙门和光绪有关八莫的质问,1885年10月29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泽之缅图无汉字,八募是否蛮暮之新街,中隔野人是否卡瓦,均不敢妄定。”[20]可见,虽然曾纪泽一开始就提出要争取八莫,但他本人对八莫的情况亦不甚了解。云南巡抚张凯嵩直到1886年1月16日,才上奏“八幕地方,现据腾越同知禀复,即属新街土名,新街在缅八幕城”。[21]身为云南地方要员,张凯嵩此言前后矛盾,究竟八莫就是新街,还是新街在八莫城里?而作为10年前“滇案”签约负责人的李鸿章,则在1886年2月6日才向总理衙门解释八莫即巴磨,又名新街。[22]因此可以认为,在曾纪泽提出八莫要求伊始,曾纪泽、总理衙门、李鸿章和光绪帝等清政府高层要员之间并没有就八莫问题交换过意见,他们甚至连八莫的具体位置都不清楚,更谈不上能够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争取八莫是身处伦敦的曾纪泽从当时清王朝的国家利益出发主动向英国提出的诉求。(7)对于上文官方文件中所出现的“八莫”“新街”“蛮暮(莫)”是否为同一地点,笔者没有能够找到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根据《辞海》,“八莫,旧称新街”[《辞海 地理分册(修订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0页]。根据《东南亚历史辞典》,“新街,即八莫”(《东南亚历史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李鸿章致光绪帝的奏折中也一直认为八莫与新街是同一地点。吕一燃的观点是,新街“即八莫,或作八募,原蛮莫土司所属之地”[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39页]。吕思勉认为“八莫,即蛮暮之新街。蛮暮本亦土司,后为缅所并。新街向为通商巨镇。”据以上种种说法,八莫即新街,属于蛮暮(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86页)。而《腾冲华侨华人》提到,“据《民国腾冲县志稿》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缅甸入侵滇西边境,云贵总督杨应琚遣腾越协副将赵宏榜率永顺、腾越兵三百余出铁壁关,屯蛮莫(八莫)、新街迎战”(《腾冲华侨华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7页),据此文,蛮莫即八莫,但与新街不为同一地方。可见对于八莫、新街、蛮莫的具体位置 ,各家说法不一,甚至互相矛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英国人对八莫却并不陌生。1871年斯赖登发表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的文章《从缅甸到中国西南的探险:通过伊洛瓦底到八莫》(Expedition from Burma, via the Irrawaddy to Bhamo,to South-Western China)就提到自己于1868年率领远征队乘轮船从曼德勒出发,沿伊洛瓦底江到达缅甸边境八莫,再往东北走就是中国云南省边境,而八莫是缅甸和中国西南贸易的商业中心。[23]在文章中,他还附有一张绘制相对详尽的滇缅边境地形图,名为《从八莫到腾越》(From Bhamo to Momein(8)Momein,亦作Momien,译作莫棉或莫米恩,是缅甸人对腾越的叫法。)。1883年3月中旬,英国人为继续考察掸邦和云南情况以及贸易前景,还组织探查从广东西江(9)西江是珠江的主流,全长2214km,发源于云南曲靖市境内的马雄山,其上源南盘江,流经云南东部和黔西南、桂西北接壤地带。到八莫的可能性。[24]同年4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英女王秘书科尔伯恩·贝克(Colborne Baker)更是从水路、铁路、公路3方面强调了八莫路线的重要性,称八莫所处的伊洛瓦底江是缅甸境内的天然交通干道,缅甸境内的铁路最终将延伸到八莫,而建设从八莫到中国边镇腾越的公路看上去也并无太大困难,因此八莫是开辟深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商业前哨。[25]在大英图书馆报纸数据库(British Library Newspapers)中搜索Bhamo(八莫),仅1860年1月1日至1886年1月1日期间的搜索结果就有1338条。可以说在19世纪末,英国人对于八莫不仅毫不陌生,而且深知其战略价值:通过八莫不仅可以掌控滇缅贸易,更重要的是可以打通从印度经缅甸到云南的战略路线。
既然清政府高层均不熟悉八莫,也没有提前就八莫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当时身处伦敦的曾纪泽又如何能够想到在英缅战争伊始争取八莫?首先,虽然清政府高层不熟悉边务,但清政府内部对于西方势力企图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和市场有着清醒的认知。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云南巡抚唐炯和张凯嵩等名臣都曾上奏提醒要提防西南边患,曾纪泽作为驻英公使,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浓厚的爱国情怀,更具备较强的外交敏感性。其次,出使伦敦的经历,使得曾纪泽能够跟普通英国民众一样即时接收到英国在全球扩张势力的一手信息。事实上,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出使伦敦时就已经注意到英国准备修造由印度阿萨姆通往云南的铁路,[26]而从水路来看,“澜沧江、湄南江两处水源并较盛,皆可达云南腹地,一通商则四路皆通矣。”[27]可见英国扩张势不可挡,尤其是1885年6月9日中法签订《中法新约》,中国进一步丧失大量主权,这不能不使曾纪泽提高警惕,预筹中英滇缅谈判,为中国争取主动权。最后,清政府驻英使馆英国顾问马格里(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直接影响了曾纪泽对八莫的政策研判。
马格里是晚清著名洋员,1863年加入淮军并为李鸿章所器重,1876年被李推荐作为翻译官陪同郭嵩焘出使英国,并协助建立清政府驻英使馆。[28]驻英期间,马格里多次作为中方顾问参与对外交涉,并能站在中方角度争取权益,由此为中方所器重。曾纪泽继任后与马格里密切合作,《曾纪泽日记》里反复出现的“清臣”就是马格里的中文字号。清政府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在与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来往的函电里多次怀疑,力争八莫是马格里向曾纪泽提出的建议。例如,1886年3月金登干告诉赫德:“3月10日的圣詹姆士报说中国之所以要求(英国)让给八莫,并非北京的意思,而是中国驻欧外交代表所制造的,特别是那些身在欧洲而为中国效劳的欧洲人所制造出来的。”[29]这说明不止是金登干,当时在英国国内也有媒体猜测中国声索八莫是由马格里向曾纪泽提出来的建议。
目前,虽然尚未有史料直接证明这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缅甸问题上向英国要求将八莫作为清之商埠的条件并不是由清政府内部首先提出来的,更不是清朝统治者给驻英公使曾纪泽下达的旨令。所以,手握无汉字的缅甸地图、不甚了解八莫位置、不清楚八莫是否为新街的曾纪泽,能够从一开始就在中英缅甸交涉中采取主动,提议将八莫争取作为清自有商埠,除了与其本身较强的政治和专业素养有关外,马格里的影响可能性很高。
二、曾纪泽与赫德对八莫问题的态度和策略差异
与曾纪泽的积极主动相比,总理衙门对力争八莫却坚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尽管如此,曾纪泽亦未放弃,因为力争八莫能够将英国势力限于缅甸境内,避免就滇省开埠问题交涉,这对于暂时缓和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在曾纪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同时,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悄然参与其中。1885年10月31日,接替奕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请赫德私下向英国了解英缅矛盾详情及英国诉求,这实际上给赫德插手中英缅甸谈判提供了机会,而且赫德从一开始就绕过清政府驻英使馆,与英国外交部直接谈判。11月15日,赫德向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庞斯福德(Julian Pauncefote)提出缅甸问题解决办法,包括英国答应缅甸按惯例每10年向中国进贡,中国尊重英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中国答应在中缅边境(云南省境内)选择一地开放对英贸易。[30]赫德的方案不仅完全没有提到八莫,他甚至对庞斯福德解释说:“英报(指《泰晤士报》)主张将中国边境扩展至八莫一节,可能是一陷阱,应竭力避免,这意味着瓜分属邦的土地,此间当然是非常不欢迎的;并且这种办法,将因插入一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地带,使英国与真正的中国永远疏隔,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往来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对此绝不可予以鼓励。”[31]
11月16日,赫德提出的方案被提交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Robert 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和印度事务部,赫德致电金登干说:“协定草稿内容虽未向总理衙门详细说明,但我相信英如同意,总理衙门必可接受。我极力主张英国全部接受,同时务必注意勿使消息外泄。中国大概可以欣然接受第一款(即朝贡条款),对第二款(即于云南边境选择一处开放对外贸易)可能迟疑,但我想也可设法使他们能够听从。”[32]可见,总理衙门此前并不知晓赫德方案,这是赫德私人、单方面向英国外交部提出的方案,且完全推翻了曾纪泽力图使英国势力止步于缅甸境内的战略意图。但庞斯福德在对待曾纪泽的问题上非常谨慎。11月23日,金登干告诉赫德,庞斯福德认为整个事情非常混乱,使得他们对待曾纪泽左右为难,只能尽量安抚,并且在此次谈话中,“庞第一次提到八莫,他说道:‘他们(清政府)也许肯以别的东西交换朝贡,比如把他们的疆界推展到八莫等等’。我说中国大概并不想扩充疆界。”[33]这一次,尽管庞斯福德在八莫的态度上有所松动,但又立刻被金登干否定。
由于印度事务部的迟疑,赫德的方案没有通过,因此曾纪泽和马格里也并不知道赫德竟参与其中。1886年1月23日,马格里和英国外交部官员克蕾(P. Currie)就缅甸问题进行正式会谈。马格里主张由中方得到八莫自行通商设埠,而克蕾却主张中方在八莫设关取税,同意中国商船在伊洛瓦底江自由航行来解决通商问题。在领土方面,克蕾以割让萨尔温江东岸的掸人居住地来要求清政府在朝贡细节上作出让步。[34]通过当时金登干从伦敦传递给赫德有关谈判进展的信息,可以看出此时中英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金登干表示索尔兹伯里答应了曾纪泽的几乎全部条件。1月30日,曾纪泽也告知总理衙门:“近商缅事,颇顺。英择缅教王(10)索尔兹伯里曾提议或许可以在缅甸另立一管教不管政的国王照旧贡献中国,但此提议并未得以通过。,候中朝俞允,并照前进献,潞江(11)曾纪泽所争“潞江以东”即为前文所提到的萨尔温江东岸的掸人居住地,这与《马格里爵士传》里曾纪泽写给罗斯伯里的信件中提到的要求是一致的。参见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23.东地咸归中国,均将定议。所争者,册封、入贡字样及八幕耳!”[35]然而恰在此时,英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索尔兹伯里内阁突然垮台,谈判风向随即发生改变。
2月27日,马格里告诉金登干八莫恐怕难以争到,因为中方提出了3个要求:一是在八莫通商设埠;二是除了英国原来准备让给中国的萨尔温江以东地带外,中国提出再将边界拓展到瑞丽江;三是允许中国商船在伊洛瓦底江上得享航运权利。而至于朝贡,如果印度事务部认为立教王的办法行不通,可以另筹别法。[36]为了尽快推进谈判,3月7日,曾纪泽电告总理衙门,其拟定了刚柔两策,刚策是拒绝英国陆路通商之请,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柔策是允许缅督和滇督互送礼,潞江以东归中国,而且曾侯做了进一步的让步,同意仅在八莫设关取税。[37]在曾纪泽发回总理衙门的所有函电里,这是他第一次放弃了将八莫作为清廷自有商埠的想法。
然而,总理衙门对以上方案并不认可。总理衙门认为,中缅应坚守固有之界,而不是以洋图为据;《烟台条约》中已经约定了通商,不可能不通,不讲诚信也有失国体;彼此送礼没有贡献之名,毫无意义。[38]这让曾纪泽陷入两难,总理衙门认为中缅应坚守固有之界,不以洋图为据,但是现实问题是曾纪泽手中只有洋图,其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力争八莫作为清自有商埠,就是要抢在英国人之前提出商埠要求;总理衙门认为《烟台条约》中已经约定了通商,若英国执意执行,中国也只能按约办事,但曾纪泽认为通商可以作为谈判的资本和筹码,因为英国人最在意的就是通商。曾纪泽虽然把八莫看得极重,但是缅祀和朝贡关乎国体,他认为与英国人谈判滇缅界务、商务就是默认了英国已经灭亡缅甸的事实,若现在不谈判缅甸进贡之事,以后更难提起。[39]1886年3月16日,曾纪泽再次致电表明看法,在没有争得缅祀和朝贡的情况下,似乎不宜遽定商务和界务,这会显示中方已经放弃。[40]此时克蕾也强硬地表示,英国占据缅甸本不需要与清政府商议,如果清政府不允许缅督呈仪,一切皆可停议。[41]
英国方面,新内阁上台后,曾纪泽于3月向新任外交大臣罗斯伯里(A. P. Rosebery)重申之前谈判已经达成的共识。[42]然而,据金登干所说,罗斯伯里反对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曾经答应清政府的种种条件,双方越谈越远。[43]4月21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报告了这几个月的谈判进展,表示英国同意将缅境潞江以东的管理之权让给中国,至于潞江以西和八莫的归属,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商议之后认为可以让清政府在伊江(即伊洛瓦底江)上设立船埠,作为中方通海之埠。[44]
与此同时,曾纪泽的驻英公使任期已到,总理衙门电召曾纪泽回国,新任驻英公使刘瑞芬也已抵达伦敦。总理衙门的本意是让曾纪泽处理完缅事再返国,但由于光绪帝认为缅甸商务和界务细节关系重大,“俟曾纪泽到京后,面加垂询,再行定议。”[45]5月14日,李鸿章在给曾纪泽的电报中也说:“上意缅事缓议。”[46]因此,曾纪泽奉命卸任回国,此后不再参与对缅谈判。
对于英国来说,曾纪泽尚未处理完缅甸事务就被召回国,不免让英国外交部不解,(12)事实上,在1884年与法国谈判越南问题时,中方就临时将谈判代表曾纪泽换成了李凤苞,同样引起了法国人的疑惑。而英国国内舆论也表达了对现有谈判结果的不满。在这个问题上,中英双方决策者的逻辑思维再次表现出巨大差异,清帝没有从现代的外交和政治角度考虑驻英公使的去留,中方没有在与英国谈判达成共识的时候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件,为后来英国在缅甸问题上翻脸埋下伏笔。值得一提的是,总理衙门一方面通过驻英使馆与英方交涉缅甸问题,另一方面又让洋员赫德私下里向英国打探消息,使得赫德有机会插手缅甸事务,并将驻英使馆蒙在鼓里,如此明暗两条线的外交让英方觉得混乱和不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打乱了曾纪泽交涉缅甸问题的节奏,妨碍了其想要主动且迅速解决缅甸问题的决心。
三、曾纪泽放弃八莫的原因及《缅甸条约》的签订
1886年3月7日,曾纪泽在征询总理衙门关于谈判的刚柔两策意见之时,第一次放弃了将八莫作为清自有商埠的想法,拟通过在八莫问题上的让步换取其他诉求。那么,曾纪泽为何突然放弃八莫?一方面,当时的谈判压力可能让曾纪泽觉得争取八莫无望。索尔兹伯里内阁下台后,无论是新任的罗斯伯里、与马格里直接谈判的克蕾,还是印度总督达茀林,都在缅甸问题上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直接拒绝了中方在八莫问题上的诉求。如果清政府不做出让步,此事必将延宕,而曾纪泽任期即将结束,需要尽快解决缅甸问题。另一方面,李鸿章对缅甸问题的看法应对曾纪泽产生了影响,并且当时中缅边境的紧张局势也印证了李鸿章的看法。
李鸿章与曾纪泽关系匪浅,从私人情感上来说,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而曾国藩对李鸿章又有提携之恩;从工作关系上来说,李鸿章从1870年开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外事问题上是曾纪泽的上司和前辈。在曾纪泽使英期间,曾、李二人除有频繁的电报往来外,还有书信往来,在官方电报中,曾纪泽多次向李鸿章咨询工作问题,而在私人信件里,李鸿章则表达了其对缅甸问题更为直接和具体的看法。
其实,英缅战事伊始就引起了刚刚完成对越谈判的李鸿章的关注。1885年11月19日,柯乐洪(Colquehoun,也译作葛洪)(13)英国探险家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ehoun, 1848—1914),1883年出版著作《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曾获得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金奖(Founder’s Gold Med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拜访金登干时告知后者称,李鸿章曾说如果英国事先与清政府有所谅解,那么它在缅甸的行动,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47]11月25日,李鸿章与印度总督委员麻葛累(Macaulay,亦译作马高藟、马高理、马科蕾,以下除引文外统称为麻葛累)和英国驻烟台领事璧利南(Byron Brenan)也深入讨论过缅甸问题。李鸿章对英国此次攻缅的意图非常了解,但仍希望英国能够尊重清政府在缅权益,由清政府出面调停,与缅王议和。[48]与此同时,英军在缅甸势如破竹,志在必得,战事的发展使李鸿章更为担心中国西南边患。在会见麻葛累和璧利南后,11月26日李鸿章致电提醒总理衙门:“英攻缅甸甚急,恐将并占北缅,则滇边西界后患甚长。”[49]12月31日李鸿章又奏称,有法国情报显示英人窥伺大理,法国绅士嘉尔芜建议中国争回缅甸,但李鸿章认为徒以口舌争之,未必有所补救,反而大理的回民叛乱更值得关注。[50]
1886年1月13日,在马格里与克蕾展开正式谈判的前一天,李鸿章又给曾纪泽发去一封私人信函,直言朝廷追求进贡虚名,虽然有“巴磨新街之说”,滇帅恐怕也没有遥制八莫的魄力,对于西藏通商,朝中议论不尽支持,而英国贪欲无厌,如果能订约禁止英国在西藏通商,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李鸿章感叹说:“外侮日增,兵饷日绌,人才日稀,虽有狠心辣手,亦有行不去之时,可为浩叹。”[51]2月9日,李鸿章又在信里对曾纪泽说:“印督锐志拓疆,未必仍允朝贡,即分界八幕,议虑尚费唇舌。”[52]由此可见,李鸿章认为英人对缅甸志在必得,未必肯答应维持缅祀和朝贡,也未必愿意把八莫分给中国,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朝贡本就是虚名,另外即便分到八莫,滇帅也无此兵力遥制。清政府现下四方多故,空言攘夷,但财用日绌,人才渐稀,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李鸿章认为如果谈判能禁止西藏通商,似乎更有现实意义。而当时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四川总督丁宝桢等人对滇边和西藏情形的奏报,也印证了李鸿章的说法。查阅同期中英之间信函的寄收时间,可知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例如,1886年1月8日赫德给在伦敦的金登干寄去编号为Z/246的信件,金登干于3月9日收到;1月16日赫德寄去编号为Z/247的信件,金登干于3月12日收到;1月18日赫德寄去编号为A/61的信件,金登干于3月12日收到。因此,曾纪泽于3月7日在中英谈判中第一次放弃将八莫争做清自有商埠之前,很可能已经收悉李鸿章于1月13日寄出表达朝贡虚名和八莫无法遥制观点的信函。而李鸿章于2月9日寄给曾纪泽的信件,曾侯则有可能在4月9日前后收到。虽然只有两封提到八莫的信件,但这两封信件的收件日期都非常关键,分别处于曾纪泽第一次对英放弃将八莫作为清自有商埠和曾纪泽最后一次就缅甸问题同英方谈判前后。
查阅曾纪泽和李鸿章的相关史料,并未能够找到曾接受李建议放弃八莫的直接证据,李也并未直接命令曾放弃八莫,相反,李只在私人信函中表达了朝廷无法遥制八莫的感慨,从未在官方电报中表露此意。这正是李鸿章的老谋深算之处。一方面,若李鸿章直接命令曾纪泽放弃八莫,也许会引起曾纪泽的顾虑与抵触。因为在之前的中法谈判中,虽然曾纪泽和李鸿章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是曾纪泽态度更为强硬,而李鸿章态度趋软。后来在谈判僵持不下之时,李鸿章奉旨调换了谈判代表,由李凤苞代替曾纪泽与法国谈判,最后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由此可见,在涉外事务中,虽然李鸿章是曾纪泽的前辈和上级,但双方秉持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对于八莫的消极态度,与其在对越谈判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光绪帝只在曾纪泽提出争取八莫的伊始明确表示了拒绝,但在曾纪泽的坚持下,清政府高层也接受了曾侯的提议,在后来曾纪泽与总理衙门的往来电报中,无论谈判顺利抑或阻滞,总理衙门都没有让曾纪泽放弃八莫,反而是在朝贡问题上无法取得进展之时,让曾侯暂时搁置朝贡问题,与英方谈判商务和界务。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也不可能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直言让曾纪泽放弃八莫。曾纪泽对清政府国力情况当然是了解的,身处伦敦的他自然也知晓在冗长的谈判期间英国势力已经于缅甸站稳了脚跟,所以英方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而他本人又面临着任期结束即将回国的问题,在回国之前竭尽所能尽快为清王朝争取最大的利益才是关键。
关于李鸿章在八莫问题上的态度,日本学者箱田惠子所引用的英国外交部档案显示,李鸿章将八莫作为牵制英国而使用的手段,原因是1886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O’Conor)发给罗斯伯里的电报中说,李鸿章曾对璧利南表示割让八莫是中国承认英国统治缅甸所应当要求的权利,但欧格讷通过璧利南告诉李鸿章,八莫对两国都没有价值,希望可以友好解决问题,李鸿章听后非常高兴,答复璧利南说割让八莫是曾纪泽的想法,恐怕是受到马格里的挑唆。[53]这表明欧格讷确实在与北京各方沟通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对于八莫和朝贡的态度。
关于曾纪泽力争八莫的问题,朱昭华认为,薛福成后来在与英国人谈判划分野人山之时,把英国人曾经允诺曾纪泽的“三端”(14)关于当时英国外交部允诺曾纪泽的“三端”,在曾纪泽个人的遗集和官方文件中均未明确提到,是薛福成在《使英薛福成奏遵旨与英外部商办滇缅界线滇境西南两面均有展拓折》(1893年11月4日)(《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7页)中提到,英国有允曾纪泽“三端”,界务一端,愿稍让中国展拓边界,商务二端,以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在八幕近处勘明一地,允中国立埠设关,但此“三端”仅互书节略存卷,存于驻英使馆。在1886年3月5日金登干给赫德的Z/416号函电中曾经提到,马格里在与克蕾谈判时提出中国的要求是“(一)八莫;(二)除了英国原来准备让给中国的萨尔温江以东地带外,再将边界拓展到瑞丽江;(三)中国船只在伊洛瓦底江上得享航运权利”。[《伦敦来函Z字第四一六号》(1886年3月5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5—66页]可以推测曾纪泽通过马格里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以上“三端”的要求,最后双方达成共识,英方允其“三端”,但做了双方均认可的调整,就是薛福成描述的节略存卷中的“三端”。与分割野人山联系起来,以分野人山地为压力,迫使英国人继续履行曾经允诺的“三端”,这可能是薛福成向曾纪泽学习的结果,“因为他认为,英国当时之所以允让三端,主要在于曾纪泽力争八莫,‘曾侯据此立论,故彼意既不将八募让还,则此三端亦足稍为点缀,用示睦谊’”。[54]也就是说,朱昭华推断薛福成认为曾纪泽争取八莫只是一个用来分散英方谈判注意力的幌子。但是,由上文可知,曾纪泽从对英交涉伊始就有意争取八莫作为清自有商埠,并多次向总理衙门请求允其力争八莫,后来在八莫问题上作出让步,是现实情况使其明白得不到或得而难以维护,顺势通过对八莫的妥协而提出其他要求,最终在缅甸谈判上取得英国允诺“三端”。可见,力争八莫作为自有商埠不是曾纪泽一开始就采取的谈判策略,而是谈判目的之一。
根据1876年《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使团由川入藏。1886年上半年,英人入藏的消息愈传愈烈,5月29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英领事璧利南前言,马高藟不日由印度入西藏游历。”[55]这再次引起清政府内部紧张。为了使麻葛累使团暂缓入藏,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做出了妥协。1886年7月24日中英《缅甸条约》在北京签订,中方代表为奕劻,英方代表为欧格讷。《缅甸条约》内容有五条:“一、由英国派缅员向中国每十年呈进方物;二、中国认可英国在缅甸的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三、中缅边界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四、英答应停止入藏,通商如可行,另立章程,倘多窒碍,英不催问;五、此约先在中国画押,候批准,在英京互换。”[56]通过《缅甸条约》,清政府仅仅得到了英方暂时不入藏的承诺和没有实质内容的缅员呈仪规定,而英方却得到了清王朝对英国在缅甸一切权利的认可,这显然是清政府为了稳定时局而仓促签订的协议。曾纪泽在离任之前同英国外交部谈好的“三端”,在此条约中完全没有体现。1886年8月13日,金登干致电赫德说:“中英关于缅甸的条约,似完全出乎马格里意料之外,并使他非常恼恨。他说不懂总理衙门为什么会将他和曾侯为他们力争得来的一切都放弃了。”[57]
在《缅甸条约》里,清政府没有得到八莫。但在中英有关缅甸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清政府却曾经有得到将八莫作为清自有商埠的可能。在中英交涉之初,赫德强硬的私人外交和曾纪泽友好的官方外交,曾经造成英方认为中方对缅甸问题的态度不明朗,英方不了解中方的底线。当英方势力在缅甸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时候,英国内部确实动过心:是否可以通过转让八莫而换取中方在朝贡问题上的妥协?在奕劻第一次找到赫德,委派其向英国人了解对缅甸出兵的诉求时,赫德曾经给出一份《税司赫德呈总署英国向缅甸提出赔罪办法电》,这其实是应金登干的要求,庞斯福德把印度事务部关于缅王暴行和英国诉求的摘要给了金登干,而在庞斯福德的原文中,摘要第五条说:“应给予英国经过八莫的对华贸易以正常便利。”[58]可见,英国虽然认为八莫重要,但并没有一定要拿下八莫的决心,也不认为清政府会轻易放弃八莫。然而,在赫德粉饰之后递交给总理衙门的《税司赫德呈总署英国向缅甸提出赔罪办法电》中,这句话并未出现。1885年11月23日,庞斯福德在金登干面前第一次对八莫问题松口,他说中国人也许肯以别的东西交换朝贡,比如把他们的疆界推展到八莫,等等,但这又被金登干立刻否决了:“中国大概并不想扩充疆界。”[59]马格里曾经拜访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曾任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说英国应当与中国妥议此事,如果能让中国展界到八莫,应该可以解决目前中英谈判的难题。当时一些英国媒体也认为可以通过对中国转让八莫来解决缅甸问题,12月14日曾有记者在《泰晤士报》重提中国在八莫展界的方案。1886年1月1日,金登干致电赫德:“《标准报》说:‘如果将中国疆界展拓到八莫办法,能够满足中国皇帝心意的话,那末从英国本身利益来看,也是颇值得推许的。’”[60]由此看来,英国无法接受中国的朝贡条件,但是在当时英国国内,无论是庞斯福德所代表的外交部,还是阿礼国所代表的英国上层社会,抑或是新闻媒体,都曾在八莫问题上立场动摇,认为可以通过满足中方八莫展界的条件来换取清政府放弃缅甸朝贡的要求。
那么,清政府又是如何错过八莫的呢?一方面,清政府在谈判初期,在缅祀和朝贡的问题上过于强硬,错过了与英方谈判的最佳时机。清政府讲究合乎礼仪,重视朝贡,必然要保留缅祀,只有缅祀存在,朝贡才有可能存在。但是对于英方来说,吞并缅甸使其成为英国一个省,必然不能保留缅王,缅王不在,朝贡就无从谈起,英国官员更不可能向清朝皇帝朝贡。金登干曾经对赫德说,“邱吉尔的机要秘书摩尔说,他们必须保留吞并问题,如果他们向下议院提出条约时,里面竟有向中国进贡的字样,岂不将引起一阵叫嚣。英国正式吞并了缅甸,再向中国进贡是绝对不可能的。”[61]所以索尔兹伯里在谈判之初提出也许可以立一个管教不管政的缅王进行朝贡,其实就是打一个名义上的擦边球,势必遭到英国国内和印度事务部的反对。事实上,在此之前刚签订的1885年《中法新约》里,法国人就没有同意中国提出的朝贡诉求,同样地,英国也不会同意。所以,在英国不可能同意的缅祀和朝贡问题上,中国耽误了太多时间,而在此期间,英国一步步在缅甸站稳了脚跟,并反复试探中国人的谈判底线,中国因此错失良机。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来说,将八莫划归大清版图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清廷内部提出来的要求,而是曾纪泽一边向总理衙门反复征询争取八莫,一边通过马格里向英国外交部提出的要求。清政府对于自身的边境建设态度尚且游离,对别国的领土更加没有野心。在放弃八莫设埠展界之后,曾纪泽依然争取在八莫设关取税,自始至终都把八莫作为重要的谈判目标。但是仅靠曾纪泽和马格里的努力是不够的,清廷决策者对八莫的地理位置和八莫的战略意义缺乏基本的认识,没有现代的外交思维和谈判逻辑,甚至错误引入赫德和金登干从中作梗。八莫的位置如此重要,本就不是英国人会轻易放弃的地方,《泰晤士报》一位权威的记者曾评论说,“任何人只消一查地图,就知道八莫战略地位的重要了。即使为了争取中国的友谊,八莫也是一个过高的代价。”[62]1886年4月18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说:“八莫和展界到瑞丽江两点,此间从来不提起,我相信也不是此间要这样办的。这些大概是某些闲得没事的人,造作出来的把戏。”[63]可以想象缅甸问题的谈判转移到北京后,由于缺少曾纪泽和马格里的参与,八莫更加无从谈起。
四、结论
在中国大一统王朝制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从中国西南边疆实际来看,至少从清中后期开始不稳定因素就已经在不断滋生和蔓延,清雍正朝以来实行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成效不一,有不少土司管辖下的边疆地区发展成摇摆于中国与周边属国之间的夹缝地带,也即清政府官员所谓的瓯脱之地,还有一些则自愿附属于周边属国管辖。19世纪中叶开始朝贡体系受到西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强烈冲击,中国周边属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也转变为中国与殖民列强之间关系,边界领土纠纷随之而来,中缅边界争端就是近代中外边界争端中的一例。领土纠纷的产生,绝不仅仅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政策的结果,纵观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划界条约,可谓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分析个中原因,不止是国家实力问题,更与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外交观念、边疆政策、羁縻举措所生弊端紧密相连。
八莫一案是清代中缅边界交涉之开端。八莫之得失不仅是领土得失,更是近代中国向伊洛瓦底江、印度洋延伸之可能性的存失。晚清政府高层在国家边疆主权方面观念落后、政策缺位,缺乏海洋意识,不清楚八莫临江达海的意义,也不曾认真考虑可借此深入印度洋以拓展外部世界的战略价值,暴露了清王朝在世界格局发展大势面前的窘迫。在整个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虽然有曾纪泽和马格里等能员干吏的不懈努力,但清王朝整体缺乏熟悉外交事务和边疆地理的可用之才,反而让赫德等人把持洋务,在对英交涉中形成明暗两条线格局,体现了清政府内部相互牵绊的涉外机制、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前后矛盾的外交决策。八莫问题交涉之失败,足见晚清外交举步维艰已远不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中缅边界谈判的结果正如中英《缅甸条约》所示,清政府得到了朝贡虚名,承认了英国对缅殖民统治,但是英国的殖民脚步却并没有因此停下,反而成为影响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稳定的严重外患。八莫问题的交涉过程充分暴露出在殖民主义东来的咄咄逼人之势面前,晚清政府仍然用传统的朝贡制度和华夷之辨来审视周边变化,重名而轻实,无论从知识体系还是国家实力上,都无法应对西方殖民者的挑战,东亚朝贡体系在近代西方条约体系的冲击下崩溃瓦解。
注释:
[1]德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德宏州年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2]《使英曾纪泽致总署拟请英以八幕为华商埠候示电》(1885年12月2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0页。
[3][54]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1—71、81页。
[4]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39—840页。
[5]王巨新:《清代中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1—205页。
[6]“Trade Route to Yunnan”,EdinburghEveningNews(Edinburgh, Scotland), August 8, 1878, p. 4.
[7]《总署奏英员马嘉里被戕一案英使词意叵测请加意边防海防折》(1875年3月21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8]张凤岐:《云南外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3页。
[9]《使英曾纪泽致总署华人据缅甸八幕城筹商办法电》(1885年1月28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051页。
[10]《旨着曾纪泽向英声明中国未启边衅电》(1885年1月29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052页。
[11][12][19]《使英曾纪泽致总署英取缅北我宜取八幕电(附旨二件)》(1885年10月25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46页。
[13]何宣、杨士吉、许太琴主编:《云南生态年鉴201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14]《论派员出查各国制造并论滇案》(1875年5月11日),《李鸿章全集31(信函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
[15]《英使致总署柏副将等由滇回缅请派人护送照会》(1875年7月26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第22页。
[16]《滇督岑毓英奏请饬总署照会英使转饬柏郎等稍缓来滇游历片》(1875年8月18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第51页。
[17]《照译英使威妥玛致李鸿章洋文节略》(1875年8月28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第44页。
[18]《请酌与威使一二事》(1875年8月13日),《李鸿章全集31:信函三》,第288页。
[20]《曾侯寄译署》(1885年10月28日),《李鸿章全集21(电报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
[21]《滇抚张凯嵩奏英缅已决战并绘进缅边地图折》(1886年1月16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90页。
[22]《寄译署》(1886年2月6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3]E. B. Sladen, “Expedition from Burma, via the Irrawaddy to Bhamo, to South-Western China”,TheJournal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 Vol. 41 (1871), pp. 257-281.
[24]“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EdinburghEveningNews(Edinburgh, Scotland), March 15, 1883, p. 2.
[25]“New Routes to China”,TheWesternDailyPress(Yeovil, England), April 25, 1883, p. 3.
[26][27][清]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十)》,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56、457页。
[28]熊月之等编著:《大辞海12(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
[29]《伦敦来函Z字第四一七号》(1886年3月12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30]《赫致金第299号》(1885年1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5页。
[31]《北京去电第三一一号》(1885年11月24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37页。
[32]《赫致金第302号》(1885年11月17日),《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8卷,第517页。
[33][47][59][61]《伦敦来函第四○○号》(1885年11月27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40—43页。
[34]FO17/1060, Memorandum by Sir P. Currie, January 23, 1886; Memorandum by Sir P. Currie, January 28, 1886, 转引自[日]箱田惠子:《<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考析——兼论晚清外交之特性》,鹿雪莹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4年第二辑,第71页。
[35]《使英曾纪泽致总署报近商缅事进行颇顺电》(1886年1月30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298页。
[36]《伦敦来函Z字第四一六号》(1886年3月5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65—66页。
[37][38]《使英曾纪泽致总署英缅事决用刚柔二策电(附旨)》(1886年3月7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326页。
[39]《使英曾纪泽致总署与英议缅甸事倘照例贡献可否了结电(附旨)》(1886年3月14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330页。
[40]《附:曾侯致译署》(1886年3月16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32页。
[41]《附:曾侯致译署》(1886年3月17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32页。
[42]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TheLifeofSirHallidayMacartney, K. C. M. 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18-424.
[43]《伦敦来函Z字第四一九号》(1886年3月20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70页。
[44]《附:曾侯致译署》(1886年4月21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40页。
[45]《使英曾纪泽致总署陈明交卸赴俄并高丽催英国退安岛电》(1886年4月25日),《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339页。
[46]《寄伦敦曾侯》(1886年5月14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50页。
[48]《附:与印度委员麻葛累问答节略》(1885年11月25日),《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77页。
[49]《致总署:论缅甸及洋药事》(1885年11月26日),《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第579页。
[50]《致总署:译送法士嘉尔芜来函》(1885年12月31日),《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第590页。
[51]《复曾劼刚袭侯》(1886年1月13日),《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第603页。
[52]《复曾劼刚袭侯》(1886年2月9日),《李鸿章全集34(信函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页。
[53][日]箱田惠子:《<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考析——兼论晚清外交之特性》,鹿雪莹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4年第二辑,第78—85页。
[55]《寄译署》(1886年5月29日),《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54页。
[5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85页。
[57]《伦敦来函Z字第四三九号》(1886年8月13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77页。
[58]《伦敦来电第五四七号》(1885年11月10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18页。
[63]《北京去函Z字第二六一号》(1886年4月18日),《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