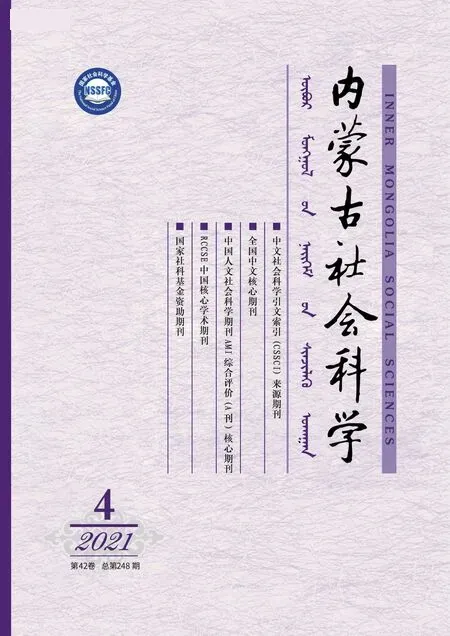空间、意象、存在
——论和瑛家族文学的时空体验与生命意识
张丽娟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文学创作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不同的地域环境与社会空间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审美关照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作家的生存状态、心理基质、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强化着作家的空间感知,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作家的创作风格上。外在的影响不断地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内化为自身的审美心理,形成不同的文化性格,从而产生了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同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一样,构建着自身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这种互动互为的统一关系,是近年逐渐被学界所关注的学术理论问题。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空间问题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以社会空间视角观照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已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是以空间理论或文化地理学对古代家族文学创作的跨界研究,表现出文学研究理论视界的开阔品质。
和瑛家族文学活动的社会空间及其丰富阅历使其诗歌创作在意象建构中表现出深切的时空体验和极强的生命意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均可谓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本文即在空间理论与诗歌美学的引领下,考察和瑛家族的诗歌创作,从社会空间和意象建构等多个维度透视和瑛家族诗歌创作中的时空体验和生命意识。这种跨界研究对于家族文学研究而言,不仅是方法论上的突破,更是对清代诗歌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和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及意义
(一)家族文学的确立是和瑛家族文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是家族文学形成的社会基础。“几千年中国文学演进的历程都与宗法制社会的发展相伴随,因此宗法制社会的特质必然对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精神层面,一是家族文化层面。这两端总的来说是统一的,因此‘国家’之‘家学’往往亦即‘家族’之‘家学’。”[1]宗法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家族成员的生存状态、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具有了相似性和趋同性,而且社会历史、地域文化对家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必然地反映在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上。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有了家族文学这一概念,特别是有清一代,在经历了元明清的朝代更替、历史流变后,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时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著述丰厚。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族层出不穷,据统计,仅北方少数民族中就有满族文学世家80家、回族文学世家14家、蒙古族文学世家约20家。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地域等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社会空间中的各种因素对家族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有着怎样的规律,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最终催生了家族文学研究的兴起。
对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流变中理解家族文学的发展,在具体的血缘、地域和社会背景中说明著姓大族的特点,进而在家族文化语境中阐释族亲文人的关联与互动,在具有地方化色彩的基层环境中感知文学生产的方式、过程及其成果,就显得尤为重要”[2]。
(二)跨界研究为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到目前为止,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家族文学研究主要包括家族文学的血缘性研究、地缘性研究,家族文学的社会性关联研究、文化性关联研究以及家族文学与文人生活姿态、经济关联研究和家族文学创作现场与成就研究。(1)参见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不言而喻,家族文学包含的内容决定了它的研究范畴、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同时也说明,仅凭单一学科的文学理论是不能满足家族文学研究需要的。文学研究需要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家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必须建构起适合其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此,“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地方性知识理论等可为研究提供一定的认知视角,但家族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和民族性的特点,故应以朴学的态度,重视文献价值,在此基础上兼容多元方法,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2]。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兼容多元方法、形成跨界研究,为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三)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充实的文献基础
前文提到,有清一代是家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创作的繁盛时期。“清中期出现了法式善、和瑛、博卿额等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因为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学修养,家族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3]和瑛家族在清代称得上是重要的文学家族。和瑛与其子壁昌、孙谦福、曾孙锡珍四代人历经乾隆至光绪六朝近150载,亲历朝野风云、足迹遍布四海。和瑛一族家学渊源深厚,其四代相承,高中进士者就有三人。因其文学创作的传承而形成了家族规模的诗歌写作,其诗风相袭,作品颇丰,皆有诗集传世。
和瑛为清代边疆重臣,《清史稿》称其“久任边职,有惠政”[4](列传140和瑛传P.4025)。但和瑛一生随仕途跌宕屡谪屡迁,入新疆、进西藏、踏遍喀尔喀。尽管生活艰苦、动荡,但也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和瑛留下了许多诗文著述,仅诗集就有《太庵诗稿》和道光刻本《易简斋诗钞》(共四卷,收录诗歌576首)两部。《太庵诗稿》虽未刊印,但收录和瑛诗作1060首,创作时间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止于嘉庆十五年(1810),历时50年。和瑛虽仕途起伏、生活跌宕,然一生笔耕不辍、勤勉著述,“可谓聿修厥德,终始於学者矣”[5](吴慈鹤《易简斋诗钞·序》P.1),令人感怀。
和瑛之子壁昌著有《叶尔羌守城记略》一卷、《守边辑要》一卷、《壁勤襄公遗书》、《兵武闻见录》、《牧令要诀》一卷,等等。留有诗集《星泉吟草》一部,共收录诗歌98首。
和瑛之孙谦福著有《桐花竹实之轩梅花酬唱集》和《桐花竹实之轩诗抄》。前者收诗百余首,后者收录诗歌268首。
和瑛曾孙锡珍承袭家学且才学出众,能诗善文亦勤于写作。虽诗无专集,但传至今者约200首。今有稿本《锡席卿先生遗稿》,其中含《奉使喀尔喀纪程》《奉使朝鲜纪程》《渡台纪程》等,均有诗附于后。他还主持编纂了《钦定吏部铨选则例》《钦定吏稽勋司则例》《八旗驻防考》《国朝典故志要》,文学造诣亦不输其祖。
和瑛家族成员以其共同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取向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使和瑛家族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成为可能,而且,作为清代重要的蒙古族文人家族,和瑛家族的文学创作为清代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对和瑛家族文学的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本文仅选取和瑛家族文学的汉诗创作,在社会空间与诗歌意象的建构中探究和瑛家族文学的生命意识。
二、社会空间中的生命体验
“人类真实的空间性存在是人自己构建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由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和习俗礼法构建起的前理智空间。作为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社会空间’才是理解和阐释存在论问题的应有语境,才是澄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真实思想平台。”[6]社会空间为文学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文学场域,在这个文学场域中,和瑛家族文学中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可以说,生命意识是探讨和瑛家族文学与诗人生命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交汇点。和瑛家族特别是和瑛本人因仕途坎坷,在被谪与迁转的无奈中曾八次进藏、七次入疆,更有踏遍漠北喀尔喀的经历。任职边疆的15年,是和瑛仕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经历。无论是政治境域的险象环生还是自然环境的变幻莫测,对于和瑛及其家族生存来说都是一次次无情的挑战,也强化了和瑛及其家族成员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成为和瑛家族文学诗歌创作抹不掉的文学记忆。
(一)“与行路难”相绾结的生命体验
川藏道上风景万千,奇观林立,但是留给和瑛印象最深的当属与中原迥异的民情风俗以及艰险崎岖的入藏蜀道,而与此蜀道密不可分的便是他进藏路上写下的众多诗作。和瑛在这些诗作中流露出的生命意识对于我们认识大清旗人对帝国声教的自豪与荣耀,以及他们面对艰难困苦时不动容的满怀豪情,都使得和瑛成为乾嘉诗坛上边塞诗创作当之无愧的代表性诗人。
川藏道既是和瑛的仕路,也是和瑛的诗路。和瑛一路前行,写下了大量诗篇。《东俄洛至卧龙石》《出打箭炉》《晓发彭错岭》等诗作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大自然的“险峻”、生命的“经历”以及灵魂的“感叹”。诗人通过抚胸惊恐、屏住呼吸、脸色突变等行为来表现自己突破自我、挑战生命极限的高峰体验,诗人此时是忘我的,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声感叹都构成了生命体验的最强反馈,他内心的波涛汹涌与磅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故而诗作被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度。因此,和瑛的入藏诗作正是通过这种自然之“险”和亲身之“历”达到了生命与灵魂的交融,突出表现了诗人的探险特质,展现了诗人追逐生命的高峰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在和瑛的《中渡至西俄洛》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除日抵雅州度岁》中,和瑛感慨“年华惊岁杪,行李半云端”[5](卷1P.13),诉说自己远离家乡、行走在艰险的川藏道上的无奈思乡和自我感怀,但是,他的诗作中并没有习见的悲苦之情。反而,在其尾联的“江山壮如此,除日等闲看”[5](卷1P.13)中感受到了诗人赋予诗作的豪迈。除了和瑛之外,这种对生命的体验在其家族成员的诗作中都有相似的体现。如壁昌行走在西域路上写道:“莫谓轮蹏苦,应怜汗马劳。”[7]他们在大清边地的荒寒与险峻中注重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其《四出玉门操》等都是表达此类情感的诗作。
(二)与苦寒边地相羁绊的生命体验
“地方感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维度,指自然对人的心理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人们借此‘烙印’来安排文化的空间布局和景观构图。”[8]地方感的探究包括“垂直空间向度”以及“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通过这两个维度研究和瑛家族川藏诗作中的景观布置,有助于我们探究创作者在景观设置中所潜隐的情感视野。如《小歇松林口》,诗人开篇就写到“晓渡三坝山,俯仰如桔槔”[5](卷1P.15),“俯仰”二字道尽山之险峻,后文之“兀坐篮舆中,冰珠生睫毛。忽下仇池底,别有洞天高。仙掌岫千仞,佛幢松万旄。泠泠涧泉响,而无鸟雀嘈”[5](卷1P.15)则铺陈描述山间如何行进,温度如何变化,自然界鸟雀之声对温度、高度变化的体现等,而诗末“小酌据胡床,亦足以自豪。幽人快奇兴,莫当寒虫号”[5](卷1P.15)表达的乐观精神,既是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昂扬风采的体现。
入藏之路艰辛,冬季大雪袭来,行路更加艰难。和瑛夜宿头塘,“罡风摇板庐,孤枕雪压脑”[5](卷1P.14),“挑灯不成寐,默坐纡怀抱”[5](卷1P.14),但因公务在身,次日促晨装。然而探路者报来的却是“且去问前途,冰镜滑如扫”[5](卷1P.14)。同样的情形在度山时诗人更有切身之感,正所谓“雪顶千迷道,冰城一线门。扶筇安稳度,天险不须论”[5](卷1P.15),在无奈与自慰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诗人乐观豁达的精神。
如果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9](卷3P.15),那么入藏之险犹闯鬼门关。面对“一剑寒暄割,西风扑面骄”[5](卷1P.17),诗人感觉到的是“冰坚银阙耸,雪卷玉尘消”[5](卷1P.17),当你希望快快远离这一切而“漫争驰快马”[5](卷1P.17)时,却不料“前路有危桥”[5](卷1P.17)。在翻越巴则岭时,眼前虽是“曳罢牦牛纤,声声舁老竿。石林穿有径,江涘俯无澜。坡仄羣羊叱,天空一鹗寒”[5](卷1P.17)的一派生活景象和自然景观,但诗人依然清楚地知晓“世途多险隘,行路岂知难”[5](卷1P.17)。
在和瑛的诗作中,这些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所传递出来的高、险、危、广阔、开放和壮观,事实上都是景观陈列带给读者的感受。诗人之所以这样分布景观,显然是受到藏地独特地理环境的影响,诗歌中独特的空间安排方式与其他诗作中的用典、地理意象一样,承载着诗人对藏地地理环境的独特感受。也正是因为多样的、复杂的描写方法和表现手法,清代川藏行旅文学才更值得我们不断去深入挖掘和细细品味。
和瑛家族不仅踏足西域边陲,而且曾去往大清王朝的四面八方。和瑛曾任职新疆、陕西、安徽、山东、热河等地,壁昌也曾履职西域、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多伦等地,锡珍曾东渡台湾海峡去往台湾,也出使过朝鲜。在行旅中,他们都写下了关于边关自然风景的诗篇。在这些诗作中,他们将自己置身于山水之中,心无旁物,在体悟大自然的美妙带给自己内心的愉悦中,体验着生命的存在、感悟着生命的价值。如和瑛之《黄湓浦渡江遇风》诗云:“远樯出没隔蓬岛,驶如点翅蜻蜓巧。金龙有灵施无患,奔流远称帆力饱。须臾震起吸江风,浩浩黄湓渡杯小。起视童奴面色青,灭烛危坐意悄悄。乾坤一噫本偶然,戏我何如戏坡老。楼船六丈万顷波,我觉身轻如过鸟。”[5](卷1P.2)诗人在渡江遇到大风时依然安之若素的生命体悟,是其生命意识中最可贵的乐观精神的呈现,这种精神不仅存在于和瑛的诗中,其家族成员也大抵如此。如壁昌吟咏多伦四季的组诗,呈现的是对寻常人看来苦寒的边地多伦的愉悦,传达的是在家族文学中存续的内在精神品质,是诗人自然的生命意态在认知自然地理环境后流淌于诗歌中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是生命意识中最为本真的一念初心,是生命体验沉浸在大自然与心灵的沟通与融合中的妙悟。
总之,在生存空间的不停转换中,和瑛及其家族不是扼腕慨叹、消极低沉,恰恰相反,面对恶劣环境的无情肆虐和仕途的跌宕起伏,他们总是坚守着积极乐观、豁达向上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对个体人生和生命的思索以及强烈的生命意识。
(三)与青灯古庙相望的生命体验
这类诗歌在和瑛家族文学中并不多见,因为无论进藏还是入疆,沿途中寺庙、佛塔之类的宗教建筑实属罕见。但在有限的诗作中,我们还是能够在对青灯古庙的书写中窥视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地对诗人产生着影响,特别是在诗人置身于时空转换的无奈与消解中。然而即便如此,羁旅途中的诗人在一边欣赏沿途的美景、一边经历着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带来的惊恐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将目光投向那些青灯古庙。和瑛并非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在其为数不多的关于寺庙的诗作中,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捕捉到寺庙作为终极关怀的一种象征唤起诗人对生命的观照,留下了为数不多却足以让我们感觉到和瑛生命体验的诗作,如“华夏龙蛇外,天西备六书。羌戎刊木鹿,儒墨辨虫鱼。寺建青鸳古,经驮白马初。何如苍颉字,传到梵王居”[5](卷1P.15)。
当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积淀于社会文化之中时,无论是在朝做官还是在野为士,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影响,其观念、意识或显露或潜在地圭臬着我们的行为,包括文学创作活动。在和瑛创作的《大招寺》《小招寺》及《布达拉》三首诗歌中,宗教并没有笼罩和瑛的身心,使其忘却当下,忘记个人使命。作为大清封疆大吏,和瑛在宗教类题材的书写中,依旧关注历史文化,所以在这三首诗歌中唐典被频繁使用,而且诗歌凝铸今古,以蒙古族诗人的身份,把藏地宗教寺庙中传达出的与汉家天下相关的唐柳唐碑、唐公主像、唐公主造银桥等政治文化遗迹以自注形式呈现出来,其间所彰显的凝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苦心,更是不同于一般诗作。
在去往他乡异地、苦寒边塞的艰难旅途中,诗人更需要精神的慰藉。“虎踞龙蟠地,西天第一门。双桥环古寺,半载访真源。信宿登云路,羁迟卧旅魂。开山三月暮,冰雪丈寻屯。”[5](卷1P.15)和瑛眼中的青灯古寺不过是与自己精神追求合而为一的象征符号。或者说,此时此刻的诗人早已将天地之无限、宇宙之永恒浸入到自己的有限生命之中。面对仕途坎坷、生活动荡,和瑛表现出惊人的平静,那种宠辱不惊已是他生命的常态。
正如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所言:“宗教的本质既非思维也非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它想直观宇宙,想聚精会神地从它自身的表现和行动来观察宇宙,它想以孩子般的被动性让自身被宇宙的直接影响所抓住和充满。”[10](P.30)和瑛用其一生去直观、去聆听、去渴望,然后获得一种平静,正是他精神世界中的生命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
三、意象建构中的生命追求
对于生命意识的追求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是人类对自身生命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前文我们对空间存在的和瑛家族文学的生命体验作了一番探析,接下来我们将笔触深入到和瑛家族文学的诗歌创作中,体察和瑛家族在其诗歌意象建构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追求。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审美范畴,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对意象作了非常形象而精辟的阐释,认为意象就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御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11](卷6P.28)。可见,意象是诗人将知识、研究、观察与情感相绾合的、具有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袁行霈先生将其理解为“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2](P.51)。“古诗词是我国古代特有且最为经典的文学形式,不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作者都通过选取巧妙的意象来丰富和传达诗词的含义和意境,所以对古诗词中意象的理解就成了解释整体意思的关键一环。”[13]和瑛作为清代蒙古族诗人,尽管其诗歌创作有其自身的、民族的风格与特点,但我们仍然不难品出其中的唐诗味道。和瑛在《诗囊》中写道:“梁园杜荀鹤,一杴泥可叹。更拟香山老,乐地黄居难。数数詅痴符,诗名怕野干。国称诗坛将,何独师黄韩。”[5](卷2P.36)和瑛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诗学理念正是性灵派所主张的诗学理论,尤其是对诗歌意象的追求,在其《易简斋诗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少量的应和诗作外,和瑛在《易简斋诗钞》中的大多数诗歌均为纪游诗。因而,诗歌意象的构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之物,一类是作为西域空间符号的边塞关隘。
“百草俱腓日,亭亭菊放黄。延龄堪作客,正色独凌霜。止酒留仙骨,颠茶助冷香。”[5](卷3P.47)在和瑛笔下,自陶渊明以来清逸悠然的菊花到诗人这里,依然因霜雪的侵凌而显现着一派正气;“一点陈根焰,中涵剥复机”[5](卷3P.57),萤火虫微弱的点点光焰,感发出诗人积极的生命赞颂。这里的所咏之物菊花和萤火作为意象,传递给我们的是诗人生命追求中的傲然正气和不懈进取的精神。和瑛在咏物之中自抒怀抱,将自己的生命意识与物之意象蕴涵于一处,以人化之物的“意格”标举诗境。另外一首萤火诗作“脐火纤如粒,安能照夜清。孤光时黯淡,阴爝柱分明。自衒功何补,含章觉有情。乘时归大化,如棘亦虚名”[5](卷3P.57),同样“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14](卷17P.860)。
此外,和瑛诗歌中频频出现、反复吟咏的还有“松”和“马”的意象。“冬雪厉松柏,秋霜汰蒲柳。”[5](卷3P.55)“清秋月照松间雪,雪月交光松心壮。四时盘错不改柯,夭矫虬龙茁无恙。”[5](卷3P.55)“庭有参天柏千本,翠螺松涛响半空。绕屋盘桓刚半载,后凋知耐岁寒风。”[5](卷3P.43)“灵谷池中影,亭亭写照松。禅枝龙虎迹,梵叶雪霜容。”[5](卷1P.2)“我心悬旆鹿马东,岁寒不凋摩顶松。林间六白决耳牖,照天蜡烛梦苍穹。”[5](卷2P.40)“天风吹落天山高,天星毓此天马骄……东野子,九方皋,权奇逸力空群豪。岂如幻青知马性,性同君子相独超。”[5](卷3P.56)松柏、骏马之意象正是诗人“岁寒不凋摩顶松”[5](卷2P.40)、“权奇逸力空群豪”[5](卷3P.57)之傲骨雄心的感性呈现。正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所云:“诗人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15](P.6)对此黑格尔指出:“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呈现出来了。”[16](P.49)因此,在《马衔鱼歌》中频频出现的“酒”“鱼”“马”“鲲鲸”“龙种”等作为诗歌意象,随时流露出矫矫不群的神气和风驰电掣般的动作变换,裹挟着一种力量,随着诗意的展开蓬勃而出,而这种蓬勃正是因诗人生命意识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而生发感动出来的。
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壁昌以回疆平定随钦差大臣那彦成往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道光八年(1828)返回。道光九年(1829),擢头等侍卫,充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此后,壁昌历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第一任叶尔羌参赞大臣、乌什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等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陕西巡抚、后任福州将军为止。由京城至西域四进四出,其间众多西域关镇意象出现在壁昌的诗作中。玉门关就是壁昌笔下的重要意象。其七言排律《出嘉峪关口占》之“山环沙绕玉门关,嘉峪云横不见山。山壮关壮人亦壮,驰驱万里如等闲”[7]诗句,写出了诗人初出嘉峪关玉门关的情景及诗人的雄心壮志。而《入玉门志感》写下的则是四出玉门关又返回的疲惫。“守边十八载,八度玉门关。戚友多不见,家园别后艰。老妻添白发,稚子改童顔。丁年初奉使,皓首始生还。”[7]玉门关这一意象在诗人笔下承载的已经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关隘,而是像壁昌这样从有为青年到衰年将领一生的荣辱。玉门关以其沉默记载岁月、也见证岁月。诗人对玉门关感慨万千,不久又写下了“玉门初出兮浩气凌云,玉门初返兮戈壁蒙尘。玉门再出兮天意回春,玉门再返兮旱海沙深。玉门三出兮壮志犹存,玉门三返兮衰老临身。玉门四出兮再鼓精神,玉门四返兮调抚青门”[7],这是他四出玉门关时的慨叹。
和瑛家族诗歌中除了上述两种意象外,在对圣贤名士的追怀仰慕中构建的意象群体也寄寓着他们的生命意识。咏物诗中的意象常常裹挟了诗人自己的生命意识,以人格化的物的状态呈现主体写作者的审美趋向、人格标举,而山河关镇中的意象凝定的又是岁月流风中的英雄情怀。在不一样的时光里,诗人对游走在英雄生命深处的光阴故事有着不同的生命内涵和生命追求。和瑛曾作有《题醉翁亭二首》。诗云:“西湖曾宴四贤厅,又到滁阳访旧亭。名醉名贤同不朽,谁知翁醉是翁醒。淮北江南试一官,太平丰乐共闲闲。何当六一先生照,写入环滁雪满山。”[5](卷1P.5)醉翁亭因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知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欧阳修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与之相关的故实和典故也会成为文人叹咏的主题。滁州有欧阳修在此做过太守的历史事实,故而欧阳修与醉翁亭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此地以人闻名,渐渐成为皖地重要的文化名片。清代蒙古族诗人和瑛对于此地的反复吟咏更是加深了这张名片所蕴含的文化积淀与意蕴。
值得重视的还有和瑛创作的咏史诗。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和瑛在四川按察使任内写下了17首咏史诗。这17首诗歌分别咏叹历史上的功臣,如赵上卿蔺相如、淮阳侯韩信、飞将军李广、大树将军冯异、好畤侯耿弇、雍奴侯寇恂、伏波将军马援、节侯来歙、虎威将军赵云、晋太傅羊祜、文贞司空魏征、梁国公房玄龄、郑国公李光弼、凤阁侍郎张柬之、白衣山人李泌、起居郎褚遂良、文贞太傅崔佑甫等。在这些留名青史的人物身上,和瑛用他们的生命体验涵育着自己的生命意识,在其诗歌意象的建构中书写着自身的生命追求,在生命意识的觉悟中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美学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以构成更高人生境域与‘本真’生命域和审美域作为审美活动的极致,把构建和熙融洽、雍容圆润的人生作为最高审美之维……熔铸光明的人生和还原自由任运的生命态势,视宇宙自然为可居可游的心灵家园,以圆融无碍之心于平常生活中体悟天地大化,乃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宗旨。”[17]
结语
对生命意识最本质的认识就是对生与死的领悟和体验。和瑛家族文学表现出的生命意识一方面源于其民族性,另一方面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空间独特性。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大自然的变化无常赐予这个民族以坚韧、豁达、向上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品格,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和“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对和瑛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思想文化同时也构成了和瑛家族文学存在的社会空间。在和瑛的观念中,生命的意义并非生命本身,而是生命对于其外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回顾历史,也许正是这种生命意识才使和瑛以及和瑛家族得以拥有“思精体大,亦复趣远旨超,自成一家”[5](吴慈鹤《易简斋诗钞·序》P.1)的地位,使其成为清代除法式善之外最富影响力的蒙古族汉文诗人。和瑛家族以其不可低估的文学成就以及自身具有的民族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属性,成为家族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瑛家族文学对边疆文化建设、对民族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和瑛家族文学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