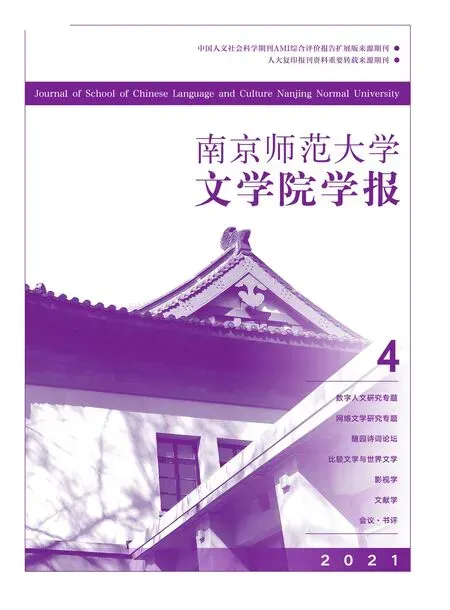漫游群体、异质情欲、碎片叙述
—— 刁亦男电影的文本建构与题旨解码
钱祝良 颜 彬
(1四川传媒学院 编导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0;2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 300387;3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2014年的《白日焰火》先是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一举打破国内艺术电影的票房魔咒,一时间,使得90年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独立制作电影的“作者”刁亦男走向主流视野当中。近年来,商业性、娱乐性、世俗性的电影充斥银幕规模化的市场语境中,刁亦男依旧一以贯之的关注着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聚焦于边缘个体的情感焦虑,契合着第六代导演们在地抒写的创作倾向,积极与商业“类型”联合的同时,在电影文本的建构与主题表达上,自始至终的坚持着强烈的“作者表述”。
从早期的商业化、工业化模式的好莱坞电影来看,无论是在情节编排还是剪辑方法上有着一定成规化的创作范式与语法结构,“类型”成为电影生产与俘获观众的商业利器,“作者”沦为规范创作的执行者。而“作者论”的提出正是对于公式化、定型化的商业类型电影的反叛,突出、强调电影中“作者”个性化风格与思想的表述。“作者表述强调导演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在其作品中对其世界观进行自由地、创造性地言说;导演应在主体、题材、语言等方面附有创造性;导演应当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性。”[1]纵观刁亦男的创作历程,无论是早期被市场拒之门外的独立制作电影《制服》(2003)、《夜车》(2007),还是“作者+类型”标签下商业片外壳的艺术电影《白日焰火》(2014)、《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以下简称《南方》),刁亦男始终关注着现代社会中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况、聚焦于情感与欲望杂糅的复杂人性,融入着个人视域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表达,一定程度上趋同于第六代导演们的创作规律与创作倾向。然而,不同于第六代导演们所关注、所聚焦、所呈现的典型环境以及其中的典型人物,刁亦男则是将视觉的中心与重心纯粹的限定在底层群体的自身。换言之,如果说第六代导演侧重的是典型环境与典型群体因果相关的外在直观的矛盾,而刁亦男的重心则是底层群体本身的内在冲突。刁亦男充分的发掘底层的“漫游身体”自身的内在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聚焦呈现个体自身“暧昧不清”的情感与欲望纠葛;以其理性、疏离的作者立场,反情节、零结局的碎片叙述方式,引导着观众凝视着多义的社会现实、复杂的人性深处,喃喃自语地表述着“语焉不详”的现实真相。
一、“反饰身份”的漫游群体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同时,人的命题在历经文革的禁锢后重新回到主流的视野当中,人的人性、情感、身体、尊严、价值得以复归。“身体”作为人“在世存在的载体”浮出历史地表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人的焦点。遗憾的是8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身体的表达上往往是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2](P85)80年代的电影不约而同地涉足历史深处,深入民族心理结构,将其中被压抑、被规训的“身体”从中予以一定程度的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甚嚣尘上地改造着社会的现实图景,改写着置身其中的人的身体与心理。不幸是,在快速变革的90年代,被解放的个体迷失在自由、宽广的现代性建设的蓝图和理想当中,呈现出典型的身体跟不上思想的现实景象。在9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第六代导演们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跃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改写的人,集体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截取当下的时间与空间,借由个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困境、情感问题指涉着社会转型变迁中的症结。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现代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只争朝夕”的迫切与时间焦虑。作为后景的现实空间在快速切换,而作为前景中的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被延宕、被接受、被适应于社会语境的变化。以至于在被改写的时间差中,造成直观的现实景象是人的身体与心理在快速切换的现实空间图景中被动地漫游与流变,迷失自我以至于“身份不明”。在不可逆转的时间焦虑中,呈现出现实生活中人的身份流变与身体漫游的焦虑。
纵观刁亦男的四部电影,与第六代导演相仿,自始至终关注着在现实生活空间中的身体漫游群体。根据本雅明的说法,“只有那些流动者和漫游者,那些不被城市法则同化的人,才能接近城市的秘密”,漫游者是“公共场景的经验象征”。[3](P131)《制服》中假冒他人交警的身份四处收取违规费用的裁缝王小建、身兼陪酒女的音像店员郑莎莎;《夜车》中辗转相亲的丧夫女法警吴红燕、意欲复仇的困顿青年李军;《白日焰火》中工作失职被辞的刑警张自力、洗衣工吴志贞、碎尸案中的活死人梁志军;《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误杀警察的通缉逃犯周泽农、陪泳女刘爱爱。他们生活在刁亦男镜头之下的现实空间中,普遍有着各自的生活困扰与情感困局,或主动、或被动地漫游其中,他们的身体,各自承载着生活的秘密。
然而,不同于第六代导演作品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式的漫游者形象,刁亦男聚焦的漫游者具有着外在直观典型的同时,兼具着内在奇观化、异质性的“反饰”(1)“反饰”修辞格被定义为:“在连贯的语流中,用前后相继的语言符号,从意义对立的两个方面说明同一事物的一种修辞方式”。参见谭学纯、濮侃、沈孟璎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65).身份。其中《制服》中假冒交警的裁缝王小建、《夜车》中性压抑的女法警吴红燕、《白日焰火》中失职被辞的刑警张自力,活死人梁志军;《南方车站的聚会》中误杀警察的通缉逃犯周泽农,目标三十万赏金的陪泳女刘爱爱。无一不是将真假、善恶、黑白、对错等二元矛盾对立的冲突“反饰”于个体一身。矛盾对立冲突内嵌于个体自身的错位感、不适感、颠覆感,将其悬置于断裂的现实缝隙中以至于身份复杂,同时“挑拨离间”了观众的心理预设与信息接受,从而使得观众对于人物的认同感暂且“保留意见”而选择中立。身份“反饰”的双重性无疑是个体矛盾性与戏剧张力的双重强化。其中,《制服》《夜车》《白日焰火》《南方》皆存在警察这一形象与身份,然而刁亦男电影中的警察与传统的集体经验意识中象征着“国家机器”化身的形象相去甚远。这些警察混迹于发廊妹、洗衣工、过磅员、小卖铺老板、陪泳女、摩的司机等混杂的底层群体的周遭,漫游在音像厅、游戏厅、洗衣店、溜冰场、野鹅塘等较为边缘的现实空间。《制服》中王小建“假冒”的交警、《夜车》中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性压抑”的女法警、《白日焰火》中落魄失职甚至于“强暴”他人的刑警、《南方》中被误认为摩的司机的警察们,无一不与传统认知经验中正义、高大、伟岸、精英的执法者形象相悖。二元对立的奇观化、异质性的“反饰身份”使得这些警察更加具有着被社会意识和集体经验抛弃的精神状态,褪下外在视觉象征的“制服”,成为《南方》中“泯为众人”的警察,同其周遭的人群如出一辙,沦为没有身份标识的漫游“身体”,更甚者成为《南方》中动物园的动物们。
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方式”[4]。而本己身体与他者身体的共同存在才能完整的构建出对于世界的经验与认知。如果说“反饰身份”是刁亦男对于银幕之上“身体”的内在修饰,那么对于“身体”漫游互动中主体间性的建构成为他们撞见秘密与声讨真相的肇始,亦是本己身体在遭遇他者身体的指认中寻求自我认知、身份认同,对抗现实断裂与“反饰身份”的唯一路径。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身体”在漫游中精疲力尽。刁亦男曾这样阐述他电影中的主人公:我的所有人物都游离在现实与梦幻的边界上。他们没有稳固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投机取巧地苟活着[5]。《制服》中以他者的交警身份四处游走、虚妄生活的裁缝王小建,在与郑莎莎的身体间的交互中间歇性、阶段性地找到了自我的身份定位,而在作为裁缝的王小建身体上依旧遭受着生活的不堪;《夜车》中穿行于性压抑的精神黑夜的女法警吴红燕,无论是对相亲对象强暴行为的反抗、对隔壁房间小姐的警告与接触,又或者是与婚托之间的交易、与多次跟踪自己的困顿青年李军最终身陷情欲,“身体”间的种种行为与能力,无一不是吴红燕那副性压抑与情感困顿的“身体”寻找与指认自我的努力;《白日焰火》中辗转各地调查碎尸案寻找真相与找回身份的前刑警张自力,不断接近受害者的妻子吴志贞,情欲交织中发现案情的真相,最终将吴志贞出卖绳之以法。而无论是王小建、吴红燕、张自力、周泽农,还是郑莎莎、吴志贞、梁志军、刘爱爱,无一例外地他们的“身体”游离在现实与梦幻、理性与情欲、肉体与灵魂、犯罪与救赎的边缘和缝隙之中,观众亦是在无意识当中被导演刁亦男移置于银幕中的“身体”之上共同体感现实。刁亦男正是将游离于现实断裂之中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统一于“反饰身份”的漫游身体,并将其挟持在银幕之上,共同构建着其影像空间中矛盾、复杂的漫游者形象。漫游的“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载体”,负累于漫游身体之上暧昧不清的异质情欲、语焉不详的碎片叙述的作者表述呼之欲出。
二、“暧昧不清”的异质情欲
作为电影“作者”的刁亦男,始终凝视着现实断裂缝隙的深处,关注着身处其中的漫游“身体”,将“身体”本身潜在的双重性与矛盾性“反饰”诸身。意欲纯粹表现人性复杂和情欲异质的他并没有局限于典型环境造就典型人物的直观传统经验。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中身处70年代初“文革”期间、学校停课的马小军、刘忆苦;路学长的《长大成人》(1997)中海外归来而无所适从的理想主义者周青;贾樟柯的《小武》(1998)中“丢失”爱情、亲情、友情而漫游的小武;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2000)中进程打工丢失自行车而遭遇种种的农村少年阿贵等等,皆是与时代环境和社会语境“因果相关”的典型时代产物。与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无意诘问典型环境的刁亦男,将“漫游身体 (前景)—空间(后景)”的全景深式图景进行后景的虚化,将观众的视点从过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思维模式中解放,单纯地聚焦于漫游身体的自身,弱化“环境”对于“人物”的改写的矛盾冲突,割裂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纯粹地挖掘人物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与戏剧张力,塑造复杂、奇观、异化的“反饰身份”的漫游者形象,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状态,无关乎外在典型环境。在这一层面上,刁亦男电影的整体艺术特征与强调表现人物内心的欧洲现代主义电影具有一定亲缘性。一方面,刁亦男着重对于“反饰”身份自身矛盾性的挖掘。另一方面,在漫游的身体交互中,刁亦男将漫游的“身体”——人物置于非常规、戏剧化的人物关系当中。
《制服》中的假交警王小建与身兼陪酒女的音像店员郑莎莎,二人的“身体”相识于交警和音像店员的身份中,身体漫游中简单的闲言碎语后的无爱之性,无疑是超出常规认知经验的爱情基础的“暧昧”。在这里,“暧昧”并非是一个贬义词,“暧昧”指的是异质性东西相反相成,指的是矛盾存在的合理性,指的是事物的辩证关系,指的是世界及其事物的不确定性。[6](P359)《制服》中假交警与陪酒女二人在洞悉彼此的身份后却又心照不宣的选择维持假象,使得本身就暧昧不清的“情”与“欲”亦真亦假,而影片的开放式结局,更是使得非常态的异质情欲更加扑朔迷离。《夜车》中女法警吴红燕在情感与欲望的双重压抑之中克己复礼,原本奇观、异质的“执法者”的身份让其自身承受着孤独、冷漠与疏离。乘坐夜车往来于相亲会中,在暗夜之中寻求情欲的出口,然而先是相亲对象的意欲强暴让其愤然离去,后是撞破婚托身份后却选择花钱让婚托对象陪伴左右,情欲在一次次的尝试中陷入精神黑夜。讽刺的是住在隔壁游走于法制与道德边缘而夜夜笙歌的小姐,却成为法律执行者吴红燕正视自我、释放情欲的镜像。同样,作为“杀人犯”的丈夫李军,在社会道德的经验意识中,同样被动地身披了杀人犯相关的边缘身份,是社会经验中难以摆脱的危险与不安。意欲复仇的李军跟踪执法者吴红燕,使得吴红燕在不明身份之下与李军发生情欲,异质的旖旎充斥银幕。而当吴红燕意识到李军身份以及目的之后,却选择沉默并未揭破,甚至对于李军的“强暴”也并未反抗。《白日焰火》中以案件调查为叙事线索,在张自力与吴志贞非常态的感情展开中,裹挟着的是吴志贞与梁志军、洗衣店老板之间复杂、扭曲的情欲。同样在《南方》中,横亘在逃犯周泽农与陪泳女刘爱爱之间的是那三十万奖金,二者在彼此利用与被利用,背叛与被背叛的关系当中情欲交织。无论是王小建与郑莎莎、吴红燕与李军,还是张自力与吴志贞、吴志贞与梁志军、周泽农与刘爱爱,奇观“反饰”的身份加上“非常”的关系,让原本“人之常情”的情感与欲望,异化成了道德、法律、理智、情感都难以对簿公堂的无证之罪。反饰身份的群体之间在非常态的关系中情欲交织,是情感为先激发了欲望?还是欲望渗透了情感?情感又何处、何时而生?欲望又因何而起?不论是对于人物自身,还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皆是模棱两可。意欲纯粹表现人性复杂和情欲异质的刁亦男,将“反饰身份”付诸于“非常”人物关系,逻辑难以闭合,情感难以自洽,有的只是“暧昧不清”的异质情欲蔓延的漩涡。
如果说反饰身份与非常关系是异质情欲的根源,那么“异质”的空间就成了异质情欲的见证。《制服》中破败封闭的钟点房;《夜车》中无人问津的水库观测站;《白日焰火》中高空的摩天轮;《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野鹅塘湖的小船,是刁亦男电影中身体情欲的体感之处。一方面,钟点房、水库观测站、摩天轮、野鹅塘等空间疏离于主流的生活空间,造成观众认知经验的失帧而对其产生陌生感与异化感;另一方面,有别于传统直观经验中常态的情欲体感空间的私密私有属性,公众空间的私密私用的本身即预示着情欲的异化。其中《制服》中几次三番追问是否加时的服务员,《夜车》中敲墙提醒隔壁小姐的吴红燕、让李军出面修理工具的工友,外界的中断行为是对异质情欲的重点突出,更是对情欲的异化的警示。
不难发现,在对于“异质情欲”的展现当中,刁亦男迷恋于“性”与“暴力”的交织与杂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造端于男女”——男女之性是作为宇宙“原发生命机制”而加以揭示,它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从根本上回答了宇宙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7]。诚如张汝伦在谈论梅洛·庞蒂有关于“身体-主体”时所言,“一个身体寻找另一个身体,性关系是人与人共存与相连的基本关系”,[8](P353)一方面,“性”构成了刁亦男电影中身体最原始的相连与交互,但是无端的性或者说无爱的性使得刁亦男电影中的性处在于“爱”与“欲”的中间地带而模棱两可,暧昧不清。另一方面,“暴力”作为与“性”亲缘的肉身之欲的另外一种表征和范式,性与暴力的交织与杂糅,使得原本已然处于爱与欲中间模糊的性更加的异质化。《制服》中王小建与郑莎莎没有感情基础的“性”遭遇客房服务员软“暴力”地追问是否加时,郑莎莎在工作中遭遇顾客的肢体上的推攘以及言语上羞辱的“暴力”,即使是刁亦男并未展现郑莎莎工作中的“性”,但是对于观众而言,不难想象郑莎莎在工作中可能同时遭受的性与暴力。在这样的处境中的郑莎莎面对温柔的王小建的“性”似乎能强行给与一定合理性与逻辑性的接受,但是并不能改变其异于常态的情欲的事实。如果说《制服》中“性”与“暴力”并未真正意义上地同时出现,那么《夜车》中作为杀人犯丈夫的李军对于作为执法者法警吴红燕的“强暴”,无疑是“性”与“暴力”交织杂糅对于“异质情欲”的一次强力证明。再者,《白日焰火》中张自力对于前妻的“强暴”未果,以及在高空的摩天轮中对于吴志贞的暴力的性,又或者是洗衣店老板对于吴志贞的“求爱”未果,处处充斥“性”与“暴力”的旖旎与发生。《南方》中逃犯周泽农与陪泳女刘爱爱的野鹅塘里的船上之“性”,以及刘爱爱遭受陌生男子的“强暴”时候被周泽农的“暴力”解救。纵观刁亦男的四部电影作品,“性”与“暴力”在作为商业类型元素吸引着观众的视觉体验的同时,亦是刁亦男对于“异质情欲”的呈现,完成观众心理感知与作者艺术表达的场域和通道。
模棱两可的情欲附着于“反饰身份”的身体,在“非常”的关系中蔓延于不合时宜的异质空间,在“性”与“暴力”的交织杂糅之下,名正言顺的暧昧不清,而这一切,皆是刁亦男意欲表现人性复杂与情欲异质的目标路径。不仅如此,刁亦男电影中如出一辙的开放式结局,更让观众如同角色一般,在暧昧不清的异质情欲的漫游中“身体”精疲力尽。刁亦男更是在将人物置身于理性与情欲的暧昧边缘的同时割裂了观众的理智与情感,使得观众在犹豫和疑惑当中,同情但不移情。犹豫与疑惑的共存,理智与情感的中立,将观众推向思考人性复杂、情欲异质、现实多义的地带。
三、“语焉不详”的碎片叙述
援引李显杰对于叙述话语的论述,“叙述”不仅具有“讲故事”的含义,它更侧重于对“怎样讲”的概括。换言之,“叙述”作为叙述主体(作者-隐含作者-叙述人)的话语,引导着观众或读者进入情节,并企图用自己的声音(解释和评价)来影响读者或观众。[9]在传统的电影叙事中,创作者沉溺于连贯、闭合的戏剧性情节结构中,明显的“人为”痕迹下——依据故事(事件、情感)的“因果关系”制造、编排“蝴蝶效应”式的叙事范式。作为故事之外旁观者存在的观众,在创作者的“主观”论述中先验地信以为真,沦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然而,在刁亦男的电影整体叙事中,有悖于“蝴蝶效应”严丝合缝的叙事链条和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情节、情感逻辑的因果关系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与疏离。作为相对客观描述者的刁亦男,碎片化、“反情节性”的叙述行为、立场、态度,将斑驳陆离、人性复杂、情欲异质的现实图景呈现于观众的视域当中,打破故事(事件、情感)本身的因果关系,破除观众“蝴蝶效应”的梦幻错觉,去关注、凝视、反思现实生活中破碎、断裂、异质、插曲的背后所隐含的现实真相。
从刁亦男早期的两部独立电影《制服》《夜车》来看。在《制服》中,王小建与郑莎莎漫游在街道上、音像店、小卖铺、钟点房等碎片化、生活流的“反情节性”叙述,以及缺乏详实的情感基础、非常规情感逻辑的交往中,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的断裂与疏离。同样在《夜车》中,吴红燕来往于相亲会,游荡在城市之中,李军因杀人犯家属的身份而被调离工作,被亲友断绝关系等一系列的碎片化的故事情节在时间的流程中稀释,以及刁亦男电影中一以贯之的缺乏详实的情感基础、非常规情感逻辑中的情欲异质,无一不在凸显着刁亦男叙事中的“反情节性”叙述与“因果关系”断裂的碎片叙述话语。而“作者+类型”标签下的《白日焰火》《南方》已然是刁亦男借助类型元素一定程度上迎合观众和市场的电影作品。但是刁亦男却并未落入类型电影的传统叙事模式中,依旧坚持着反情节性的叙述话语。《白日焰火》中,犯罪悬疑的碎尸案叙事主线流于张自力与吴志贞、吴志贞与梁志军等碎片化、生活流的叙述当中消解;《南方》中,抓捕通缉犯的犯罪叙事主线同样被周泽农与刘爱爱的互相利用、周泽农与盗窃团伙的恩怨复仇以及盗窃团伙各自心怀鬼胎的发散式的叙述中解构。环环相扣的“蝴蝶效应”式的传统叙事,在刁亦男的“反情节性”叙述中支离破碎,在异质情欲的展开中因果断裂,迫使着观众始终滞留于“叙事”之外,冷静、客观地“隔岸观火”。
生活流、碎片化的“反情节性”叙述,故事(事件、情欲)本身因果关系的断裂、疏离,是刁亦男电影中显而易见“语焉不详”的叙述话语。此外,纵观刁亦男的四部作品,毫无征兆的插曲以及开放式的结局亦是刁亦男电影中碎片叙述方式中一以贯之的存在。
《制服》中前往工厂替父亲登记的王小建,突遭不满工厂合并的工人们的打砸事件,以至于被迫接受警察问讯;陪酒女郑莎莎毫无征兆的被客人推攘嘲笑其“装纯”的长达一分钟的长镜头,《夜车》中得知李军意欲谋杀的吴红燕奔跑逃离的路上,看到的路边被车夫不停鞭打的马;李军不知何故的色情消费却突遭类似仙人跳的一顿毒打;《白日焰火》中突然间出现在居委会走廊上的马;张自力网吧调查时,一青年玩游戏走火入魔,发疯般咆哮地砸着灭火器;夜总会老板娘大笑中掉进浴缸里哭;《南方》中周泽农妻子杨淑俊的羊角风病症、躲避周泽农追击的刘爱爱误闯不明集会遭到强暴。这些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的“意外事件”,是游离叙事主线之外的“插曲”,却是现实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整体性地来看四部作品中毫无征兆的插曲,在刁亦男的电影世界中具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制服》中的被推攘嘲笑的陪酒女郑莎莎,在《夜车》变成了那个反抗嫖客致死而被执行死刑的张玲玲,在《白日焰火》变成了杀死夜总会老板的吴志贞,在《南方》中变成了陪泳女的刘爱爱。《制服》中郑莎莎被客人推攘嘲讽的一分钟,弥补了《夜车》中张玲玲杀人动机的呈现;《夜车》中张玲玲的审判与执行填补和预示了《白日焰火》中吴志贞的命运。《制服》中被警察问讯以及故事结尾被警察发现假交警身份而逃跑的王小建,分别变成了《夜车》中被人逼在墙角毒打的李军,《南方》中变成警察追击的通缉犯周泽农。《夜车》中那匹路上被残忍鞭打的马“跑”到了《白日焰火》中居委会的走廊中。刁亦男在自己的电影中建构着他所观照与体认的“故事世界”。对于“马”这一意象的使用,刁亦男在采访中的回答是:“给自己带来的第一反应是不安?是对暴力的恐惧?我们应该借此反观一下我们生活中有多少这种隐性的暴力。”[10]有违叙事逻辑“毫无征兆的插曲”是刁亦男“语焉不详”的碎片叙述手段之一,更是刁亦男对于现实断裂、碎片、意外、暧昧、不安的生活哲学的注脚。
传统的叙事法强调:终结是叙事拥有“迷人”秩序的形式标志,为了不造成令人困扰的阅读效果,故事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结束[11]。但是,刁亦男四部作品皆是“特定”的以开放式的结局收场。《制服》中假冒交警的王小建最终被警察发现,在逃脱追捕奔袭的长镜头中结束,结果未知。《夜车》中得知李军要谋杀自己的吴红燕,在与李军相视的长镜头中结束,结局同样未知。《白日焰火》中吴志贞指认凶杀现场的小区楼顶之上,张自力不顾消防员的劝阻释放着烟花,在晴天白日中无力反抗。《南方》中举报周泽农获得奖金的刘爱爱并没有将钱存入银行,毫无征兆、甚至有违叙事逻辑,找到周泽农的妻子杨淑华而止。刁亦男开放式的结尾是没有答案、没有论点的“零结局”,有的只是“语焉不详”的现实描述——生活就是如此,同时仍在继续。刁亦男在采访中这样表述:“我不会在创作之前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诉说或阐释者的位置上,等作品出来之后给人一个清晰的答案和结果。那种东西我并不喜欢,也觉得很浅显。可能我更愿意让作品缓慢地释放出味道来,更开放,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启示。生活什么时候给过我们准确答案啊?可能对生活本身也需要抱有敬畏感,别你自己写东西总结出一个道理来。”[12]正是如此,刁亦男开放式的零结局,意料之外的结尾残余、“欲语还休”,将广义的、复杂的生活解读的权力留给了观众,“强制性”地让观众凝视复杂的现实生活,思考现实的真相与本质。
反情节性的叙述、因果关系的断裂、毫无征兆的插曲以及开放式的零结局,共同建构着刁亦男电影叙事中“语焉不详”的叙述话语,而这一切“人为”的叙述话语的最终诉求——意欲表现斑驳陆离的多义现实,含糊其辞地描述着现实生活“语焉不详”的本质。
四、 总结与思忖
“作者+类型”标签下的导演刁亦男,“类型”不过是其电影景观中外在直观的形式元素,究其创作风格、立场、态度,强烈的作者意向、作者表述是刁亦男的内在根本。相较于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情境建立以及主题表达,刁亦男无意对简单、清晰明了的现实进行论述,而执着于多义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人性边缘。反饰身份的漫游群像、暧昧不清的异质情欲、语焉不详的碎片叙述,共同图绘着刁亦男电影的文本建构,抒写着刁亦男电影的题旨解码。在刁亦男的电影世界中,观众得以置身于现实提纯的银幕时空,附身于底层“漫游者”的身体穿行,体验“非常”关系的人性边缘,“异质”情欲的暧昧不清,凝视“断裂”现实的纵深之处,聆听着“语焉不详”的碎片叙述,思考着多义、复杂的现实生活。
在当今商业性、娱乐性为标榜的电影市场语境中,80年代电影聚焦历史深处,深入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反思和询唤个体意识与自我指认;90年代以及21世纪开始的十年,电影关注社会现实,观照置身其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的盛景已然渐渐淡去。刁亦男的创作范式,当然更多的需要从经过市场检验后的《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两部电影来看,刁亦男无疑是当下市场环境中将艺术表达、现实承载与商业市场成功黏合的典型。回归电影艺术与商业如何兼容的这一争论已久的命题当中,并非是要评判和遴选立场问题,而是为了希冀电影创作者不断地思考与努力,在电影艺术的发展中兼容并蓄地引领市场,推动中国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