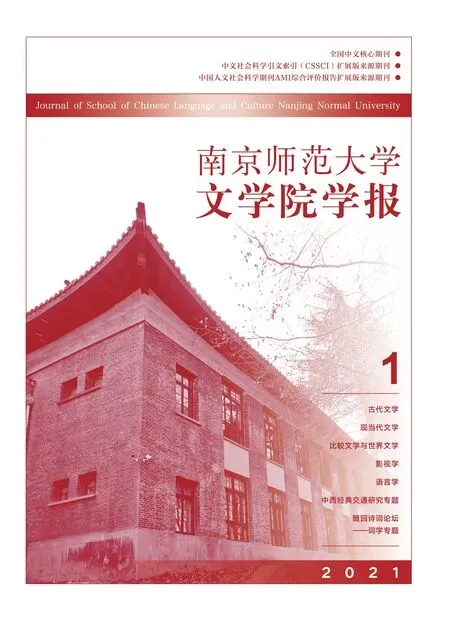也谈“过于”“太过”的副词化历程与动因
常志伟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语言科学》2009年第4期刊有胡丽珍、雷冬平先生的《说超量级程度副词“太过”的形成》一文,《华中学术》2014年第1辑刊有饶琪、牛利先生的《“过于”和“终于”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语文研究》2018年第1期刊有殷树林、高伟先生的文章《超量程度副词“过”“过于”“太过”的形成与使用特点》。三篇文章均对超量程度副词“过于”“太过”的词汇化历程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成词机制,读后深受启发。但细读之后,发现三文对副词“过于”“太过”的出现时代及其副词化动因机制的探讨结论相互龃龉,故对该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现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以正于方家。
一、“太”“过”“过于”“太过”在现代汉语中的副词用法
(一)“太”与“过”“过于”
1.“太”
“太”自古及今功能单纯,一直是超量程度副词,在现代汉语中既可以修饰单音节形容词,也可以修饰双音节形容词,有时还可修饰动词短语。从语用角度看,随着其后谓词性词语感情色彩的不同,其功能大致又可分两类:A.当修饰褒义性中心语时,突出其褒义色彩,表示该谓词性中心语所表示的性状程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比预期还令人满意。B.当修饰中性或贬义词语时,则体现贬义色彩,即在说话人看来,该性状或动作超出了所应有的程度之极限或超出了人们所能容忍的程度,隐含着说话人不满、嘲讽甚至斥责的情感态度。例如:
(1)这里的一切安排得太好了!
(2)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3)这姑娘太蠢笨了!
从感情色彩来看,例(1)“好”为褒义,体现出说话人肯定赞扬的情感态度;例(2)“大”为中性,例(3)“蠢笨”为贬义,均体现出说话人的否定与不满。
2.“过”与“过于”
“过”与“过于”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语义功能相同均表示说话人认为其所修饰的性状超过了所需要的或所规定的限度,蕴含着说话人的消极不满情态,均含贬义色彩。两者不同在于,“过”只修饰单音节形容词,“过于”只修饰双音节形容词。如:
(4)青春尚好,叹老,还为时过早。
(5)由于人口过于密集,造成城市空气污浊、水质变坏、噪音扰人、垃圾成堆。
在现代汉语中“过”与“过于”作副词时在语义上完全等值,只不过在使用上有分工。副词“过”的来源,应与副词“过于”的形成密切相关,“过于”修饰单音形容词时因音律节奏不谐,故脱落“于”修饰单音词。
关于表超量的“过分”义之“过”是形容词还是副词的问题,我们认为仍应看作形容词。张言军指出“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副词‘过于’以修饰形容词性词语为主,而副词‘过分’以修饰动词性词语为主,并且一些非心理情感类动词只能受‘过分’修饰。 ‘过分’在充当状语时可以后加状语标记‘地’,而‘过于’却不能”。[1]王启龙认为“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若能前加‘很’(加‘很’后必加‘地’)或能转换为补语,仍算形容词;否则算副词。”[2](P76)何乐士认为:“形容词作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程度或状态。”[3](P67)龚仁认为:“形容词作状语,一般有在及物动词前和不及物动词前两种。”[4](P262)吕叔湘仅把“过于”看作超量程度副词,而未收录“过”[5](P251)。综上可知,副词的主要功能是修饰形容词,而张文所认定为副词 “过分”的句法功能与副词的典型功能不一致,与作状语的形容词有较高的相似度,这说明“过分”仍为形容词而非副词。吕文认为现代汉语中的“过”不是副词,或是因为“过”有“过分”义。可见“过分”在语法功能上仍是形容词。
据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作状语的“过”,应一分为二来看:其功能与“过分”相同,在动词前作状语时为形容词;仅与“过于”相同,在形容词前作状语时为副词。两者虽然在语义上基本无别,但句法功能上有明显差异。故只有在“过”仅能理解为“过于”时才能看作副词。
由于对副词“过”的认定标准不同,那么“过”作副词始于何时,当前学界看法也不一致。胡丽珍、雷冬平认为“过”表超量程度副词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6]。其实南北朝时期“过”即便在状语位置上,仍为形容词。胡文所举例为:
(6)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后汉书·李章列传》)
(7)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
例(6)中的“过”与“滥”同义连文,均为形容词,表“过度”“无节制”义,“过滥”,即“过度”。例(7)中的“过”仍为形容词作状语。“过”为“过度”,“过醉”即“过度醉酒”。
殷树林、高伟认为“过”作程度副词始于两汉,魏晋至唐宋时期兴盛,明清以后逐渐式微[7]。根据殷文所举例句来看,明代之前的“过”,均仍为典型的“过分”“过度”义形容词。如“过急”“过多”,即“过分急切”“过分多”。因“太”作为超量程度副词在上古就已流行,“过”作形容词在语义上也表超过应有限度的“过度”义,两者在句中作状语时,会经常出现在相同句法结构的同一句法位置上。因此,“过”虚化为副词除受“过于”的影响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太”聚合类化的影响。不过,宋代之前的“过”只不过在语义上与“太”相似,在语法功能上则不同,故还应看作形容词。
(二)“太过”
由于对副词“过”的认定标准不同,也影响到对副词“太过”的认定。胡丽珍、雷冬平指出:“在超量级程度副词家族中,“太过”一词不见于字典辞书。”朱景松《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均未收录该词。笔者认为未收录原因,并不是失收,而是他们对“太过”是否成词仍存疑。因“过”作形容词有“过分”“过度”义,该用法一直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如“他这样说未免太过了。” “过分”“过度”作形容词,表示说话或做事超过适当程度或限度。该义与超量级程度副词“太”虽然在语义上基本等值,但其语法功能明显不同,表“过分”“过度”的“过”可单独作谓语。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作状语也是其主要功能之一, “太”与“过”有时虽然在线性序列上组合在一起而形成“太过”,其间关系却不是并列的,句法关系不在同一个结构层次上。故现代汉语中的“太过”也并非全是副词,只有两者都以副词身份,以同义连文的形式凝合在一起表超量程度的加深时才可看作副词。如:
(8)与别人的礼貌森严比较之下,自觉太过傲慢了。(丰子恺《作客者言》)
(9)我姐姐性情太过刚直,刚直一定招来怨恨,宫廷之中,到处都是仇敌。(柏杨《皇后之死》)(1)例(8)(9)转引自胡丽珍、雷冬平(2009)的论文。
(10)谦虚不是坏事,但是不能太过谦虚。
例(8) “太过傲慢”在现实语境中不存在“傲慢太过”的说法,说明“太过”在语义上是不自足的,即不能单独回答问题。 “太过”是副词“太”与“过于”凝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当然也可看作是“太过于”的省合用法,这也是一些学者不把看作“太过”看作副词的原因之一。虽然“太过”在语义上表 “太过于”,但不属于一般的省略,省略一般需要语境,通常是就具体语境而言,而“太过”表示“太过于”具有普遍性,也符合词的认定标准,即以一个特定形式表示一个特定意义,理应看作一个副词。这样一来,副词“太过”的来源,应在“过于”成词之后才与“太”凝合而成。故超量程度副词“太过”的形成也与副词“过于”的形成密切相关。例(9)(10)中的“过”仍为形容词,“太过”,即“太过分”。“太”与“过”虽然在语义上是等值的,但一为副词,一为形容词。在现实语境中,也存在“太过”单独作谓语的情况。如:
(11)这个鲁记者,骨架结构属于刚直太过而柔韧不足,神色倨傲而故作谦逊。
(12)他真是谦虚太过了。
例(11)与例(12)中的“刚直”与“谦虚”在句中作小句主语,“过”为小句谓语中心语(2)有学者认为该类句子中的“太过”为形容词短语作补语,我们认为 “太过”与其前中心语为陈述与被陈述关系,即某名物某方面“太过”,而不是补充说明其程度,故应看作主谓结构。,其语义指向在小句主语上。例(11)“太过”与“不足”相对。例(9)(10)与例(11)(12)相比,“刚直”与“谦虚”,句法位置不同,可“太过”的语义节奏点没有变化,因此 “太过刚直”“太过谦虚”的语义节奏应为“太/过刚直” “太/过谦虚”,虽然按照中心词分析法在线性序列上语法结构应分析为“[太][过]刚直”“[太][过]谦虚”,但两者仅在线性序列上相连既不在同一语义结构层次上,也不在同一个句法结构层次上。“过”与其后的中心语先组合在一起再受“太”的修饰,故不能看作一个副词。因此“太过”作超量程度副词应由超量程度副词“太”与“过于”简化凝合而成,其出现时代应该在“过于”成词之后。只有“太过AP”的语意逻辑节奏为“太过/AP”,并且“过”只能理解为“过于”而非“过分”义时,“太过”才能看作副词。
明代之前同时期的文献中“太过”作谓语,表示“过度”“无节制”的情况非常常见,故均不能看作副词。如:
(13)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魏书·韩麒麟传》)
(14)先是,侍御史沈与求言:“今日矫枉太过,贤愚同滞。(《宋史·选举志四》)
例(13)中的“太过”与“无限”相承,表示“客观上超过了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例(14)表示“超过所适宜的程度”。处在状语位置上的“过”与处在谓语位置上的“过”在语义上无别。通过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对唐五代宋元时期的“太过”进行了检索,逐条辨析后发现,“太过”组合均为“太”作状语修饰形容词“过(过分)”形成的偏正结构,在句中作谓语,其前主语可以是NP,也可以是VP、AP,(3)NP指名词或名词短语,AP指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VP指动词或动词短语。或主谓短语,未见组合在一起作状语用例。据胡丽珍、雷冬平考察,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太过AP”结构,这时的“太过”已经可以认定为副词。笔者认为“AP太过”中的“过”为形容词,“太过AP”中的“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形容词作状语,其逻辑节奏应为“太/过AP”,而非“太过/AP”,如“太过切直”“太过信他”中的“过”均为“过分”。
由此可见,副词“过”“太过”的来源,应不是多元化。而是在“过于”成词之后,为了迎合修饰单音词之需才单音化为“过”,为了强调超量,而凝合为 “太过于”,进而形成“太过”。既然副词“过”“太过”的形成都与“过于”的副词化历程关系密切,故在讨论这三个词的形成时,应着重探讨“过于”的成词历程。
二、“过于”表超量副词用法的出现时代
饶琪、牛利认为在中古已经出现了成词的端倪[8],其实不然。饶文所举例证为:
(15)夫万物凡事过于过大,末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太平经》卷三七)
(16)天从今以往,大疾人为恶,故夫君子乃当常过于大善,不宜过于大恶。(《太平经》卷九七)
殷树林、高伟也引用了这两个例证,认为其中“过”为形容词“过度”“过分”。其实以上两例中的“过”均为动词,即“犯错”义。饶文认为例(15)中的“过”应为“超过”“过分”。其实例(15)点校与理解均有误,正确的标点应在“末”后点断,即“万物凡事过于大末,不反本者”。其中“过”为“错”“过失”义,“过于大末”,即“错在把末梢的作用夸大,以末为本”。“不反本者”与“殊迷不解”之间为因果关系,因为不返归到根本,特别的积迷就化解不开,所以要重新返回到根本。例(16)中的“大善”与“大恶”是善与恶的两极,其中 “过”不会再为“过分”“过度”。结合上下文可知,该引文上一段是告诉如何“叩头思过”, “令欲解此过。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解子过于天地也。后有过者,皆像子。”道家思想认为,人有过失,天必有所明察而施加惩罚,要得到天神宽宥,可在旷野四达道上叩头,气候之神,即天使便会将其所请上通于天,下通于地,而得免罪。因此,该例中的“过”仍为“过失”义,该例意为“上天从今以后,非常痛恨人作恶,因此君子就应该经常在谋求大善的方向上犯错,不会在大恶的方向上犯错。”
饶琪、牛利认为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过于”成词的最早用例,所举例证为:
(17)人生之为体,易伤难养,方之二木,不及远矣,而所以攻毁之者,过于刻剥,剧于揺拔也。济之者鲜,坏之者众,死其宜也。(《抱朴子·内篇》)
殷树林、高伟也引用了该例,认为该例中的“过”为形容词“过分”,“于”为介词引出“过分”的方面。其实该例中的介词“于”表示引出比较对象。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是道教文献,该例是告诉人们如何养生,“过于刻剥”与“剧于揺拔”相对均表比较。“刻剥”,为动词,而非形容词“刻薄”。意为“人的身体,容易受到伤害而难以保养,与前述木槿与杨柳二木相比,相差很远。而对于他的伤害比对树木的刻削剥皮还厉害,比对树木的摇动拔起还剧烈。”殷文所举另一例为:
(18)刘向说上曰:“宜设辟雍,陈礼乐,以风化天下。虽不能具,夫礼乐以养人为本,就有过差,是过于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亡……”(《汉书·礼乐志》)
该例引文错误非出自《汉书·礼乐志》,而是出自东汉荀悦的《两汉纪上·汉纪·孝成皇帝纪》。该例理解上也存在问题。其中的“过于”之“过”也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差错”,“过差”,即“过失偏差”。该例是讲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刘向劝谏皇上应兴学堂,设礼乐,以教化百姓,强调了礼乐的重要性,即使礼乐不能够齐备,不过礼乐是以教育人为根本的,就是有过错,仍是错在教育人。刑罚的过错就是让人或死或伤。
胡丽珍、雷冬平认为“过于”始见于唐代。这一说法还是可信的,下面例(19)-(22)中的“过于”可认定为副词。如:
(19)然过于审慎,所上表奏,惧有误失,必读之数十遍,仍令官属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审,每遣一使,辄连日不得上道。(《旧唐书·皇甫无逸传》)
(20)朕虽寡德寡谋,自谓不居延光之下,而冯晖、孙锐过于儿戏,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军为我之患乎!(《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二》)
(21)而居常奉身,过于俭素。(《因话录·商部》)
(22)中散步兵终不贵,孟郊张籍过于贫。(白居易《诗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当此科……成狂咏聊写愧怀》)
(23)狂歌过于(4)谢思炜认为“过于”为超量程度副词,“过于胜”,即“太胜、甚胜”。同时指出例(17)(18)中的“过于”均为副词。详见《杜诗俗语词补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1期,第127页。胜,得醉即为家。(杜甫《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
(24)第一温言不可得,处分小语过于珍。(敦煌词《五更转》)
通过对唐五代文献检索辨析发现,在唐代文献中,“过于”能够认定为副词的仅4例,除例(22)在唐诗中,因配合韵律、节奏的需要修饰单音词外,其余均修饰双音词。例(19)—(21)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节奏上都已是一个副词了。“审慎”,即“周密慎重”; “儿戏”,比喻“处事轻率、不严肃”;“俭素”,即“俭省朴素”均是性状性较强的形容词或词组。例(23)该诗写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甫在通泉县时,县令姚某设宴款待王侍御,要杜甫作陪,该句是写诗人狂歌醉卧的场景。当时诗人流落在蜀,非常思念在长安的老家。“胜”为“形胜”,即“山川胜景,优美的地形”,意为“喜欢狂歌之人在胜景之中经过,能够醉卧之地就是自己的家乡”。从当前对该句诗的校点来看,在传世的不同版本中,该位置上共出现过“过于”“过形”“遇形”“遇于”四种情况,可知其中的“过”为动词,故 “过于”不是副词。例(24)是说在晡时侍奉父母用晚餐时应该怎么做,“第一温言”即“最温柔的话语”,“处分小语”即“安排饭食时的低声细语”,合言之即“说出最温柔的话语虽然做不到,但是低声细语安排饭食过于珍馐佳肴。”该例中的“珍”为名词,即“稀有精美的食品”。《正字通》:“珍,食之美者亦曰珍。”如成语“山珍海味”。该例中的“过”为动词,表“超过”。
对副词“过于”的认定还应注意这种情况。“过于”后虽为形容词,但“过于”并不表程度,而“过”为动词“过失”义。如:
(25)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唐 孙过庭《书谱》)
例(25)强调不同个性的书法家在各自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个人风格,即“随便的人作品会失去应有的规则,性格温和软弱者作品会伤在婉转无力,性格急躁恃勇的人会错在轻快”。其中“过”“失”“伤”分别相对为文,这种对举式的句式凸显出三个分句的表意焦点分别在“失”“伤”“过”上,“过”为“过失”义,“剽迫”,即“轻疾”。殷树林、高伟将该类型的“过”看作表“过分”义的形容词,也欠精准。殷文所举例还有:
(26)所以伊川云:“君子常失于厚,过于爱。”“厚”字“爱”字便见得仁。(《朱子语类》卷二六)
(27)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伤于忍。(宋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一二)
(28)又曰: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子语类》卷一六)
例(26)(27)“过”与“失”“伤”对举,可以凸现出所在小句中“过”“失”“伤”为表意焦点,是所在小句的谓语中心,是在说人犯错误特点各异:君子错在厚道、溺爱,小人错在刻薄、缺乏忍让。例(28)中的则体现朱熹的民本思想,其语法结构为 “动词+介词‘于’”。从语用角度看,在相同语义关系的语境中既可用“过”,也可用“过于”,均表超量,只不过词性不同,单独用“过”时为形容词,“过于”中的“过”为动词,即“做得过分”。如:
(29)后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处者多,只得随其浅深厚薄,度吾力量为之,宁可过厚,不可过薄。(《朱子语类》卷三八)
(30)“取予”二字有轻重否?寓以为宁过于予,必严于取,如何?(《朱子语类》卷二九)
例(29)“宁可……不可……”所表示两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例(28)相同,一用“过”,一用“过于”。例(30)“过”与“严”对举,小句的表意焦点在“过”与“严”上,均为动词,“过”即“做得过分”,“严”即“严格执行”。因“做得过分”即有了“犯过失”的意味,在相同的结构中也存在用动词“失”的情况,如“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到宋代,“过于”副词用法越来越流行。笔者对宋代的《默记》《东京梦华录》《朱子语类》《梦溪笔谈》《苏轼集》《六一诗话》六部作品中的“过于”作了穷尽性的检索与逐条辨析,发现可认定为典型副词的用例共有18例,1例为心理活动动词“敬畏”,其余均为形容词,其中双音节形容词4个分别为“高明”“刚强”“畏慎”“惨刻”,单音节形容词9个分别为“刚”“直”“乐”“严”“疏”“密”“厚”“深”。如:
(31)他是过于高明,遂至绝人伦,及欲割己惠人之属。(《朱子语类》卷六四)
(32)九三又与上六正应,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辅,自是过于刚强,辅他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33)看文字,不可过于疏,亦不可过于密。如陈德本有过于疏之病,杨志仁有过于密之病。(《朱子语类》(5)该例吴福祥看作副词,认为“过于”只修饰“AP”,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超出正常或预期的标准。详见吴福祥《〈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卷一百二十)
(34)问:“为政更张之初,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曰:“此事难断定说,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见得,何消过严?便是这事难。” (《朱子语类》卷一百八)
(35)发运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梦溪笔谈》卷十一)
(36)范氏似以“不为酒困”为不足道,故以燕饮不乱当之,过于深矣。(《朱子语类》卷三六)
例(31)“过于高明”,例(32)“九三”“上六”均为卦象,两者相应只能坚贞自守以待。例(33)中“过于疏”“过于密”既作谓语又作定语。例(34)“过于严”语与下文“过严”相应,“过于”作状语相当于“过”。此时的“过”可以看作副词的萌芽。该例意为,有人问:处理政务更改议定的事情之前,是不是也需要运用威严统一一下人们的思想呢?回答说“这种事情很难断定地说,在于个人如何处置,但是何必要过于严厉呢?如今难得的是通晓事理的人。如果是通晓事理的人,因为历练多,事情刚到面前,他就知道处理那件事情的分寸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别人自然敬畏佩服。如今往往过于严厉的人,多半是自己不明白,又怕人欺骗自己,又怕人轻慢自己,于是用大拍子拍过去,要别人畏惧他。”例(35)意为,发运司还要综合各郡县收购的数量安排计划,如果收购过多,就减少价格高和路远地方的收购量;如果还少,就增加价格低和路近地方的收购。例(36)“过于深矣”,“深”虽为单音词,但其中的句末语气词“矣”是该句表意焦点后移的的一个标记,即该小句的表意焦点在“深”上,即“深”为小句谓语,“过于”即为副词。表示饮酒的适当程度为“不为酒困”,如果“以不乱为适当”,程度上过于深了。
根据上下文来看,“过于”后有时即便是形容词,但该形容词已经名词化,“过于”仍表“动词+介词”义,“过”作动词可表 “过失”“超过”“做得过分”。故该类结构中的“过于”仍不能看作副词。如:
(37)小过是过于慈惠之类,大过则是刚严果毅底气象。《朱子语类》卷七三
(38)小过是小事,又是过于小。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皆是过于小,退后一步,自贬底意思。《朱子语类》卷七三
(39)问“观过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过失处观之。谓如一人有过失,或做错了事,便观其是过于厚,是过于薄。”《朱子语类》卷二六
例(37)(38)中的“过”均为“过分”义,在这里活用作动词表示“做得过分”。例(38)“过于小”中的“小”已名词化,即“小事”。“小过”指的是《周易》中的“小过”卦,与“大过”相对,即“在小事上过分”。“过于慈惠之类”是指“在柔弱慈惠的事情上可以做得过分”。“小过是小事,又是过于小”意为“小过是小事,又这是在小事上过分” 。接下来举例,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皆是过于小。意为“像该恭敬、悲哀、节俭的时候做得过分,皆是小事过分”。例(39)“过”为动词,“犯过,犯错”。其中“薄”“厚”也已名词化,“于”相当于介词“以”,表原因。“过于厚”“过于薄”,即“因厚道而犯错” “因刻薄而犯错”,故非副词。
在宋代,“过于”作副词修饰单音节形容词的用例多于双音节形容词。其原因大概是:A.这些单音词都是常用词,从上古一直沿用至今;B .与《朱子语类》的语言性质有关。王树瑛认为:“《朱子》的语言性质以通语为主,同时带有闽北方言成分。”[9](P10)疑与朱熹本人的语言特点与闽北方言保留上古文言词语较多有关,因而造成单音词较多。
通过对元代的文献检索辨析发现,“过于”作副词用例较少,仅见1例,“过于”与“特”相对,为副词无疑,后跟双音节形容词。这可能与元代传世文献较少有关。如:
(40)然其诗过于纤巧,淫靡特甚,不类其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卷二十)
通过对明代八部文献《徐霞客游记》、《二刻拍案惊奇》、《三国演义》、《今古奇观》、《水浒传》、《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清平山堂话本》检索辨析发现,“过于”作副词共见6例,只修饰双音词,其后中心语既有形容词,也有心理活动动词,甚至一般行为动词。如:
(41)只因府上的家范过于严谨,使男子妇人不得见面,所以郁出病来。(《今古奇观》卷七)
(42)华小姐道:“不瞒姐姐说,我小妹在闺中略识几字,家父过于溺爱,以为当今无二,不肯轻字与人。(《今古奇观》卷七十四)
(43)吾观刘琦过于酒色,病入膏肓,现今面色羸瘦,气喘呕血,不过半年,其人必死。(《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
例(41)“严谨”为形容词,例(42)“溺爱”为心理活动动词,例(43)“酒色”本为名词在这里活用作一般动词“沉溺酒色”。“过于”成词后基本上仅修饰双音词,和其后的双音词组合成四字格式,在明代已经得到了全面体现,当修饰单音词时“过于+单音词”在音节节奏上不相称,故就常以“过”来代替“过于”,这时“过”才成为超量程度副词。“过”副词用法应在明代已为常见。如:
(44)郑伯之于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听其收鄙,若爱弟之过而过于厚也。(《王阳明全集·悟真录之七》)
(45)满生道:“小生飘蓬浪迹,幸蒙令尊一见如故,解衣推食,恩已过厚;又得遇卿不弃,今日成此良缘,真恩上加恩。他日有负,诚非人类!”《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例(44)(45)中 “过于”与“过”用法完全相同,“过”可看作副词,均表示在说话人看来超过了应有的厚度。例(44) “若爱弟之过而过于厚也。”意为“好像疼爱弟弟过分而过于厚也”。
到清代,还出现了超量程度副词“太”与“过于”连用的句式,表明“过于”的副词功能与“太”完全无异。通过对明清时期文献检索辨析发现,“太”与“过于”连用一起修饰同一个中心语始见于明末清初,共出现4例,其后的中心语3例双音词(2例形容词,1例动词短语),1例单音形容词“厚”。因“厚”自古及今一直是一个基本词,其意义已经固化并为人们所熟知,使用频率极高,因此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中,能够不受影响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中。如:
(46)表兄既中了元,弟不中是实了,又何必候报。但我场中文字,做得太过于高古,若中必然是元,若非元即不中了,此在自己可以定得。”(《春柳莺》第六回)
(47)俭叔道:“文琴那回事,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六回)
例(46)“中了元”,即“考了第一名”;“ 高古”,即“高雅古朴”。例(47)“不羁”即“不受约束”。四例“太过于”与其后中心语的组合情况为,“太过于高古”“太过于谨慎”“太过于不羁”“太过于厚”,从韵律节奏的角度来看,“太过于/高古” “太过于/谨慎” “太过于/不羁” “太过于/厚”,就其节奏点来看,不符合当时四字句式的常规表达习惯,修饰语与中心语之间在音节节奏上显得不相和谐。 “太过于”为了迎合四字韵律节奏的需要就凝合为了“太过”。
到了民国时期,出现了“太过”修饰双音节形容词的用例,停顿的节奏点也是“太过/双音形容词”这时“太过”才能看作一个纯粹的超量程度副词。如:
(48)曹和奉张原有姻亲,而无大恶感,对于吴氏之剑拔弩张,志在挑战,也觉太过激烈。(《民国史演义》第十五回)
到现代汉语中,“太过”作为超量程度副词的用例逐渐增多,与 “太过于”同时并存。如:
(49)她承认印度卫生部门前一阶段在处理“非典”问题上犯了错误,太过谨慎。(《新华社》2003年5月2日新闻报导)
(50)小男孩吃完了之后,阿卡便对他说道,她认为他在公园里到处乱跑,未免太过于不谨慎了。(石琴娥译《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例(49)“太过谨慎”与例(50)“太过于不谨慎”中的“太过于”功能上完全相同,故“太过”为副词。现代汉语中的“太过”作状语既可能是副词,也可能是“太+形容词‘过(过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A.两者之间语音停顿的节奏点不同,“太过”为副词时,停顿点在“过”后,如“太过/执着”“太过/敏感”“太过/担心”等,为“太+形容词”时,停顿的节奏点在“太”后,如“太/过悲哀”“太/过用力”“太/过欢喜”等。B.“太过”为副词时在现实语境中不会出现移位至谓语中心语后作谓语或补语类用例,否则为“太+形容词”,如在现实语境中未出现“执着/太过”“敏感/太过”“担心/太过”类用例,而存在“悲哀/太过”“用力/太过”类用例。
综上所述,超量程度副词“过于”萌芽于唐,发展于宋,明代才完全成熟,清代以后流行至今。到宋代,受韵律音节节奏的影响, “过于”修饰单音词时开始缩略为“过”,“过”的副词用法开始出现。因进一步强调超量与“太”以同义连文的形式组合一起修饰其后中心语,再进而凝合成“太过”,副词“太过”萌芽于清末,到民国时才逐渐形成,到现当代汉语中才逐渐流行。
三、 “过于”成词的判定标准
笔者通过考察“过+于+AP/VP ”句式在历时发展演变中语义、语用方面的变化提出确定副词“过于”成熟的标准如下:
1.在句法上,在明代之前“过于”位于形容词或心理情感类动词或短语前,明代以后扩展至一般行为动词或动词短语。
2.在语义上,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过”不可理解为动词“过失”“超过”义。
3.从语用上看,小句的表意焦点应该在“过于”后的谓词性成分上,表意焦点是否从“过”后移至谓词性成分上是判定“过于”是否成词的关键,在句法上体现为在谓词性成分后是否有句末语气词。
4.因“过于”仅表示程度,如果“过于”删除后其后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仍自足,基本上不影响句子基本意思的表达。
“过于”必须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才可认定为典型副词。
四、“过”“过于”“太过”副词化机制与动因
(一)词义虚化
“过”的词义虚化与语义指向后移是造成“过于”副词化的主要动因。“过”本义“经过”,该义具有[+位移]的语义特征,从空间位置来看,经过某处,即越过某个空间位置点。越过某个空间位置点,与两名物相比一方超过另一方有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就引申指 “超过”“胜过”,如“不孝莫过于无后”。因某动作行为或性状超过人们所需要的或者合适的程度就为“过分”,故在“超过”义的基础上就很自然地引申指“过分”。表“过分”之“过”能自由作状语或谓语。作状语时与表超量的程度副词在语义上完全吻合,如《荀子·修身》:“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不过,“过”以形容词身份与以副词身份作状语虽然在语义上是等值的,但其语法功能不同,表示“过分”义的“过”除了作状语外还可以自由地作谓语或补语,而副词“过”不同,只能作状语,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过于”。因此,“过”成为副词的时代在“过于”成词之后。
“过于”副词化过程中就是在“过”的形容词用法“过分”义的基础上虚化凝合而成。因“过分”本身含有超过一定程度或限度的意义。当“过于”后跟名词时,“于”介引比较对象,“X过于Y”在语义上表示“X与Y相比过分,即超过Y应有的程度”。如:
(51)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宋书·隐逸传·周续之》
当“Y为名词时,“过于”小句的语义焦点在“过”上,“过”的语义指向“X”,当“Y”为形容词,使得“于”的介引功能悬空,迫使该小句的语义焦点后移至形容词“Y”上,Y直接对X进行描写,这时就迫使“过”与“于”凝合在一起表示超量,其语义指向其后的形容词。这就为“过于”成词创造了语义上的条件。
(二)重新分析
到南北朝时期,“过于”仍以后跟名词性成分为主,“过”为形容词“过分”义,“于”介引比较对象,不过也出现了后跟形容词用例。如:
(52)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宋书·孝武文穆王皇后传》卷41
(53)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宋书·乐志三》卷21
例(52)“过于”与“甚于”相对,“过”为形容词。例(53)“渴”与“饥”为形容词,在该例中分别名词化为表口渴与饥饿的状态,刚开始,人们仍会将该形容词看作活用作具有一定指称性的名词,把 “过于+形容词”句法结构可分析为与“过于+名词”一样,即“于+名词化的形容词”一起作“过”的补语,即“ ‘过’+<于+形容词 >”。随着后跟形容词,尤其是双音节形容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受人们习惯性句法分析的影响,就将该结构重新分析为“过于”表超量修饰其后的形容词中心语,可标写为“[过于]+形容词”。
由于“过于+名词”结构从产生之初一直沿用至明清,其使用频率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式微,直到现代汉语中才完全消失。而“过于+形容词”与其相反呈现出逐渐增长趋势。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使“过于”的副词性越来越得以凸显,副词功能日益完善。因此在唐宋以后的文献中“过于+形容词”结构中的“过于”是否成词也存在着两可的情况。如:
(54)今却恁地跷说时,缘是智者过于明,他只去穷高极远后,只要见得便了,都不理会行。(《朱子语类》卷六三)
(55)如家人有严君焉,吾之所当畏敬者也。然当不义则争之,若过于畏敬而从其令,则陷于偏矣。(《朱子语类》卷十六)
(56)合当与那人相揖,却去拜,则是过于礼。礼数过当,被人不答,岂不为耻。(《朱子语类》卷二二)
例(54) “过于明”中 “明”为形容词“高明”义,“过于明”即“过于高明”,同时“明”也可理解为形容词活用作名词,表示“本应有的高明的程度”。例(55)中“过于敬畏”中的“敬畏”为表心理活动动词,也可理解为动词活用名词表示“本应有的敬畏之情”。“过于+谓词性词语”中的“谓词性词语活用作名词后”与例(56)用法相同,“过于礼”即“超过了本应有的礼仪”。不过根据上下文语境来看,例(54)“智者过之”,其中的“过”与“不及”相应,即“智者超过了本应有的明”,将“过”仍理解为“动词”较合适。例(55)连词“而”连接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复句,“过于畏敬”表因,“从其令”为果,因此“过于畏敬”的表意焦点在“畏敬”上,即因敬畏而产生了后一动作,故“过于”应看作“畏敬”的修饰成分副词。因此在判定“过于”是否为副词时应根据具体语境来作出判定。
(三)韵律节奏与双音化大趋势的影响
“过于+N”中的“过”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主要有三:A.动词,超过。如例(56);B.形容词动词化,做得过分。如例(38);C.动词,过失。如例(26)(27)。这三个义项的引申路径清晰明了,“X过(超过)+于+Y” 即“X与Y相比超过了本应有的程度”,即“X与Y相比在程度上过分”引申出“过分”义,“超过了本应有的程度”就会出现“过失”。前两个义项中介词“于”均表比较,“X过(过失)于Y”中的“于”表示“过失之所在”。“过于”的成词是在“过分”义的基础上引申虚化而来。
东汉以降,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加速,魏晋以后以上三个义项中的“过于”后跟谓词性成分时,多为双音节词语,如“过于大善”“过于骇俗”“过于刻剥”“过于养人”“过于俭素”“过于予民”“过于剽迫”等。这样的四字格式在韵律节奏上刚好将“过于”推在一个音步当中,即“过于/大善”“过于/骇俗”“过于/刻剥”“过于/养人”,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过于”的凝合。唐代以后,“过于”后跟双音节形容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明清以后,其后基本上只跟双音节形容词,因形容词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与状态,“过于”后跟形容词时多体现性状方面的过度,使得“过于”凝合在一起仅体现出副词义。
(四)副词“太”的类化
“太”是一个在上古汉语中就已流行的超量程度副词,既修饰单音节形容词,也修饰双音节形容词,有时也可以修饰动词短语。表示该性状或动作行为超过了本应有的或所需要的程度。“太”的这一句法语义功能与副词“过于”完全相同,“过于”在成词之初经常出现在与“太”完全相同句法格式同一句法位置上,受词法聚合规则的影响,经常出现相同句法结构同一句法位置上的两个词因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而应归属于同一个词类。因此在“过于”成词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太”的类化。如:
(57)诏曰:“夫刑纲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58)自晋兴已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晋书·闫缵传》)
(59)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搜神记》卷十五)
(60)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以上四例中的“太密”“太严”“太多”“太纤巧”与例(33)(34)(35)(40)中的“过于密”“过于严”“过于多”“过于纤巧”句法结构相同。“太”与“过于”经常出现在相同句法结构,甚至是同一句子的相同句法位置上,并且两者具有相同的语义句法功能。因此,受人们常规句法规则意识的影响,“过于”与“太”必定属于同一个词类。
小 结
“过”和“于”本是处于不同句法层次上的两个语言单位。“过”本为动词“经过”义,后来引申出形容词 “过分”义,表示“过分”义时,“过+于+ NP”中的“于+NP”一起作“过”的比较补语。后来“过于”后的“NP”扩展为“形容词或心理情感类动词”,这时造成“于”的介引功能悬空,迫使“于”与“过”凝合在一起。到唐代,“于”后中心语基本上均以双音词语为主,并与“过于”一起组成四字格式,受四字格式韵律节奏的影响,“过”常常与“于”形成一个语音组块,出现在一个音步当中。这一句法格局与另外的一种常规句法格式——状中关系,无论在语法形式上还是在语法意义上都非常相似,在人们认知心理的驱使下,就会对此格式进行重新分析。后来再加上“过于”所在小句表意焦点的后移以及副词“太”的类化共同促成了副词“过于”的形成。
超量程度副词“过于”萌芽于唐,发展于宋,明代才完全成熟,清代以后流行至今。 超量程度副词“过”“太过”的而形成均与“过于”的成词密切相关,“过于”成词后为了迎合修饰单音词才单音化为“过”,为了强调超量,才凝合而成“太过于”,进而形成“太过”。“过”的副词用法始于宋代。“太过”成词萌芽于清末,到民国时期才逐渐形成,到现代汉语中才逐渐流行。副词“过于”的形成是由其特殊的句法位置、“过”的词义虚化与语义指向的后移,副词“太”的类化,韵律节奏与汉语词汇双音化大趋势的影响共同促成的。
——对“超量恢复”质疑学说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