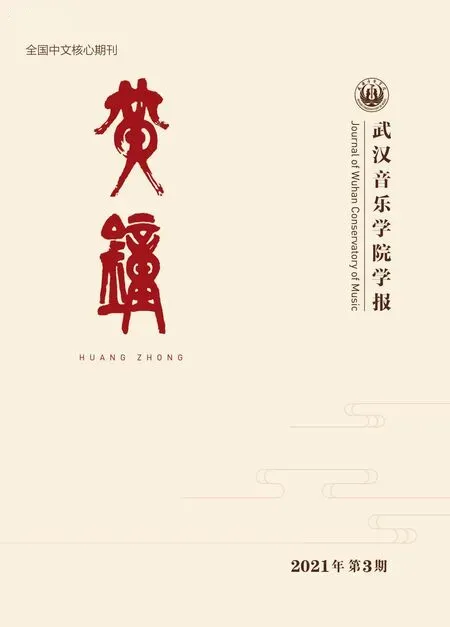杨放先生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述评
匡学飞 孙晓辉
杨放先生(1921—2014),曾名杨世华,哈尼族,毕生从事于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委、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主编,2004年获得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
因为与杨放先生一段特殊的师生情缘,笔者受杨放先生和师母唐敬老师之嘱托,整理杨放先生遗留的珍贵且丰富的音乐资料。受人之托,必当忠人之事。2017—2019年,笔者邀孙晓辉老师参与,共同完成了这批资料的编目著录工作。通过对这批资料编目,我们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杨放先生研究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学术成果,故特撰写此文以致敬他对我国云南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杨放先生生平及其学术分期
杨放先生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求学期(1921—1948)
1921年3月3日,杨放出生于云南个旧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外祖母和母亲为哈尼族。
1937年秋,考入前云南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学校(简称“昆华艺师”)音乐美术科,父亲杨九昌(字希堂)亲送其到昆明。师从黄相泉先生学钢琴,师从江芷庵先生学素描。昆华艺术师范学校创办于1936年,由国民政府在昆明今天胜利堂的位置创办,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1937年底,学校只能搬到呈贡滇池边海晏村的一个寺里继续办学。“从这个学校走上职业音乐之路的许多学生,成为了1990年代以前云南乃至全国乐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有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云南艺术学院的杨放教授。”①申波:《“横断”与“乌蒙”阻隔的风景——云南新音乐史学研究史料查阅与口述访谈的体验》,《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2期,第36页。
杨放先生曾经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昆明乐坛的董源先生对他的影响。他说董源先生最擅长将民间音调与云南方言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如《翻身花》《别让它遭灾害》等歌曲),并用昆明方言亲自演唱,遂成为广为流传的“新民歌”②申波:《清末民国时期云南的歌曲创作述评》,《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5期,第60—61页。。
1941年,杨放考入重庆国立音乐院钢琴系。钢琴受教于杨体烈、程美德、王云阶、李蕙芳等;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和作曲师从于江定仙、陈田崔、林声翕等。还曾师从于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张洪岛等。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使他系统地掌握了一些西洋音乐的理论技术。③黄泽主编:《中国各民族英杰》(第5卷),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又参见《杨放艺术自传》,杨放资料编目Ⅲ-2-13。
1946年他从国立音乐学院返回昆明,随赵沨先生积极投身民主音乐运动,在昆华女中、长城中学做音乐教员。期间创作了《萤火燃烧在广场上》《野草谣》《昆明,美丽的山城》《我们走在田野上》等进步歌曲,还创作了童话剧《金龙袍》《幸运鱼》,部分音乐唱段在长城中学由黄虹等学生演出。
1947年,杨放又为儿童舞剧《苦难的花朵》配乐,其中许多唱段都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谱写配乐小提琴曲《大青树下》、管弦乐曲《欢庆胜利》以及群众歌曲30 余首。他善于将节奏固定在基本的音型框架之内,辅以主导动机的变化穿插,使得歌曲的旋律更加易于传唱,表现出艺术化的简约风格。
1948年,他和黎虹等7位乐友各自“筹份子”,历经周折出版了一本大家创作的歌集《我们走在田野上》。他们在努力探索一种与云南民间音乐风格相融合的表达。这反映了当时云南作曲家群体在“乐歌”创作之时,主动借鉴西洋作曲技法,同时自觉地探索与云南本土民族音乐素材相融汇。
(二)《阿诗玛》的整理发掘与云南民族音乐搜集整理奠基期(1949—1982)
1949年,杨放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在政治部艺术组工作。他首先发掘整理了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音乐诗歌《阿诗玛》。杨放著文《行军琐记》,回忆1949年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粵赣湘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随主力部队向新区进军。④杨放著文《行军琐记》,收入中国人民解放部粤赣湘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史编辑组、中共番禺县委党史研究室合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资料文集(1948—1989年)》,第38—39页。每当回顾从学院走向社会的这段历程,杨放总是恳切地说:“生活的锤炼不仅使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也使我瞥见到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宝藏!”⑤黎虹:《苔痕藓迹》,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1950年9月,杨放在普梅夫主编的《诗歌与散文》上发表了他记录、翻译、整理的有关《阿诗玛》的歌词和一首曲谱发表后,颇受文艺界的瞩目,随即被译成俄文刊载于苏联文学刊物上。
1950年后,杨放在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云南省文化局等单位从事群众音乐活动及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研究,先后任文联音协总干事、文化局音工组组长等职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便在千山迤逦、万壑纵横的云岭高原上走村串寨,寻贝拾珠,日积月累地搜集久远而原始的民族民间音乐,而许多民间歌手、山民耕夫和基层文化干部,也成了他的亲密朋友。1959年,杨放到西双版纳的一个僾尼山寨釆风,一连几个月睡在火塘边,记录了老歌手偏罗咏诵的上万句古老民歌,他不辞辛苦地翻译了上百首歌词。建水文化馆的热心人张述孔,不惜翻山越岭,陪他采集尼苏人的“四大腔”。在姚安马游坪采集彝族古歌《梅郭》(即《梅葛》),杨放和省花灯团的几位演员,一股作气整整记录了7天。⑥黎虹:《苔痕藓迹》,第217页。
1959年以后,杨放在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和声、曲式、创作等课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放参与编辑的音乐曲集有:《云南民歌》(第一集)、《云南民间音乐》(第二集·花灯音乐)、《云南山歌》(第一集),⑦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辑、昆明文联音协编辑:《云南民歌》(第一集),昆明文联音协1951年版;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编:《云南民间音乐》(第二集·花灯音乐),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1952年版;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编辑:《云南山歌》(第一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还与音乐同仁一起搜集整理了《哈尼族民间器乐集》⑧《哈尼族民间器乐集》系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资料之十四,16开本,共149页,1965年8月编印,由云南省音乐舞蹈家协会编印,杨放、王珏、阳亚洛、李强华、李志礼、晋忠和、李志德搜集,李志德、普忠和等编辑。等系列资料。杨放先生资料中保留有结集的系列油印本,皆由云南省文化局、云南音乐舞蹈家协会民族民间音乐调查搜集整理、云南音乐舞蹈家协会编印,这些成果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音乐工作者集体智慧的成果。这一时期杨放与云南诸君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大规模的采风调研,编印了《哈尼族民间器乐曲》《哈尼族歌舞曲》《僮族(土佬人)唢呐调》《哈尼组、彝族(尼苏人)的乐器》《牛孔彝族(尼苏人)音乐》《桎施歌舞曲集》《大新寨彝族(尼苏人)的情歌和歌舞曲》(上下集)等油印资料,这一系列成果为日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持编纂《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云南卷》与茶马古道马帮民歌研究时期(1982—2014)
1979年4月,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各省市区文化厅(局)发出《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及关于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计划》等文件,开启了这项巨大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1981年,杨放受聘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编纂从1981年持续到2007年,共26年,杨放先生和云南音乐工作者历经普查收集、编选整理、审定出版三大阶段后才得以编竣。2016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上中下三册作为民歌集成的殿后之作正式出版。其导论《云南民歌概述》⑨杨放、王群执笔:《云南民歌概述》,杨放主编:《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云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16年版。由杨放和王群执笔写作。
这一时期杨放先生的主要成果还包括:1983年,发表《古老的合唱曲〈哦热〉》,出版《云南民间儿童歌曲选》,参与编纂《彝族曲子舞曲选集》。⑩杨放:《古老的合唱曲〈哦热〉》,《音乐爱好者》1983年第4 期;杨放编:《云南民间儿童歌曲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编:《彝族曲子舞曲选集》,1983年版。1984年7月,完成《云南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形态与民间音乐》杨放:《哈尼族云南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形态与民间音乐》,《民族艺术研究》1988年第4期。初稿。1986年,编辑《云南各族情歌一百首》杨放编:《云南各族情歌一百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发表《彝族民间音乐曲式初探》杨放:《彝族民间音乐曲式初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结构研究论文集》编辑组编:《民族音乐结构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和《云南彝族(尼苏人)民间二声部歌曲》杨放:《云南彝族(尼苏人)民间二声部歌曲》,中国音乐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多声部民歌研究文选》,第448页。。1989年,主持筹备“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暨少数民族音乐继承发展主题学术研讨会”在玉溪召开。20 世纪80年代,搜集整理发表了纳西族民间长诗《猎犬》、彝族民间长诗《独阿牟老祖爷》等10余部;采录李莼先生演唱的有关茶马古道的系列马帮民歌,如《赶马调》《数地名》《篷(棚)子客调》等;参与编辑《拉祜族张老五小三弦曲集》《哈尼族歌舞曲》《哈尼族民间器乐曲》《姚安白彝族音乐》《蒙自花灯音乐》等。1993年,在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讲论文《西双版纳哈尼族民歌初探》杨放:《西双版纳哈尼族民歌初探》,收入于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子贤、李期博主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页。。1996年发表论文《面对云南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怎么办?》杨放:《面对云南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怎么办?》,《中国音乐》1996年第4期,第69—70页。。2003年发表论文《临沧文化艺术感言》杨放:《临沧文化艺术感言》,《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S1期,第18—19页。。
期间,还与学生周凯模完成了《云南省红河县大新寨彝族歌舞曲集》《云南省红河县桎施大新寨彝族歌舞曲集》五线谱整理本,与周正松、夏鼎、聂思聪等记录整理了《拉牯族张老五小三弦曲集》五线谱整理本。2006年,获“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二、以《阿诗玛》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歌研究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思认为,一个民族的民俗就是这个民族的自传体民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研究一个民族,首先要听听他们的“古歌”。[美]阿兰·邓迪恩:《民俗解释》,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保存了历史悠久的长篇叙事长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史前人类和民族史的长篇叙事歌。杨放先生对云南少数民族长篇叙事长歌的整理贡献卓著,他主持并参与了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纳西族民间长诗《猎犬》、彝族民间长诗《独阿牟老祖爷》以及哈尼古歌等近20余部。
(一)叙事长歌《阿诗玛》
叙事长歌《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文学经典,是撒尼人民世代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的结晶。抗日战争期间,叙事诗《阿诗玛》就进入了西南联大学者们的视野,人文学者吴晗、光未然等前辈就在路南圭山发掘了《阿诗玛》《阿细的先基》等彝族民间文学,但苦于没法翻译。但他们创作了最早的歌舞剧《阿诗玛》,于1944年在昆明演出。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滇黔纵队二支队为配合游击战,发动群众,曾在彝族老歌手金国富的帮助下,创作演出了《阿诗玛》。正是杨放最早对《阿诗玛》进行了整理,并将其部分翻译成汉语。
发现《阿诗玛》。1949年的秋天,笔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先是在二支队的活动区——圭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当时笔者没有具体工作,准备随张子文同志去纵队政治部。撒尼人聚居的圭山区,对于笔者来说那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杨放:《记录长诗阿诗玛引起的随想》,赵德光主编:《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950年9月,杨放记录翻译的《阿诗玛》曲谱和部分歌词在《诗歌与散文》上发表,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了自己苦难的经历。同年11月,被《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一期转载(见谱1)。这个汉译本名为《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献给撒尼人的兄弟姐妹们》,是《阿诗玛》最早的汉译本,并首次记录了《阿诗玛》的音乐主题(见谱1)。

谱1 《阿诗玛》的主题(杨放记谱)
《阿斯玛》(原名《可怜的阿斯玛》)是活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篇劳动人民的史诗,它闪耀着人民的光辉四射的智慧,是一颗还埋藏在人民地层里的五彩斑斓的大宝石。
我们应该把它整个地挖掘出来,洗去芜秽和泥沙,让它底光辉照亮我们新民族诗歌的殿堂……
《阿斯玛》具备了撒尼人民的朴实、天真、沉默……的一切特质,同时,充满了千百年来悲惨境遇所造成的哀怨,这是一篇革命的、浪漫的叙事诗,又是一首中国妇女在罪恶的封建炼狱里挣扎奋斗的悲剧。杨放:《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新华月报》1950年第三卷第一期。
在杨放先生资料“撒尼民歌五首”(杨放资料编号为Ⅰ-1-10)的文件中保留了当年记录金国富演唱《阿诗玛》的3 首曲调,与《新华月报》刊登的曲调不同(见图1)。

图1 杨放记谱金国富演唱《阿诗玛》曲调之一
《阿诗玛》1999年入选《中国百年百部经典文学作品》,为唯一入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又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被译为英、俄、德、日、泰、法、捷克等30余种文字。整理发掘《阿诗玛》,杨放先生当之无愧属于首功!
公刘先生回忆杨放先生《阿诗玛》的精彩翻译对其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最初知道《阿诗玛》是在一九五〇年,当时,我在云南部队《国防战士报》工作。昆明有一种名叫《诗歌与散文》的刊物,虽然办得不算出色,但在到处闹土匪,不易读到内地的文学期刊的半隔绝状态中,倒也不失为一种精神粮食。这年九月号上发表的杨放同志记录翻译的《阿诗玛》片断,更使得《诗歌与散文》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读物。虽然它并非这部口头文学作品最精彩的部分,那质朴而又奇异的诗已经闪射出富有魅力的光芒了。而且,这光芒立即吸引了北京的视线,《新华月报》很快加以转载。公刘著、刘粹编:《公刘文存》之第1册“杂文随笔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36页。
(二)彝族史诗《梅葛》
《梅葛》是楚雄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史诗,广泛流传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等县,特别是姚安县的马游和大姚县昙华山。全诗共分四大部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
早在1953年至1954年间,云南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组长杨放、尹钊和柴国麓等人曾到姚安搜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除花灯、莲花落外,也曾搜集过马游等地的彝族《梅葛》的音乐部分。1953年,楚雄中学的教师夏杨和黄笛杨根据杨放的建议,深入姚安土枧槽一带做过一次搜集,由夏杨整理出一份3000 行左右的资料,经黄笛杨于1956年寄交给当时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徐家瑞。1957年5月,徐家瑞亲自到了姚安,在中共姚安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陈继平、郭开云等深入马游山区,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搜集,历时三个月,由陈继平整理出一份上万行的资料,交徐家瑞收存。1958年9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中国作家协会和昆明师范学院,共同组成了以昆明师范学院文史系部分教师和1955 级学生为主的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在中共楚雄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对《梅葛》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搜集。先后进行了五六次反复加工修改,才定稿整理出书,定名《梅葛》,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文学作品,于1959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李云峰、李子贤、杨甫旺:《〈梅葛〉的文化学解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陈永香:《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梅葛〉〈查姆〉为中心》,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三)哈尼古歌
哈尼族是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跨界民族,中国境内的哈尼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红河和澜沧江之间,聚居于红河、江城、墨江及新平、镇沅等县。“哈”即“和”,意为半山坡,“尼”指人或族之意,“哈尼”即居住在半山坡的民族。
杨放先生是哈尼人。他倾注心血搜集、翻译自己族群的音乐文化。他的笔记本手稿“哈尼古歌(3本)、长诗(9本)与杂记(5 本)”(杨放资料编目为Ⅱ-5-01至03),记录整理了《哈尼阿祖逃走》《翻过年第月底》《哈尼十二篇道理》《嫁姑娘》等哈尼古歌与长诗的国际音标发音与汉语翻译。
在整理哈尼古歌的过程中,他收录了哈尼歌手哈呗、祖乙、朱小和、李斗卑、陆万明、李正兴、白金亮等人独唱、对唱的习俗歌。哈尼族传统民歌可分“拉巴”(又称为“哈巴”,哈尼族的一种叙事古歌)、“阿茨”(又称为“阿哧”山歌)、“迷威威”(哭嫁歌)、“阿尼托”(摇儿歌)及祭祀歌和“罗作”舞歌等。杨放主编:《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云南卷》,第17—18页。其中“拉巴”“阿茨”和舞歌中存在多声部的音乐。20 世纪90年代张兴荣等在哈尼发现由主唱与合唱声部短暂重叠所构成的多声部音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乐谱也已收录在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张兴荣记谱的一首哈尼八重唱形式的“阿茨·哧玛”,见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81页。杨放先生很早观察到哈尼古歌中的多声部现象,并由此有对“云南多声民歌”(复写稿1983年,杨放资料编目为Ⅰ-1-3)的系列研究,包括云南彝族(尼苏人)的二声部民歌、纳西族古老的合唱曲《哦热》等等。
1980年7月,杨放受云南省文化厅委托,带了一支民族演唱队参加“中国部分省区多声民歌座谈会”并作了专场演唱,彝族、景颇族、傈僳族、纳西族等7 个民族的民歌演唱深受各省区听众欢迎,杨放主持介绍。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先生在会议总结时盛赞云南队的多声部演唱,并称赞杨放是“一位不多见的民族音乐学者”。
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的编辑整理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从1980年开始,到2016年正式出版,历时36年。该集成共搜集云南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基诺族、蒙古族、藏族、普米族、景颇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瑶族、布依族、傣族、水族、苗族、瑶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回族等25个民族共2813首民歌,分为上、中、下三卷出版。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理论阐释部分是杨放先生领衔的《云南民歌概述》。杨放先生全面描述了云南25 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及宗教信仰,并根据云南各民族民歌的发展历史,将云南民歌的历史分为:(一)远古时;(二)古滇国(战国至东汉)时期;(三)两爨南诏大理国(东晋至唐宋)时期;(四)元明清时期;(五)民国时期。他重点分析了云南各民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把云南民歌概括为山歌、小调、劳动歌、礼俗歌、祭祀歌、舞蹈歌、儿歌等类型,分析其音阶调式、旋律特征、节奏特征以及多声部民歌特征。他这样总结云南民歌旋律特征:
①大幅度攀升或递降的阶梯式进行。前者如藏族山歌[央]、汉族[嵩明山歌]首乐句,后者如白族单句式山歌[阿勒勒]、弥渡汉族山歌[田埂调]首乐句及宾川汉族小调[赶马调]中“欧—斗”的行腔。有的表现为二者的结合,如禄丰汉族山歌[倒扳腔]。
②级进音程构成的波浪式进行。如大部分傣族民歌,部分布朗族民歌。
③跳进音程构成的跃进式进行。如[剑川洱源白族调]、双柏彝族车苏人[四弦调]等。
④真假声交换形成的断层式进行。如彝族聂苏人曲子、晋宁彝族[小彝腔]等。
⑤抒情性与叙述性旋律的对比式进行。大部分山歌类民歌中,抒情性衬腔与述说性实词乐句(段)的对比均属此种。
⑥骨干音构成旋律的分解和弦式进行。如红河彝族、哈尼族由5↓724 构成的[罗作]、[追撵]、[三步弦],彝族撒尼人、阿细人由5135 构成的[月亮歌]、[月琴调]、[三弦调]等。杨放、王群执笔:《云南民歌概述》,杨放主编:《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云南卷》,第36页。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入选的2813首民歌是从云南各地市县搜集整理遴选出来的。为使云南各地的集成资料能够价值最大化,杨放先生倡导出版云南各地民歌集丛书。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化局1982年编印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卷·傣族民歌分卷》(上下册),云南省玉溪地区文教局群众艺术馆编印的《玉溪地区民间音乐资料》(第一至五辑),还有1981年至1988年持续整理的内部资料油印本等等。
杨放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是一本厚重的民间歌曲文献,不仅在音乐领域内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对民间诗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整理民歌的过程中最难的是翻译歌词,来自云南省民委、云南民族大学及各地州县的很多同志参与翻译,可以说是云南的音乐工作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才得予正式出版。
四、茶马古道之马帮民歌系列
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条贸易交流之路。自从唐代开始,我国多民族之间的茶叶与马匹的贸易日益繁盛,在历史上形成了著名的“茶马互市”,其是时西部各民族与藏族之间发生的以茶换马或马易茶的商贸往来。在滇、川、藏“大三角”的崇山峻岭之间,逐渐形成了3 条主干线: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每条主干线上又有无数条支线,并延伸至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界,共同构成了规模巨大的交通贸易体系。20 世纪90年代左右,木霁弘、陈保亚等6 人实地研究考察之后,正式将其命名为“茶马古道”。
马帮文化是“茶马古道”的文化主体。马锅头们前赴后继赶着牲口传唱着丰富的马帮民歌。杨放先生对茶马古道多元文化融合的马帮民歌有系统地关照,主要体现在《数地名》《大赶马调》《小赶马调》《篷子客调》等的记谱和研究上。
杨放先生整理记谱的马帮系列民歌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大理州人李莼。杨放先生把他请到昆明,在亲人般周到照料其食宿起居的情况下,记录了他演唱的《数地名》《大赶马调》《小赶马调》和《篷子客调》等。李莼先生酷爱民间音乐,进过文工团,经过商,失过业,伐过木,曾以木匠手艺糊口。他是明代自北方来滇的军家后裔,其上辈在下关(今大理市下关镇)开马店。李莼曾整理过20世纪40年代以来传唱于巍山北部地区的马帮民歌《赶马调》。温国斌、杨玉莹、刘品贵演唱,张金锡、李莼搜集整理:《赶马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杨放仔细聆听、记录,经夜以继日辛苦,终于在有生之年全部记谱保存了这些异常珍贵的传统音乐财富。
(一)《数地名》
李莼演唱的《数地名》实则为马帮在茶马古道上的商旅行程线路图:始于缅甸北部,然后历经中国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最后转回到云南省,含中缅二国66 个市县地方和地点(指并不具体属于哪个行政建制区域,涉及具体地名100 余个)。歌曲真实记录了清代至民国年间云南马帮(大理下关帮)的运输路线与真实情景,歌词中地名多数按行走路线,叙说了一条横亘大西南的环状的马帮旅程线路。这是一份纵贯时空的音乐文献地图— —乐歌马帮路线图!
野人山前花正开,花正开,(注:野人山,又名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和中国云南相邻地区)瓦城驮出象牙来,象牙来;(注:瓦城,缅甸北部曼德勒省省会曼德勒市别称)盈江竹楼傣家女,傣家女,(注:盈江,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好似芙蓉出水来,出水来。
博南古道青石板,青石板,(注:博南古道,汉时云南南华至永平路段,因永平有博南山并名为博南县而得名;青石板,一指若干路段用青石板铺成,一指当地有此地名)南津渡过彩虹桥,彩虹桥。(注:南津,应为兰津,澜沧江古名;南津渡,应为兰津渡,澜沧江渡口;彩虹桥,即霁虹桥——澜沧江铁索桥)杨德鋆:《极其珍贵的西南丝路口传音乐文献— —对著名音乐家杨放搜集马帮民歌数地名〉的注释与研析》,《民族音乐》2014年第6期,第50—58页。杨德鋆教授该文注释有160多条,地名注释非常详细。。
据《数地名》编列如下西南丝路—茶马古道路线(见表1)。

表1 《数地名》与西南丝路—茶马古道路线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系统整理记谱“茶马古道”马帮民歌时正值杨放先生的晚年,他2000年、2004年先后做了膀胱癌手术和结肠癌手术,其后又四次脑梗,每次只要病情稍稍稳定,他就在病床上继续完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的审稿工作,并听记马帮民歌。李莼唱的《数地名》,杨放先生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听记长达一年多。杨放先生夫人唐敬老师回忆说:“原来《数地名》是用集成用的大稿纸写的,杨老师想用稍小一点的稿纸重新抄一遍,但第三次脑梗后右手写字不灵活了,写简谱还可以,但小节线、增时线、减时线都需要用一个小米尺划才能保持直线。歌词部分就委托文印室打印,字稍大点,字距稍宽一点。杨老师把每一个字剪下来粘在谱子下边,有时粘歪了,就用小剪刀、小刀把该字剪下来,在谱纸背面打个补巴,等面糊干了又把字粘上去(见图2)。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做这种细致的工作,又是一年总算完成了。可能正是完成了《数地名》的整理,神经松解了,待到第四次脑梗发作,这次是无力回天了,杨老师安祥的走完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音乐之路!”

图2 杨放先生亲手粘贴的《数地名》,存放在杨放资料编目(Ⅲ-3-1-01至02)
(二)《大赶马调》《小赶马调》
《赶马调》如其歌名所言,就是赶马的人们为了排解寂寞、无聊的时光,用歌声来打发时间,其内容主要以马帮文化、茶文化生活场景为主,体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和抒情性特征,其音乐风格粗犷、自由、热情,旋律起伏直接在跳跃中进行,许多八度的大跳赋予赶马曲调极富云南高原地区音乐的张力、豪放之感。
杨放撰文《赶马调》云:“赶马人常年跋山涉水,一路以歌为伴,走多少路,唱多少歌,唱给天,唱给地,唱给山水草树,唱给风雨流云,唱给最为亲近贴心的不会说话的驮骡驮马伙伴,除了可闻马铃叮咚和雀鸟鸣叫宛若与之和声对咏外,绝大多数时候无人应声,也极少有人会当回事认真听上一听。”《赶马调》存放于杨放资料编目Ⅲ-3-7至15,主要包括《大赶马》(23 首)、《小赶马》(10首)和《放马调杂曲》(12首)等。
(三)《篷子客调》
“篷子客(棚子客)”指的是古时流落云南的“罗姆人”(吉卜赛人后裔)口传流浪民歌和下关、祥云赶马人歌。
1949年云南省民政厅编的《云南省边民分部册》(上下册合订本),附表中有13 种人因无可靠材料无法核定其族类。其中“罗姆人”100 人,指的就是流浪在中缅边境线上的“棚子客”。此书说明“棚子客”在当时已引起关注,但所列数字不准确,当时流落镇康县(含永德县)的“棚子客”不止100 人。解放后,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明确规定,凡总人数达不到4000 人以上的种族和人,以他们所在当地的族别及所操语言划定他们的族别。从此,勐楞等地的“棚子客”都划归为汉族。
20 世纪50年代,还流浪在两江走廊的永德、凤庆、双江、耿马、镇康直到缅甸的果敢、腊戍,如今除永德的土锅田外,在镇康的勐楞,居住着流落此地的棚子客后裔。张锦繁主编:《临沧记忆》,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其中镇康、永德、耿马等地曾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支点,是通往缅甸、印度等国的陆上捷径之一。由此推测,“棚子客”从印度流浪而来。张龙明主编、李德栋等撰稿:《秘境临沧之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流落到云南勐楞等地的棚子客可分为两类,一类身材高大,深目高鼻梁,称为“大种棚子”,不养猪,不吃猪肉,但养牛,吃牛肉,比较富裕,住在白帆布棚里,有的还有枪械自卫;另一种叫“黄棚子”。“大种棚子”可能是吉普赛人,而“黄棚子”是模仿吉普赛人生活习惯和谋生手段的本地人,并非真正的吉普赛人。郁知非:《书窗杂谈》,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棚子客”习惯漂泊流浪,能歌善舞。演唱时有乐器配乐。女人(“唱婆”)有口弦、竹篾弦;男人有小三弦等。凤庆锅头苗二能唱全本《大赶马》,《小赶马》和各种赶马调,是迤西帮中最闻名的“调子客”。“棚子客”唱的调子常是“连环腔”(一种几个曲调组成的组歌),变化大。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杨先生根据李莼先生演唱的“篷子客调”记录了12 首。这批“篷子客调”曲调是李莼先生传承自20 世纪50年代“篷子客”歌手陶桂花、何小玉所传唱的歌曲。“篷子客调”据称共有“九板十八腔”“七十二调”“大曲”“小曲”类。罗姆人虽为吉普赛人后裔,但汉化程度较深,所演唱的曲目均为汉族音乐。
“云南省西部地区《蓬子客调》(罗姆人后裔民间歌曲)”存放于杨放资料编目为Ⅲ-3-8,标记李莼采集记录、杨放勘校编辑蓬子客调12首。
除以上《数地名》《大赶马》《小赶马》《蓬子客调》之外,杨放先生记录的李莼先生传唱的还有“云南省西部和地区汉族民间传统歌曲《烧大火上歌台》”,存放于杨放资料编目为Ⅲ-3-9,含《过山调》《二十四个亲老表》《满老腔》《十大姐》《十大哥》《梳头调》《绣荷包》《毗雌河调》《马腊摩调》等15首。
结 语
杨放先生毕生根植于云南这片悠久且多元的五彩文化沃土,是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和研究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第一,杨放先生毕生搜集整理记录了云南各族民歌、乐曲5000 余首。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民歌》(第一集)、《云南民间音乐》(第二集·花灯音乐)、《云南山歌》(第一集)、《玉溪花灯音乐》《云南民族民间儿童歌曲选》《彝族曲子舞曲选集》《云南各族情歌100 首》《拉祜族张老五小三弦曲集》《哈尼族民间器乐曲》《哈尼族歌舞曲》《民间器乐曲》《姚安白彝族音乐》《蒙自花灯音乐》等。其研究论文《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云南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形态与民间音乐》等,充满了真知灼见。
第二,1949年杨放先生发掘记录了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对《阿诗玛》的发掘有首创之功。此后,他还搜集、整理、发表了纳西族民间长诗《猎犬》、彝族民间长诗《梅葛》《独阿牟老祖爷》和哈尼古歌等近20 余部云南民族叙事史诗。
第三,历时三十载,杨放先生领衔主持编纂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这一厚重的多民族民间歌曲文献,且具有跨学科的珍贵资料。这一文献的结集,也为云南民族音乐事业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并繁衍了大量的云南音乐研究的地域性成果。
第四,杨放先生创作了歌曲30 余首,还尝试创作了器乐曲和歌剧,其创作积极探索了云南音乐素材与西方作曲技法的融合。代表声乐作品有《营火燃烧在广场上》《野草谣》《昆明,美丽的山城》《盘江曲》(合作)等,还改编、演出了儿童歌舞剧《幸运鱼》《金龙袍》等。此外,还创作了具有傣族风格的小提琴曲《大青树下》和管弦乐曲《欢庆胜利》等。这些作品经多次演播后被认为是“溢满云岭高原色彩的佳作”。
第五,杨放先生与李莼先生合作,录音、记谱保存了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民歌系列——《数地名》《大赶马》《小赶马》《烧大火 上歌台》《篷子客调》。这些民歌是马帮民歌中最重要的资料。我们感念演唱者李莼先生和记录者杨放老师的功德!
第六,作为音乐教育家,杨放先生早期在昆华女中、长城中学做音乐教员,在云南省音协进行音乐干部培训,后长期执教于云南艺术学院,先后启蒙和培养了黄虹、张难、朱绍玉等一批杰出的音乐家。
时值杨放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杨放先生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厚爱坚守与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