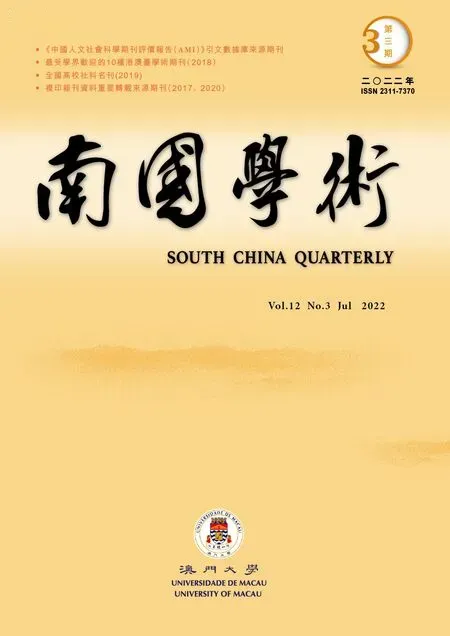內憂外患與文化競爭
——嘉道年間朝野對基督教的認識與反應
吳義雄
[關鍵詞]清朝與基督教 嘉慶帝 魏源 梁廷枏 文化競爭
近代的中西交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隨着基督教在華事業而展開。基督教在中國的擴展既導致兩種文明相互交匯的良性互動,也帶來深刻的矛盾和衝突,中西關係的整體演變亦深受其影響。中外學界對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國這兩個時段基督教在華傳播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衝突問題,一向關注較多,成果豐碩,但對處於這兩個時代之間的清中葉嘉道年間的相關問題,則較少措意①近年的研究,參見陶飛亞《懷疑遠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緣由及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一文對乾嘉時期相關情況的討論。,以致學界對基督教與中西文化關係變遷歷程的認識並不完整。在筆者看來,這一時期清政府在政策方面前承清前期的“禁教”措施而將其推至極致,又因外力侵逼而被迫“開禁”,官方和民間對基督教的認識和反應在具體歷史背景下,歷經變遷而呈現複雜形態,對晚清民國時期社會和思想具有重要影響,值得加以專門探討。
一 政治動蕩與嘉慶君臣對“邪教”的戒懼
清朝的禁教政策在康熙末年出臺,雍正、乾隆兩朝採取愈益嚴厲的措施防範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在查禁傳教活動的同時,諭旨指“西洋人傳教惑衆,最爲風俗人心之害”,對傳教士及相關人等加以處置。②“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故宮博物院 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第1冊,第24頁。但最爲嚴厲的政策是在嘉慶朝出現的,這與嘉慶朝發生的白蓮教等民間宗教大規模造反的具體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嘉慶十年(1805),即延續八年的白蓮教大起義被鎮壓下去的次年,北京發生了德天賜傳教案。德天賜乃是在北京天主教西堂“當家”的意大利籍傳教士,是年因私自與澳門外人通信遭獲,引起清廷注意。軍機處報告說,德天賜信件中有登州到廣平一帶的“路程圖樣”,認爲應加以警惕,將德天賜革去六品頂戴,交刑部審訊。③“軍機處奏傳訊西洋人德天賜私自寄信所供含糊請交刑部研審片”,《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0~21頁。刑部審訊內容圍繞信教民人擔任神甫等情況進行,德天賜在審訊後交待天主教在北京活動並向各省人士傳教的情況。而後續拿獲的信衆又供出其於“傳教惑衆”之外,還有“近年編造漢字西洋經卷三十一種流傳各地,冀圖易於煽惑入教人衆”的情況。④“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5頁。此後,德天賜被發往熱河交厄魯特圈禁,協助傳教士的中國信徒則被一一懲治。嘉慶帝在處理此案時,曾命官員查看所獲經卷。軍機處奏報查看結果,認爲“尚無悖逆詞句,惟多係荒誕支離之語”,他們將“謬妄尤甚”之處貼黃以呈御覽,建議銷毀了事。⑤“軍機處奏閱看西洋堂私刻書籍謬妄尤甚者貼簽呈覽片”,《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8頁。可見,在這些官員心目中,與“荒誕支離”的教義陳述相比,是否有“悖逆詞句”纔是最值得優先關注的事項。
但是,作爲帝王的嘉慶帝卻對那些教義書籍非常重視。他親自調閱了那些經卷,並在禁止旗人信教的上諭中,引用從傳教書籍中特別摘出他認爲的“支離狂妄”“怪誕不經”的教義:
如《教要敍論》內稱:其天主是萬邦之大君。《聖年廣益》內稱:所繫降生之耶穌係平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稱:中國呼異端爲左道,未必非默默中爲承行主之而有是言。又稱: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棄邪歸正,聖教大行,未有不長治久安者。又稱:我教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稱:憑他有道之邦,多係世俗肉身之道。又稱:聖人欲乘此機會傳教中華。又《婚配訓言》內稱:外教者如魔鬼奴才等語。
這些言論在教內當屬常識性論點,但在身爲君主的嘉慶帝看來,無一語不是對其統治地位的挑戰。因爲,這些言論意味着帝王(政權)的地位低於天主(神權)的地位,在信奉此種教義的信徒的眼裏,他這個自以爲“君臨天下、統御萬國”的君主,卻次於另一個“大君”。這還不僅是簡單的名位之爭。在他看來,這些教義還潛藏着不可測的危機:“若不及早嚴行禁止,任令傳播,設其編造之語悖謬更有重於此者,勢不得不大加懲辦。與其日後釀成巨案,莫若先事豫爲之防!”①“申明例禁傳習西洋教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8~29頁。他要預防的是,君主絕對的、最高的權威的動搖所帶來的政治危機。如果聯繫到白蓮教那種千禧年式的精神動員在一定程度上與上述言論的某種類似之處,剛剛平息白蓮教之亂的嘉慶皇帝,對這種鼓吹“萬邦大君”、聚衆舉行神秘崇拜的教義和宗教,自不能不心生惕厲,令將此類經卷銷毀。
嘉慶十六年(1811)發生的扶風教案,引起了更爲嚴重的後果。陝西巡撫董教增奏報,在扶風縣破獲天主教傳教案件,案犯張鐸德供稱,其於“乾隆五十七年到京城天主堂學習念經,曉得經內道理。嘉慶四年經南堂大人湯士選考得四品。西洋以品多爲貴。六年,湯士選見我學識甚好,又考得七品”,其後奉派到晉、陝傳教。董教增還奏稱,“入教各名姓稱,爲教譜所載,人數衆多,且散在各處”;“該教仿效職官,擅立品級,且令分路傳教,主教之人並有教化皇名目”。他認爲,須按以往歷次案例,對涉案人員加以懲治,並要求清廷關注作爲“天主教根抵(底)”的北京西洋堂。②“陝西巡撫董教增奏拿傳習獲天主教人犯訊明酌擬並請查拿西洋堂之總牧司鐸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37~38頁。這些通過訊問得到的信息牽強附會,但引起清廷的極大注意。董的奏摺於二月二十三日發出,嘉慶帝在二十六日即發上諭,特別強調:“張德鐸供出,彼教中人竟有教化皇、總牧、司鐸等名目,並仿效職官設立品級,以品多爲貴。伊係內地民人,膽敢混入西洋堂習教誦經,考得品級,倚仗總牧字諭出外傳教,煽誘多人,不可不嚴行究辦。”並令管理西洋堂關於查究西洋堂情形,令董教增查明其所稱“司牧、總鐸分在各省共有若干名”。③“軍機處寄陝西巡撫董教增除飭令管理西洋堂之祿康等查拿傳教人犯外所有拿獲傳習天主教之張德鐸著發往伊犁爲奴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39頁。後又指令他對張鐸德等反復訊問,以與北京方面對西洋堂的查究相配合。嘉慶帝所引述的上述信息,在他看來其中包含了邪教作亂的架構或雛形。
與嘉慶帝的強烈關注相配合,陝西道監察御史甘家斌於四月十九日上摺,鑒於“西洋天主教蔓延無已”,建議皇帝“敕部嚴定治罪專條及失察處分”,即就禁止天主教之蔓延傳播,追究各級官員失察之責,並認爲天主教與民間秘密宗教“同屬邪教惑人而治罪獨輕”爲不當,宜擬訂並頒行專門法條。④“陝西道監察御史甘家斌奏嚴定傳習天主教治罪專條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1頁。刑部在奏報德天賜案處理結果時已提出“查天主教並無治罪專條”,衹能照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查辦天主教諭旨辦理。參見“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6頁。嘉慶帝在摺上之日迅即諭令核議具奏。這樣就正式啓動了針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立法程序。
刑部在一個多月後即依《大清律例》及乾隆、嘉慶兩朝歷次上諭,擬訂了詳細而嚴厲的懲處專條。其中,對傳教士和教徒的最高刑罰是死刑;對失察或失責官員按責任輕重分別加以處分。⑤“管理刑部事務董誥等奏酌議御史甘家斌所奏之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4~46頁。以往官府對信徒的鎮壓是針對他們協助傳教的具體行爲,而非針對信仰這種精神生活。即使是有些關於對普通信徒進行嚴訊,但從未有過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民衆信教。這個專條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所依據的《大清律例》條文爲,以“左道異端之術,惑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煽惑人民”分別首從予以懲處,即將基督教與異端邪教完全等同。刑部上奏的同一天,嘉慶帝頒諭,令將刑部所奏專條關於禁教的內容付諸實行。嘉慶帝的上諭明確規定:“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⑥“頒定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並遣令不諳天文之西洋人歸國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6頁。稍後,吏部和兵部另外擬訂了懲治失察或處置不力官員的條例,嘉慶帝頒旨准行,以促使地方官嚴查。此外,京城官員對西洋堂進行清查,驅逐了幾名西洋人,直隸官員也奏報查獲傳教人犯。⑦相關材料見《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5~55頁。
這整個過程,構成中西交往史和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一次重要事件。爲懲治基督教在華傳教設立專條,已屬創制;而將對基督教的信仰正式入罪,即不僅懲處西洋傳教士和協同傳教的中國信徒,而且將信教作爲一種罪名正式入罪,這在禁教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次立法行爲使清朝的禁教政策真正達到了高峰。這個過程顯示,嘉慶帝對扶風教案如此升格處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張德鐸所供天主教會的“內部情況”,也就是品級、教化皇、總牧、司鐸等名目。這些名目實際上並無政治含義,但看上去又很像某種會導致重大事變的權力結構,而且天主教又有着遍佈全國多個省份的活動網絡或組織,帶有神秘色彩,故引起十分擔心內亂的嘉慶帝高度的政治敏感。御史甘家斌的奏摺說:
查該教不敬天地,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罰,種種欺公藐法,背名畔義,實屬以邪害正,情理難容。既經造書煽惑,動致數千戶人民,泯滅綱常,背違法紀,即係妖言惑衆。其設立十字架,誘衆禮拜,亦與隱匿圖像、燒香集衆者情節相同,未便治罪獨輕,致無顧忌……①“陝西道監察御史甘家斌奏嚴定傳習天主教治罪專條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1頁。
這段話將嚴禁天主教與防範亂萌的關係非常清晰地表述出來了。在統治者看來,服從於朝廷之外的精神權力、倫理、法紀而無法約束的民衆是極爲危險的,何況這種宗教與民間莫測的結社具有某些類似的特性和氣質,其所提供的思想資源也容易被後者利用以“煽惑”民衆。
當然,天主教在歷朝高壓下依然持續傳播,各地均有奏報,則是促使清廷下決心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的大背景。
董教增等辦理扶風教案,亦起獲經卷。他注意其中有勸人省身改過的內容,但重點報告的“煽惑愚民邪說”是:“人有三父母,一爲生我之父母,一爲治我之父母,惟天主爲大父母。得罪於生我治我之父母其罪小,得罪天主其罪大……受苦受罪即升天堂之價值。此愚民好新喜異,既經習教,雖受刑責而不肯背教、執迷不悟之根蘊也。”這與嘉慶帝的關注點是相同的。嘉慶帝認爲比蔑視君上權威更爲荒謬的言論有:“聽父母所命相反於聽天之命爲大不孝”,他評論此爲“蔑倫絕理,直同狂吠”;又指“不聽善勸絕不免天主永罰”之語爲“肆口亂道”。②“申明例禁傳習西洋教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9頁。經書提倡效忠宗教權威而非朝廷權威,當然會令統治者異常警惕。扶風所獲之經卷也被董教增等“概行銷毀”。③“陝西巡撫董教增奏拿傳習獲天主教人犯訊明酌擬並請查拿西洋堂之總牧司鐸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36頁。
嘉慶年間,在上述將信奉天主教作爲罪名入刑後,官方在處理相關案件時,便遇到一個頗爲棘手的問題,即如何辨別誰是信仰“邪教”的罪民?當被逮治的教民中有人願意“去邪從正”時,又如何鑒別其是否真的棄教向善而非冀圖蒙混過關?清政府逐漸形成一個鑒別天主教徒的重要方法,即令犯人“當堂跨踏十字架”。
據咸同年間的史學家夏燮說,這個方法的來源是,嘉慶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率天理教衆造反,“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七七爲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故“嘉慶中葉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齡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鞫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豚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與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夏燮認爲,“此皆出自中土無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衆謀逆……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④〔清〕夏燮:《中西紀事》(合肥:黃山書社,1988),高鴻志 等點校,第28、29頁。也就是說,跨或踏十字架是清朝官府在審辦案件過程用來對付白蓮、八卦等教教徒的,原本與天主教無關。
既然如此,天主教又爲何還是被與內亂聯繫在一起的呢?夏燮的說法是,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使阿美士德來華,引發在華西人之“觖望”與“蓄念”,“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疏,益無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雜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於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起矣”;而鴉片戰爭後法國迫使清朝弛禁天主教,“各省會匪無不以拜會之名,歸宿於天主教”。①夏燮:《中西紀事》,第28頁。按:後一句當指太平天國之拜上帝會。
這個說法從防杜內亂的角度解釋了嘉慶朝對天主教或基督教極爲警惕的原因,但未能說明清朝採用跨踏十字架來辨別基督教徒的做法及其起源。嘉慶十年(1805),德天賜案發生,刑部審訊入教信衆時,其中一些“被惑入教”者就有“情願出教,並據踩踏十字”之舉②“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5頁。,說明早在林清、李文成之變前就有這種辨別“正邪”的方法。而且百齡始任兩江總督在嘉慶十六年(1811),晚於德天賜案,故令人跨踏十字並非如夏燮所云是他的發明。在其他案件中,還有令犯人跨踏十字架,以確定是否天主教徒的例子。嘉慶二十年(1815)廣東當局逮審“私通”英人的通事阿耀(李懷遠)③吳義雄:“國際戰爭、商業秩序與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視”,《史學月刊》3(2018)。,嘉慶帝懷疑阿耀“恐有學習天主教之事”,諭令兩廣總督蔣攸銛“再提該犯研鞫,並令其試跨十字架。如該犯曾習天主教,無難一訊而知”。④“軍機處寄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再訊私通夷人之李懷遠曾否學習天主教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4冊,第24頁。蔣攸銛遵旨再訊阿耀後報告,“臣等複令當堂試跨十字架,並踐踏十字架之上。該犯立即跨架踐踏,毫無難色”(“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復訊私與英夷交好之李懷遠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4冊,第27頁)。同年,四川查禁天主教案,亦有18名教徒信徒“當堂踩踏十字架,情願具結悔教”(“四川總督常明奏審辦西洋人在川傳教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4冊,第35頁)。道光十年(1830),江蘇一個願意悔教的白維一在衙門“跨過十字架,如今情願再跨”(“兩江總督蔣攸銛奏遵旨查訊白維一喊控皖鄂有西洋白蓮邪教一案情形”,《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3冊,第26頁)。這些都說明,這個做法在當時是針對供奉十字架、聚衆崇拜的天主教的慣常做法,但也適用於在其眼裏具有可疑相似度的其他“邪教”如白蓮教。夏燮云其起於針對白蓮教,這說法衹能存疑備考。
無論如何,在跨踏十字架問題上,清政府顯然將天主教(基督教)與白蓮教等中國民間秘密結社聯繫在一起,都表明查禁天主教的一大動因是對內治隱患的關切,而對天主教的認識,則着落在認爲它是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邪教”。⑤陶飛亞認爲,乾隆十三年(1748)一道上諭首次將天主教稱爲“邪教”〔“懷疑遠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緣由及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9):44〕。這種認識在嘉慶朝的特定政治形勢下顯然較以往更爲明確。他們當然也承認天主教的宗教屬性⑥“申明例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3頁。,但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加以禁止,則因認爲天主教是一種潛在的可能引起政治變亂的“邪教”,在政治本質上與白蓮教等並無不同。
二 開放教禁之際的憂思
這種對“邪教”的戒慎恐懼,持續到道光時期。在經歷了一場影響巨大的對外戰爭後,清朝官紳對於外來宗教原本就有的警惕和疑懼,自難消退。但戰爭的失敗卻使得統治者面臨必須解除教禁的新形勢。在外來壓力下,基督教必須開禁,道光君臣需要將其與“邪教”脫鈎;同時,他們的疑懼尚在,又需籌謀對策。
當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在奏請弛禁天主教時,他爲清廷想出解除教禁的理由是,天主教“二百餘年,並未滋事,究與白蓮、八卦、白陽等項邪教不同。嗣因其藉教爲非,致有誘污婦女、誑取病人目睛之事,是以定例嚴禁”。這就試圖將天主教與此前“邪教”的認知脫鈎。耆英還說,自禁教後,朝廷執行禁令實際上寬鬆,“京中聞有破案,而各省拿辦者尚屬無多,亦係因其尚無不法重情,姑免深究,幾與禁而不禁無異”。這樣的說法,顯與雍正以後日益峻刻的禁教史實不符,目的是爲了將道光帝從既面對法國人的軍事壓力,又須顧慮禁教政策的傳統,並需要在中外臣民中維持“天朝”的體面的尷尬境地解脫出來,同意“將中外民人,凡有學習天主教並不滋事爲非者,概予免罪”,以便“夷情得以馴服,免生枝節”。①“耆英奏請將學習天主教之人稍寬禁令以示羈縻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第6册,第2877~2878頁。按:此摺日期爲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1月11日)。在此之前的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道光帝在接到耆英的上一封相關奏摺後,即在諭旨中指示耆英,“諭以天主教係該國所崇奉,中國並不斥爲邪教,實爲我國習教之人,藉教爲惡,是以懲治其罪”,並要求耆英“隨時體察夷情,妥爲駕馭,不可節外生枝”(“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75頁)。這實際上是暗示耆英,可在這一點上讓步。耆英11月11日奏摺的表述,顯爲響應道光帝的諭旨,並爲道光帝發佈弛禁上諭提供表述策略。
道光帝對耆英的用心亦甚瞭然,在諭令中說道:“天主教來自西洋,在中國並未指爲邪教,亦未嘗嚴申禁令。從前因有藉教爲惡之人,是以明令刑章,懲治其罪,與該國之天主毫無相涉”,命弛天主教之禁。②“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80頁。道光帝這一說法,是爲了遮掩屈服於外人壓力而解除教禁之難堪處境,而不顧雍正後不斷有傳教士被驅逐、監禁乃至處死的史實。但他將對天主教的禁止、壓制解釋爲針對國內“藉教爲惡”之人的舉措,卻也道出了幾代君主禁教的一個重要着眼點。
道光帝在指示耆英“即許以開禁,亦無不可”的同時,亦強調“惟此事大有關係,萬無明降諭旨通諭中外之理,其應如何措辭曉諭該夷,准其開禁之處,着該督悉心籌度,既可令該夷輸服,且不至有傷大體,即行酌擬檄諭,迅速奏明,候旨遵行”。③“廷寄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80頁。耆英在奏摺中強調作此妥協實是計出無奈,稱“屢經往復辯難,告以法度,曉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耆英奏天主教弛禁酌擬簡明節略附陳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99頁)。這表明,在當時清廷君臣看來,宣佈天主教並非“邪教”乃是出於不得已。這段話反映了道光帝爲因應局勢不得不向法國人妥協、又恐怕這一政策變更觸動既有意識形態而力圖遮掩的心態。宣佈天主教並非“邪教”,不過是權宜之計。當法國人進一步提出要求,將弛禁天主教的決策在各地“張挂曉示,使人共曉”時④“耆英等又奏法使請出示習教免罪並將康熙年間天主堂址給還習教之人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48頁。,道光帝的反應是:“現在習教愚民既准免罪,已屬曲順夷情,若再令地方官張貼告示,豈非驅安分良民群相入教,斷斷無此體制……何得妄事猜疑,強我以萬不可行之舉?”在法國人的壓力之下,他最終同意其要求,但在上諭中不忘強調“不可假託天主教名目別習青蓮、白蓮等教”。他在公開的上諭中說:“天主教係勸人爲善,與內地青蓮、白蓮、八卦等教迥不相同,自不妨俯如所請。”⑤“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50、2953、2955頁。但在耆英奏摺上的硃批云:“時事變遷,以至於此,若一味拘泥,又難集事,衹可稍從權宜。”⑥“耆英等又奏法使請出示習教免罪並將康熙年間天主堂址給還習教之人片”硃批,《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54頁。其內心的真實感受和想法不難體察。
正是因爲對“夷情”的畏懼無法消解對內患的戒備,即便後來被當作“媚夷”典型的耆英,在對法國人不斷讓步的過程中也考慮到,“惟是習教之人散在各省,若准其聚會,則流弊滋多。況近年以來,白蓮、八卦等教屢經懲辦,而青蓮教復正在查拿,倘聞知天主教奉有免罪新例,因而詭託其中,尤爲不可不預防其漸”。他命委員與法使拉萼尼交涉,聲明天主教之禁固然已弛,信徒可舉行崇拜活動,“但將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爲非,及別教之人混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⑦“耆英等奏法人已就範圍約册亦經互換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35頁。弛禁之後,清廷上下對基督教的防範仍然較嚴,保持高度警惕。按《中法黃埔條約》等的規定,西人可在通商五口內進行宗教活動。即是說,根據這些條約,在五口之外的傳教活動仍屬非法,需加取締。故在《天津條約》簽訂並換約之前,清政府官員充分發揮將傳教士活動範圍限於五口的條約權利,將到五口之外活動的傳教士拘押並解送離境。⑧如1846年,駐藏大臣琦善奏報,將到西藏活動的兩名法國傳教士解送出境(“琦善等奏盤獲傳教法人並取出書文錄供呈覽”,《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79~2980頁;道光帝諭旨及其他關於奏摺見第3005~3006、3008~3010頁。另見第3040~3041、3043~3045、3046~3049、3066~3067、3142~3143、3160等頁)。咸豐帝即位後,1850年對山東歷城丁光明案的處置,見《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1册,第62~66頁;對法國人孟鎮聲在直隸安肅縣安家莊傳教的處置,見《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1册,第255頁;對該地民人“習教滋事”的處置,見蔣廷黻 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咸豐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1册,第167~169頁。
耆英雖與西人商議將宗教活動限於五口之內的條件,但通商五口均爲繁華都市,華洋雜處,一定會生出令清政府擔憂的問題。1848年“青浦教案”即是衆所周知的典型案例,此處不贅述。在此之前,弛禁上諭剛公佈的道光二十五年底(1846),閩浙總督劉韻珂和福建巡撫徐繼畬即上摺陳情,奏報法國公使拉萼尼到廈門,“其意實在傳教”。他們認爲,天主教禁既弛,傳教、習教等自應“聽從其便”,“均免治罪”,但“近來人情變幻百出,詭詐萬端”,社會不穩。“從前例禁森嚴,尚有借傳教名色作姦犯科之事。今防禦既開,更難保不多方煽惑,任意招搖。或別教藉以影射,或藉教別作詭謀,或犯罪而投入教中,或窩匪而冀逃法外。是一匪入教勢必呼朋引類,群匪入教難免樹黨逞奸。”①“劉韻珂奏密陳習教流弊由”,《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道光朝)》,第4册,第167~169、169頁。字裏行間依然充滿了對傳教士和信衆的戒備,二人的擔憂主要是弛禁將帶來的內部政治亂象。但既然外教傳入會導致內部隱患,則“匪徒影射”問題就必定牽涉外國,外人不察,“衹知習教爲善,不知藉教爲匪,一聞查拿,必以違背成約,有挾而求。甚或明知爲匪而多方袒護,肆意刁難,更費周章。即如本年江西、湖北等省拿辦邪教,該夷聞知即以違約相期,嘖嘖饒舌……是查辦稍有未善,不特地方難期靜謐,並足釀搆邊釁,其流弊已不可勝言”。②“劉韻珂奏密陳習教流弊由”,《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道光朝)》,第4册,第167~169、169頁。道光帝閱摺後,在上諭中要求他們既要防止“邪教惑衆滋事”,又不可引起“民情滋擾”。③“上諭”,《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道光朝)》,第4册,第174頁。可見,在此時期,教案尚未成爲中國與列強間的突出問題,但劉、徐摺內所描述的這種情形,已顯現出同光年間教案蜂起的模式。故在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傳教所導致的政治問題,已非乾嘉時期那種純粹的內治憂患,也牽涉到令清廷極爲頭疼的外交困局。不過,對內部安定的憂思在此時仍是清廷上下關注基督教問題的最直接原因。
關於基督教的憂思非僅來自廟堂之上,也來自關注時局的民間人士。道光年間的著名學者張穆就認爲,世人“或謂天主教與白蓮教等,其極熾不過與林清、祝現止矣,何能爲?是大不然”。因爲民間的那些“邪教”,“爲之首者即至愚無教之民,州縣官但一出示禁之,輒伏不敢動”,“今揆茀夷情勢,儼然與中國並大,方且要所挾持,不畏我皇上,何況群有司哉?”沿海入教之民“倚敵國爲逋逃藪,負隅自雄,誰敢過問?”他還認爲,白蓮教等聚衆很多是爲了斂財,天主教則以錢收買民心。更關鍵的是,隨着這種勢力的發展,一旦外國與中國關係破裂開戰,則民、兵從之,“土崩瓦解,旋至立效,恐自古謀人國下人城者,無此速且易矣!……故曰:最爲可慮也”。④〔清〕張穆:《㐆齋文集·茀夷貿易章程書後》,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第138册,第581頁。
咸豐君臣在基督教是否邪教的問題上態度,與前朝基本一致。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曾說:“邪教惑人,大率在斂錢,獨天主教向不斂錢,設堂習經,主於廣行其教。”⑤“訥爾經額又奏天主教自弛禁後相安無事俟南省安定後再行徐圖片”,《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1册,第211頁。這就是認爲,天主教是邪教中不斂錢、衹行教的獨特派別。侍講殷兆鏞一封奏摺中的幾句話則明確地表露了對天主教作亂的擔憂:“臣不知其所謂天主教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其教可爾,何必遊歷各省,仆仆不憚煩苦若是?”⑥〔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趙春晨 點校,第270頁。咸豐帝在關於處置道光三十年直隸安肅縣安家莊法國傳教士孟鎮升的諭令中明確地說:“其傳習邪教,必非僅止安家莊一處,直隸首善之區,豈容此等邪教搖惑人心。”⑦“廷寄”,《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1册,第255頁。此時期士大夫階層多對基督教采取排斥態度。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梁章鉅在文中回顧雍正年間的禁教措施,認爲使“百年污穢,一旦洗濯”,“至今剛逾百年,而其焰復張,甚爲可恨”〔〔清〕梁章鉅:《浪迹叢談·天主教》(北京:中華書局,1981),陳鐵民 點校,第81頁〕。顯示其對天主教的定位仍爲“邪教”。
清朝君臣關於基督教與內亂關係的憂慮,因太平天國運動的基督教色彩而提升。太平天國之後的數十年中,教案此起彼伏,論者多從儒家“崇正學、黜異端”的文化傳統、基督教傳教與西方列強侵華相結合、基督教與中國社會風俗習慣之衝突等多種角度來加以解釋⑧代表性論述參見: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Paul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但清中葉君臣對基督教的“邪教”定位、對傳教運動的擴大帶來政治威脅的深刻憂慮,作爲同光年間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衝突的歷史背景,也是不應該忽視的。同光時期,官紳基於政治原因而反教,主要是因爲傳教運動加劇他們對外來侵略、顛覆的恐懼,但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對外來宗教的疑懼和排斥,則爲這種政治心理提供了歷史的基礎。
三 寬忍與探究:對基督教態度的新趨向
在基督教通過條約取得在華合法傳播權利的情況下,清朝君臣和士大夫階層除了基於政治原因對其繼續採取疑懼態度外,也表現出寬容忍讓的現實態度,而且開始對這種不得不接納的外來宗教加以學術性探究,這是鴉片戰爭後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
按照對中西文化關係史的一般認知,在西方被清朝當作“蠻夷”的時代,基督教不可避免地會被當作“夷教”而遭到蔑視。嘉慶帝在處理德天賜案的上諭中,曾指責所獲經卷宣揚的教義“蔑倫絕理,直同狂吠”,指拒絕放棄天主教信仰的旗人教衆“自背根本,甘心習學洋教,實不齒於人類”,令各“銷除旗檔”。①“發落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各犯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7頁。在1811年頒佈傳教治罪專條的上諭中又說道:“其教不敬神明,不奉祖先,顯叛正道”,故嚴定科條,“以杜邪術而正人心”。②“頒定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並遣令不諳天文之西洋人歸國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6頁。刑部在遵旨擬訂禁教科條時也說:“西洋人囿於方俗,自習其教,原屬化外之民,既爲聖朝覆幬所並容,亦即以不治治之。”③“管理刑部事務董誥等奏酌議御史甘家斌所奏之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冊,第45頁。這種將西洋人的宗教作爲化外蠻夷習俗的說法,是當時的統治者以“華夷之辨”看待中西文化的典型話語。
但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康熙末年的“禮儀之爭”之前,明末清初兩代統治者都對基督教及傳教活動表現了寬容態度。基督教與儒學一度相互交融,徐光啓、李之藻等士大夫入教並被當作該教“柱石”,也說明這種西來宗教並未被當作不爲“天朝”所齒的“夷教”。其實,即使在“禮儀之爭”發生後,統治者仍對基督教信仰表示出寬容態度。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處理宗室蘇努之子烏爾程等私入天主教案,“廷議請即正法”。雍正帝否決了這一提議,理由是,烏爾程等雖然“不遵滿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且“不願悛改”,但其“如此昏庸,與禽獸奚別?何必加以誅戮?”這種言辭顯然表達了對“西洋之教”的極大蔑視,但他又說:“烏爾程等非力能搖動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與否毫無關係。”這就是說,衹要此人沒有政治威脅,其信仰可以寬容,哪怕偏離了“滿洲正道”,那也是他自己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命將烏爾程等交步軍統領圈禁,“俾得窮究西洋道理。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請改過也”,表明他對“西洋敬天之教”也有肯定之處。他還說:“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④〔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第64~65頁。將中西之教並而觀之,認爲各有適用範圍,字裏行間透露出在信仰上可以寬容的意蘊。雍正帝的言論與後來嘉慶帝的言論顯然有着區別。
明末清初這種以中西異俗爲出發點來看待天主教的理念,在鴉片戰爭後再次成爲主流態度。1844年11月,法國公使拉萼尼向耆英提出弛禁天主教問題,“將習教之人,免其治罪”。耆英最初的答覆是:“天主係西洋各國之教,不便行於中國,亦猶中國儒教不能行之西方,何得遽改定例?”拉萼尼又稱,佛教也來自西方,天主教在中國“並未滋事”,“何不可量從寬宥?”耆英又答覆:“中國定例乃係禁中國傳習之人,原來未嘗兼禁外國。即如澳門天主堂非止一處,而米利堅請定貿易章程,亦准其在五口附近地方建堂禮拜。”⑤“耆英奏籌辦夷務漸有條理”,《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道光朝)》,第3册,第1010~1011頁。耆英這種“中西各有其教,互不相涉”的言論,與雍正帝當年的言論在對異教信仰表示寬容方面是一致的。
耆英的這種認識,與他較長時間與西人打交道相關。他曾向道光帝奏報與西人交涉的經歷,固然要使用“夷人生長外番,於天朝制度多不諳習”這種當時的主流話語,但又說,他與外人交涉體會到“西洋各國風俗,不能律以中國之禮”,在奏摺中列舉不少例證,表示對之衹能“權宜變通”。①“耆英又奏體察洋情不能不濟以權變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91~2892頁。這種認識說明,在外交前綫與西人頻繁交涉的耆英,在耳濡目染之下,已經對西人擁有自己的文化習俗這一點産生了正面或至少是客觀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也投射到對基督教問題的認識上。在這一點上,長期追隨耆英的黃恩彤持見相同。黃恩彤在與拉萼尼使團翻譯加略利交涉時表示:“中國禁天主教,乃禁中國之人藉天主教爲名,公行不法,並未嘗禁西洋之天主教。中國自崇儒教,而西洋自重天主教,兩不相妨,亦各不相謀也。”②〔清〕黃恩彤:《撫遠紀略》,收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第1分册,第463頁。清朝官員在鴉片戰爭後的具體歷史背景下對基督教及西方文化的默認容忍,與明末清初統治者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嘉慶帝那種公開表示蔑視的言辭在官方文件中消失了。
在道光年間,與官員們的態度變化同時,有一些學者則開始從儒學的觀點出發,對基督教進行學術性探索。在此,以著名學者、思想家魏源爲代表進行考察。
魏源以究心經世之學著稱,所著《海國圖志》被當作代表一個時代學術思想史的典範之作。該書百卷本之第二十七卷內容爲《天主教考》三篇,中上二篇搜集了當時他所能見到的相關著述,下篇則發揮他自己的認識和評價。觀此三篇,可知他研讀當時可見的天主教中文文獻是下了功夫的。其時,可資研讀的文獻稀缺,非教中之人,對其瞭解不全、錯解誤讀亦在所難免。魏源對基督教的這種認真探索的態度,及其所形成的認知,在當時士人群體中乃屬罕見。③魏源在述及英國所信之新教與舊教之別時,所據資料爲雍正年間刊行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及鴉片戰爭時期被俘英人安突德之供詞,可見相關資料難覓〔〔清〕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考下”,《魏源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第5册,第822頁〕。魏源對基督教的認識主要通過對其所見漢語天主教文獻進行的一系列評論體現出來。
魏源認爲,利瑪竇所著《二十五言》,“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竊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這雖是揣測之論,但也反映他希望從既有知識體系出發理解洋教。他又說,該教“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這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了真相。他評論《天主實義》《畸人》《七克》《辨學遺牘》《靈言蠡勺》時,都將天主教類比於釋氏;評《交友論》,認爲其“不甚荒悖,然多爲利害而言,醇駁參半”;評《西學凡》,涉及西人之文、理、醫、法、道諸科,認爲“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評《空際格致》,認爲“西法以火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簡用金木爲非……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評《寰有詮》:“其論皆宗天主……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真雜學也”。④〔清〕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考下”,《魏源全集》,第5册,第818—820頁。這些評論將天主教類比於佛教,又將其與儒教相對照,以中國傳統的學術語言來解釋“異學”,在貶損中又顯示了對其存在的承認和重視。在評論關於西學的文獻時,魏源對其加以一定的尊重,甚至肯定其“與儒學次第略似”,又說其“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這無疑體現出一種對異文化的尊重態度,與他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路相對應。
魏源在接下來的文字中,又就基督教的教義、思想連發十五問。這些疑問和評論,都是以華夏文化爲本位、以中國知識體系爲基礎而發出的。其中既顯示了他對這些教義和思想本能的排斥,也體現了他對於這種基督教的思想及其在中國傳播狀況迷惑和探詢的態度。例如,他說:“吾讀《福音》諸書,無一言及於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曆明時、製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療病爲神奇,稱天父神子爲創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條理,何以風行雲佈,橫被西海,莫不尊親?豈其教入中土者,皆淺人拙譯,而精英或不傳歟?”這表明他想探究基督教法之真相。又如,他說:“歷覽西夷書,惟神理論頗近吾儒造化之旨,餘皆委巷所(瑣)談,不足道也。”①〔清〕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考下”,《魏源全集》,第5册,第821~822頁。這種將基督教“神理”之論比擬爲儒家“造化”之說,已是很開放的議論了。
魏源對基督教的探索和評論表明,中國士大夫中的先進分子,開始正視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並對其教義及演變流傳的情況進行力所能及的考察和分析,其言論透露出以較爲客觀的態度對待以基督教爲中心的西方文化的傾向。他在知識上的局限並不影響他探索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洋事物的意義。透過他對基督教的論說可以看到,在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巨大創痛之後,中國士大夫對來自西方的基督教開始採取主動瞭解的態度。他們衹能依託原有知識體系來安置其覓得的新知,而這正是鴉片戰爭後意義重大的“開眼看世界”的思潮的基本特點。
四 文化競爭意識的萌生
鴉片戰爭後,士大夫階層通過對基督教的考察而産生的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是,文化競爭意識的萌生。
其實,在嘉慶帝禁止北京西洋堂刻書傳教的上諭中,已經透露出對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警惕性。他說,西洋人自己信仰可不加干預,但在中國有“一二好事之徒,創其異說,妄思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易爲所惑,不可不申明舊例,以杜歧趍”。②“申明例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上諭”,《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3頁。即是說,動用國家力量禁止傳教活動的原因之一是防止“無知愚民”被異教“所惑”。刑部根據上諭審理德天賜一案,理論上的依據之一就是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查辦傳教案所發上諭:“西洋人傳教惑衆,最爲人心風俗之害。”面對天主教在華活動依然持續的局面,刑部建議:“雖此時傳惑已衆,勢不能逐名究辦,亦應將聽從西洋傳教如號稱神甫等項內地民人嚴行究辦,俾愚民各知例禁,醒悟改悔,以維風化而正人心。”③“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第24頁。而1811年嘉慶君臣決定制訂懲治傳教專條,主要目的也是爲了遏制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使信衆回歸本土文化。
鴉片戰爭後,梁廷枏撰寫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可視爲因基督教傳播而引起的文化競爭意識的代表性文獻。
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是梁氏細緻研究當時可見的教會文獻的成果。他在書中扼要撮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教會文獻和興起演變的史實,對《聖經》的內容介紹尤詳。作爲一位士人,他能認真研讀教會文獻並加以概述,雖然不乏誤解之處,但其探索未知事物的態度與魏源一樣同屬難得。該書的標題“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已經透露出,作者的目的是要證明基督教體系無法匹敵中國文化體系。這就將基督教文明視爲中國文化的競爭對手,是很值得注意的思想動向。
梁廷枏在該書中提出並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即西方的耶穌教④按:梁氏當時也無法弄清基督宗教內部的派別,耶穌教乃是其對基督宗教的總稱。何以在多國興盛,向整個世界傳播?他認爲,這與該教的獨特氣質相關。該教“領其教者曰鐸德者,四佈徒衆,遞爲勸引,往往不遺餘力,非若中國聖人之在宥,群生聞風自起也”,其傳教的方法乃是“先之以言,不入則資之以利,不入則竟劫之以威。上好下甚,下好上從,何怪乎一方百十國之靡然向風,影隨而響應哉?”除了得益於這種“不遺餘力”的傳教精神,該教的風靡還與其獨特的教義相關:
專舉人人所必敬共敬之天體,使返思而尊崇之;確指人人欲識未識之天心,爲鑿空而顯釋之……其立爲科條也,則又寬之以倫常日用,而略限之以持齋戒殺,樂行所易,自不畏所難矣。習之以地獄天堂,而即終之以審判復活,因以其常自推信其變矣。淺之以啓其可從,又歆之以使其必從,而且更惕之,使其不得不從。而適當聲教未訖之時,爭殺相衡之會,機觸必動,勢在必轉,夫是以趨之若鶩,一發不可復遏,以迄於今也。①〔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
梁氏這種認真而冷靜的考察分析,在當時士林還是罕見的。但他認爲,上述認識還不夠,因爲從該教各種關於神跡的說法來看,似乎並不比喇嘛教高明,爲何其發展出那麽大的勢力?而且,其教義中有的說法也難以理解,如耶穌凡人肉身爲何被尊爲神,且有“分天之體”(按即三位一體)之說?也就是說,看上去並不高明的基督教何以能夠發展成世界性宗教這一點,是需要繼續加以瞭解的。顯然,基督教的全球擴張態勢對他來說構成了一種需要加以探索和瞭解的文化挑戰。
在西方的戰艦闖入“天朝”的大門之前很久,基督教就進入中國,並在這個儒家文化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社會獲得一席之地。既然儒家文化相對於基督教具有不言自明的優越性,那爲何明代以來中國有那麽多人入教,其中還包括相當多的士人,而且,即使在朝廷禁教政策的高壓下,該教依然能夠維持存在並流傳?這是梁氏必須面對的史實。他認爲,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等開創在華傳教事業,得到中國士大夫“爲之潤飾”,以至“宮中亦毀所奉佛像而偏崇之,南都則傾信者數以萬計”,原因在於:“蓋禮教刑政失於上,奇邪跛僻興於下,而樞紐之交,又在易七日之拜爲朔望,隨俗所便,故說驟得行。”②〔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即是說,明末本土文化淆亂衰敗導致天主教行於中國,而天主教的文化適應政策加速其影響的擴大與教務的流行,故“彼教”的浸入是由於“此教”的衰頽。這種認識很自然地使中西文明之間的競爭凸顯出來了。
鴉片戰爭後以五口通商爲標誌的“條約口岸體制”,永遠改變了中西關係的格局,也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之間的競爭。按梁廷枏的看法,“皇朝正學昌明,風俗醇厚”,故自乾隆年間“偶有一二無業遊民,利其資用”而入教,“自是之後,已絕根株。邊壖數十年來胥忘其事,無所用其操切”。③〔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即在清廷禁教政策下,基督教的傳播已經本來不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五口通商和教禁的解除帶來了新的挑戰:“近日廣宇通商,市地既廣,行教者涉險遠來。然自求厥福,不爲民害。如聽其自存一教,亦昭柔遠之義。”④〔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五口通商後的變局,使基督教在中國成爲難以抹去的合法存在。他很清楚,富有進取性的基督教傳教運動在百年禁教的艱難時光尚且四處傳播,在新的條約體制之下更不會滿足於“自求厥福”。他指出,來華不久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就像明末的利瑪竇、艾儒略、龍華民等“並通中西文字”的天主教傳教士一樣,“喜購內地書籍,延中土人至彼教以漢字、漢語”,而且藉助新出的傳播媒介,以“年來泰西所月行之報紙,譯出傳入內地,固半屬勸人持教邀福”。⑤〔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總之,在“天朝”的土地上,中西文化之間的競爭將是不可避免的。
鑒於此,梁廷枏提出弘揚華夏文化以戰勝基督教的歷史命題。他在序論部分就展望了這一前景:“彼懸空預擬善其所善之談,今雖盛行西國,倘他時聖教所被,識見日開,必將有辨江心之味思冀北之群者。機勢在有不券而符,況生際文治精華雲漢昭回之盛如聖朝今日者哉!”在正文的起始,他又標明:“總論彼教必將爲聖道所化,是作說之緣起。”⑥〔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他在多處明確表達以儒學“聖教”取基督教而代之的願望,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與基督教文化相競爭,“使信耶穌之教之人,得盡讀其書,暢明其義”,西方各國必將如當初景從基督教那樣,轉信“聖學”,將五口通商變局當作“其轉環之一大機也”,即“聖教”擴充之機,也就是將中西通商、基督教行於中國之機,變爲儒學教化西國之機。⑦〔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梁廷枏在此書主體部分認真地按自己的理解梳理了基督教的基本歷史、思想、禮儀等內容,認爲從這些內容來看,該教冀圖廣傳中國,但與佛教在中國傳播一樣,終將無法勝於“聖教”。⑧〔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 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2、4、7、5、42~46頁。他在介紹完基督教的歷史和思想後,再次提出以儒教與西教競爭求勝的命題:“泰西人既知讀中國書,他日必將有聰慧之人,翻然棄其所學,而思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①〔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第46、47~48頁。梁廷枏、魏源瞭解和介紹在當時還頗爲士林不屑、爲官紳戒懼的基督教,這種“睜開眼睛看世界”、直面現實的態度,已使他們成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特異者;而梁廷枏的這種主動進行宗教文化競爭、積極求勝的主張,則更是一種超越時代的主張。
梁氏評論的另一值得注意之處,是從具體的知識層面展開與基督教的競爭。在這方面他重點從歷史年代學上進行考究。基督教宣佈宇宙“開闢六千年”,則“自利瑪竇始來中土之歲,逆推至黃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他又引傳教士郭士立所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之說,云創世至今爲六千五百四十七年。即按其所信,黃帝之前衹有不到兩千年的宇宙歷史時間。但按中國典籍所載,雖然黃帝之前的歷史“荒遠難稽”,而記述中國上古史實的“《三墳》之紀已亡,諸說紛陳”,但六千年之說決非信史。“其所據,良由海邦舊少記載,一有所聞,無從辨證,總視爲枕中鴻寶耳。非真其國別有史書,紀開闢後事如《三墳》者,留傳至今也。”顯然,在他看來,這種傳教士“拘守《聖書》,殷殷舉以勸人”之說,是靠不住的知識。②〔清〕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序”,《海國四說》,第46、47~48頁。有趣的是,在梁廷枏所引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郭士立也寫道,中國史籍中的上古史記錄不可信,“中國秦始皇,有焚書坑儒,故上古世遠,或有失記。然或西域,商朝時候,有聖人摩西,親聽古傳,又感神默照,示知此事,立刻記之,其書還在。是故西域之史,或亦可信耶!”③愛漢者 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黃時鑒 整理,第6頁。即是說,衹有《摩西五書》的記載纔是信史。梁氏既引用了該刊中的言論,一定讀過郭士立的這番議論,故他的上述說法可以看作對郭士立的回應。這個例子說明,中西之間的思想—知識競爭在鴉片戰爭前後已經展開。
當然,在道光年間,達到梁廷枏上述認識層面的士大夫尚屬少數。桐城派學者姚瑩因其抨擊中國士人於海外情形“置之不講”,主張積極尋求海外知識而受現代研究者肯定。但他對於基督教則充滿戒備。清廷弛禁天主教後,他在給友人信中說:“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旦爲所挾而復開,其他可駭可耻之事,書契以來,所未有也。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畺,以正人心,以清污穢。”④〔清〕姚瑩:《東溟文後集·復光律原書》,收入《西方認識(一、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1輯第1~2分冊,第372頁。這裏表達的對基督教強烈的憤恨和排斥情緒,顯然是因爲無法接受華夏文化不得不容忍來自敵邦的異教並與之共存的現實。
不過,如果將梁廷枏的文化競爭意識看作中國士大夫群體對弛禁後基督教廣傳中國前景的一種反應,則在晚清特定時期還可以看到其他形態的文獻。例如,太平天國的宗教外衣就引起清政府和官紳對於基督教文化威脅的極大警惕。在這方面,最爲著名的文獻當數曾國藩的《討粵匪檄》。這篇檄文以相當大的篇幅表達了對太平天國以天主教信條毀棄中國文化的深切憤慨: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在這段文字之後,曾國藩還不惜筆墨描述了太平天國不敬神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這些連“窮凶極醜”的亂臣賊子皆不爲之行徑。①〔清〕曾國藩:“討粵匪檄”,《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94),第232~233頁。它將對太平天國的鎮壓表述爲對中國文化的捍衛,而不僅是爲了“我大清”的安危。這在自明末以來就對“亡天下”深懷戒懼的士大夫階層中引起強烈共鳴。深諳士人思想的曾國藩由此將這場戰爭詮釋成一場文化戰爭,在清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頭,將人們對於基督教文化滲透中國的擔憂作爲一種思想資源而運用到極致。
五 值得注意的思想史脈絡
嘉道時期這些對基督教的認識與反應,並非該時期所獨有的現象。清初,楊光先策動“曆法之爭”,反對湯若望等人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湯若望主持所修《時憲曆》封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而明謂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②〔清〕楊光先:“正國體呈稿”,《不得已》(合肥:黃山書社,2000),陳佔山 校註,第5、36頁。他指責湯若望等“實欲挾大清之人,盡叛大清而從邪教”;又稱天主教“與中夏之白蓮、聞香實同”,傳教士策劃謀反以顛覆大清。③〔清〕楊光先:“與許青嶼侍御書”,《不得已》,第10~14、8~9頁。這就將曆法問題歸於政治問題,指基督教爲邪教。楊光先更爲痛恨的是“曆官李祖白造《天學傳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爲伏羲氏,《六經》《四書》皆是邪教之法語微言”;④〔清〕楊光先:“請誅邪教狀”,《不得已》,第5頁。其將伏羲說成“如德亞之苗裔”,“則五帝三王以至今日至聖君聖師聖臣,皆令其認邪教作祖,置盤古、三皇、親祖宗於何地?”⑤〔清〕楊光先:“與許青嶼侍御書”,《不得已》,第10~14、8~9頁。又將這場鬥爭闡釋爲文化正統之爭。
楊光先時代的政治形勢和中西關係與百餘年後的嘉道時期均不一樣,但從政治穩定和文化競爭的意識出發理解基督教對中國影響的思想路徑則有相似之處。同光年間是作爲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衝突標誌的教案頻發的時期,人們可以看到對基督教的上述認識和態度同樣在官紳士人的言論中體現出來。
清朝官紳認爲,基督教傳教給清朝的政治穩定乃至統治基礎帶來很大威脅,故對於頻發的教案採取縱容乃至鼓勵的姿態。中外學者對於這一點論述頗多,這裏無須再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同治年間之前,清朝上下擔心的主要是對基督教的寬容會導致內亂的發生;而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官紳警惕的主要是基督教傳教士在西方炮艦政策掩護下圖謀不軌,使中國面臨的外來侵略更爲加劇。
同光年間,因基督教傳教活動而引起的文化競爭認識,除前引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外,還可以在不少士大夫的著述中看到類似的言論。夏燮的《中西紀事》初作於咸豐初年,而終成於同治五年(1866)。他在書中對維護儒學地位的楊光先抱有深切的同情,對鴉片戰後弛禁天主教的政策持非議態度,對《天津條約》的“寬容條款”更爲不滿,認爲“我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的情況非常值得警惕。⑥〔清〕夏燮:《中西紀事》,第32頁。王之春的《國朝柔遠記》成書於光緒初年,在書中提出:“欲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藩籬,藉天堂、地獄之說以蠱惑我民心者,其泰西之傳教乎?”⑦〔清〕王之春:“蠡測卮言”,《清朝柔遠記》,第388、390頁。這個說法將問兩種文明的競爭態勢明確地提出來了。他期望中華文化能在這種競爭中顯示出自己的優勢:
現在泰西之入學者,必習中國語言文字,所有五經、四子書概行刊刷,先刻華文,而以西文註釋之,日日諷誦。其景從之心,較之中國人之入彼教者爲更切。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仁之至,義之盡,天理人情之極,則無一毫矯強於其間,而凡有血氣者,自可不言而信、不勸而從也。將來漸推漸廣,風氣日開,聖教盛行,率薄海食味辨色別聲之人,而皆不敢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天主云乎哉?⑧〔清〕王之春:“蠡測卮言”,《清朝柔遠記》,第388、390頁。這些文字所展現的文化競爭心態,在同時代其他思想者、特別是早期提倡維新變法的士人的著述中不難發現,到康有爲則發展爲影響頗廣的“孔教”論。如對相關史實和論述認真梳理,當可展現近代思想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個發展脈絡。
之所以從政治威脅、文化競爭兩個角度解釋嘉道時期君臣士人對基督教的認識和反應,是因爲,身居廟堂的君臣更關注天下是否安寧,對基督教的疑懼主要來自這種“夷教”潛匿民間策動叛亂的可能性,故賦予其“邪教”的政治屬性,將其當作白蓮教、八卦教等威脅國家安全的反清民間宗教一體防範,防止其導致“亡國”之後果。而深受儒家文化浸潤的士大夫的憂思,主要因爲基督教來華而導致的文化競爭,警惕其可能帶來“亡天下”的局面,雖然他們對基督教勢力在華擴展造成的政治威脅也很警惕和憤懣。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天主教無法公開活動,儒家文化所受衝擊甚微,故防範打擊主要在政治層面。但鴉片戰爭後,逐漸獲得合法地位的基督教成爲士大夫階層必須面對的挑戰,他們不得不對其加以瞭解,並思考應對之道。
以往研究者更多是從傳教士與帝國主義勢力相結合,利用不平等條約特權侵擾基層社會、削弱清朝統治的角度,解釋清政府官員在晚清教案中的表現;或者從儒學“黜異端以存正學”的文化傳統、本土文化習俗與基督教必然衝突的一般性原則出發,闡釋士民參與教案衝突的社會文化背景。這些觀點都具有明顯的合理性。但是,既往研究對清代前中期形成的反“邪教”政治傳統未予足夠關注,對鴉片戰爭後中國士大夫在主動瞭解基督教文化的基礎上産生的文化競爭意識及其歷史意義也認識不足。誠然,視基督教爲政治威脅是清代官紳反教的一致原因,但嘉道時期對“邪教”的戒懼與同光年間對外敵入侵的憂慮有着較大的區別。“黜異端以存正學”的儒學基本傳統與文化競爭意識關係密切,這是在鴉片戰爭後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具體觀念,因此,需要就嘉道時期君臣士人對基督教的認識和態度加以專門考察。
——魏源对联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