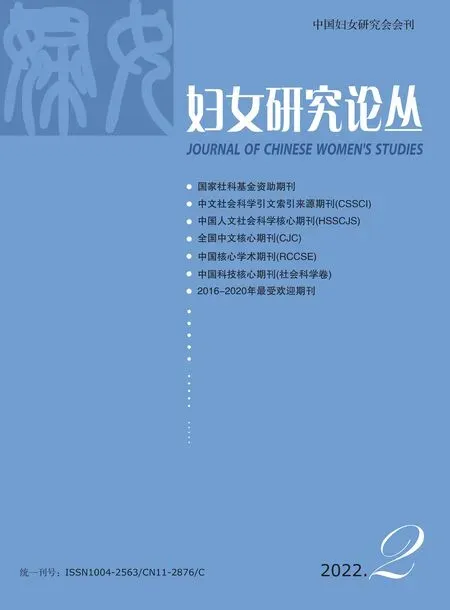被规训的“爱情”:《千万不要忘记》中的情感政治
熊庆元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丛深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代表作。该剧原名《还要住在一起》,1963年登载于《剧本》月刊时改为《祝你健康》,后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号召下做了修改,并更名为《千万不要忘记》。问世之初,该剧即引起热烈反响①。现有研究在讨论剧作《千万不要忘记》时,主要涉及对青年一代的书写及与之相关的教育革命下一代的问题,并由此进而讨论了剧作中的生活政治以及60年代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等相关问题(1)剧本问世之初,相关评论多着眼于剧中所反映的阶级主题以及教育下一代(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燕平充分肯定了剧作的阶级观点,认为“从姚母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燕平:《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上海戏剧》1964年第3期)。曹禺则进而谈到了阶级斗争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系,称该剧“使我震动,促我思考,叫我不能忘记身边一件严峻的事实:日常生活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正在隐蔽地或者露骨地和我们争夺接班人”(曹禺:《话剧的新收获——〈千万不要忘记〉观后感》,《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工人作者赵国华亦撰文肯定剧作之于教育下一代的正面意义(赵国华:《做一个红色的接班人——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观后感》,《上海戏剧》1964年第3期)。不惟如此,该剧作者丛深对剧本的创作动机也作了说明,明确提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我决定通过描写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争夺战,来歌颂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戏剧报》1964年第4期)作品问世之初形成的上述观点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79年,顾卓宇等人撰文讨论该剧时也仍持此论(顾卓宇、胡叔和、陈刚:《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新时期以后,一些不同的意见开始出现,比如,冯守棠即撰文指出将姚母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是缺乏根据的,从而对作品的阶级斗争主题作了再讨论(冯守棠:《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戏剧艺术》1980年第3期)。相对晚近的研究在基本尊重剧作的阶级主题的基础上,借助新的理论视角,开始进而讨论剧作中涉及的生活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等问题,这些研究尤以唐小兵、徐刚、蔡翔等人的著述为代表,由于后文还会论及于此,此不赘述。。这些问题显然与剧作的主旨紧密相关,但从剧本的内容来看,似仍有一些富有深意的细节可作进一步讨论。比如,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作者不止一次写到与男女爱情有关的情节,这些情节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题旨同样非常重要,而现有研究则少有论及(甚至作者丛深本人在谈及此剧主题的形成时也未曾提及于此)(2)可参见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载《戏剧报》1964年第4期)。。因此,本文试图从剧作中这些相关的情感书写入手,对其中包含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阶级联合的幻觉:相爱之人何以感到“空虚”
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不止一次出现有关青年男女的婚恋叙事,其中一个饶有兴味的情节,即老工人丁海宽看到其子丁少纯写给姚玉娟的情书,由此展开了对少纯的家庭教育。这一情节发生在第一幕丁少纯家中。剧本对这一情节的设计很有意思,丁海宽看到儿子的情书本是出于偶然,是“翻旧报纸找学习材料”时发现“里面夹着这么一张没头没尾的纸片子,是少纯的笔迹”,“从头看到尾才闹明白,原来是他在结婚以前给玉娟写信打的一段草稿”[1](PP 29-30)。从剧作后文的相关内容可知,这段草稿实际上是丁少纯在婚前写给妻子姚玉娟的情书,但关于这段情书草稿的具体内容,剧作并没有作详细交代,只提到了其中一些关键细节。剧中人物关于这段情书草稿的对话,按照戏剧情节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丁母询问丁海宽翻拣到的纸上的内容时,在二人之间展开的对话;二是丁少纯出场之后丁父围绕这段情书内容对少纯进行的批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次。当丁海宽告知丁母手中的纸是少纯婚前写给玉娟的情书时,丁母的反应是“孩子们的体己话你别给人家看”,而丁海宽的反应则是:“看看受教育!从这里看得出来少纯这孩子思想很不健康,很成问题!”[1](P30)显然,丁父关心的不是信件本身的私密性,而是信件内容中所存在的思想问题。也恰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丁父对于这封情书的解读,带上了浓厚的家庭教育的色彩。当丁母询问丁父儿子的思想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时,丁父念起了情书中的话。
丁海宽 我念几句你听听。嗯,这儿,听着啊——“每当和你分手以后,我心里总是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和什么?这两个带竖心的字咱没见过面儿。(看看丁母)你听明白没有?(丁母摇头)你没念过中学嘛,人家这是“跩文”呢!
丁 母 啥意思呀?
丁海宽 就是说,一见不着玉娟,他心里就……就……(手在胸前直划圈儿也说不清)反正就是没活路了!
丁 母 这么蝎虎?
丁海宽 你看吧,整天见面一分开还“空虚”,要是工作需要调他出去个一年半载的,那他还能工作吗?不光剩下“空虚”了吗?年青人要是都像他这么“空虚”起来,那不糟了吗?(越想越气)“空虚”就够呛了,他还来个“无限”!
丁 母 你小点声
从上述引文不难发现,丁海宽之所以会对儿子丁少纯在情书中所表露出的“空虚”的心理状态如此气愤,并不是基于恋爱问题而发的。也就是说,丁海宽感到气愤,不是因为少纯的“空虚”代表了青年男女在恋爱时所不应持有的情感状态。相反,丁海宽将青年人恋爱中所出现的这种“空虚”的心理状态转嫁到工作伦理的维度,指出青年人在工作中的“空虚”是不能被接受的。以“空虚”为中介,丁父的论述逻辑实际上是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问题转嫁到了公共领域,这也是其认定少纯思想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顺着这一逻辑,丁父紧接着也就关注到儿子情书中关于职业问题的表述:
丁海宽 你再听这儿——“你总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我却根本不计较这个”——你听他多大方!——“我认为你和我都是一样的人,你的家和我的家虽然职业不同,但那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罢了……”(拍得信纸啪啪地响)听听!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开鲜货铺子的和工人阶级就差个“职业不同”!就差个什么“社会分工不同”!这么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不都成了“社会分工不同”了吗?简直是混账!
丁 母 小点声
丁父对“家庭出身”和“职业不同”的理解显然与其子丁少纯迥然有别。在儿子丁少纯看来,他与妻子玉娟之间在家庭出身和职业方面的不同是中性的,即所谓“社会分工不同”,而在父亲丁海宽看来,“开鲜货铺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并不能被视为“职业不同”,也不是“社会分工不同”,而是阶级有别。他以“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区分进行类比,显然是为了说明儿子将“职业不同”视为“社会分工不同”的想法是模糊了阶级界限,是思想问题。
经由这一部分的人物对话,显然,丁少纯婚前写给玉娟的情书本身就不再是一份个人情感的即时记录,而是一份有政治错误的思想报告。从上述的剧本情节处理可以看出,丁少纯这封情书一出现,即不被视为青年爱情的宣言,因为其文本是经过丁海宽的叙述而被节录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情书的作者丁少纯并不是这段叙述的主体,真正的讲述者是作为情书内容转述者的丁海宽,同时,丁海宽还承担了“立法者”的角色,对情书中有问题的内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通过在爱情、职业、阶级三者之间建立逻辑联系,丁父的政治批评基本得以完成。
不过,这一部分主要还是丁海宽的自我陈述,剧中两次出现丁母的“小点声”只不过是一再反衬出老工人的愤怒,却未能完全实现剧作的青年教育的题旨。因此,紧接着这一段老夫妻(老工人)的对话,丁少纯终于出场了。显然,丁少纯的出场,就其叙事上的功用来说,是为了完成家庭教育这一目的,因此,接下来的情节一定是发生在父子之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对话。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这一层次在写法上却与上述第一层次有所不同。
少纯上场后,问父亲在看什么,父亲说是“重要文件”。接着,丁父重提了“空虚”和“怅惘”(即前述引文提到的“两个带竖心的字”),但并未由此转入对职业问题的讨论,相反,他采取了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来直接询问丁少纯对阶级问题的看法:
丁海宽 少纯,你说这人为啥还要划阶级成份呢?
丁少纯 因为经济地位不同呗。
丁海宽 不同又能怎么样呢?
丁少纯 地主、资本家压迫人、剥削人呗。
丁海宽 怎么压迫?怎么剥削?
丁少纯 (对丁母笑笑)考我呢。爸爸,这你比我知道的多,旧社会不是到处都有压迫剥削吗?
丁海宽 那现在呢?
丁少纯 现在当然没有了。
丁海宽 那还划分阶级成份干啥?不是多余吗?
丁少纯 填履历表不都得有那么一格吗?
丁海宽 要那么一格干啥呢?
丁少纯 记个出身历史呗。
丁海宽 记那个有啥用?
丁少纯 必是有用呗。
丁海宽 有啥用?
丁少纯 (语塞)那……一定是……可能是……(一笑)我也说不上来。(忽又高兴地)啊!我想起来了:出身可能和思想有关系。是吧,爸爸?[1](P32)
丁海宽从阶级问题设问,步步引导,循序渐进,最终让丁少纯意识到“出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信息记录,不是客观而中性的个人档案,而是“可能和思想有关系”的重要问题。当下已没有“旧社会”的“压迫剥削”,但却仍要做“阶级划分”,并且这一划分是和“履历表”“出身历史”有关的问题。这一历史性视角的引入,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后文对此还会论及,此不赘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丁海宽没有采取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丁母的长篇大论式的对话策略,而是以一种问答式的方式逐渐引导丁少纯认识到其思想上的问题。尽管他直接从阶级关系切入正中问题核心,但对于少纯而言,这一核心问题却是他未曾意识到的。因此,丁父的引导便显得由里及表,继而从出身和思想的关联谈到职业的区分,再到私密性的情书。
在少纯反问父亲“出身和思想有关系”是否正确时,丁父突然以一种不无讽刺的口吻展开了对丁少纯的“教导”:
丁海宽 不准吧?就拿你岳母来说吧,她虽然从前跟她老头一块开过鲜货铺子,是个小商人出身,可她的思想跟你妈有啥不同呢?
丁少纯 (想了想)可也是,在她身上是不大明显。
丁海宽 是嘛!什么阶级成份?其实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罢了!
丁 母 (着急地制止丁海宽)咳!你!……
丁少纯 (怔了半天)……爸爸,你这是——[1](PP 32-33)
丁少纯对父亲突如其来的话锋转变尚未适应,紧接着,丁海宽又问及其与岳母相处如何,少纯答道相处挺好时,父亲又语带讥讽地说道“多好哇”,少纯见机便说岳母“也有些缺点”,并补充说“上了年纪的人,免不了有点旧脑筋”。当丁父直斥“混账话!上了年纪的人就得有旧脑筋?!”时,丁少纯这时才又回到了出身的问题:
丁少纯 我的意思是……我是说这……可能……跟她的出身有点关系……
丁海宽 “可能”,哼!
丁 母 你爸爸不是早就嘱咐过你,叫你多帮助玉娟,多帮助你丈母娘……
丁少纯 我一定帮助她们克服缺点!
丁海宽 等着人家帮助你克服优点吧!把你那点优点克服净了,就省得你心里“无限的空虚”了!
丁少纯 “无限的空虚”?这是……哪儿的话?
丁海宽 忘了?(把信掷给丁少纯)看看“文件”吧!
丁少纯 (看信,羞得跺脚)妈!你瞧爸爸啥都给人看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丁海宽对丁少纯的教导,就观念层面而言,同其与丁母的对话一脉相承,但在行文顺序上,二者却截然相反。丁父由阶级问题切入,进而转论职业,最后再回到情书(有意思的是,这里,情书被戏谑地称为“文件”,也强化了丁父政治解读的色彩)。由“空虚”引入,以“空虚”作结,情感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3)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千万不要忘记》展开的研究大多未能注意到剧中的这一细节,而有些论者在提及这一细节时也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社会主义对小资趣味及与此相关的个人欲望的反拨,而未能注意到其中所涉及的性别问题。比如,宋向阳和林玲即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丁海宽对丁少纯情书的批评旨在揭示出丁少纯“恋爱时的‘小资’情调”,并认为这是一种需要被“告别”的“感性欲求”,但他们却未对这一“感性诉求”中的情感面向加以说明(宋向阳、林玲:《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深层结构和伦理指向》,《新世纪剧坛》2017年第5期)。。我们发现,虽然少纯的妻子玉娟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且这封情书也是少纯和玉娟之间的通信,但在丁海宽的教导中,受教育者是亲生儿子丁少纯,儿媳玉娟并不在场。姚玉娟的缺席,在此显然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不只是家庭教育,同时也是阶级内部的自我教育,在丁氏父子关于阶级问题的历史性的视角中,姚玉娟被作为阶级的对立面而排除在了这次教育行为之外。
因此,当个人性的、基于自然性别的生理差异和生物本能的欲望冲动而引起的爱欲被纳入阶级叙事的规范性的书写之中时,爱情问题也就变成了阶级问题。爱情和阶级之间经由职业这一中介被牵连起来。从而,丁少纯的空虚和怅惘不再是革命青年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心理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觉悟问题,换言之,即阶级自觉问题。在丁海宽对儿子的政治批评中,丁少纯在婚前写给姚玉娟的情书中所表露出的恋爱青年的空虚和怅惘以及他将自己与姚玉娟的出身之别视为职业不同的说法,被丁父解读为模糊阶级身份的政治错误,即相爱之人感到空虚实际上是缘于一种阶级联合的幻觉。
二、男女之爱抑或同志之爱:爱情的革命化与去欲望化
对于青年恋爱的描写,不止于上述带有“阶级联合”色彩的少纯情书这一情节,作品同时还写到同为进步青年的丁少真和季友良的恋爱。在关于丁、季二人的恋爱描写中,我们同样能清晰地看到个人情感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剧作第一幕和第二幕中,都涉及丁少真和季友良的恋情描写,不过,这些描写在表现形式上与少纯情书有所不同。
第一幕中,丁少纯要去打鸭子,适逢季友良来谈工作的事,二人通过选单还是选双的方式,最终决定丁少纯不能去打猎。在二人对话中,姚母建议季友良要多陪少真,由此引出了对少真和友良的恋爱状态的描述:
姚 母 我说季友良,你也该陪着少真出去玩玩,看看电影啦,蹓蹓江沿啦,多好!
季友良 她知道我最近时间紧。
丁少纯 你这家伙,对女孩子的心理一窍不通!
季友良 别摆老资格,我就不信你那一套!
丁少纯 一点也不虚心。[1](P22)
显然,姚母给友良的建议——陪少真去看电影、蹓江沿,本是符合男女青年恋爱的正常行为,季友良却以工作忙碌为由作答,当少纯指出友良不懂恋爱中女孩的心理时,友良更是以“别摆老资格”“不信你那一套”回应。友良在恋爱中这种一心投身工作、罔顾恋人心理的做法,不仅反映出其木讷的性格特点,同时也为后文少真和友良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少纯说友良“一点也不虚心”后,“心里有啥脸上也有啥的姑娘”少真上场了,从此后的情节即可清楚地看出她对友良的态度:
丁少真 (看季友良一眼,却对丁少纯说话)哥哥,我这有两张青年宫的晚会票,你去不去?
姚 母 少真,正好友良要找你去玩呢,你们俩快去吧。
〔丁少真疑惑地望着季友良。
季友良 (被动地)少真,你跟你嫂子先去参加晚会好不好?我跟你哥哥还想(抱歉地指指抽屉等物)……
丁少真 (伤了自尊心)我的活动用不着你来费心安排!(转身急下。)
季友良 少真!少真!
丁少纯 哈哈哈哈!碰钉子了吧?叫你不虚心!
季友良 唉!姚大娘,你可真坑人
少真“看友良一眼”,却和哥哥少纯说有两张青年宫的晚会票,显然是为了试探友良,希望友良能主动提出和她一起去看。这时,姚母适时地推波助澜,委实让少真感到高兴而又意外,因此她才会“疑惑地望着季友良”。从这段情节可以看出,少真对友良的性格是了解的。她并不相信友良这个“工作狂”会善解风情地陪她去看晚会,但听姚母这么一说,心里显然又怀有几分期许。当然,友良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而拒绝了陪伴少真,“被动地”“抱歉地”等语词显露出友良的窘态,提议由嫂子玉娟陪同少真去看晚会,则暗示着友良的选择。恰恰是长久以来一心投入工作而怠慢了恋情、疏忽了少真的感受,使得少真备受伤害。剧本直接点明友良的话令少真“伤了自尊心”,致使其“转身急下”。
在第二幕中,友良的木讷和工作狂的作风,再次使他和少真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少真不得不找嫂子玉娟倾诉:
丁少真 我约友良五点半去看篮球赛,五点在这儿集合去食堂吃饭,可是现在都五点二十了,他还没来!
姚玉娟 你们什么时候约定的?
丁少真 你不是教我提前两天约他吗?我是前天约的他。
姚玉娟 对,这样可以考验考验他,看看他能不能忘,要忘了那就说明你在他心里不占重要位置。
丁少真 他昨天是夜班,也许在家睡觉睡过点了,要不我现在回家去找他?
姚玉娟 瞧你!那还叫什么考验了?
丁少真 我有点经不住考验了……
姚玉娟 (笑)别那么沉不住气!你哥哥从前约会我的时候,我总要比他晚到十分钟,这样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心。
丁少真 我是怕友良睡觉没醒……
姚玉娟 他心里要真有你,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等着。
丁少真 (望左侧,忽然高兴地)嫂子,他来了!
姚玉娟 (向左侧瞥了一眼)可要端着点儿呀,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问题!(向右侧下。)[1](P47)
这里,玉娟对少真的“开导”颇为耐人寻味。其中,“考验”无疑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有论者谈及该剧时指出:“剧作家围绕着‘考验’(是否能够经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蛊惑)这一主题,设置了一系列的角色和戏剧冲突,展现丁少纯思想‘纯净—动摇—陷落—觉醒—更纯净’的曲折过程。”[2]玉娟这里所谓的“考验”,显然与丁少纯所经历的一系列“考验”不同,其似乎反映了女性对被爱的感觉的确认,提前约定和故意迟到作为这种考验的表现方式,在玉娟看来,应是女性确认爱情的一种自然心理,即一种“性别本能”,反映了女性独特的爱情本能与恋爱方式。然而,如果说丁少纯经受的考验最终使他由“不纯”而走向了“少纯”,那么,从情节的发展来看,玉娟所说的这种“考验”却面临着双重的溃败。
一重溃败来自于工作对爱情的悬搁和延宕。紧接着玉娟对少真的开导之后,季友良出场,一出场就和少真大谈特谈云母带:
季友良 (满脸不可抑制的兴奋,滔滔不绝地)少真!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些挑出来的云母带完全能用啊!中央实验室刚给鉴定的……啊,你还不知道,这是我从废品库的废云母带里挑出来的。废云母带有好几吨呢,供应科想当作垃圾处理掉,今天早上我一听说,下了夜班就跑去挑选。你猜怎么样?里面能挑出来百分之三能用的!你干么那样看我?百分之三也不少啊,你算算,一吨里就能挑出三十公斤,够咱们作多少台电机呀!
〔丁少纯从右侧上。
季友良 少纯!好消息:能用!
丁少纯 (高兴地)真的呀?
季友良 多好啊!咱们用业余时间去挑选,让这台七万二千五全用这个……
丁少纯 妙!妙!咱们创造个低成本的最高纪录!
季友良 丁主任在车间没?我马上去找他汇报!
〔被遗忘在一旁的丁少真这时再也受不住了,把脸一掩悄悄走下。[1](P48)
显然,季友良不是为看篮球赛而来,仍然是为了工作上的事。以至于看到少真奇怪地看着他时,他会心生疑问——“你干么那样看我?”当他为云母带的事兴奋不已、侃侃而谈并最终要找丁海宽汇报时,少真也终于明白季友良忘了陪她看篮球赛的事,愤而离场。从剧本后面的情节可以知道,直到“被遗忘在一旁的少真”离开了许久,季友良才“忽然发现”——“咦?少真呢?”并进而才想起看篮球赛的事。当丁少纯告诉友良“人家这是考验你,玉娟就对我考验过不少次”后,季友良的反应是“这么说我这是没经住考验?真复杂!(一挤眼)我得去赔个不是”[1](P49)。这里,少真的“经不住考验”和友良的“没经住考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想见,少真在爱情中的挫败感来自于友良一次次无心的“冷落”,而这些冷落则基本都来自于工作对爱情的悬搁和延宕。
除此之外,“考验”还面临着另一重溃败,这一溃败源自女性自身对男性在工作成就上的崇拜和认同。在友良去向少真赔不是之前,玉娟询问少真为何没同友良去看球赛,这时,少真向嫂子玉娟亲口吐诉她爱情上的痛苦与挫败感:
姚玉娟 那他见了你——
丁少真 见了我就哇啦哇啦地谈云母带,完了就干脆把我撂在一边,跟哥哥哇啦开了,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捂着发烧的脸)唉呀!真讪死我了!(擦泪。)
姚玉娟 这么说,他心里的确没有你。
丁少真 谁知道呢?嫂子,对人的心理我真是一点也不会分析,比解一道最复杂的方程式还难哪!……我希望是他忙忘了——他的确忙;可是也许他根本看不起我,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才故意谈云母带来躲避我……[1](P58)
尔后,少真回忆起友良少时与她的亲善以及在她入厂后给予的关心,但玉娟却承其前话,对少真泼了冷水:
姚玉娟 可人家现在是厂劳模了,是下线组长了,是团支委了。
丁少真 也许是他思想变了?……
姚玉娟 (气不平地)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丁少真 可是嫂子,我心里觉得他……的确了不起!
姚玉娟 那天我妈说:少真长得那么水灵,爸爸又是领导干部;季友良要啥没啥,一大家子人,可真不般配。
丁少真 我最不爱听这种话!旧思想!
姚玉娟 可不是呗。
丁少真 (希冀地)……也许他现在想起我来了,正在往这儿跑,来找我道歉……
姚玉娟 他现在在哪儿?
丁少真 在废品库,带着妈他们挑云母带呢。方才我真想留在那儿跟他们一块挑——(忽然兴奋地)嫂子!有百分之三能用的呢!他多能挖潜力呀!——可是我想起你嘱咐的话,怕他以为我死乞白赖地跟着他,就咬着牙跑这来了。[1](PP 59-60)
这里,工作与思想之间再次建立起了关联,工作热忱本身即是革命理想的正当性的表征。回到思想问题时,爱情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姚玉娟从劝说者反成了被教育者。当随后季友良赶来准备向少真道歉时,作品写道:
丁少真 (忽然喜出望外地)嫂子!他来了!
〔姚玉娟向左侧看看,手指点了点丁少真,笑着向右侧下。季友良跑上。
季友良 少真!生我气了?你看我把那个事……
丁少真 (眼里闪着喜泪花,连忙拉住季友良的胳膊)别说了!走,挑云母带去!(挽着季友良跑下。)[1](P61)
姚玉娟建议丁少真考验季友良,在作品中终究因为丁少真的“经不住考验”而宣告失败。“考验”的失效与溃败,预示着玉娟视之为女性独特的爱情本能的恋爱方式被剧作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消解。当然,“考验”是否真的可被视为女性独特的恋爱心理的外化方式可以再论,但作品无意于讨论两性情感中的性别差异,即“考验”的性别基础,这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少真和玉娟有所分别。在剧作对友良和少真恋爱经历的有限的描绘中不难看出,工作热忱及其中所蕴含的革命思想成为疗治男女双方爱情创伤的最好药剂。去欲望化的、精神性的、阶级性的同志之爱取代了私人领域的两性之爱,革命工作成为个人爱情的代偿之物,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来加以塑造的季友良在爱情上总是显得木讷而寡欲。
以阶级感情为纽带的两性爱情,不止构成了作品所要呈现的爱情形态,如前所示,它更影响了作品对爱情采取的叙事方式。剧本在叙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时,明显采取的悬搁或延宕的方式,即是极力避开私人性的情感沟通的契机。当丁少真和季友良出现私人情感联系的契机时,剧作总是极力以同志之间的阶级情感及与之相关的实践(如丁少纯和季友良当着丁少真的面讨论工作事务)来横加打断,使得私人领域的爱情实际上无法在叙事上得到延续。丁少真和季友良之间的爱情“考验”被阻断,不仅缘于季友良的木讷,相当程度上也缘于姚玉娟这一荐言者因其家庭出身而具有的错误的爱情观。少真最后的“考验”的失效,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象征,借此可以见出少真的革命情感与玉娟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之间的明确分野。因此,作品对私人爱情的拒绝并不是对爱情本身的拒绝,而是对错误的爱情观的拒绝,这也是缘于对爱情的阶级属性的强调。
三、革命爱情如何可能:阶级政治与作为场域的爱情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讨论不难发现,《千万不要忘记》中关于情感的叙事,基本都服务于其强调阶级斗争的题旨。对于青年男女爱情中的思想一致的强调,本是无可厚非的,剧作的相关叙述基本也未尝偏离这一初衷。然而我们发现,这一高度“政治正确”的爱情叙事,在具体的叙述方式上,却有其自身的特点。《千万不要忘记》一剧虽不时出现有关青年男女的爱情叙事,但剧作却基本未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展开正面的叙述,相反,青年男女的爱情常常是被作为一个话题而予以讨论的。不仅如此,在谈到爱情和阶级的关系问题时,为了凸显阶级主题,对于爱情的叙事还常常出现停滞、悬搁和延宕(尤其是在丁少真和季友良的爱情叙事中)。那么,为何剧作中的爱情叙事会呈现这样的形态呢?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少纯的情书,还是丁少真和季友良之间的恋情,都随着对工作(职业)问题的讨论而不经意地退居幕后,因此,回答爱情叙事为何呈现上述特点时,如何理解工作叙事的功能就变得极为关键。或许友良和少真的情感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恋爱状态,他们因为对工作的热忱而成为精神上的伙伴,爱情不只是两性爱欲的载体,更是一种精神契合的表征。但就剧本整体的叙事方式而言,我们对工作叙事更应从功能性的方面进行理解。恰恰是经由工作叙事这一中介,爱情被转化到公共领域,也进而从被描写的对象转化为被讨论的话题,爱情由此也就成为一个争辩的场域。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部剧作中,我们发现,正是爱情的公共化完成了阶级情感的主体叙述。但同时,工作叙事的出现虽然有效地将爱情叙事从原本的私人范畴转移到公共范畴,它却并未延续其自身的发展,伴随着这种转化的发生,爱情叙事原本的流向被阻断了。我们发现,这种情形不止出现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在同时期同类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形,比如在陈耘的剧作《年青的一代》中,林岚即明确表达了她对工作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仅和思想有关,同时也和情感有关(4)在《年青的一代》一剧中,作为革命青年的林岚对农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却对电影行业兴味冷淡。显然,从剧作的情节发展来看,对职业的好恶本身也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进而追问:为什么同时期的这些类似的作品,在处理爱情叙事时,不直接按照其本来的流向进行书写,而一定要以工作叙事来横加阻断,从而将属于私人范畴的爱情问题转化为一个公共话题?
《千万不要忘记》中一再出现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叙事,本身说明剧作者对青年的爱情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但奇怪的是,如前所述,丛深自己谈及此剧的创作动机时未曾提及于此,剧作对爱情叙事的倚重和爱情叙事无法按常态延续之间却形成了强烈的张力。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本身即说明,20世纪60年代的阶级政治仍然试图介入人的内心世界,重新组织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但显然这种介入此时出现了问题。一些学者注意到剧作对日常生活的过度关注。徐刚指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千万不要忘记》中出现的对日常生活的重新书写,实际上反映了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历史变化[3];唐小兵在其名作《〈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一文中也认为,剧作中表现出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实则包含了鲜明的政治性维度[4](PP 224-234)。对此,需要再作一些补充说明。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常被视为一种中立、客观的存在,比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就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多余的范畴”,“所有不符合正统思想、令人反感的鸡零狗碎都可以扔到里面去”[5](P77)。但法国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指出,将日常生活看作中性的范畴,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他认为日常生活——尤其是现代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异化,其包含着隐秘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已不复为有着丰富的潜在主体性的‘主体’,它已成为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客体’。”[6](PP 59-60)在《千万不要忘记》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阶级政治试图重新组织日常生活,实际上即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异化的判断,而此处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包括了个人的情感世界。在此需要进而指出的是,唐小兵、徐刚等学者在分析作品时所论及的日常生活的焦虑的出现以及作品中涉及的生活政治问题,显然并不只是缘于公对私的侵入——公试图重新界定私的范畴,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界定本身是以相当程度的牺牲私与公的历史关系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剧作的一些细微之处出现了历史性的视角。在笔者看来,《千万不要忘记》中至少有两种需要注意的历史关系。一是在少纯情书里出现的对阶级的历史性问题的讨论,二是对季友良和丁少真的过往情感经历的叙事。上文对这两种历史关系都多少有所涉及。在涉及丁少纯情书的相关情节中,阶级联合是以婚姻的形式呈现的,这本身即具有历史性。蔡翔就曾明确指出,姚母这一形象的出现,表示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工商阶层——包括其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基本得到了保留[7](P346)。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反帝反修”的历史语境中,在重提阶级斗争的时代号召下,新民主主义时期基于统一战线基础的阶级联合需要被否弃。由此可见,丁父对少纯情书中基于统一战线前提而提出的阶级联合的恋爱观的不满,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不满”(5)这种历史性的视角,同时也包括这一时期文艺创作中侧重对“家史”的书写,尤其是对革命家史——革命家庭在阶级上的历史合法性——的强调。具体论述可参见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4页)。。
阶级情感的日常性和生活化,也是共产主义革命政治性的重要标准,比如,延安时期《红布条》中的军民关系即是以高度生活化的场景呈现的(6)苏一萍的《红布条》一剧,鲜明地反映出生活中的军民关系即包含重要的政治内涵。该剧内容大致如下: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是外来的,与地方上的群众关系还未牢固,事务员作风生硬,认为群众接待八路军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与群众发生冲突。为缓解军民矛盾,班长带领战士们为群众挑水扫地,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最后缓解了军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前所述,《千万不要忘记》中少真回忆起友良在少时及其入厂后所给予的关爱,这与当下友良一味醉心工作而罔顾少真的心理感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丁、季恋情中所反映出的阶级内部情感叙述的难以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这一时期的阶级话语和革命政治的自我表述开始逐渐趋于僵化。我们发现,阶级联合的否弃与阶级内部情感叙述的难以维持形成了极为吊诡的同构关系。爱情作为话题,一方面说明爱情本身的重要性,即私人性的情感此时已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极为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急切地将私人领域的情感问题公共化,又说明现有的革命话语无法完全将个人的情感问题统合进来。这一点,从剧作对季友良这一人物的设计就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显然,《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被加以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本身负载了过多的政治内容和历史内涵。在剧中,如前所示,尽管季友良也试图去理解少真的情感(比如从“不信你那一套”到“看来我要去赔个不是”),但从根源上说,丁少真的爱情问题并不是以良性的两性互动的方式来解决的,而是以一种自我消化和自我说服的方式被予以克服的,甚至是一种“忽然”的转变(剧中将少真当时的状态描述为“忽然兴奋地”)。也就是说,丁少真的爱情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丁、季二人的和好虽以少真的热泪盈眶作结,但少真情感上的波澜突起却并未发生在友良真诚的道歉之后。友良致歉的话尚未开始,少真就在对友良的思想进步、技术“了不起”的再度崇拜中全然原谅了对方。并且我们发现,剧本直至终局,也未能为丁、季二人的爱情安排一个美满的结局,二人是否和丁少纯、玉娟一样步入婚姻的殿堂,最终也悬搁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袅袅尾音之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季友良,为何在其个人的恋爱中一定是个木讷而寡欲的人,这一问题确实耐人深思。
总之,《千万不要忘记》中的爱情书写是高度观念化的。爱情书写的观念化,使得爱情不再被视为青年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欲望形式,相反,它成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革命话语对私人情感的介入,使得爱情逾越了纯粹的私人领域,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媒介。爱情和革命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即二者不隶属于如个人/集体、公/私、男性/女性等既定的二元范畴。剧作明确否定了过于强调个人欲望和生理本能的个人主义式的爱情形态,即基于普遍人性的资产阶级爱情观,另外,在戏剧叙事上不断出现的对私人爱情的悬搁和延宕也说明20世纪60年代主导性的阶级话语无法为革命青年的爱情提供一套整全的价值图景。剧中,爱情作为叙事要素的反复出现与其在具体的叙述中不断被阻断的叙事困境,恰恰反映了60年代中国革命内在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那一时期中国革命试图赋予青年以政治主体(“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份,并试图通过规训其情感结构以形成政治认同,从而获得文化领导权,但实际上,政治话语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并未真正得到弥合。因此,《千万不要忘记》中被规训的“爱情”实则反映了60年代中国革命话语、阶级认同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应被视为一种情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