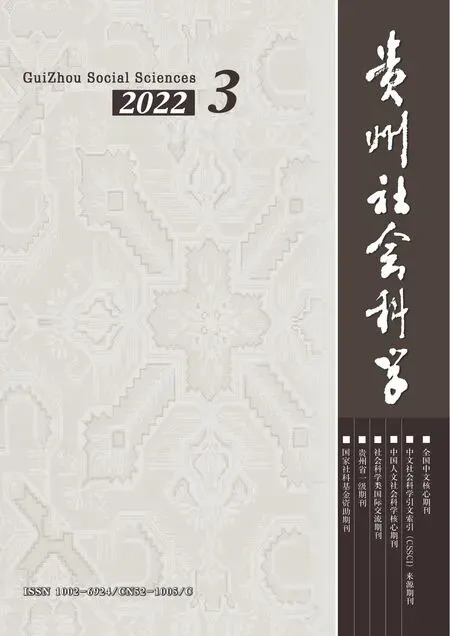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品格
古远清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大多局限于大陆的作家作品。改革开放后,台湾地区的文学作品先是从“地下”渠道进来,再后来有公开出版,但出版的作品大都经过严格筛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随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经久不衰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出国留学热和所谓“洋插队”现象。中国学术界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由文学史扩展到民族史、移民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由过于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走向语种的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外国学术界也不甘落后,如1986年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已去世)和当时在美国教书的刘绍铭,联手在德国举办了“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研讨会。这“大同世界”,是把“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th)中的“共和联邦”一词汉文化,由此延伸出“华人共和文学”。这“共和文学”或“大同文学”,是一种虚拟存在而非实体。“大同世界”也就是彼此和谐相处,联合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学组成统一战线,和强势的英语文学相抗衡。这是一种非政治性的文学抗争。
早在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香港作家作品为主。随着两岸交流的升温,台湾作家的小说、新诗已可从不同渠道获得。“港台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变成了“台港文学”。在1991年广东中山市召开的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又在“台港”后面加了一个“澳”字,形成“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格局。可这个名称太长,且“台港澳”属中国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以外的文学,因而到了1993年江西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将长名称缩短为“世界华文文学”。当然,这不是“减法”问题,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变革,即是说把用华文书写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不局限在某国某地区,很有创意。
命名的更新,源于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台港澳文学,虽属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文艺政策的差异,台港澳文学有不少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殊相”。
至于海外华文文学,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延伸。像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虽然关系密切,“华”字便说明了这一点,但其华文文学毕竟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学:除东南亚各国作家多数在本国出生或中国出生而加入了该国国籍外,还因为他们的书写有浓郁的南洋色彩。在题材上,表现的是东南亚各国的生活,语言上也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有不少作家是从中国移民去的。一旦他们“落地生根”后,其作品主题与艺术形式,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变。
这些异质性,为形成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品格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不但与中国文学有特殊之处,而且也不能等同于世界文学。不错,世界华文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世界文学使用的语言有英、法、日、韩等多种,而世界华文文学只将使用华语或曰汉语的作品列入自己的研究范畴。至于华人文学,尽管不一定用母语写作,而用所在国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虽仍有“华”的制约,但却是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而是在文化传承上与地道的英语文学、法文文学不甚相同。它是一种“双重跨文化”,与单纯的英语文学及其他语种文学所使用的“灵魂的语言”及“工具的语言”有所区别。著名的具有“流动的华人性”的共鸣性文本,得到大家肯定的有美国汤亭亭的《女勇士》、伍慧明的《骨》,还有任璧莲的《梦娜在应许之乡》以及谭恩美的《喜福会》。这些作品,在文化母题的改造,在作家的漂泊、离散过程中,已与中华文化有一定的疏离。仅从艺术形式的演进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虽不能也无法“断奶”,但“奶水”毕竟已稀释。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世界各国各地文学的总和,而是指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相互激荡、相互交流或融汇的一种现象。世界华文文学所强调的亦是一种跨文化的国际视野,是与其他语种的文学相互沟通和接受的一种文学。但其覆盖面远未有世界文学广,它只局限在“华人”或“华文”范围内。
这里讲的华文书写,也就是汉文或汉语书写。汉文与英文、日文、韩文不同,它有偏旁、有四声、有象形、会意,写诗词还讲究平仄,而华人用英语或别的语言写作,那当然会去掉汉文(语)这种特有功能。无论是用罗马字书写,还是用拼音文字去取代,与中华文化传统必然渐行渐远乃至断裂。华语书写无疑有利于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成语和约定俗成的词汇,都有典故,这典故便是古籍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改用外文书写,或将其翻译成别国文字,必然会失却原有的韵味。故华人文学中的外语书写与华人用汉语叙事,有着鲜明的文化差异。尤其是第二代移民还有土生华裔的中文写作,他们无不认为他乡是故乡,故乡亦他乡,在时空转换中找到自己的灵魂栖宿,从客居走向归属,这与传统的中国叙事自然拉开了距离。不管有何“距离”或差异,华人文学与其他语种的世界文学,都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世界华文文学不是一般的研究方向而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06年已逐渐引起中国社会科学学界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首次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列入、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样同属三级学科,这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不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支或曰子课题。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以自己的实力获得公认的一个里程碑。
凡是新的事物出现均会遇到阻力,如这门学科是否属新兴学科、其学科品格是什么,仍有不同的看法。但难以否认的是,世界华文文学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正在独立发展、自成一家。
无论是称“汉语文化圈”还是称“世界汉语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人们都十分强调跨界、跨国、跨文化。不同观点的碰撞,有利于逐步发展和日趋完善新兴的学科,有助于世界华文文学独特学科品格的认定。开放性、兼容性、多元化、成立体状态,这是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不相同的突出特点。具体说来,作为新时代的文学高地,它具有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边缘性这四种品格和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降,后殖民、后现代、跨文化、全球化、差异表达这些能指符号,特别是来自于希腊的“离散”还有漂泊、流浪,成了世界华文文学应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身份问题的理论来源。此外,中国开展的海外移民史探讨及其种族身份认同上的阐释,无不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性质相关,也就是在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学科特征以及文化变迁的母体上,提供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参照系。据有关资料显示,从中国迁到海外的移民,怀乡情态浓郁,仍想保留原来的国籍;或为了适应现状的需要,实行双重国籍制。这种情况到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华侨便断“侨”而成为移居国的外籍公民。随着从漂流四方到定居,去掉了过客心态以当地主人自居的“华侨”,便有了新的称呼“华人”,随之而来的是“华裔”[1],即不在中国出生而在异国他乡成长的新一代。他们与“华人”最大的区分是“文化中国”未必在心中扎根。不管是“华人”还是“华裔”作家,其创作的作品也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分支,而成了居住国文学的一部分。比如把东南亚华文文学看成是海外的中国文学,这会有伤他们的自尊,也不符合平等相处的原则。
这种从“战后初期的‘华侨不变论’,到20世纪60年代的‘华人同化论’,走向20世纪80年代王赓武的‘华人多重认同论’”[2]的移民史研究,再加上“双语写作”的华人文学的探讨,是学者研究海外华文作家身份转型的一种重要理论前提。
一、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性
国际性是世界华文文学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世界华文文学的生产,本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也是由其作品所体现的普遍价值及涵盖的广阔性的精神气质所决定。国际性,理所当然是世界华文文学所追求的一项重要价值体系。
决定国际性成为世界华文文学本质特征的因素,主要来自作家们的创作不局限于某国某地区。追求国际价值,原是世界华文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世界华文文学的本质是由华人一族文化的传存及其变化所组成,而这传承与变异均是无国界的。各国的华文作家,一直在致力于文化的发展与创造,促进世界各国读者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华文作家原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
国际化也体现在华文文学研究上。这种研究,是由于具有“华人血统”的移民导致研究题材的变化和视野扩大的一种带有国际性的表达。华文文学研究如果去掉了国际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国际性,既适应了以创作为根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研究人才的国际竞争需要。为了更好地强化本国政治及文化利益,世界各国均想尽千方百计在各个研究领域展开竞争,包括华文文学创作领域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潜在的竞争,官方不会出面。这种竞争,也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广泛地吸纳别人的优势,用以巩固和发展自己文化的长处和创作、研究的地位,以便有力地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向国际化迈进。
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国文化的哺育。从中国向东南亚、北美洲、大洋洲等地移民的作家们,均希望创作出超越国界的高水平作品。这集中体现在2010年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设立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这个华语世界的文学“诺贝尔奖”,以世界华文作家为对象颁发。“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是此项文学奖的永恒主题。在我国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亦创办了“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奖励优秀的华文作家和出版社。这些得奖作品,同样体现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价值。
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性,还表现在传播上,以金庸的作品为例。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港澳地区流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金庸的作品走向东南亚华人文化市场乃至欧美华人文化圈。这得力于作品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及其写作方式上对世界各地华人审美趣味的把握。这是金庸对强势英语文学的一次成功“突围”。金庸作品还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包围”。不管什么政治派别的人,都喜欢读他的作品。金庸亦突破了雅俗对立的“包围”,做到雅俗共赏,甚至实现了将通常视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向高雅文化的转换。金庸作品传播全球化,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大奇迹。
总之,具有族群性、地域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更鲜明的色彩是国际性。这既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内涵,也是其存在的根基和价值。
二、世界华文文学的移动性
在国际视野下,多层面地阐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演变及其创造性成就,必须有一种文学整体观。世界华文文学在作家队伍构成上,主要由中国移民及其华裔组成,移民和流动较为频繁。出于各种原因,往加拿大等国流动的作家比较多。从20世纪50代开始,也有从世界各地流进我国香港地区来的。这种作家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的情况,体现了世界华文文学与国际性相连的移动性这一现象。
不断地移动,就有不断的乡愁产生。所谓乡愁,是人类永恒的感情。无论他是什么政治信仰,乡愁都会驱之不去,拂之不走。这是一种模糊的怅望,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正常过渡期,也就是卡森·麦卡勒斯笔下混合着孤独的怀旧。这种乡愁文学,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乡愁的“乡”是专指某一地方,二是指精神的故乡,并不特指作者出生的某地某乡。于右任怀念的故乡便是泛指。余光中的乡愁诗,其乡也是一种文化理想之乡。他到台湾后,最怀念的是祖国大陆的长江黄河、家乡的人民及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漂泊、流亡、奔走、流浪、往返、回归所组成的移动性,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一大品格,但作为文学母题的移动与放逐,具体到各国作家的移动和书写方式不完全相同。一般说来,作家离散式的移动书写表现在“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到何处去?”“我是谁?”“我为何不停地移动?”“我的家到底在哪里?”的“拷问式”;或“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漂泊式”;还有是永远做流浪汉,永远无家可归的“无根式”。
在这种移动中,心灵移动也不可忽视。所谓心灵移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没有离家出走,但早已心系他乡。这是一种灵魂放逐,其源于对母国生活方式的不满或不认同。而身体移动,也就是移民,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欲望的驱使有一定关系。以个案为例,马华作家李永平就属典型的流浪人,他从这个岛移向另一个岛,因而他的生活状态及书写方式,有一个重要特征正是移动和流离。他生前一直没有重返故乡,故他的小说或其他作品,都是移动式的漂泊书写;而企图寻觅人类永恒家园的诗人原甸,他的移动从新加坡开始,然后到中国内地,由内地到香港维多利亚海湾,最终从东方明珠的香港回归新加坡。这种移动,是20世纪60年代向往社会主义中国的东南亚左翼青年,实行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一种精神旅程,同时也在不断移动的书写中,体现了一种精神放逐及其“去国—漂泊—回归”的文本范式。[3]
随着当时英美等国关注自己国民利益收缩签证和移民政策,也因为中国当年和一些国家没有建交,这使得中国台湾地区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的重要流入地。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移动性,不能单纯局限在从中国移动出去的作家身上,还应注意从国外移进中国的作家的原因。如台湾地区就有从南洋飘来的“旅台”马华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马来西亚到我国台湾定居或留学的马华作家就有李永平、陈慧桦、张贵兴、温瑞安、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等。他们大部分能写、能评、能编,尤其是以蕉风椰雨的异国情调成功地介入台湾文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旅台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他们或勇夺“两大报”文学奖,或进入学院体制和占领文学讲台。他们还以自己的“台湾经验”审视马华文学,在马华文坛掀起阵阵波浪。
移动性也表现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概念上。作为一门很有前途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内涵不可能完全固定。作家们生活上在不断地移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不断地平面移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拓宽研究的范畴和时空。它不可能是一个永恒的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汇集。它不是被动地等待人们发现,而多半是研究者自己去主动建构。无论是“离散文学”“流散文学”“流亡文学”“新移民文学”“新华人文学”“新华侨文学”“新华文文学”“新海外文学”或“海外中国文学”“海外汉语文学”“华美族文学”“唐人街文学”“洋插队文学”“洋打工文学”直至使用频率极高的“华语语系文学”,相对来说都缺乏鲜明的自律性,其学科归类先后也不一致。交叉性和模糊性,正是所有新兴学科的共同特征。
移动性带来了争议性。比如世界华文文学:
是“汉语的”还是“华语的”?正如沈庆利所说:“‘汉语’对应的是‘汉人’、‘汉族’之族群名称,意指‘汉人使用的语言’;‘华语(文)’对应的是‘华人’、‘华族’之名称,意指‘华人使用的语言’。”(1)沈庆利:《必也正名乎?——评析华文(语)文学的几个概念的论争》,未刊稿。显然,“华语”的涵盖面更宽广,用“华语”比“汉语”好,而“华文”的使用比“华语”更普及。两者当然可以并存,但在中国大陆普遍使用的是“华文文学”而非“华语文学”。就是台湾地区,成立的团体也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而非“世界华语作家协会”。在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生前主编的大型国际性刊物也不叫“汉学”或“国学”,而叫“华学”。
是“语种的”还是“语系的”?王德威等人提出“华语语系文学”,据说是为了突破“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格局,“语系”是相当于“系谱”的观点,其实“语系”一词纯属画蛇添足,简称“华语文学”或“华文文学”岂不更简单明了?不错,作为跨界研究的“华语语系文学”,其中使用了别人较少关注到的文学地理学方法,对不居于主流地位文学的关注有利于“中心”“边缘”文学的转换和融合。这强化了汉语文学研究范围,但不管怎么说,“语种的”比“语系的”更不易令人产生误解和误读。
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陆台港澳文学属“海内文学”,而中国以外的文学即海外华文文学,属外国文学。虽然两者有交叉之处,陆台港澳文学毕竟是从语种角度立论立名,不属于国别文学,这是不容置疑的。有人曾将台湾文学称作“海外文学”,说轻一点是用词不规范,说重一点是政治上的失误。台湾本是中国的领土,其文学当然属“海内”,这是一种基本常识。
从历史上看,学科疆界的移动不仅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有,而且比较文学学科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也出现过“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华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文文学”“民国文学”“汉语新文学”各种概念百花齐放的现象。学科的制度化,总是从阐释和商榷的往返论辩,也就是由移动走向稳定,再由学术理念的稳定回归移动。如此生生不息,世界华文文学才成为有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三、世界华文文学的本土性
本土性是指由时间累积的文化习俗,还有地域共同作用互相影响而体现出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地区性差异。比起文化习俗来,地域性更为重要。简言之,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或本土意识。
本土性的典型个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可看出在此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在战前出现的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
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时候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不断在凸显南洋本土色彩,独立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华族文学”。在这方面,新马华文学是最突出的例子,如金枝芒作品对马来亚共产党充满感情,处处不忘歌颂“人民的子弟兵”,这点与中国的一些小说非常相似,但仍有不同之处,像故事背景为热带雨林,还有“亚答”“芦萁芭”这些中国小说没有的词汇。再如泰华文学,也不再是侨居生活中的忆往昔文学。它经过80年的移植,已从“落地生根”慢慢走向“根深叶茂”,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政治上太过倾向中国、艺术风格上过于接近中国。这好比“流经泰国就成为湄公河,水源来自中国,河流属于泰国。”(2)司马攻:《泰华文学的定位》,《世界华文文学》1999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比喻的说法,湄公河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流入中南半岛后的河段称为湄公河,不完全属于哪一个国家。
与华文文学本土化相适应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爱国主义内涵的转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爱中国。后来,新马华人与侨居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居住国作出巨大的贡献,这时的新华作家,逐渐由对华夏故土的挚爱转向为对移居国的认同。他们与其他居住国的民族一样,强烈渴望铲除殖民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像原甸的《青春的哭泣》、杜红的《我不能离开我的母亲土地》、李贩鱼的《我永远站在祖国的土地上》,这里“哭泣”的对象和“母亲”“祖国”,均指向其居住国。当其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新华作家便掉转笔锋,由呼唤民族解放转为歌颂年轻共和国的诞生,如李汝林的《我爱新加坡》、董农政的《我们是新加坡人》,就是洋溢着爱国主义豪情的作品。这些新华作家,都经历了“从土地认同到国家意识的转化”[4]的过程。
东南亚华文文学除“新华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与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受到同等看待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大都属于“在贫瘠的土壤上开放的野花”[5]。由于当局不重视华文文学甚至有些地方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再加上把文学视为生命的华文作家占少数,发表园地稀少,读者面局限于少数文化层次较高的华人。东南亚华文文学这种先天不足,使他们整体的文学成就不高[6]。
台港澳文学同样存在着本土性问题。台港澳文学的独立发展,以自己的本土色彩为祖国文学的大花园增添新株。人们常说刘以鬯是“南来作家”,可他在“石屎森林”(即,高楼大厦)的香港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从他发表和出版的作品看,“南来”的色彩在不断褪化,本土色彩却在直线上升,他已成了地道的香港作家。
四、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缘性
华人离乡背井到海外漂泊,相伴他们的精神支柱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
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华文。远走他乡的华人,无论是漂泊在富得流油的西方国家,还是受英国殖民的马来亚等经济上还未飞腾上升的国家,他们在居住国均无法进入上层世界,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哪怕汉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一样是大语种,使用的人口也很多,但海外的华人一族文化仍无法占据主导。在各类语种中,英文似乎总是在“执牛耳”。
走遍世界各地,很容易找到“唐人街”。在“唐人街”,有的作家做出“告别母语”的痛苦抉择而用居住国语言文字书写,许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无奈的。这是为了谋生,为了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是21世纪“新华人”的一种退路,或曰出路。“出路”其实未必。作为不易脱胎换骨、不易被同化的族群,即使在殖民者撤退后,华人文学不仅会留下后殖民的图谱,更会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
边缘地位源于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如位于婆罗洲岛西北部的文莱,马来语和英语是官方语言,而华语属弱势,故用华语创作的作品,在文莱这个“和平之乡”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再以马来西亚为例: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其宪法规定马来语是马来亚的国语,只有用马来语创作的文学,才是国家文学,而用华语写作的文学,只能是地方性文学,也就是边缘文学。
在边缘体验方面,林幸谦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并非出生在神州大地,而是吃马来米长大,可说的却不是马来语而是汉语,写的又是中国文字。如寻根问祖的话,他的祖籍为中国福建省,故蕉风椰雨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乡。在这种情况下,林幸谦对“本体论的流放”情有独钟:人类不一定有固定的家乡,离乡背井的“井”对他来说是很难触摸的,也是不现实的幻影。不承认有实体的土地可指认的家乡梦土,这梦土历来比地理学上的乡土更具有超越性,更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魅力。正是林幸谦一类的华人在居住国属他者身份,以及华人与西方文化的难以融合的情况,这就决定了华文文学在海外是一种边缘存在。
海外华文文学不仅在西方文学中经常处于边缘状态,而且某些带有交叉特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排行榜中往往也排在后面。这好像对边缘文学不尊重,其实边缘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正因为不占中心地位,也就有可能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反映了跟中心不同的文学样貌,显示出不随大流的独特品格,从而形塑出海外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尽管它不存在“惊涛裂岸”的壮观局面,但涓涓细流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是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补充,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3)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东南亚华文小说榜上无名,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而台港小说的成就则不同。在“百强”中,台湾小说共逾四分之一。仅前50名,台湾小说就占了14部。香港小说也不甘落后,在一百本小说中占了12部,超过十分之一。这次评选尽管在标准等方面有可质疑之处,也不否认有赝品混迹其中,但基本上反映了全球华文小说创作的面貌。
总之,“边缘文学”系与华文作家居住国的“国家文学”相对而言,另一方面与他们始终生存在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夹缝有关。也可以说,华文文学的边缘性与上面说的移动性是一对“难兄难弟”。移动的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移动的特殊状况,引申出边缘性问题。这是一种因果关系,是构成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兴学科重要特征的原因之一。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突围”出来的新兴学科,为构建世界共通的华文文学意识的多维视野,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超越不同文明的畛域和不同文化的视野,探讨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期许与想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一个具有国际性、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蹒跚起步到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在“突围”中日益走向成熟,其发展前景日新月异,令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