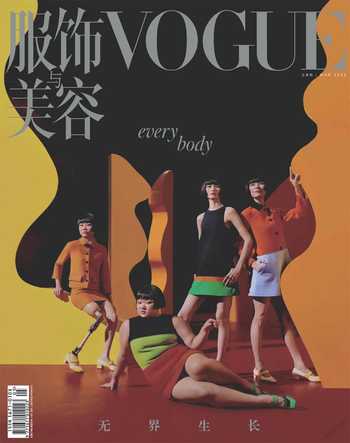肉体会消逝,但身体艺术将永存
Sinbad Cleeson
2020年年中,爱尔兰多次推行严格的封锁政策,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跻身全球最严格的封锁政策之列。而恰在此时,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位我长期关注的艺术家。几年前,在一个艺术节上,我第一次非常偶然地接触到她的作品。当时,一家报社邀请我对艺术节进行报道,我便在城里信马由缰地随处闲逛,采访不同的人,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一天下午,我发现河边有座小型建筑,那是一家画廊,里面十分昏暗,正在播放不同的视频片段。在一个片段中,一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修剪花园的草坪:而在另一个片段中,她又假装自己是个吸尘器。这位女士就是爱尔兰艺术家Aideen Barry,她在自己的作品中饰演后现代社会的完美妻子,并提出郊区孤立、家务劳动和消费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既带有政治色彩,又妙趣横生,她是一位不惧将自己的身体置于作品中心的艺术践行者。
几年后,Aideen联系了我,尽管我们居住在爱尔兰的不同地区,但还是相约共进晚餐,在此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2019年,我的书《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Constellations)首次出版,那一天,她驱车前来都柏林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往返要四个小时。Aideen的工作围绕着影片、定格动画、表演和装置艺术展开,我的工作则是写作:虽然各自投身的领域大相径庭,但参与的主题却高度重合。我们的工作核心是身体,如身体的性别角色、健康的体魄和病态的躯体等等。在《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中,我提到许多艺术家,不过,总的来说还是集中叙述身体及其承受的东西,讲述疾病如何将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切都随之改变。在新冠肺炎蔓延期间,Aideen和我都居家办公,因为学校停了几个月的课,我们还需要在家照顾各自的孩子。那时,她發邮件问我,是否愿意为她的新展览写点什么。在她发出这封邮件的时候,我正忙着完成自己的小说,以及与Kim Gordon共同编辑的文集This Weman’s Werk:Essays on Music,但Adeen的新项目听起来极具吸引力。展览名为“By SlightUgaments”,出自Mary Shelley的哥特式文学杰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属于多媒体大项目“Oblivion”的一部分,特邀多位音乐家和作曲家,以及一位美甲师、一位竖琴师和一位因纽特人喉音歌手合作。
《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怪物被复活并重获新生的故事,而我则很想知道,在后疫情时代、后疫苗接种阶段,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否拥抱朋友,能否去听音乐会,还是仅仅站在忙碌的人群中。Aideen在展览的视频部分使用了自己的身体,包括脸、鼻子、嘴,这让我不断回想起短剧《不是我》(Not)那是爱尔兰作家SamueI Beckett的作品,戏剧的重点特写是一张在黑暗中说话的嘴。为此,我写了一篇名为“Beal”的文章,Beal在爱尔兰语中是“嘴”的意思,文章内容是有关呼吸、公共空间、过度劳累,直至感觉我们与世界中断了联系。为了防范新冠病毒的侵扰,出于恐惧、安全和对他人的尊重,我们的嘴巴被蒙上了口罩。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它需要被人们听到,而不是仅仅是被阅读。于是,我与我的丈夫Stephen Sharmon合作,他是一位作曲家,我们曾合作过多个音频项目。针对“Beal‘Stephen设计了一种声音,为文字配上了具有层次感的音乐,音频通过画廊的黄色黑胶唱片循环播放。
艺术,特别是身体艺术,可以诉说无法在其它地方表达的社会、政治内容。在《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中,我写了几位艺术家,他们是一群艺术践行者,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表达的中心,其中几位还把血液当作艺术工具。比如,古巴艺术家Ana Mendieta,她的身体在其行为艺术、视频和摄影作品中反复出现。她认为,血液是父权对女性暴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女性力量的象征,并在其作品中一再呈现这一观点。艺术家Vanessa Tiegs为那些在作品中使用经血的艺术家创造了一个术语“Menstrala”,该命名引发了一场运动,借此在他们的行为实验中,甚至在以艺术形式将女性难言之事公诸于众的过程中,将艺术践行者团结在一起。
2015年,美国艺术家Carolee Schneemann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以前我从未受到过重视,女性经历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我不知道我的作品能否改变这一现状,但我必须做出尝试。”她的声音透露出显而易见的疲倦,在其职业生涯的几十年里,她总是要不断地解释或证明她正在做的事。
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最无畏的作品之一,是《内在卷轴》(Interior Scroll,1975)。这既是女权主义的一种对抗行为,也是一种对阴道偏见的矫正。她重申,阴道是负责分娩的身体部位,它是神圣的。
在作品《达至与包括她的极限》(Up to and IncludingHer Limits)中,赤裸的Schneemann被缚上绑带,然后在墙上作画,这是动态绘画的一种形式。这个作品表演了好几次,Schneemann认为,这是在与抽象画家Jackson Pollock的作品对话。即使该作品已经表演了很多年,但Schneemann仍然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画家,而非行为艺术家。就像她的许多作品,诸如短片《融合》(Fuses)、摄影作品《眼与身》(EyeBody)那样,她因不妥协的态度和以女性身体为重心的创作而备受赞誉,不过,也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她“固于男性传统”,这些话深深伤害了她。
所有的女性作品都需要一种坚定无畏的精神和对自我创作的肯定。新冠肺炎的流行让大多数人变得更加恐惧,(我们中的一些人)此前从未思考过罹患疾病、身体衰竭和至亲离去的问题。也许这种恐惧会渗入艺术和写作中,我们变得更不愿意去承担以往曾经遇到的风险,同时我们太疲惫了,无法再次面对这些风险。2021年,Aideen Barry的作品0blivion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我们是最后一代艺术家,那我们该怎么做?
对大多数人来说,熬过2020年和2021年就已足够,安度每一天仿佛已成为我们唯一的目标。我的工作是写作,这是我所做的事,可是当世界停摆、视野缩小时,我很难找到灵感。我给卧室买了一张小桌子,孩子们则在其它房间上网课,这些让人分心的事让写作变得愈发困难,但我还是接受了一些工作委托,包括书籍论文、“Beal”和另一个艺术项目。为了让别人认为我很可靠,只要有人邀约,我就应承。在世界变得如此安静之后,截稿日、合作和谈话仿佛串成了我的生活线。
我渴望再次进入画廊,回到那里,站在画作前,从不同角度欣赏一件雕塑品,坐在黑暗中观看视频。我写了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世界另一端的一家艺术画廊委托的,内容是我的前辈女性艺术家的故事,标题“Many Mamans”来自Louise Bourgeois著名的巨型蜘蛛雕塑。有一次,在伦敦泰特画廊,我就站在蜘蛛雕塑的鋼架下。这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作品,然而归根结底,它是一件温柔的雕塑。正如Bourgeois所讲解的那样,它是关于她母亲的作品,她既是纺织者,又是保护者。
“Beal”并非是我与某位艺术家的首次合作;2021年,我还参与了另一个项目,是与两位艺术家共同完成。AliceMaher堪称爱尔兰最知名的在世的女艺术家,也是我从20岁起便开始崇拜的偶像。她与艺术家Rachel Fallon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作品,那是一幅虚拟世界的地图,采用大型布雕的形式,由各种织物经过手工缝制、绘画、贴花、钩编而成。在疫情封锁期间,Alice和Rachel会互相邮寄布料,戴着口罩到画廊创作。6.5mx3.5m的大地图上展现了想象中的岛屿、国家、家族徽章、星座和风。它代表了女性遭受奴役的历史,取材大多来自爱尔兰女性,但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巨大的织物上展示了历史上诸多不公平的现象:玛德莲洗衣房强迫未婚母亲在此居住,整日浆洗衣物却不给工钱;母婴之家中,非婚生子的年轻女孩被迫放弃自己的孩子,交由他人收养:地图上还传达出多种立法行为,包括近年才解除的堕胎和离婚禁令。Alice和Rachel倾注巨大心血,耗时三年才完成这幅地图,成千上万个手缝针脚代表着女性的家务劳动,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女性在家庭中辛苦劳作却被人忽视。Alice和Rachel都对我说,整个创作导致她们手指酸痛,手腕也出现了问题,背部有时异常疼痛。这一创意对体力要求很高,她们在健康方面付出了代价,但是创造了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兼具政治意义和可观赏性。
在第一次会面时,她们问我,是否愿意使用画廊的另一个小房间,而不是仅仅要求我写一篇文章介绍其作品。我创造了一个普通女性的形象,她在Alce和Rachel的“地图”前走动,并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不公、歧视和历史带来的负担。Stephen Sharmon再次加入进来,负责创作声景:我邀请了35位女性一同录制“We Are The Map”(我们是地图一角)这句话,包括我的母亲、女儿,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在17分钟的作品结尾处,她们齐声说出这句话,时至今日,仍令我感动万分。
起初,对于“Beal”和“We Are The Map”的要求都是写一篇艺术作品简介,原本我应当“记述”作品本身。我对两个作品都做了不同尝试,但如果只观看作品并写下它的含义,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更有趣的做法是与作品深入交流,与之对话,从中衍生出两件全新的声音艺术作品。若我笔下的文字只是静态的、囿于纸面,其影响就会大打折扣;它们需要被听到,而且是在画廊这一极为特别的空间中。
有些艺术家将身体作为工具、媒介和画布,这方面,我要重新回到行为艺术主题,特别是长时行为艺术,这就不得不提TMarina Abramovi6的《节奏0》(Rhythm 0)。在长达六小时的时间里,她始终躺在一张桌子上,身边是72种物件,包括锯条、钉子、蜂蜜、刀子,甚至还有一把装了一颗子弹的手枪。参观者可以对她使用这些物件,用任何方式与她互动。
这些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挑战世俗,吸引关注。多种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均要求人们将身体遮盖、隐藏起来,并以裸露身体为耻,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我欣赏许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她们都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像对待颜料、石头或胶片那样加以利用。她们赋予了肉体和皮肤其它含义:政治表达、嬉笑逗趣,或充满情欲。身体为艺术作品提供了场地,既是载体,也是要表达的内容。
十几岁时,我在医院住过很长时间,经历了痛苦且复杂的手术过程。我经常只能躺在床上,感觉非常孤独。我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音乐,年纪稍大一点时开始欣赏艺术作品。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找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让自己不再如此孤独。作为一个16岁的女孩,我最感兴趣的艺术家是墨西哥画家Frida Kahlo,她用画笔展现了她的伤痛、她身上的伤疤和她残缺的身体。我十分欣赏她的画风。她用画作呈现了自己的一生,去对抗疾病与女性躯体的诸多禁忌。她的作品表达出了我的感受,我也由此一直欣赏并钦佩她的创作。2005年,我在伦敦泰特画廊观看了一场Kahlo作品大型回顾展。我走过每间展室,面对着不同身份的她:艺术家、女人、病人,每面墙上都是她不同的一面。走到《破碎的柱子》(The BrokenColumn)前,我停下了脚步。在这幅画里,一条长长的裂缝贯穿了她的躯干,断裂的脊柱暴露在外。没有骨头,只有一根金属柱子,一如倔强的她拒绝向痛苦屈服。几百个钉子嵌入她的皮肤,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向下流淌。这幅画不仅表现了痛苦,还让人感同身受。每当看到它,我几乎都会皱眉退缩,陷入它唤起的苦痛之中。
回想少女时代在医院度过的那些年,总有一个时刻让我心生畏惧、深感无力,那便是每天早晨:一大清早,会诊医生会带着一队实习医生查房,往往有十几人,而且大多是男性。他们挤在会诊医生身边,不和我说话,也没有眼神交流。病人在医院时常会有这种无力感,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待解的难题。英国摄影师Jo Spence对此深有感触,她用相机记录了这一切。Spence确诊乳腺癌后接受治疗,她从医院病床的视角拍下一张照片,正是一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围着另一个病人的病床。这一作品题为The Picture of Health?(1982-86),第一次看到它便让我回想起了那段日子:一群男人围在一个惊恐的女孩床边,却不去理会她。没有交谈,没有微笑,更没有宽慰安抚的只言片语。Spence的作品以摄影为主,不过她也制作拼贴画,出版图书和小册子。在Cancer Shock中,她记录了另一个医疗干预的场景:一名年轻的医生站在病床边,讨论她的乳房肿块切除情况。他没有说话,而是俯身在她身上划了一个“X”,Spence则重重地答复他“不”。
2021年已接近尾声,爱尔兰的新冠病例数量再度增加,我曾发誓将专注于我的小说创作。可当BBC的一位制片人联系我时,我还是同意再接受一项委托(如果算上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便是两项委托)。2022年是《观看之道》(Waysof Seeing)问世50周年,这本书以及电视系列片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出自伟大的艺术作家和思想家John Berger之手。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历史上获准从事艺术创作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很多是男性),而更主要的是,它教会了我如何欣赏画作,如何看待艺术作品。5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具有现实意义。制片人希望我写一篇广播稿件,讲述《观看之道》对我的影响,并选择一件艺术品深入赏析。只挑选一件是不可能的,但我设定了选择标准:具有爱尔兰特色,由女性创作,且不是绘画或摄影作品(这也是Berger在电视片中主要探讨的内容)。据此,我选定了爱尔兰艺术家Amanda Coogan的长时行为艺术作品Yellow Coogan坐在一个水桶上,身穿五米长的黄色裙子。桶里是水和肥皂沫,Ccogan一遍又一遍地洗着这条裙子。这一表演通常持续六个小时,但今年在都柏林Coogan表演了更长时间。对一些观众来说,它可能看起来很滑稽、很混乱,或只是无聊的重复。可在同样身为爱尔兰女性的我看来,其中充满了政治意味。洗涤和擦洗代表着女性的劳动:无休止地浆洗,让人联想起了过去被关在玛德莲洗衣房中的女性劳动者。但是,和所有艺术形式一样,每一个动作、每一抹黄色、艺术家顽皮吹起的每一个泡泡都蕴含着希望,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如此短暂。
身处艰难时期,我们能做的就是投身艺术、写作、音乐,还有大自然。绘画、摄影作品与文字一样,都能给我带来安慰。不过,我们的身体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用来行走、交谈、工作的肢体、心脏和手臂,都能给人以力量。同样,Jo SDence、Alice Maher,Carolee Schneemann、RachelFallon、Frida Kahlo、Marina Abramovic、Ana Mendieta和Amanda Coogan等艺术家,也在用颇具艺术美感的身体慰藉着我们。呼吸与肉体或许无法永存,但身体艺术将持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