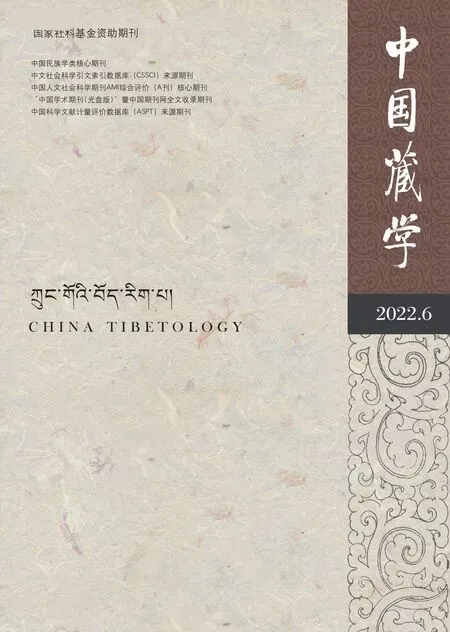《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其资料来源①
赵心愚
《西藏纪述》是清代成书较早的西藏地方志之一,乾隆十四年 (1749)即以刻本问世,光绪二十年 (1894)又被收入振绮堂丛书。乾隆初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不多,故大陆《中国地方志综录》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两种重要方志目录均著录此书,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亦将其收入。②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03页;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9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西藏”部分仅收方志3种,《西藏纪述》为其中之一。近40年来,随着西藏清代民国地方志研究受到学界重视,成书较早的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研究成果也明显增多,但对张海及其所著《西藏纪述》的研究却仍显少,有的只是在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文章中偶有提及,或就一些基本问题提出看法,未作较深入的讨论。①邓锐龄:《读 〈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铅印本,第26—27页;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在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中,笔者冒昧撰此短文,以期引起学界对《西藏纪述》一书及有关西藏的记载与资料来源的关注、重视,推进相关研究。
一、撰书前后张海的经历及《西藏纪述》成书时间
张海,浙江杭州府钱塘人,其生平事迹史志中尚未发现较完整的记载,所幸其著序及书后类似跋的一段文字有简要记述,再结合其他材料分析,可大致了解其撰书前后的经历。书后类似跋的这段文字对《西藏纪述》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先对其主要内容略作介绍和分析。
在这段文字中张海写道:“海初任四川雅州府荥经县尉。辛亥岁委赴口外协办副总理粮兼运军饷赴西藏,壬子复解藏饷。癸丑奉部行取口外舆图、户口、风俗,蒙委清查、绘图、采访,兼剖各土司历年未结夷案,驰驱十月,始获告竣。”②张海:《西藏纪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振绮堂丛书影印本。本文所引《西藏纪述》材料皆引自此版本,标点为笔者所加。所言中提到的辛亥年即雍正九年 (1731),壬子年为雍正十年,癸丑年为雍正十一年;所说的荥经 (今四川雅安市荥经县)县尉,即典史,当时沿旧制称县尉,为不入流属官。按张海自言乾隆六年丁艰离川及“任川十三载”倒推,其入川任雅州府荥经典史时间当在雍正六年或七年。③由于清中央政府将雅州升为府并将荥经归其管辖的时间是雍正七年 (见《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四月辛巳条),张海任雅州府荥经典史在雍正七年的可能性更大。贺泽等修、张赵才等纂民国《荥经县志》卷四《官师志》,记张海任荥经典史时间在康熙末年,其后从雍正元年起典史一直为徐元宪,至乾隆元年才为另一人。民国《荥经县志》有关记载当有误。乾隆十五年之前,川藏道上的粮务“向委佐杂”,乾隆十五年起才“选委丞倅,以昭慎重”④陈克绳:《西域遗闻·疆域》,1936年禹贡学会据江安傅氏藏旧抄本铅印本。。因此,虽然当时仅为未入流属官,张海亦赴口外协办副总理粮务兼运军饷赴西藏,之后又复解藏饷进藏,并奉命在打箭炉以西地区开展调查、办理积案。之后张海又言:“是年,量移泰宁巡检。其地敕建惠远庙,移住达赖喇嘛,有钦差护卫,重兵镇守。斯任则管理汉土民情,兼司粮运军务。甲寅冬,果亲王奉命至泰宁,抚恤番黎,驻节月余,一切供支竭蹶承办,幸免遗误。”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巡检一般为正九品,所以虽自言“量移”,实际上地位可能已略升。建惠远庙、移住达赖喇嘛、派钦差护卫及重兵镇守泰宁、果亲王奉命至泰宁等 (泰宁及惠远庙均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所言与《清实录》《西域全书·历代事实》《西藏志考·历代事实》《西藏志·事迹》及果亲王允礼《西藏往返日记》等记载相合。次年,张海参与了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重要行动。在这段文字中张海称:“乙卯春,奉果亲王派委,护送达赖喇嘛由类五齐、春奔色擦、哈拉乌苏等处草地,计行六月,始抵西藏。”春奔色擦即擦隆松多,在自察木多 (今昌都)由类乌齐草地进藏路程中有此地名,由此可知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所走路线。之后,“戊午升授叙永照磨,复委出口管理里塘粮务。辛酉丁艰。海任川一十三载,奔驰塞外几及十年”。乙卯年即雍正十三年,此年张海到了拉萨,以其当时的地位只能是一般参与护送行动。从《清实录》《西域全书·历代事实》《西藏志考·历代事实》及《西藏志·事迹》等记载看,七世达赖喇嘛于雍正十三年自泰宁出发时间已是夏初,可能粮草需先行,故张海称“乙卯春”。戊午年为乾隆三年(1738),此年张海虽升任叙永 (今四川泸州市叙永县)照磨 (可能已为正九品),但不久又赴里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管理理塘粮务,即在理塘粮台任职。①周伟业修、褚彦昭纂咸丰增刻本《直隶叙永厅志》卷32《职官·照磨》载:“张海,浙江杭州府钱塘人,吏员,乾隆三年五月初八日任。”从下一任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署任看,张海在四川叙永任职仅两个多月即赴理塘。辛酉年即乾隆六年 (1741),此年张海因丁忧离开四川回籍。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使张海对西藏、打箭炉口外藏地以及藏传佛教与达赖喇嘛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使其具备了编纂此书的条件。按张海在这段文字最后的说法,编纂《西藏纪述》是“以志不忘云尔”。这段文字简要记载了张海在打箭炉口外藏地及几次赴西藏的经历,也谈及撰此书的目的,但遗憾的是没有具体明确《西藏纪述》成书于何时,也未言及其丁忧之后情况。
《西藏纪述》前之序为时任安徽天长县教谕徐崙所写,内容涉及张海丁忧之后在天长任职及成书时间。②张海:《西藏纪述·序》,乾隆十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年间《西藏纪述》收入振绮堂丛书时被抽去此序及图。序称:“武林巨川张公调署斯邑”;又称,张“出其先任雅川 (应为雅州,原文有误)驰驱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打箭炉口外、西藏等记述,并绘图于上,汇成一帙以示,而更嘱为之叙”。此序中,徐崙明确谈到张海来天长任职,并称张将“驰驱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书稿交其阅并请作叙。徐崙此序署时为“乾隆己巳”,即乾隆十四年 (1749)。有研究者当据此序中“驰驱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语,认为张海在四川时《西藏纪述》已成书,书稿之后再被其带到了安徽天长县任所。③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铅印本,第27页。这一看法虽也有据,但可能与事实并不相合。其理由一是“驰驱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后还有“绘图于上,汇成一帙”语,说明最初的书稿还进行了绘图及一段时间的整理;二是据天长县志书记载,张海丁忧之后,通过保举任知县的时间在乾隆十年五月至十四年五月之间,徐崙任该县教谕的时间则是从乾隆七年起,也就是双方在徐作叙前已共事4年。在一般情况下,《西藏纪述》若早已成书并早已完成绘图及书稿整理,张海在乾隆十年五月任天长知县与教谕徐崙熟悉之后就会请徐作叙,不至于到乾隆十四年才将书稿交徐崙作叙。④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卷6中,“职官表”(二)。因此,根据目前有限的记载,《西藏纪述》成书时间只能认为在乾隆十四年或有研究者提出的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四年三月间。
二、《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特点
在清代成书较早的有关西藏的著述中,《西藏纪述》虽有一定价值但评价却并不太高。其最大的不足或缺陷是,书名虽为《西藏纪述》,但其内容记四川雅州府属口内外土司较详,记西藏各地及各方面却显略。⑤《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山东: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3—513、514页;陈家琎:《重印 〈西藏纪述〉序》,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仍为此书一重要组成部分,亦需要作一简介并指出其值得注意的特点。
收入振绮堂丛书的《西藏纪述》共76页,除最后两页为前已作简介分析的类似跋的那一段文字外,主要内容为74页。其中,前51页记“四川雅州府属口内土司”及“雅州府属口外新抚土司”,大致各占25页;从51页末江卡儿开始记西藏,直到74页,约占23页。仅从其所记篇幅看,关于西藏的记述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当然应是一重要组成部分。从所记内容看,有关记述虽未分目,但涉及西藏自然、社会与历史、文化以及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关系等诸多方面。江卡儿这一地名在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域全书·道途全载》《西藏志考·程途全载》中虽已见,但《西藏纪述》中有关西藏的记述是从江卡儿开始的,这说明著者对雍正年间西藏与川滇行政分界情况是了解的。其记述一开始即明确称:“江卡儿在打箭炉西南,距打箭炉二十八站,东接巴塘邦木宁静山界。”接着又记,雍正“四年清分疆界,奏请将土地、夷赋赏给达赖喇嘛,并将元、二年招抚之上下达拉宗、类五齐、擦哇等处夷赋悉归西藏,隶郡王普罗鼐管辖。江卡儿,藏设土目营官管理,其地乃进藏孔道,汉番贸易经由要津”。其记述文字虽简短,但西藏与四川行政分界与江卡儿区位及其管理等均一一涉及,只是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域全书》《西藏志考》中所记之颇罗鼐,此书多处作普罗鼐。江卡儿之后,按以上记述方式对乍丫、察木多、洛隆宗、拉里等又作分别记载,均明确记“四年清分疆界”事。其后,对玉树南称等族的划分经过与管理也作了简要记述。在以上记述之后,开始记“西藏”。从“西藏即唐吐蕃地,土人分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康者即察木多,土名昌都一带;卫者西藏,土名拉撒一带;藏者即后藏,土名扎什隆布一带”语及之后的内容看,此处的“西藏”应是指卫藏,但又包括了前所记察木多一带,这是此书所记含混不清之处。与前所记江卡儿、乍丫、察木多等相比,此处“西藏”所记内容则显得较丰富,除了记西藏为唐吐蕃地,分为三部外,还对黄教与达赖、班禅等呼图克图以及所受崇拜情况、拉撒 (即拉萨)城的地理环境及气候、西藏历史尤其是进入清代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治理等作了简要记述,止于普罗鼐(即颇罗鼐)加封郡王,其记述方式与《西域全书·历代事实》《西藏志考·历代事实》及《西藏志·事迹》有相似之处。这段内容之后,未分条简要记西藏地形、建筑、转经习俗及西藏各地自然与部落分布等情况。此后,分条记正东、东北、正北、西北、正西等方向各地要隘及防守情况。再后,又简要记由打箭炉粮运至藏路线与打箭炉由草地至西藏道路以及沿途地方自然、社会、民俗、交通、物产等情况。
从以上简介已可看出,《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不仅涉及诸多方面,而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将有关西藏的记述分作两部分。一为记入藏后至拉萨前各地,并记玉树南称等族的划分经过与管理;一为记“西藏”,主要指卫藏,但又涉及察木多一带等。二是注意沿川藏大道分地记各地情况,并将其置于前。前已言及,书中有关西藏的记述是从江卡儿开始的,因江卡儿“乃进藏孔道,汉番贸易经由要津”,是雍正年间西藏与川滇行政分界后川藏大道由川入藏之后西藏管辖的首个要地。江卡儿之后,乍丫、察木多、洛隆宗、拉里及归入洛隆宗、拉里两条中的说板多 (即硕板多)、冰坝 (即边坝、达隆宗)、工布江达、墨竹工卡、得庆 (即德庆)等,皆为川藏大道沿途所经要地。三是突出两个重点。一为分条记西藏正东、东北、正北、西北、正西、西南、正南等7个方向各地要隘及防守情况,如记正东要隘察木多,首先即记其“两河环绕,山重路窄,设桥为防,乃西藏门户”的要隘特点;一为不分条记打箭炉由粮运中路至藏站数与打箭炉由草地至西藏道路以及二者沿途地方自然、社会、民俗、桥梁、渡口、物产等,尤其详记打箭炉由粮运中路至藏沿途各地。四是与本书前面的“四川雅州府属口内土司”及“雅州府属口外新抚土司”所记比较,有关西藏各方面的记述文字均显简略,清中央政府治藏重要措施与一些重要事件以及西藏各地宗教、民俗多只是一般性提及,不作详记。作为方志,其体例与清代方志著作常见体例亦有所不同。①由于其体例与清代一般方志著作不同,何金文在《西藏志书述略》一书中将《西藏纪述》称为“纪程类著作”。《西藏志书述略》,第26页。以上这些特点,使此书有关西藏的内容既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人对此书的评价。
三、《西藏纪述》有关西藏记述的资料来源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论称:张海“自谓任川十三载,塞外几及十年,故所记具属目击,而非向壁虚构者”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3—513页。。《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与四川雅州府属口内外土司的记载一样,应有其文献资料基础,均有其依据,的确非向壁虚构,笔者赞同这一看法,这是因为著者具有多年生活在打箭炉口外及几次进入西藏的经历。但是,细读此书关于西藏的记载并作一定比对后发现,除有一定量的采自政府档册的资料及考察、体验与目睹耳闻资料之外,张海显然还利用了当时所能看到的与西藏有关的史志文献资料。换言之,乾隆前期已成书、刊印的有关西藏的著述也是《西藏纪述》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有清一代,随着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及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的增多,有关西藏的著述也不断出现。《西藏纪述》乾隆十四年以刻本问世,从目前已知情况看,此年之前有关西藏的著述已出现多种。张海具有“几及十年”生活在打箭炉口外及几次赴西藏的经历,当时有条件看到的著述及其抄本应有两类:一类是所谓西藏旅程之作,也称纪程类著作;另一类即地方志著作。西藏旅程之作在康熙末年驱准保藏后已出现,至乾隆十四年已出现的有焦应旂《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及王世睿《进藏纪程》等数种。具有方志体例的西藏地方志雍正年间亦出现。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李凤彩所纂《藏纪概》成书在雍正五年以前,为最早的私撰清代西藏方志。雍正《四川通志》开局在雍正十一年前,雍正十一年已成书,两年后又形成增补本并于乾隆元年 (1736)正式刊行。此志卷21为“西域志”,为目前已知的官方编纂的最早清代西藏地方志。此两志之后,乾隆初年又先后出现《西域全书》及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西藏志考》与《西藏志》。②《西域全书》抄本,南京图书馆藏。刘凤强《〈西域全书〉考——兼论 〈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编纂问题》 (《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认为,《西藏志考》是抄自乾隆元年 (1736)成书的《西域全书》,而乾隆《西藏志》则是在之后几年的《西域全书》修补本基础上编成的。除此之外,还有乾隆四年已刊行的《雅州府志·西域志》。《西藏纪述》乾隆十四年以刻本问世,从时间来看,上述西藏旅程之作及已成书、刊印的西藏方志在张海编纂此书时当均有条件看到。
比较之后首先发现,清代较早的西藏旅程之作中的王世睿《进藏纪程》,对《西藏纪述》在记述方式及资料选取上有着一定的影响。王世睿于雍正十年 (1732)奉檄运饷入藏,往返九月,后以其途中的见闻写成此书。此书中,王世睿采取分地记述方式,即从打箭炉起,经巴塘出川进入西藏之后,沿路记江卡、乍丫、察木多、洛龙宗、硕般多、冰坝、拉里、江达、墨竹工卡及得庆,尤其是入藏之后首记江卡,这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不同,这样的记述方式及顺序对之后编撰的《西藏纪述》显然有影响。同时,书中关于察木多“又名昌都,即头藏”等语及所记西藏各种“物产”,张海编纂时也应作了参考。③王世睿:《进藏纪程》,载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在乾隆十四年前已成书、刊印的西藏方志中,李凤彩《藏纪概》分目对拉萨及西藏物产的记述,张海编纂时也应作了参考。④李凤彩:《藏纪概》,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的“西域”概念及分地记述方式显然也对《西藏纪述》的编纂有着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张海还利用了这两志中的部分资料。如,《西藏纪述》在江卡儿、乍丫、察木多及洛隆宗等地均明确记“雍正四年清分疆界”,洛隆宗条即记:“雍正四年清分疆界,土地夷赋奏请仍给达赖喇嘛,归隶郡王颇罗鼐管辖。”此材料见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或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后者基本照录前者所记,故难区分),其洛隆宗条记为“雍正四年会勘疆界,将洛隆宗地方遵旨赏给达赖喇嘛”。尽管具体表述有些变化,但比较后仍可发现其资料出处。需要指出的是,在摘引相关资料时,《西藏纪述》还作了一定修订补充。如,记察木多戎空寺时,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有“援巴弋奚暨昌储巴居其内”语。①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志》,四库全书本;乾隆《雅州府志》卷12《西域志》,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光绪补刻本。《西藏纪述》记察木多时,记当地大喇嘛呼图克图名拔巴戈奚丹巴 (可能指帕巴拉六世,即帕巴拉·帕巴济美丹贝甲措),并非照录,显然作了一定修订与补充。
乾隆初成书的《西域全书》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西藏志考》与《西藏志》的抄本在西藏任职的张海显然有条件看到。《西藏纪述》有关“西藏”的记述与《西域全书·历代事实》《西藏志考·历代事实》及《西藏志·事迹》基本相同,说明这几种志书可能均被作为参考。比较之后的两段文字,则可判明资料具体出处:1.“西藏,土名拉撒。拉撒者,即佛地二字。旧有城郭,设九门,康熙六十年为定西将军噶尔弼、护国公策旺诺尔布所毁,东南筑石堤,长约十三里。”这一段文字与《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尤其“设九门”与“十三里”完全相同,“东南筑石堤”虽为“筑东南石堤”,但方位词“东南”亦同。《西域全书·历代事实》相关内容中有“设九门”及“筑东南石堤”“三十里”,但《西藏志·事迹》相关内容中不见“设九门”3字,“筑东南石堤”作“筑西南石堤”,“十三里”亦为“三十里”。2.“送达赖喇嘛赴藏坐床,封为成教度生达赖喇嘛,并将此方人民土地赐之,居于布达纳,振兴黄教,重袵灾黎。”这一段与《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相关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出现“封”为“赐封”,“布达纳”为“布达拉”等小改动,重要的是“成教度生达赖喇嘛”封号相同,“振兴黄教,重袵灾黎”语也一致。《西域全书·历代事实》中,封号为“成教度生达赖喇嘛”,“居于布达拉”“振兴黄教,重袵灾黎”语也有。《西藏志·事迹》相关内容中,将封号“成教度生达赖喇嘛”改作“承教度生达赖喇嘛”,“居于布达拉”有,但之后无“振兴黄教,重袵灾黎”语。②《西藏志考》抄本,国家图书馆藏;《西藏志》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以上这两段文字的比较,说明张海在所举部分中主要摘录的是《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资料,但也可能还参考了《西域全书·历代事实》。前已言及,《西藏纪述》对玉树南称等族的划分经过与管理也作了记载,之后才记“西藏”。对比《西域全书·招徕土地》《西藏志考·略笔杂叙》及《西藏志·外番》相关记述,尽管改动较大,且有一些错字,但仍可看出《西藏纪述》中玉树南称等族 (指部落)的划分经过与管理的资料应主要摘自《西域全书·招徕土地》《西藏志·外番》。理由是:《西藏志考·略笔杂叙》所记中除南城、巴卡、余树、纳克树外没有涉及其他族名,《西域全书·招徕土地》《西藏志·外番》所记则有三十九族、四十族名,《西藏纪述》的记载亦涉及了多个具体族名。再如,《西藏纪述》明确记普罗鼐 (即颇罗鼐)加封郡王,《西域全书·封爵职衔》《西藏志考·封爵职衔》中并无此记载,《西藏志·封爵》中却有这一记载。③同上。因此,可以认为乾隆初出现的《西域全书》《西藏志考》与《西藏志》等几部早期西藏方志,也是《西藏纪述》的重要资料来源。④笔者在《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的“康”及有关记载特点》(《藏学学刊》第13辑,2015年)一文中曾言,《西藏纪述》中关于西藏记载的部分材料参考了乾隆《西藏志》。这一看法是在未见《西域全书》与《西藏志考》时提出的,现在看来显然不全面。
四、结 语
通过以上梳理、比较与讨论,撰书前后张海的经历及《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载及特点、资料来源均得到较为清楚的反映。从《西藏纪述》资料来源的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到乾隆十四年以前已出现的西藏旅程之作及已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地方志已受到张海的关注,他注意到且参考、摘录、摘引了相关资料,表明康熙末年已出现的西藏旅程之作及雍正时期与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几种西藏地方志在西藏、打箭炉及口外藏地或川藏大道沿途迅速得到传抄或流传,这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张海的经历及《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载与资料来源还反映出,乾隆前期如张海这样的具有进出西藏地区及在当地任职经历的官吏对西藏地区一直有所关注,并重视收集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西藏纪述》尽管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但从记述方式、体例上讲,仍可视为一部早期的清代西藏地方志。这部清代西藏方志的出现,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治理及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增多、全国地方志编纂处于高潮的历史大背景下,乾隆前期西藏地方志也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①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发展的两个高潮》,载《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代前言),商务印书馆,2016年。
志者,记也。地方志,即记地方。方志著者关注、记述的是一定区域与地方,不过有的是对其整体性的关注与记述,有的则是对其某些方面的关注与记述。因记述内容涉及一地各方面或诸多方面,所以过去的方志给人的印象是其内容涉及一地自然、社会与历史、现状诸多方面,所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将其称为“博物之书”。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历代方志著者关注、记述的一个重点,即某区域内的族群或民族,具体记其地理、分布、人口、经济、民俗、宗教信仰及社会组织、与中原王朝关系,等等。地方志的书写方式及传统与西方传来的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及传统虽然不同,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也是通过田野调查做出来的”②赵世瑜:《反思“写文化时代”的志书写作》,载《节日研究》(第九辑) (《中国节日志》首发式纪念专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14年。,其内容与《二十四史》的记载一样,有不少宝贵的民族志资料在其中。李凤彩、张海等清代西藏地方志的著者及其方志著作也同样如此,编纂志书时除注意收集文献资料外,在西藏也不同程度地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获得相关资料,然后加以整理记入所纂志书之中,所以《藏纪概》与《西藏纪述》等西藏地方志中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民族志资料。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李凤彩所纂成书于雍正前期的《藏纪概》是清代首部私撰西藏地方志,其“卷之尾”中的“西藏种类”,即记著者在藏观察的西藏各地族群及其民俗。这方面的宝贵资料,是目前方志资料整理研究的一个重点,也值得今天的民族研究者去发掘。同时,还应指出,地方志书写方式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在各地重视新方志编纂的今天,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及传统也值得地方志某些部分编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