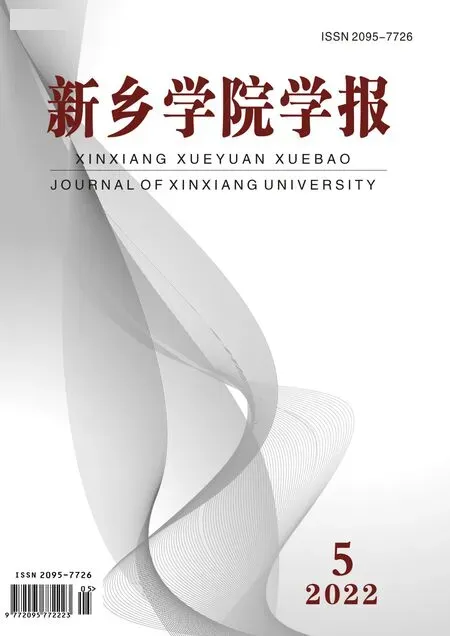“重返八十年代”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路径
赵黎波,张则天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重返八十年代”(以下简称“重返”)思潮发端于2005年,其专栏在《当代作家评论》首次开辟后,又分别在 《文艺研究》《文艺争鸣》《长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屡屡亮相,王尧、贺桂梅、蔡翔等重要学者先后参与,相关文章、著作蔚为大观,大量与20世纪80年代有关的访谈、年谱也相继出版,对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外,“重返”研究的知识谱系、所贡献的方法论也值得关注及梳理。
一、“重返八十年代”知识背景
“重返八十年代”思潮之兴起,需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话语深度转型语境中来考察。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有两套不同的主流话语体系:前者追求“启蒙”“主体性”“方法论”“本体论”等,后者在后现代理论、民族主义及殖民话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文化研究风行等影响下形成了“反本质主义”“反启蒙”“反主体”等新批判话语。 转换视角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学体制及规约的“自明性”便成了“问题”。 “重返”研究者通过阐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成规、思潮、刊物、事件等,着力解构“启蒙”“主体性”“纯文学”等概念,革新了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认知,因而,“重返”学者的知识谱系作为一种“视角”亦应被“历史化”。
谈论“重返”方法时,程光炜简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分析加后现代”,具体指“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加福柯、埃斯卡皮、佛克马和韦勒克的方法”[1]。贺桂梅谈《新“启蒙”知识档案》分析方法综合了“福柯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雷蒙德·威廉斯、 沃勒斯坦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等”[2]。 “解构”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核心话语亦在二人首批研究成果中凸显。 程光炜的 《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通过同主题文章的不同遭遇透析批评家权威力量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规约的构建, 指出“伤痕文学”附带着“文化政治”的功利动机;而他的《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则进一步解构、质疑了“伤痕”“寻根”“先锋”作品的经典性。 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从书名到其对20世纪80年代思潮知识谱系的考察彰显了福柯“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影响。 福柯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隐形渗入各大人文学院。 李陀在谈到自己知识谱系转变时,亦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福柯”[3]。 理论作为一种“现象”出现,是值得警惕的。 福柯的理论作为“重返”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背景应被“历史化”:其理论流行源于20世纪60年代工业逐渐发达的法国, 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有相似之处。它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的“相对自由”和权利的“相对弱势”。 20世纪80年代,当权力作为一种隐而不现的“话语”而非“武力”出现时,就隐含了某种意味的“自由”。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重返”学者知识谱系的重要组建成分。李扬认为“杰姆逊和福柯等人的理论对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是很有启发的”[4]。 普兰查斯从生产关系、 阶级斗争等方面指出福柯思想具有局限性,詹姆逊“历史化”等理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针对后现代理论中的历史断裂论, 詹姆逊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 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只有把它们理解成一个单一庞大而未完成的情节中的关键插曲:‘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 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5]106。 他以阿尔都塞的理论为中介,在语言学成果中重铸“总体性”历史。此外,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阐释模式或体系: 通过对它们的精神运作进行根本的历史化,从而不仅仅使分析的内容,而且使方法本身连同分析者,都被考虑在所要解释的‘文本’或现象之中”[5]171,指出“批评方法”与“分析者”也需历史化。 詹氏理论深刻地影响了“重返”学者的研究路径。 程光炜在其理论影响下,提出了“历史化”“陌生化”等方法。贺桂梅在“更长的历史范围中”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整体影响了“重返”研究的面貌。
此外,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程光炜和贺桂梅直接称自己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方法为文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二人并未照搬埃斯卡皮或曼海姆的理论方法。 程光炜更关注文学的发生与作者、 作品和大众组成的交流圈之间的隐秘社会关系。 比如他对20世纪80年代精英主义的批判。贺桂梅的研究集中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形态的批评”。
虽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背景,但“重返”研究者并非直接套用后现代理论, 而是跨学科批判吸收各种方法,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生成新研究方法。 恰如程光炜所说:“我更倾向于从文学当时发生的实际历史情况出发,而不是拿某种既定的理论方法。 自然,在收集、消化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从理论中提取一些与今天语境比较密切的成分, 然后再通过它们去重新激活问题。 ”[1]
二、个人化的“历史化”方法
“历史化”是“重返”思潮重要的研究方法。 程光炜认为不存在一种理想化的“历史化”研究方式,因为“所有研究工作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每个人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都不一样”[6]。 恰如其言,“重返”研究中的“历史化”方法也非铁板一块。
对于如何“历史化”,程光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 针对研究者难以置身于当代文学历史之外的问题,他提出了“陌生化”的方法,强调研究者主体的历史化。 “陌生化”指在研究中首先要偏离“公共经验”,即对现存文学史及其“经典谱系”、研究方法等成规产生怀疑和偏离。其次要有“自反性”,即认识自己以往被“规训”而产生的情感和意识,回到自己这代人的“历史场域”中进行研究。再次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同一历史场域的‘多重层次’中,在‘共同性’中找出‘多层次上审视差异性’”[7],同时又在“差异性”中找到“共同性”,例如把孙犁在抗战中书写人情美的问题同时放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和90年代的“文化批评”中来思考。 第二,他提出一种同情的、理解的、设身处地的批评方式,就是要对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时代政治等进行分析,“是那种不跟着作家、思潮、时尚跑的,敢于对作品文本提出质疑, 并与它展开更大空间和意义上的对话的文学批评文字”[7]。
实际操作中, 程光炜在进行历史化工作时还借助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开辟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范畴。 在《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里,程光炜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特殊社会语境、 国营出版社和书商之间竞争对杂志和作家造成的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潮三个因素,拓展出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空间,并通过个案分析展示了“文学社会学”在研究中运用的具体方法。 在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 程光炜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 “文学圈子”(编辑、批评家、作家等)与社会及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埃斯卡皮“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与集体背景这三个世界的情况”[8]理论为先导, 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扩充到了个人(个人智慧)和社会思潮(集体背景)的范围里。《“北京批评圈”与新时期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两篇文章都是以“批评圈”为视点,深层剖析了一些重要文学批评实践背后复杂的文学场域。程光炜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不限于埃斯卡皮的 “文学社会学”知识范畴,而主要体现在孔德和埃斯卡皮的两个知识层面上:“孔德抽象化地认为 ‘社会学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由此援引为我个人对当代文学史‘基本结构和关系’的历史分析;而在埃斯卡皮相对具象化的层面上,我则主张像他那样,‘文学’首先要通过‘市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众阅读的‘文化产品’,我所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即是‘抽象化’与‘具象化’能够达到相结合状态的那种研究方法。 ”[9]程光炜在《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中十分巧妙地将“抽象化”与“具象化”结合起来,用消费社会学分析了史铁生在消费年代以 “病残” 形象被批评家和书商定型的过程。 程光炜在研究中还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基础方法如田野调查法。他认为,在考证文学史料时,“不能根据作家所说而说, 文学史研究是要将其拉伸、扩展、问疑、补充,了解那里的风俗、民情、方言、古籍、疆域和人物”[10]。 此外,程光炜还注重作家年谱的整理。
程光炜认为,没有“知识化”做基础,“历史化”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在研究工作中,程光炜常借助福柯、埃斯卡皮、佛克马和韦勒克等学者的理论方法分析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例如在《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中,程光炜找出了3篇1980年左右的文献,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新时期文学”材料进行话语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这3篇材料的“陈述”都是服从于“长期以来‘极左’文艺路线‘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那种特定的语境中提出的文学主张,它们虽然是以‘拨乱反正’的姿态出现的,但其历史性格、心理逻辑和运作方式与传统的风格并无本质不同”[11]。 由此指出“新时期文学”是特定语境下产生的包含政治性的概念。 “知识化”是“重返”学者“历史化”研究的一种途径,也是理论上最重要的支撑。
贺桂梅在“重返”工作中的“历史化”,以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来重新定位和理解某个年代[12]。 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中,贺桂梅借助曼海姆 “特定意识形态”(讨论/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与 “总体意识形态”(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理论,把20世纪80年代6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即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 放在一种超越特定意识形态视野下做出历史性的分析和考察。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相较于其他研究者,王尧更关注当代文学的整体性。 “在‘断裂’中发生‘联系’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工作之一”[13]。 所以王尧的“关联研究”方法也是“历史化”工作的一个具体方法。 在《“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这篇文章中, 王尧重点分析了周扬在“十七年”、“文革” 时期以及新时期对于文学的新老观点的关联和变化, 探析当代文学制度的形成以及引起周扬话语中变化的“力量”。 之所以在“历史化”下讨论文学史“整体性”“关联性”问题,是因为“对总体的恢复是詹姆逊在语言学成果中重写历史的一个重要步骤”[14]。“历史化”的提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断裂论”。
黄平、杨庆祥在“历史化”方法层面深受程光炜的影响。 他们还运用“文本细读”“话语分析”等方法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概念做出了极其细致的梳理和探讨。 如黄平的《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系列文章通过对《哥德巴赫猜想》等文本的细读及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考释等,认为新时期文学起源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以此推断新时期文学服从以 “技术治理”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杨庆祥在 《“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中将知识分子的焦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仔细梳理、考察“主体论”提出前的一些重要意识形态,从而揭示出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性”。
三、“历史化”的阶段性发展
程光炜及其主导的学术团队自2005年始持续开展“历史化”工作。 就其发展脉络而言,自2005年至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跨度为2005—2014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固化的文学史概念进行再解读,重新阐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成规、思潮、刊物、事件以及一些作家作品。 程光炜形象地将这个阶段称为“提口号,亮招牌”。 第二阶段,即2014年以来的阶段。 这个阶段注重史料文献的考证、整理和编选。程光炜将此阶段比喻为“坐冷板凳”[15]。
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又可细分为四个时段:2005至2007年,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通过具体作品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成规”——制度、期刊、批评结论、知识立场进行反思和讨论;2008年以后,程光炜又试图从“文本细读”的视角,以文学社会学为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进行再解读, 并希望在此过程中重新寻找并确立“经典作品”及其标准;2011年, 团队工作转向对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2013年,程光炜把“重返”博士生课堂的讨论内容延伸至“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上。
第二阶段则注重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考证、整理和编选,尤为重视对当代作家研究资料——年谱、家世、地方志、文学地理等资料的整理及大型史料文献丛书的编选工作。 杨晓帆在博士论文中对路遥创作年表进行了整理, 黄平对王小波的年谱进行了初步整理。 程光炜对莫言的“家世”材料进行了整理,《莫言家世考证》 系列10篇文章也在2014年陆续见刊。 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整理了九万字的路遥文献,并对张承志、莫言、贾平凹等作家进行了专题讨论,出版了 《放宽小说的事业——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 2015年,程光炜在《小说评论》开辟“作家六题”专栏,分别对作家与故乡、批评家、编辑、读者、阅读、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 程光炜近年发表的《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六七十年代的眼睛——干校子弟忆旧文章的初步整理》等文章反映了其对作家研究资料的持续整理和关注。 在文献丛书编选工作上,团队出版了《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