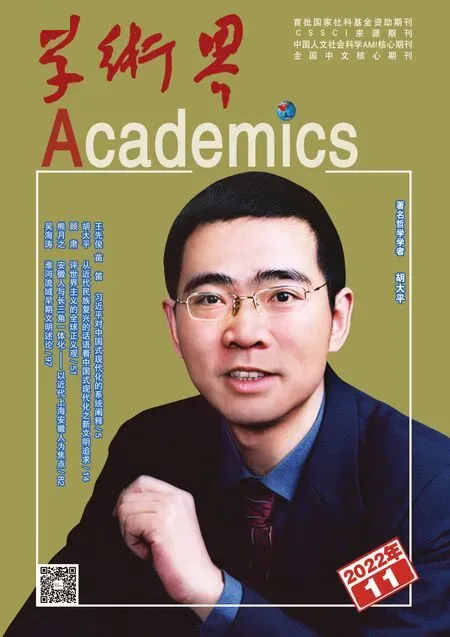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土地思想论析〔*〕
张 凯
(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梁启超为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学贯中西,穿驳古今,拥趸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此期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比如严复的译著《原富》和日、欧经济学著作,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等,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认识和看法。梁启超之《饮冰室文集》中收录了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议题,与不同派别的人围绕社会主义展开的激烈争辩。他们所辩论的主题,主要是从整个社会发展体制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为何,在欧美的落实情形有何障碍和优势,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当前和日后的中国在本质上有何落差?这些争辩虽属政治性的议题,但其中也偶有提及经济问题。现存反映梁启超土地思想的文本集中于1905—1907年梁启超围绕“土地国有”问题与孙中山之争论,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激烈交锋,梁启超前后于《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杂答某报》《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批判革命派之“土地国有论”。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梁启超经济思想中的土地思想研究都围绕这场论战,但是往往局限于“土地国有”的论点或土地制度等具体内容,如何从这场论战中较为完整地提炼、理解和评价梁启超的土地思想,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本文拟回溯历史背景,结合1906年《新民丛报》第九十、九十一、九十二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十月十五日(1906年1月1日、16日、30日)连载的《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文本,力求探析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土地思想的形成缘由和演变轨迹。
一、梁启超土地思想的生成基础
(一)思想基础
作为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梁启超不仅深谙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并且对其有着独特的理解,推动了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又遍访欧美各国,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理论,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译介过程中,他把复杂的经济学术语通俗化,并融入了对民族经济的深切关注和忧患意识。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至中国,但当时国内社会反应不一,梁启超就曾指出严复翻译的文笔过于晦涩,于是他借用严复的经济学术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通俗的语言较为全面地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尤其对“生计自由”思想甚为推崇,他认为这一思想扎根于欧洲大陆“自然理学”的哲学土壤中,并深受英国、法国同时代经济思想家的影响。所谓“生计学”,可理解为现今的经济学。此后,梁启超又开始撰写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本书集中介绍了三种西方主要的经济学派,包括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但梁启超在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经济学说史,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著作,而是结合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对这些学说加以评介,如介绍重农主义时,梁启超重点叙述了重农学派的鼻祖弗朗斯瓦·魁奈(梁译为奎士尼)的经济主张,高度评价重农主义学派“排击干涉,主张自由”的思想“实骤开斯密亚丹以后一新天地,其势力不亦伟耶!”〔1〕这部著作虽最终并未完成,但奠定了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的知识基础。
除西方古典经济学外,梁启超同样是近代中国较早了解到美国托拉斯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日本居住期间,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离日赴北美,在美国游历过程中又得以了解美国托拉斯问题。20世纪之两大“最新经济学说”梁启超均有所了解并将其介绍到了中国,《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其他介绍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章均在这一时期产生。
经济思想与历史智慧的联姻是梁启超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经济发展与政治救亡则是梁启超经济思想的主脉。〔2〕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土地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两种理论的影响,既有推崇垄断经济的一面,也有赞同社会主义的一面,后者在《杂答某报》中即有体现。但是此时梁启超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之精神”,指的是社会改良主义有关政策。〔3〕这一点则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进行了集中阐述。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这一文本形成于1905年,此前梁启超已经积累了大量西方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基础。从该文中可看出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厚学识积淀,他不仅对革命派之土地国有论的来源、理论依据颇为了解,而且引用了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与著名学派,如论及土地私有产权时,以“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亚当·斯密认为人性自私,且强调“利己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动机”。〔4〕西方主流理论经济学的核心旨向在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竭力保护私有产权,这既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也是梁启超用于反驳革命派提出的土地国有论的关键论据。此外,梁启超还在文中援引了菲立坡维治、大卫·李嘉图、亨利·佐治、理查·西奥多·伊利(即文中之“伊里氏”)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评论道:“菲氏者,现世经济学者中最以持论公平著者也”。可见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了解与推崇。
此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状况的考量也是梁启超经济思想形成的主要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加上受到在日本和欧美接触到的经济学说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他既赞成当下中国存在一些独占性质之事业,允许铁路等行业为国有,但又并不赞同完全按照社会主义政策的方式来实行彻底改革,而是主张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渐进式改良。如文中梁启超赞同摩拉氏之铁路邮电自来水等可以收为国有,可以作为国家独占事业,“既用铁路国有主义,则其线旁附属之土地,必随其路而同归国有”,〔5〕但并不赞成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梁启超曾坦言,社会主义者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而在“我国当今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6〕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构成了梁启超土地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加之其独特的“国情观”,两者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梁启超土地思想的最终内核。
(二)历史动因
198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并与孙中山等兴中会人有所联系,希望共同合作救国。在日本期间,梁与孙交往密切,大有合作之势,但梁后又听从康有为号召,1900年开始从事保皇会活动,自此双方表示分道扬镳,并在海外开始激烈争论。
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主张冲突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正面争论则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土地国有论的大辩论。双方的思想论争主要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创办的《民报》。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上刊出胡汉民撰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正式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随后,冯自由在《中国日报》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以及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继续阐发土地国有论。对此,梁启超随即在《新民丛报》第86号上发表《杂答某报》予以诘难。紧接着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又在《民报》上对梁启超的文章予以反驳。双方辩论的议题很多,与经济主题相关的主要包括两项:其一,中国日后是否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其二,是否应该采取土地国有化、实行单一土地税制。
在这次论战中,梁启超先后两次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一次为此文所讨论的1906年同革命派针对土地国有论的论战,另一次则为五四运动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时期。在这次的辩论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是三期连载长文《杂答某报》,主要讨论中国国情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梁启超依据经济学说的生产三要素理论,从土地占有、资本分割和劳动所得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西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差异,提出中国应支持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走社会主义道路。随后,《民报》刊出署名“民意”的长文——《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14号社会主义论》反驳梁启超的思想观点。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则是梁启超继《杂答某报》后的第二篇批驳革命派土地国有论的文章,属于讨论社会革命之土地革命问题,梁从财政、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来批判革命派的“简单偏狭的土地国有论”,不厌其详地列举了三十九项理由以力证土地国有制实为“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此文最后有“未完”二字,但《新民丛报》不久后就停刊,梁启超也再未就这一问题发表观点。这场大辩论由此结束。
二、梁启超土地思想的内涵要义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是梁启超少有的直接论及土地问题的文本,尽管其主要目的在于反驳革命派之土地国有论,但在言语间仍阐明了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独到见解。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私有制是“一切文明之源泉”
土地私有制是梁启超批判土地国有论的立论核心,也是与“土地国有论”最根本对立的主张观点。其一,梁启超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变的产物,“即如土地私有制度,实如历史之产物”。〔7〕虽然太古时期存在土地公有制度,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度逐渐被确立下来,是社会自然演变的结果,甚至有利于推进社会一般幸福,“而非可蔑弃者也”。其二,“土地所有权者,所有权之一种也,其性质与他之所有权无甚差异。”〔8〕而在财产所有权中,土地又属于不动产中最主要的内容。土地为“造化主之产物”,与人类制造的其他物品相同,既然人们可以保有其他物品的私有权,那么土地同样也应该属于私有,“皆以先占、劳力、节约之三者得知,而在现今之社会组织,当认为适于正义之权力者也”。〔9〕其三,“利己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之最大动机。梁启超援引河上肇之理论,提出先进社会组织下,人类的利己心是推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机,即“经济上求利益而恶不利益之念”,〔10〕这种动机是人类之性质,想要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他看来,私有制反映了当下全世界人类的普遍心理,即想要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由此才产生了各种经济行为。“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11〕如果将所有权观念去除,那么人类或许仅仅满足直接消费欲望而劳动,而不会增加更多的勤勉之心。且“积财产以贻子孙,实现今经济组织一重要之动机”。〔12〕
显然,梁启超对土地私有制的论述,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心理现状的考量,强调了“私有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土地国有论”的目的在于提前防治“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避免出现因土地集中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尽管“土地国有论”直指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土地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相比之下,梁启超对土地私有制的辩护体现了其改良派的立场主张,即反对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强调改良社会现状,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二)农业土地集中或兼并现象不具有必然性
革命派提出“土地国有论”之主要理由是欧美土地私有制下富豪垄断土地现象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会出现土地过于集中或兼并的现象。他批判革命派将全国土地一概而论的做法,认为土地大致分为“邑地”与“野地”,“邑地者,都会之地工商所辐辏也。野地者,郊鄙之地农业所利用也”。〔13〕亦可理解为城市用地和农业用地。他承认“邑地”具有独占的属性,但农业用地并不可能过于集中或被个别大地主兼并。
梁启超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农业用地应当占据较大的比例。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农业用地存在着优劣之分,但是农产品的供给并非仅仅依靠“优地”产出,因此劣地的农产品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优地的地主如果想要兼并其他土地,“势固不能,徒自丧其地代尔”。〔14〕工业或许存在利用“社会之进步而获不赀之利”〔15〕而造成“独占”的垄断局面,但是农业用地则反之。梁启超借用李嘉图之理论,提出土地生产力与劳动投入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投入过多反而有劳动报酬递减的情况,“物价趋昂,实生产费增价之结果,抵除其生产费,则不见其利润之岁进也”,〔16〕农业耕种也要受市场竞争法则的支配,因此农业用地不可能出现完全的“独占之性质”。
梁启超以世界各国土地集中状况论证土地兼并之不易,考察世界上存在土地集中现象的国家大多受封建世袭制度或传统法律影响,“尤其历史上特别之理由”,〔17〕中国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土地兼并现象,但很快因世袭制度、家族衰败等缘故“散而为数十人数百人之所有”。中国土地状况与法国类似,而法国颁布拿破仑民法典后,允许土地分割买卖自由,且废除了世袭身份制度,“我国农业上用地,绝不虑其集中过甚”。〔18〕此前在《杂答某报》中梁启超也曾提及欧洲土地兼并现象,认为土地集中并不是造成贫富分化、富人专制的原因,工业革命才是冲击传统社会秩序、造就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吞并土地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革命派形成不同观点的根源在于,他将“地主”与“农民”混为一谈,都作为“私有土地”之“所有者”。这一是抹去了历史上围绕地权问题而发生的地主兼并、侵占农民土地的史实,再则是把广大缺地、少地以及无地的贫、雇农都置于其地权主张考虑的范围之外。〔19〕尽管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农业用地的“非独占”状况时,运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加以剖析,但他据此提出地主未得“过当之利润”,“全为自身劳动所得”不免与中国近代实际情况脱节。这也是其土地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三)实行“邑地”“野地”分而治之的土地政策
“邑地”和“野地”的不同性质是梁启超阐述土地政策的重要前提。上述中梁启超认为,农业土地兼并状况并不会过甚,因而所谓实行土地国有制来解决土地兼并引致贫富差距的问题并不成立。但值得说明的是,梁启超并非完全排斥土地国有,他认为“邑地”“自由地”可以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国有或市有制度,唯有“普通有主之野地,则人们既得之所有权,国家非惟不可侵之”。〔20〕同时,“地代”的高低是影响两者兼并状况的首要因素。“地代”在梁启超的叙述中可理解为土地收益。不同于工业生产带动“邑地”价值的高速增长,“野地”的地代增长较为缓慢,加之农业产出的有限决定了地主并不能依靠勤劳耕田的报酬来实现兼并,使得“野地”与“邑地”的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应分而治之。
其一,人烟稀少、未经开垦的自由地最初可收归国有,供国人迁徙居住,且政府应“毋使桀黠者得以窃殊惠以行兼并”;〔21〕森林地、滩涂淤泥之地以及瞒报不纳税之地,皆可归诸国有。模范农场模式是梁启超所支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推崇大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认为大农业虽不免其缺点,但如果有适当的人才与资本,合理分配生产与消费资金,必定优于小农经营。对于国有之野地,梁启超也提出,可学习普鲁士之地代农场制度,将土地售卖给民众设置农村,招募贫民居住、工作,政府征收地代,并设置专门银行和监督的官员。最终除模范农场和森林地外,其余“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22〕
其二,城市用地亦可收归国有,但“其应归国有,抑应归市有”,〔23〕尚待讨论。梁启超认同邑地一般存在着独占性质,城市土地持有者往往能利用城市便利获取较多财富,独享社会的诸多特殊利益。这一部分土地可以归为国有,加之城市用地面积较小,但是地价上涨速度却较快,政府可用公债购买,最后也不至于国库亏空。另一方面,随着都市的发展繁荣带来的土地利益增长,并非该城市一己之力所得。因此,这一部分利益可以收归国有。但是,梁启超提出,都市地价增长带来的收益,市民同样应该得到报酬,从这一层面来讲,城市土地归“市有”也在情理之中。这样,城市法人团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后,不仅能改良市政、设备,推动城市发展,还能够利用地代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完善便民设施建设,促进城市日渐发达。
其三,针对国有土地经营方式,梁启超批判革命派的年期小作法,认为如果实行这一种方式,政府会在三四十年后因地价增长缓慢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无法增价。一旦将土地出租给“小作人”〔24〕后,政府将会面临破产,无法创造和提供国债收益,这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巨大的摧残。“就国民经济一方面观之,其害更有不可胜穷者。”同时,他还指出年期小作法存在明显不合理。当土地收归国有后,“小作人”会因为土地并非自己而“枯竭地力,无所爱惜”。〔25〕这种方式不仅损伤了生产主体的积极能动性,而且缺乏长远发展的稳定保障。因此,梁启超提出如果部分邑地野地悉数归为国有,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小农的切身利益和生产积极性,而且“地代非能骤进,国有之反贻国库以莫大之负担”。〔26〕
探其实质,梁启超分而治之的土地政策体现了其土地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诚然,他认同一些社会主义改良政策,在一些特定行业或可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甚至建议引入“国营农场”的方式来治理部分土地,但他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政策最终仍会归于私有,国有政策只是一种暂行的改善举措,这凸显了其土地思想中的局限性。
(四)土地国有制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反对土地国有制是梁启超土地思想的主旨论点。在他看来,私有制是一切文明之源泉,破坏私有制会妨害经济社会发展,更达不到革命派所预期的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目的。其一,土地国有制既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剥夺,也是对民众劳动产物的掠夺。如今所有权的存在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最大动力。土地国有无异于破坏经济组织的重要一角,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会扰乱社会秩序。土地国有制下的地代减少了土地所有者劳动所得的报酬,国家一旦剥夺其所有权,无异于直接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尽管政府承诺会给予其报酬,但是这种报酬的增长过于缓慢,长此以往,人们“则惟有节衣缩食,并必要之消费而亦不消费已耳”,〔27〕这是对小地主,尤其是自耕农的迫害,使其失去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二,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土地国有势必会带来财政困难、经济受阻。尽管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政策下可以奖励小农,同时倾向压抑大农,但是就实际生产力水平而言,小农远不足大农。倘若以土地国有抑制大农,长此以往“举国农业可以永绝革新进步之望也”,〔28〕而国家则成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蚕食私人企业,且不希望民间有大资本家出现,加之人地矛盾将日益紧张,则“第二次之革命,遂不可逃避矣”。〔29〕其三,土地国有违背社会发展趋势,损害小农利益和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发展,并不能起到革命派所说的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革命,这与革命派的出发点南辕北辙,“故土地制度之变革,为农业家最蒙其影响”,〔30〕工业家和商业家则几乎无关痛痒,土地国有反而对农业家最为有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行。
概言之,该时期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土地国有制展开,推及更大的背景,乃是围绕中国是否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问题展开,论战双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迥然不同。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所关怀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现状,因而其土地思想中尤其强调土地私有制对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发展是时代主题,社会革命并非当今中国所必要,仅仅依靠土地国有更不可能达到目的,甚至会危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与之相比,革命派关注的更多是社会贫富差距,侧重防范土地集中或兼并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学者指出这是一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之争,〔31〕这一评价是对双方论战作出的比较恰当的总结。
三、小 结
从梁启超经济思想史的整体上看,这一阶段梁启超从学理的高度较为系统地论证和阐明了其土地思想。戊戌政变前,梁启超撰写《说橙》,含蓄表达了变革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思想,直至与革命派土地国有论之论战才再次涉及具体的土地问题,此后较少再直接论及。
在这次论战中,梁启超对土地问题的阐发体现了其思想中的调适色彩。黄克武曾指出,在访美前后,梁启超思想有着重点的不同。访美之前,他倾向以激烈方法,彻底改造全体国民;访美之后则逐渐支持保守、渐进的调适主张,不再强调直接新民,而重视透过精英分子形成的“中等社会”,作为改革的先导,并反对滥用群众运动。〔32〕《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这篇文章以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发生于1906—1907年,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访美归来,其思想正处于从过去较为激烈破坏的主张转向保守、重视精英阶层的调适主张的时期。这种转变和重视现实的调适倾向也体现在其土地思想之中。对于中国土地的现实状况和出路问题,梁启超批判土地国有不仅会损害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且会阻碍经济发展,更多地采取一种保守、支持中等阶层发展的态度,以避免剧烈的社会革命。
梁启超的土地思想蕴含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同样也是由于其在日本和欧洲游历期间受到各种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面对中国的土地问题,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各种经济学说,另一方面又重视中国的现实状况。尽管他在学理上不反对社会主义,但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正如其所言:“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近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别为一问题;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组织,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又为一问题,此不可混也。”〔33〕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仍坚持自己对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必须存在必要前提的观点,他认可社会主义在欧洲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欧美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并非同类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是把社会主义的学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分为两个不同论域,中国要解决的是前社会主义的问题,即民族资本不发达的问题。〔34〕因而首要的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后再考虑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梁启超土地思想虽不至于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夺目”,但也构成了梁启超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了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和主张,即坚决捍卫私有制。过去学术界多批梁颂孙,认为梁启超为封建土地私有制辩护,起到了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作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反封建方面的矛盾性。〔35〕对此,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梁启超的土地主张实际上是在其社会变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相比较革命派希望推翻现有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土地国有社会,梁启超则强调现实国情,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适用这种理论。两者的初衷都是为推进社会发展,无论是革命或改良,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
梁启超土地思想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其“国情观”,强调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私有产权对于调动生产积极性、保护生产者利益具有积极作用。农民作为土地改革的直接影响者,任何涉及土地领域的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都会对其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因而必须要谨慎处置。有学者评价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并不是说他的经济思想有悖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的常理,也不是说他发现了某种经济规律或重新创立了某种经济学说。他的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主要表现为用当时国人还相对陌生的西方经济学“公例”来诊断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直面抨击政府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导入中国救亡的新思路。〔36〕革命党人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并不深入,且接受亨利·乔治土地国有思想的时间不长,理论尚未成熟,而梁启超却紧扣中国实际国情,考虑到了当时社会和农民群体的现实状况,这相比于革命派的理论是更为成熟的。
注释:
〔1〕〔2〕〔3〕〔34〕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4、163、361页。
〔4〕李学桃:《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190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5〕〔6〕〔7〕〔8〕〔9〕〔10〕〔11〕〔12〕〔13〕〔14〕〔15〕〔16〕〔17〕〔18〕〔20〕〔21〕〔22〕〔23〕〔25〕〔26〕〔27〕〔28〕〔29〕〔30〕〔33〕《梁启超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1、228、162、162、162、162、162、167、164、165、165、165、166、167、169、170、171、169、173、172、183、179、199、191、83页。
〔19〕〔31〕李学桃、彭廷洪:《经济公平与经济发展之争:1905-1907年土地国有论战再研究——以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地权思想为中心》,《理论月刊》2018年第2期。
〔24〕梁启超在文中解释:“小作者,谓赁地而耕也,日本名词。”小作人意为租地耕作者。
〔32〕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35〕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2页。
〔36〕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