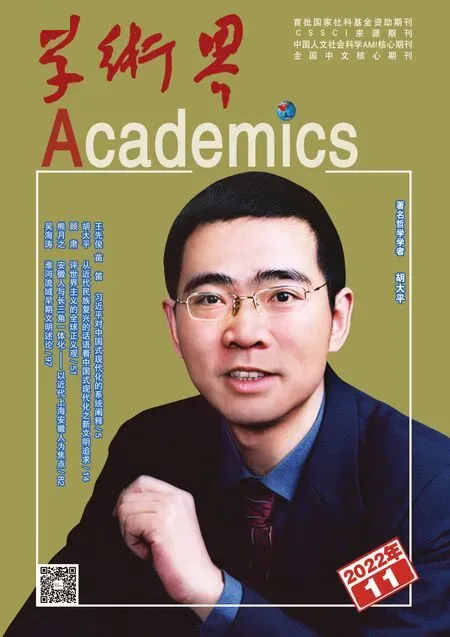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的思想立场、形成因素与价值分析〔*〕
魏凤云, 于 伟
(1.长春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2.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彼得·劳伦斯·麦克拉伦(Peter Lawrence McLaren,1948—)(以下简称麦克拉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代表人物,美国批判教育学的主要奠基者、实践者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批判教育学的重要倡导者。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形式是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的主旨。麦克拉伦对合理化存在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教育私有化与市场化,加剧人的物化与异化和阶级复制的标准化考试,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麦克拉伦认为他所倡导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一种致力于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式的实践哲学,因为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目标就是废除阶级,建立新社会。2020年4月13日麦克拉伦教授与王雁博士在《中国日报》官网上发文《美国需要脱离谴责中国的轨道》(US needs to move away from its blame-China trajectory)力挺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贡献和努力,谴责美国在抗疫上的不作为以及将责任推脱给中国的“甩锅”行为。〔1〕2020年麦克拉伦教授与王雁博士在《教育研究》第4期发文《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未来》,〔2〕重申其通过批判教育学实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立场。本文的研究是建立于对麦克拉伦教授本人及其亲友、同事进行大量访谈及查阅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和未刊手稿的基础上的。〔3〕
一、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
除了认同学校再制不平等和不公正之外,当代的批判理论家在许多分析的观点上其实各持己见。当前批判传统的论述大约可以分成两派:一派人相信可以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改革资本主义,如亨利·吉鲁(Henry Giroux)、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Apple)等,一派人认为只有废除阶级社会,实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取得社会公平,如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葆拉·奥尔曼(Paula Allman)、迈克·科尔(Mike Cole)、柯里·马洛特(Curry Malott)、格兰·瑞科沃斯基(Glenn Rikowski)、戴维·希尔(Dave Hill)、安东尼娅·达德尔(Antonia Darder)、理查德·布劳斯(Richard Brosio)和拉明·法拉曼德普尔(Ramin Farahmandpur)等。〔4〕无论是哪一派都希望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挖掘出教育过程中的反抗因素,进而实现人的解放。换句话说,这些批判理论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赋予无权力者以权力,以改变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5〕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麦克拉伦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他对教育的关怀最终仍是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自由与解放为中心。因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的自主活动才能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6〕麦克拉伦对社会革命和解放实践持有高度的期望,他指出:“作为我的中心理论和政治立场……我绝对不会放弃、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也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建构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工程的方法。”〔7〕但是麦克拉伦并非从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经过了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麦克拉伦学术立场转变的轨迹
麦克拉伦和亨利·吉鲁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并肩作战。他们都深受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致力于文化政治学部分的研究,提出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引领批判教育学向文化政治转向的立场,当时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初,麦克拉伦和吉鲁先后离开迈阿密大学。麦克拉伦转至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往更激进的路线——他不再把自己归为后现代主义者,而是常常把自己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classic Marxist)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Marxist humanist)。
麦克拉伦的学术轨迹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984年到1994年,1994年至今。〔8〕“可以说我曾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直到1994年。从1994年左右我开始认真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对我的作品的批判,例如戴维·希尔(Dave Hill)、格兰·瑞科沃斯基(Glenn Rikowski)、迈克·科尔(Mike Cole),他们都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他们在欣赏我的作品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我的作品。我在正视和研究他们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比我的论述更有力、更深刻。于是我决定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著,重新定位我的政治立场,然后也加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阵营。”〔9〕麦克拉伦从未放松过对社会主义整体观点的关注,由于对差异和代表性政治问题的兴趣,他与后现代左派进行了谨慎的批判性接触,并逐渐认同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左翼后现代主义的私有化领域代表着一个社会死胡同。沉浸在洛杉矶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他开始阅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如科尔、希尔(Cole & Hill),并开始熟悉莱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的作品。〔10〕在一次交流中,麦克拉伦提到:“我一开始是自发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最初被诸如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拉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达拉·科斯塔(Mariorosa Dalla Costa)、弗朗索瓦·贝拉尔迪(Francois Beradi)这些重要的思想家的作品所吸引,虽然我并没有在我教育学的作品中明确地引用他们的作品。后来我又开始关注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著作,如马斯(Mas’ud Zavarzadeh)、特蕾莎修女艾伯特(Teresa Ebert)的作品,然后我开始对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莱雅·杜娜叶夫斯卡娅,当然还有英国教育家葆拉·奥尔曼、戴维·希尔、迈克·科尔和格兰·瑞科沃斯基等人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作品感兴趣。”〔11〕王雁指出:麦克拉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从他进入学术界那一刻开始的,他个人的理论重点和立足点的变迁,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学习、跨学科、不断自我否定的学者形象,同时他作为批判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拓展和发展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尤其是引领批判教育学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12〕
(二)从后现代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缘由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3〕麦克拉伦认为后现代主义尊重差异,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阶级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如果没有消除阶级的不平等,所有的差异也得不到尊重,无法解决阶级宰制的问题。〔14〕这促使他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从关心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取向,转向关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取向。
麦克拉伦认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主义”的强烈批评,已经剥夺了教育理论和批判教育学的所有革命潜力。对宏大叙事和普遍性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概念和分析被边缘化,而转向了认同和表现的政治。后现代主义从阶级斗争的问题中退出,默认了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必然性。后现代主义以“异己的文化表现”取代阶级形成,在面对新帝国主义时,它“急于在教育越轨的舞台上摆出一种新颖的姿态”,却没有为阶级斗争的开放空间提供教学处方,这包含了在资本的逻辑和必然性下所有潜在的教育变革。〔15〕麦克拉伦认为,从理论上讲,后现代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其隐含的假设,即“文化”已经从经济力量中赢得了独立。这种假设就使得它无法厘清经济分配问题和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麦克拉伦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丰富情感来关怀当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便会认识到种种压迫者与受压迫者的冲突皆是阶级斗争的变形,因而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内在的矛盾最终会走向灭亡,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平等自由的新社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冲突论、劳动论、异化论等思想,对麦克拉伦的批判教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马克思对劳动和实践的重视,使得麦克拉伦认识到人是主动地通过实践来改变世界,从而不断地追求与实现梦想。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麦克拉伦“始终站在反对资本主义滥用的立场上,支持解放政治”。〔16〕“在游历各国,尤其是拉美各国时我看到了太多的普通人民的挣扎,结识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教师、工会成员、艺术家、社会活动者等,所有这些人和事都在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有多么需要马克思。事实上,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需要马克思了。”〔17〕
(三)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鉴于后现代潮流的多元论述已被资本主义渗透与利用,以及考虑到重视多元差异与族群认同的激进民主的主张将使得差异性团结被分化,反而失去了使弱势者团结的主体能动性,并将被资本主义用为分化弱势族群的策略,也使批判教育学沦为空谈,而失去了解放的可能性,麦克拉伦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对公共教育的影响,应该在后现代思潮下急迫地发展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以避免全球化资本主义对教育的破坏性影响。他呼吁,批判教育学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采用历史唯物论的分析角度,关注阶级压迫以及生活实践层面的探讨,并将他的批判教育学思想正名为“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只有如此,教育工作者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教育实践,发展出具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模式。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超越后现代主义对文化差异的强调,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体系依靠剥削运作的压迫本质。因为,平行层面的文化差异原本并不会造成压迫或歧视,文化的差异结合垂直的阶级压迫,才是导致压迫的最根本原因。麦克拉伦认为,当我们忽略了结构性的分析,我们也同时失去了主体能动性。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麦克拉伦以恰切的方式打开了批判教育学的新视角,他剖析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关注资本主义下的弱势群体,再通过不断的辩证与反思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在。麦克拉伦致力于把学校发展成学生可以开始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替代形式(如社会主义)的地方。尽管美国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呼吁在更“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体制下重新分配经济资源,但麦克拉伦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18〕麦克拉伦对于学校、教育及社会的辩证分析方法使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以下四种概念:(1)科学(描述资本主义如何运行);(2)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害影响);(3)愿景(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乌托邦假象);(4)战略(从这儿到那儿,“应该做什么”)。如B·奥尔曼(B.Ollman)所提出的那样,大多数对于马克思的解释者都只强调这些主题中的一个或几个,但是在麦克拉伦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里,尤其是在他的著作《学校生活》中,他阐释了这些元素的每一项是如何地影响其他各项,并为其他各项作出贡献的。〔19〕
二、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形成因素
学者的认知方式除了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习惯,还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关系模式:他接触了什么人,与什么人交流和学术碰撞了,引发了什么思考等。〔20〕可以说,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基于麦克拉伦长期的各地实际考察研究、理论探索的积累,还基于他个人所在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这一系列理念反映了他的成长背景与经历及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体认。
(一)内在因素
1.自身的经历与他人的影响
父亲的被迫过早退休并过早离世,前往美国反对越战的经历,对简·芬奇走廊(Jane-Finch Corridor)的孩子及他们家庭境况与遭遇的目睹,〔21〕让麦克拉伦切身感受到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社会阶级再制、教育资源不均等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摧残。麦克拉伦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人及身边的人就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
从一个小学教师到一个大学教授,麦克拉伦深深感到了培养学生批判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批判教育学必须从校园舞台跨入社会舞台的必要性。由于一直身在教育领域,麦克拉伦有机会遇见、结识批判教育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亨利·吉鲁、葆拉·奥尔曼等。这些人的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麦克拉伦,使其批判教育学思想不断发展。另外,多次深入拉美地区讲学、参与抗争游行等都强化了他进一步发展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决心。
2.勤奋钻研的精神
天才出于勤奋。麦克拉伦独树一帜的批判教育学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更非一日之功。他自小就博览群书吸收各家思想,十几岁的时候就读了各种关于哲学、政治学的名家作品,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几十年来书不离手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使很多信息和书籍可直接在网上获取,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电脑不离手成为了麦克拉伦的另一个生活习惯,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睡觉,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与写作,包括吃饭的时候他都经常一边看电脑里的资料一边进餐,他每天除了阅读专业领域的资料还会把美国的各大主要新闻媒体的网站都浏览一遍,〔22〕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里经常能够看到当今世界发生的大事或各种政策措施的最新数据和资讯作为论证他观点的材料。几十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百科全书。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麦克拉伦并没有拘泥于书上的信息或迷信书本,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并且批判地吸收或借鉴各种信息,然后加工、整理他所吸纳的各种信息,形成自己的思想落于笔端。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惊人的,自从业以来他的作品层出不穷,平均每年出1—2本书,文章几十篇。在课程设置、教育政策、教育和文化运动等领域,他撰写编辑了50多部著作,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数百篇有关批判教育学的文章,主题涉及诸如反战运动、多族裔劳工斗争、土著和新殖民主义解放运动、争取环境正义的斗争、国际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和学生行动主义等方面。可以说,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他每天都在写作。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让他取得著作等身的成就,也让他在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批判教育学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
3.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麦克拉伦自从教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领域。尽管他经常被其他学者批判,尽管他甚至被自己的学生指责上课无趣、内容空洞,尽管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威胁,尽管他被诋毁为“肮脏三十”(Dirty Thirty)之首,〔23〕尽管他在UCLA被右派排挤提前离职,麦克拉伦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将批判教育学深植于校园的理念。他一直心系莘莘学子与劳动阶级,不顾自己的名誉与安危痛斥和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
以他目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他是不属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的,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但是麦克拉伦非但没有维护资本主义的虚伪面具,反倒竭力拆穿资本的糖衣,甚而希望打倒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麦克拉伦目前的学术成就,他可以不用再如此辛苦地写作,但是他表示,人能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很少,如果他的作品和思想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哪怕作出一点点的贡献他就要一直以笔为戎,与资本主义抗争到生命的尽头。以麦克拉伦目前的学术地位,他去某些机构随随便便作一场讲座或演讲都能让他获得颇丰的收入,但是他却对不符合或违背他思想立场的讲学邀请一直持拒绝态度,哪怕收入丰厚。相反,他却经常去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地不计任何报酬地去给当地的学生、教师或工人团体等讲学,因为他觉得这些地方才更需要他,才更值得去,在这样的地方讲学或演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麦克拉伦从未离开过他的讲台,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身影。对于教育的热情与执着,是他即使有时身体状况欠佳却依然继续奔走各地,继续在发光发热的主要原因。麦克拉伦知道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功夫,而学生更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唯有将批判的种子播于学生的心田里,将来才有可能长成大树,进而开花结果。正是麦克拉伦对教育的强烈使命感使得他一直在无私地付出与奉献。
(二)外在因素
1.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严重负面后果
资本主义借着全球化的背景及主要主张,合理化其生产关系的压榨与压迫性质,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阶级壁垒更加牢不可破;资本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蔓延至全球。在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下,市场的自由经济导致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教育竟成为市场自由化、经济不平等扩张的帮手。全球化不但无法确保政治安定与社会经济平等,反而加剧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差距。当代资本主义也通过海外经济、文化殖民的扩张来巩固财团私有的利益,实质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侵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表面上是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正是为此类新帝国主义的文化与经济侵略服务的。在这种形势下亟需一种基于大众斗争的批判教育学,寻求一种社会替代方案,以取代将数字经济与全球警察国家相结合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议程。对麦克拉伦而言,马克思是其心中可以清晰洞视资本主义意图的老师,也启发了他对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看法,进而逐步提出了他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一种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式的实践哲学。
2.以往批判教育学的被驯化
麦克拉伦认为美国资产阶级总有各种诱惑的方式合并任何它打不败或改变不了的东西。他认为批判教育学已经变成了它原初思想的讽刺漫画,它原本的思想是为了更公平的社会而斗争,为没有权利的人赋权增能,为了解放而斗争,而现在已经被驯化、消减为“学生主导的学习方法”,避免讨论或重新思考“社会批判和革命日程”。
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以及对立,促使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须要创造出可以替代资本家资本积累的逻辑,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毕竟这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不平等的社会。因此,对于“衰弱的以及受到驯化的批判教育学,有必要发展所谓的革命的劳动阶级的教育学”。〔24〕麦克拉伦强调,这也是为何他坚持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针对社会不公平尤其是呈现在学校体制当中的非正义进行强烈批判的原因。他所要澄清的是,对于财富的分配不是易如反掌的,而是要去挖掘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并且进行讨论,进而去创造一个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使劳动阶级能够发展其自身的价值。〔25〕因此在以往的批判教育学被驯化、失去作用、幻灭的时候,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出现了。
三、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价值
(一)是多角度、动态审视资本主义教育本质的利器
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本质,质疑了对任何民主社会都至关重要的、被太多的教育家所长期回避的资本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威胁公共教育生存的各种力量的本质,与威胁民主生存的根源相同。人们还意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威胁到美国,而且威胁到全世界和整个地球的安全。麦克拉伦将批判教育学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有效武器,他的理论基础几经更迭,越发激进。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到后现代主义,最终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螺旋上升的转变过程意味着麦克拉伦并不是为了独树一帜而偏执于某一个学派或是理论,而是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麦克拉伦以他所处时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理论支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以往的激进教育理论进行了选择与吸收,将他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一系列观点和思想进行融合与交锋,以独特的视角对教育、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分析,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站在教育之外省察教育,又时刻不忘回归教育,这使他敏锐地把握了教育与相关学科理论以及社会之间互动的真实现状。在麦克拉伦的研究生涯中,他拒绝偏执与独断,尊重多元与差异,他不仅借鉴了欧洲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诸多学者的知识传统,也借鉴了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如巴西等国学者的理论观点,使其思想呈现出丰富的知识结构。作为一位富有责任感与献身精神且具有敏锐政治视角的杰出知识分子,麦克拉伦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行动经验,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作出了颇具综合性的分析。莱昂纳多(Leonardo)指出麦克拉伦受到了许多优秀人物和思想传统的影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象征人类学、种族和民族理论、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批判民族志和批判媒体研究等。〔26〕埃尔亚曼(Eryaman)指出,麦克拉伦的作品植根于丰富而深刻的文献中,他借鉴了保罗·弗莱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切·格瓦拉(Che Guevara)、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莱雅·杜娜叶夫斯卡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黑格尔(G.W.F.Hegel)、约翰·杜威(John Dewey)、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激进进步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家的观点。〔27〕这一系列的影响给了他“阅读文字和世界”的视角,并让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保持批判性的推理。
虽然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左派学者都被引人注目的后现代理论吸引住,麦克拉伦还是努力走出迷雾,很有勇气地从自己的作品中以及其他批判教育理论家的作品中撤回,开始拿起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武器直截了当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视线障碍和美国的民主教育实践,回归到了最根本、最中心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阶级构成是如何继续建构和保护美国学校和社会顽固的不平等的。安东尼娅·达德尔这样评价麦克拉伦:他因炽热而勇猛的作品以及他深刻抓住资本主义问题而在这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各地批判教育者的话语中成为重要转折的标志。〔28〕编汇过麦克拉伦文章评论的学者路易斯·M·韦尔塔·查尔斯(Luis M.Huerta-Charles)认为“麦克拉伦是一位反思性行动的思想开放的学者。因为他会倾听不同的见解、关注不同的替代方案并考虑自己的基本理念会是错误的可能性。我也相信麦克拉伦在他的行动中也是负责的、诚实的,因为他敢于定期地检视、评价这些行动并相信他可以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对我来说,他就是这种道德崇高的知识分子。”〔29〕
麦克拉伦的理论和学识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一直在不断探索建构理解、解释世界的理论。麦克拉伦不是一个静态的个体,因为处于静态会让他认为世界理所当然就该如此,就像在说这个世界是不能被改变的,是必然如此的。路易斯·M·韦尔塔·查尔斯认为,“由于麦克拉伦一直注意自己的设想与自己的致力于社会平等、建设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理论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他从批判理论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分析架构。现在,我们又看到他从批判教育学——一个他帮助建构的理论——转向了他所称之为的‘革命教育学’(pedagogy of revolution),由此,我说他是知行合一的。因为,在他一直寻找不会破坏他的理论的新视角的过程中,同时他一直生活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中。”〔30〕
(二)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超越课堂的教育学
麦克拉伦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中出现频率最高、也最代表他批判教育学思想核心观点的词汇之一是“praxis”,翻译成汉语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当于知行合一。麦克拉伦多年来一直践行他所倡导的这一理论,坚持知行合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麦克拉伦笔耕不辍地出版专著、发表文章宣扬其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31〕他在世界各地讲课,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积极践行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我的大部分旅程都与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和政治路线有关。旅行和会见社会活动人士远比我自己反思的时候给我带来更多的勇气和政治敏锐性。与那些在激烈的斗争中塑造了自己人生的人见面——有些人是知名人士,有些人则是所谓的‘无名小卒’——让我停下来思考,因为单凭书本,你能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呢?”〔32〕
麦克拉伦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发表演讲,常常受到热烈欢迎,部分是由于他的人道主义激进情怀,部分是由于他的深情和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始终保持警觉的性格。自1987年以来,麦克拉伦受邀到大约30个国家,〔33〕向学者、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作主题演讲或为当地大学生作系列讲座,并在许多情况下与听众结成积极的联盟。在他作为客座教授的写作和旅行经历中,他游历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每一个大陆。麦克拉伦的革命性思维与集体社会专业知识的建立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在他的公共事务中,他以激进的成人和大众教育的精神发展了一种革命性的公民参与理论。他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受众范围,而且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政治形成的新高度。在他洛杉矶的家乡机构里,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他与他的合作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政治家、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政治煽动者和普通人一起进行了许多研讨和对话。许多活动都是由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基金会赞助的。〔34〕麦克拉伦还与委内瑞拉的学者建立了联系,这些学者认可他的工作,并重视他对批判教育学的贡献。应他们的邀请,麦克拉伦前往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国内其他地方,向学者和教师发表了一系列演讲。2006年,麦克拉伦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Bolivarian University of Venezuela)成为客座教授。在多次访问拉丁美洲期间,麦克拉伦会见了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等重要人物,并为南北美洲之间的思想和实践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众多纸上谈兵的学者不同,麦克拉伦一直处在践行批判教育学理论的最前线。
他用自己的行动宣扬自己的理念,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落实革命实践的精神。路易斯·M·韦尔塔·查尔斯认为麦克拉伦是言行一致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学者,他按照他的理论生活。〔35〕国际教育学学者乔·金奇洛(Joe.L.Kincheloe)指出,简单地曝光不为人所见的东西,说出不可言说的事件是一回事,作为批判理论家,麦克拉伦把这种行动还推向了实践领域,他将他的思想表达与社会和教育行动结合起来。拥有如此行动能力的头脑在本质上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点燃了黑暗岁月的希望之光,在阴暗的学校地狱里点燃了可能之光”。〔36〕教育者仅仅关注课堂是狭隘的、悲哀的,麦克拉伦超越了很多教育界人士对于教育理想实现方式的想象。理论的发展永无止境,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新的现实,都要继续理论探索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仅仅依靠对前人理论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麦克拉伦正是这样做的。麦克拉伦努力从坐而论道的理论家成为起而行之的实践家,姑且不论其成功与否,但他致力于教育学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之精神,值得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梦想是必须通过行动得以实现的。这也正是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最终精神之所在。
四、结 语
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既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又植根于鲜活的教育实践之中,不过,他的教育乌托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美国社会和教育的种种现实。麦克拉伦提出了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其目的就是对抗资本主义,所以他批判的对象涉及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面向。麦克拉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已经在全球化、商品化的趋势潮流下,将人对人的本质与尊严的自我意识吞噬殆尽;压迫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资本主义体系剥削性质的运作方式。
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承认阶级、种族和性别间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是极为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家们接受了市场经济而未能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他们茫然的眼神中,社会发展已经迷失了它的方向和可能性;他们的社会策略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在立场上滑向了与新右派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意识形态相似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消费主义。〔37〕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追求他们的目的的具体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38〕迈克尔·阿普尔与亨利·吉鲁的批判理论虽然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是立场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倡改革资本主义,麦克拉伦虽然赞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念,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立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竭力主张以其他形式如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但是以这三巨头为代表的北美批判教育理论思想家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那就是他们都深化了教育的目标,使其不止于标准化的读和写;他们丰富了教育的价值取向,使其脱离了狭隘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他们都在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未来,思考并承担着教育的使命和责任。
对麦克拉伦而言,著书立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发展出真正能够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的学说、理论才是他的追求。有人说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太“激进”(radical)。尽管“激进”(radical)一词常常带有偏见性的贬义,然而《牛津英语词典》对radical的定义还有:“根本的;基本的;彻底的;完全的;激烈的”。〔39〕或许,对于那些认为麦克拉伦的理论太“激进”的人,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意思是,麦克拉伦太接近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仅仅在外围提出问题,不追问问题的核心有什么意义?如果对问题本质的接近,需要激进的思想,那么激进又何妨?
注释:
〔1〕Peter McLaren,Yan Wang,“US needs to move away from its blame-China trajectory”,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04/13/WS5e941a99a3105d50a3d15d91.html,2020-04-13.
〔2〕〔美〕彼得·麦克拉伦、王雁:《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未来》,《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3〕笔者自从2014年至今,一共对麦克拉伦教授作了60次访谈,累计访谈时长约150个小时,整理访谈资料约30万字,获取了麦克拉伦的思想动态和诠释其作品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正式访谈的形式,随着笔者与麦克拉伦的关系逐步密切,在日常接触中还产生了许多非正式的访谈。同时,笔者与麦克拉伦教授也通过邮件往来访谈一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间,麦克拉伦一直与笔者分享他的最新的思想动态与研究重点以及对以往研究问题的反思。当笔者遇到问题与困惑时,他随时以电子邮件或面谈的方式予以解答和帮助。笔者总计收到麦克拉伦教授152封邮件回复。在交往的过程中,麦克拉伦帮助笔者为所研究的部分问题作了文献筛选和文献推荐,并给予了建议、意见和指正。因此本文不是单一地从书面到书面的解读和诠释,而且是在长期与被研究者面对面交往,观察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并与之多次对教育、人生、政治、社会等话题进行深度交流探讨之后,融入了笔者对被研究者的感性情感和理性反思的一份研究。麦克拉伦本人曾多次提醒笔者不要受到与他私人关系的影响,鼓励笔者该批判就批判,该否定就否定。所以笔者深知需要谨慎地处理科学研究与私人感情的关系,一直把与麦克拉伦个人的接触当作一种对于科学研究的补充,以维护研究的客观性。
〔4〕〔5〕〔36〕Peter McLaren,Life in Schools: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Boulder:Paradigm,2014,pp.128,122,xi.
〔6〕〔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551页。
〔7〕〔美〕彼得·麦克拉伦:《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萧昭君、陈巨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393-394页。
〔8〕〔12〕王雁:《美国批判教育学者麦克拉伦的学术生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8页。
〔9〕〔17〕〔美〕彼得·麦克拉伦、于伟:《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访谈录》,《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10〕〔26〕〔28〕〔29〕〔30〕〔35〕Marc Pruyn and Luis M.Huerta-Charles,Teaching Peter McLaren:Path of Dissent,New York:Peter Lang Publications,2005,pp.xvii-xxxix,43,xvi,xxviii,xxvi,xxvi.
〔11〕来自笔者于2018年5月6日在麦克拉伦教授家中对其的访谈。
〔14〕Peter McLaren,Rage and Hope,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6.
〔15〕〔24〕Peter McLaren and Ramin Farahmandpur,Teaching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A Critical Pedagogy,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5,pp.17,137.
〔16〕Peter McLaren,Life in Schools: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Boulder:Paradigm,2003,p.3.
〔18〕Peter McLaren,Red Seminars:Radical Excursions into Educational Theory,Cultural Politics,and Pedagogy,Hampton Press,Inc.2005.
〔19〕Ollman B.,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
〔20〕丁元竹:《费孝通先生写作〈乡土中国〉的前前后后》,《人民政协报》2020年7月20日。
〔21〕简·芬奇走廊(Jane-Finch Corridor)是一个多种族的、多语言的、高密度的多伦多近郊贫民区,麦克拉伦从1975年到1980年在那里的小学教书,并基于期间的教学经历于1980年出版他的第一本日记体专著——《来自走廊地区的呐喊》(Cries from the Corridor)。
〔22〕笔者自2014年与麦克拉伦教授结识以来,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担任其在中国讲学的翻译和助教,并于2017年8月到2019年9月在麦克拉伦教授所在的查普曼大学访学,期间与麦克拉伦教授及其妻子朝夕相处,笔者得以有机会对麦克拉伦教授进行深度观察与访谈。
〔23〕2006年,一个自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友团体”(UCLA Bruin Alumni Association)的组织,在网上公布了一份名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危险的30名教授”的黑名单,麦克拉伦的名字位居榜首。此团体目的是通过将被认为“不爱国”的教授列入黑名单,将左派赶出大学。
〔25〕Michael Pozo,“Towards a Critical Revolutionary Pedagogy,”inRage and Hope:An Interview with Peter McLaren,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p.15.
〔27〕Eryaman,Mustafa Yunus,“Editorial Statement (English):Understanding Critical Pedagogy and Peter McLaren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Vol.2,No.3,2006,p.6.
〔31〕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22年,他出版了45本书和数百篇学术文章和章节,为一百多本书撰写了序言、刊后语、介绍、结束语、编后记,这些文章和章节被翻译成土耳其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汉语、韩语、波兰语、俄语、希腊语、德语等等20多种语言,他的作品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土耳其、希腊、中国、波兰、匈牙利、德国、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巴勒斯坦、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国家都受到对批判教育学感兴趣的人们的关注。
〔32〕Derek R.Ford.,“Revolutionary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Capital Today:An Interview with Peter McLaren”,http://www.hamptoninstitution.org/peter-mclaren-interview.html#.XT6gsi2B3FQ.
〔33〕从麦克拉伦教授提供给笔者的简历中统计而出。这些国家包括:瑞典、澳洲、南非、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以色列、英国、德国、韩国、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其中许多国家他多次访问,有些国家他定期访问,例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34〕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基金会是一个由一群墨西哥的教授和教育活动家发起和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这个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推进一些目标,包括在墨西哥和美洲培养和发展革命批判教育学,开展行动研究项目,组织会议,建立批判教育学中心,建立公共论坛,进行辩论、讨论和政治活动。该基金会目前正在用西班牙语出版一本名为Aula Critica的杂志,并计划出版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版本。
〔37〕〔38〕Junrui Chang,Changyong Yang,“Book Review:McLaren,Peter & Farahmandpur,Ramin (2005),Teaching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A Critical Pedagogy,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Vol.2,No.3,2006,p.132.
〔39〕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牛津英语词典(第四版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24页。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
——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