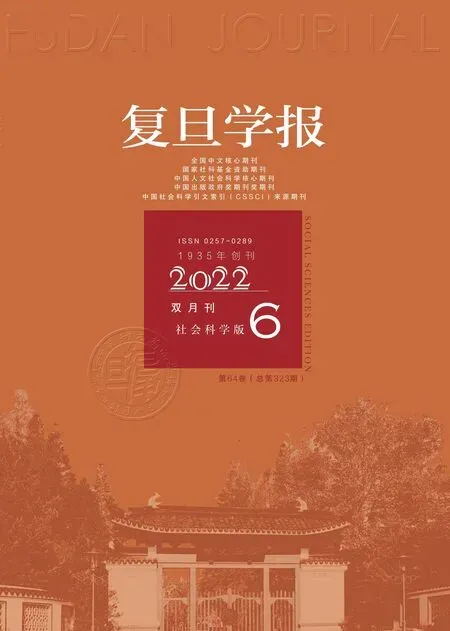审美感兴的价值论观照
张 晶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一、 小 引
在中国美学中,“感兴”无疑是最为基本的创作论范畴。文学艺术创作缘何而起?“触物兴情”是根本的动因。宋人李仲蒙所说的“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1)见[宋]胡寅:《致李叔易》,《斐然集》卷十八,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58页。笔者以为是“感兴”最为精准的界定。“感兴”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关于创作的核心范畴,它不仅关涉着文艺创作的发生,而且包含着艺术媒介的内在化运思、构形及艺术表现。“感兴”包含了“感物”,而又不止于感物,因其蕴含着主体的审美创造心理机制。感兴是文学家、艺术家进入审美创造的“枢机”,引发着审美创造主体的惊奇之感,从而开启了作品创作的过程。正如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所说:“中国美学史上所说的‘感兴’,其实就是指诗人的惊异之感。‘感者,动人心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心有所感而抒发于外,就成为艺术,其中也包括诗。”(2)张世英:《哲学导论》,见《张世英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这就寓示着“感兴”对艺术创作的整体开启作用。
感兴有着非常典型的价值论意义,尤以审美价值的创造为其实质。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表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统一状态,这种统一是符合主体需要和内在尺度的。离开了主客体关系,就谈不到价值的存在。而审美价值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的根本价值形态,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对审美价值有这样的表述:“审美价值,如上所述,则表现对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对人在世界中的确证的综合意义。这种综合意义的体现者是感性感知可以接受的、对象独特的完整形式。”(3)[苏]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9页。审美价值的创造,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与艺术创作密不可分的。艺术创作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审美价值的创造。艺术品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价值,如认识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但这些价值如果不是通过审美价值得以体现的话,那就不成其为艺术品。在审美价值产生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究竟是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在感兴中又是如何形成创造性的动力系统的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二、 感兴不同于审美移情,而是主客体双方的互相契合
有人将感兴与我们所理解的审美移情相类比,认为中国的感兴论与西方美学的移情说有相同的审美心理机制。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就是将唐代孔颖达对兴的阐释类比于移情理论的。(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598页。但笔者以为,二者之间虽然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主客体之间的彼此契入,从而产生独特的审美体验;然而,西方的“移情”说,是明确地意识到对象是无意识、无性情的自然物,而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对象中去,由于对象的某种感性形式引发了主体的情感,主体将这种情感投注到对象身上,使之似乎有了类似于主体的类种情感,从而引起了审美快感。移情说的代表人物里普斯就说:“审美欣赏的‘对象’是一个问题,审美欣赏的原因却另是一个问题。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当然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但也当然不是审美欣赏的原因。毋宁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5)[德]里普斯著,朱光潜译:《论移情作用》,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3、45页。西方的“移情”说,与其说是主客体双方的“一体化”,毋宁视为客体的主体化,或者说主体意识的外射。里普斯这样的论述更接近于移情说的实质:“这一切都包含在移情作用的概念里,组成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移情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存在。”(6)[德]里普斯著,朱光潜译:《论移情作用》,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3、45页。“移情”使对象打上了主体的烙印,强化主体与客体分立的色彩。
中国的“感兴”论却是植根在“天人合一”的广泛世界观土壤之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哲学及一般意识形态中是普遍性的存在,并使人们对自然事物持一种亲近的、友爱的态度。先秦儒家如孔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名言,表现出孔子以自然山水为友而生的情怀。孟子提出了“仁民爱物”的仁学命题。“仁民”是对人的同情与友爱;爱物,则是爱护人以外的动物植物等自然事物。宋代思想家张载将“天人合一”这一最具中国哲学特色的基本观念铭刻在了中国思想史上,并进而提出了“民胞物与”的重要命题。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则以“万物一体”来作为仁学的基本内涵,他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程颢所谓“仁”,就是以万物为自己的一部分。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更为系统地阐明了他关于人与万物一体的观念,他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8)[明]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仁者之心,不惟与人相通,而且也通于鸟兽,通于草木,通于瓦石。人与任何东西,皆因其为一体而彼此相通。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主体—客体”结构和“人—世界”结构,前者以西方哲学为主流,后者以传统的中国哲学为典型。后者的特点之一便是人与天地万物的相通相融。如张世英先生所说:“人不仅仅作为认识(知)的存在物,而且作为有情、有意、有本能、有下意识等等在内的存在物而与世界万物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9)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万物一体”的观念的另一面,则是万物有灵。在很多诗人或艺术家的眼里,山水、草木等自然物都是有灵性的。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宗炳,同时也是一个佛学思想家,他在其佛学论文《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从“形尽神不灭”的佛教哲学思想出发,认为山水自然也是有灵的。他说:“今请远取诸物,然后取诸身。夫五岳四渎,谓无灵也,则未可断矣。若许其神,则岳唯积土之多,渎唯积水而已矣。得一之灵,何生水土之粗哉?而感托岩流,肃成一体,设使山崩川竭,必不与水土俱亡矣。”(10)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0页。而作为画论家,宗炳的画论名作《画山水序》中提出了“应会感神”等命题,也是基于“山水有灵”的观念的。他说:“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一图矣。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诚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11)[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见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5页。都是基于人与山水之间的灵性互通,方能应会感神。南北朝时期的文论或作品,在涉及触物感兴的物我关系时,也是以自然物的有情、有灵、 有感为基础的。在这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是最为典型的。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时序变迁,使那些微虫丹鸟、一草一木之类,都欣然应感,因为它们都是有情之物。故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物色》篇的赞语更是写出了诗人与自然之物的互通互答,其言:“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3、695页。唐代王昌龄有《诗格》,中有“十七势”,其中第九势为“感兴”势:“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亦有其例。如常建诗云: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又王维《哭殷四诗》云:“泱漭寒郊外,萧条闻哭声。愁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13)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56页。所谓“应说”,所谓“感会”,都是人与自然物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色万象,都是可以与诗人感会的。宗白华先生谈及这种情况:“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14)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这也是普遍的感兴创作的情形。
感兴是以主体与客体相触遇——具体地说,就是诗人或艺术家与外在物色在偶然遇合中兴发创作冲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在这个偶然的触遇中唤起了诗人或艺术的审美情感,并产生创作冲动。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所说的“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15)[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01页。将兴的这种性质概括无遗!“感兴”是审美创造过程中的高峰状态,物与我交融为一,在特定的时刻,主体与客体无法分开。审美价值从中油然而生。价值论学者李德顺先生认为,“‘美’,是这样一种境界:客体的存在和属性满足了主体身心的一种特殊需要——‘美感’的需要,它是客体某些方面达到了与主体的高度统一和和谐。‘美感’需要不仅是一种精神的、观念的需要,作为人的一种感性状态,本身包含了人的感觉、理智和生理、物质状态的统一。当一片美景使人心旷神怡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阳光和煦、空气清新、音响悦耳、温度适宜、压力适中等因素同色彩、气味、形状等给人的影响有统一的效果。而这些效果的产生,不能不同主体本身此时的精神、心理、身体状态和社会生活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因此,‘美’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价值,就像享受一顿美味、欣赏一场精彩表演、观赏一幅名画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抽象思维过程一样。‘美’的境界,是主体运用内在尺度在观念上和物质上同化、改造客体的成果。”(16)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5页。审美价值既有同一般性的价值的共同属性,也有属于审美活动的特殊属性。应该说,李德顺对“审美价值”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笔者认为,审美享受是本质性的审美价值形态。审美享受是融合了身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内涵与形式等多种维度的综合性体验。我们在本文中所探讨的是文艺作品给审美主体带来的审美享受,或者说所产生的审美价值。感兴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发契机,是可以给创作主体以生机勃勃的动力源和生命感的。这种原生性的动力,并非只是在艺术发生阶段,而且是贯穿于创作的整个过程的。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杰出作品,是从一开始到整体的艺术表现,都充满了艺术家的饱满的生命体验的。著名现象学美学家盖格尔在论述艺术的审美价值时指出:“艺术那生机勃勃的效果并不是从外部附加上去的;它充满了艺术的深层效果,使得它生机勃勃、丰满充实、完美无瑕。因此,完美的艺术作品不仅对于富于精神性和理智性的人具有吸引力,而且它还对人和生命的统一具有吸引力。它使生命的力量和人格的活力充分运动起来。”(17)[德]莫里茨·盖格尔著,艾彦译:《艺术的意味》,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在中国的文艺感兴论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生命的活力。感兴是主体与客体的偶然触遇,在这种偶然触遇中,主体受到外物的触发而获得不可重复的审美经验,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由此而进入创作的过程。如刘勰在谈到登山观海时所伴随而生的审美创造冲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18)《文心雕龙·神思》,见《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4页。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概括了这种由感兴而生成创作冲动的“自然”过程,“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9)《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5、693页。尤为生动而真切地揭示了感兴时给主体带来的审美体验,“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0)《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5、693页。明代诗论家谢榛对诗歌创作特别重视感兴的根本性动力,他说:“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21)[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见《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2、1161页。谢榛还以“天机”作为感兴的概念,称赞那些美妙的诗句。“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属对精确,工非一朝,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22)[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见《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2、1161页。明代文学家徐渭通过竹枝词的由来谈到感兴对作者来说的审美体验,说:“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不知夫子以为何如?”(23)[明]徐渭:《奉师季先生书》,见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在艺术创作中,感兴的创作方式带来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高度契合。在这种契合中,审美价值得以产生出来。这种契合又是自由的、不经意的,也就是偶然的,惟其如此,才能产生巅峰状态的审美价值。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篇,描述创作中的“契”:“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24)《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4页。刘勰主张在放松心意的状态下,方能呈现出“含章司契”的理想境界。“含章司契”本义就是秉含自然之美而把握枢机之契合。“含章”语出于《周易》。《易·坤卦》云:“含章可贞。”王弼解释道:“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而发,含美而可正也,故曰‘含章可贞’也。”(25)[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含章”就包含着形式美感在内。《彖》辞有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周易正义》阐发说:“章,美也。既居阴极,能自降退,不为事始,唯内含章之道,待命而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贞’。”(26)《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含章”与美的关系,早在《周易正义》那个时代就已经很清楚了。关于“司契”的出处,《老子》第七十九章中云:“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徹。”陈鼓应先生的解释是:“‘契’即券契,就像现在的所谓的‘合同’。古时候,刻木为契,剖分左右,各人存执一半,以求日后相合符信。”(2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说明了契的本义及来源。刘勰所说的“司契”,是指文学创作中意——物——言三者的高度契合。《神思》赞语中再度谈到“契”的理想状态,“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这里也是以神思、物象和语言的高度契合为“制胜”的关键。
三、 感兴作为审美价值的创造机制
审美价值的产生是创造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主体也是创造的主体。从文艺创作来说,所谓创造,一是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或云独一无二,二是价值的新鲜感,三是作品的经典意义。正如价值论学者黄凯锋所指出的:“审美创造是人类主要的创造活动之一,它可以遍及人类生活实践的一切领域。凡是通过主体创造性活动在对象身上体现人的自由生命的都可以称之为审美创造,而真正给审美创造赋予本质意义的是艺术生产中主体的创造活动,因为艺术本身的出现就是审美具有独立意义以后的事。”(28)黄凯锋:《价值论视野中的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62页。笔者对此表示明确的赞同之意,并认为在审美创造这个问题上,艺术生产是首当其冲的。其他类型的审美活动,当然不能排除创造的成分在里面,但它们一般来说是附加的,而非主要的。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的论述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的艺术的高度。”(29)[苏]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是的,在艺术作品中的其他价值都是要通过审美价值来得到体现,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艺术品。我们也可以由此认为,艺术创作就是以审美价值的创造为其基本目的,如果不能给人们以审美享受,不能获得审美价值,它也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
感兴的直接产物就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品的产生,离开了这个前提,感兴是不存在或没意义的。感兴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审美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谈这个话题还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感兴并非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仅是存在于创作的初始阶段,也即艺术创作的冲动发生阶段,而是贯穿在作品创作的全过程的。感兴在刘勰这里,不仅是在“神思”的发动时,而且直接通往艺术的表现过程。如其在《文心雕龙·体性》篇开篇时所说的“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30)《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05、493页。“情动”是作家的情感发动阶段,但同时刘勰就联系到了“言形”,也就是语言表现、形成作品结构。隐和显,内与外,是一体化的。《神思》似乎应该是专论构思的,但他更为明确地把运思过程与表现过程作为一体化的过程,“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1)《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05、493页。作家在意象内窥时就已经“寻声律而定墨”了。宋代画论家董逌以“天机”论画,本质上就是感兴的审美创造方式。如其评论燕肃的创作时所说:“山水在于位置,其于远近阔狭,工者增减,在其天机。务得收敛众景,发之图素。惟不失自然,使气象全得,无笔墨辙迹,然后尽其妙。故前人谓画无真山活水,岂此意也哉?燕钟穆以画自嬉,而山水尤妙于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笔,登临探索,遇物兴怀。胸中磊落,自成丘壑。至于意好已传,然后发之。或自形象求之,皆尽所见,不有措思虑于其间。”(32)[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五,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97、290页。评价著名画家李伯时(龙眠)的绘画成就时也说:“伯时于画,天得也。常以笔墨为游戏,不立寸度,放情荡意,遇物则画,初不计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则无毫发遗恨。此殆进技乎道,而天机自张者耶?”(33)[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五,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97、290页。董逌论画都是以“天机”即感兴为主要的创作方式的,却从未停止于构思阶段,而是指作品的完美产生。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认为诗的发性就在于触感而兴,但同时就是一个措词达意的写作过程,他说:“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34)[清]叶燮:《内篇(上)》,《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见有所触而兴起其意,则能给人以惊奇的审美感受,成为杰出的作品,而无所触的陈陈相因,则令人倦怠,甚至“掩鼻而过”。值得注意的是,叶燮在谈感兴而作时,是直接措诸辞属为句成其章的完整过程相联系的,并非止于构思阶段。
如果仅是停步于构思阶段,或者说仅是存在意象层面,则是不可能有作品的完成与传世的。这是一个常识,却在美学史上有过一场争议。西方的著名哲学家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表现”,认为在作家的内在世界,呈现为直觉的意象,即可视为艺术的完成了。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其他美学家的批评。如英国美学家鲍山葵明确指出的那样:“在这里,我不由得觉得,我们只好遗憾地和克罗齐分手了。他对一条基本真理非常执着(他时常就是这种情形),以至于好像不能懂得,要领会这条真理还有什么是绝对少不了的。他认为,美为心灵而设,而且是在心灵之内。一个物质的东西,如果没有被感受到,被感觉到,就不能百分之百地算是具有美。但是我不由得觉得,他自始至终都忘掉,虽则情感是体现媒介所少不了的,然而体现的媒介也是情感所少不了的。”(35)[英]鲍山葵著,周煦良译:《美学三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4、33页。鲍山葵非常明确地反对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观点,而特别重视艺术媒介的功能。如果以为艺术作品仅有情感就可以了,那是并不客观也并不正确的观念。所谓艺术创造,如果没有完整的、物化的成果,只能是子虚乌有。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艺术品的“物性”有这样的论述,他说:“一切艺术品都有这种物的特性。如果它们没有这种物的特性将如何呢?或许我们会反对这种十分粗俗和肤浅的观点。托运处或者是博物馆的清洁女工,可能会按这种艺术品的观念来行事。但是,我们却必须把艺术品看作是人们体验和欣赏的东西。但是,极为自愿的审美体验也不能克服艺术品的这种物的特性。建筑品中有石质的东西,木刻中有木质的东西,绘画中有色彩,语言作品中有言说,音乐作品中有声响。艺术品中,物的因素如此牢固地现身,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说,建筑艺术存在于石头中,木刻存在于木头中,绘画存在于色彩中,语言作品存在于言说中,音乐作品存在于音响中。”(36)[德]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3页。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艺术品的物性,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这位大哲学家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其实,这正是针对克罗齐的那种“直觉即表现”的观点所提出的,而且,艺术品的这种物性,恰恰是艺术创造的前提,也是审美价值生成的前提。如何没有这种物化的存在,欣赏者作为审美主体,也就无从产生审美经验。审美是无法面对虚无的观念化的东西的。
文学创作作为艺术创作之一类,它的媒介是语言文字,我们或许会认为,语言文字是精神性的存在,它又有没有物性呢?文学的媒介不同于如色彩、木头等具体的物质,但也是有着物质性的。鲍山葵的论述在这个问题上提醒了我们,他说:“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有一个物质的或者至少一个感觉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声音。可是这是有意义的声音,它把通过一个直接图案的形式表现的那些因素,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再现的那些因素,在它里面密不可分地联合起来,完全就像雕刻和绘画同时并在同一想象境界里处理形式图案和有意义形状一样。语言是一件物质事实,有其自身的性质和质地;这一点我们从比较不同语言,并观察不同图案,如沙弗体或六音句,在不同语言如希腊或拉丁中所具的形式,会很容易看出来。用不同的语言写诗,如用法语和德语写诗,和用铁与用泥塑造装饰性作品,同样是不同的手艺。声音的节拍和意义是一首诗里面的同样不可分的产物,就如同一缍画里面的颜色、形式和体现的情感是不可分的产物一样。”(37)[英]鲍山葵著,周煦良译:《美学三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4、33页。鲍氏的论述,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所用的媒介是文字,但却是以此勾勒出内在的视觉形象,笔者也称其为“内在视像”。一件文学作品,是以文字创造出意境、人物或故事,这种内在的视像是完整的,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和审美愉悦的。也许是诗词的意境,也许是人物的命运,也许是故事的曲折,但它们都是完整的,也给人以完整的审美经验。
感兴并不止于创作的发生阶段,也是作品产生的直接基础。感兴又是非同寻常的创造,而非一般性或者拾人余唾的东西。例子就是宋代诗论家叶梦得从谢灵运诗的个案所得到的结论,他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38)[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见何文焕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6页。谢灵运在《登池上楼》中这两句作为经典名句,并非诗人刻意为之,而是“猝然与景相遇”的产物。人们多从“奇”的角度评价此诗,其实乃是诗人感兴所得。正因如此,诗中的情景与意绪也非“常情”所及,具有创造性的审美价值。叶氏并非仅仅将它作为个案,而是使之升华到普遍性的高度,认为其是诗歌创作的根本所在。谢灵运《登池上楼》的诗境,给人以独特的审美空间感以及扑面而来的春之气息。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评价的那样:“始终五转折,融成一片,天与造之,神与运之。呜呼,不可知已!‘池塘生春草’,且从上下前后左右看取,风日云物,气序怀抱,无不显者,较‘蝴蝶飞南园’之仅为透脱语,尤广远而微至。”(39)[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见《船山全书》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732页。这种因感兴而致的独特诗境,似乎与宇宙造化的气息连通为一,呈现的是超越于形似的自然之美。叶梦得又谈道:“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而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于手,筠亦未能尽也。然作诗审到此地,岂复更有余事。韩退之《赠张籍》云:‘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司空图记戴叔伦语云:‘诗人之词, 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学者不能味其言耳。”(40)[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见何文焕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5页。叶梦得所推崇的诗歌之美,是如同“初日芙渠”般的自然之妙,也是一种浑然无迹的新鲜意境。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本为江西诗派中人,但后来独辟蹊径,自成大家,其诗境新奇独特,有天工自然之美。他认为最好的诗歌创作方式就是“兴”,也即我们说的“感兴”。他说:“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焉感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41)[宋]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见刘方喜主编:《中华古文论释林·南宋金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感兴方式其实是以诗人或艺术家自身的人格修养、艺术天赋、知识积累和创作能力为前提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 驯致以怿辞。”(42)《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632、633页。刘勰认为作家的主体条件,须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这样四个方面,也就是知识储备、参酌义理、加深阅历和语言训练这四大因素。然而,文学艺术创作必以艺术品的完成为其标志,作品能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是其审美价值的尺度。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观念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神”即是作品的令人震撼的审美效应。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一篇,是就作品中“隐”和“秀”两个角度的审美价值而言的,其中说:“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43)《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632、633页。“隐”与“秀”是统一于作品的篇章之中的,也是在刘勰看来的最具创造性的审美价值。“隐”是指作品中的多重意蕴,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秀”则是作品中的亮点,成为作品的灵魂。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秀句”往往成为经典,在文学史乃至审美意识史上成为辉耀千年的明珠。刘勰认为,“秀”并非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感兴的产物,所谓“思合而自逢”,他说:“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怨,盖以此也。”(44)《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632、633页。秀句的产生,是作家与外物“思合而自逢”,而非研虑之所求,也即那种雕琢之作。而它如同自然绚美之花,辉耀文苑。《隐秀》篇的赞语,则尤为生动而又高度概括地写出了“隐秀”的那种令人惊奇的审美效果,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尤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诗论家钟嵘在其诗学名著《诗品》中提出了“诗之至”的价值标准。“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45)[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李壮鹰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释林·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8页。“味之者无极”是说诗歌篇什创造出了多层次的审美意味。宋代诗论家严羽认为李杜之诗达到“极致”之境,具有无法替代的审美价值,他称之为“入神”:“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46)[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177页。严羽还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来形容李杜诗歌的美感形态,其言:“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47)[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177页。明人彭辂揭开这这样一个“秘密”,即诗的“神”绝大多数是由感兴而生发出来的,他说:“盖诗之所以为诗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视初、盛,远矣;初、盛之视晋、宋,有间矣,晋宋之视魏,祖与孙矣;魏之视汉,父与子也。不同言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夫神者何物也?天壤之间,色、声、香、味偶与我触,而吾意适有所会,辄矢口肆笔而泄之,此所谓六义之兴,而经纬于赋、比之间者也。赋实而兴虚,比有凭而兴无据,不离字句而神存乎其间,神之在兴者十九,在赋者半之。此《国风》、《小雅》不传之秘,而灵均之《骚》所独濡染而淋漓者也。”(48)[明]彭辂:《诗集篇大序》,见徐中玉主编:《意境·典型·比兴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欣赏名篇佳什,令人产生的是非常丰富、极为广远的审美感受,而且不是那种陈陈相因的东西。那种以文字描绘出的“如在目前”的内在画面感,其实是作品意境的实质所在。唐代诗论家司空图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盖诗文所以足贵者,贵其善写情状;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诗文题目所在,四者凑合,情状不同,移步换形,中有真意。文人笔端有口,能就现前真景,抒写成篇,即是绝妙好词,所患词不达意耳。”(49)[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见《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49页。以诗文的语言文字,描绘“情状”,创造出使人们读之产生内在的画面,而此过程是可以令人产生独特的审美愉悦。这也就是钟嵘所说的“味之者无极”。宋代诗人梅尧臣曾经谈到这样的诗歌审美标准:“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50)[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见《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将难写之景以语言文字的媒介描绘出“如在目前”的内在视像,这也是文学所应有的审美效应。这类作品的创作始因,多是出于感兴的创作方式。 审美需要是一种新鲜的、独特的需要,它天然地排斥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腐经验。而艺术的感兴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新鲜的审美经验。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艺术则不仅有不同的目的,还有一个不同的对象。如果我们说,两个画家在画‘相同的’景色,那就是在非常不适当地描述我们的审美经验。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假定的相同性完全是由错觉产生的。我们不能把完全相同的东西说成是两个艺术家的题材。因为艺术家并不描绘或复写某一经验对象——一片有着小丘和高山、小溪和河流的景色。他所给予我们的是这景色的独特的转瞬即逝的面貌。他想表达事物的气氛,光影的波动。一种景色在曙光中,在中午,在雨天或在晴天,都不是‘相同的’。我们的审美知觉比起我们的普通感官知觉来更为多样化并且属于一个更为复杂的层次。在感官知觉中,我们总是满足于认识我们周围事物的一些共同不变的特征。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地丰富。它孕育着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性。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成了现实性:它们被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最强的魅力之一。”(51)[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以此来看感兴方式所创造的艺术品的独特性价值,是非常契合的。
以感兴作画,在山水画中也是创造出不可重复的艺术佳作的最佳方式。董逌在论山水画大家范宽的山水画时就说:“观中立画,如齐王嗜及鸡跖,必千百而后足,虽不足者,犹若有跖,其嗜者专也,故物无得移之,当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于心者,必发于外。则解衣磅礴,正与山林泉石相遇。虽贲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揽须弥尽于一芥,气振而有余,无复山之相矣。彼含墨咀毫,受揖入趋者,可执工而随其后耶?世人不识真山而求画者,叠石累土,以自诧也。岂知心放于造化炉锤者,遇物得之,此其为真画者也。”(52)[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六,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307页。在董逌看来,一流的山水画师的杰作,都是在这种遇物则画的感兴方式中画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心放于造化炉锤”,与造化自然融为一炉,因而成为画中的极品。明代画家沈周也主张山水画应出于感兴,他说:“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53)[明]沈周:《书画汇考》,见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711页。创造性的佳作,往往是画家与对象之间在特定情景中的相触相遇,在内心中呈现了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丘壑”。其实,这个道理无论是文学中还是绘画中都是适用的。清代画家盛大士于此指出:“画家惟眼前好景不可错过,盖旧人稿本皆是板法,惟自然之景,活泼泼地。故昔人登山临水每于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临远眺,于空阔处看云彩,古人所谓天开图画者是已。夫作诗者必藉佳山水,而已被前人说去,则后人无取赘说。若夫林峦之浓澹浅深,烟云之灭没变幻,有诗不能传而独传于画者,且倏忽隐现,并无人先摹藁子,而惟我遇之,遂为独得之秘,岂可觌面而失之乎?”(54)[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图》,见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独得之秘”并非来源于前人旧稿,而是在于画家与当前好景的相遇。“惟我遇之”,画家的主体情怀与特定情景的触遇,方能有创造性的画作的诞生。
感兴之所以能产生创造性的艺术品,同时也带来令人惊奇的审美愉悦感,就在于主体的情怀与外物的触遇, 并非是预定的,而是随机的,如叶梦得所说的“故非常情所能到”。由此而产生的作品,往往是超越于以往的认知,而呈现出一片独特的审美观感。
四、 感兴与审美价值的形式因素
审美价值中的形式因素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审美客体之所以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形式上的美感。因此,感兴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偶然触遇,使客体的自然形式与主体的内在艺术形式感在特定情景下的契合与提炼,造就了作品的独特形式美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成就之一,便是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与动物对世界的感知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名言,是与对象的形式美感与人的感官的审美机能相联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55)[德]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斯托洛维奇谈到的自然形式和规律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论断,对我们认识感兴与形式的审美创造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他说:“这类实验工作表明,甚至自然的形式和规律之所以能对人起情感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天生就有审美属性,而是由于同人的感知规律的某种‘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感官适应了对现象中不断重复的、合乎规律的关系的感知。因而毫不奇怪,在对合乎规律的关系作感性感知时,感官最正常地发挥机能,它们的活动甚至使我们产生生理愉快。”(56)[苏]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3、67页。斯氏颇为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自然形式的规律何以能对人起情感作用,这也是艺术家在以自然物象作为对象,并将其改造为审美意象后审美价值的来源。 美的规律其实就是人的创造性的规律,以自然物象为对象形成审美意象,艺术家在其中体现了创造性的劳动与天才。斯托洛维奇还指出:“某种端正、对称、节奏、适宜在自然的对象中、甚至在不直接进入劳动过程的对象中的表现,仿佛向人‘用信号报告’他的创造力,唤起一种‘审美反射’。”(57)[苏]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3、67页。这在中国文艺理论的感兴方式中可以得到印证。《文心雕龙·诠赋》篇在论述赋的创作时,即以感兴为创作的开端,所谓“登高之旨,睹物兴情”,继而所说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杂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58)《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6页。这种形式美感,是与前面的感兴一脉相承的。《物色》篇中所说的“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更为直接地道出了诗人由感物(其实即是感兴)而同时进入形式创造的过程。台湾学者郑毓瑜教授对《物色》篇的这段话分析说:“刘勰总是同时提举两个面向,其一,‘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这牵涉心与物;其二‘写气图貌’‘属采附声’与‘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则关涉言与意、词与物的层次。”(59)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页。北美著名学者王德威先生在为郑著作序时更是专门阐发了“引譬连类”作为“兴”义与辞章情采的关系,他说:“郑教授指出‘引譬连类’的渊源来自中国诗学的‘比兴’正宗:西汉孔安国即将‘兴’释为‘引譬连类’。邢昺疏曰:‘诗可以令人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而为我们所熟悉的解释出自《文心雕龙》(下略,即上引语),刘勰认为诗与物相互感动,不仅带来心身体气的交流汇聚,更与万象形成宛转应和的关联。而诗人出入感物连类的体系,发情采为辞章,自然占有关键位置。”(60)王德威:《序 诗与物》,见《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页。在诗词中,辞章之构写当然属于形式创造。
并非仅仅是辞章之美就可以视为形式创造的,作品中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内在结构,更为形式创造的基本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情采”所指正是文采焕然的整体结构,其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61)《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37页。这里所谓“立文”,并非仅指文章,而是指文采之美、形式之美。很明显,“形文”是指绘画、书法之类的艺术,“声文”指音乐,“情文”指诗赋文章。无论是“五色”而成的“黼黻”、“五音”而成的“韶夏”,还是“五情”而成的“辞章”,都远非作为作品元素的色彩、音符和词语,而是具有完整结构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发于内心、生于情感的。《情采》篇的赞语所说:“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62)《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6页。“心术”也就是作家的情感是要通过形式加以表现的,优美的文章由此而生。“英华”并非个别的词语,而是有机的整体性作品。卡西尔认为审美享受是来源于作品的形式的,他说:“如果艺术是享受的话,它不是对事物的享受,而是对形式的享受。喜爱形式是完全不同于喜爱事物或感性印象的。形式不可能只是被印到我们的心灵上,我们必须创造它们才能感受它们的美。”(63)[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在如何认识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问题上,笔者是认同卡西尔的观念的。形式媒介对于激发美感是必要的。形式的创造意味着审美情感的产生,是将内在的情感冲动,建构为可以感知的形式。萨缪尔·亚力山大认为,这种形式构造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他说:“ 审美情感是与审美冲动相应的情感,它包含了众多融为一体的要素,并与冲动本身中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其中有支配性的要素,即作为创造之乐的纯粹的建构性;也有构成性的即综合或构造的要素;还有对材料的感官愉悦。这在诗歌中是作为声音的语词和它们所传达的意象所带来的纯粹愉悦(但这不恰当地称为美),同时也在结构的愉悦之上增加了节奏和韵律的愉悦。”(64)[英]萨缪尔·亚力山大著,韩东辉、张振明译:《艺术、价值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2页。萨缪尔所说的“纯粹愉悦”,正是典型的价值,也是审美价值产生的标志。其所指并非纯粹的形式,却恰恰揭示了形式创造给创作主体带来的快感。形式的审美价值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形式创造,并非没有内涵,而是通过艺术媒介与自然冲动的情感及表现的事物密切联系在一起。 此处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艺术媒介的问题,本书的另一章会专门论述感兴与媒介的关系,但本文所涉及的观点,是需要有逻辑性的说明的。艺术作品是一种物性的存在,否则就是一句空话而已。人类艺术史或文明史上的经典之作,也都有赖于作品本身的物性本质。海德格尔所说的“物”,在艺术品中很多人都会理解为物质材料,因为艺术媒介是必须以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现在的问题是,物质材料本身就是媒介吗?黑格尔是将媒介直接视同于材料的。他在谈及艺术分类时说:“在这方面头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这个:艺术作品既然要出现在感性实在里,它就获得了为感觉而存在的定性,所以这些感觉以艺术作品所借以对象化的而且与这些感觉相对应的物质材料或媒介的定性就必然提供各门艺术分类的标准。”(65)[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页。当然,黑格尔也并非就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只是感性材料的作用,他主张:“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因此,黑格尔接下来又有这样的名言:“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66)[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黑格尔尚未对艺术媒介作出明确的界定。当代美国哲学家奥尔德里奇则明确表示:“即使是基本的艺术材料(器具)也不是艺术的媒介。弦、颜料或石料,即使在被工匠为了艺术家的使用而准备好以后,也还不是艺术的媒介。”(67)[美]奥尔德里奇著,程孟辉译:《艺术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5、56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艺术媒介”?奥氏有较为清楚的解释,他认为:“艺术家首先是领悟每种材料要素——颜色、声音、结构——的特质,然后使这些材料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合成的调子(composite tonality)。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成形的媒介,艺术家用这种媒介向领悟展示作品的内容。 严格地说,艺术家没有制作媒介,而只是用媒介或者说用基本材料要素的调子的特质来创作,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这些特质就是艺术家的媒介。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就要考虑这些特质,直到将它们组合成某种样式(Pattern),某种把握住了他想要向领悟性视觉展示的东西(内容)的样式,艺术家用这些特质来创作,而不是对这些特质来进行加工。艺术家通过对基本材料的加工,用这些材料的特质来进行创作,后者就是艺术家的媒介。”(68)[美]奥尔德里奇著,程孟辉译:《艺术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5、56页。奥氏所说的媒介,是一种以特质材料为要素的“调子”,也就是一种展现为物性的结构。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曾对艺术媒介作过这样的概括性说明:“艺术媒介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料,将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69)张晶:《艺术媒介论》,见《美学与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7页。媒介当然是离不开物质要素的,但又并非止于物质要素,而是以物质为载体的一种独特的结构。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这种媒介建构中产生的价值,对于创作性的审美主体而言,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对于欣赏性的审美主体而言,同样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关于前者,英国美学家鲍山葵这样描述:“因为这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我们刚才看到,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的媒介的特殊能力。这种愉快和能力感并不仅仅在他实际进行操作时才有的。他的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的能力里;他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特殊灵魂。”(70)[英]鲍山葵著,周煦良译:《美学三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1页。媒介直接关乎于形式的建构,在鲍山葵看来,是一个艺术家在感受世界、创造想象时就已经开始的,而这从感兴阶段就已是活跃着的了。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特殊的愉快”,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审美价值。克莱夫·贝尔的著名艺术理论命题“有意味的形式”,更为明确地回答了后者,那就是欣赏性的审美主体在形式的感受中所生成的审美价值由何而来。贝尔说:“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71)[英]克莱夫·贝尔著,薛华译:《艺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页。在美学史或艺术理论史上,“有意味的形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里所论述的,也就是对于欣赏性审美主体而言的审美价值。“激发情感”“打动人”,是艺术家所创造的形式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社会美和自然美的审美中,是缺少这一种类型的审美感受的。因此贝尔指出:“可以肯定,我们中多数的人在自然美中的所感受到的东西,一般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审美情感。”(72)[英]克莱夫·贝尔著,薛华译:《艺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贝尔所指的是绘画等视觉艺术,但他所提出的这个命题,却是关乎艺术的普遍性本质的。诗歌也是如此。诗歌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也同样是通过形式的感知所获得的。刘勰在其《知音》篇中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73)《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15页。是说欣赏与创作的反向过程。“披文入情”是通过作品的文采形式而感受到作品的审美情感的。“感兴”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范畴,起点无疑是在发生阶段,也即作家和艺术家受外在事物(包括社会事物、自然事物)的触发,而产生创作冲动,所谓“触物以起兴”,但它并非仅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也包括了艺术形式的建构。这是因为,艺术媒介的功能不仅是在作品的外在表现阶段,而是作家和艺术家感知外界事物、产生审美冲动时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刘勰所说的“寻声律而定墨”,就是在创作的内在运思阶段。明代诗论家徐祯卿颇为中肯地描述了这种机制,他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而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而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74)[明]徐祯卿:《谈艺录》,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5页。颇为完整地揭示了从感兴开始到形式建构的过程。
感兴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基本创作论范畴,也是代表着中国美学特色的创作论思想。它不仅需要外界事物的触发与刺激,更需要审美创造主体的天赋与深厚修养。它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但却并非无端而至的空穴来风。感兴的过程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性能量,用中国艺术的术语来说就是“天机”。感兴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作家和艺术家的激情,却又是包含着形式建构的审美情感。在感兴中,一切都被激活了,作家和艺术家的创造能量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因而,在感兴的创作方式下,往往产生难以重复的艺术杰作,甚至成为千古不灭的经典。对于创作性的审美主体来说,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欣赏性的审美主体来说,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审美情境之中,获得最美的审美享受。用明代谢榛的话来说,就是“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75)[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2页。从价值论的意义上来看感兴,可以使我们有更为独特的收获,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