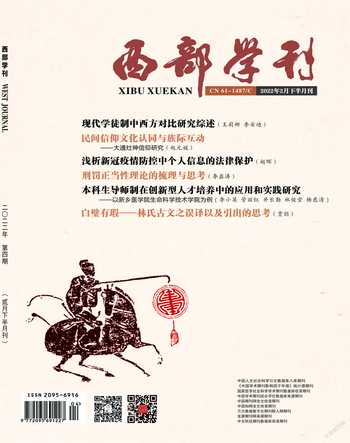民事法律行为的司法变更及其限度探析
谭颖 覃远春
摘要:由我国《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可变更”制度的删除引发了对司法是否应当对私主体意志、行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的思考。首先,通过民法与市民社会的联系以及与德国“狭义的社会原则”的结合分析,认为民法应当干预私主体的自治行为,但因民法需尊重私主体意愿而应对干预行为加以限制。其次,只有出现特殊法定情形时,在充分尊重私主体意思自治后方可适用民法进行干预。最后,应突出私主体自愿性变更的地位,删除不恰当的外在的司法变更,严格限制司法变更的适用。
关键词:私法自治;法律干预;司法变更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4-0101-04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与原则,与国家干预需要平衡与协调,完全放任自治和完全违背自愿的外来干预都不可取,民法的具体制度和规则无疑需要体现干预与自治之间的恰当平衡。民事法律制度应充分尊重私主体的自由意志,并以此为原则进行完善。2017年《民法总则》在内容上将《民法通则》可变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变更”删除,如《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中“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修改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一改变可有效避免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不当干预, 凸显了对意思自治的尊重[1]。在2021年1月实施的《民法典》中相关制度规定也体现了这一趋势。由此引发了对民法和司法机关是否应当对私主体意思自治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的思考。
一、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变更的理论基础
自然人、法人等私主体都同时生活在双重社会中,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在政治社会中,这些主体是以相关公法上的身份出现享受的权利,如自然人的身份就是公民。这种由公法身份带来的权利跟日常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市民社会中,就回归到了民事主体的身份。此时所依靠的就是私权利来进行生存和发展,这些权利涵盖人格、财产、身份等方面。民事主体因享有私权利得以交易,而交易条件即契约形成对当事人之间的拘束,各方当事人均需遵照执行,从大量的具体的民事交易准则中提取的公因式就成了市民社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经国家认可而形成法律,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民事主体的私权利,使其自由意志得到充分彰显并得到足够的尊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有赖于市民社会的法律制度提供的规制和保障,另一方面在于公民权利的觉醒来指导实践行为,不在于国家权利的扩张,是基于公民的契约式合作思维的启蒙和指导自身的实践,而非简单的情绪行为。
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对于民事交易中权利、义务、责任的合理配置为私权之实现提供了规范的保护途径。民法的制定及其实施其实是和政治社会相联系的,可以说是政治中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可以有效治理国家,对外则进行维护、扩大国家利益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总体更好运转。民事主体又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对该主体的私权利的保护,就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保障私权利的运行,维护私主体的权益,另一方面是,对私主体进行规范、制约,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运行,这暗藏了干预私主体自治行为的内涵。民法对私主体自治行为的干预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私主体的权利,就如同为每个私主体划了个圈,自己的圈内是自己的权利,如果交叉进入别的私主体的控制范围,他人的权利可能就成为自己的义务,自己的权利可能就变成他人的义务,从而对私主体的权利行使形成限制。若是没有民法来限定这个范围,就没有人去承担义务,那么也就没有人拥有权利。
执行才是法律条文的意志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执行主体以公权力机关为主,故本文将这种干预限定为司法变更。
二、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变更的论说与规则梳理
民法对当事人意志、行为的干涉是否没有边界,答案是否定的。法律赋予并且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私法自治”。生活中,人必须不停地同他人交往,因而每个人都需要私法自治,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地对自身事务作出决定并负责。当其具备了这种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和维护人格尊严,所以说私法自治是民法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上文中提到公民的契约式合作思维的启蒙,并以此指导自身的实践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在合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现代社会中,订立合同的双方绝大多数都是平等、独立的,很少存在一方依赖于另一方的关系。卡尔·拉伦茨认为:“每一方合同主体根据其自身的判断,认为另一方提供的给付之间具有等价关系,从均衡和公平原则出发,法律的任务仅在于制定一些规则,以使各方主体能够在无错误、无强制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的判断。”[2]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是经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考的,并非简单的情绪性活动,故而在民事活动中,法律过多地进行干涉是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的。
随着社会发展,存在意志上的不独立、不平等,也有实力弱经验不足从而依赖于合同另外一方,或者另一方在某些领域存在着垄断地位而导致的不独立、不平等。此时,就可以借鉴德国民法中的“狭义的社会原则”来适当地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具体而言,在不平等、不独立的情况下,仅靠私主体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摆脱这种困境的,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为维护较弱方而创造相对平衡的局面,衡平双方在地位、资金等方面的力量,故民法应适时干预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但应有其边界。
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法律干涉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从社会发展和《民法典》内容的变化来看,是逐渐回归到了私权本位和私法自治的道路上来,以下是对具体变化的梳理:
(一)《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中“可变更”规定删除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废弃了《民法通则》第五十七、五十八条中对意思瑕疵的合同请求变更的路径,仅允许当事人请求撤销。学理界对此变化存在不同的声音,部分学者肯定此举,认为是我国民法往私法自治上更进一步,称这一改变是“彰显意思自治原则上的进步”。但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有学者通过与别国进行制度对比,主张部分保留变更法律行为制度的,也有学者通过对“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案件的实证分析的角度,主张恢复可变更合同规定[3]。笔者对删除“可变更”规定持肯定态度,理由如下:
在理论上,对于此类合同的撤销还是变更,所需解决的是表意瑕疵、不自由的问题,其违反了意思表示过程应内外一致的要求和自愿原则。如若请求司法机关予以变更可试想一下两种情形:
情形一:有表意瑕疵一方当事人单方拿着合同去请求司法变更并得到支持后,意思内容就会被实质性的变更,便会产生三种结果:①法院变更后,双方当事人认为很公平便欣然接受,这是一个相当理想化的状态。②法院变更后,其中一方认为不公平,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变更后双方接受变更。③经过了一审二审,双方仍不服裁判,申请再审或被迫接受。且不说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的问题,单就这个变更的过程而言,就是法院作为第三方直接参与到合同中的强制性的修改合同实质内容。换一种稍微极端一点的说法,相当于法院给双方订立了一份新的合同。
情形二:也有学者认为,双方基于自愿请求变更的,就相当于双方将自己变更合同的权利让渡给了司法机关,希望有个公平的第三方替自己作决定。但《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并没有具体明确变更的内容、方式等实质性内容。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变更后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对变更后的结果双方能接受范围有多大也是难以确定的。
请求撤销合同有所不同,是在当事人意志不平等的条件下,赋予其撤销权,这种制度设计就是德国的“狭义的社会原则”,从意思表示这一源头入手纠正瑕疵,回到双方关系到成立该法律行为前,恢复到最初双方当事人相对平等的状态,为双方提供重新作出健全表意的机会。也就是说,若双方在合同被撤销后有继续合作意向,就重新签订合同;若没有合作的意向,双方恢复瑕疵合同订立之前双方权利义务圆满的状态,法院处于“辅助地位”而非“决定地位”,可以说是帮当事人“重新找回理智”,让一切重新开始。从私法自治的角度而言,相较于法律的强制干预而变更合同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法院对合同程序性撤销而没有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更为妥当,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影响较小,对私法自治领域的介入较浅。
从司法实践上,笔者以“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民事案件”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收集最高院的裁判文书74份作为样本分析,其中27份判决书,47份裁定书。判决书中有2份撤销全部合同、1份撤销合同部分内容、1份变更合同内容(裁判文书中未明确当事人申请的变更还是撤销)。裁定书中有11份撤销合同、1份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应当事人要求变更),综上仅2份变更合同内容。在74份裁判文书中,有28份裁定书的当事人申请撤销,但因缺乏证据或不属于撤销情形不被法院认可。其他案件则属于除斥期间经过,未申请变更或诉讼等其他情形。从这个数据统计来看,表意瑕疵相关案件,当事人和司法机关都明显倾向撤销,因为标准便于衡量,结果便于把握,也可以看出司法变更的实践作用极其有限,被删除可谓是顺势而为。可见司法干预范围是不断缩小的,且干预的限定条件之一就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从《民法典》中情势变更的规定进一步限定干预范围
相较于之前规定而言,《民法典》的情势变更存在以下变化:
1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情形。这一制度安排说明当出现不可抗力时,当事人可以寻求情势变更的救济。假设第五百三十三条仍然排除了不可抗力这一情形,当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存在合同目的不达,当事人基于签订合同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不在乎责任的全部或部分免除,而是希望继续维持合同关系,仅追求合同权利义务变更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的需求是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的。基于此,除了当事人合意的协商变更可供利用外,法律上应当为其提供协商和合同变更的空间,所以第五百三十三条不再排斥不可抗力情况。这一做法虽然看似与上文的删除变更相反,但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扩充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弱化了法律对当事人私权利的强制干预,有着强调私法自治的立法趋势在里面。
2增加了“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第五百三十三条引入自行协商机制由各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权利义务重新约定,不再像之前一样只能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或解除,体现了私法自治和意思自由原则。
故除了考虑特殊法定情形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两个限定条件外,还应考虑当事人之间协商的情况,当协商不成或者无力应对的情况下,法律才有强制干预的可能。
三、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变更的未来方向
法律干预在实践中往往通过司法审判体现出来的,故而需要明确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变更的未来方向。
首先,应突出自愿性变更地位。从《民法典》的相关变化来看,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民事领域私法自治的回归,不过其适当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验证,因此需要更加强调自愿性变更的地位,通过类似于“撤销合同”的做法,不直接干预意思自治,直接程序上予以撤销,恢复原状,后续留给合同订立的当事人重新作出意思表示的空间,强调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地位。
其次,考虑删除不恰当的外在司法变更,并且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司法变更的适用。法院对于约定违约金的调整就体现出我国制度过度干预问题。合同关系因其相对性更应体现意思自治,即使违约金数额过高或过低,订立合同时符合必要条件且不违反相关规定,法律就不应该主动干预,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自由。但实务中并非所有约定的违约金都能被认可,对其调整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干涉,除了需要法定条件外,还需要充分的正当理由。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是严格限定违约金调整的,自由裁量范围较小。但由于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至二十九条的规定,在實务操作中,才导致违约金司法变更的滥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违约金调整又未作实质性的变动。
笔者是不赞同司法层面调整约定违约金的。从实务情况来看,对于违约金的调整绝大多数法院都是调低,很少会调高违约金,如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若晚于某日交付房租,则违约金按照日租金的100%收取。”这必然属于违约金过高的情形,但签订合同之时,承租方有把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违约,或者认为这个违约金是其能接受的范围,抑或对违约金调整制度的依赖,不管出于何种思考,承租方对违约金的金额是没有认识错误且自愿的,对责任也有清晰的认识。合同有效,司法却又对其进行调整,那约定违约金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无法发挥其约束当事人行为、保障合同履行、促成合同目的达成的作用。
倘若当事人对合同中对违约金的认识出现偏差,可以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话,走相关路径,如基于重大误解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裁判即可。基于弱势地位而不得不签的话,同样也可以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按照乘人之危导致的显失公平或者欺诈、胁迫、第三人欺诈胁迫等路径的,没有必要参与到当事人之间去“搅这趟浑水”。
综上,司法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的范围应当限定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即出现了特殊法定情形时,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后,当事人之间协商不成或者无力应对的情况下,仍然无法解决时,法律才有强制干预的可能,并且未来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变更的方向应突出自愿性变更的地位,删除不恰当的外在的司法变更,严格限制司法变更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姚明斌.民法典体系视角下的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J].东方学,2021(3).
[2]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侯国跃,何鞠师.论民法典合同编对可撤销合同变更权的有限保留[J].河南社会科学,2020(2).作者简介:谭颖(1999—),女,汉族,贵州贵阳人,单位为贵州财经大学,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覃远春(1975—),男,苗族,贵州普定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