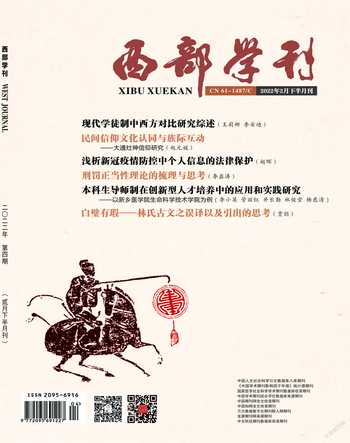影响早期汉译佛典的因素
摘要:早期中土译经所译佛典大多没有写本的传习,而是由当时外国来华沙门牢记于心口诵而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早期汉译佛典的高峰期,彼时,一些大的译场出现,翻译组织逐渐完善,一次佛经翻译工作的开展,往往需要口诵佛典底本的持诵者、负责语言转换的传译者、将汉译佛典书写成文的笔受三方各司其职、共同配合来完成,这三者便是影响早期汉译佛典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早期汉译佛典;持诵者;传译者;笔受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4-0143-04
早期中土(指汉地中部或中原王朝)译经所译佛典大多没有写本的传习,而是由当时外国来华沙门牢记于心口诵而出的[1]。最初中土佛经汉译工作至少需要两人参与,即持诵佛典底本的持诵者与精通华戎音译的传译者,两人相约对译,一人口诵外文佛典底本,一人将其所诵经典翻译成汉语,并书写在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早期佛典汉译的一个高峰期,彼时,一些大的译场出现,翻译组织逐渐完备,一次佛经翻译工作的开展,往往需要口诵佛典底本的持诵者、負责语言转换的传译者和将汉译佛典书写成文的笔受三方各司其职、共同配合来完成,事后还会有点校等对汉译出的佛典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但总的来说,对早期汉译佛典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是持诵者、传译者和笔受。
一、持诵者
在笔者看来,持诵者对汉译佛典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持诵者持诵的佛典底本是汉译佛典的基础。
受印度文化传播独特背景的影响,佛经早在传播之初就沿袭了当时口口相传的传统方式[2]50,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于书面文字的传播,它单纯依靠人的记忆传承佛典,这使得佛经在传播过程中很难保证自身不会受到持诵者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这种影响是多种多样且无法预知的,它可能是持诵者的语言或口音以及出现偏差的记忆,也可能是持诵者基于自身不同的理解,更可能是持诵者受部派归属影响的刻意为之,等等。我们无法得知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佛经和最初佛陀口中讲出的那一版到底有多少不同,正如我们被告知的现存口传史诗吟诵情况一样,即没有两场吟诵会是一模一样的:情节出现的先后可能会因为吟诵而异,有些情节甚至会被省略掉。然而,只要叙事的主要情节被保留下来并取得预期的结果,吟诵者即使略去或增添一部分内容都无足轻重,这或许同样适用于早期佛经的吟诵[2]50。如《付法藏因缘传》卷二所载:“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①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3]可见早在阿难在世的时候,佛典就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或因为理解不同,或因为辗转流变,而有谬误出现,这种谬误连阿难都无法更改。这是发生在早期佛典传承时候的事情,更遑论佛典流传到汉地时,早已经在时间的洗礼下不知产生了多少差误。
口传传统造就了佛经持诵者这一专门角色的诞生,他们是佛经传承必不可少的载体,其所属组别与记忆佛经的方式等都会影响到佛经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根据上座部传承,四部尼柯耶②定型后,即被分给不同组的人来保存,其中《长部》经典交付于阿难及其弟子负责,《中部》交付于舍利弗及其弟子负责,《相应部》交付于大迦叶及其弟子负责,《增支部》则交付于阿那律及其弟子负责[2]51。负责记忆不同经典的持诵者分属于他们自己的组别,持诵者本身并非狭义上的只是记忆佛典的工具,他们在记忆佛典内容的同时也会基于自身的理解对经文作出符合他们认知的解释,这势必会导致一些分歧的产生,就如同我们能在巴利藏经里发现方言差异这一事实恰好证明了持诵者并非一种单纯记忆的工具,如果佛经并非被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那么可比对的佛经被不同组别僧人记忆后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这或许就是不同部派传承相关佛经的经文却总有种种差异[2]54-55。
虽然,我们经常在一些僧传中见到诸如持诵僧人记忆力非凡的记载[1],可这并不是说这些记忆力非凡的持诵者对佛典底本的持诵就不会因记忆而产生偏差。一些小技巧被设计出来帮助持诵僧人记忆经文,例如,我们在佛典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文句反复出现,这些反复的文句就是为了方便持诵者记忆的一种刻意为之。“重复”是经文中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释道安著名的翻译理论“五失本[1],三不译”中就不止一次提及佛典多重复这一显要特征。假设一个外国来华沙门③因为记忆力不佳,对自己记忆的佛典有所遗忘,那么这些被遗忘的部分就不会在汉译时被翻译出来。且不同的持诵者本身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所讲语言未必相同。佛陀在世时并未要求他的弟子必须用统一的语言说法,相反,他反对用统一的、固定的语言,而更加愿意他的弟子去到哪里就用哪里的语言向人们弘法。这种做法显然利于佛经在地域上的传播,但无疑会增加佛教语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试想一部佛典可能被记忆它的持诵者带去过很多地方传诵,然后,这些佛典再经由那些地方的持诵者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再被传播到下一个地区,最终,等到这部佛典被传诵到中土时,其语言形态可能与这部佛典最早的语言形态已经大为不同,且同一部佛典还会被不同地区的持诵者传入中土,他们所持诵的印度底本如若往上溯源,大抵也并非来自同一地区。朱庆之在他的文章《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中也曾说过:“1930年以来,随着吐火罗文献为代表的古代西域非汉语文献的发现和有关研究的展开,学者们逐渐了解到早期中印文化交流主要是间接完成的,即经过了中亚的中介。”[4]24这是说,一些佛典往往是经过一个中介地再传到汉地的。方壮猷在其发表的文章《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中也说道:“盖后汉魏晋代中国所传之佛教,大抵由西域龟兹、焉耆间接输入,其时所翻译之佛典,亦大抵由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焉耆语间接翻译而来。……因此等古西域语之发见,而后汉魏晋时代佛教由西域间接传入中国之迹,乃得证明之。”[5]
关于早期汉译佛典原语问题的研究,学界有多种声音,法国学者SYLVAIN LEVI认为汉译佛典的原语可能是吐火罗语,他认为印度佛典在被翻译成中文前,先被翻译成了吐火罗文,再由吐火罗文翻译成中文,季羡林赞同LEVI的观点,并基于他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6]。这一观点在之后被许多学者引用,并被一些学者进一步推衍,进而认为汉译佛典的原语并非梵语,而是西域地区的语言,例如,龟兹文、于阗文、康居文等胡语。LEVI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难以使人完全信服,首先,支持他论点的论据只是极少的几个词汇,其次,他的论据似乎也不能百分百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早期汉译佛典的原语是犍陀罗语,JOHN BROUGH提出汉译版《长阿含经》的原语是犍陀罗语[7],但是他这一结论也只是基于对《长阿含经》中一小部分音译词的研究,而并非全部;而JAN NATTIER则认为梵语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而是某种俗语方言[8]。日本的辛岛静志显然注意到了LEVI等学者研究时的不足,于是,他在1994年发表的《长阿含经原语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对《长阿含经》中的音译词作了详细的研究。辛岛教授的结论是,《长阿含经》的原语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犍陀罗语,它不仅有西北印度方言的特征,还混合了梵语化、俗语以及地域语言要素,这种语言与西北印度碑文上的犍陀罗语具有相当大的差异[9]。
二、传译者
首先,佛教产生于印度,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印度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体现。尽管从地理的角度上看,我们和印度似乎并没有距离太远,但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与印度的文化却相去甚远,诚如朱庆之教授所言,尽管中印在地理上相去不远,但双方的文化却是根本异质的,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4]11。既然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双方使用的语言也有所区别,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即汉语系统与印欧语系统。梁启超曾说过,佛经都是翻译文学[10],佛经的翻译就是将这些外来语翻译成与之对等的汉语。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系统的巨大差异,印度佛典中势必包含了一些中土文化与语言中未有的内容,从事早期佛典汉译的译人们在翻译佛典时,并不是每一个句子、字词都可以恰巧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找到完美匹配的翻译,这时,译人们便采用音译或意译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他们语言系统中没有对等成分的内容。佛典当中一些专有名词常常是其语言所独有而中土未有的,译人们多采用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处理这些词汇。例如,佛典中对摩揭陀国早期都城名称的翻译,有时是“罗阅祇”,有时是“罗阅城”,有时是“王舍城”。據萧齐僧伽跋陀罗的《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七[11]和隋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一《序品》[12]的记载,“罗阅祇”和“罗阅城”俱都指代同一个地方,在其他佛典中,这一地方也被译作“王舍城”,巴利语写作Rājagaha,音译则作罗阅祇伽罗。“罗阅祇”是巴利语“Rāja”的音译,意译为“王舍”,“伽罗”是“-grha”的音译,意译为城,因此“王舍城”是意译,“罗阅祇”是音译,“罗阅城”则是音意合译。早期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词语有着各种各样的汉译,笔者认为,这些词语之所以有多种样式的汉译,大抵是因为传译者用语习惯、方言歧异等原因,并且,对外来词汇统一规范的翻译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所以,音译与意译乃至多重形式的翻译交替使用,甚至同时出现也在所难免。
其次,传译者在翻译佛经时所遭遇的困难并非是预先设置好的,单凭音译与意译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困难。除音译与意译外,传译者还采取多种手段翻译佛经。传译者在佛典汉译工作中负责佛典在语言层面上的转胡为汉,其责任重大,必须是兼通胡语与汉语的人才才可胜任,“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若胡汉两明,意义四畅,然后宣述经奥,于是乎正。”[1]据僧传记载,有一名叫竺佛念的僧人,兼通胡汉之语,僧祐称其为“苻姚二代译人之宗”[1],其自作的《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序》中对自己的翻译这样评价,“佛念译音,情义实难。或离文而就义,或正滞而傍通,或取解于诵人,或事略而曲备。”[1],这便是有明确记载的除音译与意译外的翻译方法。
三、笔受
以往的佛经汉译研究中,人们总是将影响汉译的焦点放在持诵者与传译者身上,而对笔受这一角色的关注度并不如前二者那么高。大家普遍认为,在一次佛典汉译工作中,笔受往往是被动接收传译者所说的话,并对这些话进行如实的记录,但是,笔者认为,笔受这一角色并非如人们以往认知中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最为显著的就是,其对传译者口头汉译的经文进行润色修饰,使其文字文句具有书面语的特征,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1]。
在早期汉译佛典时,佛典的汉译工作往往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尤其是在书面成文这一步骤上,如何选词用句,译人们往往“一言三复,陶冶精求”[1]。佛经的汉译工作到了笔受这一环节时,其接受到的语言文字已经不再是持诵者口诵出的胡语,而是经过传译者口头翻译的汉语,这些经过口头翻译的译文具有一定的口语色彩是在所难免的,但“秦人好文”[1],书面成文的佛经自然不可能全部用简朴的口头语来书写,这时,笔受就会将一些口头语转化成书面语,加之传译者的口头译文不见得面面俱到,这时就需要笔受发挥其作用,弥补口头翻译的不足,使书面成文具有可读性[1]。但笔受对译文操作的可能性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对译文的增补与藻饰可能会受制于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笔受一般会结合译者的意见,如果译者本人对其译出的经文坚持“依其义不用修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1],笔受就不得不“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1];其二,笔受虽觉译文不妥,但其因语言障碍,不通佛经原文,又与译者无法沟通,恐怕自己更改译文会扭曲经义,因此也只好放弃。
结语
影响早期汉译佛典的因素主要是持诵者、传译者和笔受,这三者对汉译佛典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应该具体佛典具体分析。对影响早期汉译佛典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汉译佛典的情况。
注释:
①阿难:又称阿难尊者(?—公元前463),亦称阿难陀,为梵语Ananda 的音译。他和文中的舍利弗、大迦叶、阿那律都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②尼迦耶(梵语nika^ya),意译为会众、部派、部、类。为佛教经典汇集。
③沙门是梵语,华译勤息,即勤修道业和息诸烦恼的意思,为出家修道者的通称。
参考文献:
[1]僧祐.出三藏记集[DB/OL].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145_001,2021.
[2]肯尼斯·罗伊·诺曼(K.R.NORMAN).佛教文献学十讲[M].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社,2019.
[3]吉迦夜共昙曜.付法藏因缘传[DB/OL].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058_001,2021.
[4]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方壮猷.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J].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4).
[6]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333-334.
[7]JOHN BROUGH.The Gandhari Dharmapada[M].London:London Oriental Series,2001.
[8]JAN NATTIER.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M].Tokyo:Soka University,2008.
[9]辛岛静志.《长阿含经》の原语の研究——音写语分析を中心として[M].东京:平河出版社,1994:8.
[1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
[11]僧伽跋陀罗.善见律毗婆沙[DB/OL].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462_001,2021.
[12]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DB/OL].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18_001,2021.
[13]李炜.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
作者简介:张文(1993—),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单位为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