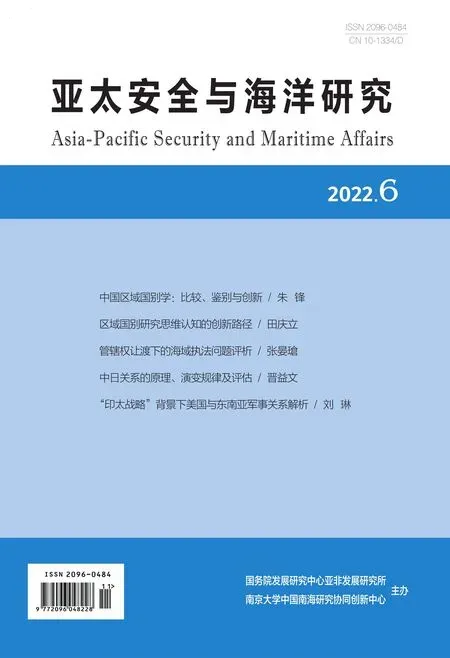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
晋益文
内容提要: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互为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对于中国而言,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时也是最复杂、最特殊的双边关系之一。2022年,中日迎来复交50周年。回首50年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综观近年来两国关系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研究界正面对着如下一些基本问题:当年中日实现复交而进入“蜜月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冷战后中日关系缘何进入“重新调整期”而呈现周期性波动局面?如何认识当今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其前景?
本文旨在以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两国间相互作用三者的总体结构为分析框架,对复交50年来中日关系阶段性变化与调整的成因、表现形态与后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复交5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近中期日本对华政策取向做出总体评估,并就推动中日关系的应对之策提出一己之见。
一、双边关系原理与中日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关系,都会受到国内与国际、双边与多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其基本性质划分,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两国间相互作用等三个主要方面。与其他各国间的双边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既具有共性,同时又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
(一)国际环境与国际地位
国际环境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际秩序层面(1)参见江时学:《国际秩序、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6期,第2—3页。,即双边关系会受到国际规则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影响;二是多边关系层面,即双边关系会受到多边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影响,而多边关系本身实质上就是国际秩序的具体表现及实现方式。
在古代,世界各主要地区分别形成了区域性国际秩序及其之下的国际关系。19世纪中期以前,东亚地区形成和延续了“华夷秩序”及其之下的多边关系,中国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并在塑造中日关系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日本则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
19世纪中期以后,中日关系被纳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性“殖民秩序”及其之下的多边关系之中,中国沦落为边缘国家,日本则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二战后,美苏冷战秩序覆盖全球,中日两国在其中都处于次要地位,两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与台湾当局“缔约”,从而关上了中日复交的大门,中日关系被冷战铁幕所阻隔。两国的区别是,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而日本则未能越过美国对华政策雷池一步。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和解并“联手制苏”一举改变了国际环境,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中日两国在美国不再阻拦的条件下,以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为前提一举实现了复交。
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由“联华制苏”转向“接触加遏制”,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在“挟美制华”与“兼顾中美”之间摇摆,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期”。
21世纪10年代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遏制加脱钩”,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日益增大,日本在中美之间周旋的余地日益缩小。
(二)两国国内条件与双边架构
每一对双边关系的架构及其变化,都以两国的国内条件为基础。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地缘、利益、国力、情感四个维度。
1.地缘维度
国际关系史表明,两国在地理上相邻有可能产生“善邻”或“恶邻”两种局面,“远交近攻”和“与邻为善”是相邻关系中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外交理念与行为模式。
中日隔海相望的地理条件,促成了两千余年的交往史。在古代,中国历朝视日本为“蕞尔岛国”,日本则经历了学习汉唐的前期和文化自立的后期。到了近代,中日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日关系经历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反哺”的前期和日本试图殖民化中国的后期。(2)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现象包括:一是大量日译西方词汇进入现代汉语,其中包括当代中国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共产党、社会主义等大量词语;其二,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启蒙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其三,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科技知识经由日本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留日学生成为其桥梁。二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20年冷战隔绝期、复交后20年“蜜月期”以及冷战后30年周期性波动期。
二战后,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向“海洋国家论”倾斜(3)自高坂正尧提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以来,主张日本为“海洋国家”、反对与“大陆国家”为伍的观点在日本颇为流行。参见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第5—14页。,其在地缘政治定位上的摇摆,是导致当今中日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利益维度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追求本国的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包含多领域、多层次内涵的复杂体系,决策者需要在多种利益中排列出主次顺序,如核心利益、主要利益、一般利益等。
古代,中日两国的利益诉求经历了不对称阶段:中国历代朝廷对日本的利益诉求主要在于政治方面,即寻求把日本纳入以“朝贡、册封”为标志的“华夷秩序”之中。而日本对中国的利益诉求则是全方位的,早期谋求吸收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后期则主要致力于通过朝贡和贸易获取大陆的财富。
近现代,中日利益关系经历了极端对立的阶段,日本把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富作为其利益诉求,中国的基本利益诉求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二战后,中日关系先是经历了“冷战隔绝期”,中国把反对日本敌视中国政策、推动对日复交和促进民间贸易作为利益诉求,日本则把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以及开展有限度的日中民间贸易作为利益诉求。1972年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进入了相互交往史上利益契合度最高的时期。
冷战后,中日两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出现了不均衡发展局面,即经济利益诉求高度契合,政治与安全利益诉求渐行渐远。
3.国力维度
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中包含国土、人口、经济、军事、制度、领导、外交、民族凝聚、对外传播等要素的规模与力量。(4)参见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在中日国土与人口对比上,“中大日小”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在此前提下,文明史的“中早日晚”,文化上的“中学日渐”以及大陆历朝的强盛等因素,决定了古代两千年为“中强日弱”时期。1894年,建立了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日本战胜了封建体制下的清廷,中日国力对比进入了“日强中弱”时期。二战后,中日两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大国化道路:中国走的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大国”的道路,日本则走上了“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综合国力大国”的道路。当今两国的大国化进程仍属于“进行时”,其相互间的互补与碰撞,也是导致当今中日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4.情感维度
情感维度,是指两国相互基于对对方的优劣判断和好恶情感而形成的集体记忆和民众情感。
古代两千年交往史的积淀,构成了中日相互集体记忆和民众情感的心理底色。古代中国历朝自视华夏为“天下”中心,视日本为“东夷”。而对日本人而言,古代中国是传授了儒道释思想、汉字和唐诗的心灵的故乡。日本起初接受了汉魏对其“倭”的称呼(5)“倭”概念首次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此时尚为抽象的地理概念,并非实指日本。参见王升:《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8页;班固《后汉书·地理志》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首次以“倭”实指日本。参见周明:《释“倭”》,《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第125—130页;“倭”字起初并无贬义,系古代汉人对日本人或政治势力自称词“ワ”的音注字,被日本接受并长期使用,只是到了近世才被一些日本人认为带有贬义。参见胡稹、洪晨晖:《“倭”字音、义再考》,《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55—61页。,但逐渐从其语感中感觉到了贬义,于是在同样发音下把“倭”改为“和”(同为“ワ”=“WA”),把“大倭”改为“大和”(同为“ヤマト”=“YAMATO”),进而把国名改为“日本”。(6)参见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53页。
近代中日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主色调是灰暗,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不时被当代中日政治摩擦所激活,已成为重新界定过的“当代版历史记忆”。对日本人而言,近代是日本从偏安一隅的岛国崛起为东亚第一强国的时代,是其建立“东亚第一”优越意识的源头。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憧憬汉唐而轻视清朝及近代中国的情感模式。日本对近代中国使用的“支那”称谓逐渐被赋予贬义(7)参见杨鹏、孟玲洲:《污蔑与辨正:“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43—47页。,直至二战后中国才得以迫使日本彻底停用这一蔑称(8)参见单冠初:《民国时期中国官民反对日本对华“支那”蔑称交涉始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1页。。
在二战后的“冷战隔绝期”,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是,其政府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其人民中则存在对华友好人士;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给日本奠定了战后民主制度与和平路线的基础,中日两国则被冷战“铁幕”隔绝而属于不同阵营。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给中国人留下了诸如产品质量过硬、影视作品优良以及日本人彬彬有礼等正面印象;日本人则看到了经济落后的中国和朴实的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差距成为影响两国民众相互认知与情感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民众越来越得以近距离观察对方。此期中国经济规模赶上和超过了日本,这对两国民众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心态带来了强烈冲击。在民族心理上,当今中国人看待日本及日本人的心态日益理性、客观、自信,日本则经历着从百年“脱亚入欧”心态艰难摆脱的民族心理调整期,其集体心态真正由“俯视亚洲、仰视欧美”转为“平视亚欧(美)”尚需时日。
(三)两国间的相互作用
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条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两国间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两国间的互动是由多个领域组成的整体,其中尤以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为主要的互动领域。
政治关系领域,是由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以及确定敌友关系和对国际秩序的态度等政治逻辑支配的。双边政治关系既可能出现“双赢”(win-win)局面,也可能陷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困境,其基本形态有友好、非敌非友、敌对等不同类型。
经济关系领域,是政治逻辑和以市场原理为核心的经济逻辑相互竞争的领地。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以自由贸易理念为核心的经济逻辑逐渐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占据主流地位。相对于政治与安全领域而言,较纯粹的经济领域是最容易产生“双赢”结局的领域。
安全关系领域,是双边关系中比政治逻辑更为集中、尖锐地反映维护主权这一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也是两国关系中最容易陷于“零和”困境的领域。
文化关系领域,则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由以相互影响、相互理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逻辑所支配。从长远的视角看,文化关系离政治与安全关系最远,因而有可能超越敏感对立问题而促进国家间交流,从而为政治与安全上的相互和解创造有利的缓冲氛围。
二、中日复交和呈现“蜜月期”的成因
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两国在有利的“天时”(中美和解的国际环境)、“地利”(中日双方的稳定周边政策)和“人和”(中日决策层的复交意愿及推动能力)条件下,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
(一)中美和解消除了中日复交的主要外部障碍
二战后,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发生政权更替而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而日本则在被美国占领期间形成了“随美遏华”路线,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缔约”。中日两国在法理上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美国成为阻碍中日复交的最主要国际因素。
1969年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协助下调整对外战略,寻求与中国化敌为友从而形成“联华制苏”态势。同期,中国决策层也着手调整对美政策,最终形成了“联美制苏”战略。经过“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铺垫,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7月15日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电视讲话,宣布将访问尚未建交的中国,并于翌年2月成功访华。
以中美和解及其“联手制苏”局面的形成为背景,美国放弃了阻止日本与中国复交的政策。在国际环境突变的推动下,以追随美国为外交“基轴”的日本决策层停止敌视中国而制定了推动日中复交的方针。
(二)中日决策层的积极互动是促成复交的主要动力
日本于1952年与溃逃台湾而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当局“缔约”,曾是导致中日复交延迟20年的首要原因。1971年11月以后,随着中日复交的机运日趋成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9)关于“复交三原则”的形成过程,参见刘世龙:《新中国对日政策(1949—197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64—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1972年7月5日,以实现日中复交为执政公约的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翌日当选日本首相。7月中旬,田中内阁表示理解中方的“复交三原则”,认为日中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在这个时机解决“台湾问题”。
在此之后,中日两国决策层就复交事宜进行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密切沟通与磋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部进行了“复交派”与“亲台派”之间的协调,田中首相就日中复交问题取得了美国的谅解(10)参见丹睿:《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前的日美协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80—190页。,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以特使身份赴台湾做了安抚工作。(11)参见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经过紧锣密鼓的前期准备,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率团访华,中日双方进行了复交谈判,并于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复交是两国领导人以两国关系正常化大局为重,既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共识,同时又以高度的灵活性在细节上达成妥协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两国决策层对复交的强烈意愿及强大推动能力。
(三)中日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是复交的基本前提
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就台湾、历史、安全、领土等问题逐一达成原则共识,使两国决策层实现复交的强烈意愿变成了现实。
1.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共识
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双方在结束战争状态、台湾归属、“日台和约”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最终逐一达成了妥协与共识。
第一,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方的《联合声明》草案写道:两国在此“确认”战争状态结束,言外之意是该问题在“日台和约”中已经解决,如今只是再次予以确认,这显然是中方难以接受的。经周总理提议,双方最终采取了中日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一表述。
第二,台湾归属问题。《联合声明》采取了双方最终所接受的如下说法:“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条文前半段是根据日方意见,采取了中荷建交时的提法。(12)参见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一语是根据中方要求加入,旨在驳倒“台湾归属未定论”。(13)参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35页。
大平外相在《联合声明》发表后的记者会上指出:“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继承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有‘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的明文规定,按照我国承诺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原委,日本政府遵循坚持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14)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日本以这种方式就台湾归属问题表明了态度。
第三,“日台和约”问题。在田中访华前,日方就对宣布“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抱有抵触心理。(15)日方认为,“日台和约”是经国会批准的,说其“无效”就等于欺骗了本国国民多年,因而主张采取“现已失效”的说法。《中日联合声明》最终采用了双方均能接受的措辞,但中日分歧本身并没有得到消除。最后,双方决定不就过去20年的法律解释问题进行争论,周总理表示中日两国友好下去是关键。(16)参见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最终解决方式是:先是在《联合声明》中采用如下表述:“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没有写入“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这一条,而由大平外相在《联合声明》发表后在记者会上宣布:“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指“日台和约”——笔者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113页。
2.关于“历史问题”的原则共识
中日复交之前,“历史问题”不可能超越冷战格局而凸显出来。1972年中日双方开始酝酿复交谈判时,如何处理日本侵华历史问题便摆在了面前。
在田中首相率团抵达北京后第一天的谈判以及当晚中方欢迎宴会等场合上,田中首相多次把日本的对华侵略轻描淡写为“添了很大麻烦”,引起了中方的严厉批判。田中解释道,这里有个中日两国语言的不同语气问题,但可以按中国汉语的习惯来表述。在9月27日晚的外长会谈中,大平外相口述了如下表述方式:“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表述最终为《联合声明》所采用。
3.关于“相互安全”的原则共识
在决定访华前,田中首相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中方提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周总理向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提出中日复交可不涉及日美安全条约问题后,田中消除了最大的顾虑。(18)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11頁。
中日复交后,日本对日美双边文件中的涉台条款的解释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由于美中、日中关系的改善,台湾海峡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远东条款”“台湾条款”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其二,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三,根据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用应慎重对待。
中日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而构建和平友好关系,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4.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原则共识
在中日复交谈判中,中方以恢复邦交大局为重,确定了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钓鱼岛问题的方针,并与日方就此达成了共识。(19)中日复交谈判第三次首脑会谈将近结束时,田中首相询问中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的态度。周总理说,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参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47页。数年后在中日缔约谈判时,钓鱼岛问题同样被搁置起来。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铃木善幸时就钓鱼岛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上述四方面原则共识,是当时中日两国决策层抓住难得出现的内外机遇,以尽早实现复交为优先考虑的大局,围绕复交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谈判、交锋与妥协而最终得出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是由两国复交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所组成的完整体系。
(四)中日关系20年“蜜月期”的定位
中日复交扫清了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碍,释放出了两国各领域全面交流与合作的巨大潜力。1972—1992年期间,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堪称“蜜月期”的历史上最好时期。
1.中日双方利益诉求、政策取向以及民间情感高度契合
中日复交前后,在日本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中,稳定周边的地缘政治因素与开发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因素占据了优先位置,意识形态差异及阵营政治因素退居次要位置。田中首相曾说,“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成为比在亚洲建立北约更强的安全保障。”(20)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75—76頁。这种新型安全观和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的考虑,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首要基础。另一方面,“蜜月期”日本对华友好政策,也受到了经济实力快速上升期日本社会舆论在对华关系上的自信与期待和对美外交自主意识的支撑与推动。
同一时期,稳定周边与发展经济也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中日复交开创了两国间和平友好局面,两国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开始全面启动。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耳闻目睹了日本经济的高度发达状况,并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借鉴了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思路。(21)1978年底,邓小平在谷牧的建议下,聘请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等日本专家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翌年又成立了由中日双方政府高官和专家组成的中日经济交流会。1984年邓小平曾对来访的中曾根首相说,翻两番是在大平先生的启发下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很多思路,都是在日本经验及日方人员的启发下形成的。参见张云方:《中日经济交流会拾遗》,《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35页。这一时期,处于发达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对华出口高端设备与技术以及在华投资建厂,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1979年12月,日本决定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日本对华ODA在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22)截至2019年,日本对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约3.3165万亿日元、无偿援助约1576亿日元,技术合作约1857亿日元,其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建设资金短缺的20世纪80—90年代提供的。2018年,日本政府宣布停止提供对华ODA。参见: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中華人民共和国』、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data.html#06 [2022-07-24]。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给日本带来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与发展机遇。
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政治大国意识的逐渐抬头以及日中关系的友好合作局面和日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等因素为背景,谋求提高对美外交的自主性和对华外交的主动性。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23)宫泽喜一首相语(《朝日新闻》1992年4月7日)。中日复交迎来20周年的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实现了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蜜月期”达到了一个高潮。
2.中日双方恪守复交原则共识、妥善处理相互矛盾
这一时期,日本也曾出现一些违背中日复交原则共识的动向。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战败40周年的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内阁集体正式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1982年和1986年,日本文部省指导修改了学校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历史的记述,如把“侵略”改为“进入”等。在“台湾问题”上,1973年3月,日本一些政要成立了“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其后多次派团访问台湾,并发表有悖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言论;1986年,日本法院把中国国家财产“光华寮”判给了台湾当局。在“领土与海域”问题上,1974年,日韩两国签订“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把约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海大陆架划入开发范围;1979年5—6月,日本在钓鱼岛修建直升机机场并进行资源调查。这些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引发了中日政治摩擦,但均得到妥善处理或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中日双方恪守复交原则共识、维护友好合作大局的共同立场。(24)参见张历历:《百年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30—437页。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相继与西方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中日复交因两国间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利益结构而堪称最为复杂、难度最大,最终成功弥足珍贵,其积极意义通过复交50年来两国各领域交流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充分证明。
三、中日关系重新调整和波动的原因及规律
冷战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与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方式均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以此为背景,复交后持续20年的“蜜月期”氛围逐渐消退,中日关系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中日经贸与人文领域交流得以全面、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则出现了一种新的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两国其他领域交流受到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而出现“政冷经热”、民众情感碰撞等现象。这一趋势的出现显示着,中日关系从“蜜月期”转入了“重新调整期”。
(一)中日关系进入“重新调整期”的原因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是导致中日关系进入“重新调整期”的背景和深层原因。
1.美国对华政策由“联华制苏”向“接触加遏制”转变,是影响中日关系转变的首要国际环境因素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美“联手制苏”的战略前提消失。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从“联华制苏”的现实主义均势战略,转向意识形态导向的促变战略。1993年以后,随着中国出现快速崛起势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又增添了战略防范因素,形成了称作“接触加遏制”(engagement & containment)的新政策。美国携手日本对冷战后因“失去敌人”而处于“漂流”状态的美日同盟进行“再定义”,制定了以“携日遏华”为基调的“新东亚战略”。(25)参见徐万胜等:《同盟视域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69—73页。日本对此积极响应,其对华政策从“友好合作”调整为“挟美制华”。美日强化以防范中国为重要目的的安全同盟,增大了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压力,恶化了中日政治互信氛围,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进入了“漂流期”。
2.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趋势和寻求“摆脱赎罪意识”的对华政策变化动向,是引发中日关系重新调整的重要原因
冷战后,日本政界的“1955年体制”崩溃而出现“总体保守化”趋势。(26)1955年,日本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分别实现大联合,形成了自民党与社会党对峙结构,前者在1955—1993年间历次国会选举中皆取胜而长期执政,后者称作“万年在野党”。该政治结构称作“1955年体制”。1993年以后,社会党因政策趋向“自民党化”而逐渐衰落,日本各政党政策趋于“总体保守化”。随着日本“战后新生代”登上政治舞台,对本国近代侵略历史缺乏正确认识、要求摆脱“赎罪意识”和“战后体制”的新保守势力逐渐占据政界主流。在此背景下,中日复交时就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等问题达成的原则共识底线不断受到日本方面的冲击。
3.中日民族心理、国力对比及互动方式的变化,是中日关系出现新局面的双边结构性原因
中日关系经过两千年“中强日弱”、百年“日强中弱”时期后,出现了向“中日两强”乃至“中强日弱”格局转变的趋势。这一国力对比变化趋势和两国舆论与民众情感恶化因素的合力,导致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中日舆论与情感因素对两国互动方式的影响日益增大;中日关系从1972—1992年期间的“高层主导、政治决断”型向冷战后的“官民互动、大众参与”型转变。
(二)中日关系的“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
以上述国际环境与中日两国变化为背景,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期,突出表现为政治关系“趋冷”与“回暖”之间的周期性波动。冷战后约30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三轮“趋冷—回暖”波动,在每次“回暖”阶段均在继承已有原则共识的基础上达成了新的原则共识。2021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进入第四轮波动局面的迹象。
1.第一轮“趋冷—回暖”波动(1994—2000年)
1994—1996年期间,中日政治摩擦频频发生,两国关系陷于复交以来的最严峻局面,研究界逐渐称之为“政冷”。
“历史问题”首先成为引发中日“政冷”局面的导火索,其主要表现是日本政要发表“妄言”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间“历史问题的现实化”不断转化为“现实化的历史问题”。
这一时期,日本显露出在“台湾问题”上渐进背离中日复交原则共识的苗头,在推进与台湾地区政治人物及台湾当局官员往来、互派机构名称升格等问题上多次打起“擦边球”,引发了中日间间歇性的“台湾问题”摩擦。(27)参见吕耀东:《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及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第20、37页。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美同盟“再定义”,开始改变复交以来中日和平友好的安全关系氛围,使中美日三边关系结束“蜜月期”而逐渐向“美日遏华”结构转变。(28)参见孙成岗:《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99—127页。日美同盟的主要假想敌从苏联转变为“周边事态”,其中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此举导致中日间初现“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局面。
中日钓鱼岛问题的“搁置争议”局面在此期间出现新变化。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团体屡次登上钓鱼岛建造灯塔,对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纵容态度。经中方严正交涉,日方有所收敛。1992年中国施行写入钓鱼岛为中国陆地领土的《领海法》(29)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25日实施。,日本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中方“立即撤销”该法。
由上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复交时就历史、台湾、安全、钓鱼岛四大问题所达成的原则共识开始受到全面冲击,两国关系滑入“政冷”低谷。
面对政治摩擦频发的局面,中日双方共同做出了改善关系的努力。1997年正值中日复交25周年,通过9月桥本首相访华和11月李鹏总理访日,两国关系开始“回暖”。199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中日发表了继复交、缔约文件之后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决策层与时俱进地给两国关系赋予新的定位,标志着两国关系重新调整进程取得了初步成果。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旨在“增信释疑”的正式访问,中日关系“回暖”势头进一步增强。
2.第二轮“趋冷—回暖”波动(2001—2011年)
中日关系的“回暖”局面于2001年中断。这一年,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并在此后任期内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中日关系陷于比上一轮更为严峻、时间更长的“政冷”期。
2006年9月日本首相更替为中日关系“回暖”提供了契机。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于10月8—9日应邀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破冰之旅”的访问,中日领导人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融冰之旅”的访问,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新调整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另一方面,安倍内阁执政一年期间大力开展构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活动,预示着21世纪的中日关系正面临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与博弈。2007年9月25日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决定,在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中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一带有“围堵中国”意味的概念。同年12月,福田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迎春之旅”的访问。此后直至2011年,尽管其间发生了“撞船事件”(30)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但中日关系总体上保持了2006年秋季以来的稳定发展态势。(31)参见王泰平:《2011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亚非纵横》2012年第2期,第38—43页。
3.第三轮“趋冷—回暖”波动(2012—2020年)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从“所有者”手中“购买”钓鱼岛。这一背离中日复交原则共识、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导致中日关系陷于新一轮“政冷”低谷。(32)参见《外交部:中日关系严峻局面由日方一手造成》,人民网,2012年9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912/c70731-18992808.html [2022-08-01]。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本已冷却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在“政冷”僵局下,中日双方为管控分歧做了共同努力。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国际会议上多次举行会晤。然而,日本却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使中日关系处在一个乍暖还寒的状态。
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释放出了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关系的钟摆再次从“趋冷”摆向“回暖”一边。2018年10月,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正式访华。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出现了积极转变,中日双方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新的共识。
4.近期:再次滑向“政冷”低谷?
2020年9月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呈现滑向新一轮“政冷”局面的趋势。菅义伟、岸田文雄两届政府在中日安全关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举措,显示出欲与美国一道把台海、东海、南海“三海问题一体化”的战略意图。
其一,继1969年《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写入“台湾条款”以来时隔52年,2021年4月16日的《拜登—菅联合声明》写入了“新台湾条款”。(33)小谷哲男『新台湾条項:台湾と日本の安全保障』(2021-05-11)、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1-01.html[2022-08-02]。日本配合美国高调介入“台湾问题”,把台海局势与自身安全日益紧密地相挂钩,日本政要不断为介入台海局势造势。(34)2021年7月5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称,如果中国攻击台湾,日本可以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同年12月2日和14日,安倍晋三两次在台湾智库线上会议上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其二,日本谋求确立“日美联防钓鱼岛”体制,屡次敦促美国重申《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对中国《海警法》的施行做出强烈反应。其三,这一时期日本积极配合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和美日澳印四边对话(QUAD),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力度。
日本的一系列动向,使2017年以后出现的中日关系“回暖”氛围几近消失,代之以日方不断做出攻击性挑衅举动、中方予以严词驳斥的循环往复局面。
2022年,中日将如何纪念复交50周年备受研究界关注。一年将尽,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业已揭晓:9月12日,中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本经团联共同举办纪念大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分别以视频方式与会致辞;9月24—25日,民间纪念活动分别在北京和东京举行;9月29日,习近平主席与岸田首相互致贺电。与中日关系的理想目标相比,复交50周年这个重要节点已在无首脑互访与会谈、无政府间正式纪念活动、无新政治文件的“三无”低调氛围中逝去。与此同时,日本基于“中国威胁论”的外交与安全战略调整趋势丝毫未见改变迹象(35)2022年10月4日,岸田首相接受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的拜访,就“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海的动向”等交换意见,重申要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予以应对。参见:『東アジア安保に連携対処 岸田首相、米軍司令官と会談』、時事通信社、2022年10月3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65f7e73d6fc03a63c675ab247b6244b976e96135[2022-10-6]。同年10月9日,外相林芳正在与马拉西亚外长赛夫丁会谈时针对中国称:日本坚决反对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参见:『林外相 マレーシア外相と会談 国際情勢に連携して対応を確認』、NHKニュース、2022年10月9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1009/k10013853861000.html[2022-10-12]。,中日间盘根错节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找到根本性解决的出口,两国民众情感与舆论氛围依然处于相当冷淡的状态。(36)吕小庆认为,中日复交50周年纪念活动存在“三个明显不对称”,即与中日关系性质、两国经贸关系、两国领导人共识明显不对称,这使人联想到中日复交30周年也曾“三十而立难立”、40周年“四十不惑大惑”,而2022年可谓“50难知天命”。参见《吕小庆:中日关系决不能搞三个对立》,中评社,2022年10月8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66&docid=106479594&kindid=0[2022-10-08]。川岛真认为,复交50周年未能成为日中关系改善的契机,有七成日本人并不知道日中复交50周年,日本没有形成广泛“庆祝”的氛围,“不用说日中友好,日中究竟要力争实现什么样的关系也没有共识”。参见《川岛真:50周年未成为日中关系改善契机》,《联合早报》2022年10月1日,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21001-1318403[2022-10-08]。
(三)中日关系“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的演进规律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是在国际环境与两国国内条件的持续变化下两国相互作用方式发生变化与调整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国关系围绕相互利益与矛盾交汇点的摩擦—妥协—再摩擦的螺旋式演进。
“政冷”,是中日相互作用的内容与形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其深层原因包括两国间多层次、多领域的博弈:一是“复交原则共识之争”,即两国围绕复交原则共识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发生了分歧;二是“大国化竞争”,即中日双方同时谋求恢复昔日大国辉煌的意愿发生了碰撞;三是“安全困境”,即中日两国都对对方强化国防力量的动向加强了预防性戒备;四是“舆论战”,即中日相互舆论环境的恶化导致两国政治关系变得异常敏感。
“回暖”,是中日两国都不愿承受“政冷长期化”代价的表现与结果。中日双方显然都有“斗而不破”的外交底线,都不想回到1945年以前的战争状态和1972年以前的对立状态。在“政冷”期,中日双方都探寻对方的外交底线,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相互关系转圜;两国的政治舆论氛围逐渐向积极一面回摆,两国的经济利益、文化纽带等正面因素重新发挥积极作用。中日双方基于谋求稳定、利益互求、友好传统等基本条件,都不愿使相互关系彻底破裂,而是都寻求管控分歧并推动双边关系走出“政冷”低谷。
“趋冷”与“回暖”代表着中日政治关系钟摆的两端,迄今为止其摆动幅度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政冷”期,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受挫,但两国复交以来的政治关系框架得以维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断交、对立与对抗的可能性尚小。另外,两国经贸、文化、旅游等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尽管也受到负面冲击,但还是得以持续发展。在“回暖”期,中日政治与安全对话得以重启,但引发“政冷”局面的结构性矛盾犹在,政治与安全互信仍十分薄弱,因而每次“回暖”又总是比较脆弱,一些政治摩擦因素很容易被激活,两国关系可能又会启动下一轮“趋冷—回暖”波动周期。
随着周期性波动的循环往复,中日之间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取向相互边界的内涵变得日益清晰,外延变得日益模糊;双方围绕利益与矛盾交汇点的博弈,沿着恶性循环轨迹已进入结构性矛盾的深水区。
四、中日关系的评估及未来思考
值此复交5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正处于继复交期、冷战后两个转折点之后的又一历史节点。如何把握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应当如何作为?
(一)当前中日关系基本特征的总体评估
21世纪2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的内外条件与两国相互作用方式,与1972年复交时期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做出准确定位,是思考两国关系各实践层面问题的基本前提。
第一,中日复交成果“1972年体制”仍是维系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中日复交曾经面临的台湾、安全、钓鱼岛三大问题正趋向于合为一体而成为中日安全博弈的焦点,其深层背景则是围绕“历史问题”的现实博弈。
中日复交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国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以及决策层的政治意愿与推动能力难得如此齐备的条件下,双方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中日复交给两国关系开辟了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例如,中日贸易额由1972年的10.38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3714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新冠疫情暴发前的超过1000万人。即使在中日“政冷”局面最严峻的几个时段,中日两国的全社会间、各领域间的相互交往与交流关系依然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而且其日益发展的总趋势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
在1972年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双方以复交大局为重,对一些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采取了点到为止、模糊处理或不涉及的方式。复交50年来,中日双方在围绕复交原则共识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两国政治摩擦也大多以如何解释和界定这些原则共识为原点。这一历程表明,“1972年体制”必须与时俱进地得到补充和完善,这就是中日双方发表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以及达成新原则共识的由来。当今和未来,只要不发生日方单方面宣布退出《中日联合声明》的事态,那么中日关系仍将在“1972年体制”铺就的轨道上继续前行和发展。
第二,中日国力与地区影响力对比的持续变化趋势,是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变得紧张的重要原因;两国围绕构建何种地区新秩序的博弈正日趋尖锐化,其深层背景是东亚权力结构变化中的大国化竞争。
中日国力对比格局由百年“日强中弱”经由“中日两强”正向“中强日弱”转变,这一趋势正在推动东亚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在重新调整进程中出现震荡局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崛起进程正在同时提速。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导致日本百年“东亚第一”优越意识濒临崩溃,并引发了其欲阻挠中国发展和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加速强军进程的意愿。中日两强崛起竞争是持续走向对抗还是在合作共赢的基调上“软着陆”,这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两种前景。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政治与军事崛起具有多重含义:其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既定的国家发展方向;其二,日本的强势崛起,势必对地区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和冲击;其三,日本欲沿着“摆脱战后体制”的历史修正主义路径实现崛起,势必引起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戒心;其四,日本把渲染“中国威胁论”作为加速强军的手段,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
当今的中日政治摩擦具有如下三层结构:表层是利益观的对立,里层是价值观的对立,而最深层则是地区秩序观的对立。说到底,中日相互如何对待对方的崛起,两国准备接受何种未来地区秩序?这是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根本症结所在。未来一段时期,中日关系的显著特征将体现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和日本基于“战略焦虑”下的对华制衡(balancing)。
第三,与中日复交时期相比,日本各界推动其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舆论氛围已不复存在,特别是日本政府和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持续拉低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主要推手;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对日舆论也已高度发达且存在复杂结构。中日关系正日趋进入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其未来走向将越来越受到两国舆论与民众情感波动的影响。因此,中日民众情感的显著好转,归根结底又仰赖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回暖”,而两国人文交流与民众交往则会起到增进相互了解、缓解情感对立的作用。在新冠疫情已连续数年阻断中日社会间交往的情况下,当前两国民众情感正处于更加易于受到两国政治摩擦和媒体报道影响的脆弱阶段。
(二)近中期日本对华政策取向的基本判断
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准确把握日本对华政策取向,是思考应对之策的首要基础。从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分析,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对华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日本决策层经过对美国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数年评估,已判定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并把此视为通过“助美制华”、在美国的支持下“保岛”、遏止中国武力攻台、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强国的“机遇期”,其对华政策正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或发生“范式变化”。(37)参见朱锋:《日本的对华战略: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吴怀中:《共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人民论坛网,2022年5月16日,http://www.rmlt.com.cn/2022/0516/647152.shtml [2022-07-3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形成了以“挟美制华”为主轴、以“兼顾中美”为辅翼、以“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为基本内容的“两面下注”战略,其对华政策调整进程与克林顿政府的“新东亚战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以及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对华“遏制与脱钩”政策具有联动关系。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定下了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基调,但同时也采取了不断“敲打”日本与欧洲盟国的单边主义。安倍政府受到了“特朗普冲击”,其对美政策继“尼克松冲击”“克林顿绕行”以来再次处于困惑与观望期,也因此对改善2012年“购岛”风波以来冷却的中日关系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在承袭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政策的同时,致力于修复与日欧盟国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显然已判定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长期化趋势以及美国在遏华战略上十分看重日本的作用。菅、岸田两届政府对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采取了积极回应、配合乃至主动推动的姿态,其对外政策的钟摆由“两面下注”大幅度摆向“挟美制华”一端,进而显示出进一步向“随美制华”乃至“助美制华”一端摆动的态势。
第二,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已经定型,岸田首相将继续推动此前已展示的以“中国威胁论”为基调的强军路线与对华政策;未来数年内,自民党内政治力学和政局变化不大可能对日本对外战略走势产生根本性影响。
岸田出任首相以来,其自民党“宏池会”会长身份是否会使其对华政策带有“鸽派”色彩备受世人关注。但迄今为止,岸田在中美之间进一步向美方“站队”,其对华政策姿态十分强硬。其原因曾被解读为,受制于幕后大佬安倍晋三的影响,抑或出于打赢参议院选举的国内政治需要。2022年7月8日安倍遇刺和10日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使岸田不仅摆脱了安倍的掣肘而且获得了稳定执政的“黄金三年”,其对华政策前景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然而,纵观过去数十年,日本首相的党派出身固然在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型期会产生较大影响,而一旦内外环境与大政方针稳定下来,出自各不同党派的首相均会顺应大势而采取大致相似的对华政策。1993年以来,日本政界曾出现各政党“总体保守化”或“总体自民党化”趋势。而当今的日本政界,各在野党涣散乏力,自民党一党超强,自民党内各派系的对华政策主张则呈现“总体清河会化”趋势。当年与中方实现复交的田中、大平的对华政策,曾立足于稳定周边的地缘安全观、开发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考虑以及淡化意识形态差异的现实主义外交三大基点之上,其深层动因还包括受到“尼克松冲击”后日本朝野上下对美自主意识的抬头以及正处于经济实力快速上升期的自信,而当时反对中日复交的非主流派势力则以亲美、亲台、反共为理念基础。时过境迁,近年来的日本政局与1972年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年非主流的对华政策,如今正以“清河会”为中心汇聚成为政策主流。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经济低迷、人心不稳的沉闷氛围中,日本舆论与选民呼唤强势首相出来引领日本,这一点在冷战后出自“清河会”的两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实现超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两相比较,小泉属于“剧场政治”型的外在风格上的强势,安倍则是欲引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路线上的强势;安倍路线业已在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强国化战略中占据主流地位,无论谁上台也都难以改变其基本方向。
岸田的“宏池会”背景对其“黄金三年”对华政策的影响将局限于战术与风格层面,而不是战略与路线层面。岸田在对外战略上很可能推行一条“没有安倍的安倍路线”,即在“黄金三年”继续推动修宪、强军以及加强西方价值观联盟;在战术层面上,岸田则有可能逐渐显示出自己的执政风格。在当今日本政界朝野、知识精英和舆论场中,试图对“岸田版安倍路线”的对外战略进行纠偏的力量将十分微弱。
第三,日本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动摇其东亚优越意识、危及其领土与航道安全的“威胁”,同时谋求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自身加速走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动力。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面临百年东亚优越意识崩溃和在中日利益博弈中立于守势的趋势。在战略焦虑与危机意识驱动下,日本正谋求在国力对比上的战略守势下采取外交态势上的攻势战略,以攻为守,攻守结合,与中国争夺其心目中的东亚主导权。
日本在由“挟美制华”向“助美制华”迈进的过程中,已把炒作“台湾问题”作为加强日美同盟、巩固美国“保岛”承诺以及防卫航道安全的一石三鸟之举。“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最关键、最敏感、最危险事项。“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不仅仅是安倍的主张,而是日本自民党、决策层及精英层的广泛共识。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将经历较长时间的适应期、战略焦虑期和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强国化的加速期,因而其对华安全战略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轨道。日本正致力于对中国实施“硬制衡”和“软制衡”,前者依靠苦练内功即增强军备以及借助外力即“助美制华”,后者则主要依靠开展“价值观外交”。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试图从两个方向对中日复交原则共识进行“修正”:一是做减量“修正”,即不诚实兑现中日复交时所做出的政治承诺;二是做增量“修正”,即试图在对华外交上“扬长避短”,改变“经济上主动,政治上被动”的局面(38)参见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3—229页。,以美式“普世价值”为依托,在人权、民主、军备、海洋政策等方面向中国提出质疑和要求。日本寻求以西式价值观为纽带构建跨区域乃至全球性的“价值观联盟”,以此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所谓价值观高地。日本正渐趋放弃中日复交文件中载入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两国间“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承诺,而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加以放大并战略性利用。
第四,日本决策层将继续配合美国构建“经济安全”体制,构建排除中国在外的“供应链”。在日本政府“去中国化”政策的诱导和干预下,在未来时期,日企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可能日益受到负面政治影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中日合作将日趋受到限制。
(三)推动中日关系应对之策的思考
基于对中日关系基本特征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势的判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课题是把握全局,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推动中日关系尽可能地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冷静、全面地认识中日关系的总体结构特征,对于两国利益与价值观博弈的长期性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定力,把握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演进的主动权和大方向。
要以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为蓝本,结合当前两国关系的实际,清晰地提示两国关系所应遵守的政治底线,在守护这些共同原则的问题上不应有丝毫的模糊与动摇。
鉴于“安全问题”与“台湾问题”已上升为中日摩擦与博弈的焦点,需要加强对日本对华安全战略及对台海局势干预态势的研究,适时向日方传递预防性信号并采取相应对策。需要促使日方清醒地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背离中日复交原则共识将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日本一旦越过干预台海局势的实质性红线,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问题上,管控分歧、防止军事冲突是中日双方的共同底线,把“海域划界”与“共同开发”区分开来加以推动,依然是一种双赢选择。日本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因而该问题不属于中日磋商的对象。
在两国相向而行的前提下,中日战略对话和“第二轨道”对话势在必行。(39)2022年8月17日,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两国时隔两年半再次举行政治对话,中日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进行了对话与交流。参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举行 外交部:望日本坚持和平发展正确方向》,国际在线,2022年8月18日,http://news.sohu.com/a/577921010_115239[2022-08-19]。其内容可包括:重温不同社会制度的中日之间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之道,围绕两国大国化进程的意图、目标与相互认知进行对话与交流,建立和完善增进安全互信和危机管控机制,探讨重启和开展防务交流的可能性。
第二,积极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地区与全球多边领域合作以及人员交往的发展,同时需要对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
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的有利条件,继续为两国双向贸易与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同时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着更高层次与水平的合作框架转型升级。
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问题,依然是今后中日两国需要应对的两大共同课题。
继续推动东亚系列合作和中日韩合作,共同探讨和推动中日双方都能接受和参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继续加强在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等地区事务上的合作;在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等易于进行合作的全球性课题上加强合作,逐步扩大合作领域与范围。
以新冠疫情缓解前景为前提,积极推动以旅游业为中心的各领域人员往来,加强友好城市、体育、教育、环保、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社会对社会全面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针对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需要适时评估中日高科技领域交流可能受到“新巴统”限制以及其他产业领域的经贸往来受到日方“供应链重组”计划干扰的风险与挑战,对此做好应对准备,与此同时,对于日本的“经贸政治化”举措需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第三,积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新闻舆论界的知识交流,特别是积极推动中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及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国际问题报道界的双边交流。
积极促进中日关系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多层次、多渠道共同研究;通过相互翻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促进历史研究成果的共享进程,向着东北亚共同历史研究的目标迈进。鉴于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对两国的舆论氛围与国民情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日新闻舆论界之间交流刻不容缓。
日本正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开展针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并以“中国正尝试以武力改变现状”为话题展开宣传攻势,这场宣传战已成为中日摩擦与博弈的重要领域;针对此现实,迫切需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日本的恶意宣传予以坚决批驳,对其逻辑与事实错误予以揭露,尤其要致力于把中国的声音传播到日本社会。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是一条不变的真理,而“和则两利”的前提是两国都要有“和”的政治意愿。回首复交50年的历程,中国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实现合作共赢的政策是稳定的,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日本在“助美制华”的道路上究竟会走多远,这将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的一大变数。
五、结 语
复交50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20年的友好合作“蜜月期”和30年的“重新调整期”,后者呈现出“趋冷—回暖”的周期性波动。究其根源,影响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的变化是首要国际要因,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日本经济低迷以及政治保守化是两国国内条件变化要因,两国围绕复交原则共识的博弈和两强崛起竞争是其主要诱因,两国的历史观、利益观、价值观、国际秩序观的碰撞则是其背后的深层根源。
中日关系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历史节点,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更高层次上的新型合作共赢模式,这是两国关系面临的三种可能前景。
中日关系能否在强弱易位的国力与心理调整过程中避免对抗乃至冲突而实现“软着陆”,能否形成政治互谅、安全互信、经济互补的良性循环局面?中日双方能否克服美国的负面影响而由两国掌握相互关系的命运,能否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些问题将是未来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中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