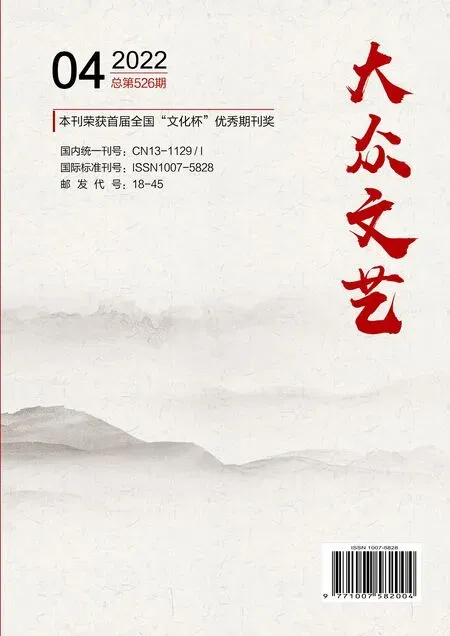国内外著名电视节展的发展经验与声誉建构比较*
王昕业 刘 洋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00)
一、市场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从传统意义上讲,世界各地的广播电视公司除自制节目以外,也会依赖各种购入的节目。自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电视机在发达国家的普及化,对电视节目需求的增加使得电视运营商开始关注节目的国际贸易。但是,仅依靠电视台自身单向度的求购,或卖家的“毛遂自荐”,不但效率低下,而且会产生诸多中介或代理公司增加买家的购入成本。这一市场需求推动了全球最早电视节展的设立,美国电视艾美奖及意大利国际广播电视节均成立于1948年(1957年从广播节目拓展到电视节目),而后慢慢衍生为海外节目亮相、筛选、交易的绝佳平台。到了20世纪60年代,非竞技类的戛纳电视节、北美国际电视节等也相继成立,电视节及国际电视展会纷纷涌现。1976年,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爱丁堡国际电视节创办后,1980年,加拿大班夫电视节也宣告成立,1986年,我国创立了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比成立于2006年的首尔国际电视节和成立于2008年的东京国际电视节更早地打造了亚洲的国际电视节品牌。
最具国际影响力和实力的电视节展基本由北半球国家举办,选择在气候比较适宜的时间里开展活动——每年从3月春季开始到10月秋季结束。同时,大多数国际电视节展与举办城市协同发展,以促进旅游、推广城市文化名片等因素为目的。很大程度上来讲,国际电视节与商品博览会一样,都是以市场为面向、促进生产制作方与购买发行及播映方的沟通和交流。大型的国际电视节面向国际市场,因此举办方通常会利用平台优势提供很多优惠待遇,吸引卖家进驻,或以赛代销。不论是竞赛或非竞赛的电视节展,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必然会吸引大量买家,这样的正面循环使得国际电视节展成为连接商业和文化之间的展示市场、贸易市场和市场节日。班夫电视节的创始人曾说:“每当电视节试图建立一个市场交易的场所时,往往卖家很多而买家很少,我们将创造一个能够让市场交易自然地发生,自由运作的环境。”因此,国际电视节既是区域性节目资源整合的平台,同时也与其他国际电视节展存在着动态的竞争。
比较而言,国际电影节有着更为明确的艺术主题和人文诉求,也更注重于发掘、培养创作者,尤其是导演的艺术个性,同时也以滋养电影节自身的“迷影精神”来鼓励观众在电影节中起到的作用。对于参赛或参展者来说,每一年中错落的电影节日历时常会影响其创作情况,也成了参加电影节的重要参考,但对于大多数国际电视节来说,这些节展虽然公众开放,并会在节展期间进行各种文化表演和节目展出,但其核心参与者大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行业从业者,因而,国际电视节之间的竞争也更具行业倾向,存在于市场领域之内。虽然不同节展在评奖时的确有着不同的文化取向或操作标准,但从结果上来看,不论是分众还是大众类电视节目,电视节展的评奖结果并不能取得如同电影节展评奖那样的戏剧性效果和“聚焦效应”,乃至成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这也是非竞赛性国际电视节展的发展相较于竞赛类节展毫不逊色的原因之一。对比而言,在我国,不论是“飞天”“白玉兰”还是“金鹰”,则更多效法电影节的竞赛制度,一方面,由于国际程度不高,足够大的国内电视消费市场无法有效刺激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恰恰因为区域内部的“内循环”产生的“内卷”而使得优秀的电视作品在三大电视奖项中激烈交锋、在奖项的争夺上也常常互有胜负,这就明显增强了电视节展的“吸睛程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一部作品或主创成员的多次获奖,反而加重了奖项的分量,实现了作品、奖项和电视节展品牌的共赢。
二、国内外电视节展的社会影响力比较
除了市场导向以外,为了稳固地在市场中建立由自己引导的话语体系,国际电视节通过各种活动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并针对时下的热点问题给予回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组织者逐渐发现,仅靠市场效益并不能解决节目编排中产生的种种具体问题,因此论坛随之产生。1963年5月,北美国际电视节(NATPE)举办了第一次有关于“电视节目网络”“政府对节目影响”等有关题目的论坛,随后逐年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更新迭代,目前,北美国际电影节已经发展了覆盖全年的各种活动,可以为会员提供包括教育、网络、专业和技术指导等各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并且为其成员提供专有的行业联网工具和在线服务,并为特殊合作伙伴提供优惠和特别的教育机会。因此,虽然并非竞赛类国际电视节,但北美国际电视节却以优质的论坛项目而在全球闻名,它不但是唯一的服务于全球电视界的美国节目市场,同时也可以提供顶级的新媒体和技术会议服务。
同样的,身在欧洲的爱丁堡国际电视节也以其具有启发性、信息性和娱乐性的论坛和会议而闻名,所有这些会议都是由经验丰富的电视制作人创建的,以确保其具有最高的质量和相关性。疫情之前,爱丁堡国际电视节可以举办超过60场的主题演讲、辩论和大师班,以及其他各种交流机会,并因而可以吸引全球超过2200名以上的专业人士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去。在“名人堂”这一板块的参与者都是ABC、HBO、NBC、Amazon和Netflix等公司的高管,如被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的大卫•爱登堡爵士、英国大明星休•格兰特、艾美奖获奖作品《副总统》(Veep)编导等。而在去年的演讲中,BBC新版纪录片《文明》的编剧大卫•奥卢索加则回应了2020年发生了乔治•弗洛伊德被残酷谋杀和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旗帜下联合的全球运动。对于他的呼吁,广播公司和历史学家也认为,种族主义已导致英国电视行业中形成了少数的“迷失一代”。可见,国际电视节的高端论坛已经不仅限于行业内的专业性演讲,而是针砭时事,立足当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肩负起监督和批判的社会任务,其高抬高放的文化站位,使国际电视节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生态中对于社会命题发声、发言、发轫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国际电视节不仅是各国电视节目的交流场所,同时还可以通过强强联合,进行跨地域的节展合作。例如东京国际电视节就与戛纳电视节合作,于2009年成立了“MIPCOM日本戏剧买家奖”,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每年固定的活动之一。对比国外举办的国际电视节展,我国的电视节还尚未承担过多的社会义务和社会功能,虽然上海国际电视节、金鹰电视艺术节等活动也举办了很多高端论坛,但不论对产业的实际影响,还是因为内容站位而产生的“破圈”效应都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国内节展更倾向于以串烧晚会、明星红毯、视频直播等方式引发社会关注的“爆点”,这就使得文化节展的“文化味”转向了“娱乐风”,难以造成严肃的社会影响力和有效的主题文化传播。节展和城市功能的组合拳打得不够力道,不论是对城市名片的提升还是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作用都不甚清晰。而且国内分类清晰的电视节展在内循环中尚无法做到联合合作,与国外的电视节展的合作就更显得方式单一,难以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互促的模式循环。
三、以声誉建构的文化地位
某种程度上来说,声誉也是国际电视节展市场交易过程中无形的筹码。相比于爱丁堡国际电视节对种族问题的批判,2021年美国金球奖被《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双重夹击,爆出金球奖的评委协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行为,经证实,金球奖的组织、职业道德、颁奖规则乃至评委自身的职业资格都具有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曾对金球奖展开调查,最终认定金球奖颁奖典礼存在严重舞弊,直到1973年,金球奖完成了一些改革之后,颁奖仪式才再次获得电视转播。不论得失与否,金球奖与国际电视节展在建立自己的声誉体系时,都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尤其对于竞赛类的电视节展来说,其核心因素——奖项的设置,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金球奖虽然仅有87位评委成员,且被外界揭露出了劣迹斑斑的评审过程,但在结果上,却能一直紧跟奥斯卡千余位评委的风向而动,作为前哨站,在颁奖日历上成为重要一环,从而受到明星们的欢迎,为了能给自己的风评造势,获得更大的舆论和声誉影响力,愿意参与到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之中。而金球奖组委会更乐见其成,以电影明星的广泛声望带动电视明星的全民影响力,相互成就,使得星光熠熠的颁奖典礼,成为类似于国内金鹰奖“金鹰女神”“歌舞表演”一类的“表演盛宴”而受到了全球瞩目。
早在2006年厦门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已经有专题研究了金鹰电视节的“声誉建构”问题。在绪论中,他指出:
五年过后看现在的金鹰节,华丽依在,却负重累累。鹰击长空,却与“越飞越高越精彩”的宣言渐行渐远,假票、黑幕、新闻垄断、组织不力、本地化、失血严重等一连串问题缠在这个五岁金鹰的头上,金鹰节的各个相关方都表示出对金鹰节的不满,“这浓缩了一个年度电视创作的长卷,在展开接受观众的检阅,但这却是一场无法敬礼的检阅。……没有一个年度的风采,更没有一个属于年代的脚印,于是一个年度又沉沦在年复一年礼节性的繁华中。”
然而,论文及其中引述的争议,却随着电视节初期的探索逐渐淡化。金鹰节的发展逐渐围绕着奖项在大众性和权威性的平衡之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并随之建立起稳固的国内声誉。今年5月21号,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也公布了全部的入围名单,纵览入围名单,可以发现,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呈现压倒性优势,《觉醒年代》《大江大河2》《山海情》等主旋律或献礼剧,不论在播放热度、社会影响和舆论关注上,都非常让人信服。而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与飞天奖、金鹰节等奖项的近年归属,也从结果上验证了电视节展的评奖如何在时间积淀后反过来型塑了其声誉建构,以权威性及获奖作品在经年累月的积淀后获得的公众认可,构成了电视节展本身声望力的支柱。
观察今年的白玉兰奖评委会名单可以发现,除了中国电视剧单元由创作界、学界和知名演员共6人的大陆评委以外,海外电视剧单元则有法国和西班牙两个海外评委,纪录片类别的三位评委中,也有日本和法国两位外籍评委,动画片类别则有新加坡与英国评委。总体来说,我国的电视节展有着与国际接轨的清晰意识,不过,在评委阵容与组织程序上,上海电视节的阵容规模和分量,仍稍显逊色,与国际其他电视节相比,也还有一些值得“取经”和学习的地方。
四、疫情之下的电视节展转型
过去一年中,全球的国际电视节因为疫情受到极大冲击,电视节目交易市场的版权买卖、流通和发行都面临阻碍,基于实体交易市场的萎缩,流媒体的平台业务借机发力,Disney+、HBO MAX、奈飞、亚马逊等流媒体平台纷纷扩展业务范围,对于卖家来说,转移线上发行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止损方式,但对于国际电视节所建构的全球发行体系来说,线上发行的方式却绕过了既有的系统,对既有模式产生了挑战。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国际电视节展将丧失其主导市场方向的能力,反之,通过一定的功能升级,国际电视节展完全可以在所谓“上层建筑”的层面上集中发力,站位于解决行业痛点的考虑,从制定决策和政策的角度,拥抱流媒体平台,不将其视之为竞争,而是以吸纳的角度,扩充为自身的资源储备。事实上,这也是国际电视节展目前的发展趋势。
受到疫情在西方世界反复的影响,电视节的线上转型,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国际电视节展以交易市场为范畴,注重自身作为权威话语的“发令官”,以及担忧新媒体及流媒体平台绕过其核心地位的因势利导的规划结果。相较而言,我国的金鹰电视节等大型节展,反而因为疫情管控良好等因素,得以保留了实体线下活动,仍较为重视节日庆典和喜庆氛围的营造,顺延“大奖花落谁家”“晚会精彩纷呈”等传统模式的成功经验,而网络会议、网络交易等平台搭建,也比较依赖各种互联网软件,且行为组织方的主体性不明晰,个人、商家、公司之间的互动较多,而非将电视节展作为一个综合平台,把控各方资源的整合和分配,进而掌握平台搭建所得的红利。究其原因,从大环境来说,有政府对疫情成功防治的“顺风车”可搭,此前办会模式在内循环过程中的“增值福利”尚未被完全开发等因素外,西方的电视网络、新的发行制作平台、流媒体播放平台等未参与到国内竞争,也使得“台网融合”的中国模式并未承受太过强烈的市场阵痛,仍处于相对平缓的市场增长期有着一定关系。
尽管疫情肆虐欧洲,2020年的戛纳电视节依然坚持举办。电视节取消了开幕走粉毯仪式,但仍邀请了接近1000位电视人参与节展活动,并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展映方式。例如在疫情之前,2018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戛纳电视节后,2019年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约有400名中方代表参与,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五洲传播中心、湖南卫视等在内的50余家中国影视机构参展。电视节继续往年的“聚焦中国”等系列活动,内容包括“中国联合展台”新形象发布会、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中国内容推荐会”之沪产内容推荐会、“中国内容推荐会”之芒果TV内容推荐会、戛纳华语派对等在内的4场主体活动以及2场专题活动,是中国连续第16年在戛纳电视节设立联合展台,为中国影视作品的发展搭建了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也成了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结语
国际电视节展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对其进行概括与综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虽然全球经受了疫情打击,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不论新媒体、流媒体的发展如何,电视节目仍然是,且会随着新媒介平台的发展,更加成为传播、形塑、影响全球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于此,国际电视节展作为电视节目展出、交易、发行、放映的抓手和平台,就愈加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中国的电视节展,也更加需要放置于国际电视节展的队伍中,进行比较研究和路径探索。通过对历史的简要梳理,本文指出,国际电视节展正在面临着融媒体转型,其市场交易为导向的节展理念,更需要国内节展对自身进行有效的媒介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吸取国际先进经验,依靠旅游、论坛、跨地域合作等形式,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与文化命题,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同时,在培养与媒体的共建关系时,反思自身建设的种种问题,及时改良,同步纠错,对会员评选、组委会构成、奖项规则等各项流程严把质量关,借鉴其他国际电视节展和重要奖项的得失,为中国电视节展的未来,构建理论自觉和路径发展。
注释:
①“Banff Preps 1st Festival covering Made-for-Tv Pix”Variety April 25,1979,59.
②严赛男.《金鹰节研究》.厦门:厦门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