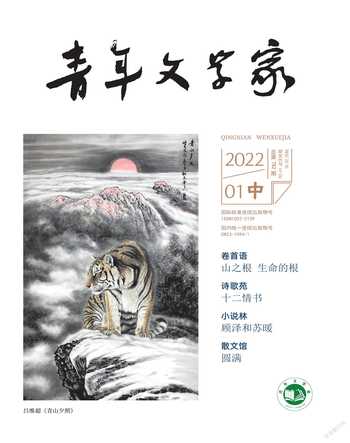从李泽厚的观点看汉大赋的美学价值
栾艺铭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汉代最为典型的文学形式当属汉赋,而其中最能反映汉代鼎盛时期精神风貌的汉赋类型则是以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为代表的汉大赋,其体式宏大、气势雄阔、意象繁富、文采华茂,形成一种独特的巨丽之美。然而,汉大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它为汉代文坛增添了生命与活力,却并未成为后世文坛的主流,甚至受到了诸多批判。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无可否认,但对于其美学价值的认识却略显不足。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李泽厚对汉大赋的美学价值给予了较高评价,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汉大赋的美学价值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对汉大赋美学价值的再认识
对汉大赋的反思与批判最早是从汉赋大家扬雄、班固等人开始的,早年扬雄也曾推崇司马相如的大赋,后来却将作赋视为雕虫小技。扬雄意识到了汉赋之美,但这种美在他看来并不具有积极作用,因为这些赋多是“丽以淫”而非“丽以则”。他站在儒家伦理道德及社会功利的角度看待文学价值,认为文学在追求美的同时更应符合儒家圣人之道,而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创作都不符合这样的要求。班固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对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创作的大赋持批判态度,因为这些赋已失去了讽喻作用。虽然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班固又认为扬雄将司马相如的赋视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是不准确的,“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但无论他如何评价司马相如,其核心都是强调文学的讽喻劝诫作用。
扬雄、班固的观点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西汉末年至东汉,社会经历了巨大动荡,昔日的盛世之景已不复存在,此时再通过文学大肆宣扬奢靡之风而轻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便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他们都将儒家思想视为正统,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以此来批判此前的汉赋创作。然而,汉大赋的重要价值恰恰不在于教化层面而在于审美层面。李泽厚视汉赋为一种脱离原始歌舞的纯文学,相较于先前多与歌舞融合、具有较强实用目的的文学形式,汉赋作为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更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在李泽厚与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一书中也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再只强调它作为政教伦理宣传工具的价值了。”所以仅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评判汉大赋的价值显然是有所偏颇的,我们有必要从美学层面重新认识汉大赋的价值。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李泽厚提出了“积淀说”,即美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因而,在考察汉大赋的美学特色时,不仅要关注其形式,更要关注其中积淀的社会内容。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体系:北方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更注重理性精神;南方文化体系以屈原的楚辞为代表,保留了较多原始神话巫术的因素,更偏于浪漫主义。而汉代起源于南方楚地,延续了楚地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李泽厚看来,虽然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南北艺术传统有日渐融合的趋势,但追根溯源,汉代艺术中流淌着的仍然是楚汉浪漫主义的血液。因而,从儒家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待汉大赋存在认识上的错位,不可能真正挖掘出汉大赋的美学特色。
除了文学价值方面的争论,对汉大赋的批判还集中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相较于后代文学,汉大赋确实在艺术技巧上不够成熟,为了追求繁复巨丽之美,便大量堆砌辞藻,极尽铺排夸饰之能事,其中多生僻艰涩之字,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这种现象在汉大赋中非常普遍。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同样指出了汉大赋在表现形式上堆砌、重复、拙笨、呆板的特点,但是,他反而将其视为汉代文学的美学特色。李泽厚将汉代艺术的基本美学风貌概括为气势与古拙,而这种气势与古拙之美同样表现在汉大赋上。这种独特的美是在无意识下形成的,是文学艺术在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等到对文学创作技巧的探讨逐渐丰富,这种天然的稚拙之美便也会随之消失。所以汉大赋是独属于汉代的文学形式,对其美学价值的考察也必须在汉代独特的文化语境下进行。李泽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汉大赋的艺术性予以了较高评价。下文将主要从楚汉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气势与古拙之美两方面具体分析汉大赋的美学价值。
二、汉大赋中蕴含的楚汉浪漫主义精神
汉发源于楚地,楚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以屈原的《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保留了较多原始氏族社会的巫术神话,其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弥漫着奇异的想象和炽热的情感,这种特质延续到汉文化中,使得汉代艺术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样蕴含在汉大赋中。
这种浪漫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汉大赋作家的创作态度上。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汉大赋之所以体制如此宏大,内容如此繁复,意象如此稠密,从创作动因上看,是因为创作者有一颗能包容宇宙、通观古今的“赋家之心”。汉大赋的创作者总是试图穷尽一切可能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容纳于自己的视域当中,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而相较于诗词,汉赋作为一种自由度較高、延展空间较大的文体,也为这种创作诉求提供了便利。
要想拥有一颗“赋家之心”,需要有极宽广的胸襟、极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向外部世界探索的极大热情。人之视线所及毕竟是有限的,但精神空间所能达到的广度却是无限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有征服外部世界的精神气魄。曾有人批评汉大赋在情感表达方面存在不足,其实不然。实际上,汉大赋当中蕴含着极其充沛的情感,只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同于儒家,儒家强调通过精神的内省实现道德的完善,所以对于情感的表达多是含蓄内敛的,受儒家理性精神影响的作家多侧重表达内心世界的意趣与情感。而汉大赋在情感表达上是非常外放的,创作者将世间万物铺天盖地地陈列开来,表现出的是征服外部世界的自信,其情感基调是愉快、乐观、积极、热情洋溢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楚文化中原始野性与活力的遗留,其精神内核是一种楚汉浪漫主义。
司马相如提出的“赋家之心”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在《子虚赋》中,司马相如借子虚之口描绘楚国的云梦泽,相继写了其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高、其埤、其西、其北、其上、其下的景物,仅从这些方位词便能看出司马相如试图将天地万物都容纳于心的宽广胸襟与壮志豪情。虽然在结尾处,司马相如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了子虚夸耀的言行,含有讽谏君王不应过度骄奢淫逸之意,但这一部分毕竟只占据少量篇幅,并不影响读者充分感受楚国地域之辽阔、物产之丰饶,展现出来的仍然是一派盛世气象。儒家的理性精神固然对汉大赋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并不足以压倒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调。
汉大赋不仅延续了楚文化传统,更是大汉帝国盛世风貌在文学领域的显著表现。只有身处盛世,才能以如此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的心态向无限广袤的外部世界探索,并拥有将之征服的雄心。司马相如是在汉大赋创作领域成就最高之人,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正是汉朝最繁荣鼎盛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尽情描绘天下之富丽辉煌是合理的,这代表了对统治者功绩的肯定,也代表了对现世美好生活的肯定。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与原有楚文化逐渐融合,使汉代艺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特色,但儒家所提倡的文学的讽喻作用依旧没能成为汉大赋的主要创作目的。
然而,到了扬雄和班固生活的时代,汉代已呈衰颓之势,虽然他们都学习司马相如的赋,但学到的更多的是模式,而非精神内核。对于社会现实的忧心使得他们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成分不可避免地减少,而增添了更多从儒家社会功利角度出发的理性思考。单从美学层面上看,失去了浪漫主义精神特质,失去了楚文化遗留下来的原始活力,汉大赋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汉大赋是独属于汉代的艺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楚汉浪漫主义才能在审美意识领域占据主流。等到汉代灭亡,汉大赋自然也就随之走向衰落了。
三、汉大赋的气势与古拙之美
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指出:“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气势与古拙之美同样可以用来概括汉大赋的美学特色,这种独特的美与其中蕴含的楚汉浪漫主义精神是相通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希腊艺术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正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同样,“正常的儿童”可以借用来形容汉代的艺术,它是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不成熟的,但正是这种不成熟的、稚拙的状态赋予了汉代艺术独特的魅力,并且它只属于汉这一特别的时代。
在中国文学史中,汉大赋尚处于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已经脱离了原始歌舞,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迈出了从杂文学向纯文学演进的第一步。汉大赋在文学创作技巧方面显然是不够成熟的,但它也相应地较少受到各种规矩的束缚,正如“正常的儿童”一般,呈现出天然、拙笨却又生命力旺盛的状态。在这一时期,儒家理性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相对有限,汉大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从楚文化远古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原始活力与野性,展现出古拙与气势结合之美。
汉大赋体制之宏大,是后代许多文学形式所不及的。诗词由于字数和结构的限制,往往会采用典型的意象来表现事物,且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但这些后代文学中常见的表现方式都与汉大赋无关。在汉大赋中,为了展现地域之辽阔、物产之丰饶、国力之强盛,主要的方式是铺陈、排比、罗列,将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以及所能想象到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现在读者眼前。汉大赋的创作者常使用同一偏旁的一系列字来描绘某种事物,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同一偏旁的字往往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为例,写到水流,一整段出现了数十个三点水旁的字;写到崇山,一整段又出现了数十个山字旁的字。其中很多字相当生僻,让人难以理解,有过度堆砌辞藻之嫌。从创作技巧上来看,这种表达方式呆板又笨拙,却展现出极强的气势,给欣赏者在视觉乃至心灵上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力。而这种气势又不会让人产生压抑之感,其中蕴含的是蓬勃的生命力,是向外部世界探索并试图将其征服的信心与力量。这种气势与古拙结合之美正是汉大赋魅力之所在,是汉大赋区别于后代其他文学形式的独特美学价值。
而这种气势与古拙之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的,其精神内核是楚文化延续下来的浪漫主义,其主题是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其背景是文学艺术在发展早期阶段的不成熟状态,这几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汉大赋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独特的美学风貌是后代文人难以通过模仿刻意创造出来的。司马相如为汉大赋提供了一定的模范,后代作家多模仿其体式,使汉大赋的创作逐渐模式化。而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儒家理性精神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也日渐深入。西漢末年至东汉年间产生的汉大赋作品,其中的气势与古拙之美已在不断减弱。最终,随着汉代的终结,汉大赋的生命力不复往昔。
文学的发展总是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但不成熟也有不成熟的美,且往往更加无可取代。用后代的文艺观看待早期文学,人们容易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因而,要想考察某一时代文学的美学价值,必须结合这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这正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致力于进行的探索。李泽厚以其“积淀说”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审美意识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其中很多观点都对我们在审美层面理解某一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探讨汉代艺术及其审美意识时,李泽厚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楚汉浪漫主义”以及“气势与古拙”,从这两点切入,我们可以对汉大赋的美学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298650118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