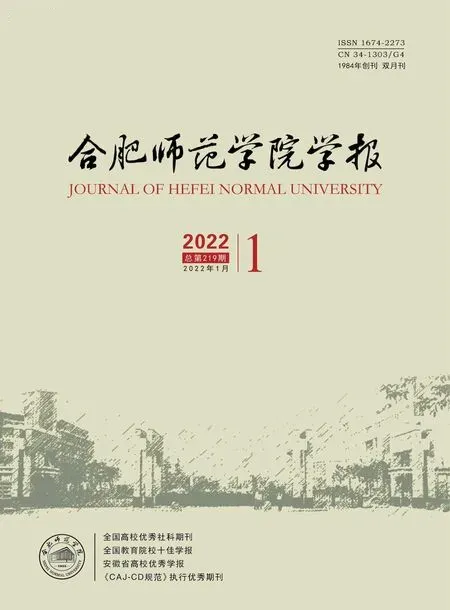明清文人篆刻艺术思潮流变及皖籍印人之贡献
武 蕾,余熙文
(合肥师范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文人篆刻产生的背景
众所周知,秦汉印和明清文人印构成了古代篆刻史的两座高峰。在文人篆刻兴起之前,印章主要体现的是实用价值,即“作为人与人交接上的信用的保证”[1]8,其中存在着古人朴素的审美观,却尚未形成系统的印章艺术理论。
至少在元代以前,人们并没有将篆刻纳入艺术的殿堂。原因有二:其一,印章文字的限制。从汉字字体演变和书法史的角度来看,秦代以降,隶、草、行、楷书次第成熟,篆书基本告别了实用书写。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的自觉以后,历代书法经典也多为草书、行书和楷书作品。因此,人们对篆书书体的陌生,造成魏晋至清代中叶之前篆书书法佳作的乏善可陈。严格来说,隶书也经历了同篆书类似的遭遇。其二,篆刻工具材料的限制。金属印材是早期印章的主要载体,采取铸或刻两种方式,作者多为专门的工匠,文人士大夫难以介入篆刻创作。即使玉、牙、角作为印材,在今天看来也绝非一般篆刻工具所能应付。
沙孟海提出印学(或称篆刻学)成为一种专门学术“是近七、八百年的事”[1]89。回顾印学史,篆刻能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首先解决的就是以上两个问题。首先是印章材质的改变。元代王冕率先用花乳石治印,开启了石材作为印章材料的先河。此后,更有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等作为印材普及,这些石材的共同特点是质地软硬适中,便于奏刀,为文人参与治印提供了操作上的便利。其次是篆刻艺术理论的出现,包括对印章文字的认识和印学观念的产生。宋代米芾《书史》《画史》已经有关于治印和用印的散论。最早系统研究篆刻艺术理论的当属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他和赵孟頫对汉印质朴审美观的倡导,“在汉魏唐宋与明清篆刻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2]31。
可以说,印材的改良和篆刻艺术理论的出现,反映出文人对印章制作的浓厚兴趣,为明清文人篆刻实践及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明清文人篆刻艺术思潮流变
艺术思潮针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当规模的较大群体而言”[3],比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涵盖的范围更广,往往包含多种流派和创作方法。艺术思潮的演变,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以及兴衰变化的缩影,明清篆刻艺术也不例外。
(一)明末清初篆刻艺术思潮——“印宗秦汉”
明初的印坛相对沉寂,直到明代中叶,文彭、何震的出现标志着文人篆刻兴盛的开始。从“文、何”到清乾隆时期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篆刻,可视为文人篆刻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真正确立期。这一时期,篆刻艺术主导思想是回归秦汉印的传统,可将其概括为“印宗秦汉”或“宗法汉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宗秦汉”观念的确立和实践,存在两个关键的支撑条件:
一是理论先行。史实表明,吾丘衍不愧为篆刻艺术理论的先行者和预言者,其《学古编》中《三十五举》前十七举围绕篆书源流和技法展开讨论,以今人眼光看,涉及的只是篆书学习的常识性问题,且非专门针对篆刻用字,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篆书的陌生,以及作者对篆法在篆刻创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后十八举重点介绍了汉印特点,首先对“摹印篆”即汉印文字正本清源,指出其“篆法与隶相通”[4]14,因为时人对缪篆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其次是对汉印的用途、形制、结构、章法等艺术特点进行详细解说,并对后人在印章制作中出现的有违古法的乖谬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总之,在文人士大夫对篆刻产生浓厚兴趣的时代背景下,吾丘衍的论著,一方面引导人们重视篆书和篆法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确立了汉印传统在文人篆刻实践中的基础地位。
二是集古印谱大量问世。明末,有顾从德《集古印谱》(1572年)和《印薮》(1575年)、杨元祥《集古印谱》(1587年)、范大澈《集古印谱》(1597年)、郭宗昌《松谈阁印史》(1615年)等。另有摹刻古印谱,如《考古正文印薮》《集古印范》《秦汉印统》《集古印正》《古印选》等,参与摹刻的作者中,不乏何震、苏宣、甘旸等当时的篆刻名家。这些印谱,以汉印和仿汉印为主,折射出当时复古的篆刻艺术思潮,也为印人熟悉汉印,进而开展“印宗秦汉”的篆刻实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末篆刻实践在拟古思潮和大量古印印谱刊行的条件下不断向汉印传统回归,逐渐成为当时文人篆刻群体遵从的创作共识。这一时期的印作,从刀法、篆法、章法等不同方面,体现了创作者对汉印形式特点的把握。如何震篆刻长于刀法,其线质与汉将军印风格近似。受业于文彭的苏宣,既取汉印之形,又追求个人风格的变化。清初,如皋派邵潜、黄济叔、许容,吴门派顾昕、沈世和,徽派程邃,虞山派林皋等印人群体都在规模汉印传统,不同流派印人在把握传统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加以创新,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丁敬。
从总体上看,至康乾时期,文人篆刻在“宗法汉印”的艺术思潮下逐步确立了规范,汉印原型在篆刻创作中的基础地位已牢不可破。
(二)清中期篆刻艺术思潮——“印从书出”
作为浙派领军人物,丁敬以切刀法奠定浙派篆刻的独特风格。丁敬的追随者众多,主要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与丁敬并称西泠八家。纵览西泠八家的总体风格,呈现出切刀法不断强化的趋势。通过独树一帜的细碎切刀法来体现金石意趣,使浙派在印坛独领一时风骚。但这种刀法被运用到极致而成为立派之本后,又为浙派的过早衰落埋下了隐患。如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跋》中批评浙派赵之琛“偭越规矩,直至郐尔”[4]596,更有其追随者故步自封,最终因艺术风格的僵化而淡出印坛。
公允地看,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前期印人,是早期文人篆刻“印宗秦汉”的集大成者,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而浙派衰落的原因,除了程式化的刀法外,更重要的是与篆刻艺术发展的规律相违背。换言之,“印宗秦汉”的艺术思潮在此时已不能满足文人篆刻发展的需要。
在浙派篆刻风格流行的同时,邓石如逐渐崛起,他将自己篆隶书法的意趣融入篆刻,使人耳目一新。篆书书法的中绝,造成清前期如王澍等习篆者,多陷入误区。“在清代书坛上,写篆书能够突破王澍一派的笼罩,广泛汲取秦、汉碑刻的不同特点加以融合提炼,邓石如是第一人。”[5]其后出现的篆书名家如孙星衍、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等,无不受到邓石如书法的影响。故将邓石如作为清代篆书艺术中兴的里程碑式人物,的确符合史实。邓石如在遍临先贤印作之后,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篆刻风格。与浙派注重通过刀法表现金石气的做法不同,他凭借自身篆书造诣,将婀娜多姿的结构和婉转灵动的笔法融入印章的刀法、篆法和章法中,形成了在印章中表现篆书笔意和书法整体趣味的风格特征,从而突破了当时“印宗秦汉”印风笼罩下“印中求印”的创作模式。这一全新的创作风貌,将个人的书法修养引入篆刻创作,迅速开启了新的篆刻艺术思潮,魏锡曾将其概括为“印从书出”[4]596。此后,吴让之等人的实践对“印从书出”的创作方法加以完善,进一步丰富了印章的书法表现力。
(三)清晚期篆刻艺术思潮——“印外求印”
“印从书出”的创作思想很快被发扬光大,但人们并不满足于此。在清代中晚期学术风气的催生下,赵之谦又有“印外求印”论,“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成为晚清篆刻艺术思潮的两翼,最终将明清文人篆刻推向了历史的顶峰。
赵之谦是一位篆刻实践和理论并重的艺术家,他博学多才,广泛涉猎书法、绘画、金石考据之学,与魏锡曾、胡澍、沈韵初等学者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叶铭《再续印人传》评其曰:“于学无所不窥,读书丹黄灿然,书画奇异天成,刻印能夺完白之席而独树一帜。”[6]313按胡澍《赵撝叔印谱序》记载,赵之谦博采众家之长,既兼收并蓄徽、浙两派之长,又力追秦汉。检视赵之谦的印作,可以看出其具备的深厚传统功底,而胡澍所言之“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4]608,正是其创新之处,也就是赵之谦在《苦兼室论印》中提出的“印外”[2]329之说,实际上指治印者应当广泛求索印章之外可化为篆刻创作的艺术元素。叶铭《赵撝叔印谱序》将这一观念总结为“印外求印”[4]610。
“印外求印”论是赵之谦总结之前文人篆刻发展规律的结果,他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对皖、浙两派的精辟分析中,提出了“巧”“拙”之论,进而“上升到流派存亡的高度”[7]。深入研究赵之谦的印论可以发现,赵之谦从批评家的视角总结了以往文人篆刻的得失,并敏锐地认识到“印宗秦汉”和“印从书出”已经不能满足篆刻艺术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赵之谦提出了“印外求印”论,意在引入更多的艺术元素支撑文人篆刻创作的深入推进。赵之谦篆刻创作所取法的印外资源,各种石刻文字、吉金文字无所不包,赋予文人篆刻作品前所未有的丰富意象。这样看来,叶铭认为赵之谦的篆刻功夫超过邓石如,绝非溢美之词。
“印外求印”论极大影响了当时的篆刻创作,其中在吴昌硕、黄牧甫的印作中有最为突出的表现。前者的印外取法以砖瓦、封泥、碑额等石刻为主,后者主要取法吉金文字。
三、皖籍印人在明清文人篆刻中的贡献
异彩纷呈的明清文人篆刻,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发展特征,大体看来,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更确切地讲,集中在今浙江、江苏、安徽一带。究其原因,应归于发达的区域经济和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等因素。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发现皖籍印人在明清文人篆刻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其做出的贡献做一梳理。需要说明,苏、皖两省是清顺治年间由原江南省划分而来的,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指皖籍包括了划分之前属于后来皖地的印人。
(一)皖籍印人有篆刻艺术开宗立派之功
明清时期,因艺术风格相同或相近而形成了众多的篆刻流派,且因为篆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篆刻流派的划分也越来越复杂细致。宗派的建立,有利于印人们取长补短,进而推动篆刻艺术的繁荣昌盛。
篆刻流派始于明代“文、何”之时,当时有“三桥派”“雪渔派”“泗水派”等之说,最早见于明末徽州休宁人朱简的《印经》。
“三桥派”以文彭为首。文彭,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但文彭传世印作极少,且伪作较多,而自称“三桥派”的印人,多有其名而无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三桥派”似乎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篆刻流派。
名副其实的篆刻流派最早当属以休宁人何震为首的“雪渔派”。沙孟海先生指出:“从嘉靖到明末约有一百年,程邃未成名以前,徽州及徽州以外各地印学家风起云涌,除有少数径师文彭,以‘文派’相标榜外,其余大多数人则继承何震的衣钵。”[1]104何震暮年更有自辑《何雪渔印谱》传世,为流派传承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开创了印人自辑印谱的先河。
“泗水派”的开创者苏宣,号泗水,徽州歙县人。文彭、何震的篆刻,都对苏宣产生了影响,苏宣结合二人之长,在取法汉印的同时表现出意法相融的韵味,有自辑印谱《苏氏印略》,叶铭评价其“与文寿承、何长卿鼎足称雄”[6]262。朱简《印经》所列“泗水派”成员还有程远、何通等人。
明末还有歙县人汪关的印风,被称为“娄东派”,后有林皋、沈世和等人被认为是“娄东派”篆刻名家。
明中晚期的篆刻流派之分,大体有以上几类。从中可以看出,皖籍印人占了主流,成为印坛的主导者。何震、苏宣、汪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自流派的开创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篆刻风格和创作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朱简等印人对篆刻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而朱简恰又是安徽休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皖籍印人对文人篆刻开宗立派,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贡献。
翟屯建认为,朱简的“流派说”是在印学初兴时人们欲“树帜称尊”的背景下提出的,“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学说”[8]217。但从中国传统艺术各门类发展史上看,艺术流派分类意识的出现,就已经体现出这门艺术的创作群体对审美理想的个性化追求。
清代,随着篆刻艺术的昌盛,印人群体数量激增,篆刻流派的概念愈加清晰,流派风格对篆刻创作的影响力也更为明显。公认的流派中,安庆怀宁人邓石如创立的“邓派”(亦称“皖派”),徽州黟县人黄牧甫创立的“黟山派”,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邓派”与“浙派”并立为清中叶文人篆刻的双峰。
(二)皖籍印人有篆刻艺术思潮引领之功
明清篆刻艺术思潮的演进,离不开皖籍印人的努力,具体表现在篆刻实践、篆刻理论、编辑印谱三个方面。
元代赵孟頫、吾丘衍对篆刻回归汉印传统的呼吁,终于在明中叶至清代中期之间完成。“宗法汉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人们对古印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步实现的。落实到实践中,文人篆刻的技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杂乱无章到规范有序的过程。何震以“执刀直冲”的刀法名扬于世,一矫工匠治印习气,建立了汉印临摹技法的基本范式。他以单刀法刻制边款,也被认为是一种创造。在人们对刀法普遍生疏的情况下,称其为“历史上第一位自觉地运用刀法创新的篆刻家”[9],的确恰如其分。苏宣传承何震刀法,但与何震偏向仿汉将军印的视角不同,他有着更广的汉印取法范围,并在《印略》序言中明确提出“始于摹拟,终于变化”[4]471的创新思想。朱简“短刀碎切”法,影响了后来浙派篆刻风格。程邃善于表现印章文字的笔意,与斤斤计较于刀法、篆法规范性的时风不同,他已经将仿汉印的创作推向了笔意表现的新境界,“达到当时印艺上的一个新的高峰”[8]139。邓石如凭借“引书入印”,开创了“印从书出”的创作方法。黄牧甫篆刻取法金文表现出的光洁之美,是对“印外求印”论的成功实践。
现存明清皖籍篆刻家的理论著述,仅据翟屯建对徽州印人的统计,就有何震《续学古编》、徐上达《印法参同》、潘茂弘《印章法》、朱简《印品》和《印经》、汪维堂《摹印秘论》、戴启伟《啸月楼印赏》、黄宾虹《叙摹印》和《古印概论》、汪启淑《续印人传》、叶铭《广印人传》等[8]190-214。这些著述中,不乏富有远见的观点,启发了后来的篆刻艺术思潮。例如朱简强调印文的书法美,虽然之前已有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但贵在朱简系统阐述了篆刻刀法应表现书法笔法的美学思想,黄惇先生将其总结为“笔意表现说”[2]112。这一观念,后被程邃加以实践,最终在邓石如及其流派印人中发扬光大。
印谱的刊行,对篆刻艺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明清大量刊行的印谱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集古印谱,另一类是集时人之印谱。其中,皖籍印人自辑或参与编辑的印谱俯首皆是。如顾从德(今上海人)委请歙县人罗王常编辑的《顾氏集古印谱》,使众多印人认识了古铜印的真正面目,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本集古印谱”[2]61。再如居于杭州的歙县人汪启淑,辑《飞鸿堂印谱》共五集,汇集了当时印坛名家印作3515方,不啻于当今的全国性篆刻大展,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艺术交流的作用,也为后人研究篆刻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皖籍印人有篆刻艺术承启发扬之功
姑且将上述艺术思潮作为明清文人篆刻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皖籍印人都起到了承前启后、将篆刻艺术发扬光大的积极作用。
文人篆刻艺术确立时期,何震作为皖籍印人的开山之祖,一方面继承文彭,另一方面力除元明以来的陈规陋习,将印作格调回归正统,成为晚明印坛的领袖。周亮工在《书程孟长印章前》中认为,何震出现后,“印章一道遂归黄山”,进而徽州“人而能为印”,久之“人而能为主臣”[6]43-44。可见,何震不仅带动了一大批印人,还使徽州篆刻的地位一跃而升,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据统计,自明嘉靖至清末民初,仅有据可查的徽州印人就有242人,其中清康熙之前74人[8]282-289。故可说,皖籍印人从文人篆刻初期就形成了群体,并始终以群体的力量作用于篆刻艺术发展而不曾中绝。
清中期,浙派篆刻如日中天之时,“印宗秦汉”的创作方法面临着危机,篆刻艺术发展的规律客观上要求印学思潮的改变。“邓派”篆刻宗师邓石如将自己的篆书书法风格融于印章中,以崭新的面貌和全新的创作方法傲然挺立于印坛,他的“印从书出”,为篆刻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一创作思想的生发推动了当时篆刻的全面革新,其影响力历久弥新,直至当代。
晚清,倡导“印外求印”的赵之谦,虽不是安徽人,但也受到皖籍印人的影响。黄惇先生分析认为,邓石如“印从书出”论是赵之谦“印外求印”论的来源之一,赵之谦的印章创作观,“是经过综合浙、皖两宗印人审美观的有价值部分后形成的”[2]329。文人篆刻鼎盛时期的晚清印坛,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篆刻和以黄牧甫为代表的“黟山派”印人,综合了前贤积累的印学财富,形成了各自的篆刻风格。因黄牧甫长期客居广州,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广东印学的发展,形成“粤派”篆刻。
四、结语
明清文人篆刻随着印材改良、技法进步以及审美趋向等因素的变化,历经“印宗秦汉”到“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的艺术思潮流变。明清皖籍印人受书法文化、徽州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领域有造诣者众多,成就卓著,在明清文人篆刻发展中有开宗立派、艺术思潮引领以及承启发扬的重要贡献,也为明清之后篆刻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在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通过厘清明清文人篆刻发展史,阐发皖籍印人所做的贡献,发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总结其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促进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