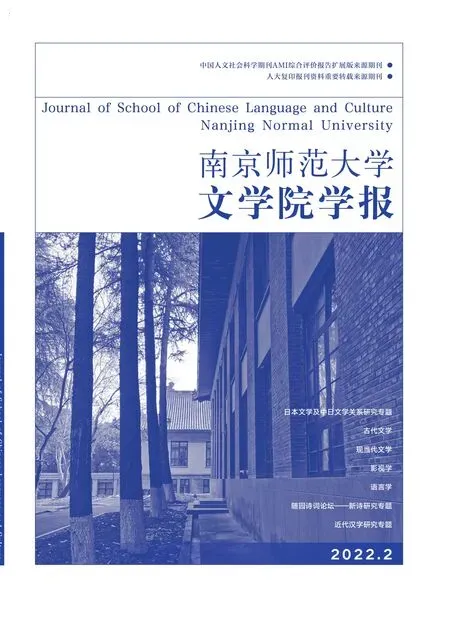从赋比兴论曹植古诗
张 萍 魏耕原
(1.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5;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曹植现存80多首诗中,有43首收入郭茂倩《乐府诗集》,剩余的39首诗中有五言、四言、六言、杂言以及楚辞体诗,习惯上统称“古诗”。相对而言,他的乐府诗多用比兴体与起兴,而古诗则多言怀咏志、送别、酬赠之作。若从赋比兴而言,乐府诗则表现较为全面,而比兴体在古诗里相对较少,起兴则多见于乐府,而比喻则两类诗都存乎其中,具有一定的个性与特点。
一、 充斥感情的铺叙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是就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与内容而言,过去论及建安诗歌只注重发抒壮志一面,而刘勰所说的“指事”,也就是他所指出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一类的题材,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这些诗需要描写与铺叙,这正展现曹植诗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铺叙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驱辞逐貌”的个性特征。
曹植诗对宴饮的描写,乐府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斗鸡篇》《驱车篇》《孟冬篇》《大魏篇》《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此处不论。他的古诗《正会》《公宴》《侍太子坐》《斗鸡》,也都属于这方面的题材,其中《公宴》可称名作: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诗咏的是西园,景色的描写当然要多,夜晚“明月”“列宿”,还把“秋兰”以下白日景观总括加以描写。这样把白天晚上、天上地下、视觉听觉依次铺叙。粗放的描写中却具精到的刻画,在“不求纤密之巧”中,别具“唯取昭晰之能”的生动感。“澄”字就把月明如洗的清萦写出来了,至于明光如水就不用说了。“参差”犹言闪烁明暗,此句犹如曹丕《杂诗》“三五正纵横”,都在模糊的用词见出清晰,语言的弹性发挥到极致。“被”字同样具备这种功能,如果用作“蔽”,话说到尽头了,还不如“被”充满生气。“冒”字犹如书法中的主笔,特别生动有神,有一种鲜活的生气,好像被风摇曳起来,包括“跃”与“鸣”,通俗的动词,都展现了不同的个性与动态。这里动词刻画已涉及到五言诗第三字为“诗眼”,讲究对动词的推敲,这似乎在唐宋时才被提到诗法上有所考虑(1)宋人范希文:“古人虽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陆士衡云:‘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潘安仁云:‘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颜延年云:‘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垅生。’江文通云:‘凉叶照沙屿,秋华冒水浔。’谢灵运:‘萍藻泛沉深,孤蒲冒清浅。’皆祖子建。”(《对床夜话》)王世贞却从反面说:“‘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清池’,‘冒’字更戾眼耳。”(《艺苑卮言》卷二)。
如果从整体铺叙上看,这六句铺叙写景颇为精心,后四句句式虽未变化,显得单一,但却增加了一种整饬感。甚至这诗首尾的叙写,高畅俊爽,“起处真是雅颂衣钵,‘终宴不知疲’句,从浑朴中露出刻骨镂心处。‘神飙’二语,写得出,画不出。”(2)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60页。此诗通篇铺叙,分作三段,各自神采飞扬,首尾两段,用笔如舌,神气高扬。末尾四语句式动宕,下笔琳琅。结末两句更是神旺气盛。
如果说上诗还要说些“公子敬好客”的“官样文章”的话,那《赠白马王彪》则全说自家话。第四章叙写中途荒野之栖惶: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
每两句为一单位,除了首尾四句,中八句全为写景,全为铺叙,句式极为灵活。“微凉”是感觉,而“发”字就带了点刺激性,“蝉鸣我侧”极言声之响。“寒”字承上“凉”,使冰凉之意散发弥漫。原野萧条中间着一“何”字,白日西匿而夹一“忽”,全是心里感觉与栖惶惊叹的情感。看那群鸟归林,自己的孤独早已成了对照,“赴”字是那么匆急,“翩翩”则不停息,再在“羽翼”前着一“厉”,急忙之意自不待言。还有孤兽索群,衔草不食,加上“走”(跑)与“不遑”,一切都是那么的急乱慌忙。这里的感觉、听觉、视觉、细节、动作的描写,整个铺叙营造了一种空旷冷寂的黄昏氛围,孤独荒冷无家可归的心情都由此荒寂之景触发出来。陈祚明说:“此首景中有情,甚佳。凡言情者,须入景方得动宕。若一于言情,但觉絮絮,反无味矣。景更哀凉独绝。”(3)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82页。曹植铺叙,言乐则欢情溢于笔端,言哀则每个字眼都灌注悲凉情绪。
建安时代战争灾疫使人口锐减,曹植《送应氏》本为送别诗,然而却为我们铺叙了那个时代的荒凉景象,连东京洛阳亦不例外: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昔日京都,今日废墟,崔嵬宫室焚烧无余,墙垣塌坏破裂,杂草荆棘高出断壁,上可参天。老年人都不见了,见到的只是年轻人,郊外良田成为荒草,连走的路都没有,原野千里,四无人烟,到处是一片萧条,冷凉到让人喘不过气来。要用不多的文字铺写一座荒冷的芜城,从焚烧的宫殿、断垣、荆棘、不辨道路、荒寂无人,粗线条、多角度地扫描,这种铺叙也就成了刘勰所说的“不求纤密”“唯取昭晰”。每两句一层,层层转换,犹如一种匆匆的广角性镜头,时时移动,展现了时代的残景与悲剧,毁灭到极处,也就只能“气结不能言”了。
《杂诗》其二写游子辛苦,先写转蓬无定:“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他的这种铺叙和《吁嗟篇》一样,是朴素的,与《名都篇》《美女篇》《公宴》的华美迥别,但却同样充满感情。它似乎是《吁嗟篇》的压缩,不同的是,后半篇直接出现了本体:“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也带有一定的铺叙性质,飞蓬也好,游客子也好,都是曹植自喻。曹植曾言“连遇脊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朴素语包涵的感情往往悲愤而引人同情。
而《侍太子座》与《公宴》一样,荡漾着热闹欢乐的气氛:“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此诗明显后边失佚,但就残存部分看,曹植还是善写豪华富贵场面,于此最为得心应手。这里夏日景象,酒席宴前,歌舞声中,写得使人心动神移,想见其“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的景象,以及“高谈阔论,问彼道原”的豪兴。
对于曹植诗,陈祚明说:“宫商合而成音,丹碧错而成锦,前沉而后扬,外缛而中朗。有条递之绪以引之,则不棼;有清越之语以间之,则不沓;有超旷之旨以运之,则不滞;有宛转之笔以回翔播荡之,则不板。故绣以能纂为文,组以善织为美,顾所用之何如,此才子之所以异于恒人也。……于此观之,可知子建之诗矣。……子建即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各成绝极,使后人攀仰莫及。陈思王诗如大成合乐,八音繁会,玉振金声,绎如抽丝,端如贯珠,循声赴节,既谐以和,而有理有伦,有变有转,前趋后艳,徐疾淫裔,璆然之后,犹擅余音。又如天马行空,籋云凌山,赴波逾阻,靡所不臻,曾无一蹶。”(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5页。这是对曹植诗的总体评价,如果以之去看他的铺叙,那才更合适不过。因为铺叙在他的诗中占了主体部分,且居耀眼位置,尤其再把乐府诗铺叙合观,更是如此。
二、自然酣畅的比喻与情感灌注的比体诗
曹植是个天才的诗人,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络绎不绝的比喻,而且自然酣畅至极。确实“绎如抽丝,端如贯珠”。这不仅在建安诗人中显得突出,即就是在李白以前诗人,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朔风》次章的“别如俯仰,脱若三秋”,是说分别是那么容易,犹如俯仰之间,而别离以后的时间更快,忽然之间恍若如隔三秋。喻其一端倒也不难,二者连在一起,出之以递接性的比喻,就不那么容易。“俯仰”言其快,“三秋”言其长,快慢连接,就显自然酣畅,把感情表达得很悲切。《杂诗》的“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以女萝依松,浮萍依水,比喻妻之依夫,说得形影不离、自然融洽。《弃妇诗》:
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抚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 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幷。
以石榴树只有丹花而不结果实,以喻妇女无子,而无子即要大归而休弃。能生子的妇女就像明月经天,面有光辉;而不能生子的妇女,就像天上的流星,从天上消失离开夫家。前者终生相守,就像日月经天那样光辉而夫妇偕老,而后者就像流星没落而无光彩。一旦无子而居处不得其所,就如同瓦石尘土一样,被人看得轻贱。这诗的最后说:“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招摇”是桂树的代词,《吕氏春秋》说过:“招摇之桂,食大如枣,得而食之,后天而老。”“待霜露”是说到秋天才结实。这几句说植物中的桂树结食晚而好,何必一定要像石榴成熟于春夏呢,以此安慰妇人迟生子没有什么不好。此诗开始从“石榴植庭前”写起,把无子之妇就像石榴“丹华实不成”,为一层比喻,再经“无子若流星”一层比喻,再用比喻“有子月经天”加以陪衬;然后再伸说翻进一层:天月终始,流星无光。反复对比,其结局一旦栖迟失所,就视同瓦石,被人弃置。最后以桂树结实晚而好,何必一定要像石榴成熟于春夏,比喻妇人迟生子没有什么不好。全诗用比喻加上对比,前后贯通起来。此诗代表弃妇语夫,先“述己之容颜美好,不幸无子也,却就石榴花而不实,凭空比起。鸟代树言,人揣鸟意,用笔甚奇。‘抚心’八句,提破无子当归本指,随就有子者两两相形,以见弃捐之痛。‘忧怀’十句,叙将归未归,辗转无聊情事。只就夜说,夜可该日也。带出弹筝要妙,亦以表己技能。末六,自反无辜,终期有子,而冀夫无遽弃也,亦用晚获良实比喻作收,章法与篇首相配。”(5)张玉谷.古诗赏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12-213页。
有时发抒胸中愤懑,不便明言,便用隐喻。《赠白马王彪》首章言恋恋不舍离京;次章言中途遇雨的行进之苦;三章言与弟将要分离,不能同路而行,悲从中起,指斥迫害者:
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
黄初四年曹植之弟到洛阳朝会,曹彰被曹丕毒杀,曹植与白马王曹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离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就用鸱枭、豺狼、苍蝇隐喻这些谗巧的监国使者。三个比喻一气使来,说他们“鸣衡扼”“当路衢”拨弄是非,就像“苍蝇间白黑”一样,污白使黑,使亲变疏,离间骨肉。想见指斥怒骂,愤慨难以控制。“好在多用比喻,只‘谗邪’一句拍醒,故能露而仍含”(张玉谷《古诗赏析》)。凡所比喻,都因情感促成。
《杂诗》其二是曹植古诗中的比体诗,显得比较别致:
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此诗十二句,中分为前后两截,第七句“类此”把上之“转蓬”与下之“游客子”挽合为一起,是说从戎之游子就像飘摇无定的转蓬。实际二者均作为喻体,本体都是作者自己。前半发飘荡迁徙的离群之苦,后半自嗟衣不掩体、食不果腹的困苦。刘履即认为是“比”,即比体诗:“此篇叹身世之飘转有类于蓬,故赋之以自比也。盖久在远外,正如蓬离本根,一旦入朝京都,如遇回飙吹入云中,自谓天路之可穷矣。及乎终不见用,转致零落,乃知高高无极,不可企及,反类游客从戎而有饥寒之苦者。是则且宜安于时命,去去勿言,而不至于溺于忧伤也。此与本传所载‘吁嗟此转蓬’一篇,词意实相表里。”(6)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20-121页。两个喻体说的一个本体的两方面,则和一般比兴体诗有别。
其四亦为比兴体,与乐府诗《美女篇》相近,发抒希有为而不得及时见用: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此首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本以佳人自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7)张玉谷.古诗赏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99页。此首明言“南国有佳人”,《美女篇》则似北国之佳人。因曹彪在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与诗中“朝游江北,夕宿潇湘”喻迁徙无定相契合。前人或谓此诗为曹彪而发,以佳人空有色艺,不为时俗所重,比喻才高有为的人安置于闲散之地,忧虑时移岁改,而淹没无闻,不见重于当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还有一首无题诗,以双鹤相失,比喻兄弟分离:“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傍。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这诗用意或许是曹植与曹彪分别的诗,表现离别的感伤和恐惧、迫害的情感。末句的“天网”比喻朝廷的迫害。此诗前六句都从离别的痛苦一路说来,末两句一转,是说一别万里也算不得可悲痛的事了,只要能不陷入天网就算万幸了。实际这也是伤心人所说的痛苦话。这样的转折抚慰,就同《赠白马王彪》的“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人至无可奈何时,每有此类强解语,其所以强为宽解,其中正有不可解之苦处。此诗末二句,亦可以作如是观。
曹植还有一首咏史诗《三良诗》,此诗因《诗经·秦风·黄鸟》哀叹秦之三臣殉葬事。王粲、阮瑀也有《咏史诗》所咏相同。曹植诗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此诗名为“三良”而发,实为咏怀。陈祚明说:“此子建自鸣中怀,非咏三良也。咏三良何必言‘功名不可为’,尔时三良,何遽不可为之功名?若咏三良,何以云‘杀身良独难,一往不复还’,盖子建实欲建功于时,观《责躬诗》可见。今终不见用,已矣功名不可为矣!文帝之猜嫌,起于武帝之钟爱。此时相遇不堪,生不如死。慨然欲相从于地下,而杀身良难,一往不还,徘徊顾虑,是以隐忍而偷生也。子桓既以夺嫡为嫌,其待陈思诚有生人所不能忍者,故愤懑而作,追慕三良。嗟乎!同气之情,令至此极,亦可哀矣!”(8)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84页。说是追慕三良,恐怕不至于此。王粲、阮瑀诗当与曹植同时而作,但他们俩的诗都有批评秦穆公之意,曹植则由三良而想起自家难处危迫之境,不知何时而有不测,故而悲伤,发而为诗。开端即言不为功名,难求忠义,先说自家话。方东树说:“此六句峥嵘飞动雄迈,浩然沛然,‘谁言’二句倏转出余意,以下但停蓄感叹,顿挫不尽,沉痛。”又言:“此篇分两段,古人用笔,最是截断倏转处,为最见法力。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得不尔。”(9)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75-76页。
总之,曹植诗多比兴,在古诗中通篇的比体诗的不为少见。其中如咏物诗、咏史诗、弃妇诗、游子诗、美女诗,他都可以在其中倾注自己的感情、怀抱与处境,所处境况不能直说者,均以比体诗作为代言工具。钟嵘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诗品》),主要就是针对他的比兴体诗言之,可见比体诗无论在古诗或者在乐府诗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三、 慷慨高亢的起兴
曹植是最早重视发端的诗人,加上时代赋予的悲凉与个人风格慷慨,使他的诗发端引人注目。沈德潜说:“陈思极工起调,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如‘高台多悲风,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10)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01页。像曹植这样注重发端的人,必然对起兴非常热心,因为起兴本身就在发端位置,而且比一般的开头更具有多重的感发作用。
沈氏所举例一,是《赠徐干》诗的开头。这两句后的“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都属于写景。把这四句用作发端,似乎赋予了一种时代气息。日落月上显示了时光的流转,然而以“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说时光匆急,那就带上了战乱中人的语气。而且月光未满而众星争粲,则引发出下文“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这样合观,开头四句既非单纯写景了。“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是《七哀》的发端,一下子就把人的感情调动起来,而引发出的“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简直是对次句的回响,而首两句为美景,引发的却是哀情,以美景写哀情,其哀就更为不堪。即就是写景,把难写之景能置于目前,尤其是把月光说成“流光”,而且把月到中天说成“正徘徊”,欲行不行景象宛然可见。所以这两句就更具有起兴的感发作用。“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是《杂诗》其一的开头,台高而风多,说是“悲风”,自是心中之悲凉;而“朝日照北林”,引人神往,而思绪飞往远方。这个开头阳光灿烂而感慨翻腾,把景之美与心之哀硬是搓揉在一起,而引发出“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的对友人的思念。似乎开头就有很多话要先说,而只说了这两句,其余则慢慢道来,这也是起兴所具有的功能。
可见曹植诗的开头,在笼括性的写景中,把种种复杂深厚的情感先行灌注其中,其中的暗示、感发、引导、启迪之作用非常强烈,如此多样的审美感,只有把起兴的特征融入其中,才会有这样的多重的焕发作用。除了以写景发端外,还用议论来发端,其中的感发作用显示出起兴效果。《送应氏》其二的“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这种感慨引发了一场朋友的饯别,自然有许多惜别之言而在下边要说了。其三开头的“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此诗写空闺织妇思念从军的丈夫,织妇之缤纷的绮缟,象征有许多思念的话要说,包括结尾“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也应当在内了。《矫志》开头“芝桂虽芳,难以饵鱼;尸位素餐,难以成居”,这是以格言式的比喻发端,超前作为喻体,然后引出以下的本体,这种格局,显得水到渠成。《三良诗》开端“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好像先提出一篇之论点,引出以下的证明,《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的发端“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用意亦复相同。《游仙诗》开头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这是为什么呢?以下要予以回答。
有些发端舒缓,用语亦较多,慢慢走来,再慢慢引出。《情诗》的“微阴翳阳景,清风吹我衣。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此为发端起兴,以鱼鸟的自在引发出以下征夫的辛苦,此则为反兴。
最后附带指出,曹植诗言情自然,张弛变化,随心而动,言从笔涌,如出肺腑,以及用词而充分发挥语言的弹性。《赠白马王彪》为曹植之杰构,真情至意发为哀歌,由七章构成,七为悲痛之大数(11)魏耕原.诗学发微[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150页。,这本身即为创见,引发杜甫的“同谷七歌”。其五、六章言情感人至深。五章以“天命与我违”引起:“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因朝京师,曹彰吃了几颗枣子而被其兄曹丕毒死。这里有质问意:为何不念同胞兄弟,竟能下得这样的毒手,使之一往不归。他的孤魂早飞回到封国故地,而冷冷的灵柩还存放在京师,亡殁者说走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而活着的人吓得要死,也难以久长。这是面对同胞暴死的至哀的大哭大悲之语,如怒如怨,如泣如诉,其中的倒装句、对比句、对偶句、比喻句,使感情更加感人至深。
第五章的“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领起,先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壮语劝人;再以“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从难以实现的反面劝导,然后再伸说一层:“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过于忧愁反成疾病,就未免儿女情长。说到这里,作为兄长,自己反而控制不住——“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心”——然而急速之间兄弟间的生离死别出现在眼前,说不悲伤是不可能的!犹如哥哥劝弟弟别哭,劝着劝着自己也哭起来了!把悲愤抒发得淋漓悲壮,沉郁顿挫,比放声长哭更为感人,千载下读之犹为酸心,何况当日!
曹植诗能把平常语习见词发挥到极致,充分调动语言的弹性与张力,使读者的能见性扩大到最大强度。如“远望周千里”,恍如置身高处,“周”字使千里之外了然在目。而“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不说“江边”,而说“江介”,似乎空间更扩大了;“驰急流”是三个动词的组合,还是形容词加偏正性的名词,无论从何角度观察,“江间波浪兼天涌”景象都可出现目前。其三的“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把动词“流”与“驰”又分散两句,似乎比聚集于一句更具有快急的速度。《公宴》的“列宿正参差”与“秋兰被长坂”,把“正”和“被”能量调动到极大的强度。《七哀》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长逝入”由一个形容词与两个动词连缀一起,急迫的心情表达得深情深意切。《赠白马王彪》的“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厉”字狠劲,“翩翩”又是那么急促,加上“赴”字陪衬,其急促可见。“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的“其”为期盼语气词,即“可要”义,有多少叮咛话包涵在这句话里,“其”字用得恰切极了。
正因为曹植古诗长于言情,注意动词、形容词、副词与语气词的使用,所以他的赋体所包涵的写景、议论、抒情能挥发得淋漓尽致或生动自然,而奠定了“建安之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