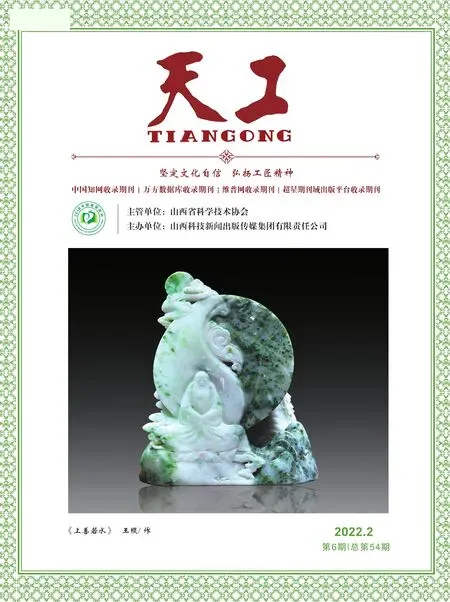满壁风动 天衣飞扬
——以图像学研究法分析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
潘佳莉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和艺术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科研中逐步探索“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作用与意义,把“图像学”的方法和理论深入历史遗迹、绘画遗存、神话形象、民间美术等研究方面,采取个案分析等手段,取得新视域下的研究成果。
敦煌壁画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素有“墙上博物馆”的美誉,题材范围广泛,内容浑厚博大,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当下,围绕敦煌壁画的图像学研究步履不停,图像学逐层递进的分析方法以及深入内因的考察方式对于敦煌壁画中各种形象的独立研究极具借鉴意义。“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形象更成了敦煌壁画耀眼的名片,是敦煌壁画图像学研究的重点。故从图像学研究法的角度对飞天形象进行探究,发现与揭示飞天形象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情趣、情感意义、理想品格。
二、敦煌壁画飞天形象介绍
敦煌飞天是敦煌壁画艺术中最著名的形象,形态优美的飞天几乎成为敦煌莫高窟艺术最优美的代言。敦煌莫高窟中的飞天形象在所有洞窟中几乎都有一席之地,甚至有俗语云“敦煌无壁不飞天”,正是用来形容飞天在敦煌壁画中的重要地位。
从时间上来看,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伴随着十六国时期敦煌洞窟的开创而同时出现的,跨越了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晚期才随着敦煌石窟的建成而逐渐消逝。在这漫长的历史推进过程中,飞天的艺术形象、审美取向、品格内涵等在不同的时期,历经了不同的艺术家,于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各有其时代的烙印,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经典形象。
从艺术形象上来看,飞天形象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形象表达,而是多种文化混合交融下的复合产物。如北凉时期的飞天形象偏向男性特征,往往头圆而大,五官浓烈,身材也较为粗短,具有典型的印度和西域文化特征。到了隋朝时期,飞天形象逐渐转为眉目清秀,身材变粗短为修长,脱离异域形象,向中原女性体态优美的形象之感靠拢。唐朝时期,飞天形象已经完全实现了中国化,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更具中国特点之处在于敦煌飞天是不长翅膀和羽毛的天人形象,摇曳的裙摆与飞舞的飘带整体带着灵巧起舞的“动势”之感,此优美飞天形象是中国艺术家在敦煌壁画中最为精致优雅的天才创作,使敦煌壁画的形象之美绽放光彩。
三、图像学视角下的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研究
潘诺夫斯基在他的书中将图像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前图像志描述阶段、图像志分析阶段和图像学阐释阶段。这三个层次内部存在着顺序上的关联以及情绪上的递进。从图像学的视角对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进行研究,先从第一层次,即原始自然意义方面对飞天形象进行自然的详尽描述;第二阶段分析传统意义,要求从飞天形象所展现的形式法则和与之相关联的背景等入手,探究飞天形象本身和与之相关的特定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即本质阐释阶段,则要求深入飞天形象与创作飞天的艺术家本身,从宏观的时代背景把握作品、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思考作品的深层意义,揭示作品内在的人文精神。
1.飞天形象的原始自然意义
对“飞天”进行自然意义的描述意味着直面飞天形象,观察其表层形象,感受作品向外传达的朴素信息,从视觉上对飞天形象具有感观上的把握,从而客观地描述飞天的内容。由于不同时期的创作均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影响,因此各时期的飞天在造型风格、意味上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千余年的演进过程中,以早期北凉时期、开创期的隋朝时期、鼎盛的唐朝时期以及逐渐没落的宋朝时期为代表,从时间顺序上对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的原始自然意义进行描述分析。
早期北凉时期的飞天形象映入观者感官的是一种“自然、笨拙、古朴、神秘”之感,这一时期处于洞窟的开凿初期,飞天在本土处于初创阶段,异域传入的外来感强烈。此时的飞天没有任何女性化的色彩,光头不加修饰,面部五官比例偏大,耳朵硕大而突出,上身赤裸,全身仅有飘带环绕和简易下装,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被视为“西域式”飞天。尽管此时的飞天略显粗拙,但仍展现了各种大幅度飞扬的姿态,腿部动作高高扬起,整体依旧有飞扬之感。
隋朝时期是飞天形象极具开创性的时期,此时的飞天形象脱离了早期笨拙原始之感,取而代之的是“生动、轻盈、缥缈”。外形上已完全脱离了西域式画风的影响,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神态婀娜多姿,中原女性的清秀之感跃然而出,飘带和裙装的样式也具备中原意味。在布局上隋代飞天常以群体面貌展现,使观者如入飞天之境。敦煌莫高窟第390窟中出现的天宫伎乐飞天,以天宫的栏墙纹为界限,绘制环窟带状飞天一周,飞天沿着一个方向飞行,或散花、或奏乐,体态婀娜多姿,造型秀丽,神情欢愉,节奏韵律轻快而富有动感,极具代表性。隋代飞天形象在豪放和清新之中创造了民族化的形象,并开始走向世俗化,成为向唐代富丽绚烂的艺术过渡的桥梁。①李立华、张元元、王佳:《千年古韵 御风飞翔——以“图像学”解读隋唐时期敦煌壁画飞天》,《美术界》2011年第12期,第87页。
唐代的飞天世俗性与故事性明显增强,不仅种类更为丰富,细节也得到改善,进一步接近普罗大众,体现出“人性”,似是天上虚无缥缈的精灵落入人世,与世俗接轨,终成人间的飞天仙女。《反弹琵琶》这一唐代壁画创作,代表了敦煌艺术的超高水准。画面中伎乐天神态怡然,略现俏皮之感,在仙乐的指引之下翩然起舞,纵身飞跃,使“反弹琵琶”这一浪漫的艺术化动势在顷刻间呈现。飞天造型饱满丰腴,线条流畅,风格写实,色彩明艳,突显唐代审美特征,而动态的热烈与色彩的运用仍带有西域色彩,整幅画面明艳华贵,尽显大唐风姿。
宋代,飞天依然被描绘在高处飞舞着,但日渐呆板笨拙,内在的灵性已逐渐消逝,外在姿态也少了缥缈的灵气。敦煌莫高窟第76窟的飞天形象依然是写实精致的,飞天吹着横笛似乎在云层上缓缓飘动,姿态平稳,画面平和,但少了那种无拘无束的自在灵巧。
四个时期的飞天形象各具面貌,观者从视觉享受中领略飞天神韵,正是运用图像学研究的第一层将图像的原始自然意义呈现。
2.飞天形象的传统意义
潘诺夫斯基所划分的图像学的第二层次进一步认识图像,分析图像的传统意义,即对图像中元素所暗含的象征意义,对图像作品所包含的主题意义以及与当时的某种文化相关联的内容进行探析。首先,敦煌飞天最大的特征在于虽为天人却无翅膀和羽毛,但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感觉却传递得淋漓尽致,这种风动的意蕴在中国绘画中是“神韵”的体现。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风格是“吴带当风”,画中从未直接描绘风,却处处生风。飞天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此种对于“神韵”的审美追求之下的创造。中国古代的画家和艺匠们运用非凡的智慧,将这种“风感”巧妙地展示,这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审美与智慧的表达。
其次,观察不同时期的飞天形象,从差异中分析所具备的传统意义。早期北凉时期的飞天古朴稚拙,基本延续对外来的模仿,中原意味不足。这种“不分性别”、稍显怪异的飞天形象与印度的宗教文化有关。而进入隋唐时期,飞天已经实现了中国化,姿态恣意昂扬,无拘无束,造型充满幻想,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给后世留下了众多精彩绝伦的飞天样式,与唐代的“享乐主义”文化密不可分。唐代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开放自由,使得整个社会氛围洋溢着欢快的情绪,艺术家和画工、画匠身处“大唐盛世”,无疑也将这种情绪反映到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中。故此时的飞天衣着华丽,装饰华贵,色彩以暖色调为主,明艳夺目,尽显大唐风范。正如唐代诗人李白咏赞仙女诗中“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空,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描绘的诗情画意。①傅强:《论敦煌飞天艺术之美》,《装饰》2004年第1期,第18-19页。而五代至宋代飞天的逐渐没落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关。五代时期国家分崩离析,战争与混乱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内心的不安、慌乱投射到艺术上,一种更为平稳的抚慰取代了昔日的恣意洒脱。宋代社会风尚是文人般的雅致,思想上理学的发展促使人们看待宗教更为理性,对“极乐世界”的热情与向往逐渐减少,因此此时的飞天逐渐丧失了灵性,线条偏向理性克制,画面氛围也变热烈为平和,呈现出典雅的特点。
由此,通过对飞天形象的进一步分析,对飞天形象的传统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飞天形象逐步饱满,不再只是简单图像的呈现,而含有具体的意义。
3.飞天形象的本质内涵
当步入第三层图像学分析阶段,意味着对于飞天形象的研究,将彻底深入其背景的海洋,思考与之相关的历史环境背景并从中打捞有关飞天及飞天的艺术创作者的一切相关内容,透过内容剖析其本质与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首现飞天,那时烽烟四起,政权更迭频繁,民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普通民众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在宗教中寻找安慰、寄托希望才能得到继续生活的勇气与信念。因此,尽管宗教艺术刚刚起步,宗教建筑、绘画艺术等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民众对于宗教的精神需求使得各种宗教艺术迅速发展,敦煌洞窟和壁画都在这时出现,人们把自己的情感与希望表达在艺术之中。到了隋唐,大一统的盛世使人们内心安定,世俗生活热闹繁华,自由开放的大唐包罗万象,东西方的交流与融合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唐代画师在创作时也突破了以往的神秘与严肃,显然是受到民间社会风气、道德、审美的影响,充满“人情味”,于是此时的飞天世俗色彩浓厚,不再是人们精神“彼岸”的向往,而是人间幸福生活的反映。敦煌莫高窟320窟,就是一首谱写世俗生活的颂歌,画面中四飞天造型自由,恣意腾飞,只有在开放包容的大唐才可能创作出如此般自由、充满生气和欢愉的飞天形象。
宏观的历史背景对于飞天的发展与演变有着大时代下的必然影响,而真正付出汗水创造出美妙绝伦的飞天形象的画工、画匠也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是他们将这一艺术瑰宝献给全人类,将精神与物质文明保留下来。走进真实的历史,这些“艺术家”们身份并不单一,有家徒四壁为讨生活的能工巧匠、有为了宗教甘愿奉献的信徒、有天灾人祸下流离失所的流民、有昔日得意而失宠落寞的京城名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庞大的“艺术创作者”群体。而他们身心的共同之处,一首出自敦煌的小诗便能完整概括:“工匠莫学巧,巧计他人使,身为自由奴,妻为官家婢。”②李蕾:《霓裳羽衣 天乐长鸣——唐敦煌飞天乐舞造型审美研究》,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4。远离故土的人思念着家乡与亲人,怅然不得志的人忆着往昔的荣光,颠沛流离的人渴求着内心的安稳……种种情感与心绪化为他们手下非凡的艺术创作。或满身技艺毅力非凡,或身受束缚无可逃离,或满怀期待寻找安慰,眼前的苟且使他们更加向往神圣的一切,自由翱翔、无拘无束的飞天也许是他们眼中所祈盼的来世的自己。画工、画匠们用他们执着的匠人精神、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偏远的西北边陲创造了不朽的艺术神话。飞天形象的创造正是这些匠人们精神的传达,是民众超越内心的精神凝聚。
敦煌飞天形象在这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发展,经历了早期初创的“西域式”古朴,隋朝开创期群像共同体现的自由与曼妙,大唐盛世的绚丽与欢愉,五代两宋的典雅平和,但飞天形象绝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而是不同时代下普通民众对宗教崇拜的表达、对社会审美风尚的集中反映。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使观者对飞天形象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表面,通过对飞天形象的原始自然的详尽描述,对形象象征意义的探析,再到深入浩瀚历史的海洋发掘不同时期飞天形成的原因以及剖析创造飞天形象的艺匠们的身心,使人们对飞天的认识拓宽了广度与深度。飞天作为敦煌壁画的耀眼成就,作为我国的艺术瑰宝,图像学的分析法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飞天的历史意义、审美情感、人文思想,“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形象将以更饱满生动的形象意义丰富敦煌壁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