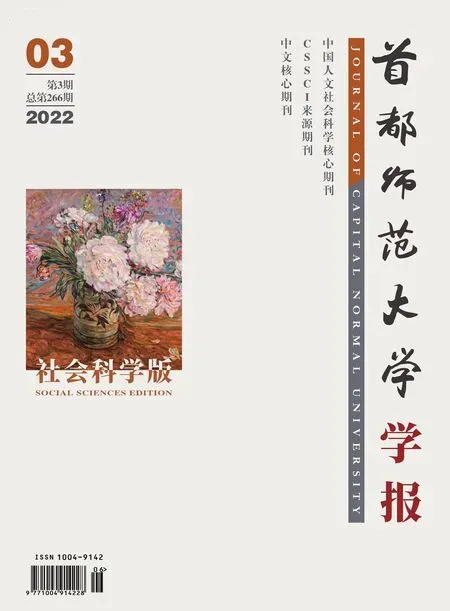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家园风景构型与伦理焦虑
张 琼
劳伦斯以其超越时代的感知天赋,敏锐地捕捉到英国正在发生的失去生命力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意识到农业英国的传统发生了断裂,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这直接导致了他小说中的矿乡是家非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工业文明正在吞噬和销毁着具有自然、完整、本真、温暖等意义的家园秩序和传统;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对乡村的渗透有目共睹,但乡村所代表的田园牧歌传统却始终存在,并承载着精神避难所的功能,伴随着人地关系的疏离,这种功能被进一步理想化,与现实社会中工业文明冲击下的矿乡共同完成了劳伦斯式的家园风景的怀旧形态和负面形态构型。通过风景这一再现媒介,劳伦斯力图抓住人们陷于这种变化中而不自知的盲目、痛苦、机械化和碎片化,并将其具象化地加以呈现,从而聚焦社会主体性身份的伦理焦虑。
一、家园风景的怀旧形态
怀旧(nostalgia)由nostos和algia两个分别表示回家(返乡)和痛苦焦灼感的意义的词根组成。1688年瑞士医生J.霍弗尔通过联合两个词根首次创造并使用了这个词,特指一种主要发生在士兵身上的思乡臆想症。之后,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①参见赵静荣:《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25页。,意义指向了“现代怀旧的中心概念不是别的,正是‘乡’或‘家’的变迁”②赵静荣:《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页。。而怀旧与家园在本义上的连接,使其成为“最容易平复现代人的流浪之心、安抚现代科技对人类伤害的一种方式”③赵静荣:《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也只有在人地关系疏离的境遇中,对家园风景的意义的探讨才展现出必要的、独特的、诗意的吸引力。“怀旧是对一个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怀想,是对一个被净化了的传统而非历史的叙述”④Lash,Scott&John Urry,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p.247.,劳伦斯小说中具有怀旧意义的家园风景的构建,表现出一种非物质、非理性、非纯粹记忆的理想化倾向。以旧英格兰为中心的家园风景包括了未受现代文明因素破坏的自然环境,身心统一的人性本真状态,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等,并以两种形态出现在劳伦斯的笔下。
一是原始宗教形态,即从古老宗教的神秘和未知的意义上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有限性加以阐释。《白孔雀》的第二部第一章中,西里尔、莱蒂、莱斯利和埃米莉散步时进入了查恩伍德森林,在森林里他们看见了香雪球,这些花出现在西里尔眼前的景象充满了神秘感:“当我和埃米莉说话时,我隐约地意识到地面有一层白光。……我踏在了一簇簇香雪球上。”⑤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99页。莱蒂也有相同的感受,“看这些香雪球吧,它们在暮霭的树叶中悬挂着,象一些奇异而模糊的光斑”⑥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页。。莱蒂和埃米莉都认为这些花的象征意义“来自一种我们已失去了的古老宗教”⑦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页。,蕴含着现代人无法了解的东西,“它们属于某种我们已经失去的知识,我们需要它们,但又感到害怕。它们似乎象征着某种命运之类的东西”⑧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页。。《恋爱中的女人》第二十三章中,劳伦斯把伯金和厄秀拉在自然丛林中的身体交合描绘成了展示自然的神秘性的符号,在两人眼中,对方裸露的身体都是“远古神秘、真实的异体”⑨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页。。《迷失的少女》中爱尔维娜逃离代表着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与规范的生活模式的曼彻斯特宅第,跟随西西欧来到未被现代文明玷污的意大利一个名为卡利法诺的村落,在陌生的深谷丘陵之间感受到了一股“在消蚀她的野蛮的力量”[10]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克拉克认为这是爱尔维娜走出家门,跨越边境,进入神秘世界的朝圣之旅。[11]Lawrence,D.H.The Lost Girl.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50,p.361.爱尔维娜所朝的“圣”是西方基督教眼中的异教,“没人能够言传山谷中着宏伟壮丽、异教味十足的黄昏,此刻在这荒蛮寒冷的山谷中,会令人意识到那些要活人祭献的古代天神。……她感到自己由此而彻底窥察到了另一个神秘世界的面貌。……那些凶残野蛮、以饮血为快的天神才是真正的上帝”[12]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这种信仰展现了人类本真状态的遥远文明,满足着人类“灵魂本身需要得到自己神秘的营养”[13]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的需求,显示出了比受到现代文明束缚的所谓高雅纯洁的基督教更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沃德豪斯这个煤矿小镇所缺失的,之所以在图克太太这样的认为“宇宙是台大机器,我们只是它的部件而已”[14]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的文明精英的眼中,爱尔维娜和西西欧的婚姻是一种“返祖”[15]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虽然人类获得了科技的进步,却并不代表着对自我认识的加深。正如埃米莉所说的:“尽管我们戴着这花。它决不属于我们。”①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页。与自然中所蕴含的神秘力量相比,人类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对于这些力量人们知之甚少,因为崇敬和憧憬而加以膜拜,这是远古宗教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自然形态,通过人对自然的感知来进行呈现。劳伦斯小说中,煤矿主住在远离矿区的田园风味的庄园,依靠类似小山丘的自然屏障遮蔽脏乱的矿区,矿工被安置在靠近矿区的居民区,这些居民区有些是统一规划建造的,有的则是依托过去遗留下的城堡和庄园的拆除改建,只有乡村中残存的湖泊山林成了劳伦斯及其笔下主人公的心灵寄托之所。《儿子与情人》第一章中身怀六甲的莫雷尔太太被喝醉的丈夫赶出家门,月光下,远处的群山,近处的“仿佛有精灵鬼怪在侧似的”②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白百合花、白夹竹桃树丛、白玫瑰树丛、一只穿过园子飞去的飞蛾抚慰着她的情绪,在害怕、紧张、激动又愤怒的她周围形成了一个香甜的、静谧的、充满幻想的世界,以至于“待在这神秘的露天里,她觉得自己孤零零的”③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丈夫酒醒开门后,莫雷尔太太看到镜子里她脸上在黑暗中沾到的百合花的黄色花粉的反应是“不禁微微一笑”④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然后擦掉花粉躺下,“但脑子里还继续冒出各种各样的念头”⑤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她还沉浸在自然的感触和氛围中,以超越现实的心理力量对抗着丈夫的态度。《虹》中厄秀拉在搬离考塞西之前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散步,“路上的小水洼宝石似的闪亮,周围的土地都变黑了,头顶上的天空就是一大块宝石”⑥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页。,奇特美景使她内心热烈的情感几乎要喷薄而出,“因冬天变黑了的草地充满了神秘色彩”⑦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9页。。“神秘色彩”一方面来自于这些地方是在人们只能按既定轨道生活的“考塞西陈旧封闭的外壳”⑧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9页。下,是厄秀拉心灵的栖息之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趣味高雅的有身份有教养的人们将会成为她的朋友”⑨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9页。的文明社会和“一定要变得新派一些”[10]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页。的布朗温家而言,这些地方代表着古老与传统。它让厄秀拉在向往着离开考塞西的文明生活的同时,也感觉到了深深的孤独。《恋爱中的女人》第十九章中对于丛林的描述,同样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对伯金的爱深感痛苦的厄秀拉在林子里散步,“夜幕早已降临,一片漆黑。可是她忘了什么叫害怕,尽管她是个极胆小的人。这里的丛林远离人间,这里似乎有一种宁静的魔力。一个人愈是能够寻找到不为人迹腐蚀的纯粹孤独,她的感受就愈佳。在现实中她害怕人,怕得要死”[11]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不知道该如何与现实中的人相处的厄秀拉在丛林中享受着抛开人际关系的束缚的自在,感受到了心灵的平静。这是人与自然超越现实层面的交流,是人的归属感的体现,就如同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的安稳。
劳伦斯笔下的原始宗教与自然往往具有同一性:保罗在乡村天然的幽冥之中感受到妈妈的力量,立下绝不走向黑暗的誓言;杰拉德在宛如神光的天色中迷失在自然的怀抱里,最终葬送机械化的生命;厄秀拉从彩虹中感受到神秘力量期冀着新的世界,迷失的少女在远古宗教的指引下融入自然天地之间;康妮在滂沱大雨中释放野性的原始欲望,点燃神圣的生命火花。自然依托生命的神秘力量,构建起了与人的感知通道。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实现了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状态。在劳伦斯看来,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从生命体验的意义上讲是对人的阉割。劳伦斯曾在1926年12月3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伊斯特伍德为“我心灵的故乡”[12]Lawrence,D.H.The Letters ofD.H.Lawrence,edited by Aldous Huxley.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34,p.674.,这种心灵的感召与伊斯特伍德对于劳伦斯的家园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原始宗教和自然为形态的伊斯特伍德家园风景的视觉体验承载了古老农业英国的空间记忆,在劳伦斯作品中展现出神秘、宁静、和谐又封闭、陈旧、野性的特质,彰显出极具价值体验的地方感。
二、家园风景的负面形态
家园风景的怀旧形态可以理解为劳伦斯描绘的家园风景的正面形态,体现的是人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在时空中的圆融和谐。负面形态则着眼于现实环境中人地关系的疏离状态,即透过矿乡景观变迁,以地志研究的话语形态呈现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扭曲,展现工业文明带给乡村风景的破坏性重塑,主要通过矿乡景观和城镇景观来展现。
劳伦斯在小说中以煤矿业的兴衰史为切入口,展现工业文明对风景的重塑。《儿子与情人》开篇的第一句话“‘洼地区’取代了‘地狱街’”①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就交代了贝斯伍德村煤矿业的变迁情况。“地狱街”是早期矿工的聚居地,那个时候“小河在一片赤杨树下流过,还没受到这些小矿井的污染。乡下到处都是这种小矿井,有些矿井从查理二世时代就开始采掘了,两三个矿工和几头毛驴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往地底下挖,在麦田和草地当中弄出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土堆和一小片一小片黑色的地面来”②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此时的地狱街有一些小矿井,采用的也是一些较为原始的手段,男人们挥洒汗水换取劳动所得,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生命的体验。矿工们虽然有统一的居住区域,但是比较分散。肮脏、简陋和贫困的生活条件给了地狱街不好的名声,此时的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村民一样,是从事着不同职业的人,并没有成为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群体。然而,情况突然就发生了改变,“小矿井被金融家的大矿挤掉了。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发现了煤矿和铁矿,成立了一家卡逊-魏特公司”③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公司成立之后才有了“洼地区”。“洼地区”是卡逊-魏特公司为安置矿工修建的居民区,由于是经过统一规划的,显得特别的整齐划一,“包括六排矿工住宅,每三排为一行,恰如一张六点的骨牌,每排有十二幢房子”④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从表面上看,矿工家庭住进了统一模式的房屋,矿工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房子倒是构造结实,相当不错。人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宅前的小园子,在下面一排屋前的阴凉处种着樱草和虎耳草,上面一排向阳的屋子前种着美洲石竹;看看那些干干净净的前窗,小小的门厅,小小的水蜡树的树篱笆,阁楼上的天窗。不过这只是外观;这一面是所有矿工的家眷们很少去用作住房的起居室的景象”⑤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矿工生活的真正状态隐藏在拥有着看似美丽的正面外观的房屋的后部,“日常住人的房间、厨房都在屋子后面,面对两排屋子的里侧,看到的只是一个难看的后院,还有垃圾坑。在两排房子当中,两长行垃圾坑当中,是一条小巷,孩子们玩耍,女人们聊天,男人们抽烟都在巷子里”⑥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所以,“尽管房子盖得那么好,外表挺不错,洼地区的实际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因为人们只能在厨房里过日子,而这一间间厨房却面对着那条有好多垃圾坑的臭巷”⑦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对特瓦萧的描写,则更直接地展现了工业文明的恶果。特瓦萧街区被黑糊糊的煤灰包裹着:“黑糊糊的砖房散落在山坡上,房顶是黑石板铺就,尖尖的房檐黑得发亮,路上的泥里掺杂着煤灰,也黑糊糊的,便道也黑糊糊、潮乎乎。”⑧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居住在这里的人也如同黑糊糊的煤灰散发出衰竭的味道,“他们内心里活生生的直觉器官已经死了,变得如同指甲,只会机械地发出叫声”⑨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可以说聚集着新矿井的斯戴克斯门在外表看似齐整的规划下却是缺乏生命力的存在:“排列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房与房之间留出空地和花园来,这是某些荒诞不经的‘主子’在地球上玩的一种奇特的多米诺骨牌游戏。而在这些住宅条块后面,则矗立着现代煤矿惊人骇人的高大建筑,那些化学工厂和长廊,其形状之庞大,模样之古怪,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新的设备中,原先的矿井架和井台都显得渺小了。而这些建筑前面的住宅,则摆列着一副永久的多米诺骨牌,等待着人们去玩出惊喜来。”①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劳伦斯小说中的城镇景观具有混乱、物质化和不和谐的色彩和特质。第一,劳伦斯认为英国城市的核心概念并未形成。“事实上,直至1800年,英国人还是绝对过着乡间生活的人,很有泥土气。几个世纪来,英国一直有城镇,可那绝不是真正的城镇,不过是一片片村落而已。从来不是真正的城镇,英国人的性格中从未表现出人的城市性一面”②D.H.劳伦斯:《劳伦斯随笔集》,黑马译,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劳伦斯认为英国人所建立起来的城镇只是一片片被糟蹋的乡村,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特瓦萧:“杂货店里堆着一堆一堆的肥皂,蔬菜店里堆着大黄和柠檬,女帽店里挂着难看的帽子,一个店接着一个店,丑陋,丑陋,还是丑陋。接下来是那个模样吓死人的电影院,外墙装饰是石膏和镀金的,一幅伤感的广告画上写着《一个女人的爱情》片名。”③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劳伦斯所说的泥土气息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包括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血性联系,它们是乡村的核心和灵魂,而被物质所裹挟的城市,其形态是丑陋的,其内核是空洞的。第二,劳伦斯小说中的城镇是物质化的中心,聚集着空虚衰败的灵魂,究其根源是人的异化。《白孔雀》中乔治表面上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但仍然感到畏惧不安;《恋爱中的女人》中伦敦城完全是一个堕落的欲望容器;《迷失的少女》中,“伦敦意大利人”④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圭肖普·卡利法诺是西西欧的表兄,他不理解爱尔维娜的选择,认为“她和西西欧结婚是屈尊下嫁。她失去了她的社会地位”⑤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以特瓦萧为代表的英国矿乡与英国城镇的关联点就在于人被物质化。传统农耕关系下,土地耕作顺应自然规律,春种、夏忙、秋收、冬藏,“农业并非是一种产业,而是人类社会和精神价值中不可替代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⑥Ford,Boris(ed.).A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Modern Ag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7,p.15.。农耕文化让人们依靠自然织就了一张血脉之网,大家既被这张网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保持着个体自身的独立,人们秉承着自然的法则,尊重自然本能的展现,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机器摧毁,人类生活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然性”⑦Bilan,R.P.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F.R.Leavis.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9.。煤矿业是工业时代的缩影,过度的物质欲求让人们无休止地掠夺自然,不断向土地更深处索取。矿乡地理景观的形成依托的是对劳动力的压榨获得的资本积累,相似的风景背后是身份的模糊引发的恐慌,“特瓦萧和伦敦五月市场或者肯辛顿这样时髦高尚的地方何其相似乃尔。眼下只有一个阶级了,那就是拜金阶级,男女都拜金,人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钱的多少和欲望的强弱”⑧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第三,接受美学视角下,城镇景观始终处于一个匆忙、压抑、阴暗、放纵、堕落的格式塔,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悠闲、宁静、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景提供的视觉体验和心理感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伯顿太太眼中的特瓦萧村是负面风景形态的典型,“这里的生活看上去丑陋、混乱得吓人”⑨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她把特瓦萧村人们的生活概括成完全围绕着金钱和欲望而展开,“这些小子脑子里只想着花钱享受,女孩子们也一样,只不过想的是衣裳,除了这个什么也不当回事”[10]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矿工们的目的“只是想多挣俩小钱去俱乐部花,或者去谢菲尔德找刺激”[11]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等他们拿到钱,就在周六下午前往谢菲尔德或诺丁汉,“上米卡多之类的高级馆子吃茶点,去舞厅跳舞,去看电影,或者去‘帝国’”[12]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他们沉浸于赌马的疯狂,或者去看“瞎编乱造的情节剧和爱情片儿”[13]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而把踢足球看成是“干苦活儿”[14]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所谓的信仰和主义只是他们获取金钱的手段,“他们没钱的时候,就去听红色分子的宣传鼓动,但没谁真信那些话”①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当金钱的意义打破了心灵的平静,放纵的序幕开启,满足欲望成了人们的唯一追求。
三、家园风景构型背后的伦理焦虑
在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中,家园风景构型的实质是城乡变动导致的伦理焦虑,并对由此产生的怀旧诉求的关注。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劳伦斯“偶然生活在一种边界上,工业的英国与农业的英国俱在眼内”②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种双重视角让他感知、审视和剖析英国时能另辟蹊径,通过对人地关系的变化来呈现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包括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适应身份的变化而产生的质疑和因现实对传统的打破而导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
乡村劳动力在身份上日渐向雇佣劳动力转变,人与土地的联系变得不再紧密。劳伦斯对煤矿业曾经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切身的体会。从劳伦斯的祖辈开始,他的家族和煤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出生和居住在煤矿公司的房子里,直接或间接依靠煤矿公司生活,“关系密切的劳伦斯家族的中心在一英里之外的布林斯里,亚瑟的父母亲约翰和路易莎住在石矿村舍,还有他当矿工的兄弟乔治、两个已婚的姐妹艾玛和莎拉”③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石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劳伦斯的祖父约翰“给煤矿公司当过裁缝”④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石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父辈这一代,“劳伦斯的父亲和三个叔叔都在煤矿干活”⑤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石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劳伦斯的叔叔沃尔特曾在劳伦斯父亲的矿井工作,“沃尔特的六个儿子后来都去当了矿工,四个女儿都嫁给矿工”⑥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石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另一个叔叔詹姆斯则死在布林斯里的井下,劳伦斯的父亲亚瑟也一直在煤矿工作,直到退休。在当时的伊斯伍德,劳伦斯家族只是千万矿井劳工家族中普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是伊斯伍德矿工家庭的普遍写照,“一份统计表明,伊斯伍德‘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劳伦斯出生时有四千五百人:包括妻子、孩子、火车司机、铁路工人、装货工、检查过磅员、矿工、职员、经理)‘靠采煤为生’”⑦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石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无论社会地位如何,人们被同一个身份联系起来,这个身份就是矿工。这个身份以绝对的优势成了压倒其他一切身份的存在。由于矿井工作的高风险,矿工的死亡也已经不足为奇,他们失去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只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矿工,女人很快就会再嫁,“是这一个男人还是另一个,没多大关系。他们都是矿工”⑧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矿井用钱捆绑着矿工,他们只能选择被卖给矿井,适应矿井的节奏,用钱折算一切,“他们对道德不道德不感兴趣——道德不道德都差不多一回事——只是个井下的工钱问题。英格兰一位最有道德的公爵每年从这些矿井获得二十万。道德就这样完结了”⑨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矿井对于人的肉体和生命的掠夺,使得在家庭中“他们只是没用的废物——一台站着的机器,一台下班的机器”[10]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表面的繁荣却蒙蔽了人们的双眼,阻碍了人们对背后存在的问题的发现。或者说,人们已被眼前的利益所征服,把机械化、工具化的生活方式视为常态,从身到心都已无力去思考和探索自我存在的意义。劳伦斯看到了这种危机,为了给迷失在自己营造的常态中的人们迎头痛击,选择了以自然为参照物,凸显了人的异化。
《白孔雀》中乔治的生命逐渐走向枯竭与他和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脱离是紧密相关的。离开了斯特利磨坊的乔治失去了生命的活力,疾病缠身,等待着死亡。虽然结局凄凉,但离开斯特利磨坊却是乔治无奈却又必然的选择。当西里尔问到乔治将来的打算时,乔治的回答是“未来自有未来的办法”[11]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3页。。他解释了这一想法中的无奈:“这是把奶头从嘴里抽出来,让奶流走、发酸。”①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3页。他心里明白土地是他生存的根本,却无法挽救现实的局面,因为农耕生活生存的环境得不到保障,“整个河谷越来越荒芜,越来越无利可图了”②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8页。。坚持直到坚持不下去,是他们能做的唯一选择。最终,乔治一语道破了商业资本运作下农民对身份的迷茫:“事实上,我们靠的是卖牛奶,靠的是我给镇议会运货。你不能说这就叫农业。我们是农民,是卖奶人、蔬菜水果商和运输承包商的可怜混合物。这行当风雨飘摇呐。”③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2-93页。尽管乔治离开斯特利磨坊后生活变得富足,但却失去了心灵原有的平静,“我赚的钱不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每当我在格雷麦德教堂后的山坡上耕种,收麦时,我就感到,是否干下去我并不在乎。……上星期我通过各种方式纯赚了五镑多钱。可现在我却情绪不安,心中不满,似乎渴望着什么东西,但又不知到底需要什么”④D.H.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刘崇丽、王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99页。。
乔治体验到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身份变化所带来的陌生感、恐慌感与无助感,甚至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产生了怀疑。而更多的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者说来不及意识到就被裹挟进时代的潮流中,不知不觉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陷阱,并甘之如饴,成为劳伦斯所说的新人:“今日的英格兰正培育出一类新人,他们在金钱、社会和政治方面过于用心,而他们的本能和直觉却死了。”⑤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虹》中小汤姆·布朗温就被认为“提高了玛斯的优越地位和新奇感”⑥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原因就在于“他长着黑黑的睫毛,神采奕奕,性情温厚,举止出众,一幅见过大世面的气派,加之他又在伦敦供职,这就给玛斯增了光”⑦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与因生气而变粗暴的老汤姆相比,脱离了农村的生活让他多了一份节制和理性,却失去了源自泥土的率真、活力和热情。小汤姆给人们的印象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又对人敬而远之”⑧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然而这样的形象却让人产生生疏感,外表的礼节掩盖的是人与人内心的距离。所以,尽管被他礼貌地对待,“人们感到心里挺不是滋味儿的,在考塞西和伊开斯顿人来看,他属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⑨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这种距离感让他无法在人们面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在老汤姆死后的葬礼上,厄秀拉在花园里看到的是脸部扭曲、呼吸急促、浑身颤抖、目光无神,“就像一头痛苦的动物”[10]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的汤姆舅舅,而在屋子里看到的却是“肃穆的神态似乎显得有点做作,是装出来的沉痛”[11]D.H.劳伦斯:《虹》,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的汤姆舅舅。在《圣经》中,大洪水是神对人在地上所行罪恶的毁灭,《虹》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小说里没有承蒙神恩的诺亚方舟,布朗温农舍无法拯救溺水的老汤姆。玛斯大洪水之后,新汤姆代替了旧汤姆,随同老汤姆一起离去的,还有赋予他生命和活力的农耕传统,其背后是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的茫然与无助。
人的自然本性虽然被压制却无法被彻底抹灭,在现实压力下它静静沉睡在人体中,劳伦斯笔下矿工们身上时而闪现着的自然本能的光辉就是对这种摧残和压制的最激烈控诉。《儿子与情人》中的莫雷尔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醉酒后还把自己怀孕的妻子赶出门外。因为与妻子不和,除了提供家用,他在这个家里就是一个多余的存在。而这个酗酒且脾气暴躁的父亲却带给了孩子们鲜活的快乐,他兴致勃勃地边和孩子们玩耍边修补家庭用品,用长麦秆麻利地甚至可以说是动作优美地给孩子们做引信,活灵活现地给孩子们讲故事。可能连劳伦斯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描写父亲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的场景时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温情:锻铁时,“看见他拿着一块火红的铁奔到洗碗间,嘴里一面叫着‘闪开——闪开!’真叫人高兴。……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看着那金属突然熔化开了……”[12]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忙完手头的活计,孩子们缠着父亲讲故事,“莫雷尔讲起故事可真来劲,叫人一听就觉得塔非为人狡猾。……塔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且大家都爱听”①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页。。《迷失的少女》中爱尔维娜在一位矿工的带领下参观矿井,矿井内拥挤的结构,封闭的环境,沉闷的空气,坟墓一样的黑暗和矿工裸露着的粗糙丑陋的手臂包围着爱尔维娜,“她吓呆了,但也被迷住了”②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这种让她吓着又着迷的东西就是矿工在向她讲解自己的工作时身上所展现的本能力量。这是对地底下世界的直觉。这种力量联系着矿工与煤矿,让矿工与矿井化为了一体,让她感觉到“某种东西,某种不受控制的黑暗力量要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③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被工业文明重新塑形的身体变形有多严重,本能的力量就有多强烈。这股被光明世界所压抑的,被看作是属于地下世界的力量“终将导致强加于他们的后日秩序彻底崩溃”④D.H.劳伦斯:《迷失的少女》,郑达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劳伦斯在小说中透过怀旧形态和负面形态两种家园风景构型,揭示工业时代人地关系的困境,极具审美价值。不同形态的家园风景中贯穿着一条精神主线,即人渴望在其中获取的家园感,一种对稳定、安全、温暖、完整和有机的状态的追寻。对矿乡景观和城镇景观的拒斥可以看作是劳伦斯在现实意义上对抗工业文明的重要武器。两种家园风景构型中展现的个体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体验差异,形成了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从自然到人造,从乡村到城镇,风景变迁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力,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的导论中肯定了风景作为文化中介的作用,指出“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透过家园风景的构型,城乡变动背后的伦理焦虑构成了文本潜在的意义指向。从家园风景构型中不难发现,“‘实用主义的’忙碌驱散了古老的家庭单子”⑤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1页。,植根于农耕传统的家园精神结构受到现代工具理性的冲击,人类在活动空间上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却离家园越来越远。从传统到当下,从农耕到工业,伦理焦虑使家园风景中的宁静、和谐、圆融的稳定感被打破,异化的阴暗面呼之欲出。追溯伊斯特伍德的矿乡发展史不难发现,劳伦斯把家园风景叙述置于帝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升华到对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的反思,“他摈弃的不是社会的要求,而是工业社会的要求”⑥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从读者的视角而言,两种家园风景构型所形成的视觉冲击深度呈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失落家园之后,人类会走向何方?劳伦斯无法给出未来的答案,而是让古老英格兰在“依恋老英国的遗风”⑦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的怀旧诉求中登场,成为家园风景负面形态的视觉参照系。家园风景构架下的古老英国空间出现了裂痕,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成为破坏秩序的不可控制的空间矢量,工业时代的资本积累与农耕文明走向没落之间的叙事张力着力于家园风景,并通过风景的对比实现了对历史的溯源与对现实的批判。虽然劳伦斯并未对人类的归属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但他对人类命运所做的思考和对社会观念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