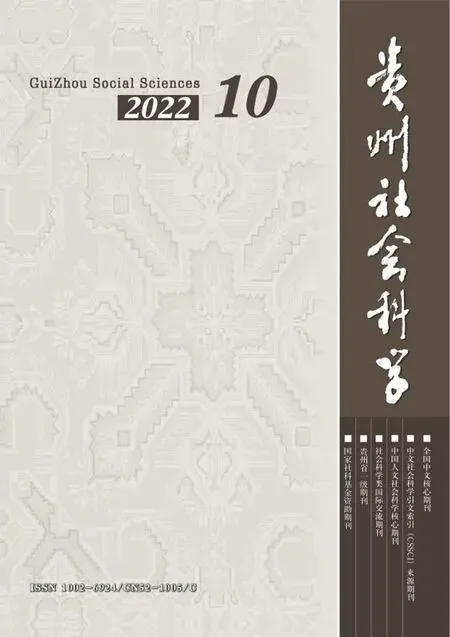论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廖志华 颜 敏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新世纪乡村叙事与传统乡土文学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整体而言,在思想意蕴方面,它不再承担启蒙教谕的功能、不再突出对乡土田园的眷恋和对宏大叙事的热衷。在审美上,现代乡土小说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的特点不再被突出强化,趋向弱化和消失,没有了写意化诗意化的风格。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创作大多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展开,在历史长河和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中国的静态恒常与躁动变迁都有关注,加上创作主体审美新质素的影响,这使得新世纪乡村叙事的策略有着特别之处。
一、乡村长篇的日常生活叙事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常生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关注的焦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1]成为文学叙事的追求之一。日常生活叙事成为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一个突出叙事特征,成为很多作家的艺术追求。从现实因素看,乡土世界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集合体,它倾向日常、务实,比较注重生存伦理,加上外部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人们普遍追求日常的实用性和经济效益。
当代文学从开始就存在关于乡村日常叙事的创作,但叙事基调比较单一明朗和叙事内容带有程式化,日常叙事是镶嵌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和新农村美好图景之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乡村主体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和具有可塑性、前瞻性的品质,带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如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新时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鸡窝洼的人家》等。到了新世纪,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和乡村的发展变迁,乡村世界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整体性,其内在的经济、文化和传统伦理秩序出现很大的松动,乡村“总体生活”特征慢慢变得模糊起来。乡土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更进一步推向前台,呈现出世俗化、碎片化的特征,充满主体情绪的焦灼感。
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在时空上展开历史书写和现实书写,两类书写都涵盖了日常化叙事。历史书写中的日常化叙事,突出地揭示乡村社会的恒常和乡村主体的精神心灵,以乡村日常来冲淡化解外在历史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矛盾冲突,昭示了日常生活和乡风民俗的永固性,如铁凝的《笨花》(2005)、周瑄璞的《多湾》(2015)、胡学文的《有生》(2021)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2009)等。《笨花》尽管将整体时代背景放置于波诡云谲、动荡战争时期,却着笔于笨花村在独特历史时代中的日常生活,呈现乡土的习俗和乡人的精神风貌。向家人在祖母同艾的教导下谨守着家业家风过日子,一根柴火棍子和下锅的米粒都是家产,是祖父向喜在外打仗拿命换来的,马虎不得。向喜由农民变为军人直至军中权贵,依旧保持着笨花人的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与军阀分道扬镳后在保定过着闲居寓公生活,向喜身穿灰布长衫,惦念着笨花村黄豆做的豆浆,院子里种着家乡的灯笼胡萝卜,解甲为民落叶归根回到笨花,坦然地做起了粪厂经理,泯然众人。一些农事习俗笨拙而又恒久地存在于笨花村。西贝家对劳作收获非常虔诚,西贝牛甚至将掏粪积肥当作是终生的心愿。男女钻笨花地里的窝棚,行男女之欢,成为笨花村的一种日常惯例,这里没有乡风道德的约束,更多地充满了乡土民间日常的人性和欲望。
周瑄璞的《多湾》写的是一位乡间女性季瓷的故事,以她为总枢纽串起了章家的日常生活变迁,于日常中描绘出家族史和人物的灵魂性格。尤其围绕季瓷展开的日常生活叙事,季瓷只身徒步到债主家不卑不亢地还了章家的欠债,挎着一篮馍、沿铁路用小脚走几十里路去学校看望儿子,跑十来趟到汉口卖烟叶挣钱贴补家用,将子女供到城里并帮他们把小孩照望大,临终给后辈只留下两个装有日常物件的箱子。小说在林林总总的日常叙事中,勾勒出一位立体化的乡村女性形象,她有地母般的胸怀,柔弱而又坚强,如水一般沉静,绵远流传。
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现实书写,整体而言、通过日常叙事描绘了乡村的故事。用小说中乡村的混乱芜杂、萧条衰败的趋势和乡村世情、伦理变迁,启发人们思考乡村现代化的问题。在美学上,日常叙事则是碎片化、细节化的呈现,采用人物心灵透视的写法。
贾平凹的《秦腔》(2005)和孙惠芬的《上塘书》(2010)都对一个村庄的日常进行了描绘。《秦腔》里的清风街寂静而衰败:村里没有资源村民贫穷,遭遇断电和地旱缺水,农民外出打工土地荒芜。各种乡俗宰制着人们的心理,如在家设香案祈祷给长辈添寿、在水碗里立筷子驱鬼。乡村伦理在坍塌,有父子兄弟翻脸成仇人的,夏天义的儿子儿媳不孝顺,家庭吵闹不断。夏天义在七里沟於地想要维护土地的荣光,保持农民种地的本分,最后不幸被垮塌的山体湮埋,夏天智努力要发扬传承的秦腔艺术在现实中受冷遇,被人们遗忘抛弃。小说着力于乡村日常的多样性,只要在清风街出现的人和事都被纳入日常叙事中,“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2],就像打核桃一样,永远是打不净的。这里,日常生活显然失去了整体性和总体性,没有历史的厚度和理性观照,“它虽然是乡土的挽歌,但它里面没有怨气和仇恨,也没有过度的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境界”[3],小说以日常叙事呈现乡村面貌的一个方面,清风街成为中国农村的艺术性写照。
孙惠芬的《上塘书》对上塘的日常生活书写,则展示了上塘村的变与不变。开头叙述上塘的地理,上塘村由前街延伸到后街,后街大多是外出打工的新农民所建的新房,而读了书的人则在城里买房,但上塘人依旧讲体面,老老实实地种地种庄稼;上塘的“政治”在与时俱进,村民晚上看电视新闻关心北京和国家大事,日常中对村长十分尊敬和殷勤请客,但上塘人还保持某些不变的信仰,那就是人心公平的道义,有值得信赖的排解纠纷矛盾的主事人;上塘的交通通讯在延展,有官道大马路通往外界城里,但上塘人还会走山道甸道,这是各属于男人女人的世界的道路。在外界现代化的影响冲击下,乡村世界难以规避和保持独立封闭的系统,但于日常生活中流散着乡土自足的世界和处事态度,这是乡村现代化背后的潜流,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现代性的润滑剂。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2005)以返乡妇女木珍的经历见闻,铺写了王榨村的日常生活,村民大都在追求享受快活,闲时打牌在牌桌上消遣村里的琐事,对农事劳动失去传统的热爱和耐心。人们日常讲究的都是钱、盖房和谁谁外出打工。男女关系或混乱或相好,讲究金钱和没有羞愧感成为村里的常态。读书在村里无市场,花钱和赚钱、打工娶媳妇,成为村子的主要氛围。这里,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占据了村民的世界,吞噬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2018)围绕一位自私蛮横的乡村人物王宏阳叙述日常生活,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乡村宗族礼仪孝道的丧失,村民为名利而争夺,延及后代的恩怨,宏阳霸横一世又无端死去,在葬礼上族人上演了几出敷衍仓促的滑稽戏,甚至为继承分割财产而纷争大打出手,还有乡村男女粗俗的言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世界出现脱序的景观。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日常一片芜杂,乡村主体的精神也显得更为复杂,其中个人主义价值主导下的人际关系的负面性显现,“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4],这些都是建设乡村现代性应该关切的。
此外,有些作品通过对人物心灵的透视,丰富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叙述,折射出乡村社会真实的现象,显得更为形象生动和深入。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路》(2019)通过写青年农民吉宽的心理来描写乡村日常的现实情形,乡村主体在进城和还乡路途上的挣扎。像吉宽这样自认为没出息、一点都不要强的懒汉农民,也被迫像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向前追求,从此岸到彼岸,却像是屎壳郎般做着无用功。这道出了现代化冲击下,乡村个体如何安顿人生的存在哲学问题。
付秀莹的《陌上》(2016)以日常生活为底子展开叙述,日常生活是散点化、片段化的呈现出来,林林总总表现了乡村的多样、丰富生活情状。小说人物以女性为主,女性的日常心事显得精微而耐人寻味。如翠台与香罗的来往附和,翠台挖空心思给香罗包了她爱吃的饺子送去,只是想求香罗给儿子介绍工作,见出女性之间关系的微妙,利益与场面是日常生活的核心。芳村的日常伦理既是朴素的,又显现出崩塌的趋势。老人乱耕的儿女在城里,回来看他吃一顿饭就离去,留下他与孙媳妇、重孙子留守一个院子,乱耕内心的尴尬委屈无人知晓,“如今村里这些个新房子,倒是高楼大院子的,气派倒是气派,可就是一样,干巴巴的,住着也难受”,“没有树的村子还叫个村子?没有树的院子还能叫个院子?他真是搞不懂,如今的人们怎么做人都这么干燥,一点滋味也没有了”[5]。人情变得淡薄,人心冷漠,导致了乡村原有的家庭伦理格局难以维系,这或许是现代化进入乡村所带来的矛盾与困境。
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一方面在历史长河中徐徐展开,激活了日常生活和乡风乡俗,还原了被忽视被遮蔽的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宏大叙事是日常生活和乡风乡俗的背景,这彰显了乡土中国的稳固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在现代化影响下乡村世界的变迁,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碎片化及荒芜化似乎成为乡村世界的一个魔咒,乡村现代化的有序发展理应破除这一魔咒。
二、多元独特的叙事视角
视角是作者所选择的观察故事的角度,体现了作者传递作品内容的技巧和作品的审美意蕴及张力。法国学者热奈特等人把视角分为三类,即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叙事视角即采用了这三种,尤其在使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和外视角方面,显得独特而充满审美意蕴,并且在一些作品中进行了视角转换,以此展现出立体化的审美空间。
全知视角是指叙述者以全知全能、俯瞰一切的姿态进行叙述,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从整体上把握操控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经历命运,能够预知结果,紧随人物,甚至潜入人物内心,表现人物情感。全知视角叙述能全景式的描绘生活,更好地把握乡村历史时代风貌与乡村主体伦理精神,具有总揽性总括性,体现了一种写作叙事的策略。《笨花》即以全知视角叙述历史、笨花村的风俗和村民的日常生活,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全知叙述下呈现出总体性和稳固性,显示了乡土中国的恒常,揭示它的超稳定性所在,并在一种舒缓从容的叙事语态中抵达乡村的本真。《多湾》以全知视角俯瞰历史和时代,讲述了多湾章家四代人绵长而动人的家族史,以及乡村向城市进发的历史进程,这是整体性的书写。又以全知视角也即第三人称叙述主要人物季瓷身处历史时代漩涡中的经历和行为,并深入人的内在精神感情进行发掘,展现了一位地母式女性形象,她拥有生命的激情和韧性,仁慈宽厚、细腻而大方的品格。小说这种全知视角叙述明显地蕴含了对乡村女性赞美的伦理倾向。《陌上》也以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芳村的日常生活,揭示了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下乡土社会的新变与异化现象。又以一种静穆的姿态潜入乡村女性的心里,表现她们的烦恼和心事,她们没有哪一位是故事的主角,但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观照下,女性的日常与心事显得密实复杂,构筑起了当下乡村的丰富生活图景。
内视角相当于托多洛夫的公式“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也就是普荣所称的“同视角”。叙述者在叙述时将叙事视角内化为小说人物的视角,通过人物的视角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和表述,并描绘人物的心理细部。在情感立场和道德伦理上,叙述者与小说人物是合二为一的,也隐现了作者对人物的赞许和理解,读者也紧贴小说人物的内心,在理解生活上与其保持共振的频率。从中也看出作家的艺术追求,在书写乡村的时候,努力把握历史时代的脉搏,精微地传达出乡村人物的精神情感,塑造出独特的乡村人物形象。
《吉宽的马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叙述者化为小说人物吉宽,对自己作为农民的性格本质作自我陈述,细腻地呈现了吉宽的心理,表现他对乡村、城市和世情人生的理解,看似单纯糊涂的吉宽对人生却看得透彻明了。叙述者对人物的行为和认知蕴含理解同情的伦理立场,甚至看出作者隐含的对这样一位纷繁世俗环境下的乡村人物的褒扬态度。《有生》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祖奶乔大梅的一生。乔大梅经历过灾荒、饥饿、战乱、瘟疫、家破人亡、运动批斗,叙述者与她融为一体,也是感知者,用生命体验去感知人物的命运遭际,尤其是叙述乔大梅作为接生婆的神圣感,“生与死只一线之隔,我必须尽全力将孩子平安引到世上,那是天命。天命,怎么可以违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解开脱,只是想说,进入那个世界,我不再属于白果,不再属于自己”[6],叙述者一同进入乔大梅的接生境界,感知她为上苍赐予的接生天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的忘我境界,读者也为之动容。这样的内视角叙述深刻地揭示了民间社会的真实情形和个体生命的纯粹性,是对以往全知视角的“宏大叙事”的瓦解。贾平凹的《高兴》(2007)中叙述者将叙事视角完全挪移到小说人物刘高兴的视角上,叙述刘高兴在西安打工的经历。表现了身处城市渴望被城市接纳而灵魂精神本质上属于农村的农民工撕裂的情感世界。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2016)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万泉和的行医经历,“我”年轻时被强推去学医,当了一名大队赤脚医生,“我”不懂治病,缺乏医术,闹出乱治错治的例子,荒唐可笑,但村民依旧认“我”为医生,有病必上门找我,农民就是认这个理……“我”又经历乡村医改的变迁,充满辛酸和无奈。内视角的运用,使得叙述潜入人物内心,真切精妙地揭示了乡村赤脚医生的历史状况 ,对其遭遇有道德伦理上的体认。
外视角是普荣所称为的“客观”叙事或“行为主义”叙事,相当于托多洛夫的公式“叙述者<人物”。这是限制型视角,叙述者只做客观叙事,扮演观察者角色,仅限于描写可见的行为而不加解释、不掺杂主观介入性评价,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申丹把外视角细分为两种,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2016)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但“我”主要不是讲述自我的故事,更多的是充当一个观察者兼叙述者的角色。通过“我”来观察当下农村人事变迁和土地的流转,描绘了乡村整体上的衰败和荒芜,“我”担当叙述弟弟的遭遇的一个功能角色,“我”叙述弟弟像一只老鼠,有神经病,全家人都不接纳他要抛弃他,“我”把弟弟带出去丢掉了,内心不安转而又去寻找弟弟。最后王村征地拆迁因弟弟是惟一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的人而保留住了两亩地。第一人称“我”在小说里不动声色地观察和叙述,显得很客观,处在被叙述的神经质弟弟与混乱不可理喻的乡村世界、贪婪鄙俗的人们形成对照,而恰恰是“我”弟弟为村庄保留住了两亩地,为人们留住了一丝乡愁。
第一人称外视角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运用,即作品中的“我”的视角是残疾人、畸人或者动物的视角,以此来观察周围人的言行和人世的情形。《秦腔》采用引生“我”作为称叙述视角,引生被清风街人视为“疯子”,已然游离于正常世界,但他得以自由地游走在清风街上,“看”到清风街的衰败和纷乱的日常生活,有时候靠耳朵在听周围的情形,“到处都是人,众声喧哗,杂语纷呈”,“这是听的小说”[7],“我”不介入事件之中,不透视人的内心,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叙述,显得客观而真实,有时又变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小说这种叙述描摹了城镇化进程中乡土的破碎状况以及乡村主体精神的荒芜,表明乡土叙事的宏大历史的坍塌。关仁山的《麦河》(2010)以瞎子白立国“我”展开叙述,揭示乡土的骚动与恒定。作为残缺人的“我”有与阴间死人对话的功能,小说在主线中又穿插了“我”叙述鹦鹉村,是鹦鹉村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而在现实中叙述者也只是旁观者,虽然“我”和主人公曹双羊是铁哥儿们,面对曹双羊要搞土地流转,大胆创建麦河道场的品牌,对企业实行现代管理制度,“我”只是心里替曹双羊捏一把汗、静观事情发展。莫言的《生死疲劳》(2012)的叙述者“我”化身为一头叫刁小三的猪,刁小三和世俗的不合作,它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对历史和世人的揶揄嘲讽,都使得叙述变得恣肆无节制。这样一种动物叙述视角,便利而合理地游离于世俗世情,以一种超越时空的姿态来旁观历史时代和人生,道出其中的荒诞悲剧和轮回命运,显得颇有深意。
三、隐微的反讽叙事
反讽概念源自古希腊戏剧,指戏剧角色采用佯装无知的行为方式,让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陷入窘境。此后,反讽渐变为一种修辞格。现在它更多是作为“后现代”的反讽解释。常被视为是“言此意反”之类的“比喻”,视为一个哲学立场[8],即矛盾性、不确定性及含混多义性的哲学立场。新世纪乡村叙事,一些作家在创作上就流露出“后现代”反讽叙事的特征,如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2021)、东西的《篡改的命》(2015)。乡村人物的话语表达很多情况下是言意相反的,含蕴着乡间的幽默讽刺气息。同时包含诸多的含混性、吊诡性,这为乡村小说的反讽叙述风格提供了现实素材。
首先是言语反讽,也叫字面反讽,即语言层次的反讽,通过改变话语叙述的常规,将不同时空和不同话语系统的语言有意并置在一起,误置语境,混淆了语言的惯常思维逻辑,从而产生内在的反讽张力效果。《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写麻县长说,“计划生育可不仅仅是裤裆里的事,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资源枯竭、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地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9],粗俗的言语和宏观高雅的言语组合在一起,达到幽默戏谑的反讽效果。孟小红给前任支书和当选的村长孔繁花分别送匾“一岁一枯荣”“一花一世界”,诗意美好的语词置于小说语境中解读,极具反讽性。阎连科的《炸裂志》(2013)小说中的朱颖在省城卖身,有了成就后开起了娱乐城,带动炸裂村人致富,乡长给她立碑:“致富学炸裂,榜样看朱颖”。正义光鲜的语词之下,透露出滑稽荒唐,道出某些乡村发展的悖论性。
其次是情境反讽,这是主要的一种反讽形态。指的是人物命运、故事结局与预设期待相背离,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巨大反差,或者是指历史时代与乡村社会内在的悖论、荒诞不可解,造成了荒诞离奇的效果。这是从文本整个的情节结构来考察反讽,也是一种明显的反讽形态。《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女村长孔繁花能干,雷厉风行搞计划生育,果断治理纸厂的污染,办事公平,也不失有手段懂得惠及村民。但表面对她服从的下属都各怀鬼胎,尤其是团支部书记孟小红当着众人奋不顾身地跳入墓坑,以此阻止外村人在官庄村闹事,表面看孟小红维护了孔繁花的尊严,实则破坏了官庄村吸引外资的形象。最后村委换届选举,孔繁花意外地落选,孟小红当选,村民在孟小红的号召下纷纷入股纸厂,等待分红,繁花茫然了。小说表层结构是孔繁花执行政策,团结基层干部,带领全村致富,朝着理想迈进;深层结构却是人心人性的暗流涌动,下属各谋私欲、暗中破坏,村民持观望态度并被利益所牵掣,基本的亲情友情伦理也成为点缀,人心不古。小说中的这种存在状况正与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破碎化状况不谋而合,因此,小说整个的情境充满着反讽意识。
《炸裂志》写一个叫炸裂的村庄改成镇、县、市直至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表面情境是现代化、工业化的辉煌前景,背后交织着土地的流失、城市化建设中的乱象和人性的倾轧、权力的争夺,各种荒诞离奇的现象。《篡改的命》写汪槐为摆脱农民身份,想方设法进城未果,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儿子汪长尺高考升学不成进城当临时工人,这对他来说也是莫大荣耀。汪长尺为实现进城的夙愿,不惜让自己的儿子改姓做了城里人的儿子,甚至以投河自杀的方式来斩断与儿子的血缘关系,从而使儿子彻底成为城里人。农民梦想脱离土地变为市民,在小说中以极端的方式从地理上甚至精神血缘上来割断和乡村的纽带,清除掉自己的乡村记忆,小说情景荒唐而极具反讽,却又充满了精神上的分裂和悲剧感。故学者认为东西的小说在艺术上秉承了先锋文学的精神[10]。
再次,从叙述语调和叙述视点来考察反讽的意蕴。语调反映了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情感态度,它关涉叙述者或接受者与所讲故事之间的关系,当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形成乖离,与叙事意旨背离,就会产生反讽的效果。它带有较强的主观性,需要细微地体察。阎连科的《坚硬如水》(2009)写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对沉溺于情欲不可自拔的乡村男女的故事,他们在言语上不时流露对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调侃和黑色幽默的语气,折射出反讽的审美效果。《有生》在叙述祖奶乔大梅“我”在村人在自己跟前膜拜祈求护佑、侄子把“自己”奉为神仙要为自己塑像立功德碑的时候,插叙“蚂蚁在窜”的场景,与人物忐忑不安的心理形成呼应。用委婉温和的叙述语调,道出乔大梅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凡人的品性,与部分人的趋利避祸、追逐功利形成内在的反讽张力。
视点反讽,即是采用异常变形的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这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和间离反差,从而产生反讽艺术。反讽往往源于理解上的不一致,叙事反讽乃是视角之间的差异所实现的功能,视角操控本身固有反讽的可能性。[11]《生死疲劳》(2005)中让死者投胎化身为猪或驴,从动物视角展开叙述,审视历史时代和品评人物,语气上充满讽喻和批判,让读者进入动物的视角,去感受体会,形成“陌生化”感觉。
四、“新时代”的新面貌
在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创作中,这些年出现很多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反映脱贫攻坚的创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小说体现了新的叙事面貌,一方面,呼应国家政策和主流话语,努力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表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学创作的人民性宗旨;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属于现代乡土小说的延续和发展,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审美。
首先,作品中历史叙事与乡村新现实叙事的交叉融合,使得脱贫攻坚题材创作既突出乡村世界的纵深历史,富有历史感和文化脉动,又落笔于乡村新现实、新气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中国故事扎根于当下的大地和人民之中,它又有历史的渊源。这类叙事出现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如赵德发的《经山海》(2019)、关仁山的《大地长歌》(2018)、滕贞甫的《战国红》(2019)、李明春的《山盟》(2017)、吴仕民的《旧林故渊》(2018)、路尚的《安农记》(2016)等,但具体表现形态又各有不同。
一方面,所叙历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致富的启示性源头及现代性建构基石。赵德发《经山海》中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小引“历史上的今天”,下乡任职女干部吴小蒿喜欢看《历史上的今天》一书,对照历史上的今天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行为,激发对扶贫工作的干劲,激励自己服务好乡村建设,致敬历史文化。楷坡镇有关腮岛出鳃人的历史,追溯秦朝历史的鼓乐《斤求两》,三百年前护佑百姓的鱼骨庙,促使吴小蒿抓落实搞“鳃人之旅”的旅游项目,发掘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鼓乐的价值,建渔业博物馆。这给楷坡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回报,树立了新农村形象。正如吴小蒿本人是学历史的,在她看来“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有点儿历史感。没有历史感的人,对当下的时代与生活,就不能有深刻的感受与思考”[12]。吴仕民的《旧林故渊》回溯了锦鲤村的传说和历史文化,一千多年前祖先迁徙至此繁衍成湖村,明清建筑和鱼巷,六句歌谣,这些构成锦鲤村田园自然、文化深厚的湖村之美。20世纪70年代锦鲤村人工修梯围田、建起锁波大堤,此举却破坏了湖村的自然生态,带来系列生态问题。历史的正反经验教训,促使锦鲤村下决心炸掉锁波大堤、还田于湖,回归生态发展、文化兴村的道路。历史文化与乡村现代性建设在此交汇碰撞。
另一方面,历史叙事与乡村脱贫的现实书写构成互文性结构。如滕贞甫《战国红》写陈放选择偏远的辽西柳城驻村扶贫,是为了当年爷爷的遗愿。这是陈放坚定决心和初心助力柳城村脱贫的精神动力,他在柳城村成立糖蒜合作社和种植合作社,帮助村民脱贫。老队长柳奎在集体时期带领村民在鹅冠山上修的七道梯田被雨水冲毁,在等待有缘人接续历史,陈放提出在山上栽大扁杏树,并成立鹅冠山红色旅游项目,为柳城村民带来经济效益。历史得到了延续,扶贫攻坚的现实与革命历史形成互文。李明春《山盟》描绘了石家三代人革命、助力扶贫的历史与现实的壮丽画卷。扶贫干部石承的爷爷当年参加红军,为乡亲摆脱贫穷是其夙愿,“大岩壁上刻着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凯子时刻铭记着,自己的靠山在这儿”[13],革命历史精神使石承改变一开始对扶贫工作的懈怠心理,义无反顾真心实意地投入工作,帮助贫困户凯子和冬哥脱贫。革命历史与扶贫现实在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延续的。
其次,对新时代乡村“新人”的叙事,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追求。“塑造新时代的新人”[14]是时代和历史的呼唤,是国家话语的体现。“新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的灵魂,主要包括扶贫干部,脱贫致富或创业的新农民,他们身上迸发出了乡村个体的生命力和活力,从“新人”这看到乡村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交织。对扶贫干部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他们运用基于城市现代文明的理念,帮助乡村脱贫的本领;另一方面,描写了他们积极融入乡村生活、认识理解乡民的行为。《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型干部,乡村的朴实和现代知识文明气集于一身,小说写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一样钻进玉米地里撒尿,顿觉自己本来就是田野里的一颗蒿草,这是回归本色,融入乡村的体现。吴小蒿在楷坡村落实“腮人之旅”项目,建渔业博物馆,造一片楷树林,坚持科技扶贫、教育扶贫,体现了现代性理念下的扶贫策略,与国家大力倡导的扶贫要扶智,变输血为造血式的扶贫相得益彰。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讲述了范少山带着青年人饱满的乡情从城市返回家乡,致力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他的身上有新型农民的新质素,即艰苦创业的干劲、带领村民致富的决心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以及现代技术。在范少山的带领协调下,白羊峪实施土地流转,建立专业生产合作社,整合资本、技术、知识观念,农民“用手机种地”,使用“互联网+”技术模式,发挥土地规模集约化经营优势,并且通过电商推广白羊峪的品牌农产品,最终村民都脱贫致富。小说叙述范少山喜爱《创业史》一书,再现梁生宝为集体买稻种的情节,范少山与社会主义创业者梁生宝遥相呼应,但他是具有新时代新农民面貌的创业者。
再次,叙事美学风格整体呈现出和谐圆润的特征,乡村诗意流布于叙事之中。乡村脱贫致富、美丽乡村建设与自然化生态化的乡村景色相融,尽显新时代乡村诗意之美。路尚的《安农记》写水稻插秧的季节,碧空晴日,人们在田里快乐地劳作,一行行插秧机插得整整齐齐的秧苗就像是列阵的士兵,等待检阅,又像是羞涩的少女,期待着长大,收获未来。王教授头戴草帽、挽着裤脚在察看秧苗,县长石润生走在田埂上,与专家畅谈发展安农产品、树立品牌的安农富民的规划。这可谓新时代乡村壮美的诗意图景。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的隔阂似乎慢慢消失,乡村生活中的人物流露出诗性自然及享受乡愁的情绪,这属于乡村的本色,它弥补了现代城市所缺乏的诗意乡愁。关仁山《大地长歌》中不时表达对乡村生活的诗意盎然的情趣,一派田园风光,引人的诗兴大发。乡长兼书记的马童力对乡村满怀诗意,面对滦河这片土地的美景,当场朗诵古诗,视察稻田基地不禁诵读起辛弃疾的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连村干部周东旺也跟着朗诵起诗来。这里以一种仪式化般的场景道出乡土诗意的自在性。
总之,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在叙事策略上的营造,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创作实践: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乡土描写的底色;表现乡土的诗意和失意、衰退和发展并存;叙事手法的多样,能够灵活自由而真实地表现乡村现实,全景式地透视乡村的内在,使得对乡村现实的表现更为立体和多样;尤其关于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书写,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交融,对乡村“新人”的叙事及诗意乡愁的表达,构建起了乡村现在与未来发展的现代性美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