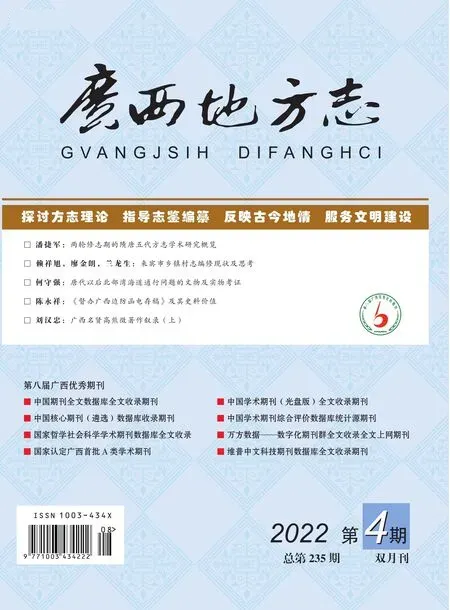《督办广西边防函电存稿》及其史料价值
陈永祥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2200)
郑孝胥(1860—1938年)是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人物。国家图书馆藏有《督办广西边防函电存稿》(以下简称《函电存稿》),三册,不分卷,为郑孝胥在担任广西边防督办期间致各方的函电及公文底稿。该《函电存稿》于2005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收入《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中影印出版,同年还被收入茅海建先生主编的《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由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重新影印出版,《函电存稿》仍收录其中。尽管《函电存稿》先后三次影印出版,且首次影印出版距今将近二十年,但仍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利用《函电存稿》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作详细的介绍,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珍贵史料的关注和重视,推进相关研究。
一、郑孝胥广西边防督办之任
郑孝胥出身封建仕宦之家,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之幕,后随李经方出使日本,至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此后又入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幕,襄办商务、学务、营务、建造铁路等事,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之初,作为张之洞的核心幕僚和得力助手,为张之洞谋划、推行洋务和自强新政,得到张之洞等人的认可和称许,并多次获得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保荐,成为有名的能员干吏。
郑孝胥广西边防督办之任,得之于岑春煊之荐,其中经过不无曲折。郑氏与岑春煊本无来往,却与岑春煊之弟岑春蓂过从甚密,且郑孝胥之名屡见于各省督抚荐章,岑春煊早闻其名而欲招致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调署四川总督,即欲延揽郑孝胥入蜀助办商务、矿务,并通过岑春蓂一再游说于郑氏。此时张之洞也决定委任郑孝胥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尽管岑春煊备受清廷宠信,时望正隆,但相对于边僻省份的四川而言,江南制造局则系郑孝胥所谋求的“洋务紧要处”[1]。因此,对于岑春煊之邀,郑孝胥虽有所动,但并未应允,而是接受了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委任,并声称要用五年精力将江南制造局办成中国第一制造厂。[2]不过,岑春煊并未因此放弃,仍在积极谋调,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请将郑孝胥调往四川,充任商矿大臣。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清廷允岑春煊之请,命将郑孝胥发往四川,随同办理商务、矿务。对此,张之洞颇为不满,虽经奏留而不得,而郑孝胥之意态则颇为微妙,他虽然坚决辞去江南制造局差委,但并未打算立即入蜀,而是托故请假逗留上海,意存观望。正当郑孝胥游移不定之时,清廷于是年三月调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郑孝胥入蜀之行遂作罢。
当时广西由边防游勇问题引发的动乱愈演愈烈,蔓延全省,并且波及云南、贵州两省,不但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也给广西财政、军事和西南国防带来巨大的压力,引起清廷的重视。岑春煊甫接调令,即邀郑孝胥同往两广为之赞助,后又奏请将郑孝胥调往两广“随同办理一切要政”[3]。得到清廷准许。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随岑春煊自武汉赴粤,被委任为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后又随岑春煊进入广西襄办军务,负责行营文案,成为岑春煊的核心幕僚,为岑氏谋划平乱之策。岑春煊抵任后,对广西军政进行大力整饬,一面将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等人奏劾革职,一面调集得力军队,遴选将领,各专责成,分路剿办。他认为广西之乱源于边防,“综论广西全局,可虑者不在内地,而在边防”[4],要实现全省平乱,必须先靖边圉。鉴于广西边防营伍积弊太深,岑春煊在经过通盘考虑后,决定借调湖北武建军入桂驻守边境,并对广西边防军进行裁汰改编,调离边境,以消除隐患,得到了清廷的准许。
武建军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编练的新式军队之一,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开招成军。全军共2000余人,以旗为单位,分左、右两旗,每旗分四营,每营分三哨。两旗各设督带官一员,每营设管带一员,每哨则有哨官、哨长等,所有营、哨官均系直隶武备学堂卒业将弁,“皆从山东新建军调来”[5],为北洋大臣袁世凯“旧部得力将弁”,各营勇丁“均挑选年力青壮、朴实勇健之人充当”[6]。武建军兼具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两方面的因素,在清末的新军中尤显特殊。武建军初成之时,张之洞委游击张彪为督操官、郑孝胥为监操官,监督武建军操练。张、郑二人对武建军之训练较为严格,使武建军成为湖北新军中仅次于护军营的精锐之师。对武建军出征,张之洞、端方和袁世凯均寄予厚望,将之视为“鄂军出征发轫之始”[7]“湖北新军出省剿匪之始”[8]和检验新军成效的机会[9]。
在将武建军奏调来桂后,岑春煊又上奏清廷,以广西边防既关军务和外交,亦需预筹建造铁路事宜,边防大员“非能练兵、能交外而又明于铁路建筑之学者”不能胜任,极力保荐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请清廷“俯念广西边防关系重大”,对郑孝胥优加擢用,赏以三四品卿衔,责以专办广西边防事务,准其专折奏事。[10]得到允准。郑孝胥由此成为继苏元春之后的第二任广西边防督办,并获得专折奏事的权力。
郑孝胥率武建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抵达龙州,随即行边,周视防地,分布各处防守,留陆荣廷统领的“荣军”与武建军共同防边,使边防局势逐渐恢复稳定。鉴于广西边境地区“匪乱”严重,“民匪不分”,郑孝胥将“销匪安民”作为治边重心,主张治理“匪乱”重在收拾民心,“不能收拾民心,断不足肃清匪乱”[11],提出“守边之计,守之以兵,未若守之以民”的守边思想[12]。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开始,在军务和交涉之外,大力推行兴办车渡、开设银号、创办边防将弁学堂、添练武建新军、创设边防医院、设立学社、资助游学、开发地利等一系列新政举措,揭开了清末广西边境地区新政改革的序幕,成为近代广西边防建设史和边境地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后来,由于边饷筹解艰难,影响到边防新政的推行,加上郑孝胥并不甘于边防督办之任,因此坚持求去,最终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卸职,武建军亦于同年底被调离广西边境。
二、《函电存稿》的主要内容
《函电存稿》收录了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期间致各方的公文函牍676件(通),分为函电稿和公文稿两种,近7万字。原稿分为三册,均用“喜云楼”稿纸,第一册封面题“函电存稿,光绪癸卯十月”,共收函电稿286件(通),实际上所收函电稿时间并不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而是涵盖了自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册封面题“函电稿,光绪甲辰四月起”,共收函电稿297件(通),时间自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光绪三十年除夕;第三册封面题“公文稿,光绪甲辰六月”,共收公文稿93件(通),时间自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日至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三册封面均钤“钦命督办广西边防事务关防”之印。据《郑孝胥日记》所记,该关防系岑春煊派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带至连城,并于同月十六日代为奏请开用。[13]
这些函电稿和公文稿均是郑孝胥督办边防期间致岑春煊等人及外务部、广西派办政事处等有关机构的函电底稿和公文底稿。结合《郑孝胥日记》和《函电存稿》来看,郑孝胥在率武建军自广州前赴龙州途中即有不少函电发出,自抵达龙州后,与岑春煊等各方的函电往来更是频繁,几乎每日均有函电收发。孟森提及,他在龙州期间曾看到郑孝胥督办公幕中的“公私笺奏、函牍、批答高数尺,数十束”[14]。可见其数量之多。因此,目前留存和影印出版的《函电存稿》只是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期间函电稿、公文稿的一部分,属于残稿,所缺者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至十月二十四日前、光绪三十一年一月至九月之间的函电稿以及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至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日之间的公文稿。郑孝胥向来比较注重保存自己的资料,他在离边前夕的日记中有“检书及案卷”的记录。[15]据此推断,郑孝胥很可能在离任时将所有的函电底稿等带回了上海,这些残稿才得以保留至今。至于其中辗转散佚的情况,已不可考。
依据致函事由和函电内容性质的不同,函电稿又可以分为公函和私函。公函是为处理边防公务而发。私函则是郑孝胥致其亲朋好友的函件,内容不涉及边防事务,致函目的包括为他人请托求官、问询或答复情况、联络信息、联系感情等。这些函电稿大多语言简洁,意思明了,但在措辞方面比较讲究,其中不无客套,如对丁槐、易顺鼎、余诚格等人的函件抬头称呼多为“仁兄大人阁下”。这些反映出郑氏的文化修养和为人处世。
这批留存下来的函电稿有长有短,长的多至700余字,少的仅十余字,与便条无异。除少数函电稿收函人抬头、发函人署名、发函日期等要素不全外,大部分函电稿的基本要素都比较完整。每件函电稿基本都有明确的发函时间,有的以韵目代替,有的既署日期也有韵目。在这些函电稿中,有的属于密函,有少数函件属于公开函,有的属于急电,郑孝胥都注明为“一等急”,有的并未实际发出,则注明“未发”。其中的一些函件并不属于真正的信函,更接近于命令和告示,有的甚至是记事条文。
从目前留存的函电稿和公文稿来看,郑孝胥的致函对象比较广泛。其中,函电稿的致函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上司及各省督抚,包括岑春煊、柯逢时、李经羲、张之洞、端方、袁世凯、丁振铎、林绍年、陆元鼎、张人骏等人;第二,同僚好友,如岑春蓂、张元济、高而谦、高凤岐、张鸣岐、沈传义、李一琴、姚广顺等;第三,广西各级文武官员及边防随员,其中有广西提督丁槐、左江道余诚格、署太平府知府吴徵鳌、太平府知府潘泰谦,太平思顺道易顺鼎、谢汝钦,龙州厅同知何昭然、冯镜芳,代理明江厅同知黄清芬,武建军督带钟麟同、刘承恩,以及张得贵、陆荣廷、胡源初、周香谷、陈永年、周翰昭等人;第四,外务部、上海电报局、武昌善后局等机构;第五,法国驻越南总督、法国驻龙州领事、英国驻梧州领事、梧州关税务司等外国殖民机构及其代表。在众多的致函对象中,郑孝胥发给岑春煊、柯逢时、李经羲、余诚格、高而谦等人的函电居多。发函的原因和目的包括报告边情、请示、问询情况、答复来函、催解边饷、联络感情、商议问题、请求协助、发布命令等,内容涉及布防、治军、平乱、边防新政的推行、对外交涉、边饷之争等边防建设和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边防新政和边饷问题的函电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与函电稿相比,公文稿程式化明显,措辞更加郑重,其中一些属于训示、训令类的公文稿甚至用比较严肃的口吻。公文稿的致函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岑春煊、李经羲、端方、陆元鼎等督抚大员;第二,外务部、户部、兵部等中央机构;第三,广西派办政事处、湖北布政使司、湖北善后总局、广东布政使司、广东海防兼善后总局、龙州厅、龙州制造局等地方机构;第四,陆荣廷、符镇堃、冯镜芳等边防文武官吏和边防随员,这些是郑孝胥的下属;第五,广西学政汪贻书、驻日公使杨枢。其中,致岑春煊、李经羲、端方、陆元鼎、外务部、户部、兵部以及广西派办政事处、湖北布政使司、广东布政使司的函稿主要是为咨复边饷查收情况等事;发给龙州厅、龙州制造局以及陆荣廷等人的公文稿涉及委任边防随员和营哨军职、委派办事、训示、训令等;致汪贻书和杨枢的公文稿主要是为了咨送、派遣边地学生应考和赴日游学。此外,在公文稿中还有一些是为了编练新军、推广学社等事出示的布告。
按传递方式的不同,函电稿又可以分为实物函稿和电稿两种。实物函稿是指以实物形式传递的信稿,电稿是指通过电报系统传递的信函底稿。从总体上看,函电稿大部分都是通过电报系统发送的,甚至很多私函、密函也主要是通过电报转达的。这得益于当时广西边境地区电报网络的发达,使用电报较为方便、快捷。郑孝胥作为边防督办,拥有较普通官员更为优越的通讯手段。①中法战争前后,为适应军事需要,清政府在广西边境地区逐步建立起相对发达的电报网络。郑孝胥抵任后,将龙州电报线展接至督办行署,并设立报房,作为龙州行营报房。参见黄嘉谟:《清季的广西边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第75-78页。实物函稿的传递方式有多种,有的是差专人送达,有的是通过邮局代寄,有的是托人通过车渡传递。差专人送往的信函一般限于龙州及其附近的连城等处,如与易顺鼎、谢汝钦及边防随员陈永年等人之间的信函往来。通过邮局、车渡等传送的则为距离龙州较远的地区。
不同于函电稿,公文稿因其大部分内容系扎委、扎饬、咨会、咨复、咨送等事,需要有纸质函件为凭,必须以实物信函形式传递,因此基本都是通过人工传递的,有的是直接发到当事人手中,寄往外地的或交专人带去,或通过邮政挂号寄出,或是由驿站送出。
保存下来的《函电存稿》虽然篇幅不大,阅读起来却并非易事。由于这些函电稿和公文稿都是用比较潦草的行书、草书写成的,且常有增删、涂改之处,一些地方写得密密麻麻,许多字迹不易辨认,对阅读、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要完整准确的阅读、理解《函电存稿》,必须对照《郑孝胥日记》等相关史料,同时还要熟悉郑孝胥的交往圈和清末广西边防的状况。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等,对一般研究者来说甚是陌生,如果不熟悉郑孝胥的交往圈和清末广西边防的情况,恐怕不易得其真确。而且,函电中提及的人物通常是使用字号、别称、职衔等,其中不少并非历史上的显要角色,阅读者如果对相关人物及其字号等没有足够的了解,往往不易判别是何人。此外,一些语句还要通过前后字、句的对照和揣摩才能得其意思所在。
第一个对郑孝胥的这些函稿进行整理和利用的人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孟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抵达龙州,入郑孝胥之幕,同年九月随郑孝胥返沪。在此期间,他利用郑孝胥督办公署中的函电稿和公文稿等公私文献,并参以其个人的所见所闻,写成《广西边事旁记》一书,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严复为之作跋。该书系统的记述了清末广西边境地区的社会动乱和郑孝胥推行的治边举措,被视为孟森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但因其中将郑孝胥视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被认为对郑孝胥的政绩过于推崇,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学术界重视。
三、《函电存稿》的史料价值
孟森在《广西边事旁记·序目》中述及:“乙巳春,游郑太夷边防幕,暇取积牍消永日,见公私笺奏、函牍、批答高数尺,数十束,悉太夷笔,无一字假他人手,私叹其精力之绝。”[16]可知这些函电及公文底稿均系郑孝胥之手笔。《函电存稿》所涉人物、事件甚多,信息量大,其中不少内容都具有唯一性,对研究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和清末广西边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一)《函电存稿》是研究郑孝胥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督办广西边防是郑孝胥人生中的重要经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依据《郑孝胥日记》《广西边事旁记》的记载及相关档案,存在明显的局限。《函电存稿》保存了许多《郑孝胥日记》《广西边事旁记》失载的内容,提供了不少以往不为人知的细节,为研究督办广西边防时期的郑孝胥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首先,《函电存稿》为研究郑孝胥在督办广西边防期间的人际交往网络提供了鲜活的样本。这批函电存稿涉及到郑孝胥与当时许多人物的交往,包含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内幕,反映出当时特定的人际关系、沟通媒介和渠道,为研究郑孝胥与他人、各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
通过《函电存稿》可以明显看到,郑孝胥不仅刻意维系与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人的关系,也十分注意维持、发展与岑春蓂、余诚格、陆荣廷、高而谦、姚广顺、余大鸿等人的联系。这些人或为烜赫一时的督抚大吏,或为当时崭露头角的政治军事新星,其中有的虽不属要角,但在为郑孝胥传递信息、密切与各方要员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孝胥近乎处心积虑的与这些人保持联系,目的是为日后的提升和施展政治抱负积攒人脉资源和政治资本,这是其人际交往趋利性的体现。
在《函电存稿》中所涉及的人际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与岑春煊、端方之间的关系。郑孝胥舍旧主张之洞而投岑春煊,实欲凭借当时深得慈禧宠眷的岑春煊之力获得晋身之机。从郑孝胥入幕到督办广西边防之初,二人关系颇相契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边饷筹解受困和治乱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郑、岑之间渐生罅隙,郑孝胥因此萌生去意。而另一方面,他主动向端方亲近。《函电存稿》保存的郑孝胥致端方的函电稿共17件(通),虽然远不及致岑春煊之数,但其中半数以上为密电,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端方移节江苏、湖南,郑孝胥都发去密电道贺,甚至还为端方分析利弊、出谋划策:“闻我公移节长沙,不胜抃贺。收人心、振士气,在此一行。中国自强,尚有可望。较其力量而论,湘固胜于吴矣。”[17]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致端方的函电中,郑孝胥甚至直接表达了对岑春煊的不满。如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通密电中称:
桂憎边防,事事掣肘,粤亦不甚为力……督抚置边防于度外,必至偾事。奈何?祈呈宫保,并乞密示机宜为幸。[18]
在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一通密电中,郑孝胥将求去的真实原因告知端方,并再次表达了对岑春煊的不满:
南京端督帅钧鉴:骏。奉勘电,蒙垂教,极感动。胥患头眩失血,奏陈求去,电旨令岑、李保荐替人,岑、李奏请暂留,奉旨已允。胥现拟再奏恳辞。柳庆匪气尚炽,财政益窘,边防恐受其害。当事者不收民心,徒逞刻酷,驱民从匪,谏之不听。幸近边安靖,交涉顺手,今不亟退,将成坐困。谨密布。[19]
这些密电的内容,郑孝胥在日记中并无一字提及。从中不难看出,在督办边防后不久,郑孝胥对岑春煊已颇有微词,其在感情和政治态度上似乎更倾向于端方。这些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郑孝胥在“丁未政潮”之际于岑春煊与端方之间的游移与取舍。①关于郑孝胥在“丁未政潮”中的表现,学界多有论及。参见李君:《“丁未政潮”之际的郑孝胥》,《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第86—90页;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95—96页。
其次,《函电存稿》为了解郑孝胥在督办广西边防期间的思想情感、态度主张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督办广西边防期间,郑孝胥的心态和情绪复杂多变,大致经历了起初的志得意满、中间的惆怅失落,再到后期的心灰意冷。其中原因颇为复杂,除去边饷筹解艰难、与岑春煊关系的变化、个人主张不被采用等因素外,还与郑氏的自我期许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边防督办之任,不甘心以“边才”为一生收束。此间种种,虽可从《郑孝胥日记》中略得梗概,但远不如读《函电存稿》来得真实详尽、生动直观。《函电存稿》中的不少内容都流露出郑孝胥内心真实的情感。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姚广顺之函中所说:“弟到边以来,勉强支持,鄂军水土不服,终未敢使之深入剿匪,随时调护,且保声名而已,惟催饷极为费力,督抚皆不谙军务,尤昧边情,政府则阳聋不闻,但以苟安目前为计,真无可如何也。”[20]从中可以看出,郑孝胥对清政府漠视边事所表现出的忧虑和无奈。同日,他还致电高凤岐、高而谦:
边防单薄已极,不能增兵,已属冒险,若再行抽调,是弃边防也。强邻密接,岂同儿戏!明知柳变紧急,焦思累日,万万无从下手,惟有恳帅为胥设法卸去督办,仍归幕中佐商军务,实为万幸。[21]
此函中所论为“柳庆兵变”后岑春煊欲调“荣军”内援之事,从中可见郑氏之愤慨。而他在日记中只记道:“致二高曰:愿卸督办,仍归幕中,佐商军务。”[22]毫无愤慨之痕迹可寻。
督办边防期间,郑孝胥虽然身处边隅,但始终密切关注时事和国内政局的变动,其思想情感、情绪心态除受边防事务、人际关系等因素左右外,还与时局的变化相呼应。郑孝胥致各方的函电稿中,有不少提及其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尤其是在致端方、余诚格、姚广顺、余大鸿等人的私函中,郑孝胥更是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政见。如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姚广顺的电稿中即表达了对官场习气的厌恶:“弟素愤中国官场习气之重,自上至下,相率为伪,无实心办事、扫除习气之人。”[23]在同年除夕致余诚格的电稿中又对时事一番针砭:“时事日亟,而举朝皆以苟安为志,必不足以自存。即以边防而论,应办之事甚多,岂可但唱空城计而已乎?”[24]诸如此类,在《郑孝胥日记》等其他相关史料中往往无从得见。
在《函电存稿》中,还有不少论及平乱治边方面的内容,其中包含着郑孝胥与众不同的思想主张。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初六日致岑春煊的密电:
边军防地太散,分扎零星,在龙之营须策应各路,要在截断越匪与内匪交通之途。如逐匪至边,自当堵剿,调剿内地,力所不及。丁镇语虽稍夸,然筑砦实有明效。民气渐固,匪势自衰,尚不失为中策。若逐贼不已,所过残破,元气愈伤,永无撤兵之日,乃下策也。惟公裁之。[25]
此系针对岑春煊“欲调武建军剿内地之匪”的复电,从中可见郑氏注重培养民气、收拾民心的态度主张及其与岑春煊等人在治乱策略方面的差异。而在日记中,郑孝胥只录“如逐匪至边,自当堵剿,调剿内地,力所不及”一句。[26]两相比较,更可见《函电存稿》史料价值之高低。
再次,《函电存稿》为研究郑孝胥的治边举措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总体上看,郑孝胥的治边举措主要包括布防、治军、推行新政等三部分。其中,布防包括边军的换防、分防及其调整;治军包括严明军纪、整顿“荣军”、扶植团练、操演军队等;新政则涉及经济、军事、医疗、教育、民生等方面,对广西边防建设和边境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为其治边举措的核心内容,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关于这些内容,《郑孝胥日记》和《广西边事旁记》中虽然都有记录,但《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的内容比较零碎、简略,而《广西边事旁记》中的内容多属粗线条式的记述,不少仅点到为止,从中很难获得直观真切的观感,对于了解郑孝胥的治边举措仍有一定的局限。《函电存稿》虽系残稿,但保存了大量关于郑孝胥治边举措的内容,涉及到边防、治军、推行新政等各方面,其中有不少内容在《郑孝胥日记》和《广西边事旁记》中无法得见。通过这些内容,可以对郑孝胥的治边举措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此外,《函电存稿》还提供了郑孝胥办理对外交涉的生动案例。郑孝胥在清末以善办交涉著称。对外交涉是清末广西边防事务的重要内容,也是边防督办的主要职责之一。《函电存稿》中保存了一些关于对外交涉的内容,其中不乏经典案例,从中可以看到郑孝胥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对外交涉方面的思想主张、原则立场和风格手段。
在致岑春煊等人函电中,郑孝胥一再表明其办理对外交涉的态度和主张:“凡办交涉,必须耐烦,虽小事不肯将就,使彼有忌惮,不敢肆行要挟,庶国家权利可以常保。”[27]总的来看,其处理对外交涉以谨慎为根本原则,正如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致李经羲的电文中所说:“为边防计,惟以练新兵、慎交涉二端为要务耳。”[28]秉持“慎交涉”的处事原则,郑孝胥一方面与法国驻龙州代领事伯乐福等人保持着友好亲善的关系。《函电存稿》中有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命人登于河内法文报的告白底稿一通,内容系致谢伯乐福为武建军施治,极称伯乐福之德。[29]另有同月十六日致法国驻越南总督函稿一通,为得知伯乐福即将离任后向法越总督恳请将伯乐福再留一任。[30]此外,还有一则告白为光绪三十年三月因伯乐福辞任回国而发,其中极称伯氏之“公正热肠”,对其辞任深表惋惜。[31]这些函稿中的内容,在《郑孝胥日记》等其他文献中并不见踪迹。另一方面,郑孝胥严格约束边防员弁,避免与法方发生冲突,努力维持边境地区和平安静的局面。《函电存稿》中有一典例。光绪三十年四月,针对法方反映的“荣军”管带杨胜广“傲慢无礼”等情节,郑孝胥除命对汛官员向法方致歉外[32],还令陆荣廷严加申饬:
中国官弁毫不知讲究威仪礼节,不似上等人举动,致为彼族所笑,实乃国家之耻。即抄函并发明鄙意,通饬各营,以后须谨守礼节,如有贻笑外人者,即当禀请撤办。此事颇关体面,亦望速查复。[33]
这一电稿透露的信息表明郑孝胥颇为重视对外交往中的礼节,意在维护清政府的颜面和尊严。
同时,在办理边防交涉过程中,郑孝胥坚持地位平等、权利对等的原则,要求法方同等遵守中国法律和中越边界会巡制度等相关约定。例如,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八日,针对法国提出的免收双方人员入境费用及允许法国船只进入中国境内的请求,郑孝胥致电柯逢时提出:
向来华人入越境者,均由法领事给单收费,故胥于对汛出示,饬照彼例办理。凡法越人入我境内者,亦须给单收费。今彼既愿两国俱免此例,而求准法国船只经过中国河流,原无大碍。惟中国船只经过越南境内河流者,亦应一律办理。请外务部以此函复法使。如果允办,应由两国各派专员就龙州会议详细之章程,务使彼此有利无害,再由外部奏明核准。[34]
像这样的主张,若非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了解,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涉经验和外交素养,恐怕难以提出。对于此函,郑孝胥在日记中只录“法船入我境,我船亦入越境,宜两国派员就龙州会议详细章程,再由外部奏请核准”一节[35],从中无法感知其确切的主张。
对于法方违反两国约定、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行为,郑孝胥坚决反对和抵制,在交涉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捍卫清政府的主权和尊严。《函电存稿》中有若干这方面的案例。试举两例。其一见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二日致伯乐福的“交涉函第一号”:
遥启者,文案罗委员……出龙州教士柯君致阁下函及转致本督办一函……据来函称,上封村有牛只、杂物被兵抢夺等情。查敝军(武建军)号令最严,自到边以来,并无民间控告敝营兵勇强抢民物之事……来函所云有何证据?如果有良民被抢,自可来营控诉,本督办定必秉公查办。若系道路谣言,教士亦不宜听信虚词,代为传布,有害敝营声名。且本督办素无歧视民教之意见,从前幕中所用文案潘君、□君均奉天主教之人,众所共知……至柯君所称约束各属教民,自系教士应办之事。惟教民本是华民,即有犯法,教士只能劝诫,如劝诫不听,应由地方惩办,因教士只有传教之责任,并无治民之权故也。本督办办事,先求权限分明,贵教士柯君既有此好意,故亦尽心相告。[36]
此函内容涉及对法方在并无实在证据的情况下控诉武建军“抢掠”和插手干涉中国地方治理和司法事务的越权行为的回应,从中可见郑孝胥在处理对外交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有礼有节。
其二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越南高禄州官率人越境进入思陵土州抢掠之事。案发之后初次交涉,双方互相诘难,“语颇龃龉”。鉴于此,郑孝胥认为“凡办交涉之案,须有确证,空言诘责,彼必不认”,决定先令思陵土州查明实在证据,再向法方交涉。[37]后来,在地方官查明事实后,郑孝胥致函法国驻龙州代领事官伯乐福,要求法方予以惩办及赔偿,“以儆将来”。[38]经过郑孝胥的驳争,法方于次年四月将肇事高禄州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39]
(二)《函电存稿》是研究清末广西边防的重要史料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严重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清末广西边防的历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已不在少数。不过,既有的相关研究在时间和研究对象上偏重于中法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初苏元春在任期间主持进行的边防建设和光宣之交张鸣岐强化边防的计划和措施。①这方面的研究以黄嘉谟《清季的广西边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第29—104页)一文最具代表性。下文所提及的清末广西边防对象、边防制度、边防地位的演变,亦见该文。对于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的历史,近一二十年来虽然不时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面世,但从总体上看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纵观整个清末广西边防历史,郑孝胥督办期间正处于转型过渡时期。一方面,随着广西边防的主要对象由法人转向“股匪”和“聚匪”,边务重心也逐渐发生转移,“缉匪”与交涉成为边务重心,而边务交涉也由以军政交涉为主逐渐转为以民政交涉为主。《函电存稿》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从中可以窥见边务重心变化的迹象。郑孝胥在任期间,将“销匪安民”作为治边重心,大力推行边防新政等一系列治边举措,正是顺应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由于边饷筹解困难等原因,郑孝胥屡屡求去,甚至不惜以撤回武建军、销去边防督办差使等胁迫岑春煊、柯逢时、李经羲乃至清廷,并多次向岑、柯、李等人提出边防改章办法。岑春煊等人最终以边防督办难得替人而决定裁去名目,将边防事务改归边地巡道办理,统辖于巡抚,使广西边防制度为之一变,边防地位也随之下降——由清政府慎重决定的国家政策转变为广西地方性事务。《函电存稿》保存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相关的函电稿,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到边防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及郑孝胥在其中所起的推手作用。
《函电存稿》还为了解清末广西边防事务的运作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特设广西边防督办,以重边防,一切边防事务统归边防督办调度。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年间,苏元春、郑孝胥先后任该职,主导进行边防建设。由于史料的欠缺,学术界以往关于清末广西边防事务运作的研究,局限于中法战争后初期张之洞、李秉衡、苏元春等人对边防大计的经始上,缺乏对边防督办本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的成果呈现。《函电存稿》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函电存稿》是郑孝胥督办边防期间的活动记录,为考察清末广西边防督办的日常事务与生活世界、了解清末广西边防事务的日常运作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从总体上看,所有《函电存稿》的内容所展现的,是作为文化精英的郑孝胥如何利用其人际关系资源经营边防、改造边境地区落后面貌的动态图景,生动细致的展示了清末广西边防事务的日常运作实态。
同时,《函电存稿》中有相当部分函电稿和公文稿涉及边饷问题,有助于深化对边饷的来源、筹解、支配以及边饷之争等问题的认识,对于理解近代广西边防建设的窘况和清末新政在边疆地区的实践困境等问题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此外,《函电存稿》中包含了一些郑孝胥针对法国增兵等情形而致岑春煊等人的函电稿,内容包括禀告情形、请示和商议应对办法等,为了解清末边防危机的应对机制和应对实态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三)《函电存稿》为研究相关历史人物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补充资料
郑孝胥的致函对象广泛,涉及到不少各种人物。《函电存稿》对研究其中所涉及的相关历史人物也有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的致函对象中,郑孝胥发给岑春煊的函电最多,达到148件(通),占总数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函稿虽然不是岑春煊的来函,但其中不少直接透露出有关岑春煊的信息。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二十四日的一通电稿称:“广州督帅钧鉴:密。奉祃电,即遵谕查访。”[40]此中所提及的查访之事,郑孝胥在三月十六日致丁槐的电稿中提及:“督帅命胥查陈参将世林发饷事,须令算清再行赴邕。”[41]可知,岑春煊曾令郑孝胥密查苏元春部将陈世林发放兵饷之事。有的函电稿甚至直接转述岑春煊的电文内容,如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一日致余诚格的电稿云:“顷得督帅蒸电云,西善后局令边防径催协饷,实属冒昧,已严饬之,并电柯帅飞催各省等语。”[42]另外还有一些电稿可以从中反向间接推出岑春煊的态度,如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致岑春煊的一通电稿称:“梧州督帅钧鉴:洪。青电谨悉。英领事非特干预广生祥等一案,兼欲挈持商政,扰乱商业,似不可从。且经纪行商已代众商垫出全年经费,如不准其照章抽取,则该商吃亏太甚,亦不合公理。”[43]此函所论之事系茴油交涉一案,从中可知岑春煊本意欲与英领事妥协,令郑孝胥予以让步,草草了结。众多与岑春煊有关的函电稿,可与近年整理出版的《岑春煊集》对读、互相补充,对于编撰《岑春煊年谱长编》也是有益的参考资料。
对研究陆荣廷而言,《函电存稿》也是值得重视的史料。郑孝胥在任期间,正是陆荣廷势力壮大的关键时期。不过,囿于史料,以往学术界对此中详情知之甚少。《函电存稿》中有不少涉及陆荣廷及“荣军”的内容,为他处所无法得见,有助于丰富对陆荣廷及旧桂系兴起历史的认识。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柳庆兵变”后陆荣廷的应变举动为例。“柳庆兵变”后,广西全省震动,岑春煊苦于内地诸军不足倚赖,经与郑孝胥多番协商,决定抽调陆荣廷统率的“荣军”五营赴援,边防另募新兵填防。这为陆荣廷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在准备赴援的过程中,陆荣廷趁机提出要求。郑孝胥在七月二十二日致岑春煊的电稿中提及:“据陆荣廷称,八响毛瑟系有烟铝弹,恐难□效,务求再拨无烟枪一千枝方能得力。”[44]在补充枪械的请求得到批准后,陆荣廷又要求对内调“荣军”的组成进行调整。郑孝胥在七月二十八日致岑春煊的电稿中称:
据陆荣廷密禀,旧部有三营系由苏革提拔来,远出恐难驾驭,求赴武缘县募其乡里子弟两营,较形得力,此间则就旧部简选精锐三营,另在归顺募三营填防等语。查所禀尚属实情。陆,武缘人,故愿用其乡人。惟边防枪械不能带去,祈饬查明应发何枪,迅饬电示为盼。[45]
此后,陆荣廷又进一步提出将其亲信调出以编定新营。郑孝胥在八月十七日致岑春煊的电稿中提到:“据陆荣廷电称,武缘之勇尚未成营,须俟将驻边各营亲信员弁调出,派补营哨各□,方能编定成营。目下官弁未到,碍难拔队等情。”[46]这些函电稿的内容呈现出陆荣廷善于把握时机、不断扩充自身实力的鲜明形象。
综上所论,《函电存稿》内容丰富,多为《郑孝胥日记》《广西边事旁记》所缺载,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唯一性的特点,无论是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还是对于研究清末广西边防以及相关历史人物都是值得重视的史料。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利用这一珍贵的史料进行研究。